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docx
《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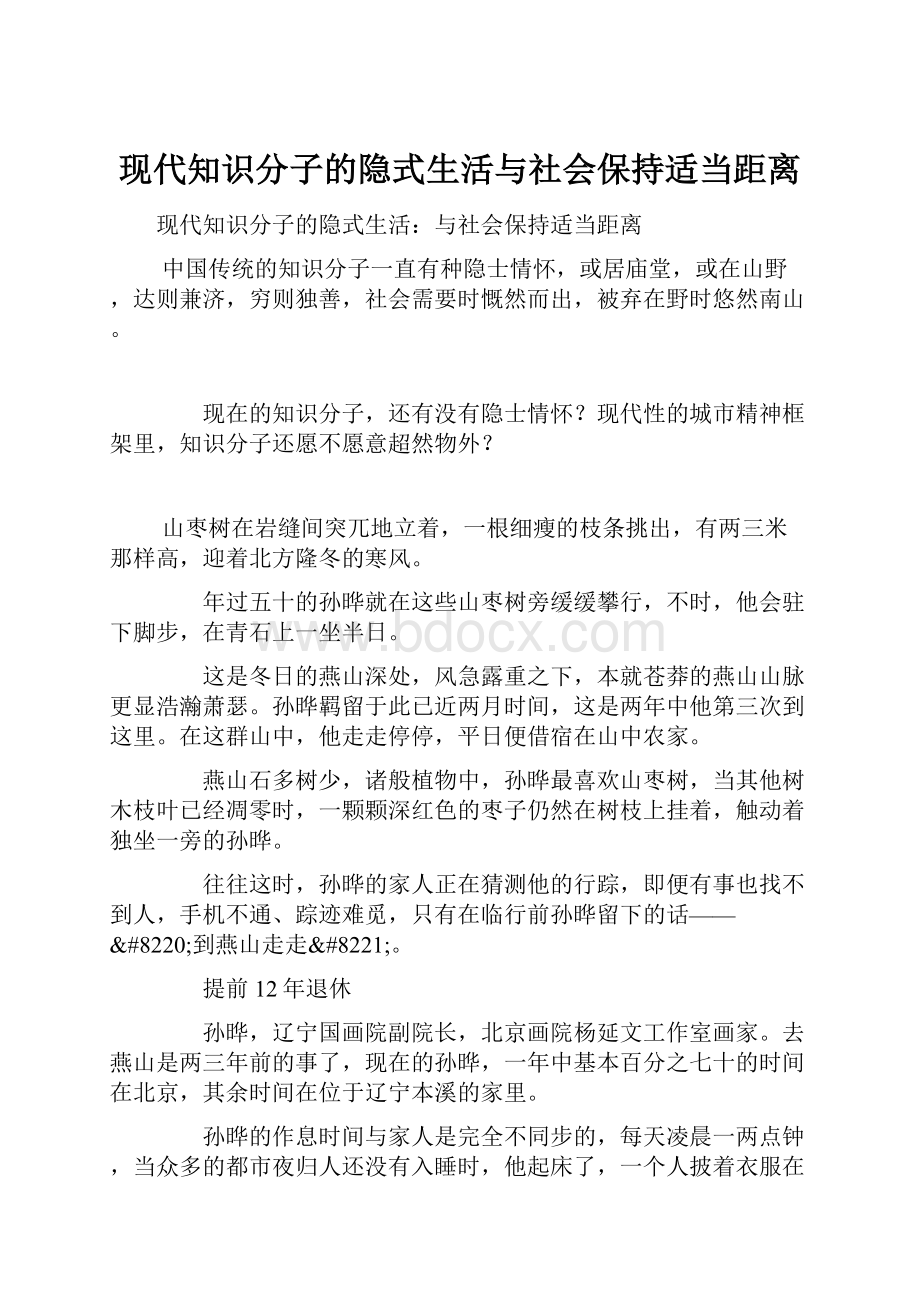
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
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
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种隐士情怀,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
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隐士情怀?
现代性的城市精神框架里,知识分子还愿不愿意超然物外?
山枣树在岩缝间突兀地立着,一根细瘦的枝条挑出,有两三米那样高,迎着北方隆冬的寒风。
年过五十的孙晔就在这些山枣树旁缓缓攀行,不时,他会驻下脚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这是冬日的燕山深处,风急露重之下,本就苍莽的燕山山脉更显浩瀚萧瑟。
孙晔羁留于此已近两月时间,这是两年中他第三次到这里。
在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农家。
燕山石多树少,诸般植物中,孙晔最喜欢山枣树,当其他树木枝叶已经凋零时,一颗颗深红色的枣子仍然在树枝上挂着,触动着独坐一旁的孙晔。
往往这时,孙晔的家人正在猜测他的行踪,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机不通、踪迹难觅,只有在临行前孙晔留下的话——“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孙晔,辽宁国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杨延文工作室画家。
去燕山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孙晔,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时间在位于辽宁本溪的家里。
孙晔的作息时间与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当众多的都市夜归人还没有入睡时,他起床了,一个人披着衣服在自己那宽阔的画室里作画。
临近日出时,孙晔会下楼,沿着小径漫步而行。
当已经有早行的人开始为上学、上班而奔忙时,孙晔悠然踱步而归,闭门休憩,如果上午没有朋友打扰,他会睡到午饭时分。
下午便在书房中读书至黄昏。
夜晚或与朋友小聚清谈、或者与家人度过,休息几小时后,又有新一天开始。
传统文人气质极浓的孙晔,即便是在没有退休之前,也过着一种半工作半“隐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钢文化艺术中心,孙晔兴之所至时经常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闭门写字画画。
有人敲门也不应,电话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在出差过程中,孙晔也常会“杳然消失”。
一次与同事路过苏州拙政园,忽遇大雨。
躲在亭子里的孙晔看着雨中竹林万千动态,看到了妙处,便让同事先行离开杭州,他则留了下来,每天醒来便到拙政园里看竹子,一连十余日,看遍了晴、阴、风、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终于了然为什么古人会有“宁可三日无餐,不可一日无竹”的情怀。
因为身兼数职,杂事繁多,孙晔1998年申请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时间早12年。
退休后不久,他便把位于市中心的三居室卖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买了一处居所,北临缓缓而流的太子河,书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这些年来,孙晔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在北京居住期间,也是住在远离市区的僻静居所,平日出门,常是一个人,夹着写生本,去处也都是野三坡、十渡这样的僻远所在。
而与朋友往来,孙晔也不擅作伪,与他相得的朋友年龄宽泛得很,时常相聚一处把酒言欢。
但对不喜欢的邀请,他也常常不加理会,实在躲不过,便离家远游,数月才归。
尽管亲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随时找到他,很难。
在他们眼里,孙晔,俨然是一个现代隐士。
我真的尽量幸福了
居于都市之中,而过着中国古代隐士般的生活,这在目前并非少数。
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及白领中屡见不鲜。
一方面,他们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同时,他们又会时常远离喧嚣,于独处中调整着自己的身心。
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精神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模糊影像。
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今天的中国“隐士”。
他们会阶段性地寻找一种缓慢的节奏或者投身自然与之亲近,以此来缓释平日积聚的压力与紧张的精神状态。
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他们会暂别平日的奔忙环境,或者远遁于乡下的居所,或者远足于异域他城。
即便身处家中,也会减少交际往来,使平日“为交际而交往,为赚钱而工作”的状态就此阻断。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生计与发展早已不是问题,关注的是如何不在激流勇进的漩涡中迷失自己,他们在积极参与社会前进进程的同时,尽力使自己保持一段可以审视他者与自我的距离,以此来保持自我的完整。
但与传统的隐士不同,他们隐与不隐与仕宦无关,隐于他们而言,更多时候,可能意义只在于生活方式。
通常他们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济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有隐的意愿和条件。
在杭州的姜含愫就是一个当下“隐者”,这个家在沈阳的姑娘一年前辞掉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于今年夏天跑到杭州西湖边上租了一处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为了学习做杭州菜,本无需打工便可悠闲度日的她,在杭州的一家报纸开了个美食专栏。
目的很明确,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杭州各大饭店品尝美食、请教厨艺。
而大多数时间里,姜含愫把时间花在了游西湖上。
每天中午出门,在西湖边上信步而行,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到傍晚才姗姗回家,发挥自己的厨艺。
有时,把脚走得磨出了水泡也浑然不觉。
对于西湖,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眷恋。
第一次来杭州是在2002年的“十一”,走在河舫街时,突然间就泪流满面了,她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于时她决定自己一定要在这里,在杭州边上,生活一段日子。
她这样对记者描述她心目中的杭州,“杭州在我心里一直是一朵桃花,是烙在我额头上的一个红印,因此我来了。
”
姜含愫说,尽管自己现在不工作,但在房地产行业有着丰富工作资历的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为如何赚钱而产生的焦虑,“好几年前我就觉得,我这生再也饿不着了!
呵呵。
”姜含愫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她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应该有一个可以围绕的原点,而在她的观察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原点是什么,有时“奋斗”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原点,但她怀疑这个原点的意义,“造福社会?
意义又在于什么呢,难道不是让大家更好的生活。
但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善待自己?
”
在杭州还要隐居多久,姜含愫说直到玩够为止,她有种感觉,觉得自己一定会在这里找到些什么——一个久已失落,但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找到了,她就会离开,也许就不离开了。
有趣的是,姜含愫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都欣赏她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的父母出于关心也会问女儿一些问题,“我是个有孝心的人,但他们能尊重我。
他们有时也问我幸福吗。
我说我幸福。
他们就放心了。
”
“而且我向上帝保证,我真的尽量幸福了。
”她笑着说。
北京北的北村
与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人不同,作家北村觉得自己的生活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没有相通之处。
北村认为,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多处于两极,要么是入庙堂,要么隐山林。
后者又多表现为放浪形骸、不拘小节。
北村对这两种都不喜欢,因为这两种精神下都不会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精神。
但北村始终喜欢一种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方式。
在福州居住期间,单位在市中心集资建房,他拒绝了,而是留在位于市郊的单位宿舍楼里。
2001年,北村来到北京,先是租房居住,所选之地也多靠于农村,经常早上起来,北村跟村民一起守在路边吃早点。
两年之后,北村决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但他选择了位于宋庄的画家村——一个比北京卫星城通州还要远的地方,并按照理想中的样式,准备给自己盖一栋二层的木屋。
结果北京的大风让这个盖了一半的木屋流产。
一笑置之的北村重盖了一个砖石的房子。
现在,北村搬到了北京北部居住,足不出户,就可以看见窗外的长城和群山。
对于他而言,在偏远处生活,可以强制自己收拢精神,从而让自己身处于一个沉思的环境里,面对的不是嘈杂的人群,而是河水、山川,“不是说与人接触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北村说。
在宋庄居住期间,北村的家里,曾经有两次有蛇爬入,这对北村和他的爱人无疑是不小的惊扰。
而且在他现在的居所附近,无论是购物还是就医都极为不便。
但这并不影响他生活方式的选择。
于此隐居的北村,与很多作家作息习惯不同。
他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的律动来调整自己的生活。
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跟爱人一起看看电视。
在北村的家里甚至没有安装电话,惟一与外界时刻联通的,就是电脑的宽带网络。
但他每天上网时间不会很久,在这个人们随时都会被“信息”冲击成碎片的时代,北村认为上网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无谓地浪费精神。
平时无事,北村也会开车到市内见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但社会上邀请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他一概拒绝了。
喜欢远离喧嚣的北村并不适应北方的天气,但他仍然选择留在北京。
这是因为北村觉得,在北京可以清晰而完整地看到城市的发展对人影响的过程。
尽管在福建也会有这种感知,但在程度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媒介传播所无法消弭的。
隐士,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符号,他土生土长,又与儒、道、释、法等传统文化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他并非是一个可以整齐划一的阶层或者群体,但从古至今,隐士都是具体而有所指,甚至在不同时期,人们大可以归纳出当时的隐士“领袖”。
通常而言,隐士指隐居不仕的读书人。
但对于隐士,人们最常联想到的是青松明月、山野林泉的野逸生活,孑孓独立、淡泊清静的高洁人格,以及不羁于流俗的独立性格。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隐士,几乎成了一个个性自由、有完整自我的代言。
但这种认识并不确切。
当社会上的外部压力足够强大时,就会有大量具有隐逸思想的人出现,为自己在精神层面开个天窗,成为一种对既有制度压迫、精神桎梏的反弹。
也因此,风清云淡的生活也只是中国隐士的一种表层现象,精神内里即便是一种沉静,也是诸多激荡后的沉淀。
正如《易》中所言:
“天地闭,贤人隐。
”又如孔子所言: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
南怀瑾先生于《隐士与历史文化》中也说到这一层,“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中,走隐士路线的人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而是非常关心,也许可以说关心得太过了,往往把自己站开了。
”
但站开了不是不管,而是在明知不可为时,不勉强去做,不会把儒家的硬砥中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正如南怀瑾先生多次提到的唐代“文中子”王通,在暴隋之时,王通便有志于天下,欲取而代之。
但考察一番之后,觉得事尚不可为,便回家培养年轻人。
至唐之开国,如李靖、房玄龄、魏徵等一干元勋多是他的学生,也算以此方式开创了唐代的三百年历史与文化。
于今,每当谈到隐士,人们多会在一种消极的语境中来审视。
但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隐逸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却并非如此单纯,“处江湖之远”者往往亦多有怀有庙堂之忧。
中国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至商周而显赫,伊尹、姜尚、伯夷、叔奇,至秦汉时的商山四皓、张子房,再汉以降的诸葛亮、陆机、谢安、陶渊明、陶弘景等,无一不是心怀时局之士。
这些人中,又多为经纬天下局势的历史关键人物。
但在崇尚“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中国,古代文人更多愿意从“德”之所立来看待历史上的贤人隐士,以此作为身处困厄时的一种心里安慰。
而对隐士现象中所反映的现世关怀,却少有注目。
这种功利性舍取的偏颇也是造成现世大家常把隐逸与消极相关联的原因之一。
《空谷幽兰:
寻访现代中国隐士》是近两年畅销的一本书,作者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比尔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隐居在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并试图对中国的隐逸文化及其传统进行梳理。
但可惜的是,按照他对中国古代隐士的既有认识——“隐士能够与天对话。
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
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
”——他找到的大部分只是也只能是一些出家人,比尔把这些修行者视为中国当代的隐士。
无疑,这发生了很大偏差。
且不说伊尹、姜尚、张子房以及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等人,即便是作为中国隐逸“掌门”的陶渊明也并非只有“采菊东篱”的静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在文学史上早已为人所知。
这里所说的并非是“大隐隐于市”的老话,而是应凸显中国隐逸传统中,隐士本身具有的个性完整与现世关怀。
如果以此为参照,那现存于中国的当代隐士绝不是比尔·波特在大陆所拜访到的那些修行者,也并非都处于名山大川中的寺庙庵堂。
他们的所在,往往就在中国快速前行的各个都市里,他们会不定期远离喧嚣亲近山野,但目光却从未离开过,这与山上不知魏晋的修行者是不同的。
就是以这种生活状态,北村一边在关注、体察着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现象、冲击与诱惑,一边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在远离市区、远离嘈杂的地方,过着悠然独立的隐居生活。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传席先生,把中国古代隐士分为十种。
完全归隐:
归于此类的隐士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他们与为仕而隐完全没有干系,即使有时机有环境有条件,甚至朝廷派人来多次延请,他们也拒不出仕,如晋宋间的宗炳、元代的吴镇等。
仕而后隐:
这种类型的隐士在中国古代很多,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
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其隐逸的名气甚至超过其诗名。
但陈传席认为在陶渊明归隐之后就变成“真隐”了。
半仕半隐:
此类人先是做官,但后来不愿做了,但辞官又无保于生计,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过着实际的隐居生活,虽然不具有隐士的名分,但却有隐逸思想,如唐之王维。
忽仕忽隐:
如元明之交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均是先做官,然后又隐居,待朝廷征召或形势有利,又复出仕,之后再归去。
陈传席先生评价这种人不果断,拖泥带水,并说王蒙创造了拖泥带水皴,董其昌的画用笔含糊不清,太暗而不明,就和他们的性格有关。
隐于庙堂:
这类隐士,虽然做官,但不执着于政事,陈传席评价之为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对国家危害最大。
似隐实假:
如明代隐士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家”。
名隐实官:
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然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
这种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以隐求仕:
通过隐逸来博得名声引起朝廷的关注,然后出仕,即所谓的“终南捷径”。
如唐代的卢藏用在考中进士后,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来果然以高士被聘,授官左拾遗,他曾对友人指着终南山说:
“此中大有嘉处。
”
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上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
这一批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
如殷商时伊尹、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是诸葛亮。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当今中国的“隐士”们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思想和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联?
他们在面对东方圣贤与西方哲人时,对自我是一种怎样的关照?
隐逸山林是否真就是消极遁世?
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我们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认识。
对此,我们采访了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黄玉顺先生。
中国新闻周刊:
你在什么地方“隐居”呢?
(记者笑问)
黄:
(笑)我还没有。
不过我有时也到朋友那里去玩,在他们乡下的居所。
但现在确实有不少大学教师的生活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艺术学院的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喜欢到郊外、到乡下去搞创作,或者与朋友们相聚。
其实不只是高校教师,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倾向。
比如说大都市里的白领阶层,也非常典型,你会发现:
他们在八小时之内,会规规矩矩地在现代性社会架构下谋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在八小时之外,他们追求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的“隐士”们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有无相通之处?
黄:
有同有异。
跟中国古代的隐士相比,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是对现行的社会架构的一种回避、拒斥、甚至反抗。
其实不只是中国如此,西方国家也是这样。
现代的“隐士”们普遍具有一种“后现代”的色彩——自我放逐。
20世纪以来,东西方的知识分子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
现代性体现在诸多方面,而表现为一种社会架构,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人们生活在其中,会觉得非常辛苦、冷酷,感受到一种压迫感,于是产生逃避、甚至反抗的反应。
在思想界,这会产生一种反思;而在个体身上,则会产生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
这与古代的、比如魏晋时代的隐者是相似的,都是对现存的某种社会架构的一种拒绝和抵制。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古今存在着相通性。
但我们要认识到的是,这毕竟是不同的时代。
现在这些“隐者”,这些具有“后现代”自我放逐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古代的隐者、比如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人物是不同的:
一个是面对的现代性的架构,一个是面对的前现代的架构。
中国新闻周刊:
那么,你认为现在这种“隐士”现象是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不是缘于中国古代的隐士传统?
黄:
不是这么简单。
一方面,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思想观念本身是在生活方式中产生的。
比如今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要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状况”作一个严格的区分:
后现代状况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在这个生存方式中才产生了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
一切都是生活本身给出的。
比如魏晋玄学时代,那些玄学家们有一种隐士倾向,他们对当时的社会架构保持着一种回避、不合作的态度,这是由他们的生活境遇决定的,他们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非常险恶。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样一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但我们的社会架构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比如大家现在觉得每天都非常累,人与人之间非常冷漠,精神上空虚、甚至很痛苦等等。
这些是现代性的一种普遍问题,东西方皆然,是由生活方式造成的情绪。
但另外一方面,这种生活方式既是现代性的,同时也是民族性的。
因此,当今“隐士”现象也与中国古代隐士传统有关。
但我想说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不论是古代的隐者,还是今天的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知识分子,你会发现,所有那些具有最典型、最强烈的自我放逐倾向的人,往往都是在当时既有社会架构下生存得最成功的人,他们恰恰是完全依赖于这种既有制度而生活的。
举例来说,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法国,那些思想家都是教授,他们恰恰依赖现代性的制度而生存。
现在一些年轻人、“新新人类”之类,他们有一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但他们都是依靠父母辈在现代性制度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来维持他们那种很“后现代”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有一个基本结论:
后现代状况只是现代性状况的一种必然的伴生现象,而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态度其实也只是现代性观念的一种补充。
选择后现代生存方式的人——当今的隐士,实际上都是依赖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社会架构而生存的。
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大自然,常会与它亲近,但我们绝不会在大自然里去谋生、去生存,而总是急急忙忙地赶回大都市来。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中国今天的选择问题。
比如说,现代化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任务,但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就已经开始出现质疑现代化的声音了,这可能会带来某种危险。
中国新闻周刊:
但中国当今的“隐士”在寄情于山水中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还是陶渊明、李白等人,而不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
黄:
在如我刚才所说,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不分东西的,而是由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之中,在生活中、在观念上积淀了丰富的民族性的东西。
法国人当然不会想到陶渊明,但我就会。
比如,我是搞哲学的,那么,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是生活所给予的,在我的意识层面,既会呈现出一些西方后现代思想家的形象,也会呈现出陶渊明等古代隐者的形象,而他们会融合起来。
而且,说到当今的“隐士”,你会发现,这种现象与影视中流行古装戏有着有趣的联系,就是当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求一种东西,那就是:
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古装戏所写的其实都是现代人,但那是一种民族性表达。
“隐士”这种意识方式也是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种需要,也是对现代性生活的一种补充,尽管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补充会一直存在下去吗?
黄:
我觉得会一直存在下去的。
任何时候,人都需要在一种社会架构下生存发展;但同时,我们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排斥情绪。
一个美国未来学家曾说过类似的话,他把在现代性“高技术”架构之外的精神上的追求叫做“高情感”,他说,“高情感”是“高技术”的伴生物,在“高技术”下生存的人一定会有“高情感”。
中国新闻周刊:
这种有着“高情感”的当今“隐士”们会对既有的社会架构有影响吗?
黄:
他们当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现代性的社会架构。
这是他们无能为力的。
但也会有作用。
比如20世纪对现代性的反思,就导致了在各个层面上对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些修补、修正,使它更加“人性化”。
所以,如果让我来评价后现代主义,我会这样说:
那只是现代性社会架构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是现代性的一种自我诊断、自我修正机制,而不能把它看作是现代性的对立面。
对于当今中国的“隐士”的评价,也是相似的。
在这个意义上,“隐士”思想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