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讲座9.docx
《现代诗歌讲座9.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现代诗歌讲座9.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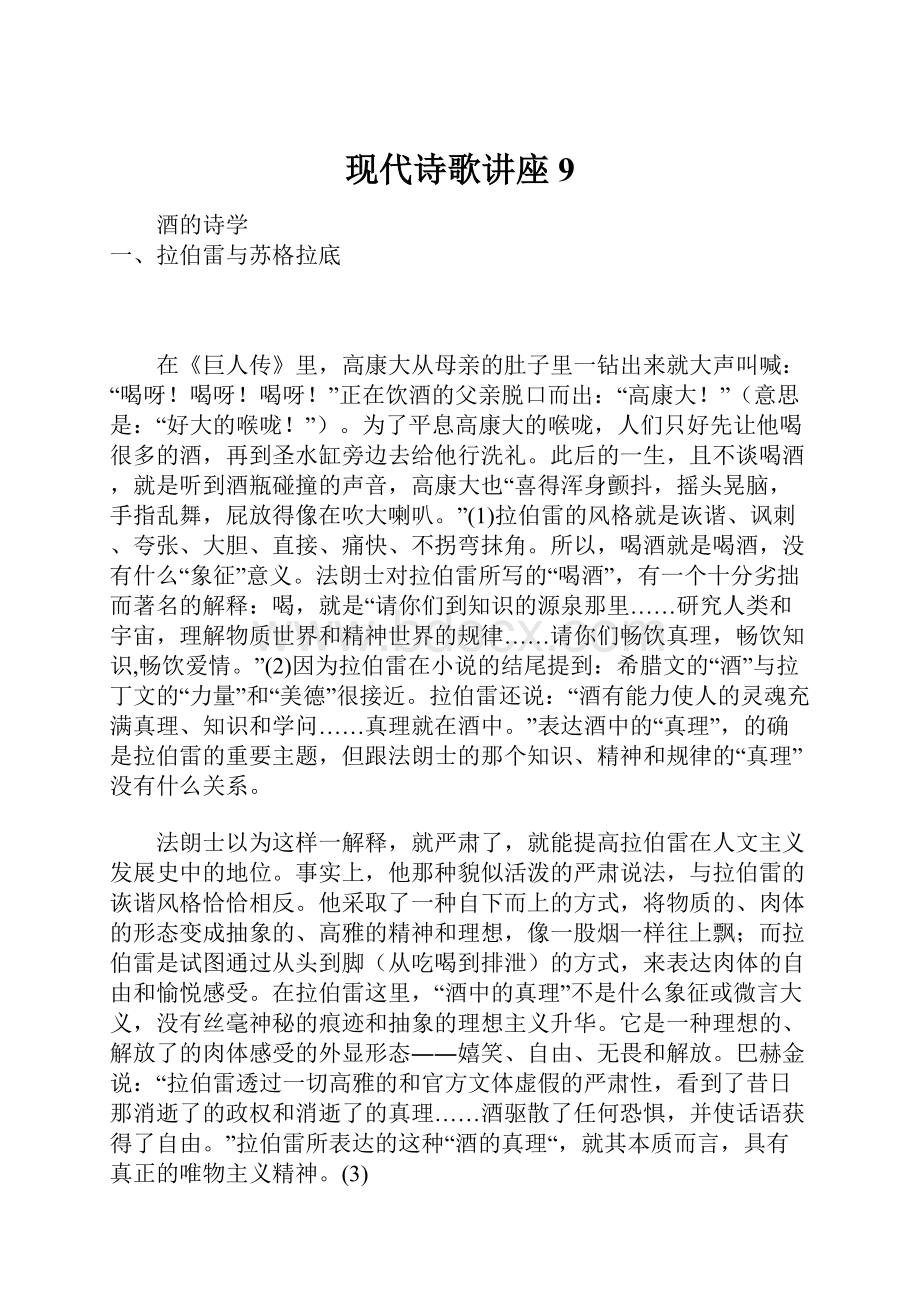
现代诗歌讲座9
酒的诗学
一、拉伯雷与苏格拉底
在《巨人传》里,高康大从母亲的肚子里一钻出来就大声叫喊:
“喝呀!
喝呀!
喝呀!
”正在饮酒的父亲脱口而出:
“高康大!
”(意思是:
“好大的喉咙!
”)。
为了平息高康大的喉咙,人们只好先让他喝很多的酒,再到圣水缸旁边去给他行洗礼。
此后的一生,且不谈喝酒,就是听到酒瓶碰撞的声音,高康大也“喜得浑身颤抖,摇头晃脑,手指乱舞,屁放得像在吹大喇叭。
”
(1)拉伯雷的风格就是诙谐、讽刺、夸张、大胆、直接、痛快、不拐弯抹角。
所以,喝酒就是喝酒,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法朗士对拉伯雷所写的“喝酒”,有一个十分劣拙而著名的解释:
喝,就是“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请你们畅饮真理,畅饮知识,畅饮爱情。
”
(2)因为拉伯雷在小说的结尾提到:
希腊文的“酒”与拉丁文的“力量”和“美德”很接近。
拉伯雷还说:
“酒有能力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真理就在酒中。
”表达酒中的“真理”,的确是拉伯雷的重要主题,但跟法朗士的那个知识、精神和规律的“真理”没有什么关系。
法朗士以为这样一解释,就严肃了,就能提高拉伯雷在人文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
事实上,他那种貌似活泼的严肃说法,与拉伯雷的诙谐风格恰恰相反。
他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将物质的、肉体的形态变成抽象的、高雅的精神和理想,像一股烟一样往上飘;而拉伯雷是试图通过从头到脚(从吃喝到排泄)的方式,来表达肉体的自由和愉悦感受。
在拉伯雷这里,“酒中的真理”不是什么象征或微言大义,没有丝毫神秘的痕迹和抽象的理想主义升华。
它是一种理想的、解放了的肉体感受的外显形态――嬉笑、自由、无畏和解放。
巴赫金说:
“拉伯雷透过一切高雅的和官方文体虚假的严肃性,看到了昔日那消逝了的政权和消逝了的真理……酒驱散了任何恐惧,并使话语获得了自由。
”拉伯雷所表达的这种“酒的真理“,就其本质而言,具有真正的唯物主义精神。
(3)
要理解拉伯雷德“酒的真理”,就必须将话语自由、驱散恐惧、唯物主义这三个要素综合在一起考虑。
话语自由不是饶舌和聒噪。
饶舌和聒噪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行为,他常常受阻于权力和威严。
也就是说,他还有畏惧。
当它与无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可能变成所谓的雄辩,或者强词夺理了。
因为无畏在这里是一种意志力的结果。
意志力是没有物质边界的,它随时都有可能崩溃,乃至最终改变意志的方向(“叛徒”因此而产生)。
唯物主义的要素克服了意志力的虚假、暧昧和盲目。
通过酒的特殊能力,将话语自由、无畏精神变成了一种肉体特征。
这种特征不仅是权力、威严、暴力、等级秩序的克星,也是具有解放和自由嬉戏性质的肉体狂欢。
酒水往下流,在胃里变成了火而燃烧起来,并穿透和瓦解了世俗肉体的边界,产生一种反时间的飘然感。
此刻的饮酒者既在群体之中感受着普天同庆,又好像是独处在自己的肉体之中。
他们狂饮但不贪婪。
带有庸俗唯物主义的利己性和养生学在这里没有市场。
温和的外表包裹着体内的暴力,粗暴的语言掩饰着柔肠。
自由的饮酒既不是纯粹的否定性(如自杀式的酗酒),也不是纯粹的肯定性(如暴食暴饮的口腹之乐)。
哭泣不是厌恶生活,而恰恰是对生活热爱的一种独有方式。
拉伯雷认为,只有在喝酒的时候,才能说出最有逻辑、最自由和坦诚的真理。
拉伯雷描述的是一种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中的理想状态的可能性。
他之所以在文学史上变得具有特殊意义,就是因为他在一个独特的背景上将世俗变成了理想,将理想变成了世俗。
就饮酒而言,拉伯雷的世俗方式既拒绝以往的神的气息,也批判后来的资产阶级的趣味。
他用唯物主义来对抗神学,用集体性来反对资产阶级卧室的日常生活。
文艺复兴的原本含义,就是恢复对古代世界(古希腊)的兴趣。
(4)事实上他们碰到的最大难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生活之中的:
要过积极活跃的生活还是沉思默想的生活?
屈从于神和命运的力量还是张扬人的力量和美德?
(5)毫无疑问,古希腊人既善于生活,又善于思考。
将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中介是什么呢?
这就是尼采所说的希腊文明中的酒神精神。
酒神不是梦,而是“醉”,它将复活与死亡、自己与他人、理性与感性、男性与女性、生活和理想在当下生活中、在酒的真理与逻辑中重新统一起来。
正像拉伯雷说的,在酒的状态下才能产生真正的逻辑和真理。
所以,在古希腊,辩论真理,讨论爱、美、死这样一些抽象问题的聚会称为“会饮”,相会在一起饮。
苏格拉底很能饮,三斤装的杯子(大概像今天装扎啤的大玻璃杯),一口一杯,没有人见过他喝醉。
但他一般不贪杯,只有在文人“会饮”,并碰上儒雅能辩的对手时,才会开怀畅饮。
拉伯雷所描写的狂饮,表面上有点类似古希腊人的饮,实际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喝呀!
喝呀!
喝呀!
”,高康大一生下来就喝,没有任何借口和禁忌。
古希腊人一般都是在酒神节祭祀狄奥尼索斯时狂饮。
后来祭祀成了狂饮的一个借口。
同时,古希腊人的饮酒中还带有理性的成份。
比如在“会饮”的时候主张不要喝得太过头了,讲究节制,反对喝色雷斯出产的纯烧酒,而是在烧酒中按 1/3或1/2的比例兑水。
这种代表“日神精神”的僵死形式,颇有资产阶级养生学的味道。
饮酒的过程常常伴随着对天命或神的虔敬。
“苏格拉底入了座……举杯敬了神,唱了敬神的歌,举行了其他例有的仪式,于是就开始喝酒。
”(6)在会饮中,开始喝酒就是开始说话,酒和话语生产合而为一。
拉伯雷抛弃了对神的虔敬和对理性的依附,将饮酒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生命体验。
他对古典精神的创造性发挥和继承,最起码在尼采之前,并没有真正被人理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没有理解酒或酒神精神的“悖谬性”。
人们将酒这种既冷又热、既是水又是火、既形而下又形而上、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既晕眩又清醒的东西,用二元论的思维割裂开来了。
当庸俗唯物主义占了上风的时候,那种普天同庆、众人狂欢、体现自由和解放精神的集体饮酒,几乎要完全沦为一种与养生相关的、资产阶级精明计算(他们在客厅或书房里独自斟酌品味,脑子里想着交换的计谋),或小农式的找各种借口凑在一起(常常是敲竹杠子)的饕餮和放纵了。
必须注意的是,在近代个人主义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还产生了一种“独饮”的特殊方式(它总是伴随着个人的孤独、绝望和自杀情绪)。
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
二、晏饮中的阴谋
只有在一个天真的民族里,才有可能实现拉伯雷所说的那样一种普天同庆式的酒的精神。
让我们暂且将拉伯雷所说的“酒的真理”当作一个理想。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还有更多的关于酒的真理与荒谬需要分析。
我们发现,在东方民族的历史文献中,很少看到有关集体性狂饮的记载。
印度的《摩奴法典》、波斯的《卡布斯教诲录》、中国的《礼记》等书,都有关于禁饮或节饮的规定。
在印度,摩苏酒是神梵天的饮料,一般人是不能喝的。
《摩奴法典》规定,醉汉要受到前额刺字的惩罚,妇女酗酒被视如麻风病,可以休掉。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集体狂饮。
印度人狂欢的方式是跳舞,而不是吃喝。
中国(文献中)的“社日”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放纵的机会。
《荆楚岁时记》记载:
“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
”也就是说,在社日的时候,要先让神喝个够,然后才能分享。
唐代诗人王驾的《社日》一诗中写到: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在社神的残羹剩饭面前,人人都可以醉。
社日尽管是一个祭祀的节日,但它依然是一个可以任意饮酒、带有狂欢色彩的节日。
这个节日消亡的确切年代已经无从考证了。
今天,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些伪节日,一些为权势立碑的、邀功请赏的、给结党营私以籍口的伪节日。
伪节日在形态上与节日相似,也有吃喝玩乐,但它不过是某种外在权威的点缀物。
并且,这种点缀与真正的祭祀性节日不同,它不是对超念事物的顶礼膜拜,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臣服。
剩下还有两种性质的集体饮酒,第一种是工作性的饮。
这种集体性饮酒给人的印象,常常像是一个阴谋。
“杯酒释兵权”,一手端酒杯,一手按着刀剑,先狂饮几杯壮壮胆,只等头儿将酒杯往地上一摔(还常常伴随着一声咳嗽,或者使个眼色),便动手铲除异己。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的战例,打败的一方也常常是因酒败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一章,也是一个中国式饮酒阴谋的例子。
这种饮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官场、商场,它以各种形态的变体出现。
另一种是民间性的饮酒,主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
它的典型表现形式就是斗酒。
斗酒不是工作中的宏观权力斗争,而是日常生活里的微观权力较量。
在一个诙谐、幽默没有地位的文化中,“严肃”(儒雅当然更好)就是一种最大的资本,要想有所作为,就得先学会“严肃”,学得好的常常被列为干部考核对象。
当你将另一个人的“严肃”毁掉,那就是将那个人的资本毁掉了。
斗酒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为什么要斗呢?
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很警惕、不会随便喝;不要说大官,就连一个获得了一点小地位的文人墨客,也不会随便喝的(不包括天生不喝的少数男人和大多数女人),所以,斗酒是十分必要的形式。
斗不是硬碰硬地拼,那是李逵式的笨方法,而是耍花招、耍嘴皮(比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一点点”,“先干为敬”、“兄弟兄弟”之类的鬼话)。
至于猜拳、行酒令、玩骰子等,都是一些能整对方、占便宜的辅助方法(规则是赢者不喝输者喝)。
如果斗酒没有什么外在目的,仅仅是为斗酒而斗酒,那又另当别论,可以将它归入遭批评的“酒徒”行列。
在公开场合随便饮酒,不警惕,甚至不加节制,进而“失态”,就是将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别人,轻则遭人耻笑,重则遭人暗算(就像孙二娘那样)。
所以,中国很少有随便狂饮的人了,或者说这种人越来越少了,我甚至想说刘姥姥就是最后一位。
在凤姐的阴谋策划下,她们用比赛吟诗这种刘姥姥不擅长的,而不是用比力气的方式,将刘姥姥灌醉,使她在大观园里出尽了丑,成了众姐妹和丫环的笑柄。
好在她自认庄户人家,“现成的本色”,并不在乎。
如果她在乎,就不是民间的村野老妇,而是大观园里的“老祖宗”了。
当我们回头看看拉伯雷笔下的饮酒、古希腊酒神节和消亡了的中国古代春社节的饮酒就可以发现,中国的集体性饮酒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阴谋。
它与其说是一个诗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学(权与谋)问题,最多也只能是一个诗学的边缘问题。
“边缘”的意思是,它只作为“酒的诗学”的对立因素出现。
在这个边缘,酒的功能并没有将他们引向生命自由的本质,更没有对解放的希冀,甚至连迷途的感伤、悲痛、孤独、逃避、自虐都没有,而是沉湎于历史和现实的中途胡搅蛮缠。
这种胡搅蛮缠者,比纯粹地、独自一人地沉湎于酒肉的酒徒更可怕。
西门庆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他不仅仅沉湎于私人生活的酒色,而是深谙中国式的集体性饮酒阴谋。
他不只是懂得酒色,更懂得官场和商场。
三、中古的酒和魏晋风度
拉伯雷在文学史中奇峰突起,他的文体是普天同庆式狂欢的酒神精神在真正的尘世生活中的回声。
他笔下的人物借助于酒的力量,让自由和解放的火苗在肉体中燃烧起来,照彻了权威及其秩序的阴暗角落。
这就是他最高的“酒的真理”和酒的诗学。
但是,这不过是透过尘世浓密乌云的一点星光。
当尘世中的集体欢饮变成了一场场阴谋,当酒宴变成了权势的恩赐的时候,对觉醒者而言,随之而来的就是“独饮”。
如果说,“酒的阴谋”与“酒的诗学”背道而驰,那么“独饮的诗学”就是对“酒的阴谋”的逃避,甚至批判。
最早的独饮者当然一些有头脑且敏感的人,比如是文人,“独饮的诗学”几乎就是文人的专利。
但是,“独饮的诗学”同样是一个歧义丛生的话题。
从酒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看,“独饮”代表了近代文化,它在古代不过是个案。
之所以说“个案”,是因为它在一种非“独饮”文化环境中独饮,因此,它常常与逃避、独异、狂放、高傲这些词汇相关联。
这种“个案”的典型代表,就是魏晋的“竹林七贤”。
关于“竹林七贤”的思想、诗歌、文章与酒的关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中、王瑶在《文人与酒》一文中都有论述。
鲁迅的文章明晰精辟,王瑶的文章严密详尽。
我只想从一个当代读者的角度发表一些意见。
鲁迅用“近代文学眼光”来评价魏晋时代的文学,说它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7)对此,鲁迅尽管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但看得出他是很赞赏的。
作为一个近代文学的概念,“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密切相关。
衡量“人的自觉”与否,不能仅仅看他是否看透了历史和现实,是否发现了生命的短暂、时光的易逝,有这种眼光的人任何时代都有,就像酗酒者任何时代都有一样。
“人的自觉”首先是个人有一种理性地把握生命本质的愿望,同时,对生命外围的环境也有清晰的了解(像牛顿那样),而不是将自己所处的世界看成神秘无比的东西。
其次,要求人的成熟,脱离康德所说的“不成熟状态”(8),因此能对自己的行为有选择能力(充分发挥个人的潜在能力和创造性);对行为的后果,尤其是悲剧性后果具有承受的能力和承担的勇气。
西方近代以来就是在努力追求这样一种成熟的成人文化。
中国的情况有些特别,这是一种熟透了的老年文化:
神秘、智慧、任性。
这些特点正是“竹林七贤”的酒与文章中所包含的主要特征。
竹林七贤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神秘的世界。
这个神秘世界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神秘主义,而是老庄的道家神秘主义。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中的肉体是一个牢笼(就像陶渊明所说的“心为形役”),不能与神秘的、超越的自然和宇宙相契合。
“饮酒正是他们求得一个超越境界的实践。
”饮酒能达到“与造化同体的近乎游仙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一种物我冥合的境界,而绝不是一种知识。
”(9)只有神秘的东西才不可捉摸,不可把握,因而就不会速朽,甚至可能成仙。
竹林饮酒派“成仙”的愿望与何晏的“服药派”相比,显得更为隐蔽。
他们充分利用了酒这种物质的现实主义性格特点(在最小的体积中蕴藏着最大的能量),从而达到“增加生命的密度”(10)的享乐效果。
这是魏晋文人和“竹林七贤”放浪形骸的任达、终日沉湎的饮酒的物质基础。
所以,这种饮酒的根本目的,还是属于养生学的范畴。
如果说由享乐到对生命与自然的神秘性合一的向往,构成了他们饮酒中的人生态度,那么,他们的社会批判态度则是由任达、放浪等要素构成的对社会的疏离、逃避。
在鲁迅和王瑶的文章中,都详尽地论证了“竹林七贤”的饮酒是为了避祸。
在黑暗的现实面前,“最好的办法是自己来布置一层烟幕,一层保护色的烟幕。
于是终日酣畅,不问世事了;于是出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了。
”(11)“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借醉得到人的原谅。
”(12)从鲁迅谈到有关嵇康阮籍教育子女的材料来看,他们真是清醒和智慧到了极点。
他们的任性、狂放,同样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在此不再详论。
王瑶认为,他们沉湎于酒的背后,“有忧患的心境作背景,内心是很苦的。
”(13)这或许是真的。
但是,这种智慧的形式,既跟人和文的自觉没有关系,更与真正的酒的精神、酒的诗学没有关系。
竹林七贤的饮酒,不是什么“酒的诗学”问题,但他们提供了一种在文化压抑之下产生的畸型的诗学外围材料。
看来“独饮”同样也可以沦为一种阴谋(或者叫计谋、智慧)。
也就是说,饮酒并不一定就是将弱点暴露在别人面前,徉醉恰恰是掩盖弱点、自我保护的办法,尤其是在强权面前。
酒在这里,不但不会促使话语的生产,反而使人缄默无语,进入一种死寂的境界。
至于嵇康、阮籍等人的个人行为,他们躲避灾祸的方法,我们没有权力说三道四。
但是,当他们成了一种诗学的典范,并且一直被人供奉到今天,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了。
狂放、任达的行为,在今天常常成了一些人放弃批判精神、不负责任的借口。
这种行为方式与拉伯雷笔下的人相比,就过于世故、精明;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相比,它就属于康德所说的“人的不成熟状态”,或者说成熟得过了头,老人心态就像儿童心态一样。
陶渊明的确是将竹林七贤的饮酒生活转变成了酒的诗歌。
但他只是留给我们一种逃避的籍口。
当有人试图自欺欺人地要解甲归田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他。
四、革命与燃烧的酒
魏晋名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名声很大,大概属于贵族阶层,曹操和司马懿要治他们都得找个借口。
他们与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属于上层社会内部的矛盾。
饮酒,一方面是这种矛盾的体现方式;另一方面,依然是竹林名士们高贵身份的标志,就像何晏那些“正始名士”的服药同样能表示高贵身份一样。
通过晕眩而放弃时间感从而达到避祸的目的,通过麻醉消磨了个人意志从而缄默,通过豪饮和狂放强化了作为等级的身份,矛盾和批判就这样“诗化”和神秘化了。
因此,竹林名士的“酒”,与其说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自我意识的消解。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就很难将它视为“人的觉醒”或“文学的觉醒”了。
西方的文艺复兴之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迅速地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对于富人来说,“会饮”和清谈已经不能标明他们的高贵身份了。
有产和有闲阶级有大量的闲暇从事社交活动:
化妆舞会、郊猎、剧院包厢里的交谈,等等。
而狂饮可能恰恰是下等人身份的标志。
伦敦的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六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没有闲暇和消遣。
晚上用蜡烛照明都被认为是一种奢侈。
“饮酒几乎是18世纪工人阶级的唯一消遣。
”(饮廉价的杜松子酒)(14)这种饮酒当然也是一种麻醉和乐趣,因为只有酒才能将自己从自卑和压抑中解放出来,从而也避免了犯罪。
到19世纪,酒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火,在劳动的无产者肉体中燃烧起来了。
左拉在《小酒店》中对此有过详尽的描写,并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呼吁:
关闭小酒店、反对酗酒、让在酒中堕落的人受教育、增加工资等等。
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巴黎的酒和下等小酒馆,他写道:
(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可疑的人……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流浪汉之流的人。
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流浪汉……不是放弃自己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
他们)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他们)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放荡者。
在秘密会议上像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谋家,突然温和起来,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老主顾。
(15)
酒的意象在19世纪曾经是一个与无产者和革命相关的意象:
贫困、居无定所、流浪、密谋、为街垒战而寻找同志。
但总的来说,它变成了类似炮弹一样的工具,成了一种壮胆的饮料。
酒的物质本性的暧昧性,决定了酒的意象的暧昧性。
巴什拉尔说,酒既是水,又是火,是液体之火,是燃烧的水。
(16)无产阶级密谋家就是充分利用酒中火的性质,将革命暴力变成一种饮酒式的狂欢。
马克思紧接着就批评他们“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监狱里就像在小酒馆里一样、追求令人惊奇的感觉、寻求“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
”
密谋家坐在小酒馆的角落里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貌似“独饮”,实际上是在为“集体狂饮”做铺垫。
这种狂饮当然不是拉伯雷式的自由和解放,而是要将酒之火变成街垒战中的燃烧弹,并试图将解放和自由精神变成可以立即兑换的支票。
他们要从酒中获取自由和解放的能量,他们消耗了酒,也获得了能量,但没有自由和解放。
根据酒的现实主义性格,热能转变成了动能(暴力)。
酒没有使语言生成,而是动作的催化剂。
结果很清楚,通过新的资本重组,形成新等级和特权。
酒的诗学就这样蜕变成了酒的政治经济学。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19世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纪。
现实主义与左拉的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不同。
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内心大多都充满了批判的激情,一种小酒馆里的密谋家式的激情。
所以,勃兰兑斯称巴尔扎克为浪漫派。
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和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超现实主义者在实质上十分相近。
关于超现实主义者的描述,能让人想起无产阶级密谋家:
“诗人是精神上的冒险家或探险家。
”(17)
“阿拉贡的诗歌……揭示街头遭遇如何像诗的意象那样令人激动得浑身打颤。
”(18)“从沉醉中获取革命的能量,这便是超现实主义的所有作品和活动的目标。
”(19)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现实主义的仇恨和批判情绪,变成了一种集体的想象(或语言)形式,“使全部革命的张力变成集体的身体神经网,整个集体的身体神经网变成革命的放电器。
”(20)也就是说,这种沉醉不是个人的身体感受,而是一种集体身体的相互感染及其激越情绪。
并且,它有意忽略酒的水的一面,而夸大它的火的一面。
五、独饮者的诗学
“酒的政治经济学”,与巴什拉尔所说的“酒的阿巴贡情结”意思相近--“喝下酒精的人会像酒精那样燃烧。
”因此,用不着担心物质会丢失。
这是一种实用的功利主义情结。
但与养生学不同的是,它带有历史或政治、经济的印记。
巴什拉尔认为,酒之中还有另一种对应的情结:
“霍夫曼情结”。
巴什拉尔写道:
酒精的火是最初的灵感,霍夫曼整个构思都在这种光亮中被照明……酒精的无意识是一种深刻的存在。
酒精是言语的因素。
它让人打开滔滔不绝的话匣子。
幻想最终为理性思想作了最好准备。
火的幻想频繁出现……突然,即逝的火的悲观色彩改变了想象,即将熄灭的火焰象征着正在逝去的年华。
时光……沉重地压在心头。
这样,讲故事的人、医生、物理学家、小说家都成了遐想者……霍夫曼把他们连接在童年的回忆上。
(21)
酒的遐想触动了真正的回忆,并且在短时间里上演一出“时间”的戏剧:
肉体在燃烧,光阴迅速流逝,时间因此改变了它的物理节奏。
所以,遐想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肉体的自燃,或带有自杀的性质。
遐想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自我的觉醒。
由遐想所产生的言语不是饶舌。
饶舌可能是遐想或言语的一种外在节奏,但不是它的内容。
波德莱尔最早将这种酒的精神变成了一种想象的形式。
他并不想将酒的意象变成单纯的火(暴力、革命)的意象。
尽管在“六月革命”时,他曾经参加了街垒战,并举着枪到处大喊大叫,但他自己解释说,对1848年的陶醉,是一种毁灭的乐趣,是对恶的爱好。
波德莱尔就是用一双因拥抱白云而折断的手,拥抱“恶”的花朵。
“恶”是人性的,“坏”是反人性的。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坏”,而不是“恶”。
波德莱尔将酒视为具有神性的饮料。
他反复说,酒就像人一样,能将罪恶和美德合而为一。
它能使人产生一种既飘然上升,又如临深渊的感受。
波德莱尔称之为“行为、回忆、梦幻、欲望、悔恨、内疚、美的深渊”。
(22)在波德莱尔这里,酒、家、祖国几乎就是同义词。
因此,酒总是与波希米亚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拾垃圾者、诗人、孤独和忧郁者相关。
对于孤独者来说,酒是一种恩惠。
他讲述过一个动人的故事,关于年轻的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与一位流浪吉他手和流浪石匠的流浪故事。
他过着吉普赛人、江湖乐手、无家可归之人的伟大流浪生活……人们跟随着他,就像跟随着耶酥……在演奏会的那天……人们找遍了城里所有的小酒店和咖啡馆。
最后,发现他和他的朋友在一起,那是一家难以描述的下流酒吧,他醉如烂泥……(小提琴声、吉他声和石匠的醉酒歌响起来了)最后,观众们变得比他还要醉……而现在,他在何处呢?
哪块土地上接受了这位世界主义者的遗体呢?
(23)
他还说:
“醉于美酒?
醉于诗歌?
还是醉于道德?
随你的便,但是请你快陶醉吧。
”(24)这与上面那段文字一样,在“恶”、“堕落”的外表下隐藏着最具人性的因素。
在昏沉中回忆、在醉意中醒来;一种水一般的(而非火)柔性物在主宰。
他的酒与爱伦·坡的酒一样,正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