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17页文档资料.docx
《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17页文档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17页文档资料.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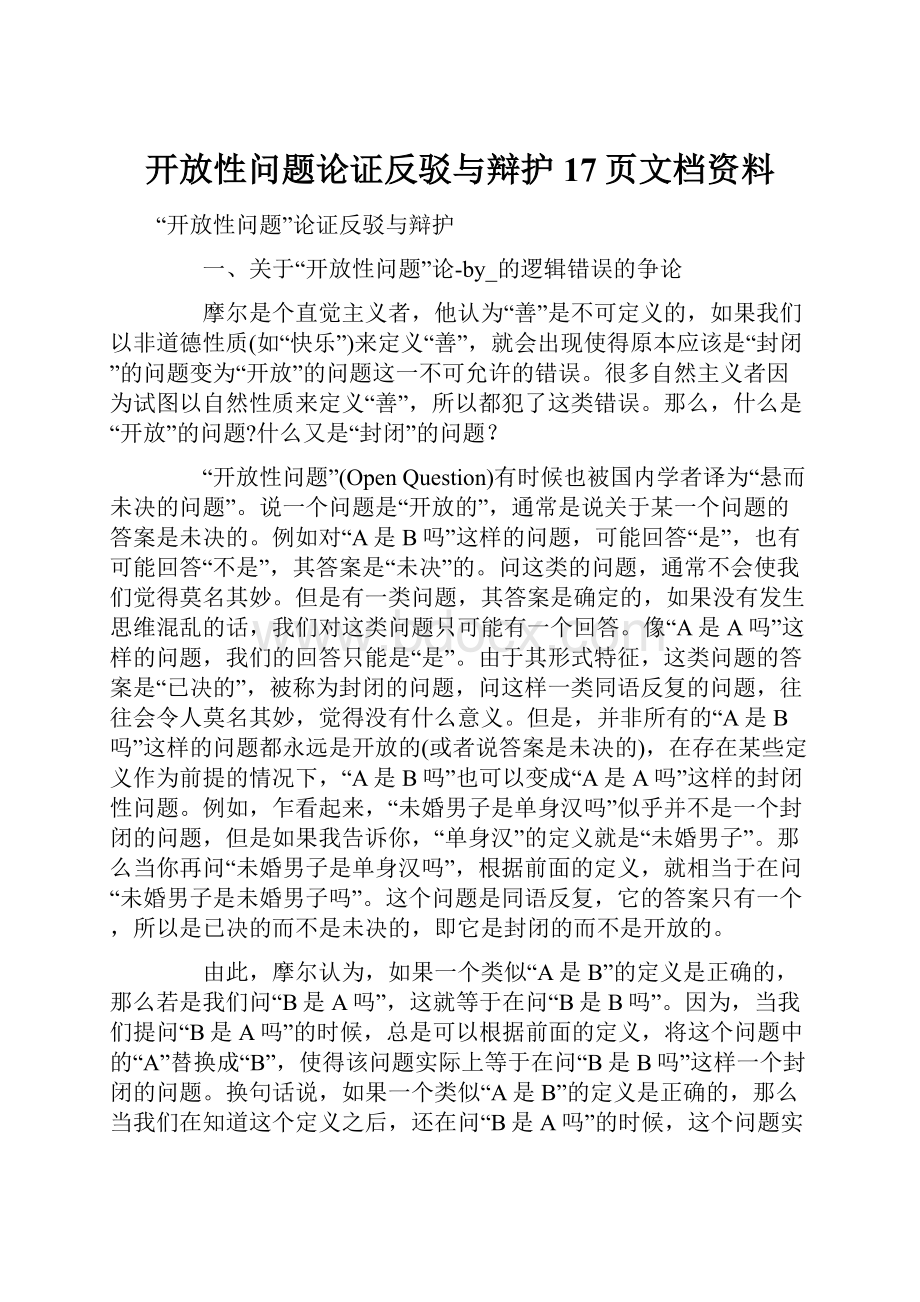
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17页文档资料
“开放性问题”论证反驳与辩护
一、关于“开放性问题”论-by_的逻辑错误的争论
摩尔是个直觉主义者,他认为“善”是不可定义的,如果我们以非道德性质(如“快乐”)来定义“善”,就会出现使得原本应该是“封闭”的问题变为“开放”的问题这一不可允许的错误。
很多自然主义者因为试图以自然性质来定义“善”,所以都犯了这类错误。
那么,什么是“开放”的问题?
什么又是“封闭”的问题?
“开放性问题”(OpenQuestion)有时候也被国内学者译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说一个问题是“开放的”,通常是说关于某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未决的。
例如对“A是B吗”这样的问题,可能回答“是”,也有可能回答“不是”,其答案是“未决”的。
问这类的问题,通常不会使我们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有一类问题,其答案是确定的,如果没有发生思维混乱的话,我们对这类问题只可能有一个回答。
像“A是A吗”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是”。
由于其形式特征,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已决的”,被称为封闭的问题,问这样一类同语反复的问题,往往会令人莫名其妙,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并非所有的“A是B吗”这样的问题都永远是开放的(或者说答案是未决的),在存在某些定义作为前提的情况下,“A是B吗”也可以变成“A是A吗”这样的封闭性问题。
例如,乍看起来,“未婚男子是单身汉吗”似乎并不是一个封闭的问题,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单身汉”的定义就是“未婚男子”。
那么当你再问“未婚男子是单身汉吗”,根据前面的定义,就相当于在问“未婚男子是未婚男子吗”。
这个问题是同语反复,它的答案只有一个,所以是已决的而不是未决的,即它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
由此,摩尔认为,如果一个类似“A是B”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若是我们问“B是A吗”,这就等于在问“B是B吗”。
因为,当我们提问“B是A吗”的时候,总是可以根据前面的定义,将这个问题中的“A”替换成“B”,使得该问题实际上等于在问“B是B吗”这样一个封闭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类似“A是B”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当我们在知道这个定义之后,还在问“B是A吗”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的问题。
它是没有意义的、同语反复的问题,问这样的问题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根据这个想法,摩尔认定,所有关于“善”的自然主义定义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不管对‘善’提出什么定义,往往可以对这样下定义的复合体(即用来下定义的那个定义项,引者注),有意义地追问它本身是否是善的。
”例如,我们把“善”定义为“快乐”,但是我们总是可以倒过来有意义地问“快乐是善的吗”。
如果这个关于“善”的定义是正确的,那么当问“快乐是善的吗”的时候,只要把“善”替换为“快乐”,就本应该等于在问“快乐是快乐吗”这样一个封闭的问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在正常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接受了一定的道德常识的人,凭着自己的直觉,都会认为“快乐是不是善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意义的、尚未解决的开放性问题,而不会认为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或没有意义的封闭性问题。
所以,自然主义把“善”定义为“快乐”是错误的。
摩尔的这一论证过程被称为“开放性问题”论证。
他得出结论说,由于所有关于“善”的自然主义定义都会受到“开放性问题”论证的反驳,所以“善”不能用任何自然性质来定义。
摩尔的论证过程如下:
我们可以用字母G代表“善”一词,用N表示用于定义G的某种自然性质,则:
S1:
将G定义成N,即“X是G当且仅当X是N”。
S2:
我们提出问题:
“X是N,但是X是G吗?
”
S3:
把S1代入S2,我们得到一个经过转化的问题:
“X是N,但是X是N吗?
”
结论是:
如果我们经过转化得到的S3中的问题和S2中的问题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S2中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同语反复的话,这就能证明S1的定义是正确的。
现在反思一下自己的心思就会知道,实际上我们总是可以有意义地问用来定义“善”的自然性质N是不是善的,这类问题是开放的,它不会像问“N是N吗”一样,令人觉得莫名其妙,没有意义。
所以,S1提供的关于“善”的定义是不正确的。
在摩尔的整个论证中,“N是善的吗”这一反问是开放的,这是整个论证的关键。
在摩尔看来,如果前面的定义足够正确的话,通过把“善”替换成“N”,这个问题就应该等于是在问“N是N吗”。
但是摩尔认为,我们根据道德常识都意识到,“N是善的吗”和“N是N吗”是两个不一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可以有意义地提出“N是善的吗”这个问题,并且明白这不是一个同语反复的问题,所以前面的定义是错误的。
摩尔的观点对自然主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甚至将所有以自然性质来定义“善”的做法称为“自然主义谬误”,而这一称呼“一时成为对自然主义等伦理学说的权威的、总体性的否定性评价,甚至演变为伦理学中一种新的教条”。
自然主义因此遭到了冷落,甚至一度声名狼藉。
为了回击摩尔的批评,一些自然主义者对摩尔的“N是善的吗”这个问题的开放性及其论证过程,提出了质疑。
1939年,自然主义者弗兰克纳(W.K.Frankena)在《自然主义谬误》这篇文章中指出,摩尔的论证犯了把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的错误。
他认为,摩尔的论证是这样的,首先,他其实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自己的结论――“善”是不能用自然性质(例如“快乐”)来定义的。
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说对于一切给“善”下定义的自然性质(例如“快乐”),我们总是可以有意义地问它是不是善的(例如“快乐是善的吗”),因此前面的定义是错误的。
但是,为什么“快乐是善的吗”这个问题不会令我们感觉莫名其妙、没有意义呢?
我们前面不是已经把“善”定义为“快乐”了吗?
这个问题不就是等于在问“快乐是快乐吗”?
我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在问了点别的什么?
弗兰克纳认为,摩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要诉诸自己论证的结论――因为“善”不能用自然性质N来定义。
这样,在弗兰克纳看来,摩尔的论证实质上是一个循环论证。
英国的伦理学家玛丽?
沃诺克(MaryWarnock)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她认为:
“这种论证是一种乞取前提的诡辩。
因为它业已假定要证明的是什么,即证明善是单纯的和不可分析的……只是因为穆尔(即摩尔,引者注)已经确信,‘善’是一种单纯性质的名称,所以他才认为,有意义的换位之可能,使这定义不可能是正确的。
”沃诺克的意思非常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事先认为“善”不能通过自然性质来定义,而是承认“善”的自然主义定义,那么“N是善的吗”就完全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问题。
关于前面的指责,摩尔的辩护者其实可以做出如下的解答:
摩尔仅仅是说,不管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定义,都可以有意义地反问“N是善的吗”,这个问题是开放的。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是开放的,我们才能够推出结论说,前面关于“善”的定义是错误的。
在此之前,摩尔并没有设定什么前提说因为“善”的自然主义定义是错误的,所以“N是善的吗”是开放的。
当然,弗兰克纳和沃诺克有可能会继续追问,如果不是事先假定自然主义是错误的,凭什么就会认为“N是善的吗”是开放的呢?
难道不能认为这就是等于在问“N是N吗”?
从摩尔常识哲学的立场上来看,他是诉诸生活背景和一般人自小培养起来的道德常识的。
我们周遭的生活世界表明,每一个正常的语言使用者总是可以问某个事物是否是善的,并且认为这样的一种提问总是有意义的,这表明我们的心思早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概念――“善”。
而这个独特的“善”的概念的存在,对于我们大家而言,也就是一种常识了。
因此,即使在用“N”来定义“善”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觉得“N是善的吗”这样的问题是开放的,就是因为当问N是否是善的时候,道德常识就已经告诉自己,我们想问的不是N是否是N,这表明“N”和“善”是不同的。
摩尔和他的支持者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
如果判断类似“N是善的吗”这样的道德命题是否开放必须依据道德常识,那么可能我依据自己的常识认定“N是善的吗”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是另一个人依据自己的常识认定这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成长起来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常识,我们无法判断何种常识比较正确。
因此,摩尔依据自己的以及他认为的大部分人的常识,并不能反对以弗兰克纳为代表的一大批自然主义者的常识,因此关于“N是善的吗”是否是一个开放性问题的回答就会依常识的不同而不同,这显然是一个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的结论。
此外,道德常识为何就能帮助我们认识到“N是善的吗”是开放的?
道德常识作为背景,只是提供一定的认识依据,要认识到该问题是开放的,还必须诉诸一种认识能力。
摩尔及其支持者把我们认识“善”的能力称为直觉,并且认为对于某个事物是否为善的把握也必须依靠这种直觉。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我们拥有直觉能力,所以在道德常识作为背景的情况下,能够察觉到该问题的开放性。
但是,以摩尔为代表的各类直觉主义者并不能说清楚“直觉”这种能力究竟是什么,直觉到底是怎样去把握“善”的,因此其理论带有一些模糊性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使得其观点也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例如麦茨(Metz)就评价摩尔说:
“尽管我们可以称摩尔是对现代哲学最伟大、最机敏和最有技巧的提问者,但是我们还必须补充说,他是一个极其软弱和不令人满意的回答者。
”正是因为直觉主义存在着上述种种缺陷,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逐步衰落下去。
二、关于开放性问题中的定义项能否替换被定义项的争论
尽管直觉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衰落了,但是关于“开放性问题”论证的讨论依然还在继续。
另外一些自然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和弗兰克纳一样的反驳,而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自然主义的反对者进行争论。
在20世纪40-50年代,以黑尔为代表的非认知主义者在这次讨论中异军突起,相当活跃,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在摩尔的论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在问了“X是N,但是X是G吗”之后,需要根据“X是G当且仅当X是N,”这个定义,将上面这个问题中的“G”替换成“N”,看看原来这个问题是不是等于在问“X是N,但是X是G吗”这样一个封闭的问题。
因此,把被定义项(G)替换为定义项(N),然后考察“X是N,但是X是G吗”是否等于在问“X是N,但Xx是N吗”,是摩尔整个论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如果人们把“善的”定义为“满足最大功利的”,那么当人们说“满足最大功利的是善的”的时候,就等于通过把“善的”替换为“满足最大功利的”而得到“满足最大功利的是满足最大功利的”这样一个重言式,然后再考察这两句话是否是一个意思。
根据摩尔的观点,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个正确的定义,总是能够把在某个句子中出现的被定义项(例如G)替换为定义项(例如N)而不改变该句子的意思。
自然主义定义正是因为不满足这个条件,所以是错误的。
但是,这样的结论容易导致自然主义的反驳,因为这样一种语词的替换未必总是可行的。
英国的哈里森(JonathanHarrison)认为,自然主义者完全可以摆出一些定义,这些定义一般来说都是正确的,而且是通过自然性质来定义自然性质,但是依然存在着在一个句子中被定义项不能被替换为定义项的情况(因为替换会导致句子意思的改变)。
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中,哈里森将这种类型的反驳总结如下:
第一,当被使用的语词出现在被引号包含的句子中的时候,即使定义双方的意思完全一致,也不能随意替换。
例如,我们可以把“三角形”定义为“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定义,两者的意思完全一致。
某一天,张三说:
“这张纸上画着一个三角形。
”张三的话能否换成“这张纸上画着一个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
显然不能!
因为前一句话被引号包括在张三的语言中,“三角形”是张三实际在说话时使用的语词,这个句子表达了“三角形”一词被实际使用的情况,而不是“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一词的使用情况。
张三说“三角形”的时候肯定不是在说“由三条线段围成的图形”,尽管两者在意思上一样,但是依然不能替换。
引号将语词予以固定化,作为一种记录,表达的是一种客观的信息,这时候我们需要考察的是语言的客观使用情况,引号中任何一个词发生了变化,整个记录下来的信息的意思也大不相同。
第二,即使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要考察引号中语词被使用的客观情况,被定义项也存在不能用定义项来替换的情况。
比如,首先我们把单身汉定义为未婚男子,然后
(1)我们有时候告诉某个不明白“单身汉”意思的人说“单身汉的意思是未婚男子”,这时我们是在告诉他关于“单身汉”一词的意义的综合性主张,它(“单身汉”一词)不能被“未婚男子”一词代替。
此外,
(2)有时候我们说“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也可能是在给“单身汉”下一个分析性的定义,要从“单身汉”中分析出“未婚”、“男子”这样一些特性来,这时候“单身汉”无论如何也不能替换为“未婚男子”。
这是因为,对于“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单身汉”的分析性的句子,由于它表述的内容是分析的,所以是永真式;但是“单身汉是单身汉”却是因为符合“X当且仅当X”这样一个纯粹的逻辑形式而永真,完全和句子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自然主义者其实可以认为,即使是关于自然性质的正确的定义,有时候把被定义项替换为定义项,也可能会导致替换前的句子和替换后的句子意思不同,那么出现用自然性质N替换“X是N,但是X是G吗”中的“G”之后,得到的句子和原来的问题并不相同的情形也是很正常的,因而摩尔不能因为“开放性问题”而指责自然主义。
这就是说,如果说“单身汉是未婚男子”不是等于在说“未婚男子是未婚男子”,这并不导致“单身汉是未婚男子”这个定义是错误的,那么,当我们说“快乐是善的吗”并不等于说“快乐是快乐吗”的时候,这也不一定导致“善是快乐”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上述观点引起了既反对自然主义又有别于直觉主义的非认知主义者的关注。
自然主义对摩尔的上述反驳,有的非认知主义者也是赞同的。
例如非认知主义的代表人物黑尔就认为:
假设我们把“狗仔”定义为“小狗”,那么当我们跟别人说“一条狗仔就是一条小狗”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用“小狗”来替换“狗仔”;换言之,由于不能用“小狗”来替换“狗仔”,“一条狗仔就是一条小狗”这句话不等于“一条小狗就是一条小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前面的定义错了。
“这种反对意见的力量就在于:
我们对‘好’(善)这个词的自然主义定义的攻击,同样也可以施诸对‘狗仔’这个词的定义;但由于后面这类定义很明显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种[对自然主义定义的]攻击必定有某些不妥之处。
”因此,“把在某个句子中出现的被定义项替换为定义项而不改变该句子的意思”就不是一个定义是否正确的标准。
尽管非认知主义者赞成自然主义对直觉主义的上述反驳,但是他们仍然反对自然主义用自然性质来为“善”下定义。
在这一点上非认知主义与直觉主义是一致的,但理由不同。
黑尔认为,价值词“善”(“好”)确实有描述的功能。
例如,说一个老师“好”,当然是在描述这个老师具有“上课认真”、“耐心解惑”、“关心学生”等特征。
但是,用价值词“善”(“好”)来说一个老师,并非仅仅是描述这个老师的上述特征,而是要用“好”来给予这个老师积极的评价,这是“善”的一个最重要的、最独具特色的用法,即“评价”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善”来称赞某人,这是任何一个非价值词都不具备的功能。
因此,是否具有称赞功能,是“善”区别于其他一切非价值词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黑尔之所以反对用自然性质来定义“善”,正是因为“善”、“好”、“勇敢”、“诚实”、“自制”一类的道德价值词具有称赞的功能,当我们用自然性质来对这些价值词下定义的时候,并不能把它们的称赞的功能表达出来。
黑尔指出:
“价值术语在语言中具有一种特殊功能,这就是赞许的功能;所以很明显,我们不能够用其他并不能发挥这种功能的词来定义价值术语;因为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会被剥夺发挥这一功能的手段。
”“单身汉”之所以能够用“未婚男子”来定义,是因为“单身汉”是一个没有感情色彩的、不具备价值属性的主词,所以它可以用“未婚男子”这个自然性质来描述和定义,因为后者也没有感情色彩,不具备赞赏功能。
而“善”、“好”、“勇敢”、“诚实”一类的价值词是具有感情色彩的,是有称赞功能的,因此它不能用表达自然性质的词语来描述和定义,因为表达自然性质的词语无法把“善”、“好”、“勇敢”、“诚实”等价值词的称赞功能和感情色彩表达出来。
例如,我们把“善”定义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没有把“善”的称赞的、鼓励的功能表达出来。
因此,我们总是可以有意义地反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善的吗”。
这其实是在问“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值得称赞的吗”,即是在问应该如何评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要称赞它,还是不称赞它,而这正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在这一回合的讨论中,摩尔的观点遭到了进一步的批评,自然主义对“语词替换”的抨击得到了非认知主义的赞同,但是自然主义并没有获得胜利,其用自然性质来定义“善”的立场遭到了非认知主义的驳斥。
这样,自然主义要捍卫自己的观点,就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
三、关于道德语词的性质综合同一性定义的争论
到20世纪70年代,自然主义对自己的理论做出修正。
他们认为,当我们提出一个定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定义项和被定义项的含义完全一样,而是说两者指称相同的对象。
例如我们说“晨星是暮星”,这不是说“晨星”和“暮星”这两个概念在含义上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晨星”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天亮时分,东方地平线上的一颗很亮的行星”,“暮星”这一概念的含义是“黄昏时分,西方出现的一颗很亮的行星”,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同。
但是,由于它们指称同一个对象――金星,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晨星是暮星”。
因此,自然主义者认为,当我们在定义的时候,通过“是”连接起来的前后两个概念尽管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指称的东西相同,这就是我们通过定义所要表达的。
例如,我们常常说“水是HO”。
显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是相同的,“水”和“HO”都指向一种具有无色无味、可饮用等一系列性质的东西,那么这个通过“是”连接起来的两个概念的同一,实际上就是指称对象的综合同一。
类似的观点可以用在像“善是快乐”这样的定义中,我们不是说“善”和“快乐”这两个概念在含义上相同,而是说两者指称相同的东西――一种性质。
例如,美国的伦理学家普特南就为自然主义辩护说:
“‘善’这个概念与其他任何物理概念可以不是同义的(在古德曼看来,道德一描述语言和物理语言毕竟是极不相同的‘文体’),但是,这并不能得出,是善的和是P――如果P是某种恰当的物理主义的(或更确切地说,功能主义的)P的话――不是同样的性质。
”普特南的意思是,当摩尔说不管用何种自然性质N来定义“善”,总是可以发现“N是善的吗”是一个开放性问题,这只能证明“N”和“善”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同,而不能证明“N”指称的性质(即自然性质N)和“善”指称的性质不是同一个性质。
先前的自然主义认为“善”和“N”的含义是相同的,所以当人们问“N是善的吗”是提出一个封闭性的问题。
但是这一观点自摩尔以来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
现在,自然主义做了一些让步,认为当他们把“善”定义为“N”的时候,并非要说两者的含义相同,而是说两者指称同一种性质P。
因此,当反过来问“N是善的吗”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问两者指称的是否同一种性质P,即是在问“P是P吗”。
所以,这一反问就不是开放的,而是封闭的,即同语反复。
因此,如果当我们说“善是N”的时候,是在说“善”所指称的性质和“N”指称的自然性质相同,那么对“善”进行自然主义的定义就可以在现实经验中避免“开放性问题”论证的指责。
当然,普特南也承认,这种关于“善”的综合同一性定义所得到的并不是关于“善”的定义在每一个可能世界都适用的必然真理。
因为,这种定义如同人们将“温度”定义为“平均分子动能”一样,是一个后天的经验真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并不保证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善”所指称的性质和“N,,所指称的性质都相同,正如这并不保证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温度”都是“平均分子动能”一样。
不过普特南指出,根据克里普克对“经验的必然真理”观点的新的阐述,一旦人们想象一个可能世界,其中“温度”不是“平均分子动能”,那么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温度”,这并不证明我们关于“温度是平均分子动能”的“性质综合同一性定义”是错误的。
类似的观点也可以用在关于“善”的性质综合同一性定义上。
人们可能会想象一个世界,其中“善”不是和“N”指称相同的性质,所以会否认“善”和“N”在性质上综合同一,“这正好是新的必然性理论所拒绝的”。
对于普特南的上述见解,西方元伦理学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我们也不可能对此一一介绍。
其中有一些反对意见是值得在此注意的。
例如摩尔的捍卫者鲍尔(Stephenw.Ball)就提示:
考虑到非认知主义的观点,我们就会明白,假设价值词在性质上真的同自然属性是一样的,那么当我们使用表示这些自然属性N的语言时,就应该具有相应的道德评价功能,或者说这些语词本身就应该进入道德语言的范围之内。
这样,这些表达自然性质的语词N本身就应该具有道德鼓舞的作用,而不是像“水”、“HO”这样,只是冷冰冰的科学技术语言。
还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两个概念――“A"和“B”不仅指称相同的性质,而且在现实中这两个概念的功能也相同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出“A是B”这样的定义,才能保证“B是A吗”是一个封闭的问题。
例如,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水”和“HO”指称的对象相同,就给出“水是HO”这样的定义。
“水是HO”这个定义之所以是正确的,之所以不会导致“H20是水吗”这个问题出现开放性,是因为“水”和“HO”不仅在指称的对象上相同,而且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它们都具有“指称”某一对象的功能。
而“善是N”这一定义之所以会导致“N是善的吗”出现开放性,是因为即使“善”和“N”指称的是同一种性质,但两者的功能不同――“善”不仅有指称的功能,而且有称赞的功能,而“N”(如“快乐”)只有指称的功能,没有称赞的功能。
因为“善”和“N”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用“N”来定义“善”不能穷尽“善”的功能。
因此。
不能用“N”来定义“善”。
我们可以看见,上述的这类反驳和黑尔的观点有类似之处,即强调以“善”为代表的道德语言的特殊用法,而这些特殊用法是一些指称自然性质的概念所不具备的。
我们可以用“善”来赞许某个事物,但不能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普遍接受的”等来赞许某个事物。
这是自然主义者面临的最大难题,但自然主义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
20世纪中后期,自然主义者在提出“善”的性质综合同一性定义的同时,也发展出新自然主义的形态。
这些学者在对某些非价值语词的研究中发现,存在许多自然语词,它们并非只是指称没有价值属性的东西。
图麦蒂举出一些功能性语词说明了这个道理:
“对一种功能性事物的概念的任何恰当的定义都必须部分地依据那个事物的功能或目的而被建构起来。
这就意味着,一个具有X型功能的事物的概念不能脱离一个好x的概念而独立地被界定。
正因为它是好X,如果没有歪曲的话,才体现了它是真正的X。
X的原初的、核心的含义就是由好X赋予的。
因而,要把握一个功能性事物的准确概念而不同时把握从适当类型的坏事物中区分出好事物的标准,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图麦蒂认为,如“音乐家”、“运动员”这样表示职业的语词就可以说是功能性的语词,尽管它们不是价值词,但词义本身却内在地含有价值特征。
“音乐家”的内在含义中就蕴含“好的音乐才华”,“运动员”的含义中也包括“好于一般人的运动能力”。
因此,当我们使用这些语词来形容某个人的时候,并不能说没有丝毫赞许的意味。
例如我们会夸奖某个孩子是个“小音乐家”,称赞某个体力充沛的人有运动员的素质。
这些新自然主义者由此认为,说指称自然性质的概念不能用来进行道德评价(如赞赏、批评等),是不合适的,我们在提到“快乐”、“同情心”的时候,内心也会产生赞许的感觉。
我们不是也常常赞许某个孩子说“他总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吗?
再比如,我们有时候也会轻蔑地耻笑某个人说“真是一头蠢驴”或批评某人是“一只懒猪”。
这里的“猪”、“驴”尽管不是道德语词,但也具有进行负面评价的功能。
应该说,非认知主义所谓的“道德语言的独特功能不能为非道德语言所拥有”的观点正是新自然主义要批评的主要观点之一。
非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