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满分作文1.docx
《回归满分作文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回归满分作文1.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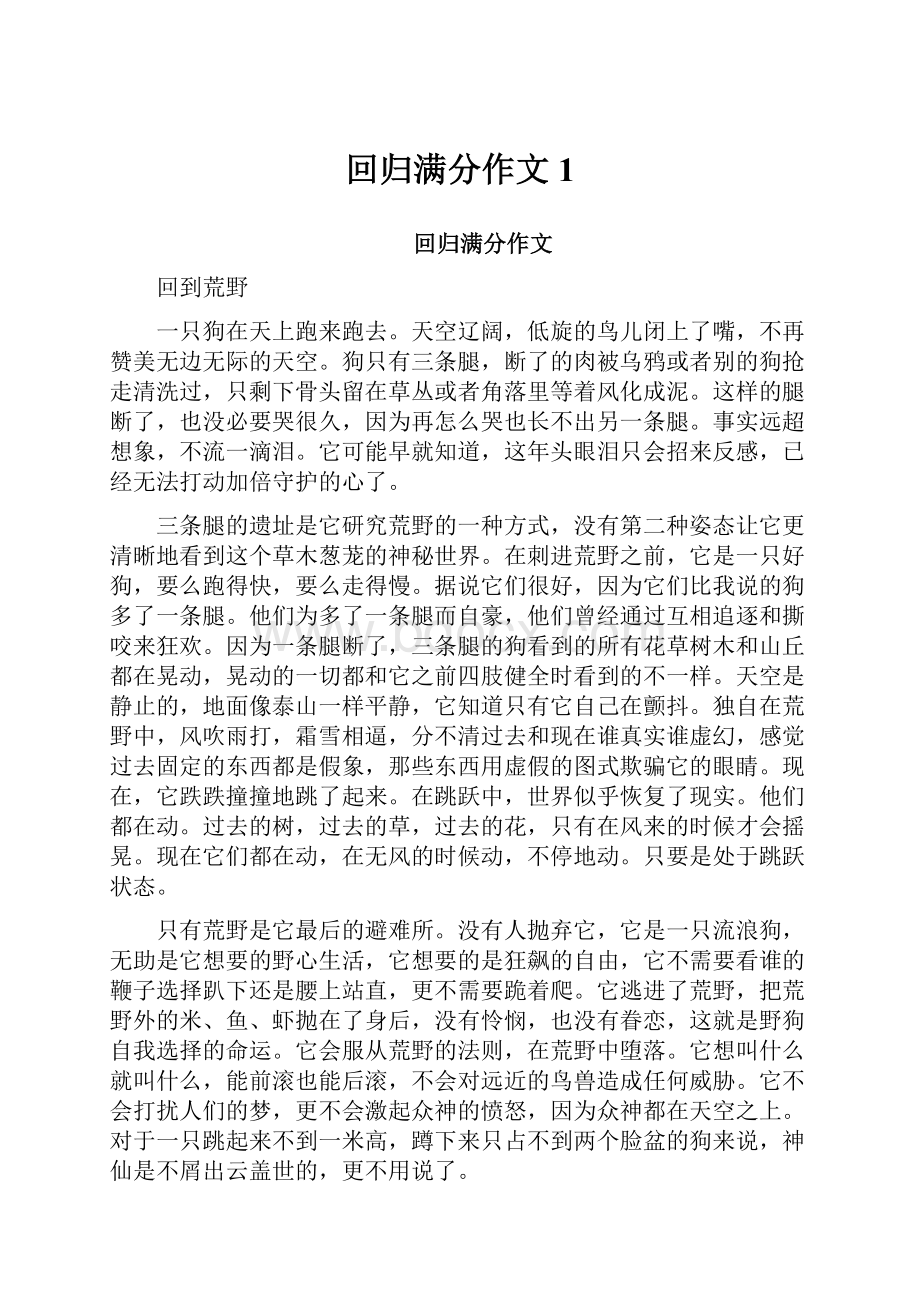
回归满分作文1
回归满分作文
回到荒野
一只狗在天上跑来跑去。
天空辽阔,低旋的鸟儿闭上了嘴,不再赞美无边无际的天空。
狗只有三条腿,断了的肉被乌鸦或者别的狗抢走清洗过,只剩下骨头留在草丛或者角落里等着风化成泥。
这样的腿断了,也没必要哭很久,因为再怎么哭也长不出另一条腿。
事实远超想象,不流一滴泪。
它可能早就知道,这年头眼泪只会招来反感,已经无法打动加倍守护的心了。
三条腿的遗址是它研究荒野的一种方式,没有第二种姿态让它更清晰地看到这个草木葱茏的神秘世界。
在刺进荒野之前,它是一只好狗,要么跑得快,要么走得慢。
据说它们很好,因为它们比我说的狗多了一条腿。
他们为多了一条腿而自豪,他们曾经通过互相追逐和撕咬来狂欢。
因为一条腿断了,三条腿的狗看到的所有花草树木和山丘都在晃动,晃动的一切都和它之前四肢健全时看到的不一样。
天空是静止的,地面像泰山一样平静,它知道只有它自己在颤抖。
独自在荒野中,风吹雨打,霜雪相逼,分不清过去和现在谁真实谁虚幻,感觉过去固定的东西都是假象,那些东西用虚假的图式欺骗它的眼睛。
现在,它跌跌撞撞地跳了起来。
在跳跃中,世界似乎恢复了现实。
他们都在动。
过去的树,过去的草,过去的花,只有在风来的时候才会摇晃。
现在它们都在动,在无风的时候动,不停地动。
只要是处于跳跃状态。
只有荒野是它最后的避难所。
没有人抛弃它,它是一只流浪狗,无助是它想要的野心生活,它想要的是狂飙的自由,它不需要看谁的鞭子选择趴下还是腰上站直,更不需要跪着爬。
它逃进了荒野,把荒野外的米、鱼、虾抛在了身后,没有怜悯,也没有眷恋,这就是野狗自我选择的命运。
它会服从荒野的法则,在荒野中堕落。
它想叫什么就叫什么,能前滚也能后滚,不会对远近的鸟兽造成任何威胁。
它不会打扰人们的梦,更不会激起众神的愤怒,因为众神都在天空之上。
对于一只跳起来不到一米高,蹲下来只占不到两个脸盆的狗来说,神仙是不屑出云盖世的,更不用说了。
天空下,一只三条腿的狗在跑来跑去。
天空很广阔,不管天空有多广阔,对这只狗来说都没有多大意义。
抬头看看星空,想想头上两条腿站着的庞然大物是什么。
一只狗,一只跛行的狗,拥有一片广阔的荒野就足够了。
这种浩瀚不亚于天空的浩瀚和狭窄。
可以看到,荒野的边缘比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天空更长,更难穷尽。
在这样的荒野里,什么能让狗更快乐?
没必要决定这是谁的弃儿。
它只想回家,没有朋友和亲人的家。
呼啸的风,猛烈的雨,飘忽不定的动物,来来去去的鸟都是它最亲密的朋友。
它懂得弱肉强食。
虽然到处都有埋伏,虽然弱小,但它知道自己不是四面受敌,牙齿锋利,爪子仍然是杀人的武器。
它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算逃不出死鬼的追击,也应该选择葬在荒野的腹地,而不是横尸荒野之外。
没有什么能阻止它回到荒野。
死亡是一件不需要担心的事情。
该来的总会来,该走的谁也留不住。
它会用树枝和草叶为自己搭一个小窝,那个窝一定包含了天地的热量,即使天冷也不会觉得天寒地冻。
它会出去觅食,驰骋百里,很有可能累了就不回窝了。
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张天地之床也是一大乐事。
如果你晚上一个人走,它摆动的尾巴会甩出花露的余香,倦鸟归林的声音,还有一个可以期待和规划的未来,这几乎让它成为荒野中的三足王子。
喝血喝毛,多日之后会恢复狼的本性。
它的骨头像铁一样坚硬,荒野会缩到它的胸膛里,成为它像城堡一样坚固的图腾。
它是狼,不是狗,这是荒野给它的祝福。
它不需要太多,它可以填饱肚子,有办法让它张开三蹄,在半月夜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够了。
是的,会有的。
会有一些它需要的东西。
因为这里不是纸荒。
走得很远
我想日夜用两条腿走很远的路。
距离在哪里?
翻山越水,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走到远方。
但是现在我背对着别处,在我的腿后面走,后退,后退。
我的后脑勺没有黑白分明的眼睛,但我仍然可以找到回去的路。
有风吹过我的耳朵。
这些风带着泥沙,把灰尘撒在我脸上,吹着我的衣服。
雨声沙沙作响,几只青蛙左跳右跳,无法跳出雨幕;当然有阳光,它没有脚,但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跟着我;有昆虫,各种无名的昆虫,有的在我头顶咆哮,有的在地上悄悄爬行或移动,向我说的远方进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一尺宽的黄泥地上的两棵树,一只手掌很大的村子里的狗,一条张开双臂就能量出腰身的河。
我想说两棵树,一棵是桃树,另一棵是桃树。
不同的是,前者是肉眼可见的桃树,后者只能在遥远的记忆中找到。
也就是说,当我向后走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棵活树和一棵死树。
它们都生长在同一片黄泥上,阳光和雨水像往年一样滋润着这方寸土地,但当年的树看不到今年的树的树荫,今年的树看不到当年的树的婀娜。
这棵死桃树是我种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光脚的孩子。
我把长在石头缝隙里的桃树树苗,移植到吊脚楼前的空地上,希望它快快长大,开花结果,就像父亲希望我一夜长高一样,帮他种瓜种豆。
春天种树,秋天收获果实,会让你不开心,但我没办法。
我不能马上把葫芦变成瓢。
我只能等待。
第一,和春天冬天比起来,我在季节性跨栏上打了六七个前滚,和爸爸的黑发卡白头发比起来,和我的口钻比起来。
出几根黑毛,终于等来了桃树果实累累。
可是父亲的白发渐渐赫然醒目之后,这棵桃树竟然先于父亲的最后一根黑发枯逝世了。
它是被虫子蛀空树干而逝世的,桃树倒下后粗大的树根用指甲一划还可以见到树皮是绿的,我想来年树根还会长出新芽,它不会轻易逝世掉。
可它毕竟没能熬过虫子猖狂的啮咬,过了一个漫长的夏季就变成了百无一用的朽木。
既然枯木长不出枝叶,那我就种下新的桃树苗吧。
于是就种了,于是今天我看到了这棵活着的树,它枝繁叶茂,果子压弯了枝条。
那棵早早逝世去的树,它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走出这个小小的村落呢?
滋养它的土地是这样的贫瘠,要不它也不会过了六七年才成果,让壮年的父亲在等候里长成了小老头。
这片土地还有遍地的虫子,这些虫子很聪慧,在庄稼树木还没到收获的时节它们息事宁人,比及稻果一飘香它们就来势汹汹难以拦阻。
如果它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在一个难以探究的神秘空间里,一棵树是有着丰盛驳杂的心坎世界的。
那么它会不会像我一样日日夜夜想凭着两条腿走向远方?
我不克不及给出一个确实的答案。
我很突兀地想到:
活着的这棵桃树就是逝世去的桃树的远方,活着的一切就是逝世去的所有的远方。
这算是给那棵倒下的桃树一个牵强附会的安慰吗?
一只狗从我身旁蹿了过去,同时传来的还有狗主人大声的斥骂,我模糊看到他扬起一根木棍摆布挥动。
狗逃进了荒原,它走过之处草尖树叶沾着星星点点的血迹。
不知道它到底是因为什么受的伤,到底是因为什么被赶出家门,但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漏网之鱼。
这狗我是认得的,先前它的运动范畴就在村庄四周,它的主人将它训练有素,可以叫狗在荒山野岭里找见他的畜生,狗主人凭狗的叫声就可以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把他的牛马赶回圈。
那狗有时还会牵扯主人的裤脚带他找到牛马的藏身之处。
狗主人视狗如本身的另一个儿子,煮成的饭菜要先给它吃,给它洗澡捉虱子,对大伙说狗逝世后要厚葬要给它立碑。
但是现在这只狗却仓促出逃,它的叫声凄厉无助,我怎么都想不到一只好狗竟会有这样的下场。
荒原似乎也不是它最终的归宿,极有可能它还会返回村落,在主人的脚下匍匐低头。
这狗,在被扫地出门前有像我一样日日夜夜想凭着两条腿走向远方吗?
它的听觉那么敏锐,必然是听到了同类从远处传来的召唤声,但是,是什么东西牵绊住它而不弃主人走出村落呢?
仅仅是因为割舍不掉主人赐予的恩宠吗?
仅仅是因为分开了人就没法保存吗?
我也没法给出一个确实的答案。
这狗被痛打一顿后我想真的不会一气之下远走他乡,因为还有一个静谧的荒原供它容身,供它舔舐伤口。
而我现在却倒退着行走,我能退到哪里去?
哪里才是我退后的终点?
没有一个荒原供我退后,我的退后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中。
还有,我见到了一条河,一条清澈见底的河。
河上倒映的蓝天白云晃成粼粼的碎片,河底的沙石历历可数。
站在河岸上,我听到哗哗的流水说:
“去远方,去远方!
”我低声说:
“牧童不再骑黄牛了,不再遥指杏花村了,不再笛弄晚风三四声了,他们脱下蓑衣丢下笛子,去远方了,去远方了,去远方操弄起了轰隆作响的机器,扛起了水泥挑起了砂浆做起了小贩。
村姑不再绣花布鞋了,不再这边唱来那边和了,不再打猪菜砍柴火了,去远方了,去远方了,远方是金是银的稻谷一望无际,她们正在挥镰流汗收割。
耕牛不再爬上山坡了,不再引颈哞叫了,不再披星带月回家了,去远方了,去远方了,去屠宰场了,田里爬行的是悍然作响的铁牛。
”
站在河岸上,我看到杨柳拂堤,拂堤的杨柳像是一只只手挽留日夜奔流东去的逝水。
风拂我脸庞,它不会像杨柳挽留河水那样挽留我,风是雨的前奏,雨一来,堤岸上就会空无一人,我会退到一个未知的处所躲风避雨。
流水,你告知我,这个未知的处所在哪里?
去远方!
去远方!
不,我现在只想倒退着行走。
倒退着行走亦即远方的一种。
骑上马背以后
我在读成为美国异乡人的纳博科夫的《娜塔莎》,我非方非圆的脑袋是一个平原。
平原跑马,骑上马背,我越去越远,我的影子和身材脱离,我成了本身的异乡人。
梦幻一般,我看到窗玻璃上映出娜塔莎朦胧的影子,她和巴伦。
乌尔夫来到郊外,娜塔莎说十岁时家里的餐厅走进一个急促的女人,光着脚,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外衣,肚子很大,脸却很小,又瘦又黄,眼神极其温顺,极其神秘,这个女人就是圣母玛利亚。
从郊外返回家的途中,巴伦。
乌尔夫说他爱她,娜塔莎幸福得似乎漂浮起来,好像被悬在半空一样。
她满怀幸福却感到本身越来越衰弱,恍惚中她好似到了家,看见父亲穿着一件黑色外套,一只手护着没有扣扣子的衬衣领子,另一只手晃着房门钥匙,脸色张皇走出来,在薄暮的薄雾中微微驼着背,朝报亭走去,等她真的走进家门,却发明父亲躺在床上,已经放手人寰。
合上小说,疲惫压过火顶,我睡了过去。
梦里我回到了家。
家是黑瓦石墙的家。
石墙的青石是父亲一块块垒砌上去的。
老屋四旁的黄土地从未发生一个能振兴家业的儿女但却盛产青石。
父亲用钢钎撬起青石板,抡起铁锤砸上去,一块块不规矩的青石就乱糟糟横在父亲脚下,柔和了父亲的目光,虽然父亲眼里的青石质地仍然是坚硬的,边角还锐利如刀。
我看到屋子四周的一些荒草还没有干涸,依然绿着。
那是一种蒿草味的绿,这种绿孤单了二十几年,布满时间暗褐色的青苔,一岁一枯荣。
梦里的我被绿的汁液爬满,青苔也跟了上来,它们奔驰追逐,从头到脚,从体内到身外,仿佛我是平原,它们是跑马。
它们打着唿哨,四蹄奋飞越去越远,我的梦越拉越长。
我的梦成为了我的身材的异乡人。
我坐在屋顶的瓦片上,看到十几座高耸入云的山,山高可齐天,再往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堂了。
但是云雾漫山坡的时候,天堂的门应当是无迹可寻的吧,或者,天堂的门就是父亲破烂的屋子朝东而开的门,只要太阳一升上山头,父亲的石头房就被镀得金黄金黄。
天堂的门都是金黄金黄的,不信你们在凌晨八九点钟时试着仰望天空。
梦中的母亲佝偻着背在田边捡枯草,这些枯草一投入火炉里,就会燃起熊熊火光。
没有灯油的夜晚,在我的童年,这样的火光就是照亮我的眼眸的灯。
火光一闪一闪,我的世界一会儿含混一会儿清楚。
这样的夜晚容易使我沉入空想,我把本身变幻成孙猴子在村庄上空腾云跨风,只要想得到什么,拔根毫毛吹一口吻就可以得到了,在神奇的法力的作用下,我会有像别人家那样的一盏电灯,天一擦黑,一拉灯绳,咔嚓一声过后灯就亮了,眼前的暗中白纸般透明。
我还会成为电影院的守门人,那是一个气势汹汹的角色,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克不及进入电影院。
我感到我童年的额头还在隐隐生疼,那是被守门人用指节敲打出来的成果,如果我真的成了守门人,我必然把小镇所有眼睛充斥饥饿的光的孩子放进电影院,分文不收。
火光熊熊,不熄不灭,在我的梦中。
如手的火光抚摩在母亲粗糙的脸庞上,比我的手还要广大,比一杯煮酒还要温热。
火是母亲生涯的一部分,但具体而微的生涯却不克不及使母亲一展笑容,但这火却能温暖母亲的身子,它似乎是一股鲜活的血液流入母亲的体内,让母亲苍白的脸红润起来。
它比生涯有情,比生涯有义。
母亲养了两女三男,大姐到了要出阁的年纪却咽下断肠草一去不回头,二姐数年后就远嫁高山之上的寨子,而大哥二哥不是女人,却像女人一样嫁给了城市,两三年难见回一次家,他们把城市滴漏下来的钞票塞进口袋,也把母亲望眼欲穿的眼光塞进了空空的胸膛。
家里,唯剩我一人陪同在母亲身边,母亲从我身上捕获出大姐日渐含混的影像,从我摔跤喊疼时想象大哥二哥捂着胸口朝故乡眺望生出的苦楚。
不知多少次,母亲总是在日落傍晚时走到村头举目遥望,她的眼光渔网一样抛撒在荒草丛生的黄泥路上,盼望一眨眼,渔网就会把大哥二哥拉回她的身边,在她眼前高声喊:
“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这个时候,母亲老是低声唤着大哥二哥的乳名,嗓音拉得长长的,长得不住地发抖,似乎这样一喊,眼光止境的路上就会跳出两个儿子的身影朝她飞驰。
大多时候,母亲看到的黄泥路都是空无一物,偶尔路上闪出几匹回圈的马,母亲的眼光马上爬到马背上,当马翻过风坡口,母亲的眼光就会跳下来,然后拨草攀崖钻到一个半坡上的岩洞口引颈呼喊,呼喊大姐回家,回家。
黑乎乎的岩洞里掩埋着大姐的骸骨,洞口的茅草野花肆意疯长,摇曳身姿用沙沙的响声答复母亲的呼喊,而泥土之下的皑皑白骨却缄默如铁,一言不发,任由母亲的眼光有家难回。
梦醒了。
这个时候,娜塔莎的父亲已经咽气了很多很多年。
他逝世前,鼻子苍白得像蜡一样。
我赶回家里,眼前的速生杨飞快掠过,它们长得高大挺立,枝桠弄出奇异的声响,那是一种智慧的声音,但是它不知道我赶回家就想证实母亲到底是不是在田边捡枯草。
站在屋子上方的坡地上,遍地的枯枝败叶证实了我的到来绝非春天。
远处的松树林不声不响,我听不见但我想情况会是这样的。
娜塔莎在郊外看见的松树林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她所看见的松树林长有桦树,树叶如烟似雾,松树林边还有湖,湖面上漂浮着闪亮耀眼的云朵,比如俄罗斯人列维坦画中的风景。
我看到的松树林没有这些东西,除了松树就是低矮的杂草,那些杂草我一低头你们就想象到了它的样子。
我一步步走向老屋,我的双腿不再灵活如往昔,那是因为它注满两袖空空一无所有的自责和悲惨。
在这片寂寞的土地面前,我不得不承认本身和它一样一贫如洗。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不会谢绝彼此的到来,尽管我不克不及献给它富贵和光荣,它不克不及赠予我平原和跑马。
屋前的几棵银杏树直挺挺地摸向傍晚的天空,摸出了满地的金黄落叶。
落叶形如脚趾,风吹来,脚趾移动,像是百十个人负重行走。
落叶,我是你们最忠诚的伙伴,你们走,我也走。
你们要到哪里去?
风大你们飘,风小你们下落。
今夜如果暴风大作大雨倾盆,你们是不是要奔往未知的远方一去不回头?
你们一去不回头,我三步一回头,在我进入或者分开村落的时候。
我就这样了,像你们母体的根,诞生或者逝世亡,都属于这片贫瘠的黄土地,走不出去,也不想把本身连根拔起。
娜塔莎的父亲老赫兰诺夫的两个儿子逝世于他家乡人的手下,他的家乡人又把他和娜塔莎赶出了俄罗斯,他们逃到美国,感恩上苍还让他们活着,老赫兰诺夫说当春回大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像鹳鹤那样返回俄罗斯。
银杏,落叶迎风起舞的银杏,这些,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一把铁锁把满地落叶关在了门外,母亲不在家。
我引颈观望,对面小山坡,黄泥路上,母亲背着竹篓,缠着花布头巾,走向另一座更高的山坡。
我大声喊:
“春回大地,重返俄罗斯!
”
母亲回头过来,满脸愕然,花布头巾从头上飘落。
我说:
“妈,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