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docx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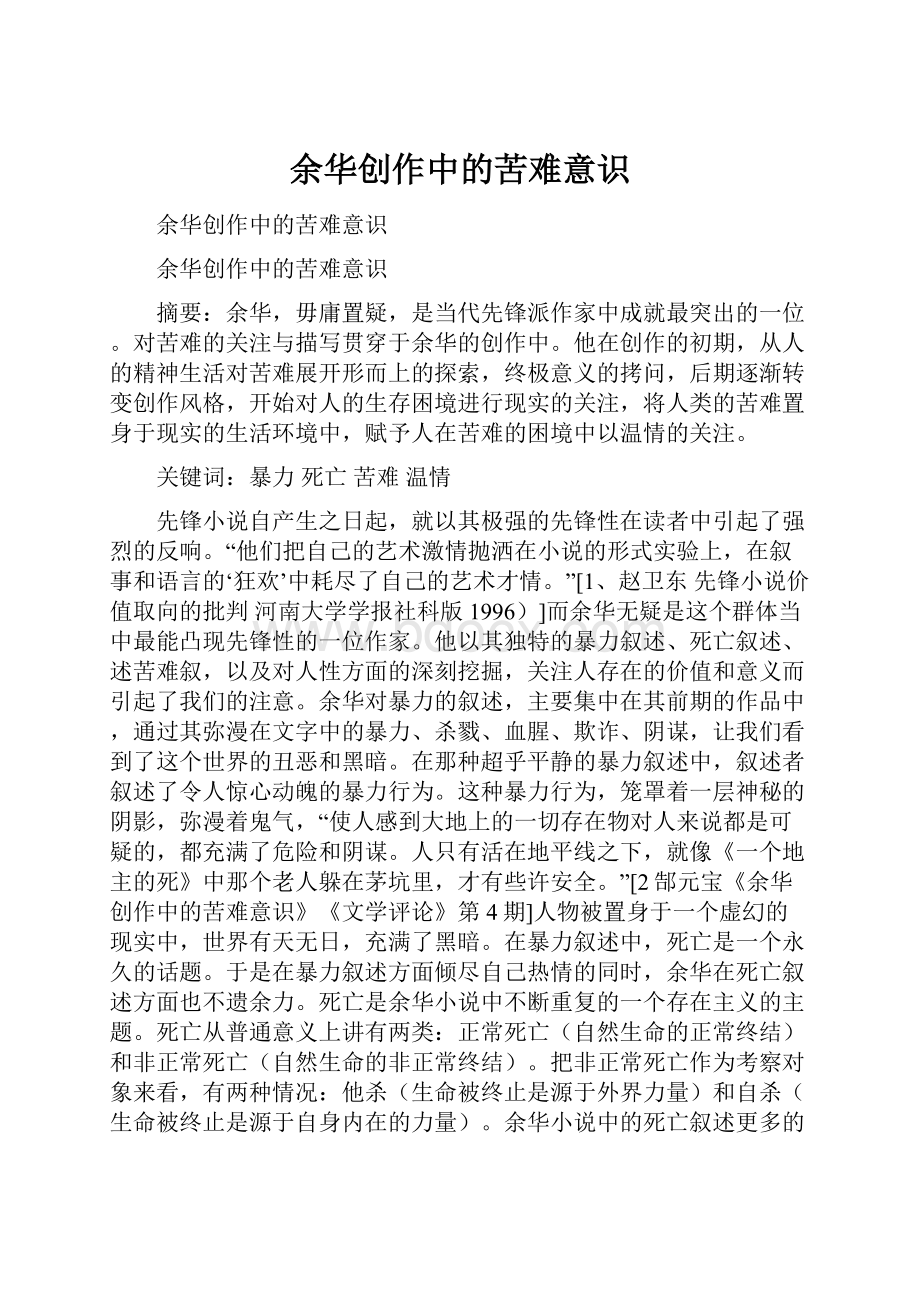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摘要:
余华,毋庸置疑,是当代先锋派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
对苦难的关注与描写贯穿于余华的创作中。
他在创作的初期,从人的精神生活对苦难展开形而上的探索,终极意义的拷问,后期逐渐转变创作风格,开始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现实的关注,将人类的苦难置身于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赋予人在苦难的困境中以温情的关注。
关键词:
暴力死亡苦难温情
先锋小说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极强的先锋性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激情抛洒在小说的形式实验上,在叙事和语言的‘狂欢’中耗尽了自己的艺术才情。
”[1、赵卫东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而余华无疑是这个群体当中最能凸现先锋性的一位作家。
他以其独特的暴力叙述、死亡叙述、述苦难叙,以及对人性方面的深刻挖掘,关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其前期的作品中,通过其弥漫在文字中的暴力、杀戮、血腥、欺诈、阴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和黑暗。
在那种超乎平静的暴力叙述中,叙述者叙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暴力行为。
这种暴力行为,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阴影,弥漫着鬼气,“使人感到大地上的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都是可疑的,都充满了危险和阴谋。
人只有活在地平线之下,就像《一个地主的死》中那个老人躲在茅坑里,才有些许安全。
”[2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第4期]人物被置身于一个虚幻的现实中,世界有天无日,充满了黑暗。
在暴力叙述中,死亡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于是在暴力叙述方面倾尽自己热情的同时,余华在死亡叙述方面也不遗余力。
死亡是余华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一个存在主义的主题。
死亡从普通意义上讲有两类:
正常死亡(自然生命的正常终结)和非正常死亡(自然生命的非正常终结)。
把非正常死亡作为考察对象来看,有两种情况:
他杀(生命被终止是源于外界力量)和自杀(生命被终止是源于自身内在的力量)。
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更多的是关注非正常死亡中的他杀现象(有时也包括病亡和失踪等)。
《现实一种》中山峰、山
人的生存困境时,首先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条件提出自己的质疑。
正是从这种质疑出发,导致了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这种苦难意识主要有几种表现形态:
1、对历史的重新审视。
余华以过人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对历史残暴的一面予以揭露,对粉饰历史的行为予以批判。
他的作品虽然缺少了诗意,却多了几分赤裸的真实。
他对历史阴暗面的过多关注,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正视历史。
2、对传统文化的颠覆。
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长幼有序,亲人之间是不能乱伦的。
可在〈世事如烟〉中,孙子与祖母同睡一张床,还使祖母有了身孕。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承担了双重反叛的形象,作为祖父孙有元的儿子,他不但不孝顺,反而想方设法折磨自己的父亲,盼望他早死。
作为“我”的父亲,他对我漠不关心,还把我当作内心暴力欲望的发泄对象。
3、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思考。
《现实一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
母亲不关心儿子,儿子不关心母亲,哥哥不爱护弟弟,弟弟不尊敬哥哥。
在《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竟然想方设法算计别人,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
在余华的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思议,亲人之间形同陌路,家庭内部危机重重。
4、对社会强势群体的批判。
在《活着》中,有庆的死耐人寻味。
我们如果探讨有庆他抽血过度而死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在于医生对县长权力的敬畏,而忽略了弱势群体的生命价值。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每次卖血都要送礼给医院的血头,血头没有什么政府官衔,但是他们仍然是那个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手中握有决定谁卖血的权力。
余华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呼唤着公平与正义。
余华凭借其对苦难的深刻感知能力,对苦难进行了不同凡响的叙述。
从他早期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他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要的著作〈许三观卖血记〉,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余华所描述的苦难,其表现形式是在不断嬗变的。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将余华所叙述的苦难的分为两大类:
抽象的、行而上的苦难和实在的、行而下的苦难。
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绝大部分表现的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苦难。
这种苦难非常具有神秘感,令人难以捉摸。
在《世事如烟》这部小说中,父亲把女儿一个个卖掉;6在江边与无腿的人三次邂逅;接生婆为一个怀孕的女尸“接生”;死而复活的司机要求为他娶亲;祖母和成年的孙子同床而眠,并且怀了孕……道德沦丧,梦魇横生,生命处处受到压抑、摧残和戕害。
然而,这些苦难是怪诞的,不可理喻的,所有的一切都如梦如烟,永远都找不到理由,永远都不明真相。
而到了九十年代的《活着》中,苦难消失了它的神秘感,消失了它的行而上性质,而只有了炊烟般的气息,它实实在在地和大众的苦难发生了联系,走到了一起。
主人公福贵经历的苦难都是有其现实世界的理由和动机的,福贵被拉壮丁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有庆之死是由于给县长夫人输血,更始由于医务人员唯官是从的“官本位”文化思想的作祟;家珍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因为饥荒,苦根吃多了豆子而活活胀死……福贵所遭遇的每一次苦难都是有现实依据的,并且能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同情。
形而上的苦难与形而下的苦难,概括了余华苦难叙述的所有类型。
我们更进一步的探究这两种苦难类型的根源,则会发现,这一切都和余华与现实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关。
余华与现实并不是和睦共处的,而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对抗。
当他与现实紧张的时候,他的作品里叙述的苦难是形而上的、抽象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华正是与现实的紧张相处时期。
在当时他作品已经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可,以达到超越同辈作家的目的。
另一个方面,当时中国大众正从“文革”的历史大灾难中中走出来,集中精力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而余华对身处的现实环境表示怀疑,他看到了社会犯罪率明显提高,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认为这和大众传媒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信息大相径庭。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丰富,余华对现实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现实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过尔立之年的余华开始了对现实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也许是看的多了,听的多了,经历的风雨多了,看惯了希望的失落、理想的破灭,他的心态反而平静了、从容了,不在意气用事。
对待现实的态度,不再走极端,不再像过去那样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是冷静的思索,客观的批判。
现实毕竟是有两面性的,我们既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
对待正面,我们应该褒奖、歌颂;对待反面,我们应该揭露、批判。
余华说:
“一个作家总是要表达他的理想,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一样,有屁用。
当然还有一些现实因素的作用,我现在没有工作,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可能和任何人发生直接冲突,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变的美好起来了。
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种疲于奔命、在工作中老是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艰难的状况下才会发出对世界的仇恨,而我现在确实感到现实很美好……[3、余华《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三期8页]这是1996年余华的心声,它表明余华和现实的关系开始变得缓和多了、融洽多了。
此时的余华在中国文坛大有名气,在外国又获得了多项文学大奖,与现实已经没有冲突了,他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可以和现实和平共处了。
他笔下的苦难不再是抽象得难以理解而是使人感到实实在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伴随着苦难类型的不断嬗变,他对苦难意识的阐述也在跟着发生逐渐的变化,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彰显苦难
余华说:
“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
“[4、《活着》前言,《活着》第一页,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余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创作时的一个重大发现。
在这一时期,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的中国大众,经过短暂的思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而此时的余华,正在海盐的一家医院里干着令他索然无味的牙医工作,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与勤于思考的性格,在业余时间思索人性的美丑善恶。
在沉默的思考中,余华对所处的现实开始表示怀疑的态度,不在认为现实是美好的,而是丑陋的,现实是不真实的,而是虚假的。
于是,作家以先锋的姿态,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进行颠覆,对传统的日常生活诗意进行消解,转而着手建构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虚构的的精神世界,不再充满善良与美好,不再弘扬淳朴与高尚,不再传播文明与思想,弥漫与我们眼前的,充塞于我们心间的是那种铺天盖地的血腥的图景,血流成河,尸骨横陈。
这个虚构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暴力与血腥,充斥着荒谬和可笑,充斥着狡诈和阴险。
余华的初期创作,先锋的姿态锋芒尽露。
我们试看《死亡叙述》:
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冲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
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
那过程十分简单,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
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的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
当我还来不及用手去捂住肠子时,那个女人挥着一把锄刀朝我脑袋劈了下来,我赶紧歪了一下脑袋,锄头劈在肩胛上,像是砍柴一样地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
我听到肩胛骨断裂时发出的“吱呀”一声,像是打开一扇门的声音。
大汉是第三个冲过来的,他手里挥着一把铁搭。
那女人的锄头还没有拔出时,铁搭的四个刺已经砍入了我的胸膛。
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
而两旁的铁刺则插入了左右两叶肺中。
左侧的铁刺穿过肺后又插入了心脏。
随后那大汉一用手劲,铁搭被拔了出去,铁搭拔出去后我的两个肺也随之荡到胸膛外面去了。
然后我才倒在了地上。
我仰着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望四周爬去。
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
我死了。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近乎麻木,失去了知觉,只是保持“零度情感”对暴力与血腥进行陈诉,将人性的残忍进行夸张的暴露,达到将苦难彰显到极至的目的。
在这个凶杀的片段中,我们没有看到丝毫善良人性的闪光,我们接触到的是没有情感的近乎动物之间的猎食行为。
余华在这里将人性的丑恶张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使我们看后仍然心有余悸。
在这一时期,余华以一种创作的理念刻意的带给我们惊悚,使我们去深度的体会那种人性美缺失后人性恶支配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后果。
在《祖先》中村民们面对施暴的场合,人人激情澎湃,奋勇向前,不但将祖先乱刀砍死,还将他分而食之。
余华在这里将“祖先”置换到了人的位置,而人则被置换到了动物的角色。
人在某个时候,连畜生都不如,人性比兽性更加残酷。
在《古典爱情》中,人吃人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为了保持肉的新鲜,竟然不把人杀死,而是从活人身上割肉下来卖。
人吃人的事情在古代确实有过,余华在这里将它夸大,进行历史的重现,将人等同于畜生,人性的凶残可见一斑。
在《现实一种》中,哥哥的儿子摔死了弟弟的儿子,弟弟踢死了哥哥的儿子,哥哥又用更加残忍的手段将弟弟谋杀,最后弟媳又盗用嫂嫂的名义将哥哥的尸体捐献给医院,让他死无全尸。
人物一连串的死亡,我们从中看不到点滴人物的眼泪,感觉到的一系列的复仇行为。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亲情的严重遗失,让我们不寒而栗。
疯狂的复仇使我们毛骨悚然。
人性的善已离我们仿佛有几亿光年的距离,而人性的恶则如影相随,不离左右。
在《一九八六年》中,历史教师在精神错乱的支配下,疯狂的对自己进行残忍的自戕,动用历史上存在的各种酷刑对自己进行可怕的肢解。
人性又被余华置于历史的时空中进行一种纵向的对比参照,丑恶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从古至今,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直宣扬人性本善。
可是人性本善,为什么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时常充斥着暴力,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
余华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撕去人性本善的面纱,正视人性丑恶的一面。
余华为什么要这样偏执的展现人性丑恶?
我们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
余华一意孤行的去彰显苦难,我认为这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历史时间)、个人童年生活、工作经历、阅读视野有关。
历史因素。
余华生于1960年,童年时代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揭发、批斗、斗争……这些充满了暴力意味的革命性话语,开始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略知世事的孩子面前。
他无法理解人们那种癫狂的理想,只能从亲眼目睹的许多残酷的杀戮、各种各样的迫害中,去感受成长过程中的迷茫。
直至余华长大之后去回想那段苦涩的岁月,感慨良多,浮想联翩,间接的加深了他思想的深刻性,对苦难有了个性的理解。
当时,“大字报”是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攻讦的最有力的武器,他被人们大肆利用,张贴在每条大街小巷。
它们一片鲜红,一层覆盖一层,每隔一会儿就有新的出现,其刷新的速度几乎不亚于如今网站上的新闻页面。
余华在当时阅读资料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开始注意了街头小巷的“大字报”。
无独有偶,这正好引领了余华的文学之路。
余华曾说:
“……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侯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小时。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都得到了极度的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5、余华:
《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大字报就是一种暴力文学,余华在这种文学模式的影响下,其前期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捩气,也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再者,正如余华这段话中所言,大字报上的人他“都认识都知道”,一方面自己眼见过的熟悉的人,一方面是暴力文学对人的改编,两相比较,幼小的余华自然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他过早的体验到了人世的荒诞性。
荒诞的人性就给暴力的产生制造了一个无需理性的理由,人在荒诞的支配下,使用暴力已成了一种常态。
童年生活与工作经历。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写作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童年记忆中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最初获得的人生经验,它的新奇特征、鲜亮程度、陌生化效果,都会以异常丰实的景象存留于他的内心中,并构成他的潜在的记忆资源。
余华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医院里游荡,所有的鲜血、死亡、病痛的哀号、亲人的绝望……都像一张张图片存储于他的内心。
这所有的一切成了他日后重要的写作素材,也是我们考察他为什么迷恋暴力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余华曾毫不避讳地认为:
“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
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侯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
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衣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着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
当时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
”[6、余华:
《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19岁的余华成为了一名牙医。
每天都有面对血腥的场景,还要不断的处理各种手术过程。
这种整日与淋漓鲜血打交道的工作经历,成为了余华描写血腥场景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
在写作《现实一种》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应用。
余华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有过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拔牙这个工作对我写小说影响很大,因为我很小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
……所以我前期的小说的血腥气比较重,也与那个有点关系。
而且,当了牙医之后,我还曾经去继续那个血淋淋的事业。
”[7、余华:
《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余华的这种特殊经历,给了他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叙事资源,为日后叙述血腥、暴力、场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视野。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学艺术开始解禁。
外国的各种文学理论如现代派理论、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和一些意识流小说、唯美伤感小说陆续传入中国。
余华这个文学爱好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选择了卡夫卡、川端康成、马尔克思、福克纳、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模仿创作对象,进行反复揣摩,逐渐培养了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可以说,阅读的启发在余华的早期创作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余华在研究川端康成的写作技法上发现了他注重细节描写。
余华学以致用,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非常注意细部的叙述,尤其是在叙述暴力的施展过程中,将施暴的过程放大。
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力的沉醉同样使余华痴迷,如果我们将血腥施暴的细节叙述与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叙述方式上的某些同样的思维特征。
二忍受苦难
在经历了七八年的中短篇写作训练后,余华的写作技巧已日臻成熟,逐步的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思路,开始按部就班的着手长篇小说的尝试了。
随着《在细雨中呼喊》的最后定稿,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了。
这部小说是余华创作潜力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是创作主体自身的一次艰难嬗变——由冷静、强悍、暴烈向温暖、缓和、诗意转移,由人性恶的执迷陈诉转向人性善的深情呼唤。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已不在叙述凶狠暴力的凶杀场景,读者也很难嗅到心惊肉跳的血腥味。
余华已另有所爱,对苦难的彰显退居其次,着重于突出人物对苦难的惊人的忍受能力。
同时余华对人类苦难的的承受载体作了转移,不再以前期的肉体受苦为主要载体,而转向以精神为受苦的主要载体。
作品中人物受精神的折磨是其受苦的主要原因。
《在细雨中呼喊》它以一个江南少年孙光林的成长经历作为主要的叙述主线,通过双重叙述者的分分合合,展示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中的孤独、迷茫、痛苦和无助,同时又通过时间的自由穿梭和往返更替,在孙光林的成长主线中,不断融入了父辈(包括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和母亲,养父母王立强和李秀英等)、祖辈(爷爷孙有元)等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苦涩命运,折射了几代人精神上的各种痛楚。
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孙光林的受难是通过心灵的恐惧和战栗来表现的。
幼小的孙光林一开始就被置身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黑夜里独自聆听来自远方的凄惨的哭声。
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黑夜里久久得不到人间的回应,孤独与凄凉的氛围弥漫在整个故事的始终。
在故事中孙光林似乎是个多余的人,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将他像废物一样抛弃。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灵找不到温暖的归宿,他渴望亲情的甜蜜,友情的温暖,可现实的处境总与企盼背道而驰。
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在毫无道德感与尊严感的父亲孙广才的暴力统治下,他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困顿之中。
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均无亮色可言也毫无希望之说。
暴力、恐吓、辱骂、如影相随。
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镇,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当养子。
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
从此远离那个暴力、恐吓维持下的家庭,开始新的幸福生活。
可事实并不如此,在王家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孙荡体验到了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快乐,可好景不长,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他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甚至连家也没有了。
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孙光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次回到了南门。
重回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番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
于是他选择以游离的方式希冀获得更多的安全。
可这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他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
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风波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寂之中,甚至被排斥在家庭之外。
这种不受关注与重视的情态,这种被漠视与忘却的对待,使孙光林内心的恐惧与战栗无限增加,性格上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与内敛。
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神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冷漠感受,都表明了他在那个成长的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以孤独与敏感的方式,承受来自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的精神折磨。
事实上,除了孙光林的苦难成长之外,作品中还有许多人物的经历体现着受难这一主题。
年轻漂亮的冯玉青因为遭到王跃进的抛弃,从负气出走到后来一步步地沦为暗娼;父亲孙广才因为弟弟孙光明救人而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雄父亲”的称号,结果不但梦想没有实现,反而因治安事件而拘留;因为青春期性本能的骚乱和冒险,苏宇被处以劳教;由于妻子的多病而导致了王立强的婚外情,结果却被人们无情的跟踪和捉奸,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因为母亲的死亡,再婚后的父亲无情地将年幼的国庆抛弃于世;在母亲冯玉青被劳教之后,无家可归的鲁鲁只好在监狱外流浪;音乐老师因为与学生曹丽发生关系,从此毁灭了自己的一生;在没有生理教育的年代,孙光林、苏宇、郑亮等同学整天因为手淫而惶惶不可终日……余华在这一系列的受难事件中,使小说人物有了某种自觉的受难意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忍受生活中没有预告的苦难折磨。
如果说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里,余华笔下的人物忍受的苦难都是形而上的、抽象的,那么在《活着》这部作品里人物忍受的苦难则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我们在《活着》这部作品里能够看到人物如何去忍受苦难,看到人物生存的超强韧性,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人活着的不易。
余华在《活着》韩文版前言中说:
“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无法埋怨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
千钧一发。
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重压,它没有断。
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在这里,余华给活着下了一个定义,顽强地忍受生活中不期而遇的苦难。
因此,《活着》就是关于生活中如何忍受苦难的书。
福贵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的他在女人的胸脯上找寻快乐和眼泪,在他们的肩膀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心竟摇荡地体味生命的激情和冒险。
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之后,当这一切都被他轻而易举地毁掉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沉重代价,也同时看到了苦难对他的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自此以后,所有的厄运开始紧紧地追随着福贵的脚步,并毫不含糊地夺走了每个与他相依为命的亲人的生命,一次次将他逼进绝望的深渊,使他成为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力自拔的鳏夫。
只有与自己影子似的象征物——那头叫富贵的老黄牛相依为命了却残生。
但是,福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却始终相信:
即使生活是最为悲惨的,即使命运是最为残酷的,自己也应该鼓足勇气和拼足力量熬过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福贵平静的直面苦难,面对汹涌而来的苦难他以平静如水的心态咀嚼人生的苦难。
在《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我们看到余华一直在强调人如何去忍受苦难,承担生命中的诸多不幸,在创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悲悯的情感已渗人文本中,对人物的命运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
如果我们探究其由彰显苦难到忍受苦难的原由,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1、注重内心真实。
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通常是以迎合常识性生存状态为起点,即一切话语形式(包括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命运)都必须遵循世俗性生存现实,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性。
这种真实性,使得作家在发挥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受到无处不在的理性钳制,客观现实的钳制,一切艺术的真实被客观化。
创作主体的审美目标是与现实世界高度吻合,因此,作家的想象和自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
而现代作家的自由禀赋和创造欲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这种现实生活的常识性逻辑,他们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也都要求他们必须对一切常识性生活逻辑进行义无返顾的超越和反叛。
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内心真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