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docx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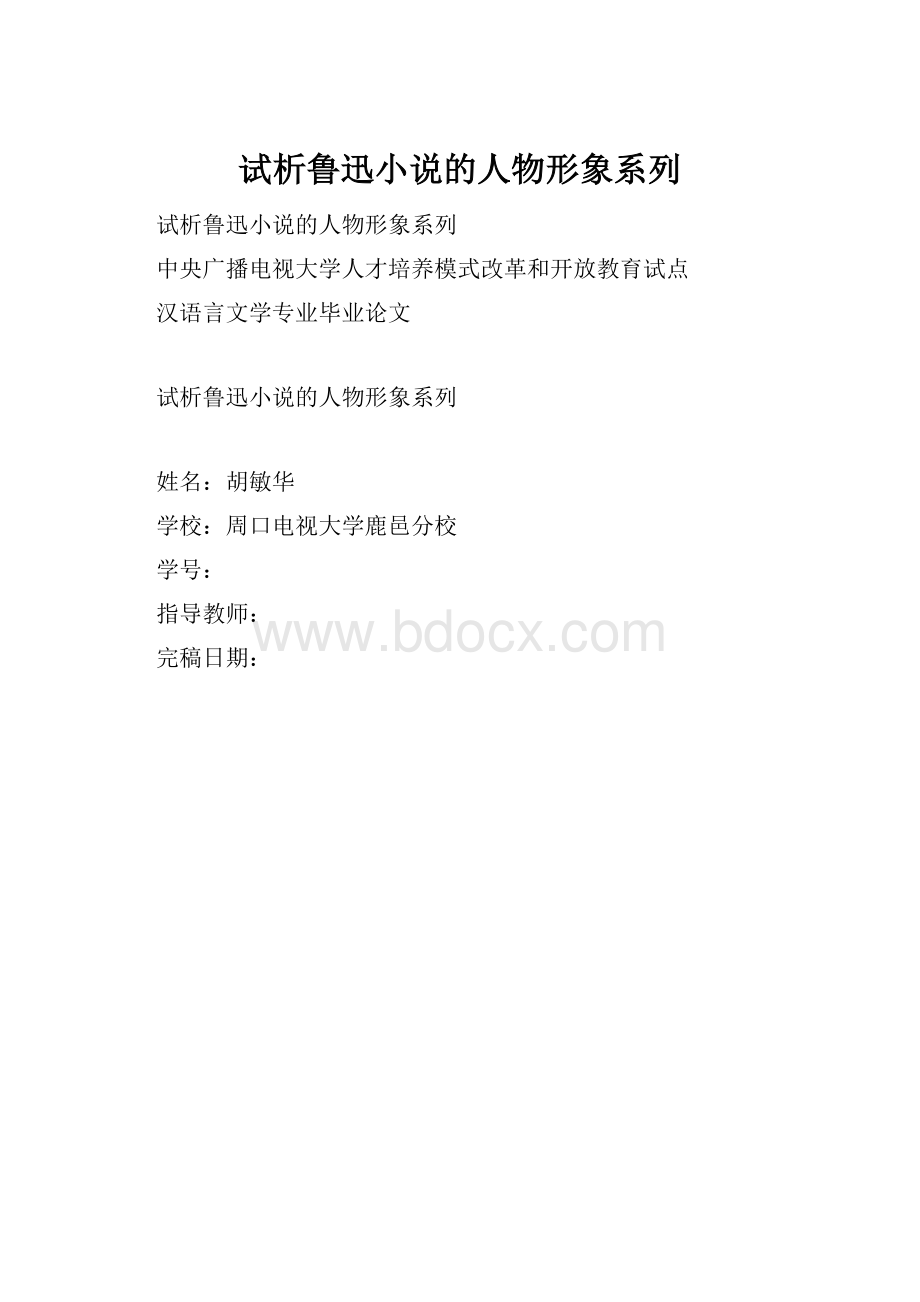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
姓名:
胡敏华
学校:
周口电视大学鹿邑分校
学号:
指导教师:
完稿日期:
己找理由: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在这里用“窃”取代“偷”妄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越辩越黑,越辩越显得可笑。
难怪酒店里的看客们总拿他寻开心。
从一般意义上说,孔乙己受雇于人钞书换一碗饭吃,将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偷走当然是不对的,挨打活该。
但这只是一种简单的道德评判,而不是历史的分析,文学的读法。
如果联系作品的思想主题,结合全文看待孔乙己这个人物,他的“偷”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制定出来的规范封建时代读书人的一个美丽的“陷阱”,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通向飞黄腾达的惟一通道。
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驾驭读书人的伟大“发明”。
科举考试给封建社会许多读书人带来的极度悲喜,在初中课文《范进中举》一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孔乙己的生活的时代已到了科举制度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逐渐被社会所抛弃的价值观念却仍被孔乙己这样的人顽固坚守着,于是悲剧必然发生。
这位在科举时代连秀才也中不了的读书人,又不知道谋生,把自己弄到将到讨饭的地步,这本来已经够悲惨了,却声称自己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以“清白”而高人一等。
而另一方面,他却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而被人充当无聊生活中的“笑料”。
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人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和荒谬性,并展开对那个社会合理性的深刻质疑。
让我们根据以上理解再回到文本。
由于孔乙己“偷书”的恶习,后来竟没有人叫他钞书了,迫于生存,他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了。
作者在这里使用“免不了”“偶然”这样的字眼,这是否可理解为是对孔乙己命运一定程度上的同情呢?
再注意下面的转折:
“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
”这说明孔乙己拥有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行:
诚信。
这正是“别人”所比不上的。
而他给儿童分吃茴香豆,则证明他又拥有另一种可贵的品质:
善良。
当大家看见他脸上的新伤痕而推测他又偷了人家的东西时,他“睁下眼睛”“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这字里行间也许又暗示着他心灵深处的一点尊严:
羞愧。
确实,谁愿意当小偷呢?
哪怕是他教人写“茴”字的行为,我们也不能全盘否认,虽然迂腐了点,但也可归为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性:
好为人师。
既然他有这么多的优点,读者自然也就会想:
在他的这些优点面前,他的那点偷窃(并且是偷权贵者的财物)品行不算什么。
从这里看出,就是作者本人,当他把孔乙己的偷窃行为置于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和这个人物全部品性中去考察时,作者表现出了踌躇的态度:
既否定又同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
这无疑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开掘了作品的思想的深度。
所以,当我们把孔乙己的“偷”放在小说反封建科举制度和揭露国民冷漠无情这一主题下来思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鲁迅在小说中并非重在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谴责,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反思:
第一,孔乙己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受害者,他之偷书是迫于无奈,迫于生计;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者才是逼迫孔乙己行窃的幕后黑手;第二,孔乙己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廉耻之心的偷窃者,即是说他并非一个无道德品行的人,而是一个讲信用不赖账有爱心热心肠的人,他的偷窃行为与他的整个为人相比,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那个病态社会恰恰不需要他的善良、诚信、爱心,他的偷窃倒成了致他于死地的原因;第三,鲁迅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揭出了孔乙己的偷窃行为,但这些看客们并没有成为一种正义力量的象征,我们也并不觉得鲁迅笔下的看客们对孔乙己偷窃行为的严重愤慨,而是拿孔乙己当成下酒的“佐料”。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批判国民性的主题。
二、受封建等级思想毒害的底层农民──偷碗碟的闰土
这一细节出现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和母亲也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
从这一节我们看到,说闰土偷碗碟是杨二嫂的指控,至于是否真的是闰土将碗碟埋在了灰堆里,这是一个谜,自从作品诞生后就留下的一个谜。
这同时成为上个世纪50年代有名的“谁是小偷”之争的起因。
有人认为在灰堆里埋碗碟的就是闰土,他就是小偷:
通过前后两个闰土(少年时代与中年时代)的对照的描写,鲁迅就把一个因为受到生活过分的重压,而变成沉默、自卑、私心,(在灰堆里藏了十多个碗碟)甚至麻木的当时中国农民代表之一种的形象,真实地也批判地表现出来了。
但当时出于一种普遍的阶级立场的考虑,大多数分析者都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作为被压迫者的闰土,鲁迅在作品中对他是寄予深切的同情,他不会是小偷我们也不应该把他当成小偷,否则就是给自己阶级的脸上抹黑;而杨二嫂恰恰是庸俗小市民的代表,鲁迅对他的态度是讽刺和嘲笑。
为此,有人提出,说闰土是小偷,那是杨二嫂的诬陷,她自己才是真正的小偷:
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闰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以及“我”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是可以判断在灰堆里藏碗碟是杨二嫂为了贪图便宜而栽诬闰土的,关于在灰堆里埋碗碟的事,便可断定不是闰土干出这种事来,其次是因为“我”明明允许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况且,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讲。
杨二嫂是一个市侩气重的小市民,……从字里行间,我们看到“我”对杨二嫂的态度,始终充满着嘲笑和讽刺。
50年代各套教科书普遍采取的策略是不追究:
既然这是一桩难以破解的悬案,就没有必要也没办法去解决。
所以有的教科书主张:
“……应把学生的爱憎从个别人物身上转到整个社会制度上去,因为这种事情在旧社会是常常发生的普遍现象”。
这种引导学生通过阅读一部作品或分析一个人物进而憎恨一种社会制度的教学方法,在那个年代里的语文教学中很常见。
姑且不论偷碗碟者是否闰土,这一形象都可归入鲁迅小说中塑造的封建思想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受害者──社会底层劳动者人物形象系列之中。
先看闰土,鲁迅是把他的少年与中年对比着来描写的,写少年闰土的天真可爱、无忧无虑、纯朴自然,写闰土中年后的辛苦麻木、挣扎求生、等级观念。
母亲说他现在的“境况很不如意”,他自己说生活“非常难”,而这一切,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灰堆里埋几个碗碟是符合生活逻辑和闰土当时的生活境况的。
而另一方面,通过小说情节可以看出,杨二嫂固然是个小市民,充满市侩气,但她贪小便宜一般都是直接伸手要,而不顾及什么面子: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
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还有两个细节又印证了她的这一性格特点:
往外走的时候,当着“我”和母亲的面顺便将“一副手套塞在裤兜里”;待她告发了闰土埋碗碟的事之后自己奖励自己,又顺手抄走了“狗气杀”。
闰土则始终没有主动开口向“我”要东西,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看不上“我”家的那些东西,而是有着其他的心理原因。
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想:
大概与他觉得自己是“我”小时候的伙伴而不好意思开口有直接关系;而“我”虽然同意闰土“自己去拣择”搬不走的东西,但在他所选的几件东西中,并不包括碗碟。
但我们注意,小说中写到这么一句话:
“他又要了所有的草灰……待我们启程的时候,他用船来载去。
”所以后来杨二嫂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去”的推论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并未写到其他来“我”家要东西的人,所以,闰土的“作案”嫌疑最大。
我们倒不必照顾闰土因为属于被压迫的下层劳苦人物,就断定他一定就不会“偷”人东西。
实际上,鲁迅写上这一笔,其目的正是要达到人物性格塑造的多面性。
并且,即使是闰土藏了这些碗碟,也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同情和对社会的反思。
所以,从道德评判、思想意义和艺术塑造三个不同角度理解,其内涵也就不一样。
三、被封建统治者逼得无路可走的无赖雇农──偷萝卜衣物的阿Q
如果不是因为秉性问题,一般来说,之所以发生小偷小摸的行为,要么是因为贪小便宜,要么是因为穷,所谓人穷志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面分析的两种形象都可以归结为“穷”:
孔乙己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只好偷人家的书籍纸张笔砚去卖(但也有人说他是因为仇恨而心理失衡导致的报复行为,此说有些牵强);如果闰土确实是偷了碗碟,那也是因为他家里穷,穷得连碗碟都买不起。
阿Q去净修庵偷萝卜,是因为自从他调戏吴妈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打短工了,出现了“生计问题”:
没了饭吃,饥不择食去偷萝卜;而进了城一开始是给丁举人打工,后来由于好吃懒做,跟着别人一起做起了小偷。
所以,阿Q的两次“偷”,性质不一样,前一次偷萝卜,虽表现出他极度的无赖: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
”“这是你的?
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你……”却让人感到无尽的辛酸:
对于赵太爷之流来说,生萝卜哪里用得着偷,生萝卜是人吃的东西吗?
对于一般穷人来说,萝卜可能也不是充饥的好东西;但对于阿Q来说,他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想此“下策”,干此“勾当”。
平心而论,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哪怕是在一个稍微有一点人情冷暖的地方,拔地里几个萝卜吃,主人也大可不必“上纲上线”说人家是“偷”。
谁让阿Q生活在未庄而不生活在平桥镇呢?
谁让他得罪小尼姑而不碰上六一公公呢?
所以,阿Q偷萝卜的故事,与其说是在显现他的无赖本相,倒不如说是在揭示世态的冷酷,探究阿Q出现“生计问题”的社会根源,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深思。
而阿Q到城里当小偷,则与词典上“偷”的含义更为接近:
好吃懒做与游手好闲,交上几个“道”上的朋友,促使他将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
他回未庄向看客吹嘘自己的“壮举”,作为自己见过世面的证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人觉得可笑又可气。
但当我们掩卷沉思,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是封建统治者把这样一个“真能做”的阿Q逼上了做“小偷”的路上。
人们常说,孩子不会有错,责任全在父母;我们同样可以说,百姓的违法犯罪最终应归咎于社会。
阿Q的那些小缺点可以原谅,但赵太爷之流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该枪毙的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长衫人物等而不是阿Q王胡小D,但恰恰是前者又成了新政权的投机者和把持者。
没有一场全面而深入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推翻封建政权,阿Q们的命运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悲轮回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偷”及其遭致的悲惨后果,同样表现的是深刻的反封建思想革命主题。
四、未经封建思想污染的少年儿童──偷罗汉豆的双喜们
小说写道,几个小伙伴在看戏回家的路上,本来就对戏很失望,觉得无聊,且摇船摇得既乏且饿,于是想起了偷东西吃。
研究文本发现,这次“偷盗事件”的策划者是一个名叫桂生的少年,他说,“罗汉豆正旺相,柴火又现成,我们可以偷一点来煮吃的”。
而响应并采取行动的是大家,里面突显了一个叫双喜的少年,他提议不仅在阿发家偷,而且去六一公公地里偷。
所以,这是一次“团伙作案”。
但我们要问,双喜们的行为是小偷小摸吗?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与其这么说,更不如说是少年的一种游戏行为。
理由如下:
在这个“作案团伙”中,有一个名叫阿发的小伙伴,当别人问是偷他家的还是六一公公家的时,他似乎没有什么犹豫地说:
“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可见在阿发的心中,并没有成人心中的所谓自家的和别家的之分(即无私心);阿发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如果是他的娘知道了,一定会说他傻,在许多成年人看来都是这样:
谁会带着别人偷自家的东西呢?
而在阿发的观念中,罗汉豆只有长得好和不好之分,而没有是张家的还是李家的之分,好不好是他们判断偷谁家罗汉豆的惟一依据。
从这一点说,他们的所谓“偷”与一般意义上的“偷”的含义就很不一样。
这正说明他们有着一颗天真纯洁的童心。
六一公公事后对他们和行为表现出来的态度,让小伙伴和读者都感到十分意外:
六一公公不仅没有责怪他们,反而表现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情绪,作出了另一种“道德评判”:
“豆可中吃呢?
”
我又点一点头,说道:
“很好。
”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来,将大拇指一翘,得意的说道,“这真是大市镇里出来的读过书的人才识货!
我的豆种是粒粒挑选过的,乡下人不识好歹,还说我的豆比不上别人的呢。
我今天也要送些给我们的姑奶奶尝尝去……”这令人想起
《故乡》中少年闰土给年少的“我”所讲的那一幕:
“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
”这句话可以作为双喜们“偷”罗汉豆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社戏》是节选,联系全文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把他成人以后在城里看戏与儿时的看戏对比着来写的,写成人世界的污浊,童年世界的清洁;写城市生活的无聊,乡村生活的纯朴,从深层次上表现了一种反封建的主题。
通过以上三方面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这里的“偷”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之间的小偷小摸,而是表现了一种极为融洽的邻里关系,表现了未经污染的农村纯朴自然的民风。
作者塑造的一是一群未曾受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毒害的自然人,这群自然人不仅包括未长大成人的双喜们,也包括年老的六一公公们。
这一世界与鲁迅在其他作品中表现的世界(如未庄、鲁镇、吉光屯等)形成巨大的反差。
参考文献:
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徐中玉著,上海自由出版社1954年版
④《激动人心的优美诗章──〈故乡〉──兼评〈故乡〉分析中的若干错误论点》,箭鸣撰,《长江文艺》1956年第9期。
⑤《北京市初级中学课本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北京市教育局中小学教材编审处、河北省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合编,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