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蓄水后的N个百年不遇.docx
《三峡蓄水后的N个百年不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峡蓄水后的N个百年不遇.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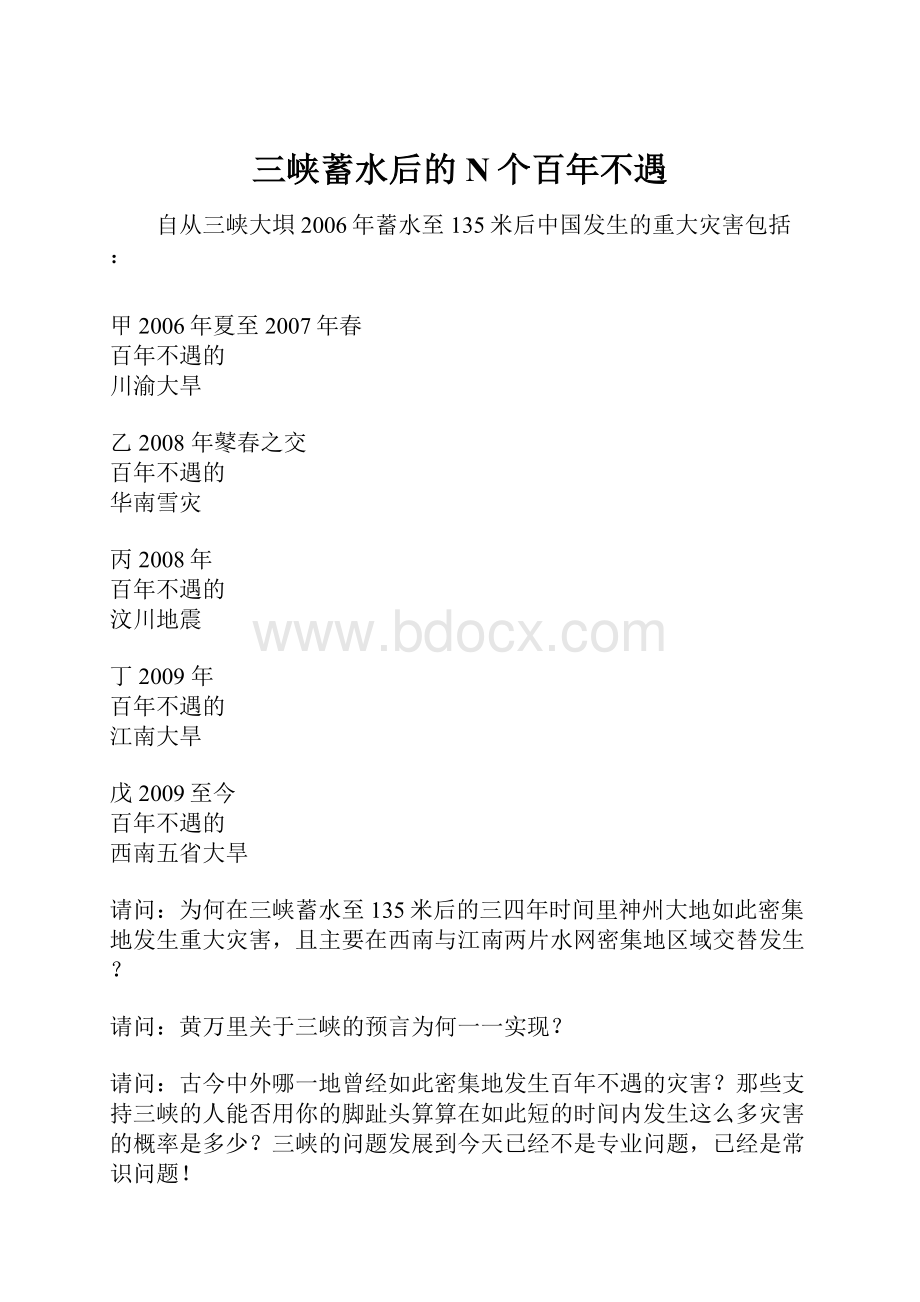
三峡蓄水后的N个百年不遇
自从三峡大垻 2006年蓄水至135米后中国发生的重大灾害包括:
甲 2006年夏至2007年春
百年不遇的
川渝大旱
乙 2008 年鼕春之交
百年不遇的
华南雪灾
丙 2008年
百年不遇的
汶川地震
丁 2009 年
百年不遇的
江南大旱
戊 2009至今
百年不遇的
西南五省大旱
请问:
为何在三峡蓄水至135米后的三四年时间里神州大地如此密集地发生重大灾害,且主要在西南与江南两片水网密集地区域交替发生?
请问:
黄万里关于三峡的预言为何一一实现?
请问:
古今中外哪一地曾经如此密集地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
那些支持三峡的人能否用你的脚趾头算算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多灾害的概率是多少?
三峡的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专业问题,已经是常识问题!
请问:
为何当局不曾给予反对三峡的黄老平等对话的机会?
压制黄老的声音意味着什么?
若天下人良知尚存,就不该对黄老的声音置若罔闻,就不能漠视对三峡的合理质疑!
* * *
附文三篇
文一:
黄万里:
三峡工程祸国殃民,永不可修
文二:
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
文三:
黄万里毕生反对三峡工程 预言大坝终将被迫炸掉
文一:
黄万里:
三峡工程祸国殃民,永不可修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颤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九十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二十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
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
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
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
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
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
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晚年的黄万里仍然不改初衷,从对千秋万代负责的高度看治理江河。
黄万里后来写道:
“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
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
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Canyon,现通译为“大峡谷”)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
……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
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
黄万里对《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作者赵诚讲过,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测量,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曾有三人在风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
这样的悲剧使他“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
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
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
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
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
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他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这就是:
四川盆地一带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
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
我爸关于长江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1986年登在《华东水利学院学报》上。
那时关于三峡工程,还没有拍板定案,还可以冒出些不同声音。
寄出无数封信没有回音
1985年3月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一年,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在全国人大通过,中共十四大刚结束,黄万里以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编者注:
如网友有此稿件来源,敬请提供)等论稿。
他认为:
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
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
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
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
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他先后三次致书小布什,指出:
“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
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
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
在信中,黄万里还附上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是三峡是李鹏坚持要上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决策者深刻反思总结。
而“长官意志”为什么主上呢?
作家郑义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编者注:
如网友有此稿件来源,敬请提供)文中分析说:
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因为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
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
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
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
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
郑义的说法并不是无端揣测:
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涉嫌贪污钜款而失踪,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当局公布什么,他才了解什么。
在与对方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算。
1988年长江大洪水后,身患绝症的黄万里申请讲课。
他特地穿上白西服以示郑重。
这是他的教学生涯中最后一次讲课。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三峡,他在请教一些专家时,
“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
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在局外焦灼地关切长江的命运。
李锐在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披露,黄万里同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
“钱正英春节曾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
黄万里回忆:
在三峡大坝开工前,写了三封信。
大坝开工后,又写了三封信——给上面一共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
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
他不仅接着写,还向监察部去申诉,对决策者拒不答复人民来信,他要讨个说法——虽然他得到的,还是不答复!
他还一度诉诸法律。
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
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
他多次跟学生谈过:
“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
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甚至激愤地对他说:
“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无人出版他的著作
黄万里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在亲友中散发。
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但黄万里没有资格在那里出书。
二OO一年黄万里九十岁寿辰前,经领导开恩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课题费中凑了钱,为黄万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十六开本、三百六十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五百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一九五八年的得意门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
他自知沉屙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起来。
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
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觉得话没说完,遂索纸笔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
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话。
一贯主张疏导的黄万里,为何提出“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对如何拦得严密还想得那么细?
记者读到此,百思不解。
后来读到郑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
“三峡钜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
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
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他生病时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去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
“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
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
黄万里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
黄万里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
尚待时间来证明。
这时间将有多久?
* * *
文二:
黄万里给钱正英的信
【据《财经》2003年9月5日载,“8月19日,新一届国务院举办第一次学习讲座,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主讲《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和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时指出,国务院组织学习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法律和现代管理等知识,是一项重要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
”
这里公布于众的,是已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1988年6月25日致钱正英的信。
在信中,作者特别提到与当前政府这一由总理主持的“学习讲座”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政府决策人与专家,以及“积有研究并能铮铮发言”的专家与“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的判定。
黄教授遗文有机会发表于今日——原本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而退出领导身份后,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传授知识的专家——看来不无教益。
下边是原信,信的眉额处有“黄先生给钱正英部长写的信”字样,想来出于负责转递此信的办事人员之笔。
至于钱正英部长有没有收到此信,收到之后又如何处置了,就不是保藏这封信的黄家人和黄先生生平研究者所能知道的了。
】
信件原文
正英同志∶
郑州开会期间,多承招拂,无任感荷!
又承告知,辛白先生为我同族。
返京后经查家谱,载有“元一公生五子,长留句容,次徙湖广,三迁淮安,四由姑苏徙吴江路至崇明西沙黄家村,五随兄而东居嘉定清溪镇。
传十一世至细一公。
”
按元一公为宋徽宗侍卫,北宋亡后南渡,名黄彦,是春申君黄歇的四十一世孙。
元一公传十九世为雪谷公,定居川沙高家桥(高家行)。
传二十七世为我一代,多以钟字排行。
今家谱称“雪谷公家谱”,雪谷以下有氏族详载。
未知辛白先生是否出于嘉定一支?
有便当趋候。
若属同族,则当以宗嫂相称矣。
会中亲见嫂氏精明强干,分析总结迅速;勤劳工作,亲自奔走处理;真是难得的干才,国内少有的女强人。
今余热尚炽,而退为闲职,于国家诚属可惜。
退后还为长江黄河制定规划,足见爱国心切,长戈难歇。
可是私下询问同事,多有不满之辞∶或不满于嫂氏撤消北京设计机构,或不满于独断孤行,甚至在技术上也一切先自决定,命令下属遵行。
若然,则水利方面许多技术性错误,皆由嫂氏一人负责,岂不冤枉?
按负行政总责者,责在执行国家既定政策,技术性决定只能由专业者作出,并负总责,因为他是内行。
可以说,在行政上,外行必须领导内行;在技术上,内行该由自己负责。
外行的行政领导,硬要充内行去领导技术,就不免自找苦吃。
技术内行该由外行来作行政领导,那麼领导除了掌握政策外,该认识哪些内行的事务性知识呢?
下面三项似乎是不可缺的。
这些知识,只要有人讲清楚,一个具有进大学前的知识程度的政治家应该都能接受。
所以一个政治家并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今天可以当外交部长,明天可以当一任经济部门的部长。
国外就是这样。
1)
要知道这一部门中业务的分类及各自的作用,[知]其知识分类和基础学术。
要能领会技术领导的非专业性的技术报告。
要能识别专家和工客(专业出身,却无真本领的冒充专家)。
按我国工界有工客、农有农客、商有商客、学有学客,他们都有一套装扮自己形象的本领,用来欺骗无知的政治家。
一个真正的专家,例如水利专家,他们都是经历过实地测量、施工(坐办公室挂名的不算)设计和规划,又有广博而深邃的知识。
可能只专于一门,但却是老老实实自知其知识的局限性。
领导要从内心出发,真正地尊重他们。
2)
要懂得工程或企业的步骤∶规划、设计、施工、运行。
规划包括某项工程的可行性鉴定。
只用简略的勘测资料就能定出工程的大概规模、造价、效益和经济价值,需要最高的知识。
因为设计代价可达工程造价的3%至3 ,若可行性不成立,就白费了设计。
所以先作可行性考查,定其取舍,可行才进行设计。
3)
工程经济核算的一些简单原理,领导必先懂得,才可能理解可行性报告的内容。
1980年以前水利部一些高级工程师声称,部内从未做过经济核算。
他们不懂得工程本是一个经济问题,未经考核经济的工程,纵使站住没有坍下来,若其经济价值不成立,等于买卖做成了,但是亏本的。
下面是解放后水利方面一些显著的失误,未必是部长个人的错误,但部长应负总的责任∶
一)舍弃了浅层地下水却去鼓励开发深层有压地下水。
在沦陷期间,华北普遍没有手压汲水机,每机可汲深度最多8米的浅层水,灌5亩地。
解放后没有去整顿这些汲水机,却去放款鼓励打深井。
深层有压水的露头远在山西,其承水面积有限,相对汲水地面只有很小一部分,因此供水有限。
深井多了,水位下降了,水易枯竭。
政府不催地方还款,原是好意,而因此人民大量开深井,只要负担些电费,于是全面告竭。
直到五、六年前,水利部才觉察到而停止贷款。
再加上河北省前领导压制人民,禁用浅层水,于是地下水的利用成了既枯竭又浪费的局面。
地下水勘察又归地质部领导,但又不管工程。
水利部和地矿部不相协作,影响地下水的开发利用。
河北省在石家庄开发回灌地下水,在南宫研究地下水回灌并利用卓有成效,水利部竟拒不援助。
须知地面水库与地下水库联合运营,水资源才得尽量合理运用。
二)没有从三门峡坝规划的错误吸取教训。
1955年我在黄河规划讨论会上不同意苏联提出的规划;1957年我反对苏联提出的三门峡坝修建初步计划,说明不仅将来库区淹没,淤积还将上延,今日的开封险境将搬到渭河上。
经过七天的辩论,汪胡桢等同意了先不封闭六个施工排洪闸,但是最后仍照苏联原设计修成。
这也许是政治问题,但人们应该从此吸取教训,分析清楚三门峡坝的错误所在,以免再犯。
从1964年起,不断有论文发表,先说淤积末端到交口(泾河入渭之口)不会再上延,再说不会超过临潼;又历次提出改修三门峡坝的方案。
现在证实了我在1973年提出的相反意见,淤积将毁坏渭河南岸农田∶由于地下水随河槽淤积而抬高,农田盐碱上升,农产将逐年减少。
当我沿渭河观察,看到18岁的少年赤著膊修生产堤,天真壮健可爱;再倾听华县宁东梅公社主任的报告,不觉心酸。
回来成诗一首∶《倾听华县毕家公社宁冬梅主任报告三门峡修坝后灾情》
听罢毕家遭苦害,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更悲。
三门峡坝的错误规划有两点∶
(1)库区地质属地堑区,潼关以上尚在淤积过程中,淹没损失不限于仅仅库区,这以上将继续淤积,盐碱上升,影响将达咸阳。
(2)把减少库区淤积寄托希望在水土保持上,也明知其无效,又以一半拦沙任务放在支流拦沙库上,这是不现实的,至今人们不敢以实践来考查。
人们误以为只要打开泄流洞增加大坝泄洪能力就可将积沙排出。
按未修坝前三门峡以上原是淤积著,再打多少洞,也赶不上没有坝时排沙畅快,淤积总比以前要多。
淤积上延是不可免的。
所以历次改修坝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淤积不上延是可能做得到的。
三门峡坝可以改建好使恢复原来期望的发电功率。
”人们上了当,不研究错误所在,又不肯了好好学习,硬说坝修好了,淤积不会再上延了。
这是欺骗群众,欺骗领导,所以我在大会上说,请大家深刻反省。
三门峡坝这一乱摊子没有收拾好,又去设计小浪底坝,这意味著不管这乱摊子了,让淤积发展罢。
这怎样回答周故总理的叮嘱∶确保下游,确保西安呢?
三)1963年河北省天津市大水,政府事前提出要确保天津和津浦路通车,这原是做得到的。
由于行洪的方法错误,酿成水灾。
若行洪得当,则津浦路以东的损失和人民淹死是可以避免的。
我曾提供政府这次行洪的错误所在。
在中山公园展览的四役拦洪抢救的模型,大肆宣传,竟无人向政府指出其纰缪。
这说明我国防洪知识普遍地低落,也显示了政府的无能。
我作为水利工程的教师,也有责任。
我若缄口不说,就是不爱国。
有人提出了,政府就该考虑,分析清楚,使大家心中有数。
也应惩治指挥的技术负责者。
四)1966年四川汶川渔子溪要开发一个长输水道水力发电站,这在解放后还是创举。
在全国各地可修建的地方很多,由我校水利系张永良书记和张光斗教授率领半系教师前往当地设计。
我听了报告后,就提出这设计有三方面错误。
其中一点是把调节日内用电用水不匀的小水库设在河中输水道之首,这样峰载时的需流45秒立米必须由输水道通过。
照常例若在输水道之末端山头上设一前池作日内调节,则输水道只须通过6.5秒立米,也不需要昂贵的调压塔了。
过水流率减小7倍,输水道可改明渠,工程大大减小,全部土木工程费用可以减少四倍之钜,我系内无人信我的话,反而批判了两次。
后来造完了,我又提出了具体意见,也送到水电部设计施工的单位和水电研究院,没有下文。
第二级开发仍照同样设计,又浪费了四倍的工程费。
我到成都两次演讲,说明长输水道必须设前池于山头,来调节日内流率,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因为西南山头到处有这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发电。
我把渔子溪设计作为一个反面教育,不然国家将重复这种错误,损失将多大!
五)1970年长江葛洲坝的修建是否失误,应好好总结。
这将有助于决定三峡大坝的可行性。
修建这两坝等于否定工程必先通过经济核算,必先考核对于上下游水文地貌的影响。
这方面我已发表过两、三篇文,不赘。
许多人说,假使不修葛洲坝,可以改为修多少中小型的电站,而投资早就回收。
这原是上级的决定,但现在还有争议,说明政府屡次申令要注重经济效益,负责人又不对上争论,政令自相矛盾。
这次可公开讨论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是可取的民主方式,但被邀者多正面人氏,像我这样的反派人氏就要排除。
或许鉴于1957年黄河三门峡之七天争辩,有黄万里一人出席,会就太热闹了吧。
六)1975 年河南两个土坝溃决,死亡人数打破人为水灾的世界历史记录。
黄河开封淹城、汉水决堤也只数万人。
若按今兴安岭失火例,则部长和各级领导难免问罪。
这且勿论,事后便怪洪水设计太小、现行统计法有误,竟擅自下令一律改用
“最大可能降水量P.M.P”法。
按此法是设想极限情形下的最大暴雨,没有概率的概念,转算成洪流,中间误差很多很大,是不可靠的。
现在计算所得结果都大致把统计所得的成果加上20%左右,实际上这是统计中一个样本误差问题,有的统计系列短,校正样长,误差就该加20~30%或更多;系列长的加5%左右。
今一律加大20%左右,又硬说是考虑了概率问题,一方面有的加得太多了,造成浪费;另方面有的加得还不够,仍欠安全。
像这样的问题,不是那些总工程师们所能懂的,就该请专家商讨。
贸然以行政命令推行,就是领导不信任科学。
洪水设计规范也未规定必须外加这种校正标准,也未规定必须用最小二乘□线法定出各参数,制订规范的该负一部[份]责任。
七)关于1978年的东线南水北调会议和1979年的治黄规划会议。
为了华北缺水,提出东线南水北调,似是顺理必然之策。
河以北,西有太行,北有滦河,南有黄河,三面环水,高高在上,地下还有深浅层的潜水,可谓得天独厚。
惟有东面临海,余沥可排碱出去。
地形隆突成三角洲。
与太行东冲积平原交界线就是黑龙港窿道,这一带旱涝盐碱沙为灾,十分贫瘠。
假使引黄河浑水大量淤灌,汛期余水蓄地下,就可彻底改良土壤,辅以深层排水,当地可很快繁荣起来。
南水北调过黄河,水头抽高须达70米,而水量即以100秒立米计,终年不停,也只有每年31.5亿立米。
水流过苏北,沿途必被截用,那里有千万亩海滩黑地,人民见水如命,无法劝止拦阻。
所以说,北调江水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不经济的。
而部里却念念不忘,终不罢止。
水土保持不可能减少下游泥沙,经历了30年无效,就改说50年,把责任移交子孙。
用整治河道方法,想把泥沙全带出海去,可以证明是不可能的,却仍要求耗费每年250亿立米水输沙出去。
世界任何三角洲上都是分流水沙淤积灌成肥沃田地的,惟有我们顽强地封住两堤,不让水沙沿著现成的廿二条流派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