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docx
《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docx(3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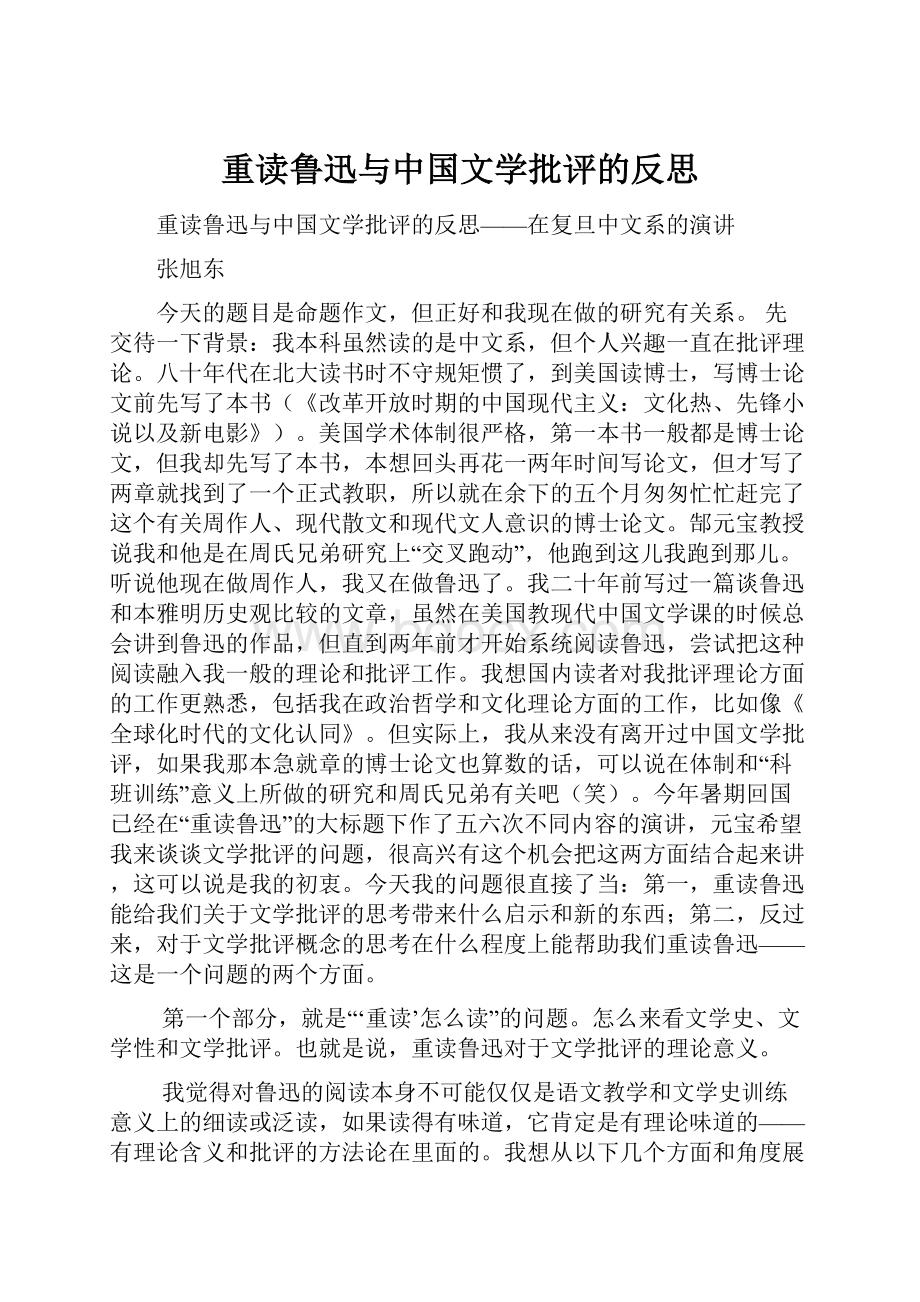
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
重读鲁迅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反思——在复旦中文系的演讲
张旭东
今天的题目是命题作文,但正好和我现在做的研究有关系。
先交待一下背景:
我本科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个人兴趣一直在批评理论。
八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不守规矩惯了,到美国读博士,写博士论文前先写了本书(《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
文化热、先锋小说以及新电影》)。
美国学术体制很严格,第一本书一般都是博士论文,但我却先写了本书,本想回头再花一两年时间写论文,但才写了两章就找到了一个正式教职,所以就在余下的五个月匆匆忙忙赶完了这个有关周作人、现代散文和现代文人意识的博士论文。
郜元宝教授说我和他是在周氏兄弟研究上“交叉跑动”,他跑到这儿我跑到那儿。
听说他现在做周作人,我又在做鲁迅了。
我二十年前写过一篇谈鲁迅和本雅明历史观比较的文章,虽然在美国教现代中国文学课的时候总会讲到鲁迅的作品,但直到两年前才开始系统阅读鲁迅,尝试把这种阅读融入我一般的理论和批评工作。
我想国内读者对我批评理论方面的工作更熟悉,包括我在政治哲学和文化理论方面的工作,比如像《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
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文学批评,如果我那本急就章的博士论文也算数的话,可以说在体制和“科班训练”意义上所做的研究和周氏兄弟有关吧(笑)。
今年暑期回国已经在“重读鲁迅”的大标题下作了五六次不同内容的演讲,元宝希望我来谈谈文学批评的问题,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讲,这可以说是我的初衷。
今天我的问题很直接了当:
第一,重读鲁迅能给我们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带来什么启示和新的东西;第二,反过来,对于文学批评概念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能帮助我们重读鲁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第一个部分,就是“‘重读’怎么读”的问题。
怎么来看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
也就是说,重读鲁迅对于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
我觉得对鲁迅的阅读本身不可能仅仅是语文教学和文学史训练意义上的细读或泛读,如果读得有味道,它肯定是有理论味道的——有理论含义和批评的方法论在里面的。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展开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串名字:
从本雅明到保罗-德·曼,到德勒兹,到杰姆逊——我并不是来向大家介绍西方理论的思潮、模式和方法,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只是想借用这几个批评模式来说明我在读鲁迅的过程中的一些考虑,这样比较方便;但这些都是关于文学史、文学性和文学批评这几个基本概念的考虑。
我想先从本雅明讲起。
先声明我不是要套用本雅明的方法来读鲁迅,我不主张这么做。
读鲁迅就是读鲁迅,用一种老式的说法就是:
用一种中国气派的读法读出自己的东西来—一切都在文本里。
但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在现代学术体制里边又不得不假借一些这样既成的符号来解释我们所做的中国内容。
今天介绍的是大家不太熟悉的早期本雅明。
在本雅明在搞青年学生运动、做博士论文、研究德国浪漫派这个时期的一系列没有发表过的小文章、手稿里面,专门谈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我有一个感觉是:
在九十年代以来所谓国内学术界“思想被学术代替”的总的势态下,文学史概念变成学科范围里的笼罩性概念。
我们的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到博士的训练,从对文学作品的感知到教授出版评核职称,统统是在围绕文学史转。
我们的学生到中文系来学习,实际上是来学习一大堆文学史,即有关文学生产、流播、研究和评价的种种通史、专门史、断代史。
而本雅明的问题很简单,他那时还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但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
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哪个重要——这的确是一个很基本、很要紧,但大家却不太去想的问题。
本雅明以他特有的出人意料的方式做了一个回答:
文学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派生的;没有文学批评就没有文学史,但好的批评家其实都已经是文学史家了。
这观点在今天的学科氛围里看好像有点不专业,有点离经叛道。
你搞作家评论、当代文学批评这个怎么能代替文学史呢,我们文学史是学术,而批评家不过就是发发议论。
但本雅明说不然。
他问道,“文学史”的重音是落在“文学”上,还是落在“史”上?
如果说文学史基本上是个“史”,属于历史科学,historicalscience,那么西方从古希腊的史学写作传统,经维科以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科学,到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都有非常严格的“家法”。
按照这个传统衡量,文学史不要说是个“边缘学科”,它基本上是个不够格的、没有严格标准的史学写作形态。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文学史放在近代西方历史科学的标准上来看,它没有一个史学的基础;它唯一能提供的历史知识,以及人们兴趣的来源,都是来自文学,而从来没有哪一部文学史作品能够跻身于伟大的史学著作之列(但我们知道有伟大的科学史、交通史、边疆史、战争史、外交史,等等)。
所以,读文学史的人感兴趣的是文学,不是史;它存在的理由最终来自文学,而不是来自史学。
但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从文学史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有关文学的编年史、资料史、作家生平传记、文学活动纪事、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积累和整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能为人提供什么样的对于文学的理解呢?
本雅明当然不是否定种种有关文学的知识的重要性,但他相信真正喜爱文学的人都会本能地吸收这样的知识而不受文学史窠臼的限制,因为文学史一方面不具有历史科学的严格性,但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为“什么是文学”这样的问题提供答案,就是说,它在终极意义上,对人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无所裨益。
放在我们今天,问题就是,我们读鲁迅究竟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的“物件”去读呢?
还是作为文学批评的对象上去读、从审美判断的方向去读?
是作为文学史、学术史的材料?
还是作为文学文本和写作来看?
进入鲁迅文本的前提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我觉得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解决这个争议,但这不要紧——关键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样我们可能通过对鲁迅文本的又一次的接触、体会、分析,在试图确定我们和鲁迅这个文本的关系的同时,推动有关文学史、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的理论性讨论。
在本雅明看来,文学史附属于文学批评,文学史是由文学批评派生出来的。
由于我们对文学的兴趣,对阅读的兴趣可以派生出来对文学的来龙去脉、它的材料、传记性的知识、历史的传承,所有这些对文学史知识的热情来自于对文学的热情。
对文学的热情首先是对文本的关心,对文学性的关心。
这种兴趣、热情和关心是无法被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满足的,任何知性的、分析性的东西都不属于这个范畴。
而文学批评则关系到文学作品和文学本身的“诗的使命”(thepoetictask)和“诗的前提”(thepoeticpremise),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不但最终通过阅读和批评完成自身的使命,它的存在本身都是由这种阅读和批评为前提条件的。
这是本雅明从德国浪漫派的文学史、文学批评追溯到——因为我们知道,德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根源在德国浪漫派以来的文学研究,包括翻译,作家作品研究,这是他很熟悉的一块,他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题材,《德国浪漫派的批评概念》。
最终本雅明指出,文学批评自己也不是第一性的,它的哲学基础来自审美判断或康德定义的“判断力”。
打个比方说就是,文学史是三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美学是一级学科。
文学批评或艺术欣赏最终的问题是一个判断力的问题,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判断”。
我们知道康德写过三个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处理知性问题(认识论问题);道德伦理问题;和审美问题。
这三种人类基本官能在康德看来各有其自律性,分属不同的范畴。
如果仅从这个分析来看,文学批评和文学本身同属审美范畴,而文学史则属于认知范畴,远近亲疏,当然很明显了。
我们读一个作品最后是要做判断,最终要对作品的艺术和审美价值作出评价和判断。
批评的基础就来自这样一个基本范畴,而批评的活动范围在外延上涵盖了文学史的知识领域和认识旨趣。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康德所谓的judgment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美判断,比如看见一件艺术品就可以发表议论,品头论足,最后下个判断“好看”、“令人愉快”,或“不好看”等。
康德用的德文词(Urteilskraft)相当于“判断力”,中文翻译比英文翻译到位,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力”:
能力、潜力、可能性和自由。
正是这一层意思界定了康德“第三批判”的自律性,因为在文学艺术和审美判断的领域里,我们不需要知识和道德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确信,获得对世界的一种非知性、非道德的把握,它让我们感受到特殊之物(比如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一个情结或一种旋律和节奏)内涵的一般性、普遍性真理,虽然后者不是由知性所把握的。
这种感性和理性结合的“直接性”,这种个别事物同普遍原则的“可结合性”和“可交流性”,就是审美判断(力)所代表的能力、潜力、可能和自由,它体现了人类心灵的绝对的个别性与普遍原则只见的奇妙的沟通;它不能以认识、分析、论述的方式获得,而只能通过一种创造性活动—--创作和批评—来获得。
我个人重读鲁迅的努力,就是尝试把文学史的东西暂时放在“括号”里,从文学批评的层面进入文本,在判断力或judgement的层面展开鲁迅写作的特殊的能力、可能性、自由和批评的潜力。
第二点是保罗-德·曼所谓的文学形式本体论的问题,它反映了他对新批评以来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不满,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换一个角度来谈本雅明提出的问题。
德曼指出,所有有关于文学的认识性和分析性研究,归根结底上都无法回答一个问题:
文学是什么。
我们所有人在做的工作最多都只是回答了文学不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回答文学是什么呢,德·曼说这个问题是连问都没办法问的,因为“文学本体”的存在方式对“什么是文学”构成不断的颠覆,并通过这种颠覆和混乱使文学不断回到文学性的起点和根源:
文学性。
任何一个好作品都会颠覆前面一个好作品确定下的什么是好作品的概念,任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体裁和写作样式都会把以前确立的标准相对化。
史诗确立起来了,悲剧把它打倒了;悲剧建立起来了,小说把它打倒了;小说建立起来了,散文、散文诗、现代诗把它打倒了;包括纪实与虚构的边界的打破,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不断地颠覆既定的文学的本体论。
文学的本体论,换而言之,是一个永远在被重新界定的过程,它的“新”实际上是不断地要归向一个更古老的源头。
在这个问题里,不考虑文学本体性内在的颠覆性,文学的“法”是个“无法之法”,是自身颠覆自己的一个“法”,始终是把一个成文法变成一个不成文法、再把不成文法变成一个成文法的这么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德·曼是用这个方式来回应新批评派以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同时也是在对抗马克思主义要把文学还原为历史、社会学以及意识形态的生产等等,它是强调文学内在的“法”,这个内在的“法”是一个自我颠覆、自我消解、又自我生成的一个虚无的本体,一个有生产性的nothing,就是“找不到”的一个东西。
联系到鲁迅的写作,我们不妨看看《野草》、《朝花夕拾》,看看《吶喊》和《彷徨》里面的许多篇目,比如《社戏》、《故乡》,更不用说他后期的杂文,就明白鲁迅的写作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形式创新”,而是一种不断的颠覆和重建,是在不断地探索文学的边界,是在看似离文学最远的地方把白话文学同中国文学的源头重新联系起来。
《野草》是散文诗,某种程度上它既颠覆了诗的稳定性也颠覆了散文的稳定性,在这个互相颠覆中,诗在形式空间内部把散文这个形式变成了一种内容。
《野草》这么难读,我想有一个原因是它内部的形式空间是双重的,诗以散文为形式,散文以诗为形式,在纯形式的层面上,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
就是说文学形式之间互相形成了一个寓言式的互相生成的关系,这是把一个既定的文学法则既颠覆了又重新确立起来的过程。
《朝花夕拾》一般认为是个人回忆性质的散文作品集,可是它这里边有很强的叙事性、虚构性。
有些篇目比如《阿长与山海经》、《五猖会》,它都有文学的虚构的形式,有它的复杂性。
《吶喊》与《彷徨》里边的作品又有些回忆和传记性的杂文和散文。
我还有个比较离经叛道的说法是,《伤逝》不是个小说,是个哲学论文。
还有杂文和杂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界定这个杂文和杂感。
杂文是鲁迅写作的一个高峰,集大成,这听上去是个很传统的说法,但我的意思是,在杂文里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可能是最极端的,最微妙的那种文学性是可以通过杂文来把握的。
《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的散文编中几个大家都出现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高的实际上是散文。
因为会写欧洲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会写三一律的戏剧,白话诗等这些符合既成的文学体制的(文学样式),说难听点就是创造性的照搬。
但是唯独杂文或说散文,一方面是没离开自己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是它没有一个定规,既是最充分的西化又是最不充分的西化,既是最传统的又是最不传统的。
更不用说鲁迅的那些杂文和杂感,比如《华盖集》前面那个序里说现在写杂感的人越来越少了,他是把自己写的东西当成杂感的,杂感是连基本的文学性都可以不要的,有个什么事我就发发议论,就是个杂感、时评。
这个好像离文学的“核心”——形式自律性、体制性的物化——最远,最零散、最杂乱、最不成形,文学性简约到再也无法简约的地步是在杂文里,它已经没有任何外在化的依靠和凭借。
也就是在文字这个意义上,在“写”这个意义上,文学性在哪,鲁迅写的这部分文字在什么意义上是文学。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深入地讨论下去的话,将来是不是要重新界定文学的概念。
说《荷塘月色》这是文学,很美,这很容易,而杂文好像是最“粗放型”的一个定义,从这些杂感和杂文,特别是不那么“美”的杂感和杂文里边,比如骂人、那种“匕首投枪”式的文章,或者是报流水账那样的文章里,怎么看待文学性。
我们把它当文章读的话,那对文章的理解,在西方的意义上,在文学判断的意义上,在有中国气派的意义上,什么是文学性的核心,这里面有这样一个重新界定的可能。
再下面一点我想借用德勒兹的一个“大文学”(majorliterature)和“小文学”(minorliterature)这对概念来谈谈重读鲁迅的可能性。
我觉得德勒兹这个“小文学”的概念很重要。
“小文学”其实翻得不太好,或许该叫非主流写作、次文学,我还没有好好想过译名的问题。
他的“大”和“小”是这么讲的:
近代欧洲以来的大文学、主流文学、纪念碑式的文学都是关于中产阶级兴起以来他们的生活的世界、核心价值的,所谓资产阶级主旋律,如果用一个中性的词,不叫“资产阶级”,叫“市民阶层”。
他们的“主”(主旋律)按照我们共产主义的教育体系来看其实是非常边缘的。
资产阶级主流文学写的大部分是财产权(问题),比如《傲慢与偏见》写的是个嫁女儿的故事,陪嫁多少,底层阶级怎么和上层阶级联姻,财产交换;或者是性爱,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通奸、婚外恋,讨论女人内心的世界;一直到现代派,西方主流意义上的现代派,写潜意识,梦,变形,纯私人的内心孤岛。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很奇怪,他是对权力意识比较清楚的一个阶层,他要权力,他有个目标,他革命要杀国王的头。
但等革命完了他就把权给那些想去当官的人,这样以便于自己可以“埋头打理私人事务”,做生意做买卖,搞保险业,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本的管理委员会。
这个主流文学是从资产阶级的主流生活生发出来的。
按照学术和思想的观念,或者说从大的历史方面来看,它(资产阶级主流文学)不是史诗,它没有英雄,没有所谓的公共性,或者集体性,和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面定义的文学的大问题不相干,比较而言是“小”的。
说在近代以来,只有往“小”里写才能写得出“大”,以小见大,这是中产阶级文学的一个特点,它的价值就在这里。
确定了这个资产阶级文学主旋律后,德勒兹就给他来了一个内部的颠覆,他讲的小文学的例子是卡夫卡,其实我觉得用来说鲁迅同样恰当,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更恰当。
卡夫卡只有两部长篇小说,《美国》和《城堡》,就是篇幅较长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情节展开和人物描写,不像《安娜·卡列尼娜》,有线索有高峰,卡夫卡写的都是短小的、寓言式的东西。
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是书信、小说、日记、短篇寓言故事,像《伊索寓言》那样的东西。
《在法律面前》、《流放地》、《变形记》等,都不太成形。
德勒兹说你看这样的文学小吧,这个小一个指形式意义上的,没有成形;另一个指语言意义上的。
卡夫卡的语言很别扭,他是用德语写作的、是住在捷克的的犹太人,他的身份有好几层。
他为什么用德语写呢,他要解释一下,这不是个无须解释的问题,他说德语对于他像是“偷来的别人家的孩子”。
德语至少在东欧是个高级的语言,哲学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但他的身份是个犹太人,捷克犹太人,在语言内部他就包含一种(前提),这语言不是我的,在语言的层面上有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关系,我写来写去都不可能找到一种语言上的归属感,在语言的内部我时刻意识到语言本身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它的压迫性和解放感,它的社会根源和阶级、种族、权力属性。
德勒兹说这样的语言或语感肯定带有“内在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不是要接受任务,而是它把作家的自我意识变成了一种“群”的意识,給它注入了一种“集体性”。
这样看,卡夫卡的写作就不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孤独感或疏离感,而是通过一种语言内部的挣扎和斗争表现写出了一种集体的命运:
犹太人的命运、小人物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边缘人的命运。
所有这些都不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任何事物“理应如此”,这就使卡夫卡的写作脱离了主流文学的意识形态幻觉。
“小文学”不是一种写作态度或立场,而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存在状态和感知状态:
这不是我的语言,这不是母语,这里面没有“自然”,通过语言内部多重的协商、斡旋,写作摆脱了“个人”或“私人”、“非功利”或“为艺术而艺术”、“不朽”等等偏见的束缚,而参与到一种集体政治性的寓意性表达之中。
德勒兹说你看它是零零碎碎的“小”寓言故事,minor不是小孩的意思,是次要的意思、是边缘的东西,但是,你看卡夫卡的小说里写的那些东西,《地洞》里面那人像个冰冷的耗子似的觉得自己不安全,在这儿留一个出口,在那儿留一个出口。
《变形记》里公司小职员早晨起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甲虫有个特点,它翻过去就翻不回来了,陷入焦虑里边,吃饭的时候他就想下去看看亲戚看到我变成虫子会吓成什么样,人和虫子已经分不开了。
这个东西你跟《傲慢与偏见》、跟狄更斯、跟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样的主流文学比较,他没有写出历史,没有写出革命,没有写出现代性,看上去很小,但是,他写出了和整个现代社会的关系,我们简单概括就是“异化”这个问题,是人和整个现代世界在存在意义上的关系和政治意义上的关系,集体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的小文学就比主流文学更大,因为他没有天真到认为文学就是纯私人的东西,也没有认为文学是个纯自律的东西,不认为文学是资产阶级在打理完个人事务之余也想有娱乐、审美、有他们的梦、他们的性的问题、不能跟人交流但可以写出来无伤大雅的游戏性的事物。
这样的一些主流文学的基本前提跟卡夫卡的写作比起来又小了,不够大,它没有触及到绝望、人类的命运、异化、语言内部的陌生感流放感,这些现代性最深层的问题在现代主流文学里的体现往往不如在边缘次要的文学里更充分。
我们看鲁迅的写作,比如《阿Q正传》,不是长篇小说,你怎么把它往上拔也拔不到史诗的高度——是个滑稽故事,流浪汉体,报刊连载;是一个没有情节、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复杂和不充分的东西;“正传”就是传记,一个传记有它自己的内部矛盾,开篇也有个交待:
我这个“传”没有办法“作”,“本记”、“世家”、“列传”之类的“体”,可是它都不合,只好生造两个字来,不是“立言”,就随便抓出两个字来,就是“言归正传”或《书法正传》里抓出来的,说“顾不得了”。
整个的故事就是东洋的漆棒、小D的事、秀才娘子绣花床、吴妈的事、不许姓赵的事、不许革命的事……这么一个完全没有充分展开的文本。
八〇年代的文学焦虑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了阿Q以后大家都很绝望,说我们为什么没有史诗,为什么没有长篇小说,凭这种东西怎么能拿到诺贝尔奖。
但是《阿Q正传》从语言、形式、叙事和寓言的层面上来讲,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文学最大的作品,因为阿Q就是中国,不是隐喻上的,阿Q就是中国,就是“中国的传”,是对中国人集体传记在语言和叙事形式上的不可能性和可能性的寓言性探索。
以前我们说里面有民族性,落后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还可以读出别的东西来,这就使整个中国文化作为“命名系统”的“不可能性”、“传”的“不可能性”被《阿Q正传》写出来了,从而把意义的命名行为、价值和“难堪状”在各个层面上给“再现”出来了,representation就是allegory。
这要比电视剧式的叙事更具有文学性,像《闯关东》、《金婚》这样的情节剧,一写几十年,好多故事,反而小了。
这样的作品再怎么“大”也不如《阿Q正传》大,因为《阿Q正传》不是写实的小说,也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章回小说,什么“体”都套不进,不符合,完全是个边缘的、“次要的”、讽刺性的东西,但它却具备一种文学写作的张力和寓意能力,具有一种语言内部的激进性和艺术体制内部的颠覆性。
这种内在的张力同作品外部环境形成一种对应或呼应关系,由此而确定了《阿Q正传》的伟大意义。
德勒兹最后亮出了自己在文学性问题上的立场:
真正的文学是要能通过语言的实践和行动不断地保持、恢复、重新激发文学写作语言内在的激进性、革命性。
革命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审美形式上的,只有在小文学里,只有向语言和写作可能的边界不断冲击,这样才能不断地让文学把自己建立起来。
换句话说就是,文学要“小”就不能“大”,文学要“大”就必须“小”。
这是德勒兹的结论,这是个非常反中产阶级主流、文学体制、文学消费、文学审美的力量。
越读鲁迅就越觉得是这样。
在客观的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批评是接受这一点的,但在意识的层面上不接受,我们在自身传统中接受了,但在今天的写作、论述、媒体和学术语言中还不接受。
觉得返回30年代很老套,但中国文学研究界又反反复复离不开鲁迅,不断去读、去想。
鲁迅的全集现在是18本[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它是个大文学还是小文学?
它是个大文学,这在更大的传统中实际上是被接受下来了。
但重读鲁迅对当前关于纯文学的讨论、文学形态的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都会非常有帮助。
这一点我希望能反过来激发对文学批评的讨论。
下面我们谈一下民族寓言(NationalAllegory)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要过多纠缠于为什么西方文学就是文学本身,就高级,而我们偏偏要被戴上个“民族寓言”的比标签才能进入世界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视野。
这是不是在贬低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写不出像西方作家那样的“纯文学”、“真正的”文学作品。
如果我们避开这个概念,从正面理解“民族寓言”,我觉得杰姆逊这个概念和德勒兹的大小文学概念非常相似,它指的无非是在一个中产阶级革命和体制化建设没有充分完成的社会,即一个没有充分分化、分层、法制化、私有财产的符号化、法律符码的科层化都没有充分完成的社会,人和人是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不管好坏。
这就像以前我们住在大杂院里,一家人住一间房,亲戚朋友谁也分不开,你没有隐私,没有一点个性,可是现在我们有隐私了,同时也在哀叹人和人隔这么远,人都没有归属的感觉,没有共同体的感觉。
在资产阶级市场和法制没有充分体制化的社会里边,任何一种写作都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私人写作,哪怕你在写私人语言、私人身体,你还是会一不小心写到你的同事、领导或党、政府,因为你的“私”是被这个“公”界定的,或多或少是对这种“公”的指控或反叛。
你不可能完全把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撇干净。
这么看,杰姆逊就等于是在说,非中产阶级写的就不是中产阶级文学。
关于这点有很多人抗议,抗议的名目是西方中心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就是抗议你们这些已经充分中产阶级化的西方学院、教授不许我们做中产阶级,那等于是阿Q去抗议赵家不许他姓赵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中产阶级,不能有中产阶级的大文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是小文学,谁说我们非要写出政治性、集体性,谁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文学内在的张力或者说激进性,谁说我们一定要写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题材”,卡夫卡意义上的重大题材?
因为跟卡夫卡题材的重大性相比,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题材还不够重大。
中国人在文学问题上对杰姆逊这个民族寓言说法的抗议实际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背这个担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文学就当一幅画,就当作安乐椅,艺术就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