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docx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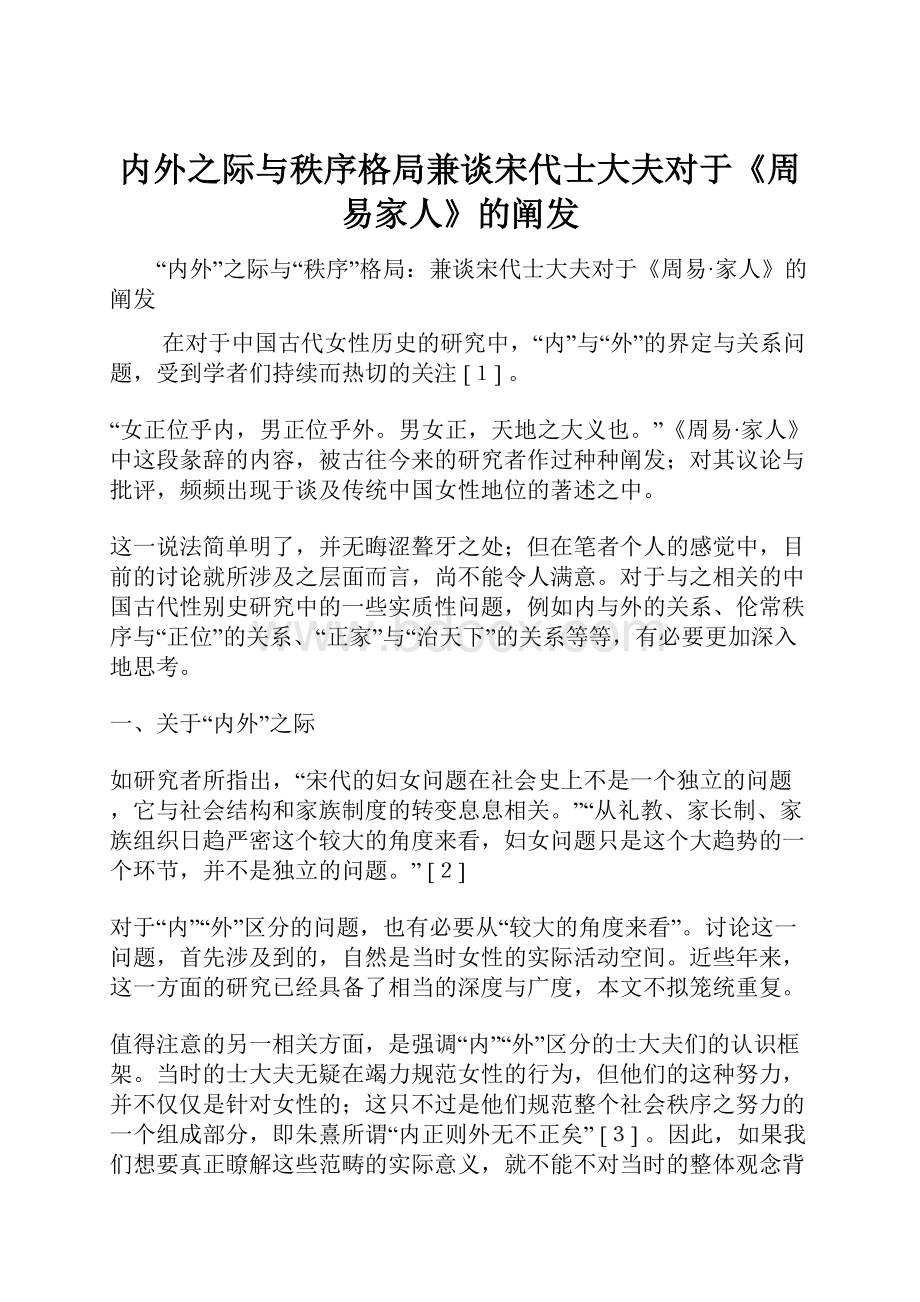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
兼谈宋代士大夫对于《周易·家人》的阐发
在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历史的研究中,“内”与“外”的界定与关系问题,受到学者们持续而热切的关注[1]。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
”《周易·家人》中这段彖辞的内容,被古往今来的研究者作过种种阐发;对其议论与批评,频频出现于谈及传统中国女性地位的著述之中。
这一说法简单明了,并无晦涩聱牙之处;但在笔者个人的感觉中,目前的讨论就所涉及之层面而言,尚不能令人满意。
对于与之相关的中国古代性别史研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例如内与外的关系、伦常秩序与“正位”的关系、“正家”与“治天下”的关系等等,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思考。
一、关于“内外”之际
如研究者所指出,“宋代的妇女问题在社会史上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与社会结构和家族制度的转变息息相关。
”“从礼教、家长制、家族组织日趋严密这个较大的角度来看,妇女问题只是这个大趋势的一个环节,并不是独立的问题。
”[2]
对于“内”“外”区分的问题,也有必要从“较大的角度来看”。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到的,自然是当时女性的实际活动空间。
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本文不拟笼统重复。
值得注意的另一相关方面,是强调“内”“外”区分的士大夫们的认识框架。
当时的士大夫无疑在竭力规范女性的行为,但他们的这种努力,并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这只不过是他们规范整个社会秩序之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朱熹所谓“内正则外无不正矣”[3]。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瞭解这些范畴的实际意义,就不能不对当时的整体观念背景予以进一步思考。
(一)
内、外本来是一組空间概念,而它一旦与男、女对应起来,便涉及到观念中对于内外的判别,彰显出了一层道德文化的含义。
刘静贞即曾指出:
“对宋人而言,所谓妇德主内,妇人无外事,不单只是社会分工的现象,而且带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
”[4]正因为如此,内外之际的分隔认定绝非简单问题。
我们所接触到的史料,几乎都是透过当时士大夫们的观察、思考而存留给后人的。
不仅形形色色的列女传、墓志铭中寓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即便是“存于家”的记叙文字,目的也是“庶使后世为妇者有所矜式耳”[5]。
在这种情形下,要讨论“内、外”的问题,就不可能脱离开当时士大夫的观念体系。
宋代士大夫对于“严内外之别”的强调,屡见不鲜。
研究者所频繁引述的,是司马光《书仪·居家杂仪》[6]中的以下一段文字:
凡为宫室,必辨内外。
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厕。
男治外事,女治内事。
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
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
男子夜行以烛,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亦必以袖遮其面。
女仆无故不出中门(盖小婢亦然),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
铃下苍头但主通内外之言,传致内外之物,毋得辄升堂室、入庖厨。
众所周知,这段话脱胎于《礼记·内则》中涉及男女行为空间的相应内容: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非祭非丧,不相授器。
……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内言不出,外言不入。
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如若我们将二者稍加比对,即不难发现,《居家杂仪》对于《内则》之“发展”主要在于两处:
一是以“中门”为限,强调了内外分界:
“妇人无故不窥中门”,而当“有故”之际,所出也只能是“中门”,这样就从规范上把女性完全框在了宅院之中[7];二是把《内则》中“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说法,直白地阐释为“男治外事,女治内事”,从而点明了“言内”与“言外”的实质含义。
[8]
内外之分,就唐代的墓志来看,似乎较少正面具体的强调。
唐代(特别其前期)的女性墓志铭高度程式化,往往依照一定的书写范式甚至套语敷衍而成。
墓志中对于所谓“开芳兰蕙之姿,曜彩荆蓝之德”“内外之所取则,宗党之所归仁”一类“母仪女德”的赞颂,使读者体味到这类固定范式中所渗透的主流文化理念。
摆脱了靡丽模式的宋代女性墓志铭[9],对于“内外之分”的问题有许多直接的阐述。
妇人不预外事,这在宋代当然被男女两性所认同。
墓志的撰著者们既意识到明确内、外区分在伦理观念及整体秩序建设中的重要性,又显然意识到如此区分与之俱来的矛盾。
吕祖谦曾经说:
“门内之治,女美、妇德、母道,三而有一焉,既足自附女史”云云[10],宋代士大夫所做女性墓志铭,经常刻意强调女性相对于父母、舅姑、丈夫、子女的家内身份及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例如“以孝力事其舅为贤妇,以柔顺事其夫为贤妻,以恭俭均一教育其子为贤母”[11];“在父母家为淑女,既嫁为令妻,其卒有子为贤母”[12];“为妇而妇,为妻而妻,为母而母,为姑而姑”[13]等等。
即便内容最为空泛的女性墓志,也很少忘记对于墓主人身份合宜之赞颂称扬。
在宋代的士大夫们看来,“内”之作用,无疑是辅助“外”的:
丈夫们“尽心外事不以家为恤者,以夫人为之内也。
”[14]“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俭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
用能退食委蛇,无内顾之忧。
”[15]正是这种“辅助”带来了沟通与跨越的可能。
“辅助”本指分担家内事务;而进一步的积极“辅助”,则势必逾越内外界线,过问乃至介入夫君子弟掌管的“外事”。
这使我们感到,在讨论“内/外”问题时,更为切近于主题、更能揭示其实质的,并非所谓“内”与“外”的隔离区划,而更在于二者相互交叉覆盖的边缘,在于其联系与沟通。
这一边缘地带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没有固定不变的界域,作为“内”与“外”两端的衔接面,它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内”或“外”,而可谓亦内亦外。
在这样一个充满灵活度的弹性场域中,最容易观察到诠释者区分“内”“外”的判断标准及其如此区分的主观意图。
这种互相连结、互相定位,甚至互相转换的模糊性,才是蕴涵“内外之际”真谛之所在。
(二)
《道乡集》卷三七有邹浩为周师厚妻范氏(范仲淹侄女)所做墓志铭,据说这位范夫人在子婿被贬逐之际,深明大义地说:
“吾妇人不知外事,但各愿其无忘国恩而已。
”在铭文中,邹浩继而赞曰:
惟文正,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
习见闻,逮女子,施于家,率由是。
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
要所存,似兄弟,若夫人,可无愧。
所谓“习见闻”,是指范仲淹的处事精神被范氏经耳濡目染所自然继承,随后而“施于家”。
而“笃忠义,忘乃身,徇国事”是士大夫们处理“外事”的原则,本来与“不知外事”的“妇人”无干。
对此,最为方便恰当的解释自然是“自其夫,暨后嗣,助成之,靡不至”。
在这里,“助成”二字轻而易举地将“内”与“外”联系贯通起来。
有一组例子颇有意思。
梅尧臣在称赞他的妻子谢氏时,说到她的一种习惯做法:
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间,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
[16]
无独有偶。
苏轼在为其亡妻王弗所作墓志铭中也说:
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
“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
”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
“恐不能久。
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
”已而果然。
[17]
还有一位符氏,她丈夫张公雅
居常与士大夫议论,夫人多窃听之。
退而品第其人物贤否无不曲当。
[18]
另有一例,在《东莱集》卷十所收“汤教授母潘夫人墓志铭”中,吕祖谦不仅概括地称赞这位潘夫人“厘身治家,皆应仪矩”,而且具体地讲到她为教育儿子而养成的一种素习,即每逢客人到来,她总要“立屏间,耳其语”,亲自判断谈话内容有益与否。
这里有两个不同层次的相似之处使我们感到有趣。
一是这些夫人行为举措的相似:
她们显然都感觉到了自己处身于“内”“外”之间的为难,也都在找寻着“内”“外”之间可供她们存身的罅隙。
曾经“立于屏间”的谢氏、王氏、符氏、潘氏夫人[19],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而且显然对于“外事”一向有所瞭解;她们在家中有发言权,夫妻母子间能够有所沟通。
这些夫人所站立的“户屏之间”,正是前堂与后室、外厅与内房的联系空间。
就位置而言,因其处于牖户之后,可以归入“内”的范围;而选择此处站立,显然又是因其通向“外”室。
就站立者关心的问题而言,亦属内外兼而有之:
一方面“窃听”的是夫君子弟接触的“外人”与“外事”;而另一方面,这些外人、外事又因其与夫君子弟的关系而变成了“内人”们有理由关心的内容。
正因为如此,夫人们似不因站立位置的尴尬而介意,丈夫子弟们也未因受到暗中的“窃听”而不快。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记叙者所持态度的类[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