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意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docx
《角色意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角色意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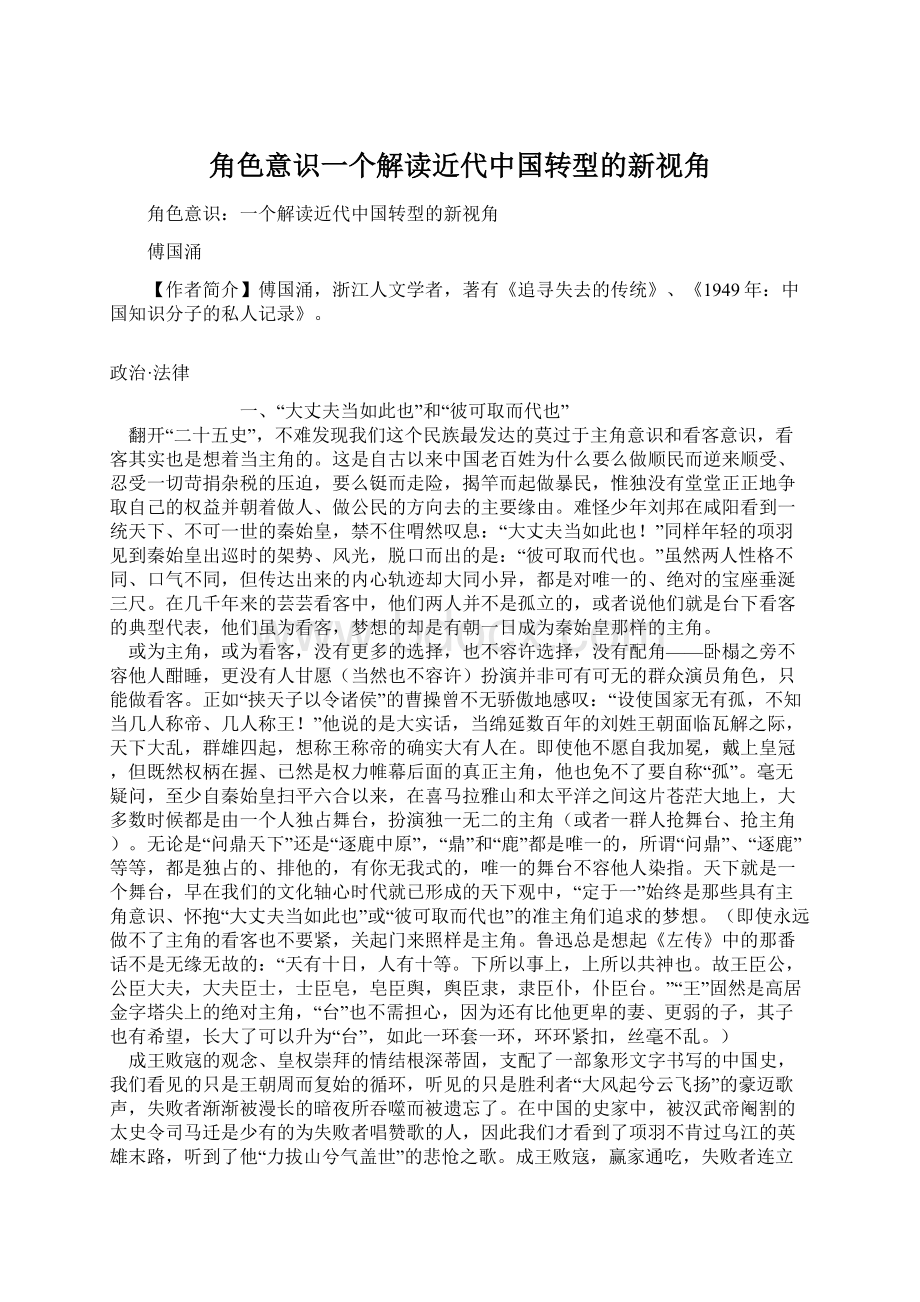
角色意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
角色意识:
一个解读近代中国转型的新视角
傅国涌
【作者简介】傅国涌,浙江人文学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
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政治·法律
一、“大丈夫当如此也”和“彼可取而代也”
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
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么做顺民而逆来顺受、忍受一切苛捐杂税的压迫,要么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做暴民,惟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并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
难怪少年刘邦在咸阳看到一统天下、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禁不住喟然叹息:
“大丈夫当如此也!
”同样年轻的项羽见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架势、风光,脱口而出的是:
“彼可取而代也。
”虽然两人性格不同、口气不同,但传达出来的内心轨迹却大同小异,都是对唯一的、绝对的宝座垂涎三尺。
在几千年来的芸芸看客中,他们两人并不是孤立的,或者说他们就是台下看客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为看客,梦想的却是有朝一日成为秦始皇那样的主角。
或为主角,或为看客,没有更多的选择,也不容许选择,没有配角——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更没有人甘愿(当然也不容许)扮演并非可有可无的群众演员角色,只能做看客。
正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曾不无骄傲地感叹: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他说的是大实话,当绵延数百年的刘姓王朝面临瓦解之际,天下大乱,群雄四起,想称王称帝的确实大有人在。
即使他不愿自我加冕,戴上皇冠,但既然权柄在握、已然是权力帷幕后面的真正主角,他也免不了要自称“孤”。
毫无疑问,至少自秦始皇扫平六合以来,在喜马拉雅山和太平洋之间这片苍茫大地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由一个人独占舞台,扮演独一无二的主角(或者一群人抢舞台、抢主角)。
无论是“问鼎天下”还是“逐鹿中原”,“鼎”和“鹿”都是唯一的,所谓“问鼎”、“逐鹿”等等,都是独占的、排他的,有你无我式的,唯一的舞台不容他人染指。
天下就是一个舞台,早在我们的文化轴心时代就已形成的天下观中,“定于一”始终是那些具有主角意识、怀抱“大丈夫当如此也”或“彼可取而代也”的准主角们追求的梦想。
(即使永远做不了主角的看客也不要紧,关起门来照样是主角。
鲁迅总是想起《左传》中的那番话不是无缘无故的: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
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仆,仆臣台。
”“王”固然是高居金字塔尖上的绝对主角,“台”也不需担心,因为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其子也有希望,长大了可以升为“台”,如此一环套一环,环环紧扣,丝毫不乱。
)
成王败寇的观念、皇权崇拜的情结根深蒂固,支配了一部象形文字书写的中国史,我们看见的只是王朝周而复始的循环,听见的只是胜利者“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歌声,失败者渐渐被漫长的暗夜所吞噬而被遗忘了。
在中国的史家中,被汉武帝阉割的太史令司马迁是少有的为失败者唱赞歌的人,因此我们才看到了项羽不肯过乌江的英雄末路,听到了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怆之歌。
成王败寇,赢家通吃,失败者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要么抢到龙椅拥有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以保障。
历史的逻辑就是如此严酷。
这就决定了在每个王朝末世群雄蜂起之时,各个“打天下集团”之间不可能妥协、共存,即使在推翻旧王朝时达成暂时的联盟,一旦天下在望,就要合纵连横、大打出手,拼个你死我活,分出个高下来,直到其中一个集团击败所有的对手,得到觊觎已久的“鹿”和“鼎”,才会罢手,然后等待下一轮的循环。
这一切都根植于一元的文化心理、绝对的主角意识当中,如此悠久,如此深厚,又具有如此旺盛的繁殖力。
几千年间,“打天下、坐天下”的逻辑几乎支配了我们全部的政治文化,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当配角,因为当不上主角就意味着在这方舞台上出局,只有等待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宰杀的命运,或者乐不思蜀的下场。
著名的传说中,隋朝末世,怀抱“打天下”大志的虬髯客一见李世民的“王气”就自动放弃,远走海外,另辟新天地。
1945年12月,《大公报》名笔王芸生曾发表过一篇长文《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
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
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
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
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
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
胜利的刘邦、朱元璋们可以建立起一姓王朝,子子孙孙绵延数百年之久,当然也有不过二世而亡的秦和隋,失败的从陈胜、吴广到王巢、李自成、洪秀全,更是史不绝书。
说他们打天下、争正统也好,说他们争主角、争舞台也罢,为此目的他们都可以杀人盈野、流血漂杵而不在话下。
从秦末项羽、刘邦之争,到元末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之争,再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之争,无不如此。
由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中缺乏兼容、多元的因子,完全是封闭的,逐渐形成了一种“天无二日”(或你死我活、有我无你、不共戴天)的潜意识。
这样的政治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打天下集团”击败另一个集团,单独扮演舞台的主角,一方面是残酷的专制制度本身造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角意识又进一步强化(乃至毒化)了一个民族的政治思维。
中国传统中最典型的就是《水浒》里面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上下等级秩序井然,高低尊卑一清二楚。
这样的观念几乎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就很难形成一种彼此可以信任的社会空间、发展出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的人格的具有包容性的观念。
比如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一样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或者如梁漱溟信奉的“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这样的观念,这是构成一个理性社会或者说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
与主角意识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敌人意识”,排除异己、非己即敌、非黑即白之类就是自然而然的。
历史因此弥漫着血腥气。
鲁迅说翻开每一页都是“吃人”二字,但翻开每一页,又何尝不是血污?
!
明末的张献忠因为眼看着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洲人入了关,争主角失败,天下已不再属于他,于是他在四川大开杀戒。
鲁迅一生曾多次地提起此事:
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注: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张献忠在明末的屠戮百姓,是谁也知道,谁也觉得可骇的,譬如他使AB杀C,又命A杀B,又令A自相杀。
为什么呢?
是李自成已经入北京,做皇帝了。
做皇帝是要百姓的,他就要杀完他的百姓,使他无皇帝可做(注: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蜀碧》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
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
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
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注: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鲁迅全集》的注解中总是一再地指出旧史书、野史夸大张献忠杀人,其实,这可不是出于鲁迅的文学想象、杂文笔法的虚构,史书上的记载可谓墨迹斑斑。
张献忠杀官绅、杀读书人、杀一切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仅青羊宫一次就将包括贡生、举人、进士在内的读书人诱杀了1.7万人,成都的河道都为尸体堵塞,不能行船。
对此清史专家萧一山等都曾有过详实的考证。
我不知道在世界史上还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例子。
鲁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张献忠的“杀人如草”,就是为这种荒唐而残酷的逻辑充满痛苦。
张献忠一旦确切地意识到做主角无望,可以想象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就杀人,尽可能多地杀人。
正是独占的、排他的主角意识下容不下配角,甚至也不需要群众演员,天下人都只是供其役使的奴才、看客,唱的都是称“孤”道“寡”的独角戏(从历史舞台到戏曲舞台,我们都可以听到帝王自称“朕”“孤”“寡”,也就是孤家寡人),竞争天下的失败者是无路可走的,恐怕欲做看客都不得了。
这种中国式的天下观支配下的主角意识畸形发达,是我们民族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
几千年来,不断地重蹈覆辙,不断地恶性循环。
所以,我们只看到王朝姓氏的更迭,看不到制度的转型、文明的更新、文化的演进,当然也不可能滋生出新型的角色意识。
直到近代,引进了维新、共和思想之后,情况才开始改变,但是长期以来被主角意识笼罩的民族要走出这一步又是何其艰难。
即使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袁世凯身上,我们照样可以依稀看到多少个世纪前司马昭的影子,明明有帝制自为之心,却偏偏要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上表“劝进”,还要假惺惺地再三退让,最后在举国舆论“斯人不出,奈苍生何”的呼声下,才肯黄袍加身、粉墨登台、牺牲自己(或者说陷自己于“不义”),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披上黄袍。
这种权力游戏简直已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不成文的经典规则(注:
参考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221、264~26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鲁迅说:
“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
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
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
”(注: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2、259、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所有王朝更迭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原地踏步,以鲁迅锐利的目光早已洞穿中国历史算不上秘密的秘密。
或许也只有异质文明的因子,输入新鲜的文明的血液,才有可能改变我们几千年来目光专注于抢椅子的政治文化心理、绝对主角意识、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的集体潜意识。
在宋教仁身上,我们或许依稀可以看到一闪即过的一线曙光。
他倒在了血泊中,但刹那即是永恒,毕竟曙光已经闪现,道路就在脚下。
二、剧本之争还是舞台之争?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依然逃脱不了陈旧的主角之争模式。
这种主角之争,本质上不是剧本之争,而是舞台之争。
争主角,争的是中国这方舞台,也就是要将天下据为己有、定于一尊。
没有发言权的天下人不过是看客而已。
宋教仁试图将政治竞争纳入和平的宪政轨道,以政见主张来争政权、争主角,就是要改变游戏规则,将数千年习惯的舞台之争变为剧本之争。
谁的剧本更适合观众的需要,就将谁推上舞台。
而舞台之旁容许其他人合法地监督、觊觎,上与下,进与退,都有程序可循。
胜者不是王,败者也不是寇,是非高于成败。
既然在和平的轨道上争主角,争的是剧本,就是以政见、主张来争,由观众来决定取舍。
胜者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不是永久的、绝对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一劳永逸地独霸舞台,而是要时刻面对七嘴八舌的议论乃至喝倒彩,或干脆撒手而去。
这是一种全新的竞争模式,是宦海里浮沉了一辈子的袁世凯们所难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才会视之如蛇蝎、如洪水猛兽,年轻的宋教仁也因此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洞察民国初年政局的名记者黄远生在《论衡》发表过《一年以来政局之真相》,分析当时的局势,精辟地区分了剧本之争与舞台之争:
人有常言,国家犹舞台,政治乃犹演剧,今一国之中,盖有嗜历史剧[旧剧]者,有嗜社会剧[新剧]者,于社会剧之中,有嗜理想主义之剧者,有嗜写实主义之剧者,于是新旧剧派各得炫示其角色技艺以相为进退于舞台之中,视客之所嗜好,以为兴衰。
固无害其并立,乃若有两造之人,在各欲争取此舞台之主权,而其所谓政策之异同,特利用之题目,而其本意初不在此。
则社会观客,永无得睹政治演剧之日,而惟睹此两造之强有力者,抢攘垢詈于舞台之上,其强有力之羽翼,则各欲其主人之得占此舞台,拼力誓死为之助战,则栋折榱崩、同归于尽之祸,容复可免,故人国之所谓政争,乃剧本之争,真政争也。
吾国之所谓政争,乃非争剧本之得失,而争舞台之所有权,乃个人势力之争,非真政争也。
……彼争剧本者,其意未尝不在舞台,顾于他造登台奏艺之时,其本身特处于诚实之批评及监督的地位,决不若吾国之根本不相容,其所挟以为攻击者,仅针对其剧本[政策]之精粗美恶而立言,决不若吾国之专认己造之人格,而取消他造之人格,故其决胜负也,仅求之于选举及议会,决不求之于兵力(注:
《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第969页,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
)。
革命派与立宪派,“自其主义言之,虽有急进与渐进之别,而爱国之本义则同,然略知二派之内幕者,则因其持论之异同不相下,运动进行之各相妨碍”,在清朝瓦解以前,两派之间就已演成“互相水火不共戴天之势”,不仅是政治主张的距离,还有历史渊源、领袖个人的性格等因素在内。
然而,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宪政与革命二派,曾在推倒清廷的目标上达成了暂时的共识,等到南京临时政府出现,同盟会掌握了主导权,“旧日两派之恶感,隐然勃发。
而革命中之不平分子,复凑合以与为标榜,党争之烈,已萌发矣”。
所以政治的胜利果实既不属宪政派,也不属革命派,最后而落在了袁世凯的手里。
黄远生认为“其最大原因,则不外势力之莫与敌而已”,恐不尽然。
不过他确实看清了,当时的政治之争仍未跳出权力之争的老套路,“大半由于势力问题”,双方或三方之间都把政见放在其次(以宋教仁为代表可能是个难得的例外),“惟是以暗中角斗势力为宗旨,而以政治主义、法律问题云云者为利用之口实,一年以来,莫非势力角逐之幻想,而绝无政治主义胜负之可言。
盖以其出发点之本以势力为根据故耳”(注:
《远生遗著》卷一,第68、69、28~29、49页,上海书店影印本。
)。
如果孙中山、黄兴等代表的革命派和梁启超、张謇、汤化龙等所代表的立宪派和袁世凯代表的官僚派三方之间,从旨在舞台的主角之争转向旨在剧本的主角之争,而不是以武力为后盾暗中角逐,或者动不动就诉诸武力、大打出手,把古代史上一再重复的天下大乱时期那种“逐鹿”“问鼎”式的主角之争,变成近代文明背景下的主角之争,争剧本而不是争舞台,以剧本论英雄,而不是气力争高下,近代的转型也许就顺利得多了。
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所有伏笔早已深埋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甚至本人都很难察觉,民族潜意识是世代累积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轻易改变的。
辛亥革命是雷霆、是闪电,它撕开了满清数百年统治的长夜,形式上结束了皇帝的垂拱而治,但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古老的土壤,改变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
那需要阳光,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且不单纯是政治层面的努力。
其实,包括黄远生在内的有识者,当时已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
三、“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
抑为民主乎?
”
1905年7月28日,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第一次约见宋教仁、陈天华时,就表示: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注:
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5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孙中山似乎意识到了,“驱逐鞑虏、创建民国”的事业完全有可能淹没在主角之争这一古老循环的波涛风浪中。
黄兴也很早就对太平天国领袖之间“互争权势、自相残杀”深为忧虑,极力想避免重蹈覆辙,他所以一心要做配角,从未打算取代孙中山的主角地位,就与他的这种忧虑有很大的关系。
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无论是改良者与革命者之间、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都将一再地陷入旧式的主角之争泥潭。
孙中山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求与维新派的合作,却遭到康有为一而再地拒绝,一度热心合作的梁启超最终也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乃至把兴中会仅有的华侨基础也占去了。
即使在以海外华侨和受过西式教育的人群为基础的兴中会内部,也有过主角之争。
在孙中山与杨衢云之间,早就为谁做会长、谁在武装起义成功后做总统而发生分歧。
杨衢云原名杨飞鸿,1861年12月生于香港,比孙中山年长5岁。
他早年就读于香港英文学院,毕业后执教于圣约瑟学院,后在招商局任职,对西方文明有相当的了解。
1891年,他与孙中山初识,但没有深交。
1892年3月13日,当他和香港公务局职员谢瓒泰等16人发起以“开通民智”为信条的“辅仁文社”时,孙中山并没有参加。
到1895年,孙中山的檀香山兴中会与辅仁文社联合成立香港兴中会总会。
孙、杨二人在社会背景、所受教育、西学知识、兴趣爱好等方面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的。
1895年中日之间不平等的《马关条约》签字前,兴中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重阳节(10月26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孙负责军事行动,杨负责在香港筹款、购买军火、募集死士。
据说杨的朋友黄咏商把一所洋房卖了8000港币,并全部捐出。
部署已定,10月10日在香港乾亨行举行会议,“始投票选举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注:
冯自由:
《革命逸史》第四集,第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杨衢云志在必得,曾亲口对孙中山说“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
郑士良、陈少白极力反对,郑表示这个位置非孙中山莫属,“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孙中山劝止。
小小的兴中会中分成了挺孙、挺杨两派,争夺子虚乌有、八字没有一撇的“总统”位置的斗争异常激烈,乃至双方的支持者几乎为此而放弃起义计划。
当时杨的势力在兴中会占有优势,最后孙中山为避免发生内讧,顾全大局,“表示谦退”,而杨当选(注:
冯自由:
《革命逸史》初集,第24页。
据陈少白回忆,郑士良得知杨想当总统,说:
“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
”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5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
广州重阳起义计划挫败后,兴中会香港总会也随之瓦解。
此后杨在名义上担任兴中会会长达五年之久。
康有为派也更愿意与杨打交道,而事实上孙中山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影响力都要在杨之上,特别是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孙中山成了国际知名的中国革命家。
1896年11月26日,香港《德臣西报》转载日本《神户记事报》的一篇文章《中国的革新》,未署名的陈少白在文中称:
“当今对中国有深切了解而又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者,舍孙医生别无他人。
仅此勇气就足以使其整个民族复兴。
”两天后,杨的忠实追随者谢瓒泰为此郑重其事地给《德臣西报》编辑去信澄清:
“革新派的领袖是杨衢云,一位真金般高贵,白璧般无暇的进步人士,一位彻底的爱国者和革新派人物。
他被称为护国公,孙逸仙医生只不过是革新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德臣西报》在11月30日刊登了这封没有署名的来信(注:
转引自黄宇和:
《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3~106、156页。
)。
谢瓒泰对孙中山评价一直不高,他在1895年5月5日的日记中说:
“孙的提议让人嗤之以鼻。
他以为他什么事都能办到——通行无阻——纸上谈兵!
”1896年6月23日又在日记中说:
“我知道孙希望人人都听他的,这不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就他的经验来看,完全依靠他是有危险的。
”(注:
转引自黄宇和:
《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3~106、156页。
)因此,当杨衢云于1900年1月辞去名不副实的会长时,谢瓒泰才会感到惊讶,但杨解释:
“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
我向孙中山说,我十分乐意放弃我的职位,还劝告他不要促使分裂。
我也告诉他,岂止我的职位,为了事业的利益,我经常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注:
转引自薛君度:
《黄兴与中国革命》,第3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出版时没有自称兴中会的领袖和创建者,有史家认为这与杨还活着有关(杨于1901年被清廷密谋刺死)。
1910年2月,孙中山在旧金山与《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谈话时说:
“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衢云与予大闹,几至用武,谓非民国不可。
衢云死矣,予承其志誓为民国,帝制自为,吾必讨之。
”(注: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少白回忆说,孙、杨结识不久,有一天,两人为了是否建立共和而发生争论。
杨十分恼火,揪住孙中山的发辫要打他,是陈把他们挡开了。
转引自黄宇和《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第106页。
)如此看来,在杨衢云与孙中山的兴中会主角之争背后隐约可见剧本之争的闪光。
这一点几乎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史家的注意。
孙中山最初更重视的确是“驱除鞑虏”,而不是“创立民国”,其故乡广东香山有个素有帝王思想的富商刘学询,对民权思想毫不了解,孙中山早年办“农学会”,刘曾列名发起,孙中山与刘商量过广州起义的计划,刘大喜,并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居,而以孙中山为徐达、杨秀清。
孙因为刘思想陈腐而难以合作,逐渐与其疏远。
1900年,为了利用刘的巨款策动李鸿章独立、乘乱在广东起兵,孙中山仍有过推刘为帝、自揽兵政的方案(当然没有成功)。
直到1905年的同盟会成立会上,有人突然向孙中山提问:
“他日革命告成,先生其为帝王乎?
抑为民主乎?
”全场寂然,孙中山竟“不知所谓,默然莫对”。
最后是程家柽出来解了围(注:
宋教仁:
《程家柽革命大事略》,《宋教仁集》下册,第43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从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可知,杨衢云对他矢志追求民国、反对帝制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四、孙黄辞职:
“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1912年中华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出现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随后而至的孙中山辞职也是一件大事。
历史只有翻到这一页,我们才在孙中山、黄兴、蔡锷等极少数几个伟人身上看到他们勇于放弃权位的壮举。
孙、黄一度主动扮演政治主角之外的社会配角,这样的配角意识更是极为可贵的,是真正的民主思想的体现。
可惜昙花一现,很快就被一心只想扮演唯一主角的袁世凯打得粉碎。
邹鲁在《回顾录》中说:
“当时最好的现象,就是个个人心地纯洁,大公无私,毫无利禄观念;只想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中国。
因之让贤让能,却是常有的事;争权夺利,毫无所闻。
全国笼罩在新精神之下,可说前途无限光明。
不料袁世凯做了总统便想做皇帝,竟利诱威迫破坏国民道德造成以后混乱的局面。
这真是可痛心的。
”(注:
邹鲁:
《回顾录》,第44页,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
)这番话也许太简单化了,辛亥革命之后固然有革命党人功成身退、毫无权力思想的一面,但这当中照样发生过上海陈其美暗杀陶成章和广东陈炯明杀许雪秋、陈芸生以及湖南焦达峰、陈作新被杀等惨剧;另一方面,孙、黄辞让背后有复杂的现实因素,不能单纯从道德上寻找原因。
几年后(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邓泽如的信里曾重提往事:
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
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
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注: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不过,包括邹鲁、谭人凤等在内,许多人也都认为这种“谦让举动”——“是功是罪,却很难断言的”。
但无论如何,孙黄的表现确实足以一新数千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