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一.docx
《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一.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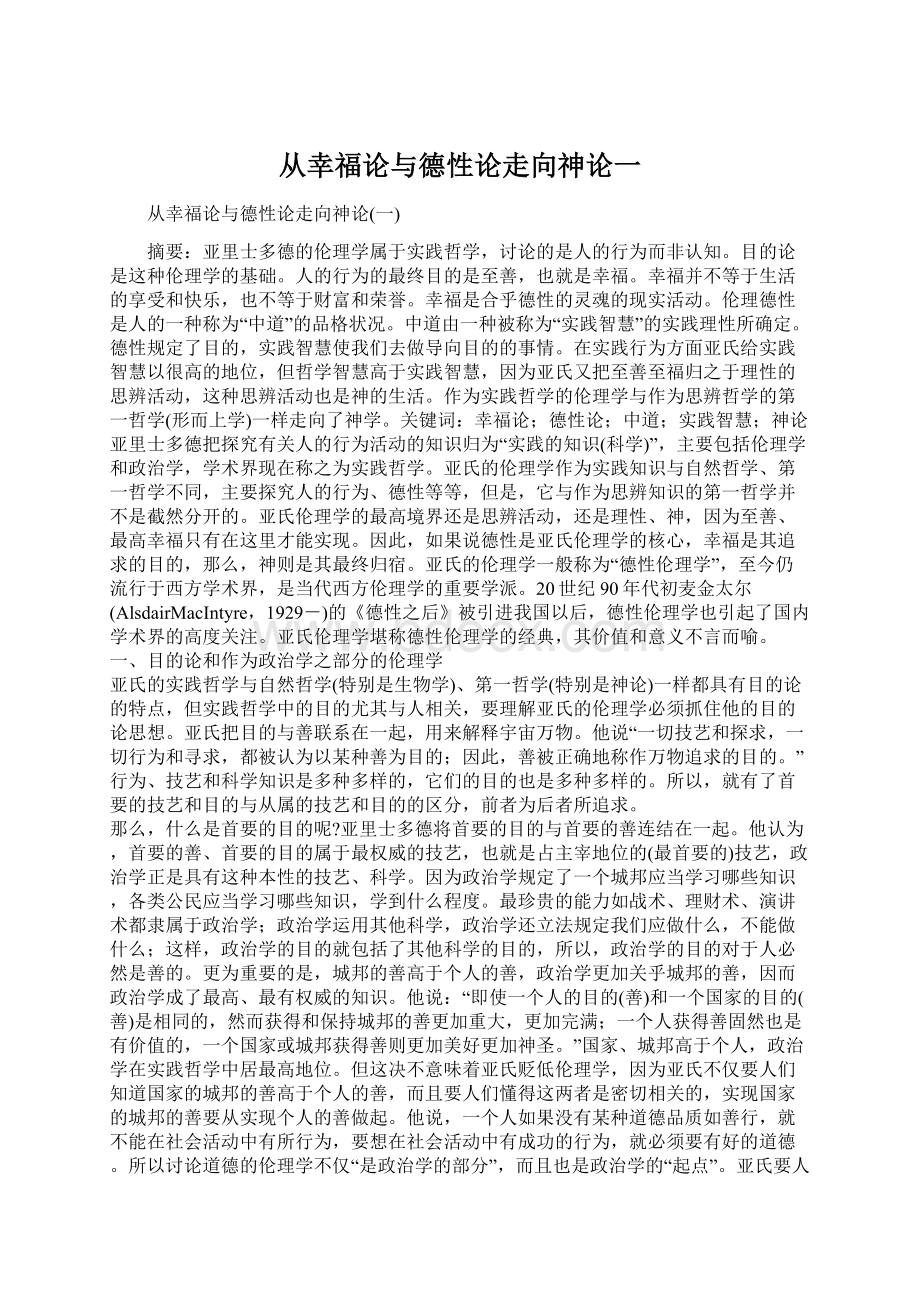
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一
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
(一)
摘要: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属于实践哲学,讨论的是人的行为而非认知。
目的论是这种伦理学的基础。
人的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至善,也就是幸福。
幸福并不等于生活的享受和快乐,也不等于财富和荣誉。
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
伦理德性是人的一种称为“中道”的品格状况。
中道由一种被称为“实践智慧”的实践理性所确定。
德性规定了目的,实践智慧使我们去做导向目的的事情。
在实践行为方面亚氏给实践智慧以很高的地位,但哲学智慧高于实践智慧,因为亚氏又把至善至福归之于理性的思辨活动,这种思辨活动也是神的生活。
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与作为思辨哲学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一样走向了神学。
关键词:
幸福论;德性论;中道;实践智慧;神论
亚里士多德把探究有关人的行为活动的知识归为“实践的知识(科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学术界现在称之为实践哲学。
亚氏的伦理学作为实践知识与自然哲学、第一哲学不同,主要探究人的行为、德性等等,但是,它与作为思辨知识的第一哲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亚氏伦理学的最高境界还是思辨活动,还是理性、神,因为至善、最高幸福只有在这里才能实现。
因此,如果说德性是亚氏伦理学的核心,幸福是其追求的目的,那么,神则是其最终归宿。
亚氏的伦理学一般称为“德性伦理学”,至今仍流行于西方学术界,是当代西方伦理学的重要学派。
20世纪90年代初麦金太尔(AlsdairMacIntyre,1929-)的《德性之后》被引进我国以后,德性伦理学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亚氏伦理学堪称德性伦理学的经典,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一、目的论和作为政治学之部分的伦理学
亚氏的实践哲学与自然哲学(特别是生物学)、第一哲学(特别是神论)一样都具有目的论的特点,但实践哲学中的目的尤其与人相关,要理解亚氏的伦理学必须抓住他的目的论思想。
亚氏把目的与善联系在一起,用来解释宇宙万物。
他说“一切技艺和探求,一切行为和寻求,都被认为以某种善为目的;因此,善被正确地称作万物追求的目的。
”行为、技艺和科学知识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就有了首要的技艺和目的与从属的技艺和目的的区分,前者为后者所追求。
那么,什么是首要的目的呢?
亚里士多德将首要的目的与首要的善连结在一起。
他认为,首要的善、首要的目的属于最权威的技艺,也就是占主宰地位的(最首要的)技艺,政治学正是具有这种本性的技艺、科学。
因为政治学规定了一个城邦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各类公民应当学习哪些知识,学到什么程度。
最珍贵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演讲术都隶属于政治学;政治学运用其他科学,政治学还立法规定我们应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政治学的目的就包括了其他科学的目的,所以,政治学的目的对于人必然是善的。
更为重要的是,城邦的善高于个人的善,政治学更加关乎城邦的善,因而政治学成了最高、最有权威的知识。
他说:
“即使一个人的目的(善)和一个国家的目的(善)是相同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更加重大,更加完满;一个人获得善固然也是有价值的,一个国家或城邦获得善则更加美好更加神圣。
”国家、城邦高于个人,政治学在实践哲学中居最高地位。
但这决不意味着亚氏贬低伦理学,因为亚氏不仅要人们知道国家的城邦的善高于个人的善,而且要人们懂得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实现国家的城邦的善要从实现个人的善做起。
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某种道德品质如善行,就不能在社会活动中有所行为,要想在社会活动中有成功的行为,就必须要有好的道德。
所以讨论道德的伦理学不仅“是政治学的部分”,而且也是政治学的“起点”。
亚氏要人们注意,不要脱离政治学来讨论伦理学,要从政治学的背景、视界讨论伦理学;反过来说,他所说的政治学不是剔除伦理学,而是包含有伦理学的意义的。
二、善和幸福论
如上所述,一切知识、技艺都以追求某种善为目的;那么,政治学、伦理学所追求的、为行动所达到的最高的善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并不反对善是幸福的观点,但是他反对从生活经验出发简单地把幸福等同于生活上的享受、快乐或者财富、荣誉等等;把这种看法视之为流俗的平庸的意见。
他提出有3种生活类型:
享乐生活、政治生活、思辨生活。
他认为,大多数人想过的享乐生活实际上完全是奴性生活,是适合于牲畜的生活,其中不乏名门贵胄。
他说:
“财富显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是为了其它东西的缘故。
”他也批评那些高贵有教养和积极活动的人把幸福与荣誉等同起来作为政治生活的目的,指出对于我们正在寻求的东西来说这太肤浅了。
因为这样的善就有赖于授予荣誉的人,而不在接受荣誉的人身上了,但善并不是这样一种东西。
而且,人们追求荣誉是为了确保善,是以他们的德性为基础的;“政治生活的目的是德性而不是荣誉”。
那么,第三种即思辨生活是否能达到幸福、善这个目的呢?
思辨生活必然涉及普遍概念即普遍的善这个问题。
亚氏说,这一探究非常难,因为它涉及善的理念(或形式),而理念论是我们尊敬的人(朋友)提出来的;不过,为了维护真理哪怕牺牲我们的友情,这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作为哲学家或爱智者;虽然真理和友情两者都是我们所珍爱的,但我们的责任要求我们更加尊重真理。
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
亚氏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分析了善的理念,认为善的理念在理论上说不通,只是个空洞的名称,在实践上对各种知识、技艺、行为都无用。
当然,亚氏反对理念论并不意味着他否定通过思辨生活寻求最高的善和幸福。
那么,究竟什么是最高的善?
如何去达到呢?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它是最完满的。
这个最终目的必须是只为它本身而决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被我们所选取所愿望所追求的,它就是幸福。
最终目的被认为是自足的。
所谓自足并不是指一个人单凭自身过着孤独的生活,而是指:
无待而有,什么都不缺,生活成为快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
“幸福是最终的和自足的东西,是行为的目的。
”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从人所特有的功能和活动能力之中深入探究幸福和善。
他认为,善和长处(优点)就存在于功能之中。
人所特有的功能应是理性的活动,一部分是服从理性的活动,一部分是具有和进行思维的活动。
人的功能是某种生命,它是遵循或包含理性原则的灵魂的现实活动。
人的善就是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如果德性有多种,则须合乎最好最完满的德性,而且整个一生都须合乎德性。
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或一个白昼,一天和短时间的合乎德性的行动并不能使人至福和幸福。
这就是说,幸福是人的合乎最佳德性的理性灵魂的持久的活动。
亚氏把善分成3类:
外在的善,身体的善和灵魂的善。
灵魂的善是最恰当的真正的善。
而且,灵魂的善与前面讲的幸福就是生活优裕、行为美好是一致的;把幸福看做生活好、行为好,与把幸福看做德性,这两者也是一致的。
但须注意,亚氏说幸福就是德性,指的是德性的现实活动而不是心灵的状态。
因为他认为,具有善和使用善、心灵的状态和心灵的现实活动是大有区别的。
心灵可以具有善而不产生任何好的结果,就好比一个睡着或完全不活动的人。
但现实活动不会这样,它必然要行动,而且行动得好。
就好比在奥林匹亚比赛中,桂冠并不给予最美和最强壮的人,而授予竞技参加者。
行为高尚者才赢得生活中的美好和善良。
亚氏又认为,这种合乎德性活动的生活本身也是快乐的,所以幸福也可以说是快乐,但这里的快乐指的是灵魂的快乐。
每个人总是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感到快乐,合乎德性的行为使爱德性的人快乐。
“幸福是世界上最好、最高尚、最快乐的事”。
关于快乐与善和幸福的关系问题也是那个时代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亚氏认为,善是一种快乐,按照人性,人总是选择快乐的,避免痛苦的;但不能简单化地说快乐就是善。
他从大量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合乎善和幸福的快乐。
他提出,快乐是和现实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快乐发生在感觉、思想或思辨和相应的对象之间,即动作者与承受者之间相互良好作用的时候。
没有现实活动就不会有快乐,快乐使现实活动因而也使人们所愿望的生活完美(完成),所以人们有充分理由追求快乐。
生活(现实活动)与快乐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还须指出的是,充分肯定、重视灵魂的善并不意味着否弃外在的善和身体的善;相反,亚氏提出,幸福要以外在的善和身体的善为工具、手段、补充才能真正达到。
在许多行动中要用朋友、财富和政治权力为工具。
有些事如果没有好的出身、孩子和美容,就会使幸福受损;相貌丑陋、出身卑贱或孤寡和没有孩子的人不能说是幸福的;孩子和朋友极其卑劣或好的孩子和朋友已经死去也不能说是幸福的。
可见灵魂的善也需要外在的善和身体的善的辅助。
三、德性论、伦理德性、中道
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把幸福看做是合乎完满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所以德性论是他的实践哲学的核心思想,不仅对伦理学而且对于政治学也同样是重要的。
德性在灵魂之中,“正是由于灵魂的德性,我们才生活得美好”。
亚里士多德根据灵魂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划分,将德性也分为两类:
理智的和伦理的。
哲学智慧、理解和实践智慧(明智)是理智德性(intellectualvirtue);慷慨、节制(谦恭)等等是伦理德性(moralvirtue)。
他认为,理智德性由教导而生成、成长,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
伦理德性则由习惯造成。
他特别强调的是,伦理德性既不是出于自然本性(因自然而存在的东西不可能改变习性,如石头向下落,火焰向上升,反之则不成),也不是反乎自然本性,而是顺乎自然本性接受下来,通过习惯达到完善。
在自然赋予我们的东西中,我们首先得到的是潜能(能力),然后展示出现实。
我们是通过先做德性行为而具有德性的。
通过做正义行为而成为正义,通过做节制或勇敢的行为而成为节制或勇敢。
亚氏特别强调,伦理德性和技艺一样是在做、行的现实之中形成的。
工匠技艺的好坏不是天生的,是在实际操作活动中造成的。
一个人是在处理与他人的行为之中成为公正或不公正的;在面临危险时人们由于习惯于恐惧或自信而采取不同的行动,有的成为勇敢的,有的成为怯懦的;欲望和愤怒的情感也一样,由于一些事情上各自的行为活动不一,有的人成为节制温和,有的人成为放纵暴戾。
“品格来自现实活动”,“品格状况是与现实活动之间的差异相对应的”。
所以,从小养成某种习惯不是件小事,而是非常重要,甚至比一切都重要。
由于伦理德性具有实践的特性,亚里士多德指出,伦理学研究并非旨在理论知识,并不是为了认知德性是什么,而是为了成为善的,否则这种探求就是无用的了;必须考察的是行为的性质,也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行动,因为行为决定了由此产生的品格状况。
在亚氏看来,对伦理德性而言,行重于知。
公正和节制是经常实施公正和节制的行为的结果。
有公正的行为才会有公正的人,有节制的行为才会有节制的人。
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光说不做,对于伦理德性是毫无意义的,好比病人光认真听医生说却不照着做,不能改善身体,空谈这样的哲学也不能改善灵魂。
那么,德性究竟是什么呢?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德性”在古希腊是一个用得很多很广的概念,指人、动物、自然物等等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优点、长处、特长、品性(品质)等等。
亚氏说:
德性就是使事物状况良好,并使它很好地发挥功能。
譬如,眼睛的德性就是使眼睛好,而且视力优良;马的德性使马成为一匹好马,而且善于奔跑。
人的德性就是人的品格状况,这种品格使人成为善(好),并且使人很好地发挥他的功能。
亚氏进一步指出,作为人的伦理德性的人的品格状态是一种“中道(中庸,mean,intermediate)”。
那么,何谓中道?
亚氏认为,中道可从两方面来看:
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两端点之间的中点,如6是10与2之间的中点,这个中点是一个,而且对所有人是一样的;相对于我们人来说,中道是指既非过度又非不足的适中点,由于是相对于人的,所以这个中点就不是一个,而且并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
所以,技艺大师都要避免过度和不足,寻求和选取“中道”——当然不是对象自身的而是相对于我们人而言的。
好的技艺成果既不能增加一点,也不能减少一点,过度和不足都会破坏技艺成果的优点。
伦理德性和技艺一样,也要瞄准“中道”,因为伦理德性关涉感受和行为,其中存在有过度、不足和中道,过度和不足造成失败,中道获得成功,得到赞扬。
成功和被赞扬是德性的两个品格,过度和不足是恶的品格,中道才是德性。
从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