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docx
《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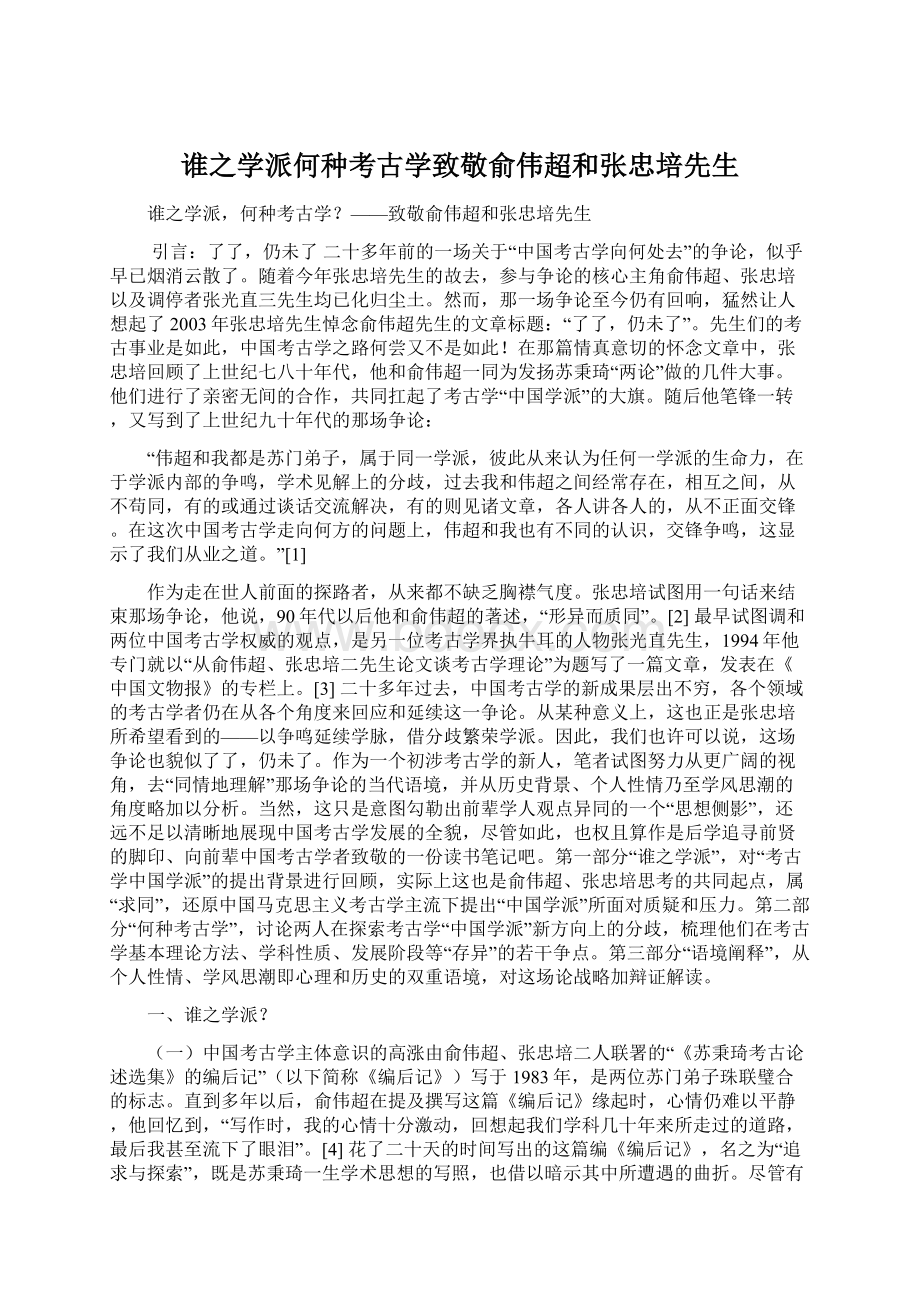
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
谁之学派,何种考古学?
——致敬俞伟超和张忠培先生
引言:
了了,仍未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场关于“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的争论,似乎早已烟消云散了。
随着今年张忠培先生的故去,参与争论的核心主角俞伟超、张忠培以及调停者张光直三先生均已化归尘土。
然而,那一场争论至今仍有回响,猛然让人想起了2003年张忠培先生悼念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标题:
“了了,仍未了”。
先生们的考古事业是如此,中国考古学之路何尝又不是如此!
在那篇情真意切的怀念文章中,张忠培回顾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和俞伟超一同为发扬苏秉琦“两论”做的几件大事。
他们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合作,共同扛起了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大旗。
随后他笔锋一转,又写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场争论:
“伟超和我都是苏门弟子,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从来认为任何一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学派内部的争鸣,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过去我和伟超之间经常存在,相互之间,从不苟同,有的或通过谈话交流解决,有的则见诸文章,各人讲各人的,从不正面交锋。
在这次中国考古学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伟超和我也有不同的认识,交锋争鸣,这显示了我们从业之道。
”[1]
作为走在世人前面的探路者,从来都不缺乏胸襟气度。
张忠培试图用一句话来结束那场争论,他说,90年代以后他和俞伟超的著述,“形异而质同”。
[2]最早试图调和两位中国考古学权威的观点,是另一位考古学界执牛耳的人物张光直先生,1994年他专门就以“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文物报》的专栏上。
[3]二十多年过去,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层出不穷,各个领域的考古学者仍在从各个角度来回应和延续这一争论。
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张忠培所希望看到的——以争鸣延续学脉,借分歧繁荣学派。
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这场争论也貌似了了,仍未了。
作为一个初涉考古学的新人,笔者试图努力从更广阔的视角,去“同情地理解”那场争论的当代语境,并从历史背景、个人性情乃至学风思潮的角度略加以分析。
当然,这只是意图勾勒出前辈学人观点异同的一个“思想侧影”,还远不足以清晰地展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全貌,尽管如此,也权且算作是后学追寻前贤的脚印、向前辈中国考古学者致敬的一份读书笔记吧。
第一部分“谁之学派”,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出背景进行回顾,实际上这也是俞伟超、张忠培思考的共同起点,属“求同”,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主流下提出“中国学派”所面对质疑和压力。
第二部分“何种考古学”,讨论两人在探索考古学“中国学派”新方向上的分歧,梳理他们在考古学基本理论方法、学科性质、发展阶段等“存异”的若干争点。
第三部分“语境阐释”,从个人性情、学风思潮即心理和历史的双重语境,对这场论战略加辩证解读。
一、谁之学派?
(一)中国考古学主体意识的高涨由俞伟超、张忠培二人联署的“《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的编后记”(以下简称《编后记》)写于1983年,是两位苏门弟子珠联璧合的标志。
直到多年以后,俞伟超在提及撰写这篇《编后记》缘起时,心情仍难以平静,他回忆到,“写作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回想起我们学科几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最后我甚至流下了眼泪”。
[4]花了二十天的时间写出的这篇编《编后记》,名之为“追求与探索”,既是苏秉琦一生学术思想的写照,也借以暗示其中所遭遇的曲折。
尽管有些小插曲,但此文于1984年一经发表,无疑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俞伟超的泪水既是对恩师的感念,也是对自己数十年亲身参与和见证这个学科所走过的道路和命运的喟叹。
共同署名的张忠培,也从不讳言中国考古学需要回答“扛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他一直把苏秉琦视为“中国考古学的旗帜与永远屹立着的丰碑”。
[5]这篇《编后记》,可以说处处积蓄着一种以建立“考古学中国学派”为己任的情怀和担当。
“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一词,是极具主体意识的提法。
苏秉琦和两位苏门弟子无疑是扛旗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研究百废待兴之际,考古学界能率先提出这一极具主体意识的概念,远早于其他学科,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
要知道,据说直到1988年的“两会”上,戴逸还以“哲学贫困”、“史学危机”、“法学幼稚”、“经济学混乱”来形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6]成为当时学界广为流传的一个断语,这其实是中国人文社科界的“集体焦虑”。
不过早在1983年,北大考古专业就从历史系独立出来,所以考古学似乎也无须划入面临“危机”的史学。
而在某种意义上,清史专家戴逸教授所不甚了解的考古学,不得不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例外”。
苏门师徒之所以敢于率先树起“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大旗,从客观上说,也是由于考古学本身的特殊性所致,考古发掘在建国后占尽地利、独享材料。
尽管与其他学科一样,与海外学术交流也是基本中断,只能闭门研学,但考古学却不至于像其他学科完全为政治挂帅左右,虽也有影响波及,但尚能保持其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还能有所发展。
[7]而历史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其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成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由于最高领袖的史学偏好,学术完全沦为“影射史学”的政治斗争工具。
此外,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社会科学,由于学科性质本身,改革开放后才大量移植西方学术概念、理论、体系,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才逐步开始反思各自学科作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问题。
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就展露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的理论雄心,在经历30多年思考之后,更明确提出“建设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其有中国的、现代化的中国考古学”。
[8]而俞伟超、张忠培合署的《编后记》,则首次将考古学的“中国学派”归结为三大特点。
想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在此仅略述之。
第一个特征,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观察分析考古现象和材料,这是具有明显时代烙印的方法论。
第二大特点,是区系类型理论,从分期分型分式到分区分系,极大拓展发展了考古类型学方法,这一条被认为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最核心特征,也是苏秉琦最大的理论创见。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强调考古学是以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为目的。
这一条其实写得比较笼统,用“激发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团结思想情感”等相对政治性的话语来表达。
或许我们可以稍微深一层次的理解为,这一条,意味着考古学“中国学派”既是对“五四”以来“疑古”思潮的回应,也是开启了后来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系列理论探讨,也不免被目为“民族主义”倾向的考古学特点。
但是这三大特征,是否足以支撑起一个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提法呢?
(二)夏鼐的一盆冷水:
中国学派特色在哪里?
毋庸置疑,建国后的中国考古学发展,无论其问题意识、思想方法,都是来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即大家所熟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等等。
对考古学理论没有太大兴趣的夏鼐都承认,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考古学思想,是“中国考古学这个新阶段的标志”。
[9]既然如此,俞、张两人把“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作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的首要特征,就不可单纯看作只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修辞书写,而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真实写照。
面对以这两位苏门弟子为代表的学术“主体意识”的冲动,夏鼐却对“中国学派”的提法泼了一盆冷水。
在1984年的夏鼐日记中,我们看到接连几天记录了他对俞、张两人的稿子以及所谓“中国学派”的看法:
2月19日星期日……阅新出的《文物》1984年第1期,主要为张忠培、俞伟超的《探索与追求》(《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的“编后记”)。
其中有些论据颇有问题,用铅笔注于旁……写信给张忠培同志。
2月20日星期一……与他们[安志敏与王仲殊]二人谈及《文物》这一期《探索与追求》一文,他们都有些意见,尤其认为关于考古学“中国学派”一称的提法,很不恰当。
[10]
又过了一天,2月22日夏鼐甚至直接找到苏秉琦,谈俞伟超、张忠培的稿子,劝苏秉琦“最好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要让以误传误”。
[11]可见夏鼐还是颇为郑重其事,认为“中国学派”的提法很不恰当,有必要当面指出。
其实据俞伟超回忆,夏鼐在1983年郑州考古学会上,就否定了考古学会的年会应讨论理论问题的提议。
正是这一刺激,才促使了《探索与追求》那篇文章的产生。
探讨夏鼐和苏秉琦在考古学研究学术背景、方法进路等方面上的异同,并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
[12]如果我们暂且忽略两位前辈大家私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那么,夏鼐认为“中国学派”提法究竟“不恰当”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月,在参加成都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夏鼐又进一步对苏秉琦在会议提出的“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进行了全面质疑:
[苏秉琦说]我国的考古工作及考古学发展已进入一个新时代,它的主要标志是:
一、已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草率的田野考古工作、工地和原始资料(鼐按:
这只是相对而言,“新时代”是质变而不是量变。
从量变到质变,什么数量才算是“新时代”呢?
)。
二、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鼐按:
曾问过这与所谓“中国学派的考古学”是否一回事?
所谓“特色”是体系的特色,或仅只内容是中国材料,犹是中国特色的历史,即中国史。
他说这是后者)。
三、已有一批在建国后新培养成长起来的专家学者(鼐按:
要有新人,是必要的,但有新人并不便是新时代,还要新人的学术思想及拿出的成果,是否足以代表一个新时代)。
[13]
夏鼐针锋相对的按语值得玩味,尤其是第二条则颇为击中要害。
其实,后来张光直对此也有过和夏鼐一样的逻辑质疑,他在为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1895-1949)》一书写的序言里问道,“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应有什么样的重要特征?
1949年以后的中国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
”[14]由于张光直的疑问并不针对具体的个人,也许更能说明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与夏鼐的质疑相比,张光直的问题不可谓不尖锐。
尽管夏鼐也承认,考古学研究对象毕竟是社会现象,“需要通过实物来研究社会组织、经济状况和文化面貌,也便是由生产方式到意识形态,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但夏鼐只是十分谨慎的认为,“我们从前曾号召要建立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中国考古学,但是现在仍是不能认为已有这样一个体系”。
[15]也许可以将夏鼐和张光直的疑问换成一种更加直白的表述:
是不是考古学“中国学派”的特色主要在于内容是中国的材料?
而“体系”即问题意识、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则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
(三)苏秉琦“一个人的学派”?
当时,俞伟超、张忠培无疑都直接感受到了来自夏鼐的压力,毕竟夏鼐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质疑至少在逻辑上说不无道理。
因为,如此若可称之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话,那么,同时代的历史学乃至其它学科只要研究对象是中国的、框架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似乎也可以称之为某某学“中国学派”了。
[16]而张光直的追问则包含了另一个视角,暗示着中西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对比,换言之,如果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特征,那么除了研究对象不同之外,与西方其他受马克思主义方法影响的考古学研究有什么区别?
比如柴尔德就接受了苏联的影响,也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
[17]又与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有何不同之处?
[18]当然,从源流上说,1949年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所受的影响,主要还是来自于苏联学者,比如苏秉琦就回忆吉谢列夫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报告指出苏联考古学与旧俄罗斯、英法美考古的区别在于两个方面:
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
一方面,“历史唯物论是抽象的灵魂,可是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真实的,要有血有肉”,另一方面“论又不能离开史,史就要讲理论”。
[19]但实际上,这也还不足以成为考古学“中国学派”的标识。
何况此后,苏秉琦很快意识到,“当时以为一手拿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一手拿着考古实物资料,两者一结合,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但结果谁都不满意,他经过反复思考后感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与考古学专业理论属于不同层次,发展中国考古学并没有现成模式,只有开辟自己的路”。
[20]直到晚年,他还强调“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和中国“大一统”观念一样,是考古学理论研究需要打破的“两个怪圈”之一。
[21]其实,俞伟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考古学的野外能力和器物分期能力都具有国际水平”,但“‘中国学派’的真正内涵(或其特征)仍未得到真正的确立或被认可”,所以他认定“中国学派”的重点还是“区系类型理论”。
[22]苏秉琦对考古学“中国学派”的问题也一直念兹在兹,1995年他到南开大学演讲时说,也回归到自己最具创见的区系类型理论:
1975年我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讲解区系类型说时,就提出过(中国学派)这一问题。
之后,在1981年和1987年分别提出来过,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探索,一个考古学上的“中国学派”已经开始出现了。
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
说什么中国学派,不就是你的学派!
[23]
苏秉琦对此不以为意,可见他对自己以区系类型的方法论为核心的思想充满信心,并在后来不断推演到对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多元论等创建,他以一己之力创设区系类型理论固然已载于中国考古学术史册。
后来,张忠培选取了六个标志性事件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分期,这六个标志分别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冈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的《瓦鬲的研究》。
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
5.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6.1984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重大课题》讲演。
[24]
他以此作为关键节点,将中国考古学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基本上以10-15年为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划分标准中,选了苏秉琦三篇文章,占了一半,具有明显的苏门色彩,因此要说是苏秉琦“一个人学派”恐怕并不为过。
不过,与其说所谓“一个人的学派”有着俞伟超、张忠培为其座师开宗立派的目的,不如说这也促进了两人对超越区系类型理论本身的所作的尝试和努力。
因为,如果说考古学“中国学派”这只是苏秉琦“一个人的学派”,则必然会遭遇瓶颈,依靠一个人开创的时代终将会过去。
此后,俞伟超、张忠培朝着不同的方向努力,于是也才有了两人在发展中国学派究竟需要“何种考古学”上的分歧。
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不断延续和发展他们老师的考古学“中国学派”。
对于这一点,两人有着清晰而坚定的认识,与俞伟超撰写《编后记》时动情落泪相比,张忠培在2009年纪念苏秉琦百年诞辰演讲时的结语,则显得掷地有声:
“当今中国考古学仍处于苏秉琦所开创的时代,我们仍要高举苏秉琦的旗帜,才能将中国考古学推向前进,才能超越苏秉琦,走出苏秉琦时代”。
[25]
二、何种考古学?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