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docx
《论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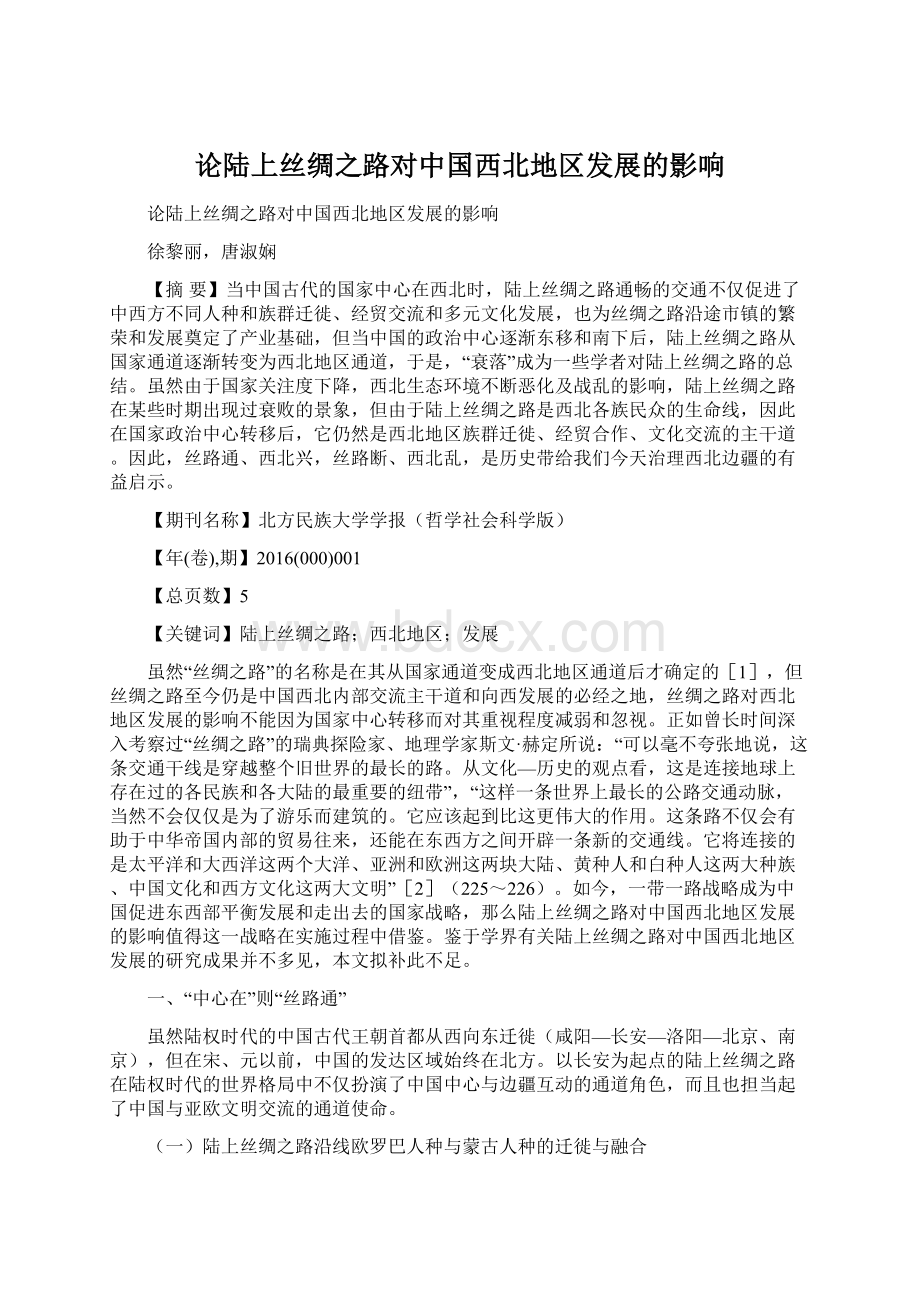
论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
论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
徐黎丽,唐淑娴
【摘要】当中国古代的国家中心在西北时,陆上丝绸之路通畅的交通不仅促进了中西方不同人种和族群迁徙、经贸交流和多元文化发展,也为丝绸之路沿途市镇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但当中国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和南下后,陆上丝绸之路从国家通道逐渐转变为西北地区通道,于是,“衰落”成为一些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总结。
虽然由于国家关注度下降,西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及战乱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在某些时期出现过衰败的景象,但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是西北各族民众的生命线,因此在国家政治中心转移后,它仍然是西北地区族群迁徙、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主干道。
因此,丝路通、西北兴,丝路断、西北乱,是历史带给我们今天治理西北边疆的有益启示。
【期刊名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00)001
【总页数】5
【关键词】陆上丝绸之路;西北地区;发展
虽然“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在其从国家通道变成西北地区通道后才确定的[1],但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国西北内部交流主干道和向西发展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对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不能因为国家中心转移而对其重视程度减弱和忽视。
正如曾长时间深入考察过“丝绸之路”的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所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
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这样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交通动脉,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游乐而建筑的。
它应该起到比这更伟大的作用。
这条路不仅会有助于中华帝国内部的贸易往来,还能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
它将连接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个大洋、亚洲和欧洲这两块大陆、黄种人和白种人这两大种族、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明”[2](225~226)。
如今,一带一路战略成为中国促进东西部平衡发展和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那么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值得这一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借鉴。
鉴于学界有关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补此不足。
一、“中心在”则“丝路通”
虽然陆权时代的中国古代王朝首都从西向东迁徙(咸阳—长安—洛阳—北京、南京),但在宋、元以前,中国的发达区域始终在北方。
以长安为起点的陆上丝绸之路在陆权时代的世界格局中不仅扮演了中国中心与边疆互动的通道角色,而且也担当起了中国与亚欧文明交流的通道使命。
(一)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的迁徙与融合
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陆上丝绸之路就已成为欧罗巴人种与蒙古人种迁徙与交流的通道,这从新疆考古挖掘的苏贝、札滚鲁克、楼兰等古墓中可以证明,如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城址东郊古墓6具头骨中,有5具人类学特征接近地中海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1具头骨具有明显蒙古人种特征”[3]。
A.基思对楼兰头骨进行了描述和测量比较之后,认为“所有的头骨代表单一的民族,具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两个大人种的特征,是一种中间类型,称之为‘楼兰型’(Loulantype)”[4]。
中国体质人类学家韩康信也认为,“从接触到的新疆古代人类头骨材料来看,时间越早的,原始欧洲人的特点越为明显,人种越为单纯。
而到了楼兰的后期,则出现了黄种人特征明显的颅骨。
韩康信将来自新疆的180多个古代人类头骨与黄河甘肃青海地区的青铜时代到汉代的400多个头骨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新疆蒙古人种是零散的、少量的,直到汉代才出现蒙古人种与白种人的混杂现象”[5]。
这说明陆上丝绸之路首先是人种迁徙与融合之路,只有人类在这条通道中循环往来时,经贸、文化交流才会随之而来。
(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经贸合作
尽管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几经变化,但从狭义上讲,它主要指东起中国,穿越西域、古印度、阿拉伯—波斯社会,一直通向希腊—罗马世界的这条道路[6]。
这条纵横交错在草原和绿洲穿行的道路,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不同族群进行商贸合作与交流的通道。
粟特人“从公元4世纪初叶开始,就在丝绸之路上形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7]。
唐代粟特人大举向塔里木盆地和中国内地进发的同时,也越过吐火罗斯坦,向印度、西藏方向挺进,并在霍城、高昌、龟兹、长安、敦煌等地留下他们贸易活动的足迹。
当时传入中国的“商品”不仅包括动植物、日用品、工业原料及各类宗教器物和书籍,也包括人口等。
巴尔托里德曾经这样评价粟特人沿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
“握有丝路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庭之间使者的往返,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撒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
”[8](6)在今天已经变成交河故城的高昌城内则设有官市,“主要交易的商品有五种:
香料、金、银、脑砂和丝,其他商品如输石、药材、铜、蟹金根和石蜜。
从交易量看,买卖双方所进行的是批发贸易而不是零售”[9]。
元朝时,金帐汗国的乌孜别克族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经新疆到内地经商,从16世纪到17世纪,从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东来的乌孜别克族人,以叶尔羌(今莎车)为中转地,经营丝绸、茶叶、瓷器、皮张、大黄和各种土特产,有些还途经阿克苏、吐鲁番、肃州,将货物转销内地[10]
(2)。
由此可见,当中国古代国家中心仍在西北时,沿陆上丝绸之路的经贸活动处于繁盛状态。
(三)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的发展
当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内地的不同民族沿陆上丝绸之路从东向西迁徙,当中亚、中东、欧洲地区不同种族的人也从西向东,由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不同民族融合之时,丝绸之路也就从地理通道变成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通道[11]。
主要表现在宗教、艺术等方面,如在宗教方面,“除了佛、道教盛行外,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相继传人中土,使中国宗教进一步多元化”[9]。
在艺术方面的交流更为突出,如“流行于粟特地区的安国乐、康国乐、胡旋舞、胡腾舞等在唐代风靡一时”[9]。
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就吸收了北非的“努巴”、中东国家的“达斯特拉赫”和中亚的“马卡姆”等的曲风和结构,与维吾尔族传统音乐舞蹈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十二木卡姆”。
从艺术形式和内容上来说,它不仅是阿尔泰语系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雅利安文化的相互吸收和借鉴,更是丝绸之路上各种不同民族相互融合的见证。
以上语言、宗教和艺术上的互相吸收和影响,为中国西北边疆的多元文化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正如学者所说:
“丝绸之路的凿通,南亚印度佛教文化、西亚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的传入、突厥游牧民族的定居,以及粟特人商贸的介入等文化大事使西域文化出现重大转折,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回鹘西迁,西域文化进入新时期;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王国、西辽帝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的兴衰更迭,西域文化高潮迭起,曲折发展。
”[12]多元文化则为中国西北地区各族民众安居乐业奠定了生活基础。
(四)西北边疆在绿洲城镇通达中保持稳定
伴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国西北边疆在通达中保持安定。
一些经贸交流的集市或交通要地逐渐发展演变为商人或当地居民的定居地,并逐渐成为城镇所在地。
如汉武帝后,“河西四郡的疆域又续有调整,并于西汉末最终形成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由西到东依次排列的格局”[13],河西四郡从此成为陆上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重要城镇。
除此之外,汉朝在西域设置的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在汉代人口超过八万,魏晋时,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近似[14]。
除龟兹外,较大的城镇还有鄯善、于阗、莎车、姑墨、疏勒等[15]。
至唐朝时,不仅横贯欧亚的中西商道畅通兴盛,而且穿越天山、昆仑山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支线也行人不绝,天山南北新兴的绿洲城镇不断涌现。
不同民族居住在这些绿洲城镇中,既维护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又保卫了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如唐初以安西都护兼四镇经略大使,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始称四镇节度使。
其后置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所统辖的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不仅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交通基础,更是西北边疆安宁的重镇。
因为安西都护府所辖区域“东至焉耆镇守八百里,西至疏勒镇守二千里,南至于阗二千里,东北至北庭府二千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北至突骑施界雁沙川一千里”[16](2999)。
显然,陆上丝绸之路的通达既保证了包括中国在内沿线各国通过商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而生息繁衍和动态适应,也为边疆的城镇兴起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繁荣的商贸合作、文化交流、城镇兴起则是中国西北边疆和谐发展的具体表现。
二、“中心移”则“变边道”
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权来说,陆上丝绸之路因中国的政治中心从西向东向南移动,而在国家战略层面则表现出重视与忽视之别,在陆上丝绸之路纵向发展轨迹上则有兴与衰之别。
但对中国西北区域而言,无论盛世或乱世,这条在亚欧大陆上延伸的丝绸之路都是西北各族民众的生命线。
(一)陆上丝绸之路的人口迁徙仍在进行
其中,从东向西的迁徙就是中国西北民间所谓“走西口”。
“早在明代开始,人们将长城沿线的关隘称为‘口’,习惯上经常把河北张家口称为‘东口’,而杀虎口位于张家口以西,所以被称为西口。
”[17]“走西口的人们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入和林格尔和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平原,也有一部分到达河套平原和后山地区。
晋西北和陕北府谷等地的汉民则出固城西口往北进入伊克昭盟。
”[18]清代后期,西口从杀虎口“改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走西口就是晋西北、雁北、陕北以及豫、鲁地区的贫苦农民到归化城以西的地方谋生的移民运动”[19]。
可见,在中国中心东移南下后,随着内地人口不断增长,富余人口便通过走西口而沿丝绸之路来到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居住。
与此同时,中亚的一些民族也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
如清代文献中将前来新疆南部探亲、经商的乌孜别克人称为安集延人,因为“乌孜别克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为安集延城、安集延街、安集延村。
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20]。
到1828年,“据查,寄居在新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和田、喀什噶尔、英吉沙各城市十年以内浩罕人289户,寄居十年以上而土著化了的浩罕人2247户。
以每户4人算,当时南疆各城约有浩罕人8900多人。
到光绪三年(1877年)为止,仅在南疆的乌孜别克族人口就有2000户以上”[20]。
以上资料显示,中国中心东移南迁后,沿陆上丝绸之路的人口迁徙与融合仍在延续。
(二)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仍在进行
与国家中心在西北时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不同的是,此时的贸易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不宜海路贸易的物品仍由陆上丝绸之路承担。
如从15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大黄贸易因海上丝绸之路潮湿的环境不宜运行而一直经由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运往威尼斯、葡萄牙或乌兹别克斯坦,茶叶贸易虽然主要通过海运,然而从中亚到俄罗斯内陆地区所需的茶叶仍走中亚陆路[21](218)。
因此,惧怕受潮而易变质的货物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输仍是中西商人们首要的选择。
第二,西北区域贸易仍由陆上丝绸之路进行。
如17世纪初,从印度越葱岭、经塔里木盆地到肃州的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所说,鸦尔看(今新疆莎车县)“商贾如鲫,百货交汇”,肃州则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22](280)。
进行贸易的货物也很多,如清道光年间,在处理张格尔叛乱善后事宜时,那彦成“彻查内地茶叶、大黄、瓷器、绸缎等项,为外夷所必需。
前因安集延等助逆滋事种种不法,已奉旨严禁卡伦断绝贸易在案”[21](84)。
这说明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是西北地区进行经贸交流的通道。
(三)西北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沿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与互相吸收在中国中心东移南迁后仍然在进行。
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藏传佛教在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几个著名历史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萨迦·班智达,他曾在凉州与阔端会谈,开启了蒙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尊八思巴为帝师,则开始了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的传播与发展,“十五、十六世纪,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亦称黄教)在西藏迅速崛起,并迅速传入到蒙古地区,成为蒙古族的全民宗教”[23](82~87)。
伊斯兰教也如此,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经过三次西征后,在中亚、中东和东欧建立了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金帐汗国,由于这些汗国建立在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为了统治当地民众的需要,这些汗国都毫无例外地皈依了伊斯兰教。
明清两代伊斯兰教沿绿洲丝绸之路继续东传,如周燮藩就认为伊斯兰教的苏非派“首先传入新疆,明清之际已在内地传播……苏非学说通过汉文著译而作为性理之学得到传播,对内地穆斯林产生过深刻影响。
新疆依禅派对内地的渗透,成为甘、宁、青等地一些门宦的道统传授渊源”[24]。
以上两种宗教在中国古代中心东移南迁后,逐渐在中国西北落户生根,并促进了中国西北多元宗教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中国西北多元文化的深入发展。
如甘肃作为过渡地带,就是通过连接丝绸之路、藏彝走廊和长城而形成多元文化地带[11]。
青海、甘肃两省作为多民族省份,新疆和宁夏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区域则充分体现了多民族的文化特征。
因此,各个民族的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多样性人文生态中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以上资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东移南迁,沿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北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多元文化区域。
三、结语
“丝绸之路”之名是在丝绸之路从国家通道变为区域通道后,被德国地理学家命名且为沿线各国广泛认同的名称,反映了不同文明的人借丝绸光滑的质地期许这条道路永远畅通的象征意义。
因为在以马和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中国陆权时代,丝绸只是作为奢侈品主要流通在贵族阶层,布衣才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所需。
对于由陆海空硬边疆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伸缩于硬边疆和软边疆相交织的现代国家来说,“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中国适应全球化与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必然选择。
因此,维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是西北地区发展和西北边疆安宁的基石,也是中国沿丝路走出去的前提。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北地区发展的影响,其经验与教训必须记取。
这一经验与教训就是丝路通、西北兴,丝路阻、西北乱。
因为中国西北地区虽然领土辽阔,但绝大多数区域是由戈壁、沙漠和绿洲组成的生态文化区域,适合人居住和生存的区域只有绿洲。
那么,将绿洲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当然就成为唯一通向边疆的通道和各族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地带。
因此,保护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障丝绸之路通畅与顺达,中国西北地区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互和谐的环境中真正走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孟群.丝绸之路的兴衰[J].中国投资,2014(9).
[2][瑞典]斯文·赫定.丝绸之路[M].江红,李佩娟,译.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3]韩康信.新疆楼兰城郊古墓人骨人类学特征的研究[J].人类学学报,1986(3).
[4][英]A.基思.塔里木盆地古墓地出土的头骨[J].英国人类学研究所杂志,1929(第59卷).
[5]南向红.洋海发现:
东西方文明凿通在丝路之前[N].南方周末,2007-02-01.
[6]周义颦.1979—2009年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34).
[7]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J].西域研究,2005
(2).
[8][俄]维·维·巴尔托里德.中亚简史[M].耿世民,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5.
[9]李瑞哲.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分析[J].兰州大学学报,2009(3).
[10]米娜瓦尔·艾比布拉·努尔.中国乌孜别克族[M].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11]徐黎丽,杨朝晖.民族走廊的延伸与国家边疆的拓展——以长城、丝绸之路、藏彝走廊为例[J].思想战线,2012(4).
[12]李竞成.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特质[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4(4).
[13]李炳泉:
西汉河西四郡的始置年代及疆域变迁[J].东岳论丛,2013(12).
[14]殷晴.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对新疆开发史上若干问题的思考[J].西域研究,2001(4).
[15]石培基,李鸣骥.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J].人文地理,2000(15).
[1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七)[M].王文楚,等,校点.中华书局,2007.
[17]珠飒,佟双喜.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J].山西大学学报,2007
(2).
[18]王俊斌,王守恩.“走西口”与近代内蒙古中西部的土地荒漠化[J].沧桑,2004(5).
[19]刘春玲.试析清代走西口的成因[J].阴山学刊,2004
(2).
[20]房若愚.新疆乌孜别克族经商传统与人口城市化[J].新疆社会科学,2005(5).
[21]潘志平.浩罕国与西域政治[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2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77.
[23]全荣.蒙古族宗教研究综述[A].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学研究年鉴》编辑部.蒙古学研究年鉴[Z].2005.
[24]周燮藩.苏非主义与明清之际的中国伊斯兰教[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
(1).
【责任编辑冯雪红】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民族关系比较研究”(14XMZ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