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片叶子中英对照.docx
《后一片叶子中英对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后一片叶子中英对照.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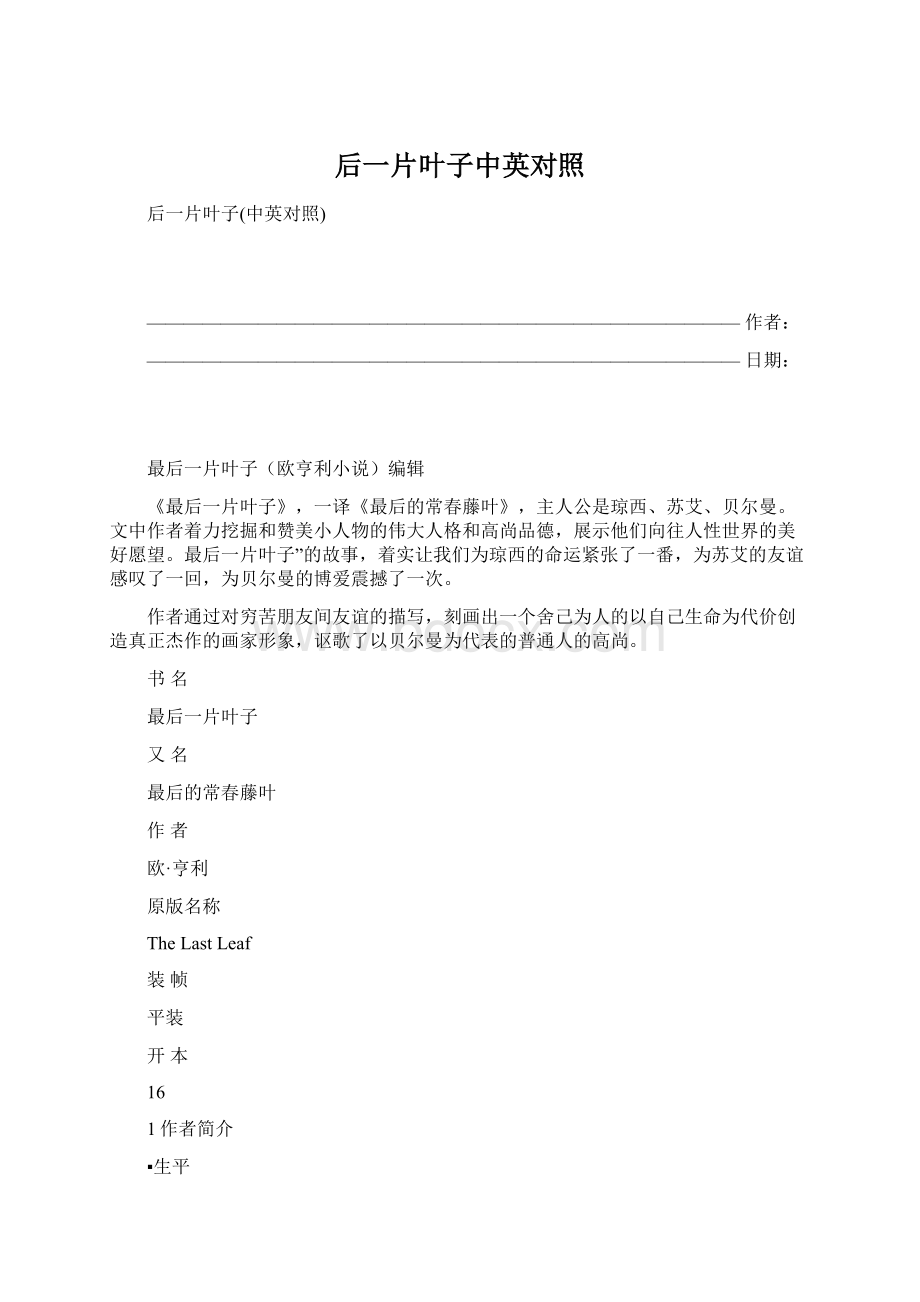
后一片叶子中英对照
后一片叶子(中英对照)
————————————————————————————————作者:
————————————————————————————————日期:
最后一片叶子(欧亨利小说)编辑
《最后一片叶子》,一译《最后的常春藤叶》,主人公是琼西、苏艾、贝尔曼。
文中作者着力挖掘和赞美小人物的伟大人格和高尚品德,展示他们向往人性世界的美好愿望。
最后一片叶子”的故事,着实让我们为琼西的命运紧张了一番,为苏艾的友谊感叹了一回,为贝尔曼的博爱震撼了一次。
作者通过对穷苦朋友间友谊的描写,刻画出一个舍己为人的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创造真正杰作的画家形象,讴歌了以贝尔曼为代表的普通人的高尚。
书名
最后一片叶子
又名
最后的常春藤叶
作者
欧·亨利
原版名称
TheLastLeaf
装帧
平装
开本
16
1作者简介
▪生平
▪手法
2作品内容
3作品原文
▪中文原文
▪英文原文
4作品赏析
1作者简介编辑
生平
1862年9月11日,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欧·亨利(O.Henry)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有个名叫格林斯波罗的小镇。
曾被评论界誉为曼哈顿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国现代短篇小说之父。
1862年他出身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波罗镇一个医师家庭。
父亲是医生。
他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WilliamSydneyPorter)。
他所受教育不多,15岁便开始在药房当学徒,20岁时由于健康原因去德克萨斯州的一个牧场当了两年牧牛人,积累了对西部生活的亲身经验。
1884年以后做过会计员、土地局办事员、新闻记者。
此后,他在德克萨斯做过不同的工作,包括在奥斯汀银行当出纳员。
他还办过一份名为《滚石》的幽默周刊,并在休斯敦一家日报上发表幽默小说和趣闻逸事。
1887年,亨利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儿。
正当他的生活颇为安定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改变他命运的事情。
1896年,奥斯汀银行指控他在任职期间盗用资金。
他为了躲避受审,逃往洪都拉斯。
1897年,后因回家探视病危的妻子被捕入狱,判处5年徒刑。
在狱中曾担任药剂师,他创作第一部作品的起因是为了给女儿买圣诞礼物,但基于犯人的身份不敢使用真名,乃用一部法国药典的编者的名字作为笔名,在《麦克吕尔》杂志发表。
1901年,因“行为良好”提前获释,来到纽约专事写作。
正当他的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健康状况却开始恶化,于1910年病逝。
欧·亨利在大概十年的时间内创作了短篇小说共有300多篇,收入《白菜与国王》(1904)[其唯一一部长篇,作者通过四五条并行的线索,试图描绘出一幅广阔的画面,在写法上有它的别致之处。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小说章与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够紧密,各有独立的内容]、《四百万》(1906)、《西部之心》(1907)、《市声》(1908)、《滚石》(1913)等集子,其中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的作品为最著名。
他把那儿的街道、小饭馆、破旧的公寓的气氛渲染得十分逼真,故有“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之称。
他曾以骗子的生活为题材,写了不少短篇小说。
作者企图表明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里,有不少人就是高级的骗子,成功的骗子。
欧·亨利对社会与人生的观察和分析并不深刻,有些作品比较浅薄,但他一生困顿,常与失意落魄的小人物同甘共苦,又能以别出心裁的艺术手法表现他们复杂的感情。
他的作品构思新颖,语言诙谐,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因此,他最出色的短篇小说如《爱的牺牲》(AServiceofLove)、《警察与赞美诗》(TheCopandtheAnthem)、《带家具出租的房间》(TheFurnishedRoom)、《麦琪的礼物》(TheGiftoftheMagi)、《最后的常春藤叶》(TheLastLeaf)等都可列入世界优秀短篇小说之中。
他的文字生动活泼,善于利用双关语、讹音、谐音和旧典新意,妙趣横生,被喻为[含泪的微笑]。
他还以准确的细节描写,制造与再现气氛,特别是大都会夜生活的气氛。
手法
欧·亨利还以擅长结尾闻名遐迩,美国文学界称之为“欧·亨利式的结尾”他善于戏剧性地设计情节,埋下伏笔,作好铺垫,勾勒矛盾,最后在结尾处突然让人物的心理情境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或使主人公命运陡然逆转,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拍案称奇,从而造成独特的艺术魅力。
有一种被称为“含泪的微笑”的独特艺术风格。
欧·亨利把小说的灵魂全都凝聚在结尾部分,让读者在前的似乎是平淡无奇的而又是诙谐风趣的娓娓动听的描述中,不知不觉地进入作者精心设置的迷宫,直到最后,忽如电光一闪,才照亮了先前隐藏着的一切,仿佛在和读者捉迷藏,或者在玩弄障眼法,给读者最后一个惊喜。
在欧·亨利之前,其他短篇小说家也已经这样尝试过这种出乎意料的结局。
但是欧·亨利对此运用得更为经常,更为自然,也更为纯熟老到。
2作品内容编辑
穷画家琼珊得了重病,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对面树上的常春藤叶子不断被风吹落,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的凋谢代表自己的死亡,于是她失去了生存的意志。
医生认为再这样下去琼珊会死去。
贝尔曼,一个伟大的画家,在听完苏艾讲述室友琼珊的事情后,夜里冒着暴雨,用心灵的画笔画出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春藤叶,让琼珊重拾对生命的希望,而自己却因此患上肺炎,去世了。
3作品原文编辑
中文原文
在华盛顿广场西面的一个小区里,街道仿佛发了狂似的分成了许多叫做“巷子”的小胡同。
这些“巷子”形成许多奇特的角度和曲线。
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
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他的可贵之处。
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在这条街上转弯抹角、大兜圈子的时候,突然碰到一毛钱也没收到、空手而归的自己,那才有意思呢!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了。
他们逛来逛去,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
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烘锅,组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在一座矮墩墩的的三层楼砖屋的顶楼设立了她们的画室。
“琼珊”是琼西的昵称。
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
她们是在德尔蒙戈饭馆吃客饭时碰到的,彼此一谈,发现她们对艺术、饮食、衣着的口味十分相投,结果便联合租下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
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
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绅士。
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
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一成希望,”他说,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这一成希望在于她自己要不要活下去。
人们不想活,情愿照顾殡仪馆的生意,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
你的这位小姐满肚子以为自己不会好了。
她有什么心事吗?
”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海湾。
”苏艾说。
“绘画?
——别瞎扯了!
她心里有没有值得想两次的事情。
比如说,[1]男人?
”
“男人?
”苏艾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
“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
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
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艾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
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做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
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
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艾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
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珊的眼睛睁得很大。
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艾关切地看了看窗外。
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
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
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
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亲爱的?
”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
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
我数得头都疼了。
但是现在好数了。
又掉了一片。
只剩下五片了。
”
“五片什么,亲爱的。
告诉你的苏艾。
”
“叶子。
常春藤上的。
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
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
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
“哟,我从来没听过这么荒唐的话,”苏艾满不在乎地说,“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同你的病有什么相干?
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
得啦,你这个淘气的姑娘。
不要说傻话了。
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好的几率有十比一!
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
喝点汤吧,让苏艾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买些猪排给自己解解馋。
”
“你不用买酒了,”琼珊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
不,我不想喝汤。
只剩下四片了。
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
然后我也要去了。
”
“琼珊,亲爱的,”苏艾俯着身子对她说,“等我画完行吗?
明天我一定得交出这些插图。
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
“你就不能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画吗?
”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要在这儿陪你,和你在一起,”苏艾说,“再说,我不喜欢你老是盯着那些叶子看。
”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珊说着,便闭上了眼睛。
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
“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
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
“你争取睡一会儿,”苏艾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曼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
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你不要动,等我回来。
”
老贝尔曼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
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
贝尔曼是个失败的画家。
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
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
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
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
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
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犬。
苏艾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贝尔曼,满嘴酒气扑鼻。
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都还没等着。
苏艾把琼珊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珊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曼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
不,我才没功夫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
你怎么可以让她胡思乱想?
唉,可怜的琼珊小姐。
”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艾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
好吧,贝尔曼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算了,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啰唆鬼。
”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
”贝尔曼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
走,我和你一块去。
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
老天爷,像琼珊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
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那时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
“
“一定的!
”
他们上楼以后,琼珊正睡着觉。
苏艾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曼到隔壁屋子里去。
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
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
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
贝尔曼穿着他的旧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艾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珊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
”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艾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
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
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
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
”琼珊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
我听见风声了。
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
“哎呀,哎呀,”苏艾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
我可怎么办呢?
”
可是琼珊不回答。
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
那些把她和友谊极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
后来,夜的来临带来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珊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枯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珊躺着对它看了许久。
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儿,苏艾,”琼珊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曾经有多么坏。
想死是有罪的。
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
“苏艾,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艾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
”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艾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
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
他的名字叫贝尔曼......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
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
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
第二天,医生对苏艾说:
“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
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
下午苏艾跑到琼珊的床前,琼珊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
苏艾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曼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
他只病了两天。
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
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
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
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
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曼的杰作。
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
英文原文
InalittledistrictwestofWashingtonSquarethestreetshaveruncrazyandbrokenthemselvesintosmallstripscalled"places."These"places"makestrangeanglesandcurves.OneStreetcrossesitselfatimeortwo.Anartistoncediscoveredavaluablepossibilityinthisstreet.Supposeacollectorwithabillforpaints,paperandcanvasshould,intraversingthisroute,suddenlymeethimselfcomingback,withoutacenthavingbeenpaidonaccount!
So,toquaintoldGreenwichVillagetheartpeoplesooncameprowling,huntingfornorthwindowsandeighteenth-centurygablesandDutchatticsandlowrents.ThentheyimportedsomepewtermugsandachafingdishortwofromSixthAvenue,andbecamea"colony."
Atthetopofasquatty,three-storybrickSueandJohnsyhadtheirstudio."Johnsy"wasfamiliarforJoanna.OnewasfromMaine;theotherfromCalifornia.Theyhadmetatthetabled'hôteofanEighthStreet"Delmonico's,"andfoundtheirtastesinart,chicorysaladandbishopsleevessocongenialthatthejointstudioresulted.
ThatwasinMay.InNovemberacold,unseenstranger,whomthedoctorscalledPneumonia,stalkedaboutthecolony,touchingonehereandtherewithhisicyfingers.Overontheeastsidethisravagerstrodeboldly,smitinghisvictimsbyscores,buthisfeettrodslowlythroughthemazeofthenarrowandmoss-grown"places."
Mr.Pneumoniawasnotwhatyouwouldcallachivalricoldgentleman.AmiteofalittlewomanwithbloodthinnedbyCaliforniazephyrswashardlyfairgameforthered-fisted,short-breathedoldduffer.ButJohnsyhesmote;andshelay,scarcelymoving,onherpaintedironbedstead,lookingthroughthesmallDutchwindow-panesattheblanksideofthenextbrickhouse.
OnemorningthebusydoctorinvitedSueintothehallwaywithashaggy,greyeyebrow.
"Shehasonechancein-letussay,ten,"hesaid,asheshookdownthemercuryinhisclinicalthermometer."Andthatchanceisforhertowanttolive.Thiswaypeoplehaveoflining-uonthesideoftheundertakermakestheentirepharmacopoeialooksilly.Yourlittleladyhasmadeuphermindthatshe'snotgoingtogetwell.Hassheanythingonhermind?
"
"She-shewantedtopainttheBayofNaplessomeday."saidSue.
"Paint?
-bosh!
Hassheanythingonhermindworththinkingtwice-amanforinstance?
"
"Aman?
"saidSue,withajew's-harptwanginhervoice."Isamanworth-but,no,doctor;thereisnothingofthekind."
"Well,itistheweakness,then,"saidthedoctor."Iwilldoallthatscience,sofarasitmayfilterthroughmyefforts,canaccomplish.ButwhenevermypatientbeginstocountthecarriagesinherfuneralprocessionIsubtract50percentfromthecurativepowerofmedicines.IfyouwillgethertoaskonequestionaboutthenewwinterstylesincloaksleevesIwillpromiseyouaone-in-fivechanceforher,insteadofoneinten."
AfterthedoctorhadgoneSuewentintotheworkroomandcriedaJapanesenapkintoapulp.ThensheswaggeredintoJohnsy'sroomwithherdrawingboard,whistlingragtime.
Johnsylay,scarcelymakingarippleunderthebedclothes,withherfacetowardthewindow.Suestoppedwhistling,thinkingshewasasleep.
Shearrangedherboardandbeganapen-and-inkdrawingto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