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选中篇小说跑路作者袁亚鸣.docx
《期刊精选中篇小说跑路作者袁亚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期刊精选中篇小说跑路作者袁亚鸣.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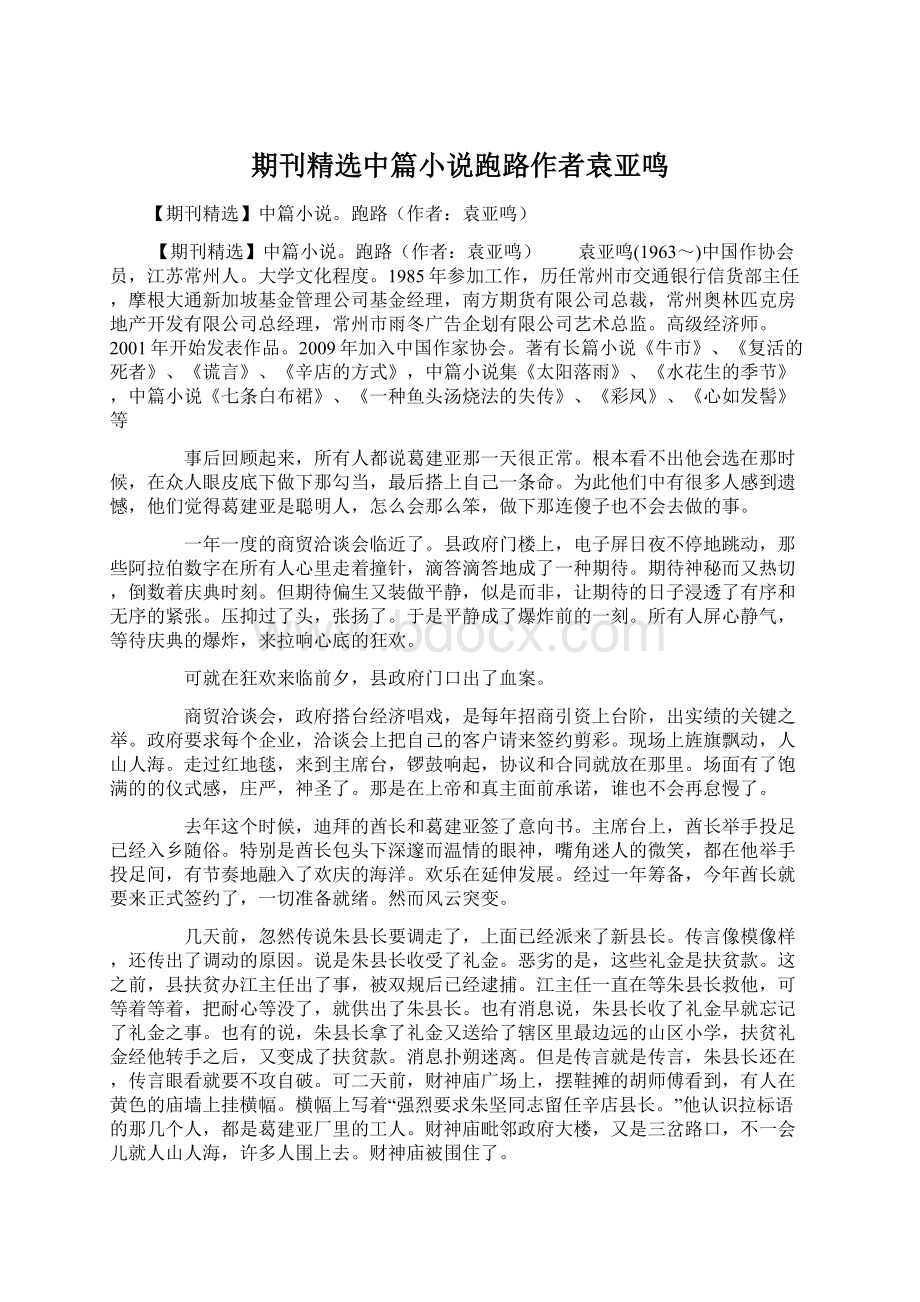
期刊精选中篇小说跑路作者袁亚鸣
【期刊精选】中篇小说。
跑路(作者:
袁亚鸣)
【期刊精选】中篇小说。
跑路(作者:
袁亚鸣) 袁亚鸣(1963~)中国作协会员,江苏常州人。
大学文化程度。
1985年参加工作,历任常州市交通银行信货部主任,摩根大通新加坡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南方期货有限公司总裁,常州奥林匹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州市雨冬广告企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高级经济师。
2001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牛市》、《复活的死者》、《谎言》、《辛店的方式》,中篇小说集《太阳落雨》、《水花生的季节》,中篇小说《七条白布裙》、《一种鱼头汤烧法的失传》、《彩凤》、《心如发髻》等
事后回顾起来,所有人都说葛建亚那一天很正常。
根本看不出他会选在那时候,在众人眼皮底下做下那勾当,最后搭上自己一条命。
为此他们中有很多人感到遗憾,他们觉得葛建亚是聪明人,怎么会那么笨,做下那连傻子也不会去做的事。
一年一度的商贸洽谈会临近了。
县政府门楼上,电子屏日夜不停地跳动,那些阿拉伯数字在所有人心里走着撞针,滴答滴答地成了一种期待。
期待神秘而又热切,倒数着庆典时刻。
但期待偏生又装做平静,似是而非,让期待的日子浸透了有序和无序的紧张。
压抑过了头,张扬了。
于是平静成了爆炸前的一刻。
所有人屏心静气,等待庆典的爆炸,来拉响心底的狂欢。
可就在狂欢来临前夕,县政府门口出了血案。
商贸洽谈会,政府搭台经济唱戏,是每年招商引资上台阶,出实绩的关键之举。
政府要求每个企业,洽谈会上把自己的客户请来签约剪彩。
现场上旌旗飘动,人山人海。
走过红地毯,来到主席台,锣鼓响起,协议和合同就放在那里。
场面有了饱满的的仪式感,庄严,神圣了。
那是在上帝和真主面前承诺,谁也不会再怠慢了。
去年这个时候,迪拜的酋长和葛建亚签了意向书。
主席台上,酋长举手投足已经入乡随俗。
特别是酋长包头下深邃而温情的眼神,嘴角迷人的微笑,都在他举手投足间,有节奏地融入了欢庆的海洋。
欢乐在延伸发展。
经过一年筹备,今年酋长就要来正式签约了,一切准备就绪。
然而风云突变。
几天前,忽然传说朱县长要调走了,上面已经派来了新县长。
传言像模像样,还传出了调动的原因。
说是朱县长收受了礼金。
恶劣的是,这些礼金是扶贫款。
这之前,县扶贫办江主任出了事,被双规后已经逮捕。
江主任一直在等朱县长救他,可等着等着,把耐心等没了,就供出了朱县长。
也有消息说,朱县长收了礼金早就忘记了礼金之事。
也有的说,朱县长拿了礼金又送给了辖区里最边远的山区小学,扶贫礼金经他转手之后,又变成了扶贫款。
消息扑朔迷离。
但是传言就是传言,朱县长还在,传言眼看就要不攻自破。
可二天前,财神庙广场上,摆鞋摊的胡师傅看到,有人在黄色的庙墙上挂横幅。
横幅上写着“强烈要求朱坚同志留任辛店县长。
”他认识拉标语的那几个人,都是葛建亚厂里的工人。
财神庙毗邻政府大楼,又是三岔路口,不一会儿就人山人海,许多人围上去。
财神庙被围住了。
朱县长要走了?
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在边上解释,不希望朱县长走的可以在横幅上签名。
县里的人第一次撞到这种事,不断有人过去,在横幅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后来组织部门来调查这件事,胡师傅紧握鞋掌的手颤动起来。
他激动地说大家签名留朱县长,都是自愿的,我也签了,没有人来叫我去签,也没有人给我钱叫我去签。
签名的有上千人,其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公务员,甚至包括六七十岁的老人。
胡师傅说我是真心希望朱县长能留在这里为我们办好事才去签名的。
他说他摆摊的地方原来是个斜坡,一下雨就满是泥泞,整修后这里变成了步行街,不仅平整,而且相关部门还给他划好了摊位。
在这里揽活并不收费。
步行街项目,正是在朱县长主导下修建的。
集会影响到了交通,加上没有事先申报,警察干预了。
有几个不买账的,直接冲撞了起来,撕破了几件衣服,有两个人,鼻子流了血。
成了血案。
那次集会确实有蹊跷之处。
说有组织吧,所有签字的人都很真诚,说没有组织吧,可那天的活动层次分明,内容层出不尽。
所有人都知道葛建亚跟朱县长关系好,所以这一切被认为是葛建亚策划和组织实施的。
葛建亚的企业能有今天,绝对离不开朱县长。
朱县长多次为葛建亚招商引资,迪拜的这个项目就是他亲自出马,才洽谈成功的。
这是这个县史上第一个境外项目,总投资超过3亿。
现在离项目签约的日子不到十天,朱县长怎能被调离呢?
但不管人们怎么想,朱县长调离的结局已无法改变。
朱县长真被调离了。
调到地区行署当建委副主任,享受正处级。
调令来得不是时候。
起码应该等到洽谈会结束。
但事实上不是,调动显出了刻不容缓的神色。
人们纷纷猜疑,正是葛建亚组织的挽留事件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上级下决心。
可一个政声显赫,为百姓称道的好官为何调走?
一个产值数10亿,承担县财政半壁江山的企业家,又为何要用这样的方式挽留父母官?
人们再次议论纷纷。
这就有点乱了。
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朱县长身上,是各种各样的情绪。
情绪是可怕的,有情绪就会出问题,因此问题当时就有了苗头,但没人重视。
当时一切很平静。
特别平静。
事后想想,当时的平静太不正常了。
尤其是葛建亚,没有任何异常举止,该说话说话,该举杯举杯,该签约签约。
一切妥帖到位,丝毫不反常,更不要谈情绪化了。
这使人们相信,他做他的企业,他的企业和朱县长调动没有任何关系。
再看朱县长,虽然卸任,但他是迪拜酋长的朋友,如果他情绪反常,酋长朋友就会感觉异样,这个项目将结局难料。
所以阿拉伯酋长硬拉朱县长照像时,他红光满面,嘴角抿得很紧,笑得很自信。
反而是新来的县长在边上,有些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阿拉伯朋友在洽谈会上成功签约,证明了朱县长是一个讲党性、讲友情的好干部。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样的平静下面,一波超级巨变转移了人们的视线,酝酿生成了。
签约结束后,葛建亚参加交通银行牵头的银团会议。
所谓银团会议,就要说到银团贷款。
银团贷款是由一家银行牵头为主,多家银行参与的集体贷款。
一般二、三家,三、五家银行,规模不等。
这也是朱县长在辛店的创举。
根据辛店情况,政府出面与银行协调,由银行为当地企业提供贷款。
这种模式在交通银行最早的银企合作关系上,加进了政府元素。
但政府只向银行推荐、建议,最后贷不贷,贷多少,都是银行自主决定。
但是说自主决定,并不是真的跟政府一刀两断。
银行毕竟在地方上生存,要导入当地资源,就少不了政府的支援。
而且银行的主要领导,一般也有当地政府推荐,上级行审核使用。
这样一来,政府领导对银行的影响就很大。
朱县长的经验推出,受到了兄弟县市的推崇。
很多地方争相效仿,但成功的并不多。
原因是政府领导,企业和银行不仅要有良好的影响和沟通能力,还必须相互信任和默契。
尤其后者,如果做不到,事情就不好办,因而辛店的成功经验弥足珍贵。
在辛店,只要朱县长批准,就一定能取得银团货款。
很难设想换了领导,辛店银企之间还会如此默契。
特别眼下要应对流动性冲击,在央行连续调高准备金和利率,银根抽紧的局面下,企业货款越来越紧。
屋漏偏逢天大雨,这时候交行袁行长又调走了,银团会议理事长换了原则性极强的李行长。
椐说李行长来就收贷款,已经超额完成了压缩信贷规模的任务,为此还和朱县长发生了几次争执。
这次葛建亚提出用迪拜的购入资产作抵押申请贷款,这工作去年就开始做了,不仅得到袁行长支持,而且上级行领导也有过明确的态度。
照理说,这笔贷款早就可以放了,但朱县长为了体现辛店经贸工作系列成果,把迪拜项目当一个典型推出,竟然决定把货款合同放到洽谈会上去签。
那这个项目的前期投入怎么办?
朱县长叫葛建亚自己先想办法。
反正只要几个月,他抿着嘴唇笑着说,几个月的办法你终归有的吧。
他的那种笑是一种招牌,了解他的人实际上都知道他那样不是在笑,他是在下决心。
他下决心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在笑。
他下决心了,葛建亚忙说知道知道。
他听懂了朱县长的话,他可以去借高利贷。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借,也不是借了一点点了。
可是人算如天算,没想到就这几个月,金融政策完全变了。
不要说放新贷款了,就是老贷款也要只收不借。
至于说还要用境外资产作抵押,那更是乱说西游记了,这场金融风暴,就是海外资产抵押的次贷危机引起的。
本来是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转眼已变成了老虎屁股。
大家都慌了,找上级银行,上级行的领导先是支支吾吾的,后来就避而不见。
李行长本来要借机取消项目,无奈朱县长和新任县长的压力,勉强同意暂不撤销项目,并继续进行项目论证。
论证,论证是什么概念?
无限止押后,而且能不能贷款成了悬念。
如果没有了资金来源,迪拜项目就要违约,前期投入的1个多亿就要泡汤。
朱县长本来承诺只要撑几个月,可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葛建亚还能不能撑下去,他靠什么撑下去,他不抱怨吗?
这些都是所有关心这个项目的人担心的事。
可是现在在葛建亚身上,却一点看不出破绽,这正常吗?
会议由新来的县长主持,首先是葛建亚发言。
葛建亚以一贯的热情介绍自己的企业,他把他的企业发展战略归纳为“4+1”。
企业所属的四个传统行比喻为四个车轮,把一项发展目标比喻为企业腾飞的翅膀。
4个行业中,传统的外贸厂由盛转衰,正经历艰苦的结构调整,而新兴的房地产业,旅游服务业处于培育期,尚未产生收益,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对接经济加速发展,眼下唯有迪拜境外项目最有希望拉升企业规模,但这个项目急需投资。
葛建亚这份发言稿在多种场合用过。
语言出了逻辑重音,还配了肢体表达,让他的发言生动感人。
新县长带头鼓掌,给会议一开始就营造了很融洽的氛围。
接下来由总会计师雪琴发言。
每次开会前夕,雪琴都要准备几本帐,比如给银行的帐和给税务的帐,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银行的账要最大限度地体现盈利,只有赚钱多的企业,才能获得银行的青睐。
而税务,你要懂得描绘困难,亏损至少可以不缴纳所得税。
可雪琴的介绍开始不久,就被李行长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说企业报表大家都看过几遍了,你帐面上负债2.98亿,可去年财务费用就有1亿多,今年又有了几千万,这利息是怎么算出来的。
雪琴愣在那里。
葛建亚轻咳一声,语气极有分寸地答道,财务费用不一定就是银行利息。
那还有哪些呢?
李行长似乎有些尴尬,但语气穷追不舍。
比如……葛建亚停了一下,这时新县长看见他朝朱县长瞥了一眼,反正这里有清单,葛亚建马上连贯地说道,这样吧,我们会后可以向所有银行提供财务费用的明细清单。
问题还不在这里,李行长皱着眉头,翻着手上准备好的几张纸,你的负债连上银行的贷款不过5个亿,可资金占用超过12个亿,扣除自然升值因素,还有将近6个亿的资产没有来源对应,只是负债栏里有其它一项,你说说你这其他是什么概念呢?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目光扫向葛建亚。
葛建亚手上自然地颠动着一支笔,笑吟吟的,既像在思考,又不像在思考。
这个问题很尴尬,那是要把老底当众揭穿了。
回答,有难言之隐,不回答,那银行贷款还要不要?
所有人都屏心静气,这在将他的军。
但是葛建亚轻松得很,他好像早有准备,等行长说完,他就语气和缓地说道,好的,我来向大家汇报一下。
可话才开了头,电话响了。
这让新县长很意外,会议之前他看见葛建亚关机的,这响的电话是备用手机。
备用手机只有很少人知道,只有出现紧急情况才会响。
葛建亚朝新县长示意一下,然后匆匆走出去听电话。
这时候朱县长有点坐不住了,他忽然觉得,这是新县长借李行长之口在对他和葛建亚进行火力侦察,那架势,好像他们做了什么手脚似的。
他知道,葛建亚在社会上借了很多钱,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银行借不到,企业等着用。
总不能这么大的企业停下来,不做事吧?
包括迪拜项目的资金,他甚至暗示过葛建亚向社会筹集。
他本来想解释几句,可是清了清嗓子,还是忍住了。
这时候葛建亚走进来,他神色紧张,在新县长身旁弯下身来。
新县长听着听着,眉头马上锁紧了,他连声说道,那你快点去,快点去。
葛建亚起身而去,这时候会议室里一个光头跟着葛建亚站起来。
光头边走边打电话,这个人一看就不是银行或者厂里的人,他的举止与会场的气氛很不协调。
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
新县长对开会的人员解释,葛总出口的产品出了问题,人家要退货索赔,他马上要去海关处理。
葛建亚走得很急。
除了开会就一直拿在手里的小包,他什么也没有带,甚至办公室也没有回。
他带了雪琴和另外一个管质量的干部上了汽车。
在走过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又看见了那些鹅卵石。
那些石子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像是是顽童游戏间不经意的遗留物。
前些天还只是一颗一颗地出现,现在却是成双成对的了。
从汽车的反光镜里他看见光头收起了电话,放弃了对他跟踪。
他长叹一口气,一仰头靠在了汽车上。
他累极了,他一直在强迫自己演戏,每句话,每个动作,都深怕自己一不当心把角色演砸了。
现在虽然还没有彻底解脱,但是起码好先舒一口气了。
汽车开进滨城,人家海关已经下班了。
一算日子,明天就是星期六,一等就要两天,按正常情况,应当先回去,星期一再来。
可葛建亚连夜布置任务,叫雪琴他们马上开展外围工作,不要回去了。
他说回去也贷不到款了,不如早点把这里的事情解决好,多少还好带点钞票回去应应急。
雪琴说这点钱拿回去等于汤浇雪,什么用场也派不上,几个银行收贷款,弄不好还要为这点钱打起来。
葛建亚有些心不在焉,他只是随口说说,到了这一步还说什么呢?
也不是我们一个企业,连到台州那么有实力的集团资金链都断裂了,还上了报。
也只好拿点算点了。
雪琴说这样终归不是办法,现在做外贸单子,做得多亏得多;房地产压资金,付不清土地款开不了工;境外项目又在等着花钱……现在我们还在等米下锅,再过些日子,就是无米下锅了。
葛建亚叹了口气,他说你也不要多想了,我这几天趁出差的空隙,会再出去找找资金的。
说到这里,他加重了语气,我干脆现在就走,这里的事情你们先办就可以了,反正能迁就就迁就一些,能拿到现款就行。
我呢,再到省城我同学那里看看,让他们想想办法,帮我们弄点钞票过来。
雪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要再不出马,就歇搁拉倒了。
葛建亚又关照了一句什么,然后说那我先走了,如果别人问起来,先别说我在干嘛,免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人都是往你的短处上想事情的。
雪琴似有所悟,你放心吧,我懂。
葛建亚转身就走,让雪琴突然觉得葛建亚太急了,急得有点不正常。
她叫司机送他,可他夸张地作出了拒绝的动作,一刹眼就消失在马路上了。
他生怕有什么东西会把他牵挂住,影响到他的离开。
他直奔机场,一路上不停地看表,不时小声地催促出租车司机,请再开快点,赶飞机。
一见航站楼,他忽然不安起来,手指着楼,话都说不出了。
车还没停稳,他就下了车,他早准备了一张大钞给司机,钞票捏在手上,湿透了汗水。
他直奔售票处,说马上飞的飞机。
吓了人家一跳。
面前这个人慌慌张张,而且语无伦次,太可疑了。
可售票姑娘是退役空姐,似乎她更习惯微笑,先生,请你说清楚买哪里的机票。
葛建亚这才定了定神,告诉售票的姑娘航班班次,可是姑娘告诉他这个航班已经调整了,今晚只剩下最后2个航班,飞沈阳和海口。
先生只有明天走了。
明天?
葛建亚浑身一阵紧缩,露出了让人震惊的眼神。
不不不……他连声说道,我从沈阳转机,为了弥补自己失态,赶紧再解释,我有急事,有急事。
此刻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浑身大汗。
身上的衣服终于让他觉得芒刺在身。
他来到小买部,他看也没看就说买一套休闲衣服,越宽敞越好,要短裤的那种。
服务员笑了起来,她说先生可是你很瘦啊,葛建亚朝她看了一眼,不耐烦地说道,你管呢。
葛建亚没有买过衣服,可是他还是知道机场的东西太贵了,这样一套短衣短裤,居然要二千多,服务员有点着急地向他解释,这可是全棉的啊,舒服得很呐。
除了衣服,葛建亚还买了一个休闲包,他早就着迷这种能挎在肩上的包了,不要时时刻刻,把一个累人的公文包挟在手上。
葛建亚急不可耐地在更衣室换衣服,身上的衣服绑了他太久,绑得他气都透不过来了。
那套全棉全白的衣服果然舒服,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轻松感。
轻松的感觉让他疲劳万分,他想最好马上能找个地方睡一觉。
可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他浑身过电一样颤抖了一下。
他已经丢掉了所有从县城里带来的东西,唯独这个电话。
实际上对电话他也早有过细节方面的考虑,比如直接关机,或者重新启用新号码,但这在目前还是不合适。
他专门有一种方法,直接把电池倒置在电槽里,这样电话打进来,听上去一直是忙音。
好象他一直在接听电话,而不是故意不接电话。
不能关机,一关机马上会招来疑心,影响到他的计划。
他本来想换好衣服再装电话,可不等他换好衣服,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新县长找来的。
县长的语气既紧张又不失庄重,他问葛建亚情况怎么样了。
危急下葛建亚还是酝酿了感情,尽量凝重地说道,还在处理。
县长沉默片刻,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放下电话,葛建亚松了一口气,他赶紧操作电话,把通话状态调整到了永久性忙音上。
上了飞机,他很快就睡着了,连点心也没有顾得上吃。
飞机着陆后,他要了一辆车,告诉司机到机场最近的宾馆。
因为天一亮,他就要换乘最早的航班,直飞他计划许久的目的地。
葛建亚失踪了,那是从整个地球上消失。
葛建亚是从大家眼皮底下消失的。
一个产值几十个亿的老板,这种人到哪里都是中心。
想把自己消失在众人视野里,太难太难了。
领导要找你,各种各样的领导,参观访问的,赞助聚会的,催办各种指标的,通知各种会议的,下来检查问题的,包括村里的计划生育问题……各种各样的平行单位、协作单位、客户,还有名为合作的强势单位,如银行保险机构、投资公司、基金公司……各种各样的下属,无数需要签署的文件……还有亲朋好友之间的联系,应酬,不一而足,谁只要找不到他,谁就会满世界喊的名字,要是三个人连着打听不到,就是人肉搜索了。
因此他在哪里,在干什么,绝对是公开的事,公开得几乎透明。
葛建亚显然知道自己的透明度。
要挑战透明,知难而上,那要智慧和胆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
那是一种光芒。
葛建亚选择了光芒,光芒有力地覆盖了透明度,透明度耀眼了,一晃一晃的,居然就晃过了所有的人。
半个月,整整半个月没人发现他踪影,不可思议的是,明明失踪了,人们还坚决不肯相信事实。
什么概念啊,那么多资产,说不要就不要啦,那不成喇天封神榜啦?
几十年拼搏的心血,谁会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连身换洗的衣服也没拿,老娘重病在床,真一走了之,连面也不再照一下啦?
这光芒是什么光芒?
等光芒散去之后,光芒就说明了他离去的决心,还有策划的精心。
凡事精心到刻意之极,反而又返璞归真,让人看不出心思的痕迹,透明也就不透明了。
他失踪之后,人们更愿意想象他还在为企业融资奔忙。
但厂里的工人最早不稳定起来,他们怕再次遭到裁减。
人民币破七后,外贸单子一落千丈,工厂工人最多时四、五千人,现在只剩了千把人。
下来会裁谁,大家议论纷纷。
随后银行也来过问这件事了。
雪琴竭力否认葛建亚失踪,她坚定地宣称葛建亚正在千方万计地筹集资金。
李行长说筹集资金连电话也不通了吗?
李行长刚说这话,没想到雪琴眼睛一红,泪水都要出来了。
他想劝,又不知道该怎么劝,没有抓拿的样子。
雪琴一边连连摆手,一边连声说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借点钱有多难。
到了第四天,雪琴来到县长办公室,忍了忍没忍住,哭了。
新县长是那种可以信赖的人,最重要的,他代表着组织。
眼泪流给信赖的人,但新县长没有准备好,手足无措了。
忙开始劝,但越劝越乱,眼泪横飞,还捶胸顿足了。
伤心决不是一点点。
好半天,新县长才大致听明白,雪琴不是担心葛建亚失不失踪,而是担心葛建亚又去借高利贷了。
为什么要去借高利贷呢?
新县长不明白其中的奥妙,银行不是都在支持建亚集团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人家银行行长在葛亚建失踪那天会议上就提出来了。
建亚集团规模扩展得这么大,资产超过了10个亿,银行才区区两个多亿,怎么够呢?
雪琴朝朱县长看了一眼,才对新县长说道,迪拜的资金银行没到位,葛建亚把生产上的流动资金垫了进去,等到生产上要用钱,钱就没了。
于是只能向社会融资。
说是向社会融资,实际上就是高利贷。
而且个人借贷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唯有找地下钱庄。
新县长一跺脚,你们这是饮鸩止渴啊。
雪琴又哭了起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啊?
外贸业务受了影响,钱收不回来,这边生产要钱,那边新项目也要钱,银行不支持,不支持还要收贷款,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
新县长叹了口气,他看了看朱县长,他话说归说,心里明白得很,在当地,企业借高利贷已经成了一种风气。
雪琴说她和葛建亚多次找过地下钱庄,谈判的时候是不准接电话的,可从来也没有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的。
她说有几次他们拖欠了地下钱庄的利息,这次有可能是对葛建亚报复。
她说葛建亚可能会失去人身自由。
新县长说,那早点报警找人吧。
雪琴连忙摆手,她几乎带着哭腔了。
既然他说他去找钱就让他去找吧,有什么事他会和我联系的。
还是自己先找找,要是报警,银行又要出乱子。
人心不稳,企业就完了。
新县长点点头,他忽然意识到,他最后给葛建亚的那个电话,可能是葛建亚和他的最后一次通话了。
他看看朱县长,他请朱县长一齐找找葛建亚,朱县长只是点了点头,没吭声。
组织上找了他,明确了,他要留下来。
找不到葛建亚,他知道自己不能离不开辛店。
可现在他在想,光是为葛建亚借高利贷,雪琴不至于这么痛哭的,那究竟又为什么,雪琴要这么伤心呢?
在随后的日子里,雪琴并没有等来葛建亚的电话。
但她在激动之下坚信,这样的电话早晚会来,一定会来。
几天前,她刚刚获悉自己有了身孕。
几十年过去了,他未得一子。
而现在一失踪,却马上有了子嗣。
这样神圣的消息,即便身隔万水千山,就是阴阳两界了,也会有神灵相佑,可以享通的。
她必须马上行动,找到葛建亚。
她先找了葛建亚的老婆高慧,高慧在上海,她拿下了那块地之后,把那块地命名为高慧酒店,直接请上海的营销公司和策划公司帮她搞策划和营销。
听到葛建亚的名字,她就打断了雪琴的话,她的话说得很平缓,她说我在开会,随后就掐断了电话。
高慧没有葛建亚的消息,雪琴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她又打国际长途,钱多的电话却不通。
钱多是迪拜项目的负责人。
她原来不叫钱多,当过导游。
雪琴第一次看见钱多时,钱多和葛建亚站在一起,珠光宝气的样子,好象全世界的钞票都贴在了她身上,她就叫她钱多。
后来许多人都跟着她叫她钱多。
迪拜的项目最初就是钱多介绍的。
当时葛建亚去中东商务旅行,钱多是迪拜的一个导游。
迪拜项目成功后,葛建亚投过去几个亿,钱多更忙了。
找不到钱多,她又去找蔡兰英。
蔡兰英是袜业公司总裁,后来成立服装公司,她就升任袜业和服装公司总裁。
这两个产品是集团公司的产业基础,企业吃饭的项目。
当年葛建亚创业时,蔡兰英在省外贸公司做科长,专门接外贸单子。
集团公司的外贸业务最早就是蔡兰英打开的,后来蔡兰英扔掉了铁饭碗,帮助葛建亚创业,一心一意要和葛建亚结婚。
可到最后,和葛建亚结婚的却是高慧。
葛建亚失踪的消息显然让蔡兰英怒不可遏,拔卵无情的东西,雪琴看见蔡兰英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失控地颤抖。
看着她被香烟薰黄的指头,雪琴不由想起蔡兰英当年进厂之际的满头青丝。
这个企业已经费尽了蔡兰英的青春和青丝,蔡兰英仿佛变成了一面镜子,照蔡兰英,也照了她。
这个畜牲,就没有做过一件人事。
他一走子之,别人来给他擦屁股。
蔡兰英带着雪琴一起来见新县长。
蔡兰英把手里拿的一个塑料袋往新县长办公台上一放,很多药瓶纷纷滚了出来。
她的声音听上去已经沙哑不堪,我天天要吃安眠药才能困觉,可现在安眠药也没用了。
5000个工人,现在不到500个了,厂里还在欠工资,现在他走了,谁来给他当替死鬼啊。
新县长和蔡兰英最多只见过两次面,进门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认出她来。
他给蔡兰英端茶让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蔡兰英会一把扯下自己的假发套,露出满头的疥疮。
她饱含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她放开嗓子哭,吼得县政府都为之一震。
她把假发往县长台上狠狠一甩,我作什么孽啊,她喊道,我这去养猪也不做这种倒头厂长了。
说完扭头就走,一路哭天抢地,有了戏腔。
象要唱尽一辈子无穷无尽的冤屈了。
新县长刚问了一句她怎么了,不想雪琴又是干呕了一声,忍了戏腔,却泪洒襟衫,饱含委屈的泪化作离别叮咛,找朱县长想想办法吧。
就完转身而去,給新县长留下了悬念和盼头。
朱县长还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新县长去找他的时候,看见他正打电话。
朱县长收了电话,脸上笑容分明,却是撒不尽的几抹疲倦不堪。
他对新县长说,我比你急,找不到葛建亚我离不开这里。
这话有话,就像茶有回味。
这话明明没说什么,但什么又都说了。
新县长还在发愣,朱县长指指电话,我已经找到葛建亚的旅游夫人了。
她说昨天下午葛建亚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