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docx
《中国当代文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当代文学.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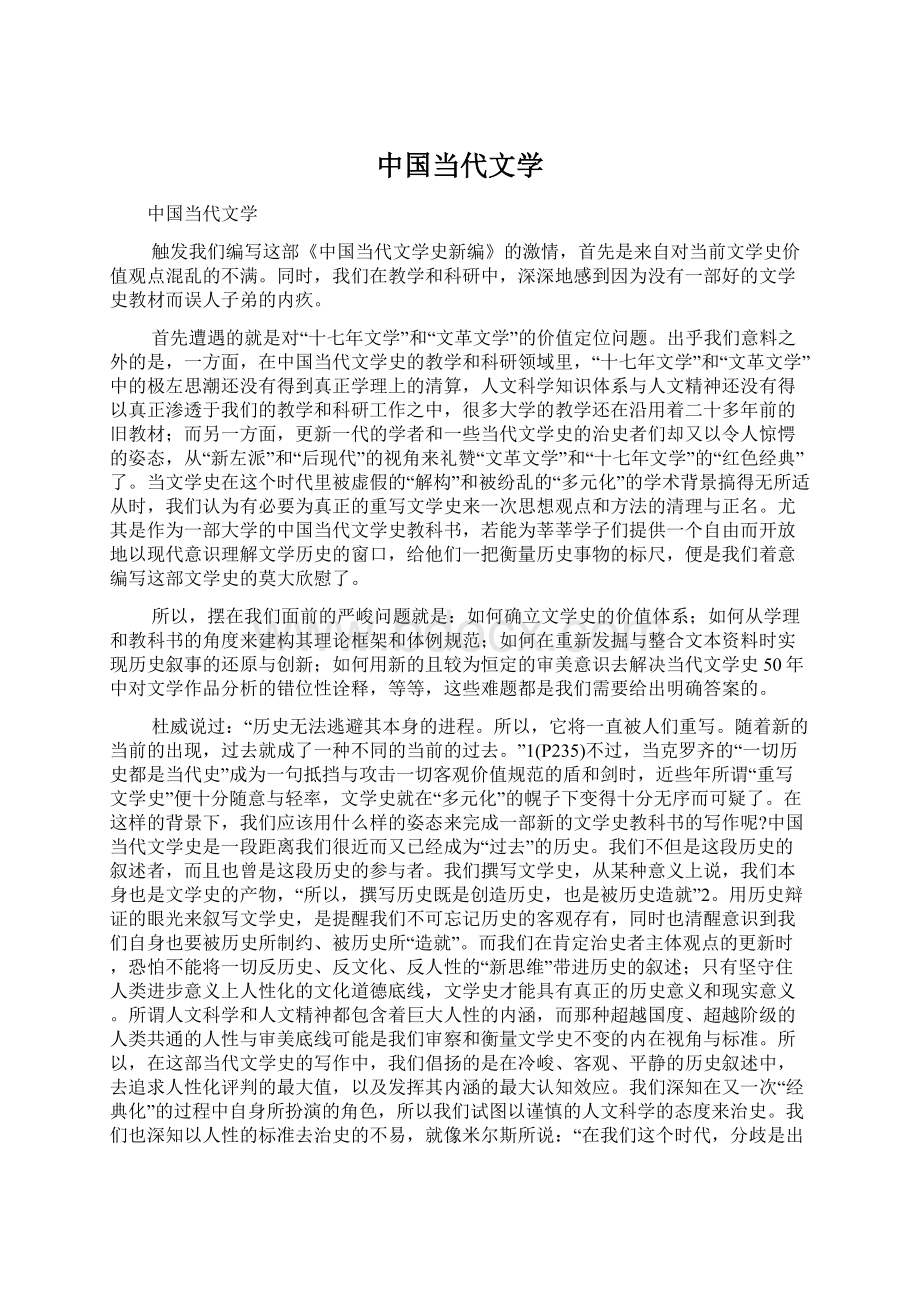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
触发我们编写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激情,首先是来自对当前文学史价值观点混乱的不满。
同时,我们在教学和科研中,深深地感到因为没有一部好的文学史教材而误人子弟的内疚。
首先遭遇的就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价值定位问题。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方面,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科研领域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极左思潮还没有得到真正学理上的清算,人文科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精神还没有得以真正渗透于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很多大学的教学还在沿用着二十多年前的旧教材;而另一方面,更新一代的学者和一些当代文学史的治史者们却又以令人惊愕的姿态,从“新左派”和“后现代”的视角来礼赞“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红色经典”了。
当文学史在这个时代里被虚假的“解构”和被纷乱的“多元化”的学术背景搞得无所适从时,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点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
尤其是作为一部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科书,若能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一个自由而开放地以现代意识理解文学历史的窗口,给他们一把衡量历史事物的标尺,便是我们着意编写这部文学史的莫大欣慰了。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
如何确立文学史的价值体系;如何从学理和教科书的角度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和体例规范;如何在重新发掘与整合文本资料时实现历史叙事的还原与创新;如何用新的且较为恒定的审美意识去解决当代文学史50年中对文学作品分析的错位性诠释,等等,这些难题都是我们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
杜威说过:
“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
所以,它将一直被人们重写。
随着新的当前的出现,过去就成了一种不同的当前的过去。
”1(P235)不过,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一句抵挡与攻击一切客观价值规范的盾和剑时,近些年所谓“重写文学史”便十分随意与轻率,文学史就在“多元化”的幌子下变得十分无序而可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完成一部新的文学史教科书的写作呢?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段距离我们很近而又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
我们不但是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而且也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
我们撰写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本身也是文学史的产物,“所以,撰写历史既是创造历史,也是被历史造就”2。
用历史辩证的眼光来叙写文学史,是提醒我们不可忘记历史的客观存有,同时也清醒意识到我们自身也要被历史所制约、被历史所“造就”。
而我们在肯定治史者主体观点的更新时,恐怕不能将一切反历史、反文化、反人性的“新思维”带进历史的叙述;只有坚守住人类进步意义上人性化的文化道德底线,文学史才能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所谓人文科学和人文精神都包含着巨大人性的内涵,而那种超越国度、超越阶级的人类共通的人性与审美底线可能是我们审察和衡量文学史不变的内在视角与标准。
所以,在这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们倡扬的是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以及发挥其内涵的最大认知效应。
我们深知在又一次“经典化”的过程中自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试图以谨慎的人文科学的态度来治史。
我们也深知以人性的标准去治史的不易,就像米尔斯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歧是出在我们人性上,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描述上。
历史学至今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局限和含义。
”3
我们认为,一些学者,尤其是一批青年学者,他们在远离了“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单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并借助某些外来理论来还原历史文化和文学语境,而这种“陌生感”给他们带来的所谓审美的新鲜和刺激,使他们在重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定位时,采用的是“否定之否定”的简单的逻辑推理。
他们试图从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挣扎出来,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态度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实行一次终极的褒扬,这种褒扬首先是建立在对这个时期文学作品艺术的“重新发现”和重新肯定的基础上。
尤为不可理解的是,他们竟然能够用西方后现代的艺术理论在反现代、反人性的“革命样板戏”中发现一种巨大的现代性元素,竟然也能够大肆宣扬“红色经典”的“革命性”主体内容。
当然,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种种复杂的生成因素,乃至“新时期文学”中的诸多值得深刻思考的文学现象,我们都应该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和评价。
但我们认为,那种忽略了具体历史语境中强大的以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意识为主体的特殊性,忽略了那时文学作品巨大的政治社会属性与人文精神被颠覆、现代化追求被阻断的历史内涵,而只把文本当作一个脱离了社会时空的、仅仅只有自然意义的单细胞来实行所谓审美解剖,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的客观审美态度。
我们所担心的是这些离当时历史语境和人性化的历史要求甚远的误读,会在变形的“经典化”过程中造成新一轮的文学史真相的颠覆。
这种颠覆将误导学生,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注入新的毒素。
也正是因为我们充分地考虑到“十七年文学”在政治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我们才在分期时将人们思想的发展脉络作为一个判断文学史发展的阶梯。
在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例如,把1962年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界线,凸显阶级斗争扩大化下文学的进一步异化的特征,显然可能从中发现一些文学发展突变的因子。
同样,在“文革文学”的梳理中,我们发现在“9·13”的“林彪事件”爆发后,人们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本质性的裂变,同时也给文学,尤其是像“朦胧诗”那样的“地下文学”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1971年就成了一个文学的敏感时间段,就以此作为文学史的一个断面,我们似乎可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文学史内容。
我们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创新”,而是为了清晰地把下一代应该看到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还给他们,也还给历史本身!
毋庸置疑,任何一部文学史的构成,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作家作品文本的解读,而任何一个解读者与他人的解读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在一种共同的具有人类通约性的人性视阈下的文本解读,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文学内涵和审美认知上的大体统一。
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绕不开的是写作主体对文学史对象的价值定位。
资料发现与价值过于显露,成为一个叙写的悖论,也就是如何处理好“史”和“论”的关系,恰当地把握两者之间的维度,让历史的客观叙述自身表现其价值观点,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工作。
一方面我们要防止资料堆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为了表达新观点,为了表现一种价值观点的超越性,而有意识地去突出被第一次历史叙述所淘汰、被人性和人道主义这把筛子筛下去的那些“二次抛光”的“新”东西,对其实行有违历史真实的褒扬性解读与阐释。
对那些能重新回到筛子里,能被我们重新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度,不要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化的偏向。
我们须得防止的另一种倾向是“混合主义”治史态度。
把历史的链条切断,把历史进程的前后次序打乱,抽象出一个个具体现象和文本来实行解读,这显然仅仅抓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从根本上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新生与没落的价值界限。
当下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针对现代性的弊病而发展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端,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其合理性,但有时却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
即使如此,西方学者也普遍认为现代性在西方社会文化进程中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而中国的“后学”者们却忽略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还是一个远远没有完成的仪式这个历史事实!
中国尚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那样的十分典型的工业文明历史阶段,它当前正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混合交杂在同一时间与空间维度平面上的历史时期,而把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硬性地移植和使用到中国来,就形成了严重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成为防碍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的一种反动力。
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质的某些极左的思想都当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华,这无疑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嘲讽与亵渎。
西方的后现代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试图更符合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人性发展的要求,是他们的文化发展到一个更高历史阶段的精神文化诉求。
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却是一古脑儿地盲目反现代性的,这恰恰是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语境,很多理论根本不符合当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实际,所以,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拙劣的效颦只能给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
针对重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肯定“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学术背景,我们要持有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基本文化批判立场。
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点,貌似历史的公允,将历史的环链紧紧相扣,其实是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巨大差异性,取消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点、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本质上的区别。
通常说“新时期文学”还有一些旧的因素在延续,如一些“左”的倾向没有肃清,作家头脑中的种种旧观点在创作中还时有表现,等等。
但有些人却使用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从“五四”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无差别的历史时段。
在他们看来,批判“文革”的文学叙事策略和修辞方法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叙写,并由此抽象出一个虚空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
如果把文学分析抽象到这种水准,那么从古到今的文学都是没有差异性的,任何作品都是由文字和语言所构成的,也就没什么本质性的区别了,这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诡辩术。
还有一种倾向就是庸俗的技术主义。
我们的文学过去有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化现象,被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历史创痛过于深切,于是,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成为一种时尚,技术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近几年来思想文化的多元趋向,远离政治中心的呼声日益增强,很多人试图完全回到文学本身,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话语体系。
但是这又往往走进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在文学审美的旗号之下,舍弃社会历史文化的具体内涵,陷入纯粹技术主义的迷宫,甚至要在文学史的叙写中消解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完成的五四启蒙话语。
过去有人讽刺俄国形式主义只注重分析各种叙事技巧的搭配,近年来这种文学上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中国的创作界与学界愈演愈烈。
同样,在所谓文学史“民间话语”的发掘中,也潜藏着这种倾向,它无形消解了很多文本的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政治文化内涵,这种“民间”文化立场显然是从巴赫金对拉伯雷的分析中得到启迪,但这些文学史论者却舍弃了巴氏话语中的哲学文化批判的历史内容。
巴氏认为拉伯雷是利用“民间”观点批判当时那个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官方的“美好的图景”,而到了我们的“民间话语”的发掘者手上,“民间”却成了纯技术性的形式主义工具。
又如,有人在所谓“审美历史语境”中发现和获得了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成就(审美价值)”比《创业史》、《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的结论。
如果真有脱离历史政治文化内涵的“审美”,那么毒瘤上的红色也同样是鲜艳灿烂的。
离开社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离开政治文化背景,离开发展的人性内容,而单纯注重叙事技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我们是不能避开这个话题的。
把叙事技术与巨大丰富的历史思想内容分割开来的方法,应该说是文学史叙写的一种隐形的倒退。
“去政治化”、“去社会化”、“去人性化”的极端就是把文学与社会文化思想实行有意识的割裂,使之成为一个僵死的、机械的物质现象,此种文学的技术主义至上思想已经成了一个具有较大普遍性的学术倾向。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反对用单一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作品的陈旧的极左观点,同时,也要反对文学史的叙写走向纯技术的形式主义的陷阱。
其实,过去的文学史叙写已经证明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以往文学史的撰写往往忽略了对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的描述,因而缺乏一个先进文化与文学的参照系,这样我们就很难在文学史的平面化的叙写中看清楚我们文学史所处的真实位置。
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在宏阔的视野中获得对文学史对象的背景清晰和清醒的把握。
在1949年以来大陆的文学研究中(当然也包括起始时对文学的即时性评价),我们所犯下的一个不可饶恕的致命错误就是采取了封闭的研究方式:
完全删除了这段文学史与当时整个世界文化格局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序格局,只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当作先进的榜样,而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强势的反差和落差遮蔽起来,这样就很难从一个更新更历史客观的高度来看清楚这段文学史的真实面貌和本质特征。
其实,从文化特征来看,整个五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化背景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就是一个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争斗过程。
而这在当时是无法鉴别其优劣的,只有在与这段历史拉开了时空距离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代性把握的关键,不但在于作家作品的文本选择,而且在于方法的选择。
“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乃至“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这些问题的存有都是我们在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始终只限定在一种视角框架之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视阈稍稍放宽一点、远一点,那么,我们就会完全改变对当代文学史的认知方式:
比如观照40年代末“二战”以后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思考它对以后的世界文化与文学格局有着什么样的长远影响等重大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认清中国文化与文学在关闭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交流和沟通的大门后,给当代文学史带来的是一个怎样的严重后果。
又比如,50年代的美国文学中出现了成熟的先锋主义文学及理论,现代派文学继20世纪初蓬勃发展之后又在整个西方世界出现了包括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种种新的变化,而我们的文学却在实际中回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之下,文学仅仅成为政治的“简单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而已。
落差和反差凸显出来以后,我们再重新审视作家作品,可能会看出很多隐藏着的常识性问题。
所以,回到常识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首先寻找文化和文学的参照系,在反差的比照当中,把文本和文学现象放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去探讨,才有可能使文本和文学研究更加出新,更加合乎历史的真实。
沿着这条视线延伸下去,我们觉得会实现对过去治史方法的较大更新。
淡化当时过度情绪化的政治背景因素的干扰,冷峻地从文化与文学结构层面入手,细心地把各种文本与文学现象乃至文学思潮放到世界文化进步趋向的进程格局当中去实行考察和检验,在这种比照里,看出它们之间的优劣,是文学史叙写的重要内在构成因素。
事实证明,在封闭的文化观点下大谈“民族化”,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越说越与先进文化拉开距离。
五四新文学始于向西方政治文明与文学艺术的学习、借鉴。
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与它的开放姿态密切相关。
但是,40年代以后,五四精神一步步被“革命”所消解。
文学重新回到了封闭的老路上。
大陆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时段,恰恰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史的时段,文学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个“复归”是有个过程的。
从80年代开始,我们能够从“文革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我们却似乎很难从“十七年文学”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种从弱势走向强势的过程,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
1979年以后,文学被重新导入上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层面,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然后又从批判现实主义迅速蜕变,重蹈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覆辙。
这20年的中国文学发展与五四一样,同样几乎是在浓缩了的西方一百多年的文学史进程中行进。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大陆50年来的文学史的基本状况是:
文学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即使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是进入了一个世界化的文化语境。
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能够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
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因为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对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不可行的。
如果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
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个参照系。
当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获得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也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才可能清晰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一批批作家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成为只会写颂歌和战歌的被动写作者而进入“共和国文学史”的事实。
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它符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此来说,它完全是旧体制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文学与文本现象。
只有将它们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文化语境当中,我们才能从时空的距离中获得真谛,研究格局与思维一旦突破了陈旧方法的藩篱,我们就能够对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学思潮、文学观点,都能够寻求另一种更深意义上的解读与界说。
同样,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评判更应该保持一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因为它所面临的是历史的首次筛选,是考验我们历史眼光与审美眼光的重要环节。
当80年代中国大陆逐渐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体味到西方文学的“恶之花”的后果,就进入了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欢之中了。
“无论在哪个时代,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时代感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
它也许变成新的,不同于以往的;也许破坏旧的,成为混乱甚至破坏的执行者。
”“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席卷一切的一种现象势必波及我们的时代。
该词或其意义实际上在前此的用法中充满了重重矛盾。
比方说,我们通常誉为现代主义运动开山祖的波德莱尔把现代性说成是昙花一现的,不稳定的,仅止半个艺术,而另一半才是永恒的。
”4所以,当我们重新回眸这20多年文学进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与身在其中时的迥然不同的感受。
从“朦胧诗”到“现代派”;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从“新写实”到“新生代”……在眼花缭乱的创作思潮当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幕幕上演。
对于这些站在潮头上的文学创作,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充分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它们从纷繁的理论烟雾中解放出来,还其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所以,更准确地梳理近20年来的文学进程,让它在首次进入文学史时少留下一些遗憾,则是我们的历史叙写追求。
总来说之,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指导思想是:
要具有自觉的历史感,但不为客观历史所束缚。
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就要体现出历史感,现在有很多书缺乏这方面的自觉。
前面提到的“混合主义”以及“新左派”、“后现代”的种种观点就是舍弃了历史感。
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强调历史感,一是要承认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二是要承认这个发展过程内部前后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仅仅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
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能够叫1949年以来这个时段的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过在未来(比如设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样被命名。
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这个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
这个史段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不能离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同时,我们在拥有充分的历史感的同时,还要拥有再创造历史的清晰的文化批判意识。
所以,在面对很多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历史实行“思想的考古”。
比如,针对文学史叙写中肯定“样板戏”和为政治服务文本的文学史叙写思潮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从“文革”前期到“文革”期间“样板戏”普及的历史过程写得更详细充分一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叙写中获得价值评判的思想资源。
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背景,才能真正地体现出强烈的、而且是真实的历史感。
5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其中有曲折,有断裂,有变形,并表现出革命化与现代化的交叉矛盾状态。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化有时推动现代化,有时候又防碍现代化,当革命化代表了先进的要求来冲击旧体制的时候,它推动现代化,但当革命化一旦形成一种带有封闭性的高度的政治专权,就会防碍现代化。
所以我们就应该区别五四革命和以后的伪革命的本质的区别。
比如国民党40年代的腐败政治文化以及“文革”时期的极左政治文化,这个时期的革命化就是防碍现代化的,是伪革命。
在此,我们应该强调和注重那些特殊历史时段中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
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很多有影响的作品,现在也应该历史地被列入重新审视的范畴的,我们的文学史一定要涉及。
其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
我们应该对精神生活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因为它是中性的,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作为一种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生活。
“十七年”和“文革”那个时代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现代社会中现代人不应有的精神生活。
能够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有现代人应享有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不自知的精神生活。
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做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能够解决很多文学史的难题。
如果我们在每一章里都能够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理解到一些作品怎样以前参与了对当代50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的强加的奴化的,它以前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也许我们就会拨开层层叠叠的理论和思想迷雾,在叙述当代文学50年的历史时,尽量努力去缝合价值立场与历史情境之间的错位和裂隙。
对关键词的重新清理和厘定是文学史叙写的另一个关键所在。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文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加以廓清,并需要对它们重新实行批判性的理解。
比如“深入生活”的提法,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体验就无法写作,这本是创作的基本常识问题。
外国作家不提“深入生活”并不是说不要生活,而是强调作家体验到的独特生活,它涉及到每个作家生活的人生经验与感悟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却将这个常识注入了很特殊的内容,演变为强迫作家下去实行思想改造的机制。
“深入生活”至今仍然还是一个使用频率极大的话语词条。
事实证明,凡是带着主观设定的问题、带着强加的政治任务去“深入生活”者,写出的作品是很少有成功的,包括最高明的作家像赵树理在内。
因为它根本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
同样,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词条,这是建国后评论文章中使用得极为频繁的话语,是随时能够戴在作家头上的一顶帽子,事实上这是乌托邦话语和封建专制主义之下为了排挤知识分子而虚造的一个话语体系。
再如“时代精神”这个关键词也用得非常混乱,动辄评价某某文学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它成为话语霸权者的一个“奖牌”。
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党性”、“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三突出”以至“红色经典”等等概念,也需要重新厘定。
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已经形成公论甚至定势的概念术语,需要我们今天以先进的、发展的历史眼光来加以考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持续地膨胀,同时国际上狭隘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势头也很凶猛。
在这种世界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