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docx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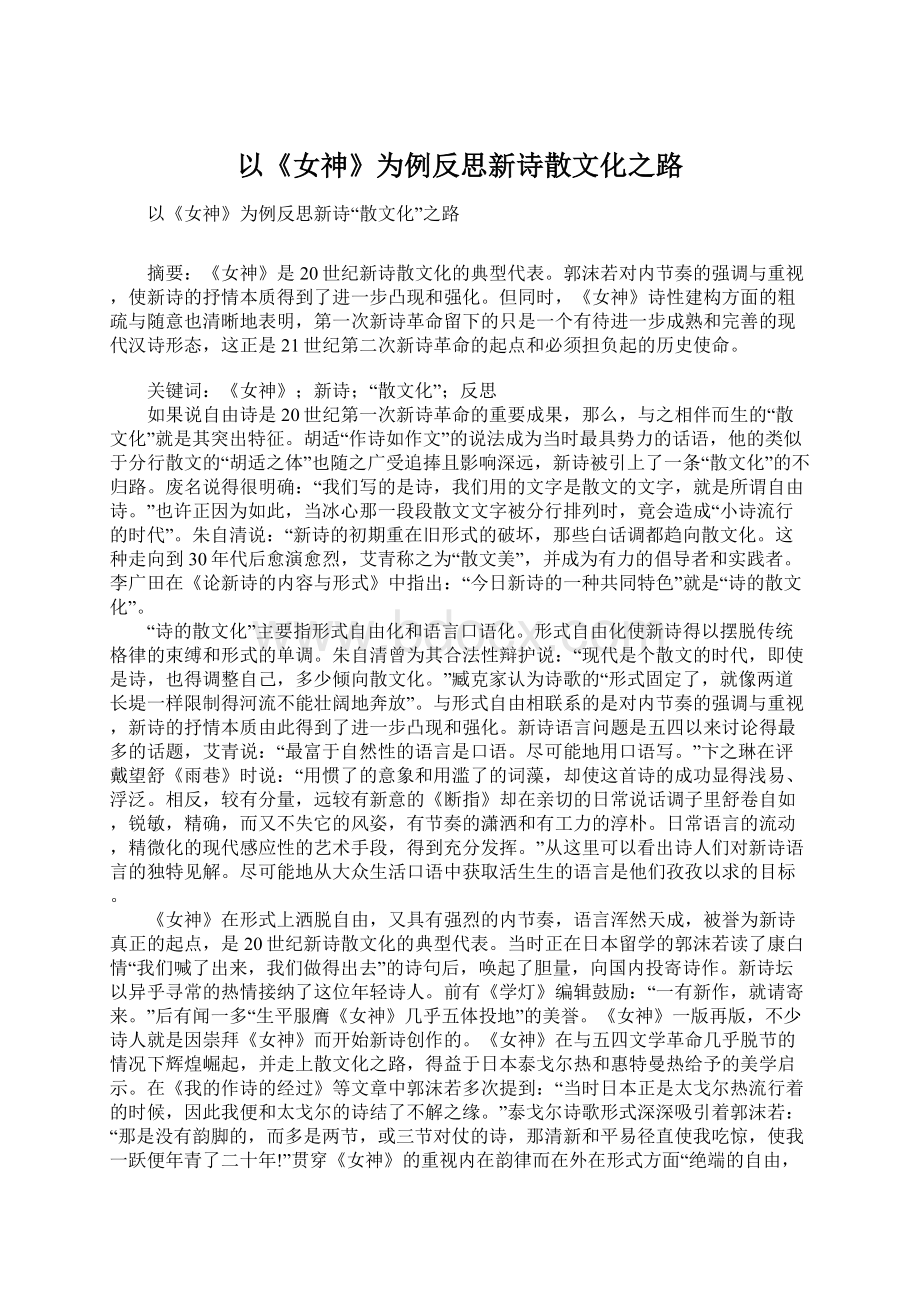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摘要:
《女神》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
郭沫若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使新诗的抒情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
但同时,《女神》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表明,第一次新诗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这正是21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的起点和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女神》;新诗;“散文化”;反思
如果说自由诗是20世纪第一次新诗革命的重要成果,那么,与之相伴而生的“散文化”就是其突出特征。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说法成为当时最具势力的话语,他的类似于分行散文的“胡适之体”也随之广受追捧且影响深远,新诗被引上了一条“散文化”的不归路。
废名说得很明确:
“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冰心那一段段散文文字被分行排列时,竟会造成“小诗流行的时代”。
朱自清说:
“新诗的初期重在旧形式的破坏,那些白话调都趋向散文化。
这种走向到30年代后愈演愈烈,艾青称之为“散文美”,并成为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李广田在《论新诗的内容与形式》中指出:
“今日新诗的一种共同特色”就是“诗的散文化”。
“诗的散文化”主要指形式自由化和语言口语化。
形式自由化使新诗得以摆脱传统格律的束缚和形式的单调。
朱自清曾为其合法性辩护说:
“现代是个散文的时代,即使是诗,也得调整自己,多少倾向散文化。
”臧克家认为诗歌的“形式固定了,就像两道长堤一样限制得河流不能壮阔地奔放”。
与形式自由相联系的是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新诗的抒情本质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
新诗语言问题是五四以来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艾青说:
“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
尽可能地用口语写。
”卞之琳在评戴望舒《雨巷》时说:
“用惯了的意象和用滥了的词藻,却使这首诗的成功显得浅易、浮泛。
相反,较有分量,远较有新意的《断指》却在亲切的日常说话调子里舒卷自如,锐敏,精确,而又不失它的风姿,有节奏的潇洒和有工力的淳朴。
日常语言的流动,精微化的现代感应性的艺术手段,得到充分发挥。
”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们对新诗语言的独特见解。
尽可能地从大众生活口语中获取活生生的语言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女神》在形式上洒脱自由,又具有强烈的内节奏,语言浑然天成,被誉为新诗真正的起点,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读了康白情“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的诗句后,唤起了胆量,向国内投寄诗作。
新诗坛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接纳了这位年轻诗人。
前有《学灯》编辑鼓励:
“一有新作,就请寄来。
”后有闻一多“生平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的美誉。
《女神》一版再版,不少诗人就是因崇拜《女神》而开始新诗创作的。
《女神》在与五四文学革命几乎脱节的情况下辉煌崛起,并走上散文化之路,得益于日本泰戈尔热和惠特曼热给予的美学启示。
在《我的作诗的经过》等文章中郭沫若多次提到:
“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
”泰戈尔诗歌形式深深吸引着郭沫若:
“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
”贯穿《女神》的重视内在韵律而在外在形式方面“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创作原则,正是从泰戈尔散文诗中萌芽的。
惠特曼被称为“现代抒情诗最伟大的形式革新者之一”,他提出“现在是打破散文与诗之间的形式壁垒的时候了”。
虽然郭沫若首先是以“泛神论”为基点接受惠特曼,但惠特曼诗歌独特的形式魅力却给了郭沫若更大的震撼。
他说:
“是惠特曼解放了我”,“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暴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
《女神》审美范式形成也与日本诗坛有关。
日本诗歌历来不尚对偶声律而重节奏,而《女神》创作的1916至1920年间正值日本“新体诗”运动和口语诗运动此起彼伏之时。
当时日本诗人热衷于借鉴欧美诗歌,创作欧化自由诗即“新体诗”。
川路柳虹《垃圾堆》将口语诗运动推向高潮,随后民众诗派、人道主义诗人群相继登上诗坛,以惠特曼为宗师,刻意追求浅显易懂的口语风格。
1917年还诞生了被称作口语自由诗巅峰之作的荻原朔太郎《吠月》。
和歌领域也出现了打破俳谐和歌格调而采取自由律的诗体解放趋势。
如此文化氛围加上自身性格气质,年轻的郭沫若成为写诗“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
因此,《女神》虽然诞生于日本,但其汪洋恣肆的诗句、挥洒自如的语言风格和强烈的情绪节奏,与国内诗体解放的想象相契合,被推上了第一次新诗革命的历史巅峰,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新诗的最高成就。
它的成功为新诗的情感方式、表达策略、散文化走向等提供了范本,同时其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显示了第一次新诗革命在文体建设方面的待完成性,并为新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启迪。
诗与其他文学样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音乐性,形成音乐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节奏,所以诗歌文体建设首先表现为节奏建设。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开宗明义:
“诗的所以能激发情感,完全在它的节奏。
”也就是说,如果失去了节奏,那就不是“散文化”问题,诗已经变成散文了。
所以与形式上的自由化相联系的是诗人们对内节奏异常重视,而这正是《女神》最值得称道的地方。
郭沫若主张诗应该具有纯粹的内在律:
“诗之精神在其内在的韵律(IntrinsicRhythm),内在的韵律(或日无形律)并不是什么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官商徽羽;也并不是什么双声叠韵,什么押在句中的韵文!
”所谓内在律在郭沫若看来就是情绪的消长:
“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
情绪的进行自有它的一种波状的形式,或者先抑后扬,或者先扬后抑,或者抑扬相间,这发现出来便成了诗的节奏。
”由于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郭沫若在留日期间构建了一座“生命的文学”理论之塔,因此他的内节奏理论是与“生命的文学”联系在一起的,他说: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
”郭沫若这一观点显然与弗洛依德关于艺术创造来自于生命冲动的本能力和性驱动力的理论有关,同时也有他早年倾心的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
在郭沫若看来,“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
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
”《天狗》一诗正是让情绪在循环往复中递进和变化,大起大落,形成强烈的内节奏。
生命的文学观和泛神论相结合,使《女神》全神贯注于来自心底的喜悦,常常具有一种见景起兴、随物婉转的自然节奏,不少诗感应博多湾的自然节奏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格特征。
博多湾西接东海和日本海,与太平洋相通,平日水波不兴,郭沫若甚至认为“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但每到九、十月间大风一起,排山倒海。
1281年元世祖的庞大舰队即在博多湾全军覆没。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尾注“1919年9、10月间作”,正是此时。
这时的博多湾惊涛拍岸,浊浪排空,诗人惊呼:
“啊啊!
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郭沫若说:
“这是海涛的节奏鼓舞了我,不能不这样叫的。
”而面对“雪的波涛!
/一个银白的宇宙!
”诗人也“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创作了相应的诗歌节奏。
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说:
“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
”
与重视内节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外节奏方面,《女神》并不特别用心。
不过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朱湘就曾说:
“郭君在一班的时候,对于文艺是很忽略的,诚然免不了‘粗’字之讥。
但有时候他的诗在形式上、音节上,都极其完美。
”如《上海印象》用圆圈式抒情结构,造成一唱三叹的韵味和铿锵有力的音乐效果。
《炉中煤》采用复沓变奏,从一个意象出发、展开,又回归起点,造出既繁富又单纯的综合美感。
不过总体上说,《女神》在外节奏建设方面没有太多的创新与突破。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认为,这“也许就是太不‘做’的结果”。
在他眼中,“郭君是个不相信‘做’诗的人”。
捧着《女神》走上诗坛的闻一多深知过度散文化和忽略外节奏建设对新诗艺术的危害,在批评郭沫若“我们不能不埋怨他太木认真把事当事做”的同时,他在新诗外节奏建设方面十分用力。
他关于诗歌音尺的划分、韵脚的设定和诗行诗节的整体安排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依据语言的韵律及其可能出现的节奏效果,一方面暗含着对现代汉语节奏感及其可能的探求,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新诗文体规范建设和诗与散文严格分界的诉求。
如针对现代汉语双音词多于单音词的现象,闻一多提出了“音尺”理论,强调让“二字尺”和“三字尺”差参排列,则诗句节奏显得活泼,自然流畅。
此后的卞之琳在闻一多基础上提出了“顿”的概念,把它视为新诗节奏的核心问题,从而将这一理论的探讨进一步引向深入。
此外,闻一多还从文字符号的造型性来考虑诗歌在视觉方面的节奏美感,认为由于汉字是象形文字,较之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更多了一些在视觉形式方面的造型力和感染力,也因此具有了诉诸视觉的节奏美。
闻一多的外节奏建设还表现为一系列韵式的大胆尝试。
从《红烛》中可以看到由无韵到有意识押韵的变化。
他曾向友人宣称:
“现在我极善用韵。
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
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
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
”可以说,正是《女神》在文体建设方面的疏漏启发了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而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新诗“散文化”的美学盲点。
诗歌是节奏的艺术、语言的艺术,自白话诗诞生的第一天起,诗人们就自觉地开始新的诗歌语言的寻找。
汉民族虽然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丰富的诗歌宝藏,但那些约定俗成的语言组合经千百年的重复沿用,必然导致新鲜感的丧失和美感的减弱,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的需要。
因此从大众中、从生活中获取活的语言,成为第一次新诗革命的共识。
《女神》娴熟地运用生活口语,显出亲切如话的艺术风范,如《黄浦江口》:
“平和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新诗以短短的历程,要对抗古典诗歌在几千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深厚而纯净的文化结晶,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适当地运用、合理地改造古典文学辞藻,用以表达现代感情,也应该是新诗的一种语言策略。
《女神》偶尔也采用古诗词汇,或将文言融入诗中,使之具有丰富的暗示性,从而营造出一片耐人寻味的艺术天地,如《春愁》“海语终难解,/空见白云飞”,《蜜桑索罗普之夜歌》“上有星汉湛波,/下有融晶泛流”。
《女神》提供的这种艺术可能,30年代的卞之琳走得更远。
他认为,在诗中“化古”是为了力求以尽可’能少的言词,为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创造尽可能大的审美空间。
《尺八》反复插入“归去也,归去也,归去也——”的句子,文白变动,仿佛一股从古流到今的思乡情绪,默默注入诗中,既有古典余韵,又不失现代精神。
可见,新诗回味深长的品格,有时也来源于传统诗学中含蓄蕴藉一脉的丰厚滋养。
但是由于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强调的是音节的美感效果,一般不宜机械照搬古典诗词的“炼字”。
当然,在保持节奏自然流畅和语言亲切的前提下,诗美世界的创造仍然需要从标题到一字一词乃至标点符号都贯穿精品意识,力求一词一标点都顾盼有神。
《女神》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精品,如《霁月》:
“淡淡地,幽光/浸洗着海上的森林。
/森林中寥寂深深,/还滴着黄昏时分的新雨。
”《鸣蝉》:
“声声不息的鸣蝉呀!
/秋哟!
时浪的波音哟!
/一声声长此逝了……”《雷峰塔下》其二:
“菜花黄,/湖草乎,/杨柳毵毵,/湖中生倒影。
//朝日曛,/鸟声温,/远景昏昏,梦中的幻境。
”正是由于精心打磨,这些诗句祛除了日常口语的零乱芜杂,音韵完美,珠圆玉润。
语言表达的生动、贴切、灵活多变,是《女神》的成功所在。
但总体上说,《女神》在语言诗性建构方面是比较随意的。
如《金字塔》“一个高,一个低,一个最低”、《光海》“阿和要我登,/我们登上了”这样的句子不在少数,而且,似乎随手拈来的“因为”、“但是”、“所以”、“或许”等连词,更使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的界限变得模糊。
诗应如集成电路一样在短小的篇幅中蕴含丰富的情致。
如何将松散的日常语言提升为诗句?
这是每一位诗人都必须直面的问题。
正如袁可嘉所说:
“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目的显在二者内蓄的丰富,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作为创造最大量意识活动的工具;一度以解放自居的散文化及自由诗更不是鼓励无政府状态的诗篇结构或不负责任,逃避工作的借口。
”大凡成功的作品都是建立在对语言与艺术思维矛盾的超越之上。
诗的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诗人内在情思与语言形式的搏斗史。
新诗尤其需要极富个性的奇思妙想,词与词之间富于现代情绪的瞬间撞击与粘合。
只有独具洞察力的慧眼灵心才能给现代读者一个美的惊喜。
穆木天1926年在《创造月刊》上发表《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批评胡适“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
有趣的是,面对因《女神》而风光无限的郭沫若/作为创造社同仁的穆木天不仅对《女神》无一誉美之辞,甚至连其中的篇章都无一提及,可见《女神》并不符合穆木天“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的“纯诗”理想。
《女神》在胡适开辟的散文化路径上昂首阔步的同时÷也暴露出新诗诞生之初注重白话而不是诗歌、致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藩篱而非构建新诗艺术殿堂的隐患。
正因为如此,穆木天倡导“纯粹诗歌”,一方面寻找西方现代派与新诗艺术的契合点,一方面力图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为新诗重树规范,给“散漫化”、“平庸化”肆虐的诗坛注入新鲜血液。
遗憾的是,与闻一多的格律诗一样,“纯诗”的道路并没有能走多远。
抗战爆发后,文学工具化倾向蔓延,于是废名旧话重提,强调当年“胡适之先生所谓‘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个论断应该是很对的了”,要求诗人坚持这样的创作原则并“不怕旁人说我们不是诗了”。
新诗革命又回到了起点。
以后虽还有“九叶”诗派、朦胧诗潮崛起,但均未从根本上扭转新诗散文化的狂澜。
新时期以来,崇尚口语化的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此起彼伏,提倡用直白口语写作的所谓“新口语诗”也频频亮相,尤其近年来网络流传的“梨花诗”及其仿作,更是将诗歌变成了恶搞的对象。
诗人从被顶礼膜拜的巅峰跌入万丈深渊,诗在新世纪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和困境。
追根溯源,《女神》其实已经显示了第一次新诗革命形成的这种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的先天不足。
在《女神》获得广泛认可而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其散文化偏颇所导致的“非诗化”倾向也在不断被复制和放大,被极端化,或隐或显地阻碍着新诗艺术的前进步伐,最终使其生命萎缩,举步维艰,被嘲笑为只有“自由”没有“诗”。
艾青1939年发表《诗的散文美》一文,举例说有位工人在墙上写了一个通知:
“安明!
你记着那车子!
”认为“这是美的,而写这个通知的也该是天才的诗人”。
不过到80年代艾青出版《诗论》时却将这句话改为“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秉赋”。
这一细节其实透露出老诗人对文体规范问题、语言锤炼问题的反思。
如何在总结新诗所经历的曲折的基础上,开辟一条通向辽阔艺术世界的、顺应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潮流的新诗之路,这是《女神》留给我们的思索,也是第二次新诗革命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