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文化之三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docx
《理想文化之三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理想文化之三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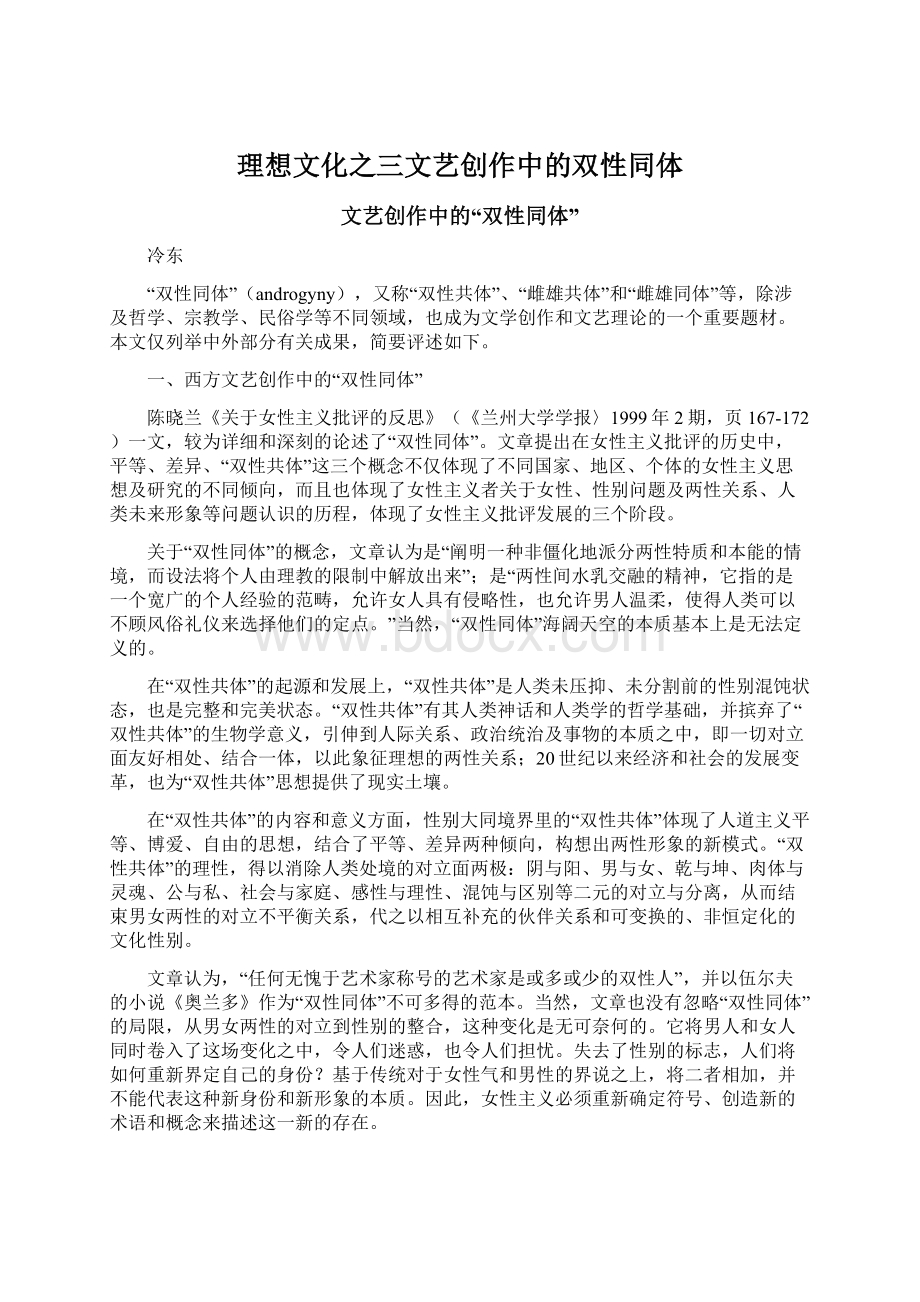
理想文化之三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
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
冷东
“双性同体”(androgyny),又称“双性共体”、“雌雄共体”和“雌雄同体”等,除涉及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不同领域,也成为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题材。
本文仅列举中外部分有关成果,简要评述如下。
一、西方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
陈晓兰《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2期,页167-172)一文,较为详细和深刻的论述了“双性同体”。
文章提出在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中,平等、差异、“双性共体”这三个概念不仅体现了不同国家、地区、个体的女性主义思想及研究的不同倾向,而且也体现了女性主义者关于女性、性别问题及两性关系、人类未来形象等问题认识的历程,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关于“双性同体”的概念,文章认为是“阐明一种非僵化地派分两性特质和本能的情境,而设法将个人由理教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是“两性间水乳交融的精神,它指的是一个宽广的个人经验的范畴,允许女人具有侵略性,也允许男人温柔,使得人类可以不顾风俗礼仪来选择他们的定点。
”当然,“双性同体”海阔天空的本质基本上是无法定义的。
在“双性共体”的起源和发展上,“双性共体”是人类未压抑、未分割前的性别混饨状态,也是完整和完美状态。
“双性共体”有其人类神话和人类学的哲学基础,并摈弃了“双性共体”的生物学意义,引伸到人际关系、政治统治及事物的本质之中,即一切对立面友好相处、结合一体,以此象征理想的两性关系;20世纪以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革,也为“双性共体”思想提供了现实土壤。
在“双性共体”的内容和意义方面,性别大同境界里的“双性共体”体现了人道主义平等、博爱、自由的思想,结合了平等、差异两种倾向,构想出两性形象的新模式。
“双性共体”的理性,得以消除人类处境的对立面两极:
阴与阳、男与女、乾与坤、肉体与灵魂、公与私、社会与家庭、感性与理性、混饨与区别等二元的对立与分离,从而结束男女两性的对立不平衡关系,代之以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和可变换的、非恒定化的文化性别。
文章认为,“任何无愧于艺术家称号的艺术家是或多或少的双性人”,并以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作为“双性同体”不可多得的范本。
当然,文章也没有忽略“双性同体”的局限,从男女两性的对立到性别的整合,这种变化是无可奈何的。
它将男人和女人同时卷入了这场变化之中,令人们迷惑,也令人们担忧。
失去了性别的标志,人们将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
基于传统对于女性气和男性的界说之上,将二者相加,并不能代表这种新身份和新形象的本质。
因此,女性主义必须重新确定符号、创造新的术语和概念来描述这一新的存在。
徐岱《论美感的生命形态》(《文艺理论研究》1997年5期,页11-19)一文认为:
“双性共体”是以刚与柔为其表现形式的大自然“天地之道”的真正体现。
在我们的生命里,这个“阴阳之道”主要存在于作为生命之根的性别上。
在人类学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雌雄双性体,这个双性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
所以,“每个人都天生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这倒不仅仅因为从生物学角度考察,男人和女人都同样既分泌男性激素也分泌女性激素,而且也因为,从心理学角度考察,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
”因为只有这样,两性之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协调,达到真正的理解,因为人真正能理解的其实只是和自己同类的事物。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正是从这里提出了著名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理论,分别用来指男性和女性心理意识深处隐藏着的异性原型。
为了使个体人格得到健康和谐的成长,应允许男性人格中的阿尼玛(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阿尼姆斯(男性)因素,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一定的展现,否则,这些被压抑到意识深处的异性因素的逐渐积累,最终会危及生命主体的存在。
“我们必须永远记着,在每个个人身上都混合着两类特征,只不过与‘他’或‘她’的性别相一致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数而已。
”
作者列举了几个例证。
一是海明威的传记作家库·辛格曾指出:
“海明威外观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有男子气概。
但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
”从心理分析来看,有“雄狮”之誉的海明威最终自杀身亡,同他平时过多表现男子汉气质而压抑了阿尼玛情绪的正常宣泄,最终使内心女性化而变得脆弱不无关系。
另一个例子是乔治·桑。
初上文坛的乔治·桑虽已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妇人,但却“取了一个男人的名字,打扮成男人的模样,在男子中间完全象男子一样生活。
”这不仅使她在文坛上独具异彩,更重要的是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将其阿尼姆斯情绪作了尽性释放。
”还如巴尔扎克小说《幻灭》里的男主角吕西安是这样被描写的:
“他脸上线条高雅,大有古代艺术品的风味:
希腊式的额角和鼻子,女性一般的皮肤白得非常柔和,多情的眼睛蓝得发黑,眼白的鲜嫩不亚于儿童。
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粟色的睫毛很长。
腮帮上长着一层丝绒般的汗毛,色调正好同生来蜷曲的淡黄头发调和。
一口整齐的牙齿衬托出粉红的嘴唇,笑容象凄凉的天使。
”与其说这是一位典型的男性肖像,不如说这是一个在阳性气质的底色中描绘出来的阴性形象。
显然,正是生命的阴阳二力的“互渗”性和“复合”性,形成了我们审美体验的整个“光谱系列”,使我们的美感享受显得丰富多彩、无穷无尽。
张在新《笛福小说“罗克珊娜”对性别代码的解域》(《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4期,页98-108)一文中,引用柏拉图的《乡宴篇》对话录,早在几千年前就将“双性同体”表达得流畅有力。
借亚里斯托芬口中说出太初时的人类形态是雌雄同体的,宙斯为了避免危险,便将人类分割开,造成这些分离的半体在大地上漫游,无休无止也永不成功地追求结合。
张在新进而认为笛福小说中“男女人”罗克珊娜即是拉康式“双性”的集中表现,她兼有“男性”或“女性”的文化代码和它们所象征的意义,体现在她既有女性情感丰富的一面,又有男性理智坚强的一面。
并有别于她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父系象征体系”和在第二部分的“母系符号体系”这两个时期的性别代码意义,是有关父系和母系互相贯通、互不对抗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样板,它抹去了某些女权思想中针对性别代码的二元思维的痕迹。
廖咸洁:
《“双性共体”之梦:
〈红楼梦〉与〈荒野之狼〉中“双性同体”象征的运用》(台湾:
《中外文学》1986年4期,页120-147)一文,具体以二十世纪德国现代小说家赫曼.赫塞的名著《荒野之狼》为例,说明“双性同体”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的角色。
哈利是一个年近五十,新教徒中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或因为秉性特异,或因心智发展脱俗,哈利逐渐对自己出身的社会及其伦理观感到不满与怀疑。
这种情绪随著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
那是一种双重的冲突:
一是布尔乔亚伦理的僵化倾向与追求真我的欲望二者间的对立;二是追求真我过程中精神面与感官面的对立。
这种双重的挣扎使哈利在形体与精神两方面都颠沛困顿,流离失所。
在这个自我放逐的过程里,哈利将自己比作一只“荒野之狼”,涵盖了前述的两种对立,亦即“布尔乔亚与离经叛道或麻木不仁与自我追寻,或保守与创新的对立”,以及“精神”与“肉体”或“理性”与“本能”的对立。
也就是“暗阳”与“暗阴”的对立。
内心“狼性”与“人性”的交战,使得哈利四处流浪,不得安身之所。
就在他日惭丧失生活意志,甚至考虑以自杀一了百了之时,他遇见了赫敏娜,一个美丽而善体人意的妓女。
她以睿智的言行,特别是具有“双性同体”的特质,最终将哈利度出布尔乔亚之苦海,度入双性兼美的原始无意识状态。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书中提出,“双性同体”作为性别文学和妇女社会生存理想的提出,最早发端于英国女性主义文学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名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不但提出了“女人的男性”,也提出了“男人的女性”。
按照伍尔夫的解释,即是“一个人一定得女人男性或是男人女性”,这种传统的“双性同体”主张,实际上是通过淡化性别意识,模糊性别差异的界线,而树立起性别平等的概念。
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对这种传统的“双性同体”概念进行了批判,提出她的另一种“双性同体”:
“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中一性。
”“这种双性并不消灭差别,而是鼓动差别,追求差别,并增大其数量”。
西苏认为,传统的“双性”即是中性,亦即无性。
而“双性同体”的当代阐释却强调了女性的思想表达和身体经验的关系,强调了女性愿望、女性满足和女性气质的作用。
在以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男女二元对立社会中,西苏以既有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来解构这种顽固的二元对立。
妇女“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而且在结合了男性力量之后,变得更加强大。
妇女就这样变成了西苏所说的具有无尽包容性又不排斥差异的新的双性同体,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因为双性的出现而被解构。
胡全生《“仁”与“智”的撞击—美、法女权主义批评之比较》(《国外文学》1997年1期,页20-26)一文也认为,伍尔夫在《自己的房间》里不仅讨论了妇女成为作家的物质条件,而且也讨论了其心理条件。
她认为心灵像身体一样,也有两个性别,心灵的正常和舒适状态是最有益于创作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灵中的男女性两个方面是“和睦相处的”。
她说:
“在男人的心灵中,男人管束女人;在女人的心灵中,女人统辖男人。
正常和舒适状态存在之时,亦是二者和睦相处、精神互相合作之时。
如果一方为男人,心灵的女人部分必须仍有作用;而一个女人也必须与她身上的男人交合。
”伍尔夫由此得出结论:
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颗双性同体心灵,莎士比亚、济慈、斯泰因、库伯、柯勒律治皆如此。
”肖沃尔特则对伍尔夫的这种雌雄同体见解不满。
认为伍尔夫的见解是种逃避主义,不足以解决性政治问题。
她说:
“雌雄同体是帮助她逃避她自己的痛苦女性、使她能扼杀和压抑其愤怒和抱负的神话。
”“双性同体心灵……是理想艺术家的乌托邦投影。
”此外,肖沃尔特对伍尔夫在书中运用的创作技巧(重复,夸张,滑稽模仿,怪诞,多重视角)亦大为不然,视此书“极端的非人格”,“躲躲闪闪,戏语连篇”,尽和读者“玩游戏”。
杨莉馨《扭曲的“镜像”—西方文学中的“悍妇”形象》(《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3期,页45-54)文中指出,无论是以克吕泰美斯特拉、美狄亚等为代表的“悍妇”或“女巫”,以珀涅罗珀等为代表的家庭天使,或是以潘多拉、海伦为代表的“尤物”、“祸水”,均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制时代之后的产物,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希冀和篡改。
它们是不能代表女性在本真意义上的情感和欲望的。
而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势必会受到来自于主流话语、传统批评尺度、自我心理乃至语言手段的缺乏诸方面的束缚而陷入困境之中。
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人性阐扬,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伴之而来的男女两性的进一步理解、尊重和合作。
只有在充分尊重男女独立人格的基础上扬弃传统文化的弊端和偏见,才能完善和发展健康的人性,建立一种双性文化,从而达到在“双性同体”基础上的最大限度的自由”。
到了那样的阶段,“悍妇”文学现象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
张在新《羽毛皇冠的符号象征游戏—评辛格的小说《羽毛皇冠》(《外国文学》1998年5期,页43-49)一文认为,如果电闪雷鸣象征着上帝惩罚的严厉,而阳光雨露则体现了他仁慈的温暖,上帝的这个两重性折射男性的威慑力和女性的感染力,这正好与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情感相对应。
如果祖父和祖母的幽灵象征上帝的两个不同方面的话,那么上帝不是单性的,而应该是双性的。
而阿克萨对幽灵的背叛就是对上帝的男性和女性的背叛。
最终,羽毛皇冠对祖父和祖母幽灵象征意义的解构就彻底取消了上帝及其庶民的男/女对立地位,把它瓦解成为纯粹的语言象征符号。
艾晓明《雌雄同体:
性与类之想象:
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3期,页50-57)一文认为,雌雄同体是一种艺术想象,它涉及到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们在理论和创作中探讨过的重要思路。
对性别经验的正视和描述是女性文学在20世纪以来最有冲击力的一举。
雌雄同体的一部现代小说经典是弗吉尼·伍尔芙发表于1928年的小说《奥兰朵》(Orlando),在伍尔芙的文本中,她尝试写出一个人可以有多重自我,性别可以转换,就像服装一样。
性别是可以选择的,“正是奥兰朵自身的变化,促使她选择了女人的服装和女人的性别。
在这个选择中,她也许只不过是更公开地表现了……某种存在于大多数人身上却又不曾如此明白显露过的现象。
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又遇到了两难的困境。
性别固然是有差异,但两性也的确会混合。
在每一个人身上,性别总是在两极间摇摆,男性或女性的外表,往往仅由衣服来维持,而衣服底下却遮盖这与表面截然相反的性别。
1993年英国女导演莎莉·波特(sal1yPotter)根据小说拍成了电影《奥兰朵》,从电影来看,小说中的意念被简化,一直到最后一个场景,才能看得出来,活了四个世纪的奥兰朵是个作家,她的打扮也十分中性。
在电影中,换装的奥兰朵确实很好地体现了伍尔芙的名言:
是衣服在穿我们,而不是我们在穿衣服。
当她身为女性时,她表达了与男人不同的价值观。
影片中另一个被引申的意念是寻求同伴,话外音说:
奥兰朵继承了象征财富、名望的姓,但她一直得不到的优宠是:
同伴。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奥兰朵,都没有同伴。
影片结束时,奥兰朵带着她的女儿回到城堡(在此之前,作为女性,她没有继承权,一直到有了子嗣,不过电影里把儿子改成了女儿)。
在城堡前的参天大树下,她听到了天使的歌声,歌中唱道:
“我来了,我来了。
我熬过来了,穿越时空走向你。
在这融为一体的时候,我在这里,既非男人,也非女人,我们二而一,紧密不分离。
有着身为人的面目,我身在尘土,我身在苍穹,我正值新生,也正在凋零。
”这歌词表达了一种自在欢喜,自足自立的精神世界,是影片中给奥兰朵寻找同伴的一生的一个终结一种雌雄同体的理想境界。
二、港台文艺创作中的“双性同体”
饶竼子、陈丽虹《海外华文女作家及其文本的理论透视》(《文学评论》1997年6期)一文提出,由于海外华文女作家所处多重文化冲撞处境的复杂性、流动性、边缘性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在既反对性别歧视,又抨击种族主义,同时探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区别方面是最具启发性的。
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意识”的形成和“寻根热潮”的深化,她们也开始在一个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和追问“性别”、“民族”、“文化”等问题的复杂性。
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也使她们对传统文化进行自省,对女性在多重文化背景中的位置和形象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她们在欧美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中,所受冲击较大,其创作题材涉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及交融中的两难境况,边缘人心态,失根的惶感,对女性在历史的变迁文化的转变下的境遇也有深刻的体认及敏锐的探索。
在她们的作品中,出现明显的“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即力图使人们认识到,基于生理不可克服的男女差异,将是各自的优势,而不成为权力压迫的借口;通过互相补充,最终建立男女平等的和谐关系。
这种不带性别偏见的文化设想,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
虽然就目前而言,距“双性文化完善互补”的理想似乎还较为遥远——男权中心依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权文化的巨大网络仍渗透于各种缝隙之间:
阻碍女作家的思考及言说,但“双性文化完善互补”仍不失为一种文学写作的理想,也就是说男女作家都应在两性的互补共存之中,在探索存在意义的高度上确立文学的坐标,从而将人类生存的境界推向更完善和更高级的层次。
陈晓兰《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2期,页167-172)一文提出,港台的女性主义之所以与西方女性主义较为接近,对“双性共体”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翻译、介绍并在批评实践中大量应用“双性共体”的理论,这一方面是由于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她们看来,“双性共体”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合一”、“阴阳互补”观念存在着相通之处,而且,“双性共体”思想也比较符合中国的中庸之道。
“双性共体”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者解决妇女问题、两性关系和男性之人格困境的方法和答案。
它使女性主义者从二元对立和中心/边缘之对抗的男性化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而不是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
因此“双性共体”可看作是女性主义思想及文学批评的未来,是现代和未来男女两性人格之全面发展的理想。
陈晓兰对廖咸洁:
“双性共体”之梦:
〈红楼梦〉与〈荒野之狼〉中“双性同体”象征的运用》也进行了很好的评论。
台湾廖咸浩在《“双性共体”之梦:
〈红楼梦〉与〈荒野之狼〉‘双性同体’象征的运用》一文中,首先回顾了“双性同体”观念的产生和变化,认为“双性同体”所隐含和透露的讯息是人类对于其生存处境的深刻不满,是男女两性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觉得自己被支解了,被拆散了。
这种“拆散”的本质是人类一次致命的灾难,同时也是人世结构的一次本体上的改变。
这种向往流露出一种对万物归一的失乐园的追怀。
身为人类,我们对于彼方或对方最原始、最切身的体谅,往往来自异性;而对于“完整”最强烈、最具体的憧憬,也多半得自对异性的渴慕。
因此用“雌雄同体”或“双性同体”来象征两性并存和“双性和谐”的理想,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中一种极普遍的现象。
而个人发展模式是由“混沌的无意识状态”变成与意识对立的“意识后潜意识”,造成人类存在的二元对立状态。
这种对立状态使人类性格出现两类相反的倾向:
一类是“意识”居于上风时的倾向,如理智、思虑、区别心、支配性、自我肯定性等,称为“阳半”或“暗阳”。
另一类则属“潜意识”居上风时的倾向,如情感、直觉、混同心、接受性、整体认同性等,称为“阴半”或“暗阴”。
如发展受到障碍而不及时解决,则对个体化过程造成严重干扰。
但“自我”若能及时面对阴影,则不但能解除阴影压力,且能透过阴影之助,回到“双性兼美,万物共存”的原始潜意识中,实现“双性同体”的“真我”。
文章具体分析了《红楼梦》中主人公的性别人格内涵及其困境的根源和内在的追求。
认为《红楼梦》的题旨可以看作是宝玉的存在挣扎。
宝玉把世界截然划分为二,一是女人的世界,一是男人的世界。
女人的世界清澈,男人的世界污浊,他因此珍爱女人的世界而厌憎男人的世界。
大观园里的世界是女人世界的延伸,园外的世界则是男人的世界。
女人的世界代表的是潜意识,主宰的意识模式是“暗喻性阴柔”,男人的世界代表的是意识,主宰的意识模式是“暗喻性阳刚”。
宝玉因对寻找原始潜意识过分依恋,而至缺乏个体化意识。
他沉溺于女人的世界,排斥男人的世界。
因为在他眼里,男人的世界就是贾政所代表的“恐怖父亲”的世界,这正是宝玉的悲剧所在。
宝玉的生存意向是退却式的,是拒绝成长的。
同时,外部世界的丑恶使得宝玉无法完成从女儿国向男人国、由孩童向成人、由女性向男性倾向的转化。
他变得无家可归,精神上自我放逐,人格、本质、身份无所确定,只有远离这个世界,脱离尘缘,进入“太虚幻境”。
刘介民《苍茫世界的求索:
〈沉默之岛〉之秘藏与“雌雄同体”的象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3期,页118-123)一文,对台湾鼓吹“双性同体”的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4年11月出版)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认为小说的大胆突破精神是试图推翻传统的“女性典范”,展现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和雌雄同体的性爱实验。
《沉默之岛》的文体理念主要表现在1、反正统、反单一,追求交杂。
包容身体器官和性的自由,探讨双性之美、男女皆非、忽男忽女,两性交杂的最佳象征。
2、逾越传统的意识形态,男女性别反转倒置,雌雄同体为时尚,将一切秩序关系相对比,具有颠覆性。
3、不断更新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性别的不确定性,男女性别不断变化,追求“雌雄同体”男女特质的兼美,挣脱两性刻板的角色,不断游离于两性之间。
主人公晨勉是一个三十岁的知识女性,因秉性特异或心智开发脱俗,逐渐对自己的身体和传统的社会伦理感到不满和怀疑,传统文化的制约又使她潜意识里为自己的“离经叛道”感到罪疚,内心的矛盾使她的足迹遍及香港、印尼、新加坡、英国、德国……,不能安心一处。
在这自我放逐的过程里,晨勉将自己比作“沉默之岛”。
其天性有别于性灵,由对立的成分构成,一是“人性”,一是“生物性”,以“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本能”相对立。
晨勉在这种纠葛不清的矛盾中,不断受着内心冲突的煎熬,影响了她的生活意志。
最后澳籍男子辛(一个年青、英俊、潇洒,具有国际化倾向的“双性恋者”)的帮助下,使晨勉赤裸地回到“原始无意识”中,体会双性之美,以便重估她人格内部久被压制、抑郁的“潜意识”,恢复“真我”的本来面目。
因为辛具有“双性同体”或“雌雄同体”的特质。
在辛的引导下,晨勉可以深入地回到涵盖两性、包容万物的世界中,从而一窥“原始潜意识”之美。
小说通过“雌雄同体”意象,深刻领悟了人格与人世是如何的多样与不定,而传统观念的陈腐是多么天真与无益。
女人的真实经验、真实需求,女性的自我实现在晨勉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本书以“暗喻性阴柔”与“暗喻性阳刚”之间的对立为故事发展的动力,且将“雌雄同体”标为理想的存在状态,那是作者向往的理想境界。
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在随着意识形态的洪流载浮载沉的过程中,何时才能实现这一理想?
也许那永远是苍茫世界中的“谜”。
艾晓明《雌雄同体:
性与类之想象:
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它小说》(《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3期,页50-57)对香港作家董启章的新小说《双身》(获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作品)进行了深刻论述。
文章首先分析了作者在创作《双身》之前的第一部探讨“双性同体”的小说《安卓珍尼》,该作品曾获1994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首奖。
《安卓珍尼》描写一位女学者,到偏僻的山上独居,寻找叫作安卓珍尼的动物,这动物是一种蜥蜴,单性,全雌性品种,雌性间进行假性交配而繁殖(安卓珍尼即英文androgyny,雌雄同体)。
这个女人和丈夫的关系有问题,她不能安于做一个给男人传宗接代的容器。
在山上,她于孤独中隐然感到,仍需求助于男人。
这时正好有一个看房子的园丁,他帮助了她,也使她落入男人欲望的压服下。
后来,男人为她捕来了安卓珍尼,这东西目睹了两个异性人物之间一场场挑战与征服。
“他一边蹂躏我的身体,我一边絮絮不休地折磨他的精神,只要我说话,他便害怕,他害怕超越他能力范围的东西。
很奇妙地,我变成了话语和声音,近乎忘却了肉体的感觉;当他把精液灌进我的体内,我便把说话灌进他的耳朵。
”
单性的安卓珍尼仿佛是存在于女主角心目中的一种理想:
不假异性,无涉它求,独立地繁衍生命。
这样岂不是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在阴道内进行的真正的战争”?
包括在整个社会上,由于女人承担的生育的角色、由于她们体质上的弱势而被另一性置于的被压制的地位?
在《双身》中,雌雄同体的指涉与《安卓珍尼》不同,作品不是写一个女性寻找单性的自足体,而是写一个男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女人。
他的生命被时间划分为两半,既拥有前半生作为男子的记忆,又面对现在的女子身体,如何认同自己的新的性别身份,如何与过去的亲人、朋友调整关系及相处的过程。
这些都围绕一个性别认同的问题。
它是一个失去了男身,而还不愿意接受女体的人物的回忆,因此,这些回忆带有寻找过去自己身上双性成分的含义。
这样,叙述成为一种非男非女的中性角度,它是回顾在一个社区的人群中,人们如何识别性别,那些被认为反常的形貌会陷入怎样的处境,身在这种规定中,识别自己的性别身份实际上何其困难。
而与异性相处,也同样牵扯了复杂难辨的脉络。
朱双一《台湾文学中的“新女性”角色设计》(《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1期,页97-104)一文提出,寻求妇女解放之途,不仅需要“破”—揭露、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打破数千年来妇女头上的枷锁,而且需要“立”—造就有别于旧传统的女性人格,树立新的女性形象。
这种“新女性”的角色设计至少可有三种类型:
一曰角色翻转,反客为主。
这种女性对男权主义的压迫有深刻的体会和愤慨,不惜以各种方式加以反抗,甚或“以其道反制其人之身”地对男性施于压迫和制裁。
它以“女尊男卑”的关系式对传统两性关系作了180度的翻转。
二曰保持特性,呈示自我。
这类女性并不否认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但却不承认所谓男优女劣的传统认定,因此顺应自然地保持着女性诸多固有的特质,并以此显示了女性“自我”的存在和价值。
它显现的关系式是两性的“并列”。
三曰双性人格、雌雄同体。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