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wejr13成中英 从法到行中国佛学的发展与建立.docx
《Abwejr13成中英 从法到行中国佛学的发展与建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Abwejr13成中英 从法到行中国佛学的发展与建立.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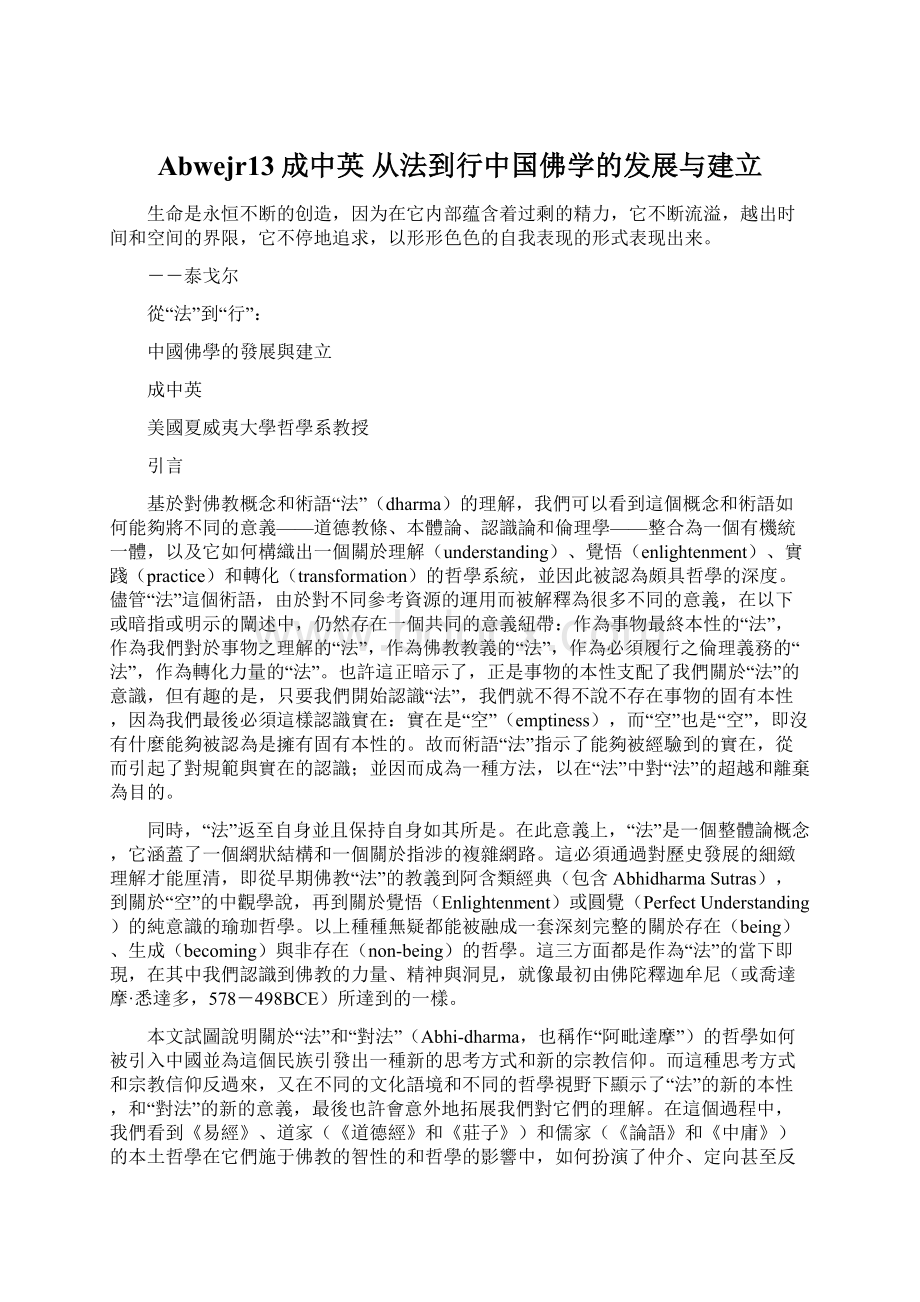
Abwejr13成中英从法到行中国佛学的发展与建立
生命是永恒不断的创造,因为在它内部蕴含着过剩的精力,它不断流溢,越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的形式表现出来。
--泰戈尔
從“法”到“行”:
中國佛學的發展與建立
成中英
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
引言
基於對佛教概念和術語“法”(dharma)的理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概念和術語如何能夠將不同的意義——道德教條、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整合為一個有機統一體,以及它如何構織出一個關於理解(understanding)、覺悟(enlightenment)、實踐(practice)和轉化(transformation)的哲學系統,並因此被認為頗具哲學的深度。
儘管“法”這個術語,由於對不同參考資源的運用而被解釋為很多不同的意義,在以下或暗指或明示的闡述中,仍然存在一個共同的意義紐帶:
作為事物最終本性的“法”,作為我們對於事物之理解的“法”,作為佛教教義的“法”,作為必須履行之倫理義務的“法”,作為轉化力量的“法”。
也許這正暗示了,正是事物的本性支配了我們關於“法”的意識,但有趣的是,只要我們開始認識“法”,我們就不得不說不存在事物的固有本性,因為我們最後必須這樣認識實在:
實在是“空”(emptiness),而“空”也是“空”,即沒有什麼能夠被認為是擁有固有本性的。
故而術語“法”指示了能夠被經驗到的實在,從而引起了對規範與實在的認識;並因而成為一種方法,以在“法”中對“法”的超越和離棄為目的。
同時,“法”返至自身並且保持自身如其所是。
在此意義上,“法”是一個整體論概念,它涵蓋了一個網狀結構和一個關於指涉的複雜網路。
這必須通過對歷史發展的細緻理解才能厘清,即從早期佛教“法”的教義到阿含類經典(包含AbhidharmaSutras),到關於“空”的中觀學說,再到關於覺悟(Enlightenment)或圓覺(PerfectUnderstanding)的純意識的瑜珈哲學。
以上種種無疑都能被融成一套深刻完整的關於存在(being)、生成(becoming)與非存在(non-being)的哲學。
這三方面都是作為“法”的當下即現,在其中我們認識到佛教的力量、精神與洞見,就像最初由佛陀釋迦牟尼(或喬達摩·悉達多,578-498BCE)所達到的一樣。
本文試圖說明關於“法”和“對法”(Abhi-dharma,也稱作“阿毗達摩”)的哲學如何被引入中國並為這個民族引發出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
而這種思考方式和宗教信仰反過來,又在不同的文化語境和不同的哲學視野下顯示了“法”的新的本性,和“對法”的新的意義,最後也許會意外地拓展我們對它們的理解。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易經》、道家(《道德經》和《莊子》)和儒家(《論語》和《中庸》)的本土哲學在它們施于佛教的智性的和哲學的影響中,如何扮演了仲介、定向甚至反對的角色,它們的影響導致了中國佛教的形成和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看到,為了在佛教進入中國智性文化傳統主流的本土化過程中達到更好的融合、和諧與實踐,“法”和“道”作為兩個強大的哲學范式和文化符號,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尤為需要。
以“道”轉化“法”的同時,“道”也被“法”所轉化。
後者的轉化同樣是真實的。
所以,在中國文化意識中,“道”和“法”作為聯結並融合洞見與智慧的兩種力量,始終保持著活躍的生命力。
這可看作是“法”與“道”兩者的傑作。
中國佛教的道路:
譯“dharma”為“法”
我們必須承認,自從佛教從西元4世紀被引入中國以後,對“dharma”的中國式理解也已走上一條開放但迂回曲折、充滿挑戰性的發展道路。
這一發展最終以鳩摩羅什(344-413)和玄奘(596-664)這樣的偉大翻譯家以及如吉藏(549-623)、智顗(538-597)、法藏(643-712)這樣的佛教領袖與學者的翻譯與闡釋的偉大成就為標誌。
i
至於術語“dharma”(它被堅持作為實存的要素)的翻譯問題,儘管還不知道它被譯為中國術語“法”(法則、方法)的確切時間,但最初的翻譯不可能早于三世紀,因為此時小乘經典中的“dhyana”(定)和“prajna”(智)開始被翻譯。
在由於北方部落入侵引起的混亂中,早期佛教的七個宗派在中國興盛起來,六個在南方,一個在北方。
有趣的是,西元220年到420年期間,所有的佛教概念都以道家語言為基礎被描述或解釋。
例如,“sunyata”的概念被理解為“無”(虛無),而“tathata”(真如)的概念則被翻譯為“本無”,即原初的無。
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dharma”在這一時期被翻譯為“法”。
這個術語確實已在《維摩詰經》的鳩摩羅什譯本以及僧肇(384-414)的《物不遷論》和《不真空論》中出現。
在《物不遷論》中,僧肇引《放光經》雲:
“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又引《道行經》雲:
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
但什麼是“法”?
為什麼要將“dharma”譯為“法”?
由於它意有所指,又缺乏相反的歷史證據,我們可以提出以下回答。
由於“dharma”原本意為佛陀的道德教條,同時被看作一種達到“般若”(prajna)和“涅槃”(nirvana)的方法、模式和法則,所以,“法”作為法則和方法的概念可使之作為合適的譯名,而且比譯“空”為“無”的翻譯更恰當。
但這也意味著中國譯者可能沒有將毗曇宗視“dharma”為實存或最終實在的要素進行的再解釋考慮在內。
儘管如此,作為實存要素的概念終究還是被引入到術語“法”的使用中。
因為在《百法明門論》的翻譯中,就提到了“五位法”(lawsoffivepositions)和“百法”(ahundredlawsasversussay,75laws),他們統攝人類意識內外的一切事物。
在考慮他們由什麼組成時,他們正是那些可以歸入我們感官經驗、感受、行為以及對存在或非存在可能模式進行想像和思考的事物。
在此意義上,“法”更多地被理解為存在和非存在的狀態、事件、模式、屬性和關係。
但將存在和非存在的這些狀態稱為“法”,就是指出它們的確被給予了作為我們經驗內容乃至實存的各種形式的構成性要素的意義,指出了構成事物結構和活動等級的一切東西其存在狀態的不變性。
然而,仍然有一個來自阿含類經典的關於“dharma”的理論,沒有被帶入到術語“法”的帶有暗示性的微小差別中,即作為總是在變化的事物之原子要素的“法”。
直到現代的熊十力(1883-1968)才承認了“無間”之“法”的刹那(ksana)理論。
熊十力將“法”的基本理論解釋為洞徹世間變化本性的基礎,這就走向了將“法”作為事物不斷變化中的個別點的易經式解釋。
需要注意的是,“法”原本是個規範式的術語,根植於人類意向並指向人類的行為。
它在本質上是規定的。
但當這些用法是有意為之時,通過在文本與語境的世界中指涉事物和物件,其意義產生了微妙的形上學的變化,“法”便通過這一變化取得了實存要素的描述性意義。
這一發展對不僅作為一種救世論還作為一種本體論的佛教的發展十分重要和關鍵,它是將佛教救世論建立在被稱作“法”的存在的本體論基礎之上的結果。
然而毗曇宗將“法”的存在視為“存在”的同時,也將其作為不斷變化的生成,中觀派則通過表明作為存在的“法”實際上既不是“存在”也不是“非存在”駁斥了這種實在主義的本體論。
之後,瑜珈行派在對中觀派的回應中,提出了意識理論,認為“法”被表明有能力通過意識深層的種子顯現事物界。
這兩個宗派在中國是作為空宗(SchoolofEmptiness)和有宗(SchoolofHaving)被認知的。
ii需要注意的是,當龍樹(100-200CE)被介紹給中國時,無著(410-500)可能還未闡釋他的“瑜珈學”,亦即唯識學,更無需提比他年輕的世親(420-500)將理論系統化的工作。
直到玄奘645年帶回許多瑜珈行派的經典後,這套學說才被完全引入中國,而這已是無著最初形成這套學說的150年以後。
其間,作為“空”的“法”將自身建立為理解佛教的底基。
然而新的學說實現了這樣的目的:
將人心與“空”聯結起來,將事物界解釋為人類意識的顯現。
這為將空宗和唯識學融合為一個關於覺悟的實踐哲學和中國禪的“不執著”打下了基礎。
這種融合之為可能是由於對“道”持物力論式的理解,這種理解既是發酵的力量,也是轉化和融合的最終方式。
作為存在於印度大乘佛教和中國大乘佛教之間緊張和競爭的產物,這種融合既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當融合在人心覺悟的行為和事件中得到實現時,人得以像佛陀或菩薩那樣自由行動。
在覺悟及隨之而來的自由行動的語境中,“法”的強制性力量完全消退,並為“道”所復原。
在扮演了指涉實存要素的角色之後,將“dharma”譯為“法”或方法和法則,則也完全且最終地合理化。
當然,這個過程不意味著“dharma”或“法”作為實存要素的形上學教義被拋棄了。
正相反,它以歸入覺悟學說的方式存在,在作為錯覺基礎的同時,也作為朝向覺悟興奮的基礎。
在此意義上,不管是在印度佛教還是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中,毗曇宗哲學都發揮了有益而適時的作用。
如此理解“法”,問題在於厘出“法”的理論在中國佛教實際發展中的演化特徵,其間它出現於4世紀,而到8世紀則達到了禪宗的高度。
在我看來,我們可以對應500年間中國佛教發展的五個階段去追溯這段演化過程。
這五個階段標記了對“法”的理解的轉換,“法”又帶著與其根本性質和功能類型相關的不同獨特屬性和發現,而這又被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打上了烙印。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既是“法”這個概念在理論上的豐富也是實踐的轉化,正如佛教哲學理論的豐富和實踐的轉化。
事實上,沒有中國佛教的哲學發展,“法”的概念不會如此鮮活而普遍地被引用,且普遍存在於中國佛教經典的形式和所有對它的使用中。
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中國佛教的發展中存有創造一種哲學式融合的優勢,並不會感覺到被印度那裏從“法”到“對法”的歷史發展所束縛。
當大乘佛教在印度開始回應毗曇宗實在主義原子論的形上學問題時,在中國的中國佛教宗派則可被看作是根據“道”或道家的經驗與理解所產生的對印度大乘佛教的一個哲學回應。
因此,我們必須發掘對作為一個結構和一個實現過程的“法”的更深入的理解。
我們可以看到存在“法”的四個方面:
本體論的、認識論的、倫理的、救世論的。
在印度佛教中,“法”的這四個方面總是被提及或是被暗示。
“法”解釋事物的實存、事物的存在方式、它們如何被理解以及我們如何達到、實踐和體現“法”。
救世的信念常常被認為是佛教徒成佛覺悟的偉大旅程:
既可以是從存在的佛和菩薩那裏尋求幫助,也可以是佛性通過自身努力走向覺悟這個過程的實現。
我們在《華嚴經》第二十六部中的《十地經》那裏能看到的“十地”(bnhumi,地),顯示了一個投入和專注的菩薩可以轉化到一個已達到完全解脫和自由的狀態,這個狀態被稱為“佛”。
iii
“法”和“道”的哲學性比較
如何將“法”的概念和“道”的概念進行比較?
首先,“道”不像“法”,在研究存在的亞里斯多德式的本體論意義上,它並不首要地是、也不僅僅是一個本體論術語。
它更多地是在一個本體宇宙論意義或宇宙本體論意義上被使用,而非僅是本體論意義。
對於《道德經》中的老子(西元前六-西元前五世紀)而言,“道”是世界萬物的最終源頭,而且它被設想為無休無止地生成和維持著所有的事物和事件。
因此,“道”是創造性的、發生性的、生產性的、原發性的和始終活躍著的。
但是“道”的創造和活動不是簡單地通過從存在到存在物的生成,而是最終由“非存在”或“無”中產生“存在”。
這意味著“道”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無”創造了“有”(being),並且它的創造是自然的或者說是自發的,無為以使萬物成。
因此,“道”的行為是一個無索取的給予行為,也是不作任何要求的自我否定的行為。
所以是“無為之為”,呈現的是無形式的形式。
道家中這種創造和創造力的概念是理解道家如何將印度佛教轉化為中國佛教(尤其是禪宗)的關鍵。
“道”另一個重要的顯著特徵是,它是無所不包而普遍深入的,因此術語“道”不指向世界上事物的任何特殊方面。
但如莊子(c.395-299BCE)所言,就“道”是“非佔有性”的這一點來說,它必須居於世界的所有部分中,無論尊卑高低。
根據“道”這種普遍深入的存在,所有事物無論尊卑都通過“道”而被平等化了,亦即以“道”視之,它們在價值和用益方面平等卻又並非同一。
在此意義上,“道”是宇宙和世界的生命精神,一個事物僅僅是“道”的生成,它通過作為“道”的一個部分來實現它的特性。
最後,“道”可以被人心所經驗。
這意味著人心體現了“道”並且為了意識到“道”而要求對事物轉化的反思和直接的感覺。
它要求對於“道”更多的反思和理解,以使得一個人可以在“道”中生活,由此超越存在的界域甚至自由於死的焦慮和生的煩惱之外。
生死都是“道”的轉化的創造性階段,對於二者,一個人應為之快樂和懷有感激。
iv
基於對“法”的概念和“道”這些意向的和已實現的意義的基本描述,這兩個概念一定是代表了經驗這個世界的兩種相反方式,以及思考自然和人類存在的兩種相反方式。
它們的不同基本上在於客觀指涉的本體論與時間性創造的宇宙論的不同,也在於幻覺和拒斥的現象學與承認和接受的現象學之間的不同。
二者都可以尋求精神自由,從奴役中解脫,但它們的行為模式迥然有別,其樣態正是我所稱的否定辯證法與調和辯證法之間的差異。
v
必須注意,這兩條進路在邏輯、本體論和宇宙論上都構成了一個到達實在的補充:
實在既是客觀化的也是“生生的”,既是結構的也是過程的,既是可定義的也是不可定義的,既是超越的也是內在的。
但是在我們作為人的態度上存在著根本的不同,這種根本的不同要求至深的努力和創造性的思考方式以達到我們所期望的妥協和融合。
也許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三論宗和唯識宗,中國佛教的其他三個類型,即天臺宗、華嚴宗和禪宗佛教,都可以被準確地看作是為了印度佛教與道家或道家/儒家之間的妥協和融合而努力的矚目成果。
在此意義上,處於真正發展中的中國佛教可被看作印度佛教與中國道家、印度文明與中國文明之間的一座橋樑和接合點。
最後,我們要指出儒家在中國佛教的創生和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準確地講,正是在《中庸》和《易傳》中找到的儒家的和諧辯證法使“法”和“道”的妥協和融合在禪悟的實現中得以可能。
為理解“法”和“道”如何變得有不同的指涉和不同的意義,就需要理解,一個哲學傳統中的一個根本概念總是對實在的深刻體驗,故而恰好是代表實在的最重要和最具啟發性的方面。
我們不必去假定實在必須在人不同的經驗中揭示其本性的同一面。
這依賴於人去確定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方面。
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傾向於是實在的這樣一個方面:
它強調深刻的客觀性和持久性,甚至在表面上也主宰了所有的事物。
但以中國本體宇宙論的經驗來說,“實在”最重要的方面似乎是,它在存在的各個領域中富有創造性的無限變化,它作為變化的結果卻也同是生成的領域。
我們必須注意到,在中國哲學的“道”的語境中,“法”的概念所經歷的中國佛教式的轉化有五種形式。
這五種轉化形式在許多共同因素上的重疊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但作為既是歷史的又是哲學的發展的五個階段,又實現了意義和重要性的新的維度。
中國佛教中“法”轉化的五種形式是:
(1)三論宗中作為“空”的“法”;
(2)唯識宗中作為心靈中“識”的“法”;(3)天臺宗中作為覺悟方便(upaya)的“法”;(4)華嚴宗中作為“真如”的“法”;(5)禪宗中作為“明心見性”的“法”。
我們對每個宗派學說的實質有所把握後,就可以對作為“實在”轉化象徵及人之實存覺悟的工具的“法”有更深的理解。
以下我們將具體描述中國佛教五個宗派發展的特徵,它們試圖努力將哲學論題和理解置於“法”中。
吉藏的三論宗
因為它建基於鳩摩羅什對龍樹兩部重要論著——《中論》和《十二門論》——的翻譯,以及對他弟子所著《百門論》的翻譯,這個宗派本質上是龍樹中觀哲學的代表。
儘管鳩摩羅什和他的弟子僧肇已為發展龍樹的觀點打下了基礎,但卻是吉藏(549-623)最終將其哲學作為中國的一個主要宗派進行發展和系統化。
吉藏深化了“二諦”(theTwoLevelsofTruth)和“八不”(theEightfoldNegations)。
眾所周知,“二諦”是指永居於短暫名相中的、有依賴性的偏狹真理“俗諦”,和普遍性的絕對真理“真諦”,真諦指出所有的“法”都是空的。
這個學說被看作是“八不”這一論證過程的結果,“八不”認為法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去、不來的。
這個論證根本上是建立在龍樹對“四否定”(tetralemma)的運用上,它是對“法”作為存在、非存在、既存在又非存在以及既非存在又非非存在的分別否定。
儘管“四否定”似乎是種邏輯,但卻不是邏輯的暗示(因為邏輯的暗示仍然是人必須肯定“法”的存在或肯定“法”的非存在)。
它代表的是否定的過程,為看到“法”的“空”,這個過程被看作是必需的。
因為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擁有否定的兩極,每一極都蘊涵另一極的否定。
所以,為了肯定“法”的存在,必須否定它的非存在,反之亦然。
然而我們卻不能同時肯定二者或否定二者。
在此意義上,“法”的本體地位是不確定的也是不能確定的,也正在這個意義上有了“空”且不應執著於它。
對中國人的心靈和傳統來說,這種邏輯和這種“看”的方式都是陌生的。
中國人的心靈和傳統極為看重人對作為現象出現的事物界或人自身的經驗,沒有任何思想過程可以剝奪實在的這層意義。
儘管一個人能通過一個大的、無所不包的“道”來超越實在,但將“法”的超越看作持續不斷的否定卻會導致一個自我反駁和自我挫敗的困難處境。
在此之後,當禪悟被經驗到時,它便被同時經驗為否定和確證。
被否定者逐漸轉化為人的一個更高的或更原初的狀態,這滿足了對本體論和救世論的雙重需要。
然後被認為是“法”在人對“法”的經驗中實現的一個新本性。
這就是“法”被認作佛性(Buddhanature)的本質。
儘管三論宗持虛無主義立場,但直到9世紀晚期它仍在中國使自己保有一個典型的印度式見解。
它作為一個動因和從俗諦到真諦的超越而存留下來。
至於什麼是真諦,則需要一個洞見和新的解釋。
玄奘的唯識宗
如前文提到的,唯識宗(瑜珈行派)由玄奘及其弟子窺基(632-682)建立。
這又是個典型的印度宗派,它關注人心,視其為八種意識構成。
除了由人體五種感官而來的五種意識之外,還有第六識“意識”(manoavijnana)和第七識“我識”(manasvijinana)。
第八識則是“藏識”(alaya),它存有過往的善行與惡行的種子,並作為其他七識能量的引擎與源泉起作用。
這第八識處於持續的變化中,並且維持著種子與從外在顯現引入的知覺、認識之間的持續的相互作用(熏習)。
第七識緊緊依附第八識,並且形成了自我的概念,它由自我利益的惡的種子組成。
第六識和前五種感官意識的活動是辨別與區分,這通向外部事物的顯現。
不過,每種感覺產生一種關於感覺的特定客體,而第六識通向的則是客體作為整體的顯現。
所有這些活動也根據因果律被解釋。
為了解釋世界的客觀性,這一教義還為每個意識提供了“四分”(fourproof-functions),即:
見分、相分、自證分和證自證分。
正是基於作為一個複雜意識系統的心智活動,我們才有了一個被區分的“法”的世界。
在此意義上,諸法(dharmas)是在世界中展現的形式。
因此術語“法相”被用來指這個宗派。
這暗示了“法”通過心靈的意識不可避免地被轉化為“相”,而且還必須看到諸法一如形式那樣呈現出來,而且諸法也一如心靈的轉化。
“法相”的概念也指出可以將事物和人自身的本性看作是意識的轉化,而又不受之束縛。
看到這一點是超越與自由的關鍵。
作為近似的反思救世論,把“法”轉化為“相”的法相哲學(“相”的概念,暗示著交互作用的可能性,用來與指自然形象的自然主義概念“象”相區別)導致了理解“法”的三種形式,即作為偏計所執結果性呈現的“法”,作為依他起結果性呈現的“法”,以及最終作為圓成實結果性呈現的“法”。
通過律法和修行,一個人可以瞭解到理解的最後形式,並可因此不受第八識熏習效果的影響。
這就是最後的拯救。
當然,它預設了在第八識中存在著淨與不淨的種子,以及人能夠以淨的種子獲得克服不淨種子的力量。
這再次指向了一個人本性中這麼去做的潛在能力,而這也一定是在第八識的本性中。
這些假定在“法相”哲學中並不明顯,也沒有被討論。
不過,這個宗派的文本引出的問題導致了一部叫作《大乘起信論》的論著對第八識的結構革新,它為在道家和儒家影響之下的其他宗派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
在這部作品的影響下,可能會有猜測認為唯識宗很快就失去了它的訴求,而7世紀禪宗的興起確信和承認“八識”結構的人心有一個底基,即佛性,它應最終為克服業力(karma)來源的不淨種子和將人提升至解脫境界提供引導和力量。
在現代,陳榮捷在其《中國哲學文獻選編》(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vi)中提到的,正是章炳麟(1868-1936)與佛教學者歐陽競無(1868-1936)、太虛法師(1889-1947)一起,使瑜珈學著作中的興趣重新復蘇,並如前文所提,促使熊十力在重建新儒家哲學以回應其時代時採用了唯識理論。
但實際上,熊氏這樣做時,除了將人心看作理解世界和自我實在的工具之外,也訴諸“法”的毗曇視角。
“法”於是被揭示為中國哲學“道”和“易”在古典意義上的創造性的變化過程。
智顗的圓融的天臺宗
“二諦”的中觀學所表達的“法”在天臺宗那裏,被智顗(538-597)發展成了“圓融三諦”理論。
這個發展是對中觀概念“法”的自然回應,這裏的“法”是基於重複性否定的“空”。
事實是,儘管對表像加以否定,但仍然存在一個表像的世界。
就“中道”能夠被看成是對兩端的否定而言,為什麼它不可以被看成是對兩端的確證,亦即二者都是短暫而空虛的?
“中道”必定是理解“法”的一種方式,以至我們能夠看到最終的真理並過上和諧的生活。
問題是,我們怎樣來解釋以此為目的的“中道”,怎樣解釋我們對作為“中道”的“法”的經驗。
智顗提出了這些根本的問題,並且以綜合、調和和圓融的精神回答了這些問題,而這都是《易經》和道家著作思考方式的特徵。
尋求圓融以及確證所有將實在作為真實的經驗是這種思考方式的兩個基本要求。
天臺宗的“中道”因而是通過對“二諦”的領會而實現的二者統一體,也因此是“三諦”的統一體。
這無疑是一種新的經驗,也是“法”的一種新道路,也許它植根於“法”的本性之中。
所有“法”的相互認同的經驗,就是“中道”的真實本性。
關於世諦,智顗看到所有的“法”都是暫時的且彼此依賴的。
他通過“一念三千”表達了這種洞見或“中道”的新意義。
“三千”指的是三千世間,它是如此得來的,即具有真如十性(性,相,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的十界“存在”進行相互乘積,再將結果數位1000乘以3,“3”包含的是眾生、國土和五蘊。
因此,在對任何事物的一念之間或任何觀念的產生中,所有存在都不可避免地捲入“法”在時空中的相互貫通和彼此依賴。
這更意味著所有現象都是本性(即佛性)清淨心的顯現,並且每個顯現都是作為渾一整體的清淨心。
我們可以看到,智顗的學說中承認了清淨心的實現是每個人和每個存在的最終本性。
與唯識宗中的心不一樣,清淨心是保持持續和不變的。
由此可以肯定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能成佛,就像儒家所認為的人人皆可成聖賢。
這就使之成為有關普渡的學說。
如我們在《易傳》和《道德經》中所看到的,這種學說產生於一切變化中的“道”的概念,它是普遍而無所不包的。
同時,這種學說還以孔子(551-479BCE)、孟子(371-289BCE)性善說為基礎,將善看作持守原初的本性。
事實上,將心本身看作一個原初本性(佛性)的顯現是一個儒家概念,它集中落腳于《易傳》和儒家的孟子。
在考慮有關普遍拯救的闡釋在理論上如何可能時,這一問題就產生了,即從佛教文本中取得哪些相關的資源使得這種解釋變得可行、具有啟發性?
一個建議是《法華經》中有真如十性的教義,而《中論》中“中道”的“空”也是涉及到“法”的特性的學說。
但是要發現這些概念並將其放到一處形成關於“三諦”的學說,則要求慧文對其有所洞察,他是智顗的祖師。
由於他的洞見,當來到浙江天臺山生活和說法時,智顗被啟發將其闡述為一個完整的學說並將《法華經》尊為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