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
《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易中天走近顾准12.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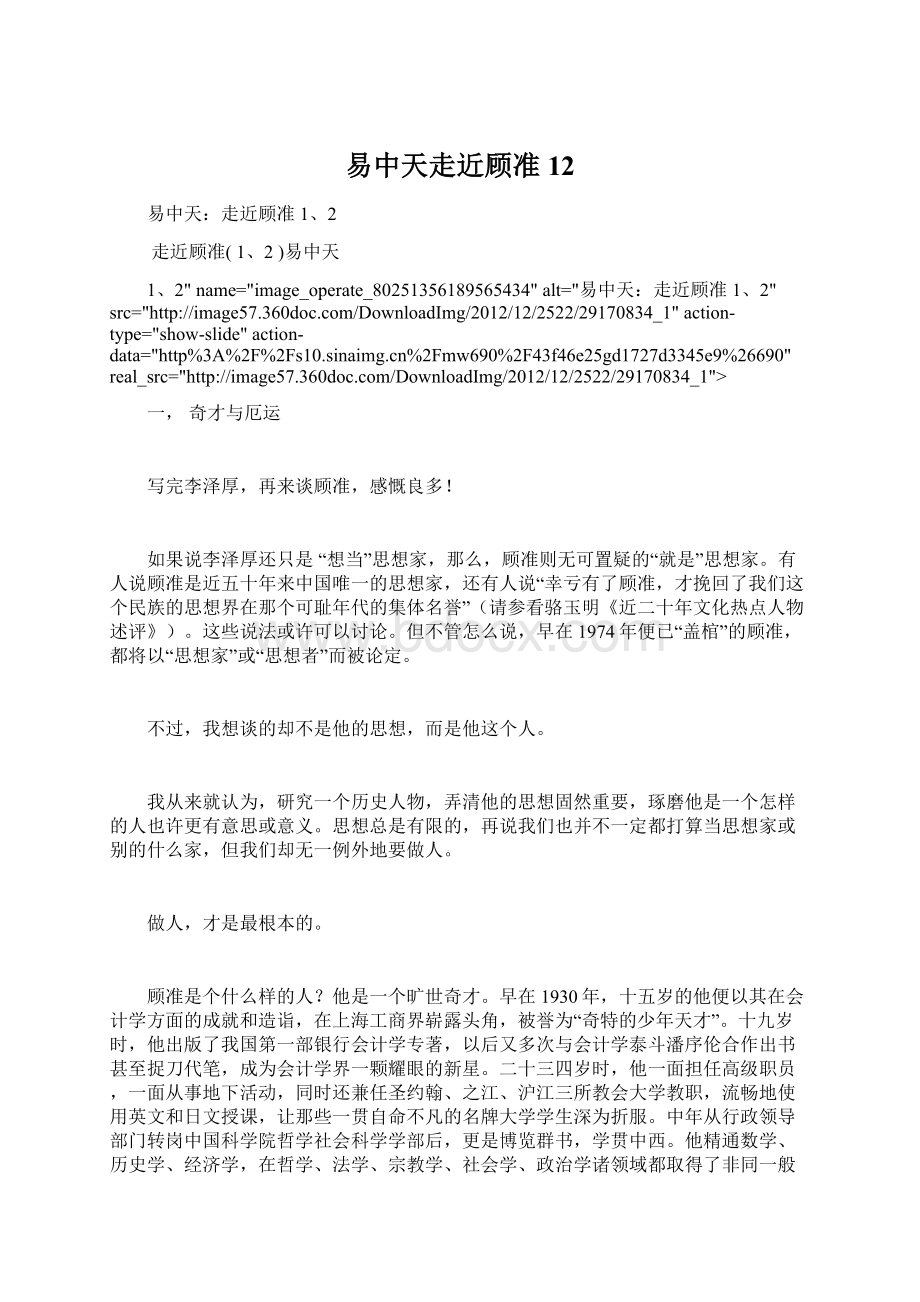
易中天走近顾准12
易中天:
走近顾准1、2
走近顾准(1、2)易中天
1、2"name="image_operate_80251356189565434"alt="易中天:
走近顾准1、2"src="action-type="show-slide"action-data="http%3A%2F%2F%2Fmw690%2F43f46e25gd1727d3345e9%26690"real_src="
一,奇才与厄运
写完李泽厚,再来谈顾准,感慨良多!
如果说李泽厚还只是“想当”思想家,那么,顾准则无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
有人说顾准是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还有人说“幸亏有了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请参看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这些说法或许可以讨论。
但不管怎么说,早在1974年便已“盖棺”的顾准,都将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论定。
不过,我想谈的却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这个人。
我从来就认为,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也许更有意思或意义。
思想总是有限的,再说我们也并不一定都打算当思想家或别的什么家,但我们却无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顾准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旷世奇才。
早在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十九岁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专著,以后又多次与会计学泰斗潘序伦合作出书甚至捉刀代笔,成为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二十三四岁时,他一面担任高级职员,一面从事地下活动,同时还兼任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教职,流畅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课,让那些一贯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学学生深为折服。
中年从行政领导部门转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更是博览群书,学贯中西。
他精通数学、历史学、经济学,在哲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诸领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围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译著、论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如果他象陈寅恪、钱钟书那样,有着家学渊源、留洋经历倒也罢了。
然而他却出身不过学徒,学历不过初中,少年为生计困扰,青年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症折磨。
如此艰难困苦,却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以至于被认为“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叹服。
顾准又是一个老革命家。
早在三十年代,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斗争,并于1935年入党,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据地,在“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
1949年,三十四岁的顾准,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掌管了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并成为显赫的副市长候选人。
这时的顾准,真可谓意气风发,光彩夺目,前程似锦。
上海多少领一点世面的人,无不知晓他的大名。
无论按照旧社会的眼光,还是新中国的标准,年轻的顾准都是男性羡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仪的“白马王子”,光是求爱的情书都不知收到多少。
如果说真有什么“天赋”和“运气”的话,那么,命运对顾准似乎不薄。
孔子说:
“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
顾准呢?
十五岁当校长,三十岁当局长,岂非“天资聪颖”又“少年得志”?
二,才气与骨气
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会历史方面的“客观”原因或者说“大气候”就不去说他了。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就连章乃器这样的共产党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连彭德怀这样的元帅元勋都要被置于死地,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都保护不了自己,遑论其他?
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
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
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和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拉出来凑数的了。
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
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
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
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
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
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
因为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
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这就是“草菅人命”了。
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
问题是即便要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
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
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
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
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
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
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惲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资本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
顾准有什么呢?
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
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
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
一种猜测是:
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
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
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
顾准实在太聪明了。
当会计,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有三个大脑”。
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而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
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
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
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
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
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
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
“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
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
早在三十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
“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
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
他会掂量你的斤两。
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
徐雪寒说:
“我不把自己当作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
”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这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徐雪寒没有被顾准“看不起”,不等于别的干部没在他那里吃过瘪挨过训碰过钉子。
许多熟悉顾准的老干部都说:
“他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型知识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极强,有时与人说话,显得得理不让人,又耿又倔,争辩时甚至言语尖刻,容易伤人”。
这大约是确实的。
因此,当有人举报顾准扬言“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时,就连陈毅也信以为真。
顾准本人是一再否认的,而且多次辩诬。
以顾准之真诚耿直,如果当真说过,不会不承认。
但尽管是谣言,却谁听了都觉得“像”。
第一,顾准确有这个能力,至少当市长没有问题。
第二,顾准确实敢于任事,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看着不对劲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口气像。
怎么个“像”呢?
还不是平时说话向来口气就大,而且一贯口没遮拦,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说!
的确,顾准总是“忍不住”。
即便当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层地狱,也本性难移。
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庄赞皇县农村劳改。
下放干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大搞“土法炼钢”和“技术革命”,他却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热讽:
“什么土法炼钢铁?
一场蛮干罢了!
”“不经过生产实践,怎么改革农具和磨子?
这也是一场蛮干!
”说完还不算,还要加重语气冷冷甩出一句:
“哼!
我不能不反对你们的蛮干!
”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你想,顾准翻到沟底了还这么“猖狂”,“高高在上”时还不定怎么样!
所以,要整治顾准,真是太容易了。
因为他的“辫子”实在太多,一抓一大把。
1951年,中央财政部要调他去担任预算司长,陈毅找他谈话,他却表示愿意留在上海。
不去也就罢了,何况陈毅也同意。
可是,当同事问他“何时入阁”时,——那时把调入中央部门戏称为“入阁”,他却说什么“入阁以后就成了盆景,长不成乔木了”。
这是什么话!
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乔木”?
中央部门都是摆设啊?
中央部门是限制人才发展的地方啊?
你把党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人?
如此胡说八道,不下拔舌地狱才怪。
要命的还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开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让人”。
他这个人,平时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还了得?
自然是死都不让。
他顶撞上级部门,顶撞苏联专家,就因为他有理么!
甚至在沦为阶下囚、俎上肉时,只要他认为真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向恶魔让寸分”。
这就坏事了。
在顾准自己,是“坚持真理”,在别人看来,则是“顽固对抗”。
好嘛,那就先杀杀你的威风,打打你的气焰。
这是顾准在“同类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别厉害、挨打次数特别多的原因之一。
顾准总是书生气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讲道理。
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
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
自然是“整你没商量”。
甚至,当整人被视为“革命行动”时,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就变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权威。
“革命”这个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顾准的那些小道理。
你有理,他还有理呢!
你不让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脚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会让?
你和他们讲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在这样的情况下,保全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赶紧“转变态度”,“低头认罪”,至少也做“低头认罪”状。
再起码,沉默,不吭气,什么也不说,哪怕少说两句,总可以吧?
然而顾准不。
只要有机会,他就说,而且还要大声说,当众说。
1961年11月,顾准刚刚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对欢迎他的家人大声说道:
“我不反对三面红旗?
胡说八道!
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在批判所谓“张(闻天)孙(治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都一边倒地慷慨陈辞,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以略带嘲讽的目光,睥睨着大批判队伍,铿镪有力地宣布:
“我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
”结果怎么样呢?
“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
而且,因为他“态度恶劣”,这回定的是“极右”。
是顾准不识好歹不知厉害吗?
否。
如果说“少年得志”时的顾准,确实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尽了苦头并被整得死去活来以后,他对自己言行的严重后果应该有着足够思想准备。
但在他看来,真理和人格比肉体更重要。
因此他决不肯轻易低下自己高贵的头。
不就是孤立吗?
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
不就是毒打吗?
那好,干脆把脸送过去,让你打个够,反正打死也不就范。
不就是低头弯腰“坐飞机”吗?
哼!
“你别看我前面的头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实,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啦!
”在“文革”那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动权威”都紧紧夹着“尾巴”。
不少人逢人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起码,也要穿得“朴素”一点,“普通”一点,甚至衣衫褴缕,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
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顾准,不但从不讨好任何人,还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烂衫时,身着西方绅士的背带裤,配西装背心,戴玳瑁眼镜,在众目睽睽之中昂首阔步,一脸对人爱理不理的神态。
顾准的傲气、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敛。
顾准“出格”的事情还很多。
“文革”初期,当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时,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
“读史”。
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还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如此公然对抗运动,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没有一身正气一身傲骨一身虎胆,岂是做得出来的?
当然,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顾准也曾违心地写过“认罪交代”,但这决不意味着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
`比方说,他可以承认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却断然不肯承认自己在劳动时“偷奸耍滑”。
其实“偷奸耍滑”云云,原不过是“革命左派”为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胡乱找的借口;而召开所谓“地头批判会”,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阶级斗争观念强”,时时都在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类批判会,是最没有道理可讲的。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以谁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无非显示“革命左派”有权任意处置“牛鬼蛇神”而已。
而且,在“革命左派”看来,“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的人。
说你“偷奸耍滑”,那还是轻的。
然而顾准都认为这是对自己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他一生正直认真,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凭什么要认帐?
不认帐,那就打。
打也不认,那就再打。
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顾准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但是,面对法西斯淫威,顾准却死活不认这个鸟罪。
当“革命左派”揪住他,恶狠狠地问“你到底服不服罪”时,顾准高高地昂起头来,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态度大声喊道:
“我就是不服!
”在场的劳改队员和干校人员,都无不为之深深震撼。
这就不是傲气,而是骨气了。
正是这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使我们一想到顾准这两个字,就肃然起敬,心潮难平。
古人云: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顾准就是。
他一身都是才华,而且都长在外面。
一身都是骨头,而且也都长在外面。
在中国,一个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条,便几乎注定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顾准却兼而有之。
那么,他不受磨难谁受磨难,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