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结构论 从中国古典诗歌看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建构.docx
《心物结构论 从中国古典诗歌看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建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心物结构论 从中国古典诗歌看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建构.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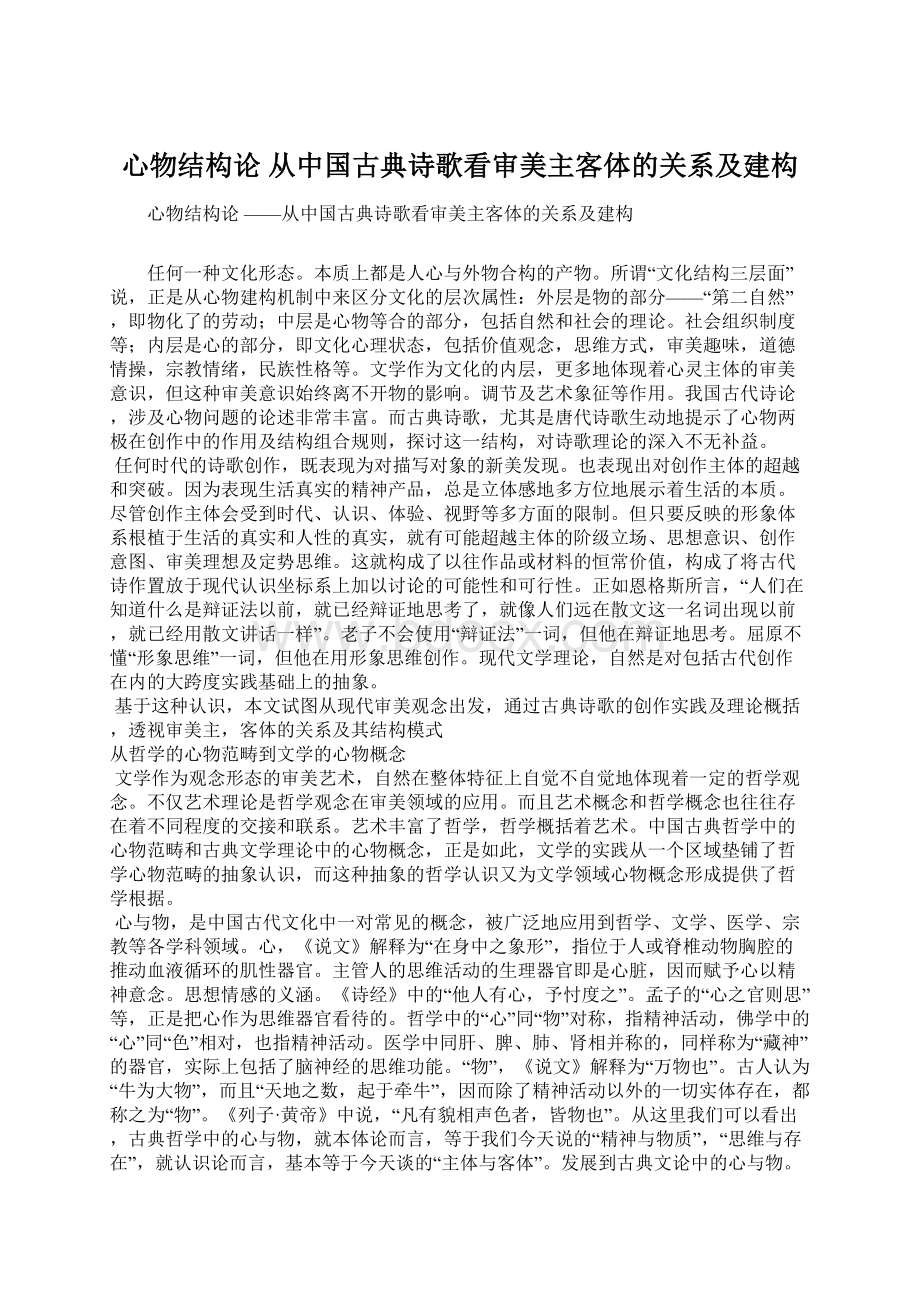
心物结构论从中国古典诗歌看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建构
心物结构论——从中国古典诗歌看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建构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
本质上都是人心与外物合构的产物。
所谓“文化结构三层面”说,正是从心物建构机制中来区分文化的层次属性:
外层是物的部分——“第二自然”,即物化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等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的理论。
社会组织制度等;内层是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
文学作为文化的内层,更多地体现着心灵主体的审美意识,但这种审美意识始终离不开物的影响。
调节及艺术象征等作用。
我国古代诗论,涉及心物问题的论述非常丰富。
而古典诗歌,尤其是唐代诗歌生动地提示了心物两极在创作中的作用及结构组合规则,探讨这一结构,对诗歌理论的深入不无补益。
任何时代的诗歌创作,既表现为对描写对象的新美发现。
也表现出对创作主体的超越和突破。
因为表现生活真实的精神产品,总是立体感地多方位地展示着生活的本质。
尽管创作主体会受到时代、认识、体验、视野等多方面的限制。
但只要反映的形象体系根植于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就有可能超越主体的阶级立场、思想意识、创作意图、审美理想及定势思维。
这就构成了以往作品或材料的恒常价值,构成了将古代诗作置放于现代认识坐标系上加以讨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就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
老子不会使用“辩证法”一词,但他在辩证地思考。
屈原不懂“形象思维”一词,但他在用形象思维创作。
现代文学理论,自然是对包括古代创作在内的大跨度实践基础上的抽象。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从现代审美观念出发,通过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及理论概括,透视审美主,客体的关系及其结构模式
从哲学的心物范畴到文学的心物概念
文学作为观念形态的审美艺术,自然在整体特征上自觉不自觉地体现着一定的哲学观念。
不仅艺术理论是哲学观念在审美领域的应用。
而且艺术概念和哲学概念也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接和联系。
艺术丰富了哲学,哲学概括着艺术。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心物范畴和古典文学理论中的心物概念,正是如此,文学的实践从一个区域垫铺了哲学心物范畴的抽象认识,而这种抽象的哲学认识又为文学领域心物概念形成提供了哲学根据。
心与物,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对常见的概念,被广泛地应用到哲学、文学、医学、宗教等各学科领域。
心,《说文》解释为“在身中之象形”,指位于人或脊椎动物胸腔的推动血液循环的肌性器官。
主管人的思维活动的生理器官即是心脏,因而赋予心以精神意念。
思想情感的义涵。
《诗经》中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孟子的“心之官则思”等,正是把心作为思维器官看待的。
哲学中的“心”同“物”对称,指精神活动,佛学中的“心”同“色”相对,也指精神活动。
医学中同肝、脾、肺、肾相并称的,同样称为“藏神”的器官,实际上包括了脑神经的思维功能。
“物”,《说文》解释为“万物也”。
古人认为“牛为大物”,而且“天地之数,起于牵牛”,因而除了精神活动以外的一切实体存在,都称之为“物”。
《列子·黄帝》中说,“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典哲学中的心与物,就本体论而言,等于我们今天说的“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就认识论而言,基本等于今天谈的“主体与客体”。
发展到古典文论中的心与物。
已包含了审美主体与客体,神韵与形象,内情与外景。
心性与境界。
理念与表象,思想感受与生活源泉等多区间的涵义。
这些不同区间的概念,在同一心物术语中交错出现。
从而带来了概念的宽泛和理解的模糊。
特别是面对区分“唯物”和“唯心”问题,容易把不同质涵不同层次的问题放到同一维度上处理,造成歪曲、误解、错位现象。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心物的质涵加以辩分。
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清这样几个问题:
①认识论意义上的心物范畴同本体论意义上的心物范畴有什么不同?
②文学的心物概念,应归属本体论范畴,还是认识论范畴?
③审美的认识和哲学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④诗歌意象在一般审美认识中有什么特征?
既然,心物这对范畴在古典哲学中兼俱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两种来自不同属域的概念,那么,显然就不能把它们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当然,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不可分割的哲学体系。
一定的认识论总得以相应的本体论为前提。
人生活在世界上,世界的存在及其本源问题自然是研究人的认识结构、功能及其方法的基础。
认识论中的主体和客体,归根结蒂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实体发展衍生的结果。
但是,认识论和本体论毕竟从不同的视域解释问题,对应的范畴往往存在差异。
主体和客体与精神和物质相对照地看,除了涵益性上不同的义指,又有关联性上不同的规定,虽然它们都是并列的对偶范畴。
但精神和物质不像主体和客体那样具有相互依存的关联性。
并称的范畴可以分割独存。
而互依的两极则不能分割独存。
正如恩格斯所言:
“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
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
。
精神是物质运动的产物,精神不能离开特定的物质。
而物质可以离开精神独立存在。
地球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只是35亿年以前的事情。
作为具有人的精神活动的生命出现则更晚。
至于主体和客体,只有当它们相互并存时,才具有各自本身所含的意义,认识的客体。
不是所有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只有那些进入人的感知区域、纳入主体对象性活动结构中客观物质,才能称之为认识的客体。
换言之,作为认识本体结构的两极,主客体二者的规定性都为对方所规定。
我们把“没有天就没有地”这句话的“天”、“地”解释为“天上”、“地下”时,这句话是成立的。
解释为“天体”、“地球”时则不成立。
道理如出一辙。
两对概念的层次。
属性不同。
因此,严格地说,认识论意义上无所谓主客体之间的分离和独存。
更不存在谁为本源的问题。
以往的哲人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往往笼而统之地谈论心物关系,或把不同区间的范畴加以等同,或把二者的联系机械地加以割裂,或把精神物质的关系二元化,或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本体化。
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多见。
在外国亦不乏其例。
“心外无物”的命题只有放在认识论的主客体互依关系上解释是合理的。
可是古代哲人并未作出界分。
“神不灭”论把精神和物质二元化。
“天人合一”的命题把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本体化。
而“万物一齐”、“芴漠无形”的说法则表现为相对主义的怀疑论。
王明阳解释山岩花树和人心的关系时说,未看此花时,花与心同归于寂,看花时,花色一时明白,便知此花不在心外从本体论角度看,这是彻底的主客唯心主义。
但不可否认。
王明阳从认识论的角度发现了审美主客体相互关照才能产生美感结构的组合规律。
问题在于古人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模糊地整合于一体之中。
苏格拉底认为普罗泰戈拉学说的归宿和结论是:
“物与我。
施者和受者。
无论存在和变为。
必是彼此相对相关。
……因此。
物与我惟有即时即境彼此相束相羁”。
这一观点,从本体论看是二元论。
从认识论看则指明了主客体的相互联结。
普罗泰戈拉亦未作出明确的界分,继往开来陷入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泥坑。
这并不是说。
在认识论中不存在唯物和唯心的区分。
既然一定的认识论总以一定的本体论为前提,那么,本体论中的唯物或唯心观点,必然贯穿到相应的认识论中去。
一般地说,如果把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那么就相应地把抽象理念“心理的东西”当成某种先天模式、先天结构和出发点,把认识成果作为超物质存在的绝对理念和永恒真理而顶礼膜拜。
如果把精神看作是被动的,僵死的,机械的,那么就会把认识归结为主体对客体直观关照的二项式结构。
但问题在于,本体论和认识论所讨论的重心有所不同,一是回答世界的本原问题,一是回答人的认识结构、方法问题,所以必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地看待。
在哲学本身便是如此,引用到文学理论方面,则更应当注重文学的特殊规律。
文学并不立足于本体运动规律的直观反映。
而立足于审美认识规律的能动反映。
所以,更应当从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上来探索审美结构。
当然,本体角度的探索也不能没有,认识始终是对宇宙及人的本体的认识。
事实上,古往今来的艺术理论派别在涉及人心与万物的关系时,均不外乎从本体论或认识论两个视角上加以研讨。
有些理论明显地有所侧重,有些理论则没有界分,随势立论。
玄学家从本体论出发探索包括艺术活动在内的心物关系。
拉普派主张用哲学认识论代替艺术认识论。
我国几十年来的文艺理论研究,事实上踏着拉普派的足迹徘徊。
随着近几年思想的解放。
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人们才开始从多方位上重新审视文学的特性。
从而开始突破单纯用哲学本体论解释文艺现象和用哲学反映论代替文学审美认识的局面。
在艺术审美理论研究中,从认识论和本体论双线交织的角度上研究心物关系。
并且注重文学审美的特殊规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这是因为:
审美认识活动不是发现对象的本体存在,而是发现对象符合人心美感的契机;这种发现始终不脱离人的感觉和表象,感觉和表象既是感性认识的升华,又是人类历史的自然积淀,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
情感和想象是审美认识中的内在灵魂,这个灵魂却不是认识论所研究的中心对象。
审美活动与一般认识活动在人的心理结构、功能特点上显然不是同半径的同心圆,而是中心错置的交叉圆。
所以,文学理论有必要突破一般认识论,向文艺心理学的深度发展。
认识论以相应的本体论为前提。
而对任何本体的认识必然转化为认识论;本体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对象,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方法;而这种对象和方法都要求落实到文学审美这一特定领域。
总之,认识论和本体论双重地同步化地统一于艺术实践活动中。
所谓双重同步,不是说二者绝对地均等于一切艺术生成的过程中,在艺术的本源和构成要素方面,更多地体现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功能;在艺术创造能力的结构体系中,更多地体现着认识论意义上的功能。
勾通二者的联系,才能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文学艺术的起源和本质,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
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物这对概念尚有存在的必要,当然更有定义和阐释的必要。
可是,遗憾的是,在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中。
人们对情景、形神、意境、虚实等对偶性概念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对这些概念的最后支石——心物问题。
却缺乏必要的研究。
主要原因在于躲避“唯心”的嫌疑。
事实上,讲“心”不等于“唯心”,关键要看讲什么样的“心”,怎样讲“心”,在什么层次上讲“心”。
如果把讲“心”,强调“心”的作用当成“唯心论”,那么就如同宣布生理学是唯物论,心理学是唯心论的一样可笑。
恩格斯曾经明确说过:
“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识。
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
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呢?
”。
在文学中,在审美活动中,比其它领域更神秘地体现着人的“理想的意图”和“理想的力量”。
不可否认,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对审美认识的研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但是,审美认识作为一个特殊的认识领域,有其特具的形式和独特的功能,有其特殊的结构和特殊的规律,也有其特定的对象和特定的方法,不能为一般的认识论、反映论所代替。
审美创造同样表现主体客观化的倾向,需要通过感知的感性形式和情感的形象形式体现,以凝聚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审美体验和美学理想,从而成为反映主体本质的一面“镜子”。
美的建构并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美的体验本质上属于人的潜意识的觉醒,美的内核是感性生命,深层心理中的情绪骚动,美的创造立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美的欣赏是铸陶性灵、净化人心的高层次的实践活动。
审美活动一般是在安全保障和生活保障得到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
自我实现的精神境界中包括了审美需求的真正实现。
早在我国的先秦时代,墨子即已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
审美活动需要相应的感知、理解、思维、品鉴能力。
需要具有社会人的多层心理元素,实质上即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形式。
科学认识的对象是物质实体和思维本体,审美认识的对象是人的性灵关照下的物质精魄。
科学忠实于客观、理性、逻辑、原理,文学忠实于主观、情感、潜意识、隐秘的心灵,科学要求事物的规定性,广延性,质量性,文学要求事物的形象性,独特性,美趣性,譬如说,对于颜色这种极为普遍的物质现象,科学认识和审美认识便从不同的方位入手,以达到不同的极限目标为终。
物理光学研究色的波长等物理现象,化学研究色的配合反应等化合作用,色度学研究准确可靠的测色标准应用知识,而绘画以色装点美的形容画面,建筑艺术以色渲染美的雕梁画栋,文学语言以色的文字符号组建美的形象意境。
色彩美感既以色光对人的生理、心理效应为基础,又能在情感的作用下冲破生理、心理效应,产生主客体组合的新质。
我们试以富于色彩描绘而又长于蕴寓性灵的唐诗来看,这一问题则显豁若揭。
“西岳出浮云,积翠在太清。
连天疑黛色,百里遥青冥”,自然山色的深邃,神秘,幽冥,显然不独是在自然属性,而是注入了人的能动的审美情趣,“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云绕黑山”色泽固然可佳,可在这里给人凄楚聊落、哀怨感伤的心理感受。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频生”。
人的审美情趣在山花水草中找到了对应物,“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流荡崩涌的色感恰恰出于豪迈不羁的天才诗人的视角。
“生僧柳紫白于棉”。
“塞山一带伤心碧”,则完全把诗人的内心的主观积闷移入了外界无情欲的物色之中。
可见,审美认识总是区别于科学认识,在审美区间中。
不同的审美对象、型类、体裁,自然也有其不同的特征。
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审美有别于绘画、电影、雕塑、音乐,文学不能直接诉诸画面的观视和音响的聆听,也不能作用于直接的肉体感触,而是通过特定的文字符号把情感、物形、色相、思想、情节翻示出来,它的形色、音像、意感都通过内心视觉、内心听觉、内心意觉加以传输和加以接收。
在文学体裁中,诗歌的审美又有别于小说、剧本、散文,诗是内视点最高的艺术,它的句式整齐,容量有限,音韵和谐,节奏分明,而且最忠实于人的性情灵感,最长于传达主观情思。
“感情是诗人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诗是以我们内在的感情,以我们的内心对一切美丽、善良并且理智的事物的向往作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按主观色彩的浓淡程度把艺术类别和文学体裁顺序排列的话,那么就会现出这样队列:
文学——书法——舞蹈——绘画——雕塑;诗歌——散文——戏剧——小说。
这些特征,使诗不同于以铺叙故事,展开情切为特征的小说,也不同于以展示人间矛盾冲突为主线的戏剧,更不同于多功能、多角度地反映生活的影视艺术。
诗在单刀直入地表现自我,跳跃式地抒发心灵世界。
就诗歌文学形式的涵盖面而言,它远不能囊括其它文学体裁的形式特征,但就诗歌审美揭示人的潜意识功能来看,它更能代表文学审美的本质特征。
小说是文学审美的膨胀面包,诗歌是文学审美的压缩饼干。
诗歌以其聚化的抒情色调高居于文学金字塔的顶点。
所谓诗是“艺术的王冠”的称号,就是从情感浓烈程度的层面上立论。
尽管,叙事诗的性质接近小说,但叙事的最终旨意仍在反映人的情感、愿望、要求,而且是用诗的形式和语言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审美认识比科学认识需要更多的心性、情性、灵性,诗歌审美比其它文学体裁需要更多的心性、情性、灵性。
但话又说回,心性、情性、灵性在诗歌创作中始终离不开特定的物象,凝练的情和艺术化的物如何融会组合,就成为诗歌创作中至关要紧的问题。
尤其是我国古典文学,直接导源于抒情短诗,并把诗歌作为整个文学史的主线,心物一体的理论在诗歌理论中显示得更为突出和成熟。
事实上,古典诗论中的形神、意象、虚实、有无、情景等两极性概念,都不可避免地以心物概念为基石、言志、缘情、比兴、意境诸说也程度不同地围绕心物这一中轴旋转。
早期诗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言志说,稍后的缘情说可以看作是言志说的补充。
言志缘情都从诗的内容要素出发揭示其本质职能。
但要说明情志的来由和表达的方式,那么就必然涉及心物两极的汇流和认同。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作了这样的补充解释:
“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
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
发见于言,乃名为诗。
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歌咏。
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
无心无物,自然谈不上言志缘情。
《诗大序》提出了诗歌最基本的三种创作方法——赋比兴。
就创作方法来研究诗的规律,通过赋比兴把诗人心志外化为语言,恰恰是把人心和外物加以连缀,《诗品》解释赋比兴“三义”时说:
“文有尽而志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李仲蒙的解释则更为详细:
“叙物以言志,谓之赋,情尽物也,索物以托志,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总而言之,赋比兴就是把心物化,把物心化,两相交接,合而为诗。
故此,意境说的出现,在心物结构中找到了诗歌审美的内核。
这一点后面还要讨论。
情景说和形神说,可以看作是心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即质涵上的升华,类属上的分衍。
情景说虽然针对描写自然风光的诗歌而言。
但由于诗的形象特征决定其很少不触及风物景象。
因而情景说仍然可以涵盖古典诗歌,特别是格律诗。
《诗薮》认为:
作诗不过情景二端,正是用情景这一具体的二维结构代替了心物这一较宽泛的二维结构。
《四溟诗话》说:
“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情融乎内而深且长,景耀乎外而远且大”。
这种外构的远大之景和内构的深长之情的统一,便是以人心情感再现自然万物的造化之功,以色容物态重展人性的隐秘之情,所谓“景语”与“情语”、“意句”与“境句”、“写景”与“造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区分,都是在处理心物二维结构时重心有所偏移而造成的。
就总体特征看,情景是不可分割的,“关情者景,自大才疏与情相为珀芥也。
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截分两橛,则情不是兴,而景非其景”,“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
“诗人萃天地这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
无景之情只能是空洞抽象的诉情书。
无情之景只能是枯燥乏味的说明书。
都不是血肉俱全、活灵活现的诗。
形神说从另一途径入手补充了情景说,以形取神是中国传统的一条贯穿久远的审美原则。
如果说,情景说是横向的二维结构。
说明了人心情感同外物景象的对应关系的话。
那么,形神说则是纵向的二维结构。
说明了美的形态同美的内涵之间的必然关联。
不论是以形写神,形神兼备,还是取神舍形,其本质精神是相通的,无非是借用特定的外构形象传输内观的美感内涵。
“神”的内涵固然不排斥“情”,但它不仅仅是情化的心理感受,而更多的属于情感淡化了的高层次上的美趣兴味。
情景交融往往来自感性冲动的直接体验,而形神兼备则是在感觉的审美体验基础上经由理性加工提炼而形成的艺术辐射的灵光,明清以降的性灵说偏重情感而与情景说靠近,神韵说偏重理性提炼而与形神说相仿。
它们都触及了心物合孕的园圃,从而各有侧重地触及了诗歌的结构内核。
但由于它们过分地强调了含蓄朦胧和性情灵感,局限了诗的表现广度,容易导致浮泛空虚和轻佻不实的毛病。
至于格调说,肌理说尽管对研究诗歌的特征、形式、方法有着不少补益,但对诗歌的本质特征、内在组合规律缺乏探讨。
故此,它们的流传影响就没有意境说的深远。
物象——诗的元素
人类自身是自然的确良产物。
人作为宇宙因果链条上有机的一环,不可避免地受着自然规律的支配。
人们的精神活动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
“人的感受、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人的意识是一种高级有组织的物质性,人的感觉、知觉、表象、意念、情感、思维等精神活动,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的总和,其本源无疑在于世界物质的客观存在。
主体意识的出现,是有机物质演化的结果,生命有承担者蛋白质是整个自然联系所经给予的一定条件下完成的。
人之所以有理性精神,有生命情感,从生理基础上来说是由于有大脑和以大脑为中心的并包括各种感觉器官的高级神经系统。
情感表现虽然通过主观体验,但情感的渊源在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多维整合。
因此,外物在人的各种认识活动中,始终具有优先的和基础的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看,精神活动的内容,总是反映着物质的形态、结构和运动规律。
“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
理念是客观事物在人脑思维中的抽象,情感是客观生活在主体意识中的孵活。
即使主体世界中作为潜意识复显的梦境,本质上也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再现。
梦不是空洞的心理感受。
它在特定的场景,氛围中展开活动,不管它显现得多么奇特,总是割不断和现实世界的联系。
比如说,纳兰性德的词往往写到梦境:
“风一更,雨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比声”是说风雨交加的夜晚,怀念故园难以成梦:
“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捣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是说过去的记忆萦绕着梦意,醒后使人感到惘然若失;“不知何事萦怀抱,睡也无聊醒也无聊,梦也不曾到谢桥”。
因感念旧事而百无聊赖,怅恨作梦难回故地。
梦境,无疑是心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合影,是在心灵世界中发酵了的现实世界,悬于真空而不涉尘世的思想。
性灵是不存在的。
超越是对现实的否定,不是发现不现实的现实;超验是对经验的怀疑,不是获得非经验的经验。
现实生活始终在人的内在素质中以本来的或扭曲的面目展现,始终塑造着内在素质的形态。
这决定了人情和物性始终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人要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幸福和自由,必然向自身生活的环境——客观世界进军,努力探索其规律和奥秘。
在这一探索中,人之所以能以其它动物没有的加速度向前进展,就在于人的思维和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自然规律。
在于思维规律和存在规律的同一性,在于心物两极内在的同型和对应。
人的美感活动,无不是外界物质在人脑中的激活和感应,无论是雅情,还是俗兴,本质上导源于外物的招示。
诗歌审美活动中,就审美对象对人的心理效应来说,存在着界限不甚明显的三个层面:
①情感化的美;②兴趣化的美;③理念化的美。
古典诗论的延伸,从缘情说到性灵说,侧重强调情感美;从兴味说到神韵说,侧重强调兴趣美;从风雅比兴、美刺箴诲、温柔敦厚的诗歌说,到强调诗歌为政治服务,则侧重理念美,不管侧重于哪个层次的美感,都不是主体“心”密闭而生成的幻影,而是客观现实作用于人的产物,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古人早有真知灼见。
《礼记·乐记》中说: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也,基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里的“乐”,是诗、歌、舞的统一体,可以看作是所有文学艺术的代称。
《乐记》在这里用直观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论述了文学艺术的客观来源。
这个观点,在古典诗论中一直被继承下来,而且不断地有所发展。
《文赋》“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讲时运物移对人心的影响;《诗品》“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讲歌舞活动的起因;《文心雕龙》“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讲心物之间的微妙的对应关系,这些论述,为中国古典文论、诗论奠定了唯物论基础。
物是情的起因,也是情的载体。
诗人要把内心的情志表达出来。
无不走向现实世界的人物氛围。
江淹的《别赋》、《恨赋》,全是写人的内心感受的,但在表述种种离情别绪、愁怀愤懑时,只好从环境物态,人间世道的客观原因落笔。
“因物感兴”和“秉意取象”,从心物璧合的过程看有历时性的差异。
但从心物璧合的结构看却有着共时性的妙用。
作为一个诗人,不仅需要“因物感兴”、“感物而动”的神绘敏觉性,而且更需要“借物寓志”、“以象取意”,捕提神奇微妙的形象系列的感应力。
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散文杰作,就因为它极其成功地攫取了与人情对应的景物。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元穷”。
人生的易逝和世界的永恒使善感的诗人惆怅。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人身的渺小和宇宙的无垠使敏觉的诗人长叹,“自其变者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用诗人的辩证法反观物我,或一瞬即逝,或无尽无休,人生的空寂冷寞,在缥缈的阐意中得到和谐的填补。
正是这种特定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时光,“清风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