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docx
《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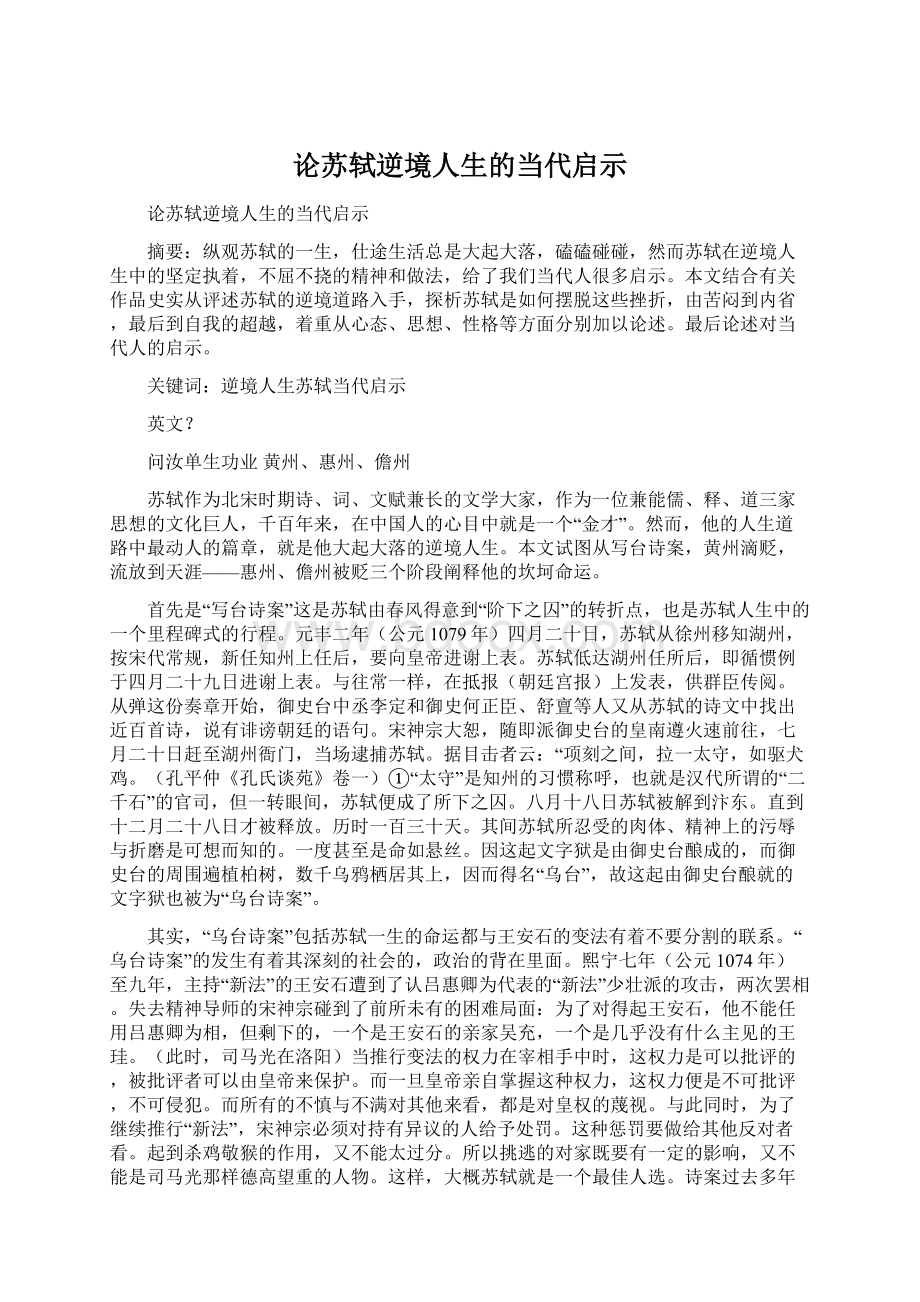
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
论苏轼逆境人生的当代启示
摘要:
纵观苏轼的一生,仕途生活总是大起大落,磕磕碰碰,然而苏轼在逆境人生中的坚定执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做法,给了我们当代人很多启示。
本文结合有关作品史实从评述苏轼的逆境道路入手,探析苏轼是如何摆脱这些挫折,由苦闷到内省,最后到自我的超越,着重从心态、思想、性格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最后论述对当代人的启示。
关键词:
逆境人生苏轼当代启示
英文?
问汝单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诗、词、文赋兼长的文学大家,作为一位兼能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文化巨人,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金才”。
然而,他的人生道路中最动人的篇章,就是他大起大落的逆境人生。
本文试图从写台诗案,黄州滴贬,流放到天涯——惠州、儋州被贬三个阶段阐释他的坎坷命运。
首先是“写台诗案”这是苏轼由春风得意到“阶下之囚”的转折点,也是苏轼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行程。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按宋代常规,新任知州上任后,要向皇帝进谢上表。
苏轼低达湖州任所后,即循惯例于四月二十九日进谢上表。
与往常一样,在抵报(朝廷宫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
从弹这份奏章开始,御史台中丞李定和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又从苏轼的诗文中找出近百首诗,说有诽谤朝廷的语句。
宋神宗大恕,随即派御史台的皇南遵火速前往,七月二十日赶至湖州衙门,当场逮捕苏轼。
据目击者云:
“项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一)①“太守”是知州的习惯称呼,也就是汉代所谓的“二千石”的官司,但一转眼间,苏轼便成了所下之囚。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解到汴东。
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被释放。
历时一百三十天。
其间苏轼所忍受的肉体、精神上的污辱与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一度甚至是命如悬丝。
因这起文字狱是由御史台酿成的,而御史台的周围遍植柏树,数千乌鸦栖居其上,因而得名“乌台”,故这起由御史台酿就的文字狱也被为“乌台诗案”。
其实,“乌台诗案”包括苏轼一生的命运都与王安石的变法有着不要分割的联系。
“乌台诗案”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的,政治的背在里面。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至九年,主持“新法”的王安石遭到了认吕惠卿为代表的“新法”少壮派的攻击,两次罢相。
失去精神导师的宋神宗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为了对得起王安石,他不能任用吕惠卿为相,但剩下的,一个是王安石的亲家吴充,一个是几乎没有什么主见的王珪。
(此时,司马光在洛阳)当推行变法的权力在宰相手中时,这权力是可以批评的,被批评者可以由皇帝来保护。
而一旦皇帝亲自掌握这种权力,这权力便是不可批评,不可侵犯。
而所有的不慎与不满对其他来看,都是对皇权的蔑视。
与此同时,为了继续推行“新法”,宋神宗必须对持有异议的人给予处罚。
这种惩罚要做给其他反对者看。
起到杀鸡敬猴的作用,又不能太过分。
所以挑逃的对家既要有一定的影响,又不能是司马光那样德高望重的人物。
这样,大概苏轼就是一个最佳人选。
诗案过去多年后,苏轼的政敌和朋友刘安世回忆说:
“东坡何罪?
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②这几句简短的话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在亲朋好友、旧党臣僚、湖杭百姓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大力营救下,苏轼最终获释,被贬黄州,朝廷的目的已经达到,苏轼由此也迎来生平第一次贬滴生涯。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
官僚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水部员外郎是水部(工部的第四部)的副长官,但“检校”则表示这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团练副使是唐代的地方军事的理官,宋代只是表示官僚的级别,根本没有这样的职务;比较实在的倒是“本州安置”,规定苏轼要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苏轼一到黄州就写了一首诗,对这个官名开点玩笑。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初到黄州》至五月份),苏轼将共家眷送来,举家迁居到恰奉亭,大有饥寒之忧,只好痛自节俭。
第二年,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清得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躬种,以此来稍济困窘。
这块菜市地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
“东坡”,他也由此自居“东坡居土”。
后来,他在东坡造了几间屋,称为“雪堂”从此以后,黄州就有了一个“东坡居土”,在中国文化史上,东坡居士的出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苏东坡比苏轼家喻户晓,在黄州的时候,有一阵子东坡因眼睛生病,几近失明。
然而苦难再一次的降临到苏轼的身上。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心力劳瘁,黄年早逝,这样太子赵煦继位。
宋哲宗越煦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登基为帝,年方九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主政。
在这段时间,苏轼渡过了他人生之中较为顺畅的短暂时间,然而“新”、“旧”之间的党争以及旧党中认苏轼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间的争吵又让苏轼身心疲惫,如果说熙宁竞争中苏轼是主动积极作战的话,在元佑竞争中他却是被动的。
因此,走出东城去当地方官对他来说,会话得比较轻松,这一方面可以避开竞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地方上自己做为百姓办一点实事。
随着高太后的去世,苏轼的厄运再次光临,哲宗决心继承神宗的政策,继续推行“新法”,历史上称之为“绍述”。
元佑大臣内部的竞争,便他们不能及时改变“旧党”在宫明中混乱局面,也丧失了争取哲宗妇感的机会。
元佑九年四月(公元1094年)哲宗改年号为“绍圣”起用章惇为相,大张旗鼓地开始“绍述”之政。
就在这一年,御史台沿用“乌台诗案”的故伎,纠集苏轼以前起草的文件中有训斥神宗之语,时过境迁,到这个时候来看苏轼的文章,满眼都是颠倒黑白、愚弄君主的话。
苏轼马上落两职(取消殿学士、翰林待渎学士的称号),追一官(罢定州知州位)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责知黄州治所的严惩,随后,以左朝奉郎表知黄州的沼命刚下迅速再降为“充压承议郎(正六品下散官)仍知黄州。
问四月诏书又下,所谓“三改滴命”,但接下为还有更基的,六月份苏轼赴贬所经过当涂(今属安徽省)时,又被贬为建冒军司马(今江西南成)惠州(治所在今广东惠阳东)安置,苏轼只好把家小安顿在宜兴,独与侍妄王朝云,幼子苏过南下,当途经庐陵(今江西吉安)地,又被贬为宁远军(今湖地宁远)节度使副使,仍惠州安置。
这样滴令已五改。
苏轼在惠州的条件委实艰苦,除了朝廷到地方无所不在的压力外,年老多病(此时苏轼已58岁)物质生活的困乏,岭南地区相对落后的瘟疫,差点要了苏轼的老命。
苏轼的第三任夫人王朝云的病逝,又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绍圣四年二月,(公元1097年)朝廷又一次大规模地追贬“元佑党人”,将苏轼责授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一是他将家眷留在惠州,在苏过的陪同下再次走上贬途。
依宋代不杀士大夫的细则,为人臣者得罪至大,亦不过远贬,而到了海南岛,则远无问远,无以复加了,唯有一死了。
在“元佑大臣”中苏轼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
海南的生活条件,当然化惠州还要艰苦,东坡给友人的信中说:
“此间依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复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
”(《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他以儋州后先住在官舍里,但次年无符元年(公元1098年),朝廷派人按照岭外,又将他逐出官舍。
这种情形在苏轼的一首《和陶渊明诗》中有清晰的记述:
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
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
因窘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的一生处于新党与旧党的矛盾夹缝之中。
屡遭贬滴,屡受打击。
杭州、密州、黄州、湖州、常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多年的近乎流放的生涯并没有将他摧垮,他反而在这种滴贬中,实现了人生的自我超越,在人们的心目中,苏轼总是以一个乐观主义者的形象出现的,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忧患来临时,一笑置之。
那么,又是什么精神支柱支撑着苏轼摆脱这些挫折,由苦闷到内省,最后到实现自我超越的呢?
先从心态上来看,因为态度决定一切。
如他在滴贬黄州时期,生活环境非常的艰辛,但苏轼的心态却变得乐观多了,他努力超越困窘的现实,往往在别人不能忍受的艰苦环境中发现快乐。
初到黄州,他就发现了黄州的可取之处:
“长江绕新知鱼美,好行连山觉笋春”(《初到黄州》)在黄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渐渐觉得黄州也没有那么偏僻了:
“某滴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无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首》其三)概括起来讲,苏轼在逆境中的心态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从心理上作好了要做一辈子老百性的准备。
不是安居家乡的百姓,而是以待罪之身随遇而安。
苏轼在自己的一些作品中常自称“幽人”“散人”等,如“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逐良夜”(《定惠院愚居月夜偶出》)“散人出入元町哇,朝游湖北淮西。
”《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从人称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逐渐变得平和,不再那么锋芒毕露。
其二,追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精神境界,在他与其弟苏辙(守于由)的信中说: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内心,无别胜解。
”(《与子由弟十首》之三)在现实生活中的他遭受排挤,是不自由的,然而他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他对自由的向往。
在他的一首词《临江仙》中这样写道: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间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在作品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逍遥自在的境界,可以随心所欲。
其三,知运常乐,追求平实的幸福。
经历了宦海风波的浮浮沉沉,苏轼内心更愿意去追求平淡朴实的生活。
在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进有)的末尾,作者喊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呼吁,向世间所有离别的人,包括自己的弟弟子由,发出了诚挚的慰问和美好的祝愿,他在《惠州一绝》中这样写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庐桔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万辞长作岭南人。
世态资源,人情淡薄,这岭南的黎族人民仍旧是热情好客,今苏轼感到莫大的慰藉。
再从思想上来看,苏轼是杂柔了儒、释、道三家的大家。
他从三家的学说中汲取了其中积极的因素。
四川大学张志烈先生在他的《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一文中总结了近20多年中,学术界大略的三种风解:
共一前期以儒为主,后期以释老为主,其二认为是儒释道相混合的思想;其三是认为以儒家思想积极面为立,佛老思想是对持政治迫害和困苦遭遇的精神武器。
③本人在这里,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
苏轼毕竟是一个读书人,虽然他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一直是其基础和主导。
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古误码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使他把自我人格的完善和社会责任感紧密联系在一起。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惠州。
此时苏轼已59岁,垂暮之年,被贬南荒,可渭九死一生,但在绝望中,他对惠州之地,立生了感情,和惠州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史》本传载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芥带,人无贤愚,皆得欢心。
虽然自己有职无权,但他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为惠州人民作了大量的义举善事。
一次苏轼赔程正辅(苏轼的表兄,时任广南东路提刑)游玩博罗香积寺,看到寺后的溪流,苏轼想到惠州人民的生产工具极其落后,便向程正辅提出建造水碓水磨的建议,并嘱县令大力推广。
他还通过博罗等县令推广新式家具“秧马”让农民坐着插秧,省时省力,效果也很好。
“今惠州民皆施用,甚便之”。
(《题秧马歌后》)苏轼目睹岭南缺医少药,百姓又无钱医治,很多人因而病死,苏轼便积极施医散药,救死扶伤。
如用姜、葱、豉制成汤,煮浓热呷,防治流利疾病,效果果然很好。
这些正是儒家主导思想——仁爱的具体体现。
佛老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固然有消极地因素,使他深刻地感受到命运无常,世事虚幻,人生如梦等,但也有着积极的一面。
在逆境中,他用佛教万物皆幻的观点和老庄万物齐一的观点来消释现实带给他的痛苦。
正因为他深信“万物从来风过耳”。
(《无愁可解》)故能超然物外,对待人生的浮浮沉立,起起落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苏轼也曾有过彷徨与苦闷,但很快便在佛老思想中找到了排解的办法。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冬至后,他斋居天庆观四十九日,静观默照,荡涤心理的尘埃。
“冬至后,斋居四十九日,亦无所运行,聊自反照而已。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二)他在一次去沙湖途中遇雨,他写下了千古名篇《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呤啸且徐行。
行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蓑烟雨的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泠,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睛。
小序中写到“同行皆狼狈,余不觉。
”解明地体现出他任天而动,随缘放旷的独特气质。
他对学佛求道的态度是理性而实用的,他在《答毕仲举二首》其一阐述了他学佛的这种态度:
佛书旧亦乍,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
………仆尝语述古,公之所淡,劈之饮食龙肉,而仆之所学。
猪肉也,猪之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
苏轼并不相信对佛学超风出圣的高淡阔论,更不愿真正遁入空门,黄卷孤灯伴佛眠。
龙肉固然是凡夫俗子心向往之的。
但毕竟是虚幻的,远不如猪肉味美而又触手可及。
无伭是佛学禅理,还是老庄哲学,对苏轼而言,反是提高人生境界的工具。
苏轼在坎坷多艰的逆境人生中并没有消沉下去,与他的性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有人说苏轼的性格是爽放旷达,其实,苏轼性格的内核是“真率”。
对于这一点,王水照先生这样说:
“保持一已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自然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其实早在少年时代,父亲苏洵就注意了苏轼弟兄不同的性格,在《名二子》一文中,苏洵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
轮、辐、盖、轸、皆有职于车。
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
轼乎,吾惧汝汝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辙乎,吾知免也矣!
”曾枣庄先生对这段话有过精彩的点评:
“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汝不外饰也”。
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显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性命不保;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乎祸福之间。
苏轼性格冲和淡迫,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竞争中,虽也遭受滴贬,但终能免祸,悠闲地渡过了晚年。
⑥一开始,王安石变法时,苏轼觉得新法过于激烈,为害百性,反对变法,因此遭到新党排挤,只好外放杭州通判,但他在任地方官期间,看到新法的某些利民之处,于是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旧党上台后,苏轼批评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因而又遭到旧党的围攻、排挤。
但无论承受多大的打击,苏轼都能够坚持自己“真率”的性格。
在蜀洛竞争中,苏轼继承苏洵的观点,肯定人欲的存在,反对把“情”和“性”分解开来,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讲求的是“存天理,更人欲”的宋代理学。
苏轼对程颐的虚伪、死板、固执十分地反感,并常常讥讽程颐,得程门弟子。
这也是他日后不断受到程门弟子排挤,弹刻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昏因性格而起。
苏轼更是一个出色的幽默大师,他的出默与他的个性经历,生活情取,学识修养,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源湝出默也是他低御人生逆境的强有力的武器,在乌台诗案中,东坡一家都被追捕的浩大声势吓倒了,都相拥而泣,不知东坡随着官差一去,生死如何。
东坡见此情状,便对他的第二任夫人王润之等人讲了个故事:
从前,在宋真宗的时候,宋真宗皇帝想要便访天下的隐土,有人推荐了杨朴。
于是真守就让人把杨仆找了来,见了面。
真过问杨仆:
“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送你诗呢?
”杨仆回答:
“只有臣的妻子作了一首诗:
且休落拓贪洒杯,更莫猖狂吟诗,今日捉恃宫里去,这回断了老头皮,真宗听了,大笑不止,就放他回家归隐了,故事说完了,那你能不能像杨仆的妻子那样,作一首诗送我吗?
王代听了东坡的话,本来哭得很伤心,却反被逗笑了。
东坡和弟弟子由,学生秦观在一起,也多以玩笑取乐。
苏轼《戏子由》中这样写的: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读经史,忽然欠身屋打头。
“宛丘先生”指的是子由,“长如丘”之丘,指的是孔丘,人言九丘身长九尺六寸。
秦观见苏轼多髯,洞笑曰:
“君子多乎哉!
”苏轼快活道:
“小人樊须也。
⑦众人皆大笑。
苏轼的这种幽默目的在于排患人生道路上的挫诉、失败,忧愁和痛苦,更多的带有自我解嘲的意味。
三此心安处是各乡
苏轼在他的《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郞》一文中“此心安处是吾乡”一句可以说是苏轼一生处世态度的概括。
下半阙是: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只要心中安然,就会笑口常开,就会无往而不乐,无处不吾乡。
苏轼在逆境中的奋斗精神给了我们心灵的巨大震撼,我们可以从他直面逆境人生的种种方法以及态度中,得到很多关于人生,交往的启示。
首先,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挫折的准备。
这种准备更是要包括身体上的和心灵上的。
苏轼从少年时就深受正统思想的熏陶,熟读经史,纵论西今,“奋历有当世志”。
⑧也曾少年得志,名动京师。
也曾踌躇满志,满求建功立业。
然而苏轼从政之后,仕途一直很不幸,先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通判杭州,以后又转知密、徐、湖三州。
元丰二年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旧党”上台,他又被召回京城,但又与司马光政见不合,被迫出任杭州。
无佑六年又调回京都,可立即又受到政敌的打击、排挢,被迫离京,转到颖州,又移杨州。
元佑七年九月又被召回京,因形势的变化,他又清调定州,接着“新党”再度上台,他被责贬惠州、琼州。
纵观苏轼的一生,都处于新党与旧党的夹缝之中,屡遭贬谪,九死一生。
然而,政治上的一连串打击并没有消磨掉苏轼的斗志,反而便他实现了人生的超越。
虽然多灾多难,而他不屈不挠,虽然饱经沧桑而他又谈笑自如,困难与挫折把他磨炼得更加坚韧,更加顽强,更加毅然。
形成苏轼独特气质个性——“东坡精神”不因个人的人生挫折而失去对人生目标的不懈追求,执着生活,处穷排难,随缘自适,超然旷达。
⑨
在乌今物质为上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替负着社会、家庭的责任,激烈的竞争法则让我们甚至有时喘不过气来。
虽然我们不可能像宋代的苏轼所遭受的那样坎坷的命运,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一些我们不愿意去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当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学习苏轼的这种奋斗的精神,勇敢地去面对现实,积极地克服人生路上的种种艰难,不退缩、不逃避。
同时,在与困难作斗争的过程中享受胜利的喜悦,使自己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强者。
其次,在逆境人生中,我们更应该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维护自己的人生尊严。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是中国文人一直追求的人格理想,也许在思想上确立这一目标并不难,但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它却不容易。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仕途名利没有把他同化为虚伪、阴险弃权的俗史政客,而是表现出少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长期的流放生涯也没有使他“万物其不关心”,只求一已之安的闲人隐土,而他更是以“出世态度入世业”⑩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朝堂之上,忠正谋国,尽“尊主”之责;“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外放地方,关心民瘼,济危解困,履行的是“泽民”之任。
(11)熙宁年间,在京直史馆任职时,因不同意王安石急功近利的变法而据理力争,抚言直谏,令“介甫(王安石)不悦”,因此获罪新党,长期不被重用,元佑年间,高太后主政,司马光为相,又是由于和司马光尽废新法的想法不一致而被旧党所疏远。
难道是苏轼不懂得官场上的规矩吗?
很显然,不是的,而是因为苏轼要给君主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况,为百姓谋求更多的福祉。
对我们自身而言,人生所面对的众多挫折和困境,大多不是本人所能够决定或改变的,但无论何时何时,我们都应该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生活,判断是非,黑白、曲直,且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更不能在利益,金钱等面前,丧失自己的人格。
现在的很多官员纷纷落马,不是因为没有坚守自己的人格而堕入罪恶之渊的吗?
最后,我们从人际关系方面来看,如何创造一个和谐、有效地人际关系,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沉思的一个话题。
可以说,苏轼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十分和谐。
这也就不得不说到王安石和苏轼的关系。
执着而又坦率的苏轼,作诗论事,猛烈地掸去新法和讽刺王安石,而遭到贬滴和坐牢。
二人政见不一,一开始是相互责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情的变迁,两人心地逐渐而充分的袒露,促使双方指弃前嫌。
苏洵曾写《新奸沦》对王安石进行了深刻的人身攻击,王安石未必会遗忘苏轼乃苏洵之子,但他胸襟开阔没有在他当权的时候泄私愤而压抑人才。
只此一端,也是以证明王安石为人正直和气量之大。
“乌台诗案”发生后,当时已罢相赋闲在金陵的王安石对人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
也可见,王安石是一个识人才,爱人才的人。
新派中的“内江”是苏轼对王安石看法转变的转机。
新法派中的吕惠卿,曾布之流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大肆搜寡民脂民膏,搞出好多有背王安石变法意愿的举措,招致朝野的非议,而他们却把这此诬陷推给了王安石,此如吕惠卿就卑鄙地公布王安石早时写给他的私人信函,捕风捉影地制造舆论,动摇王安石的地位和影响,离间王安石和皇帝的关系,最终导致王安石再次罢相,这倒引起了苏轼的同情。
通过对王安石冷静、客观地分析,苏轼逐渐发现王安石从来不纵欲,从来不贪污,是个真心实意地为富国强兵而奋斗的政治家。
这里,我们暂且不谈王安石变法的利弊,这是经济学家的事。
包括司马光在内,大凡是有良心的政治家总是以民生为本,从来不是中饱私囊,都是为明为民着想,两人的思想在一点点地靠近。
后来,苏轼写了一首诗《次荆公韵四绝》其一: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王安石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开始退隐,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刚好十年,王安石也曾劝苏轼买田隐居的话,一对宿放,终成朋友。
这也使我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有了新的收获,那就是要以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人接物,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对人一棍子打死。
我们应该以宽容的心去包容他人的错误,给别人一个机会,更是给自己一条道路,这也正所谓:
职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金无足迹,人无完人。
当然在苏轼的身上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到某些教训,引以为戒。
诸如,苏轼在挫折面前,有时候表现得非常消极“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华阴寄子由》)他在黄州时还修仙访道,妄求长生不老。
在他的《石芝》一诗中:
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他有时梦中食石芝。
这些有时也误导了对苏轼盲目崇拜的人。
这些都算是他带给我们的消极因素吧。
结语:
苏轼是人,不是神。
他自然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正是以平常人的心去对待不平常的逆境人生,才构成了“东坡意义”。
(12)的美学范畴和文化范畴,吸引着更多的人去研究他,赏析品评他。
苏轼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已有九百多年了,但他留给他们了丰富的人生之书,值得我们耐心地阅读。
他的逆境人生之路,更是对当今的“小皇帝”“小太阳”们进行挫折教育的生动教材呢。
注释:
①②王永照朱刚撰《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50页
③张志烈着《诗性智慧的和弦——儒释道与苏轼的艺术人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5月第26卷第3期第96矾。
④唐玲玲着《东坡乐府研究》马蜀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第15页。
⑤王水照着《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54页。
⑥曾枣庄着《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13页。
⑦彭宗林着《苏东坡与三苏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72页。
⑧苏辙《东坡先生基志铭》、《东坡乐付编年征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页。
⑨李显根着《沦苏轼诗文中的“东坡精神”》《求索》2003年第4期第232页。
⑩马银华着《达则策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沦苏轼的自由人格》聊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页。
(11)张尹炫(韩国)着《出世态度入也业一对苏轼人生态度的一点思考》齐鲁学剂2006年第3期部属经156期第41页。
(12)李泽厚着《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8月第2版第159页。
参考文献
(1)《苏轼全集》傅成穆俦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苏东坡传》林语堂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3)《中国文学史》游国思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7月北京第2版。
(4)《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