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学.docx
《谱牒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谱牒学.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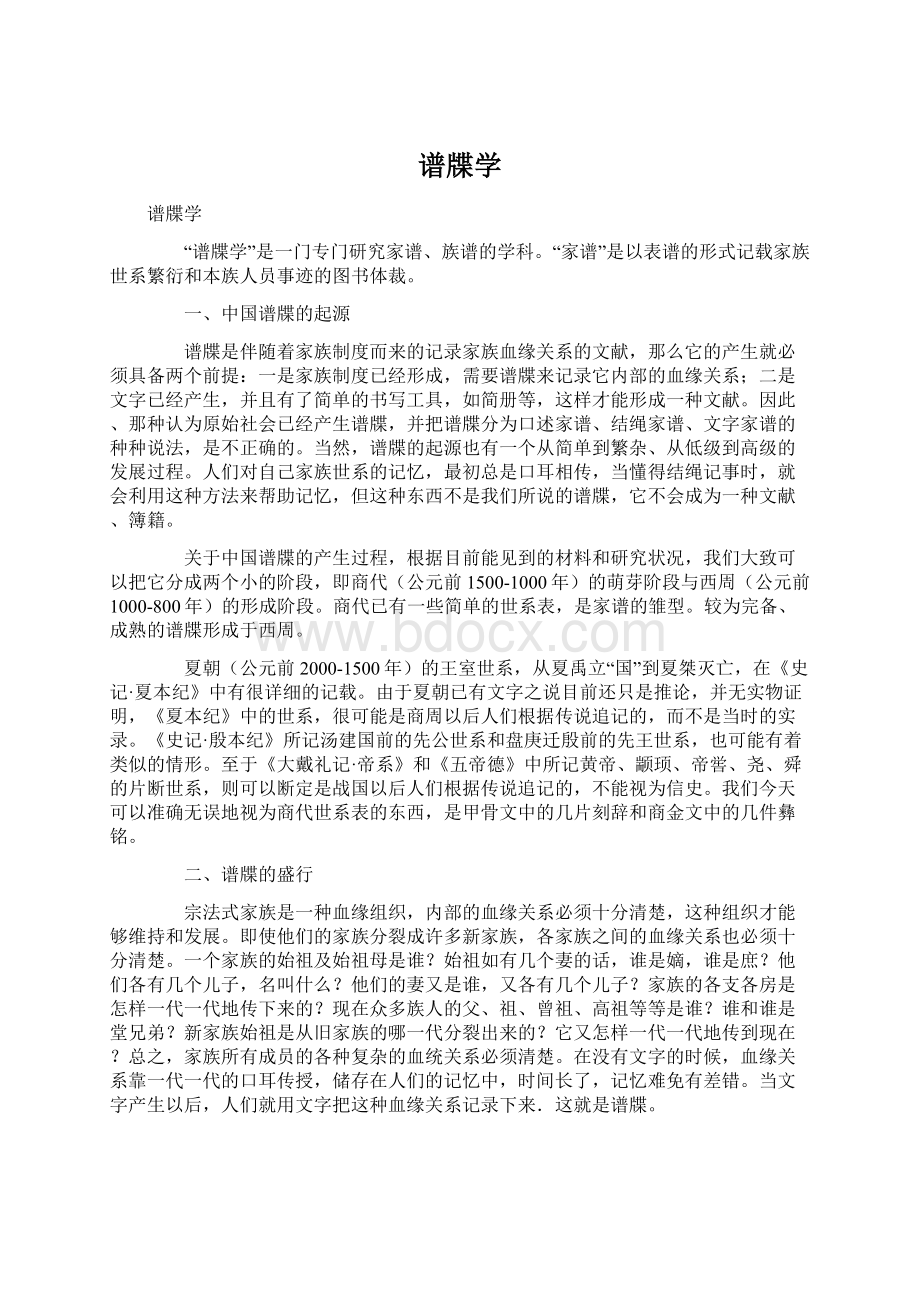
谱牒学
谱牒学
“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
“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
一、中国谱牒的起源
谱牒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那么它的产生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谱牒来记录它内部的血缘关系;二是文字已经产生,并且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如简册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文献。
因此、那种认为原始社会已经产生谱牒,并把谱牒分为口述家谱、结绳家谱、文字家谱的种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当然,谱牒的起源也有一个从简单到繁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人们对自己家族世系的记忆,最初总是口耳相传,当懂得结绳记事时,就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记忆,但这种东西不是我们所说的谱牒,它不会成为一种文献、簿籍。
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
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
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
夏朝(公元前2000-1500年)的王室世系,从夏禹立“国”到夏桀灭亡,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很详细的记载。
由于夏朝已有文字之说目前还只是推论,并无实物证明,《夏本纪》中的世系,很可能是商周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而不是当时的实录。
《史记·殷本纪》所记汤建国前的先公世系和盘庚迁殷前的先王世系,也可能有着类似的情形。
至于《大戴礼记·帝系》和《五帝德》中所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片断世系,则可以断定是战国以后人们根据传说追记的,不能视为信史。
我们今天可以准确无误地视为商代世系表的东西,是甲骨文中的几片刻辞和商金文中的几件彝铭。
二、谱牒的盛行
宗法式家族是一种血缘组织,内部的血缘关系必须十分清楚,这种组织才能够维持和发展。
即使他们的家族分裂成许多新家族,各家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必须十分清楚。
一个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谁?
始祖如有几个妻的话,谁是嫡,谁是庶?
他们各有几个儿子,名叫什么?
他们的妻又是谁,又各有几个儿子?
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样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的?
现在众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等是谁?
谁和谁是堂兄弟?
新家族始祖是从旧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来的?
它又怎样一代一代地传到现在?
总之,家族所有成员的各种复杂的血统关系必须清楚。
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血缘关系靠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时间长了,记忆难免有差错。
当文字产生以后,人们就用文字把这种血缘关系记录下来.这就是谱牒。
商以前还没有较为完整的谱牒,连司马迁也没有见到过。
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
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不能登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三、周代(公元前1000-公元前200年)谱牒的内容和形式
周代谱牒现在虽然亡佚干净了,但汉朝人看见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作过一些描述,战国以后成书的《周礼》、《礼记》对它有片断的论述:
关于谱牒的内容,要记录族众的忌、讳。
讳是名字,忌是哪一天死的。
族众生子,要记某年、某月、某日生,自然还要记是谁之子。
族人有谥者要记其谥。
有谥的族众,当然只能是诸侯、卿大夫了。
关于谱牒的形式,从桓谭说的“旁行邪上”一句话来推测,应是一种表格,父辈名讳居一格,子辈名讳居一格,子子孙孙按辈份各居一格,叫做“旁行”。
父统诸子,子系于父,谁是谁之子,谁是谁之父,一目了然,叫做“邪上”。
在各人的名讳下注明生卒年月日及配偶、谥号等等。
这样,就把一个家族从始祖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记载得清清楚楚了。
四、魏晋至唐代(公元200-900年)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
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
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
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
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
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谁出身太原王氏?
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
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谁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
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1、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
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
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
如:
《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
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
《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
《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
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
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
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
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2、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
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
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
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
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
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
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
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
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
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
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
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
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
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
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
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
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
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
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
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3、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
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
怎么查呢?
查谱牒(又叫簿状)。
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
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
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
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谱牒,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好作罢(《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
又如陈朝时,陆琼作吏部尚书,人们认为很称职,就因为他“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
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
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
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士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
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4、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和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
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
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
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
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
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
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
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
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
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
事未成而被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
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有的。
五、唐代(公元600-900年)谱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
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
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
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
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
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贞观初年。
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
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
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
第二次是高宗时。
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
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
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
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
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
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
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
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
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
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
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
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
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
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
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
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
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
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
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
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
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
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
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
《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
多贺秋五郞:
《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
)。
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
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
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
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
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
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
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
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
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
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
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
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唐末(公元900年)谱牒的衰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1、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
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
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
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
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
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
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
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
“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
”崇韬回答说:
“经乱失谱牒。
曾听先父说:
去汾阳王已经四代。
”(《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
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
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
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
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
《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
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
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
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
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
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
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
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
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
(张载:
《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
《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
七、宋明(公元1100-1600年)以来,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