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暴力美学本质.docx
《议暴力美学本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议暴力美学本质.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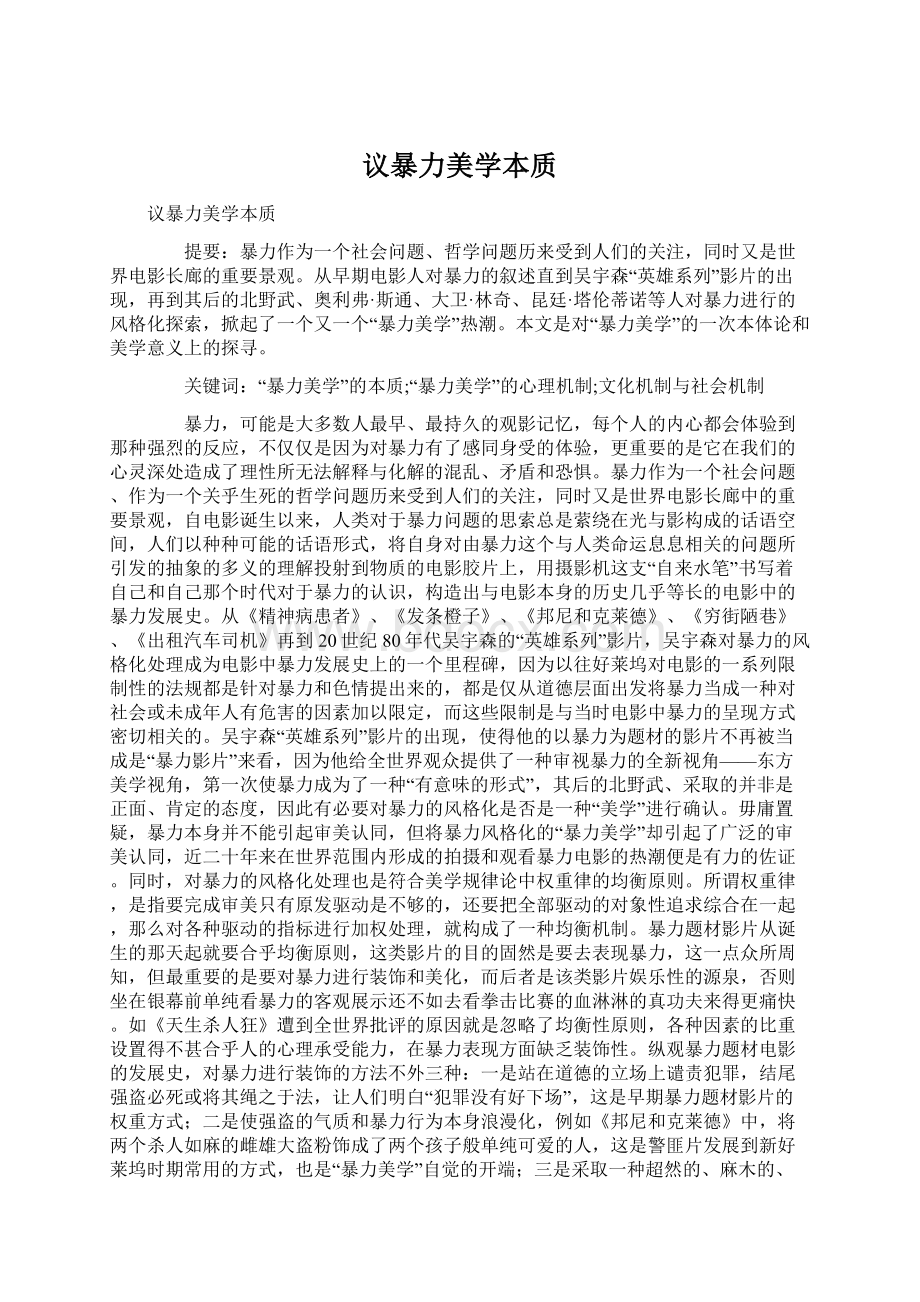
议暴力美学本质
议暴力美学本质
提要:
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的重要景观。
从早期电影人对暴力的叙述直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再到其后的北野武、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廷·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进行的风格化探索,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暴力美学”热潮。
本文是对“暴力美学”的一次本体论和美学意义上的探寻。
关键词:
“暴力美学”的本质;“暴力美学”的心理机制;文化机制与社会机制
暴力,可能是大多数人最早、最持久的观影记忆,每个人的内心都会体验到那种强烈的反应,不仅仅是因为对暴力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造成了理性所无法解释与化解的混乱、矛盾和恐惧。
暴力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作为一个关乎生死的哲学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又是世界电影长廊中的重要景观,自电影诞生以来,人类对于暴力问题的思索总是萦绕在光与影构成的话语空间,人们以种种可能的话语形式,将自身对由暴力这个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问题所引发的抽象的多义的理解投射到物质的电影胶片上,用摄影机这支“自来水笔”书写着自己和自己那个时代对于暴力的认识,构造出与电影本身的历史几乎等长的电影中的暴力发展史。
从《精神病患者》、《发条橙子》、《邦尼和克莱德》、《穷街陋巷》、《出租汽车司机》再到20世纪80年代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吴宇森对暴力的风格化处理成为电影中暴力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以往好莱坞对电影的一系列限制性的法规都是针对暴力和色情提出来的,都是仅从道德层面出发将暴力当成一种对社会或未成年人有危害的因素加以限定,而这些限制是与当时电影中暴力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的。
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使得他的以暴力为题材的影片不再被当成是“暴力影片”来看,因为他给全世界观众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的全新视角——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后的北野武、采取的并非是正面、肯定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对暴力的风格化是否是一种“美学”进行确认。
毋庸置疑,暴力本身并不能引起审美认同,但将暴力风格化的“暴力美学”却引起了广泛的审美认同,近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拍摄和观看暴力电影的热潮便是有力的佐证。
同时,对暴力的风格化处理也是符合美学规律论中权重律的均衡原则。
所谓权重律,是指要完成审美只有原发驱动是不够的,还要把全部驱动的对象性追求综合在一起,那么对各种驱动的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就构成了一种均衡机制。
暴力题材影片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要合乎均衡原则,这类影片的目的固然是要去表现暴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最重要的是要对暴力进行装饰和美化,而后者是该类影片娱乐性的源泉,否则坐在银幕前单纯看暴力的客观展示还不如去看拳击比赛的血淋淋的真功夫来得更痛快。
如《天生杀人狂》遭到全世界批评的原因就是忽略了均衡性原则,各种因素的比重设置得不甚合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暴力表现方面缺乏装饰性。
纵观暴力题材电影的发展史,对暴力进行装饰的方法不外三种:
一是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谴责犯罪,结尾强盗必死或将其绳之于法,让人们明白“犯罪没有好下场”,这是早期暴力题材影片的权重方式;二是使强盗的气质和暴力行为本身浪漫化,例如《邦尼和克莱德》中,将两个杀人如麻的雌雄大盗粉饰成了两个孩子般单纯可爱的人,这是警匪片发展到新好莱坞时期常用的方式,也是“暴力美学”自觉的开端;三是采取一种超然的、麻木的、带有科学眼光的叙事方法或纪录性风格,导演仿佛是一个社会学家,在光影的实验室里拿着放大镜、显微镜研究暴力现象,如《好家伙》中马丁·斯科西斯用优美的音乐、定格、旁白等多种手段将暴力审美化,用学者的眼光看待罪犯的成长,《出租汽车司机》中对血腥场面的冷静直观,都可以归结为“暴力美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后来的昆廷·塔伦蒂诺也积极实践着这一方式,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态度将暴力以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展示在人们面前。
所以,本文姑且将因对暴力的道德判断而否认暴力风格化是一种美学样式的质疑抛到一边,因为所谓“暴力美学”本身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削弱了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是应该重点从电影美学的角度看:
这种风格化在电影史和当今世界影坛上已成为了一种较为成熟和普遍的具有电影美学意义的风格形态和创作潮流,让大家都能认识到原来暴力也可以被美化、风格化,暴力成为一种“美学”已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电影理论界对于“暴力美学”的命名也更多地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而非伦理道德的角度,这也是本文立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廷·塔伦蒂诺等人对暴力进行的风格化探索在世界影坛上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暴力美学”热潮。
冷战结束以来,恐怖和暴力问题没有一天不在困扰人类,暴力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每个人都应对暴力及由暴力问题衍生出来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本文试图以发展的电影史学眼光,不割电影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探寻“暴力美学”在主题形态、风格外观和深层意识形态意味、文化内涵等方面的特质,力图总结出电影中的暴力从客观展现到高度风格化的变化与大众观影的心理机制、文化观念、社会道德观念等方面变化的映照和互动关系,从而得出暴力只有到了后现代、后工业社会才成为一种美学观的源泉的结论。
一、电影中的暴力和“暴力美学”“暴力是为了个人利益的满足,旨在伤害受害者并不顾社会的制裁而采取的有意的、反社会的、使人遭受痛苦的行为。
”为叙述方便,本文所涉及的电影中的“暴力”概念,大多数只限定在既不包括战争这样一种集体式大规模的暴力,也不包括刀枪剑戟型的传统武侠片、李小龙或成龙式拳脚功夫片,而是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中小团伙之间、警匪之间枪械式的血腥斗争。
之所以将研究重点放在现代警匪片、枪战片而不涉及传统武侠片和拳脚功夫片,并不在于它们使用器械的不同,而是在于它们在真实性问题上的差异,即充满理想色彩和虚构成分的传统武侠片和拳脚功夫片对暴力的展现较之现代警匪片、枪战片,似乎更缺乏一种社会真实性。
“暴力美学”则专指肇始于希区柯克惊悚片中仪式化暴力场面和新好莱坞影片中暴力风格化的从萌芽到自觉,再到吴宇森“英雄系列”影片将暴力场面的形式美感和风格化程度发展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削弱社会道德教化功能和意识形态功利色彩的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美学形态。
在这里,“暴力美学”不仅仅是指将暴力进行“美化”,一切将暴力风格化的处理都可称为“暴力美学”。
本文对“暴力美学”的研究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分析“暴力美学”的风格外观,二是挖掘其中具有悲剧美感的精神内涵。
“暴力美学”一词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当时是在什么意义上界定的?
这个问题今天已很难确切地考证,但在80年代吴宇森的“英雄系列”影片诞生后,“暴力美学”这个名词便在报章杂志上大量涌现出来,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虽然这个名词在一定程度上为暴力题材的电影正了名,但是暴力的风格化能否称作一种“美学”,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
众所周知,“美学”这一术语本身包含着对某一艺术现象正面的、肯定的态度,而电影中对暴力的表达在大多数情况下[美]阿·沃泽尔、盖·洛梅蒂《电视暴力研究》,胡正荣译,《世界电影》1992年第4期,第153页。
参见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5页。
二、电影中暴
力叙述和“暴力美学”形成的心理机制、文化机制与社会机制任何文化现象的研究都不能离开特定的语境,对“暴力美学”的研究也应如此。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人对于暴力的叙述是截然不同的,暴力题材电影也并非是讲述一个血淋淋的故事那样简单,而是有其特定的心理机制、文化机制和社会机制。
1.心理机制
提到暴力电影产生的心理机制,我们不能不提到几乎与电影同龄并影响了西方一个多世纪的精神分析学。
这里,我们首先从精神分析学探讨一下艺术作品中的暴力叙述。
精神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认为,人是最易受攻击的脆弱的主体,他把人的心理世界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本我是人的最原始的本能冲动,其中就包括暴力攻击的本能,它服从于“快乐原则”,是人的各种行为的最后根源和决定因素。
超我是道德化、理想化了的自我,它以社会习俗和道德原则为标准,将本我中不合理想的行为压制在无意识领域。
自我居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代表着人的常识和理性,起调节作用。
一方面通过知觉和思维来使本我的部分愿望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保护机制,就像一个恪尽职责的守门人,将本能冲动斥回到无意识之中,以避免与社会道德公开冲突。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文艺创作起源于本我原始欲望宣泄的需求,而人类的原始欲望包括两类基本的本能:
性本能和死本能,两者既相互对应,又相辅相成。
生命本能包括饥渴、性欲等等本能,事关人的自我保存及种族繁衍;死亡本能的作用正好相反,是使有机物退回到无机物的状态。
弗洛伊德将死本能称为“攻击性的本能”,死本能隐伏在无意识之中,使人把自己变成对死亡的旁观者甚至参与者,弗洛伊德说“:
假如远在往古,生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起源于无机物,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那时已有一种本能要以毁灭生命而重返于无机状态为目的。
又假定我们所称的自我破坏的冲动源于这种本能,那么这个冲动便可视作任何生命历程所不能缺少的一种死亡本能的表现。
”死亡本能决定了任何一个个体生命最终将归复到无机物质的恒态,但它又不是表现为一种求死的欲望,而是派生为种种破坏力和攻击力,于是现实生活中人类就出现了内在的暴力本能,出现了向外攻击的倾向,而暴力攻击无疑是这种本能所能找到的最直接的实现形式,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就是层出不穷的暴力、凶杀和自虐等场面,均可视为死亡本能的直接外化。
由于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的限制,人们潜意识里的攻击欲望只能在指定的狭小区域内予以释放,例如拳击运动。
而电影这一“造梦工厂”,由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任意地表现暴力而又不必像拳击运动那样面对真正的血腥,同时又比暴力题材的小说更直观、更形象,因此成了人们发泄攻击能量的最好选择。
同时,死本能与生本能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电影中对暴力和死亡的描写其实蕴含着强烈的人类求生的本能,电影人通过拍电影释放死亡焦虑,而观众则通过看电影释放这种焦虑,这是电影中的暴力和“暴力美学”形成的最根本的心理机制。
一般说来,人们对暴力和死亡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恐惧,这是最本能的被动的层面;一是以暴制暴,这是比较主动的反应。
暴力题材影片也始终逃不脱对这两种反应的表现。
其次,荣格的心理原型理论认为,每个人的人格中都包含具有重要意义的四种原型:
人格面具、女性潜倾、男性潜倾、阴影原型。
其中阴影原型可能是其中最强大最危险的一个,是人格中的卑劣部分。
荣格认为,阴影是个性的有机部分,它的存在不会因为人们对它有所争议而消失,它的危害也不会因为把它理性化就可以消除掉。
尽管如此,阴影的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又可以是消极的。
阴影的消极性源于几个方面。
首先,是阴影的动物性特征,“阴影即那个隐藏着的、受压抑的部分,因为正是那最大部分的卑劣与负罪人格中的最大分支可以追溯到我们动物祖先的王国中去”。
按照他的看法,阴影中所包含的人的基本动物性比任何其他原型都要多,因此,它可能是一切原型中能量最大、最有潜在危险的原型。
其次,阴影的消极性是它的受压抑性。
由于阴影中有很大的卑劣成分,而且这些成分一直受到自己与社会的压抑,这反而使阴影所包含的能量和潜在的危险更大。
当压抑变得过于严厉,或者疏导的途径不适当时,阴影就很可能以灾难的形式爆发出来。
再次,阴影本身也有一种人格化的要求。
荣格认为:
“阴影将一切个人不愿意承认的东西加以人格化,但也往往将它自己直接或间接地强加在个人身上”,这样一来,阴影不仅会损害人格化过程本身,而且必然还会影响人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
于是,为了让阴影在人格化过程中,也就是从无意识进入意识的过程中,把卑劣的成分转化为好的品质,为了使一个人成为集体中奉公守法的成员,就有必要驯服容纳他的阴影原型中的动物性本能,方法之一就是发展一种强有力的人格面具,既抑制阴影中种种卑劣成分的显现,又释放了阴影的巨大能量。
然而阴影是十分顽强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屈服于压抑的。
处于阴影中的恶的因素和暴力倾向并不能从一个人的意识中彻底消除,而是撤退到了无意识之中,一旦突然面临人生困境、发生精神危机,阴影就会利用这一机会对自我或他人实施其威力。
当阴影原型受到社会的严厉压制,或者,社会不能为它参见狄其骢主编《文艺学新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56页。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参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提供适当的宣泄途径时,灾难往往接踵而至。
这一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暴力行为和百年电影史中热衷于表现暴力的深层心理原因。
人们经常说,许多暴力电影使得犯罪率大大上升,也有许多暴力犯罪分子坦言他们是看了某部影片而去模仿的,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我们不否认影视作品中过分的、超越道德伦理界限的暴力可能会导致现实中的犯罪,但我们也不要否认,经过风格化处理的暴力在成为一种“美学”风格样式之后给观众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的感觉,似乎能够减轻其内心深处由阴影原型所激发出来的暴力嗜血的冲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体验,有时心里窝火恨不得把惹自己发怒的对象痛打一顿,但当有的人看了电视上的一场拳击比赛或一场暴力题材的影片后,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关上电视或走出电影院的瞬间,一切烦恼、怨愤都消失了,一场暴力事件的萌芽就这样被扼杀在了大脑这个“摇篮”里,这难道不是一个成功地抑制了“阴影原型”肆虐的范例吗?
那么,同样是暴力题材的影片,为什么有的会引起犯罪,有的会制止犯罪呢?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关于电影中暴力表现的“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与人们的接受心理密切相关的。
众所周知,暴力是人类恶性最普通和常见的形式,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内心深处确实有一种对暴力的迷恋,人们似乎喜欢看到别人受到伤害而自己安然无恙的场面,欣赏人类受难时的“壮美”场面的兴趣超出了犯罪和暴力本身的吸引力。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机会,人们就会驻足观看一个受难的人或是其他灾祸,这也是灾难片的心理源头;同时,观看艺术作品中坏人受到暴力惩罚的场面会使人获得一种道义上的满足感,例如中世纪教会处死“异己”的仪式常常要与重要的庆典同时举行,观看者道德上的满足感决不亚于参加庆典的快感。
但人们对于暴力的接受也有一个限度,即太少了不满足,太多了又过于残酷、血腥,过犹不及。
而“暴力美学”是对暴力进行“包装”“、修饰”后的产物,牢牢地把握住了暴力表现的“度”的问题,“增一分则太多,减一分则太少”,即使昆廷·塔兰蒂诺的暴力表现得很直接、很残酷,看似没有“包装”,但背景音乐的加入和总体情境的荒谬,使得人们观看起来也觉得心安理得,甚至感到兴味盎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暴力美学”是在“戴着脚镣”潇洒地舞蹈。
当然,就像荣格的人格面具有时也不能抑制阴影原型的肆虐一样,“暴力美学”也不是万能的,它可能会抑制犯罪倾向,使胸中的狂野得到暂时的宣泄和替代性满足,但也可能会成为罪犯或有犯罪倾向的人模仿、迷恋的对象,这个问题属于社会学和伦理学研究的范畴,这里不做过多探讨。
第三,暴力长期以来作为一种道德禁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增添了许多神秘感。
一种东西之所以遭到禁忌,本身就说明这种东西应该是人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东西,否则就没必要将其设为禁忌,因为伦理、道德从来不会去禁忌、限制对公众有益的活动和为公众牺牲的行为。
往往礼教越禁止的东西,就越能激发人们对它的兴趣,因此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人们对禁限之物的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
因为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兽化”,只能在灵肉两极之间的巨大张力中燃烧和舞蹈,而电影中暴力的叙述及“暴力美学”对暴力奇观化的展示无疑满足了观众对暴力这种禁限之物的向往,也让观众在享受着现代文明、接受着礼教制约的同时尽情体验着“兽化”时的疯狂感觉。
2.文化机制
20世纪的“身体叙事”理论为“暴力美学”提供了大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支持。
在整个20世纪的学术领域中,“身体”成为了一部分先锋理论家关注的焦点,对身体的热切关注成了后现代喧嚣的话语狂欢中最时髦的声音,“从巴赫金到妓院,从利奥塔到紧身衣,身体变成了后现代思想关注最多的事物之一”。
例如米歇尔·福柯将研究目光投诸精神病学,将生理、病理和心理学与社会权力的运作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身体叙事的研究文本。
20世纪叙事学的兴盛使人们发现“身体”在许多时候隐蔽地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性与暴力主题成了人们察看身体叙事的一个有效视角。
但性主题叙事却常常被人们认为会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相比较而言,身体叙事之中的另一个主题——暴力——便浮出了水面。
暴力的叙事时常隐含了另一个潜在的情节:
人们无意识中的攻击能量因为一个酣畅淋漓的释放而复归于平静。
如果说拳击的游戏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暴力性身体侵犯的血腥意味,那么,叙事作品毋宁说是使暴力拥有另外一种“合理性”的合适语境:
暴力行为被有机地组织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之中,种种凶残的施虐由于故事的“上下文”而变得理所当然了,例如,再残酷的暴力一旦加上一个“复仇”的理由就会变得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
通常,文学的叙事作品是一种虚构,刀光剑影或者拳打脚踢仅仅是一种文字游戏,合上书本即像玩电子游戏一样“GAMEOVER”,然而,影像符号栩栩如生地展现了种种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们与暴力的距离近在咫尺。
表面上,人们仍然遵守社会文明的种种规则,文质彬彬地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之前;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由阴影参见[美]C·S·霍尔《容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页。
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1页。
原型而产生的嗜血欲望和暴力倾向制造一个个幻想性的满足,暴力题材的电影无异于是对人的感官进行“按摩”。
20世纪以来,除了理论研究的身体叙事外,纯然表现自我本能,源于身体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甚嚣尘上,对普遍价值的怀疑、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对身体和性的追捧成了人们看似无奈实则又颇具自发性的群体追求,得到了一种群体性破坏的快感,五花八门、绚烂多姿的暴力是制造这种快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身体叙事作品诱人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带来最本真、非社会的情感体验,这与前面提到的弗洛伊德的生本能、死本能和荣格的阴影原型理论可以做互文式的印证。
一个成功的正常运作的社会需要以各种极端之物的中和作为基础,暴力就属于这种极端之物,它相当于支撑社会的“理性之幕”上的一个破绽,是对人们终生拒绝直面的终极问题——死亡——的一次窥视。
同时消费社会追求快感的满足的需求要求艺术作品中对暴力的表现不能只停留在客观书写的地步,只有对其进行夸张化、风格化的处理才能刺激人们越来越麻木的神经和日渐“粗粝化”的审美感觉,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难伺候的欣赏胃口。
3.社会机制
电影对暴力问题的思考从其诞生初期开始发端,到后来达到一种较为典型和颇具特色的美学形态,始终都是与世界舞台上的政治风云、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思潮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的社资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两大阵营消失后的世界多元化格局,到21世纪的“9·11”恐怖事件和局部的战乱纷争,无不影响着电影对于暴力问题的思考,因此对于电影暴力叙事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更全面地梳理出这类题材影片的历史发展脉络,更是试图通过纵向的梳理和横向的比较,从而把握世界舞台上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这也是本文的社会学意义。
尽管有关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争论几乎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就有了,但就人类的自然本性来说是有“攻击性”的一面这一结论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社会生物学创始人之一E·O·威尔逊曾说,从调查和实验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显著的遗传特征,这就是说人类在处理矛盾时采取暴力行为,或者说采取有暴力倾向的行为,这是有内在的生物学根据的。
但他又在《论人的天性》一书中指出,与自然界万类比较起来,人类决不是最好暴力的动物,人类的暴力行为大多还是环境与文化的产物。
这点实际上也为中国的古圣先贤所认识。
孟子曾说: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非天之降才而殊也,其所以馅溺其心者然也。
”当社会秩序失去平衡时,就需要解决激化的社会矛盾,而暴力解决问题比较痛快、暴力实施者的内蓄能量得到了释放,这是人们在盲目状态下解决问题时的首选方案,因此也引发了人类对于暴力问题的思索,电影便是一种最为形象和直观的思考途径。
下面我们就从世界电影史的第一页开始读解不同时代电影人对暴力的不同理解,以期从中探寻出电影中的暴力发展到后工业时期所出现的风格化现象的社会动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争的阴影和不可名状的“世纪末情绪”深深地影响着刚刚诞生不久的电影艺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传统观念和精神文明危机加速了上世纪末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强调“内心真实”的超现实主义成为许多先锋派电影的最终归宿,他们力求揭示潜意识的偶然、狂乱和幻觉,热衷于把潜在于生命物之内的“情绪力量释放出来”。
残酷的社会现实引发了部分先锋派电影人对暴力问题的思索,如布努艾尔《一条安达鲁狗》中割破眼珠的镜头被称为电影史上“最残酷的镜头”之一,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着对黑暗无序世界的不满与人类前途的盲目、虚无这样一种“世纪病症”。
二战”期间,阴森恐怖的世界政治大气候使得表现暴力、犯罪、堕落、虚无主义的“黑色电影”应运而生,其阴冷、低沉的影调,偏斜、失衡的构图和暴力、犯罪主题凝聚成了当时时代的缩影,表达了孤独、冷漠、愤世嫉俗、对人生不抱任何幻想等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蒙上了浓重的死亡的阴影,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导致暴力、死亡再度成为电影的热点题材。
同时许多人在生死之间经历了恐惧、焦虑、孤独、荒谬等刻骨铭心的体验之后,在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对于暴力、死亡和个人的责任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
在暴力面前,有没有坚持自己的理想?
有没有帮助自己的邻居或素不相识的人免遭迫害?
在非人道的暴力面前有没有坚持自己的良心?
……这些都成为当时暴力题材电影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二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政治阵营的冷战再次给短暂享受和平的人们心头蒙上了更为浓重的战争阴影。
西方社会自进入60年代以来,通俗文化在后现代理论的宣讲中逐渐赢得了昔日所不曾拥有的堂皇权力,因为通俗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消费性,从此它可以公开打出消费的招牌,它还可以在艺术大旗上毫无顾忌地写上“娱乐”的字眼,再也没有人会去理直气壮地斥责它侵犯了艺术神圣的领地,因为通俗文化已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攻击现代主义经典的同盟者。
后现代主义在其与大众艺术的结盟之日起,大众艺术便裹挟着它无法自拔地陷入了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中。
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叛到最后可悲地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商业趣味和消费心理的妥协,后现代艺术从此被纳入了市场机制,转引自《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
参见崔君衍《一条安达鲁狗》,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第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堕落成为一种商品,丧失了最初的批判精神,而这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不可遁逃的宿命。
顺应这种享乐趣味,以消费为主要目的的文化工业也应运而生,好莱坞炮制的所谓“新电影”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世界舞台上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频繁爆发的局部战争以及“性解放”造成电影中对性和暴力的再度热衷:
敢于直面残酷的人生、放浪形骸的性与暴力成为当时影片争相表现的主题,如《出租汽车司机》明显发泄了60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崩溃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暴力的崇拜,展示了患有“越战后综合症”的一代人的痛苦,彻底否定了当时甚嚣尘上的“通过暴力获得新生”的美国文化的神话;《穷街陋巷》也体现了这种“黑色精神”,其中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精神;《野蛮的一伙》则用无节制的暴力和疯狂的氛围将浪漫的昔日经典西部片中的西部变成了一场展示暴力与血腥的“芭蕾”,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