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名人文章母亲的手庄因.docx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母亲的手庄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母亲名人文章母亲的手庄因.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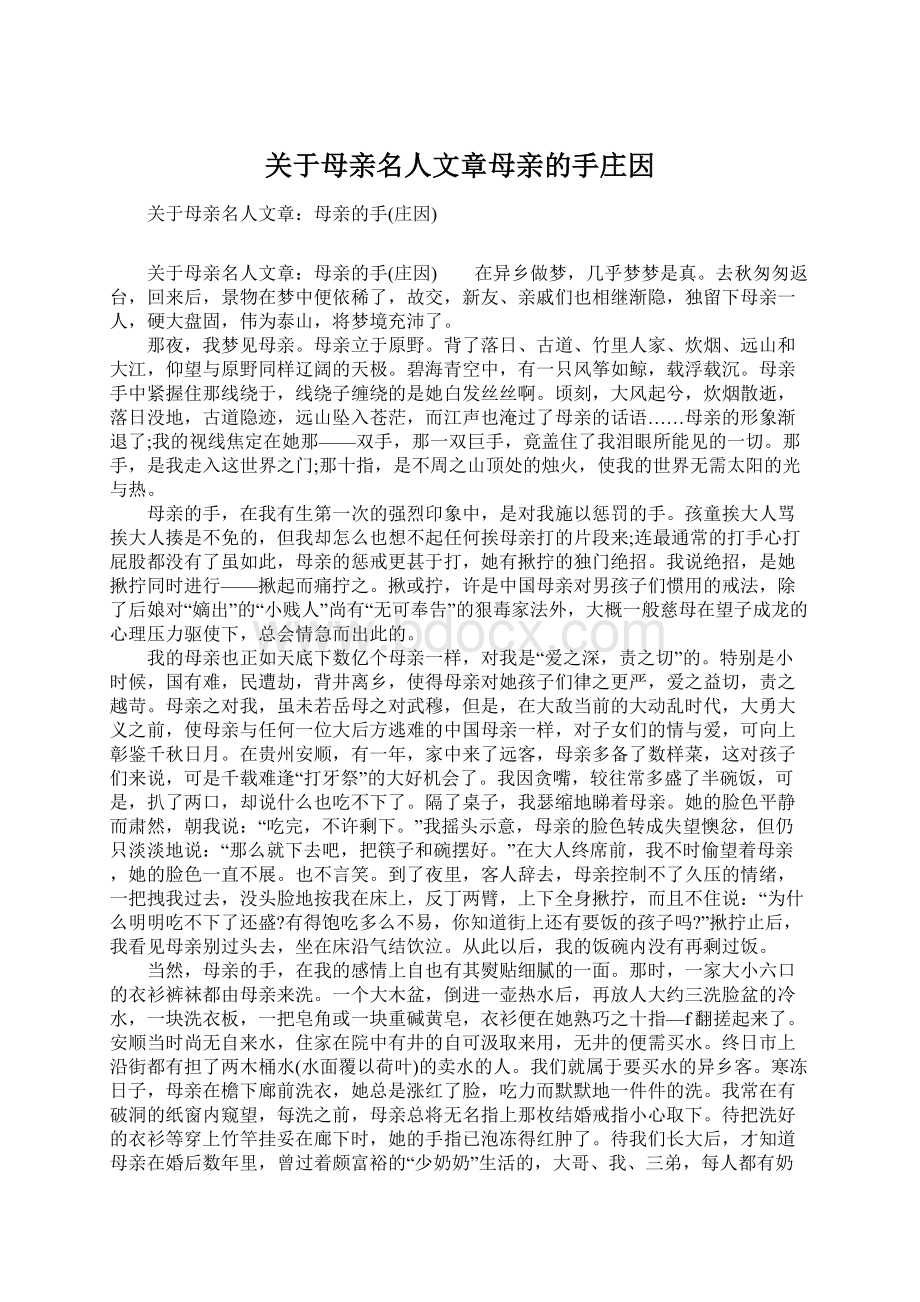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母亲的手庄因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
母亲的手(庄因)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
母亲的手(庄因) 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真。
去秋匆匆返台,回来后,景物在梦中便依稀了,故交,新友、亲戚们也相继渐隐,独留下母亲一人,硬大盘固,伟为泰山,将梦境充沛了。
那夜,我梦见母亲。
母亲立于原野。
背了落日、古道、竹里人家、炊烟、远山和大江,仰望与原野同样辽阔的天极。
碧海青空中,有一只风筝如鲸,载浮载沉。
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于,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
顷刻,大风起兮,炊烟散逝,落日没地,古道隐迹,远山坠入苍茫,而江声也淹过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形象渐退了;我的视线焦定在她那——双手,那一双巨手,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的一切。
那手,是我走入这世界之门;那十指,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使我的世界无需太阳的光与热。
母亲的手,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
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了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
我说绝招,是她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
揪或拧,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除了后娘对“嫡出”的“小贱人”尚有“无可奉告”的狠毒家法外,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的。
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
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
母亲之对我,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大勇大义之前,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对子女们的情与爱,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
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打牙祭”的大好机会了。
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
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
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
“吃完,不许剩下。
”我摇头示意,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
“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
”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
也不言笑。
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丁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
“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
有得饱吃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
”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
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
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
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人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f翻搓起来了。
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
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
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
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
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
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
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的,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
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
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
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
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
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
可是,出乎意外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
“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
”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灯,开始为我们衣袜缝补。
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的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罢!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
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萧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
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才情的了。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
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
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
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
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晶的润饰。
唯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
我的母亲(季羡林)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
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
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
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
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
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
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
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
奈之何哉!
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
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
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
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
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
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
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
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
"儿啊!
你让娘想得好苦呀!
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
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
"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
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
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
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
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
这是可能的吗?
这是真事吗?
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
我对"母亲"说:
"娘啊!
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
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
"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
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
"母亲"连声说:
"是啊!
是啊!
我要走了。
"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
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
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
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关于母亲名人文章:
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
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
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
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
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
我是“老”儿子。
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
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
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
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
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
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
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
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
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
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
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
她是我家中的阎王。
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
命当如此!
”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
是的,命当如此。
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
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
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
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
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
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
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
“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
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
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
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
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
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
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
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
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
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
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
这是一笔巨款!
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
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说了句: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
”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
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
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
大家都怕她晕过去。
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
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
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
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笑了。
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
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
”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
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
时代使我成为逆子。
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
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
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
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
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
我疑虑,害怕。
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
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
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
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
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
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
唉!
还说什么呢?
心痛!
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