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docx
《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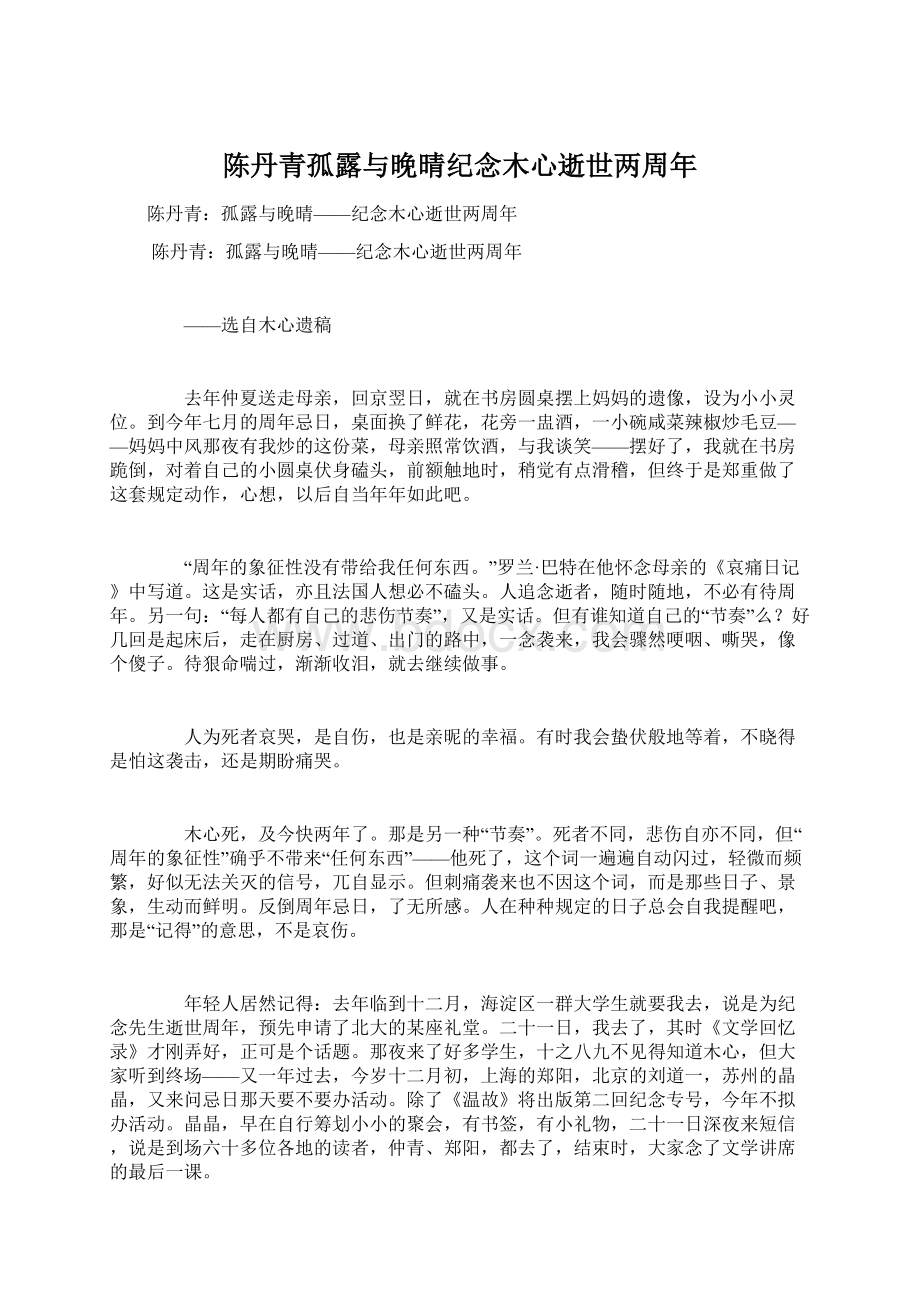
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陈丹青:
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陈丹青:
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
——选自木心遗稿
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遗像,设为小小灵位。
到今年七月的周年忌日,桌面换了鲜花,花旁一盅酒,一小碗咸菜辣椒炒毛豆——妈妈中风那夜有我炒的这份菜,母亲照常饮酒,与我谈笑——摆好了,我就在书房跪倒,对着自己的小圆桌伏身磕头,前额触地时,稍觉有点滑稽,但终于是郑重做了这套规定动作,心想,以后自当年年如此吧。
“周年的象征性没有带给我任何东西。
”罗兰·巴特在他怀念母亲的《哀痛日记》中写道。
这是实话,亦且法国人想必不磕头。
人追念逝者,随时随地,不必有待周年。
另一句:
“每人都有自己的悲伤节奏”,又是实话。
但有谁知道自己的“节奏”么?
好几回是起床后,走在厨房、过道、出门的路中,一念袭来,我会骤然哽咽、嘶哭,像个傻子。
待狠命喘过,渐渐收泪,就去继续做事。
人为死者哀哭,是自伤,也是亲昵的幸福。
有时我会蛰伏般地等着,不晓得是怕这袭击,还是期盼痛哭。
木心死,及今快两年了。
那是另一种“节奏”。
死者不同,悲伤自亦不同,但“周年的象征性”确乎不带来“任何东西”——他死了,这个词一遍遍自动闪过,轻微而频繁,好似无法关灭的信号,兀自显示。
但刺痛袭来也不因这个词,而是那些日子、景象,生动而鲜明。
反倒周年忌日,了无所感。
人在种种规定的日子总会自我提醒吧,那是“记得”的意思,不是哀伤。
年轻人居然记得:
去年临到十二月,海淀区一群大学生就要我去,说是为纪念先生逝世周年,预先申请了北大的某座礼堂。
二十一日,我去了,其时《文学回忆录》才刚弄好,正可是个话题。
那夜来了好多学生,十之八九不见得知道木心,但大家听到终场——又一年过去,今岁十二月初,上海的郑阳,北京的刘道一,苏州的晶晶,又来问忌日那天要不要办活动。
除了《温故》将出版第二回纪念专号,今年不拟办活动。
晶晶,早在自行筹划小小的聚会,有书签,有小礼物,二十一日深夜来短信,说是到场六十多位各地的读者,仲青、郑阳,都去了,结束时,大家念了文学讲席的最后一课。
我无法知道木心怎样想象他的读者,也不能知道读者怎样想象木心。
五月晶晶来乌镇,我领她进了先生的卧室,给她看搁在书架上的骨灰盒,还有纽约电影人拍摄先生的剪辑版——木心于是在自己的卧室缓缓说话,电视屏幕对着他的空床,我们就坐在空床上——晶晶没见过先生,几分钟后,她退开,说是不忍再看。
小代头一回看,也只片刻,起身走去客厅墙角,默默抽烟。
他不哭。
惟春末来过短信,说为别的什么事下泪,念及木心,趁势大哭一场,“好痛快”。
先生逝世一年半,这孩子总算哭出来,说,他还是不能接受先生“变成了盒子里的一堆灰。
”
木心留下的事,可得一件件做起来。
初起着手《文学回忆录》的工作,长路漫漫,待一字字敲下去,倒是可把握的。
母亲在医院昏迷的十天,再是昏累惨苦,回家坐定,录数百字,人即刻沉静。
此事前后八九个月,如今回望,只一瞬,今年以来,则每月去一次乌镇:
晚晴小筑,将要辟为木心故居纪念馆了。
晚晴小筑的幽静,如今转为凄清。
一楼客厅陈设如昔,终日窗帘拉起,黄昏,临院仍是群鸟归巢的密集啁啾,入夜后,全楼漆黑,唯过道与吃饭间亮着灯,小代小杨仍住这里看守。
面南三进小庭院那株枇杷树,枯死了:
每片叶子并不掉落,有姿有态,就那么枯死了。
两条狗,莎莎、玛利亚,是洗衣妇起的名字,春末莎莎死了,入夏,纪念馆开工,东门常是开着,不经意,玛利亚出走,不再回转。
西墙外是昔年孔令境先生的孔家花园,种有茂密的竹林,不知何故,去年割除大半,今年春,许是根脉窜入晚晴小筑,花园西墙根冒出十余株小笋,未久,竟成数米高的小竹林。
四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小代站在南院空房里发呆。
晚晴小筑落成后,南门迎对东栅景区街面,常年关闭,门内三进与北端的花园由白墙隔开,中有小门,进门穿过花园,便是木心暮年居住的二层宅邸。
宅邸另有甬道通向东门,门外是公路,为避游客,主客由此出入。
2006年先生还乡后,“木心美术馆”尚未动议,我催他将这面南的三间空房设为展厅,余事由我和镇方操办,可木心从未打算清理,直到他逝世,经年空置着。
垂老后,先生诸事嫌烦,除了勉力画画写写,他已放弃一切。
固然,他活着时,安康最是要紧,现在他死了,每想到南院空房,我便犯愁——位于西栅的美术馆去年动工了,纽约的设计者冈本与林兵来了怕有二三十回,亲自督造——纪念馆迟早总要弄出来,怎么办呢?
“平畴远风
良苗怀新
坐东卧西之堂
作而不述之室”
拟将悬在纪念馆的几幅匾额,先生几年前就写好了毛笔字。
凡纸笔之事,他早早就有腹案,题签之类,平时就躲起来弄妥、放好,此外的事,做,还是不做,木心永在犹豫拖延中。
新世纪头几年每次回纽约探亲,去看他,水斗堆满隔顿未洗的碗碟,我要洗,先生总是断然地说:
“不要弄!
我们讲话。
”之后瞅着话语的空挡,他幽然笑道:
哪有哈姆雷特天天洗碗的?
作孽!
木心哎,如今的事,何止隔顿的碗碟,便是一件件做成了,你也看不见。
一年来,靠小代步步跟着帮衬,南院三进总算辟为家族馆、绘画馆、文学馆,每馆的展墙竖了起来,十余枚展柜也做好了,两处小庭院栽种了新竹、李树、桃树,还有蓬勃的鲜草,草坛边缘,由本镇花匠编了弯弯的护篱。
各厅的匾额、木心的字画,均已送去刻制配框,文稿和遗物好在现成,昭明书院有位木心的学生匡文兵,在网上购得三百多册民国版书籍,明年元月打扫干净,着手布置,我已看见这些物事放入展柜的效果了。
沉重之事,是先生的大量遗稿,单由我做,断难下手的。
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哪里?
木心文学的常年研究者童明,远在加州教书,我能倚靠的,便是出版社。
十二月中,《新周刊》为《文学回忆录》颁发年度书奖,典礼假乌镇举行,我与主编刘瑞琳、责编曹凌云、助理编辑雷韵和罗丹妮,联袂前往,化了三天工夫,清理遗稿。
到乌镇那天,先领大家上楼看望先生,众人站定,瞧着骨灰盒,三位女士先后抽泣了,依次上前行礼。
除了颁奖那夜,我们朝夕聚拢晚晴小筑面北的画室,各人手里捂一杯热茶,将先生五六十册笔记本、数千页散稿,粗粗分类。
小代,忠诚而细心,平日即留意木心散乱放置的稿本,葬礼过后,是他与黄帆,那位镇方最初派往侍奉先生的姑娘,默默集拢全部遗稿,等我们来。
现在,哪些是废稿、正稿,哪些是早期、晚期,均须大费周章,逐一辨识;已发表与未发表者,则待今后一次次再来,细细审读了。
十二月十五日夜,分类后的所有遗稿贴上标签,登记在册,放回保险箱,遗稿出版的工程,总算上路了。
也巧,我与小代初次试着归拢木心的稿本,也在两年前的同一日。
其时先生在桐乡的重症病室,不省人事。
下午三点探视前,我们无事可做。
静静翻阅着,我忽然意识到未经先生同意,而另一尖锐的意识迅即跟进:
没有同意这回事,完全没有了。
惊痛,郑重,茫然,瞧着满桌稿本,我又像是对着木心的性命,不知所措。
几十年来,我眼见先生开写、修改、丢弃、重来,狱中所写六十六页手稿是他仔细折拢了,缝在棉裤里,日后带出囚室……两年前,是的,就在这一天,我意识到木心遗弃了毕生的文稿。
“去吧去吧
我的书
你们从今入世
凶多吉少”
……这是先生遗稿中涂写的几句话。
那天下午,我最后一次面见活着的木心,又过六天,他就死了。
这些凌乱而标致的手稿,部分写在各种稿纸上,大部分写在纽约文具店出售的笔记本,至今留着价目的贴片。
木心讲究衣物用具,却不介意使用廉价的本子写作——以繁体字工整抄正的稿面,落笔矜矜,清雅优美,草字疾书的稿本则布满涂改;他会在每行白话诗尾端核算字数,斟酌节奏。
可恼的是,每首诗、每一短句、每篇稿子,至少重写四五遍,分布在稿本不同页面,实在难以判断究竟哪篇是他所满意的正稿。
年迈后,他的字迹缓缓变化:
越新世纪,人老手颤,笔划歪斜,气息愈见虚弱;整个九十年代,落笔矫健,神完气足,或是米粒大小的正楷,谨严而端正,或是纵笔行草,字词与行距密不透风,任意写满纸页的正反面;好几个本子才写三五页,整册空白着,大量本子则是全部写满,写满了,还在篇幅间横竖添加——1983年我与先生密集交往,亲见他恢复写作后的头一批原稿,此番搜寻,未发现:
没有《明天不散步了》,没有《哥伦比亚的倒影》,也没有《温莎墓园》。
“又写好一篇呀。
”他在电话里说。
那些年,隔三差五,木心就来报告。
“哦,不得了,你凶……”“凶”,沪语即“厉害”的意思“像煞摊大饼,又是一只!
”“写得怎样?
”“可以呀,还可以。
”
会面地点通常三处,一是当年我们的“留学”之地,曼哈顿五十七街第七大道交汇口“艺术学生联盟”咖啡馆;一是过学校朝北两条街对过的中央公园;若在冬季,木心便来我的寓所。
现在想想不可信:
那些年,我竟连连看的是先生的手稿。
头几回,他如小学生那般,脑袋凑过来,从第一行开始陪我读,点明若干潦草的简笔字,三言两语解释我所不识不懂的词,便催我往下读——看画读文,我是会叫唤的:
啊呀木心,这句好!
他的回应,或是急速退回上身,瞪眼瞧着我,忍着得意地笑,竭力正色道:
呶—呶—呶,看出来了呀,你知道!
或是一怔,喃喃地说:
噫,你怎会晓得?
你怎么也能懂?
!
这样的几率不很多,多的是瞧我越过他所得意的段落,便止住我,手指点着稿面的某处:
看这里呀,看见吗?
于是自己念起来。
什么句子呢,年头委实久了,我已不能记得。
其时我三十出头,木心五十八九。
有几篇稿子经我无心撩拨,而他果真写了——去林肯中心,我说,音乐会的咳嗽,你有本事写吗。
散场了,他喃喃地说:
“咳嗽倒是不好写……”于是有《S巴哈咳嗽曲》。
春天,中央公园繁花盛开,木心缓步说出花草的名目。
我说怪了,美国的花为什么不香?
你写呀!
他凑近花丛,嗅着,忽而神色飞扬回过头:
“杭州桂花开出来,喔——唷!
胡天野地,香得昏过去!
”几天后,写成《九月初九》——写成了,急急来见。
那天是在金高家,一屋子人,他看我坐定了自管读,忽而满脸窃笑走过来,低声说:
“你这样子当真,我交关开心,交关开心哩!
”说着,香烟递过来——每次分手,我们常会彼此送一程。
某日傍午,对了,就在杰克逊高地,我到站,木心说,那么再走走。
长长的露天站台,脚下街面,车声隆隆,一老一少站在风中各自点烟——其时纽约尚未全面禁烟,简直天堂——那天正大谈人在异国的寂寞,不肯歇,好句子堵嘴边,木心就挫身停住,目光灼灼看着我,双手擎着纸烟和火机,一字一顿说:
“人害怕寂寞,害怕到无耻的地步!
”那天回家,他就写《竹秀》。
很久很久的事了,但我记得。
“……那么尼采叔本华,你怎样讲法?
”是在曼哈顿中央地铁站,我与木心仍在昏天黑地聊:
“呶!
一个么阴,一个么阳,一个借借佛家,一个去寻希腊……两只狗交配,见过么,弄好了,浑身一抖,”同时就脸颊猛颤颤,学那狗模样:
“这就是生命意志呀!
”来源:
《经济观察报》|来源日期:
2014-01-25|责任编辑:
蒲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