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docx
《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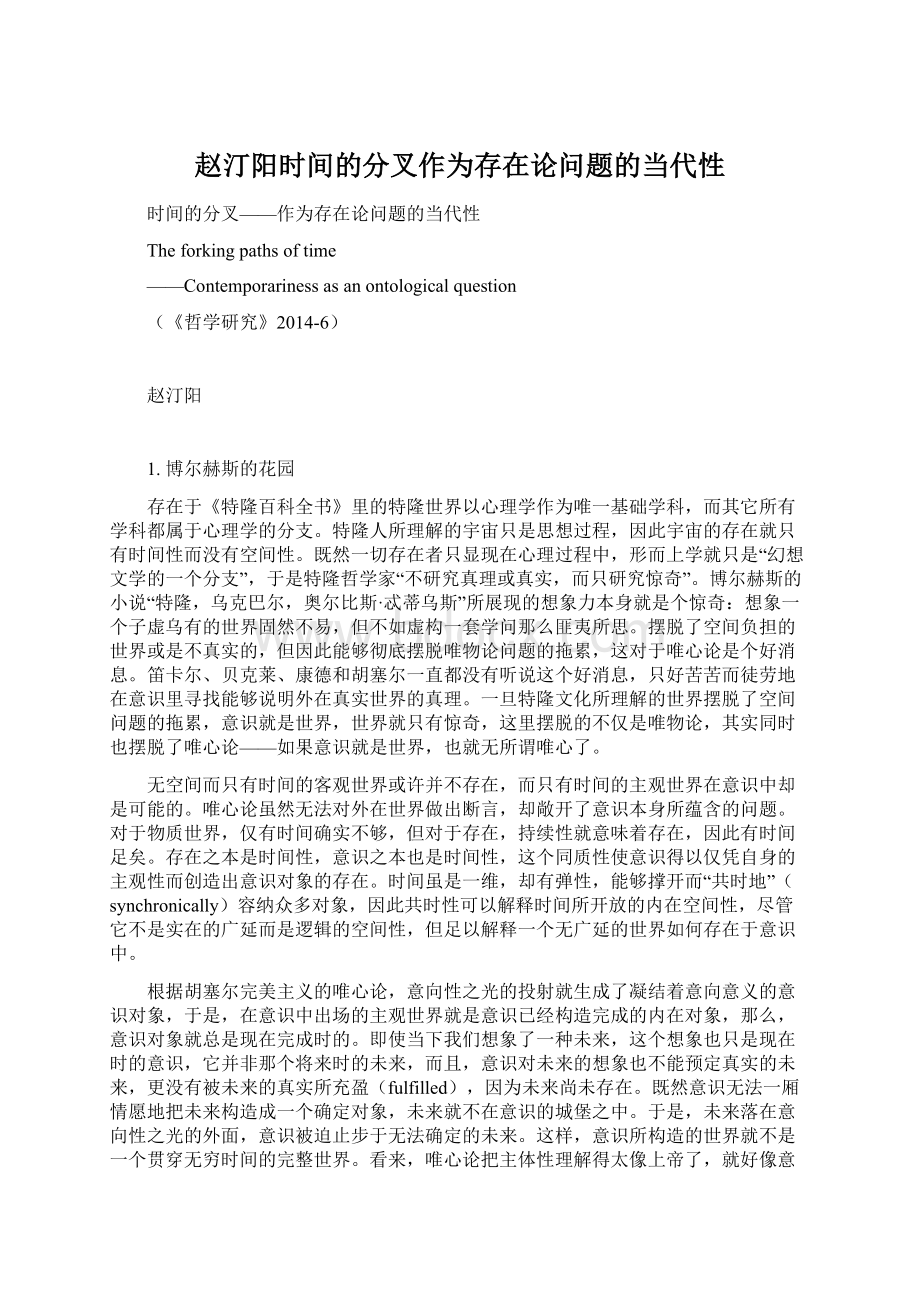
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
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
Theforkingpathsoftime
——Contemporarinessasanontologicalquestion
(《哲学研究》2014-6)
赵汀阳
1.博尔赫斯的花园
存在于《特隆百科全书》里的特隆世界以心理学作为唯一基础学科,而其它所有学科都属于心理学的分支。
特隆人所理解的宇宙只是思想过程,因此宇宙的存在就只有时间性而没有空间性。
既然一切存在者只显现在心理过程中,形而上学就只是“幻想文学的一个分支”,于是特隆哲学家“不研究真理或真实,而只研究惊奇”。
博尔赫斯的小说“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忒蒂乌斯”所展现的想象力本身就是个惊奇:
想象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固然不易,但不如虚构一套学问那么匪夷所思。
摆脱了空间负担的世界或是不真实的,但因此能够彻底摆脱唯物论问题的拖累,这对于唯心论是个好消息。
笛卡尔、贝克莱、康德和胡塞尔一直都没有听说这个好消息,只好苦苦而徒劳地在意识里寻找能够说明外在真实世界的真理。
一旦特隆文化所理解的世界摆脱了空间问题的拖累,意识就是世界,世界就只有惊奇,这里摆脱的不仅是唯物论,其实同时也摆脱了唯心论——如果意识就是世界,也就无所谓唯心了。
无空间而只有时间的客观世界或许并不存在,而只有时间的主观世界在意识中却是可能的。
唯心论虽然无法对外在世界做出断言,却敞开了意识本身所蕴含的问题。
对于物质世界,仅有时间确实不够,但对于存在,持续性就意味着存在,因此有时间足矣。
存在之本是时间性,意识之本也是时间性,这个同质性使意识得以仅凭自身的主观性而创造出意识对象的存在。
时间虽是一维,却有弹性,能够撑开而“共时地”(synchronically)容纳众多对象,因此共时性可以解释时间所开放的内在空间性,尽管它不是实在的广延而是逻辑的空间性,但足以解释一个无广延的世界如何存在于意识中。
根据胡塞尔完美主义的唯心论,意向性之光的投射就生成了凝结着意向意义的意识对象,于是,在意识中出场的主观世界就是意识已经构造完成的内在对象,那么,意识对象就总是现在完成时的。
即使当下我们想象了一种未来,这个想象也只是现在时的意识,它并非那个将来时的未来,而且,意识对未来的想象也不能预定真实的未来,更没有被未来的真实所充盈(fulfilled),因为未来尚未存在。
既然意识无法一厢情愿地把未来构造成一个确定对象,未来就不在意识的城堡之中。
于是,未来落在意向性之光的外面,意识被迫止步于无法确定的未来。
这样,意识所构造的世界就不是一个贯穿无穷时间的完整世界。
看来,唯心论把主体性理解得太像上帝了,就好像意识能够构造一切对象,可是在未来面前,意识的魔法失灵了,意识无法主观地决定并且构造未来,意识的权威和构造能力仅限于现在完成时。
对于作为超时间绝对存在的造物主而言,未来不是个难题,只要造物主乐意,无穷时间和无限存在都可以同时一起出场,类似于瞬间穷尽了无限数目。
可是对于存在于时间中的人,未来尚未存在而只是无穷未定的可能性,人无法对尚未存在的无穷可能性进行有效的比较,也就难以决断,于是意向性踌躇不前而滞留于现在完成时。
除非意识放弃自由,按既定惯例行事,使未来成为现在的复制,意识才有确定的前行意向。
可问题是,重复性的前行方式正好否定了未来。
假如失去了不可测的未来性,未来就还等于现在,重复存在意味着尚未进入未来。
我们只好承认,意识所构造的主观世界不可能是完整的,总有一半尚未存在,意向性之光是有限的,世界总有一半在黑暗中。
这正是主体性的难处:
人虽是生活和历史的作者,却对自己的创作毫无把握。
博尔赫斯在另一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里揭示了关于时间意识的关键问题。
那个古代中国的建造师的遗作令人费解,似乎处处矛盾百出,就像是一个让人迷失的路径交错的花园,它暗藏的谜底是无穷分叉交错的时间。
通常,在面临未来的多种选项时,我们只能选其一而排它,所以永远痛失众多可能性。
可是那本谜书却超现实地“同时选择了所有选项,于是创造了多种未来,多种时间,它们分离又交错”,于是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种种结局,但结局并非结束,而是通向其它更多分叉的出发点,因而未来总在步步分叉中无穷演化。
交叉小径花园的作者“不相信单一绝对的时间,而相信存在着无限的时间系列,存在着一张分合平行扩展的时间之网”,这张不断分叉的时间之网包含了一切可能性,因此“时间总是不间断地分叉为无数个未来”。
这就是自由选择的困境:
无穷展开的未来永在意识的能力界限之外。
时间分叉打破了时间流畅的一维性,导致了时间断裂,使投向未来的意向性永远处于尚未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状态,就是说,既然未来永远是个谜,那么,投向未来的意向性就不可能生成确定的意义而陷于未来的迷宫之中:
一切互相矛盾的可能性都是同等可能的选项,没有事先预定的优先排序而平行铺开在现时之中,并且在更远的未来里还可能互相交叉或互相转换。
不可测的未来撕裂了意向性,使之难以凝聚。
作为时间分叉的多种未来可能性虽然共时地存在,可它提出的却不是共时性问题,而是当代性问题。
这两个问题有所不同:
“与时间同在”(contemporary)不同于“在同一时间里多个事物同在”(synchronic)。
在某个时刻,多个事物同时存在,我们意识到的是这些事物的平行状态,却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当我们意识到时间分叉为多种尚未存在的可能性,而且还将无穷分叉为更多可能性,此时意识到的不是事物,而是时间本身,或者说是时间的时间性,以及我们与时间的同在关系。
意识到与时间同在从而意识到意识自身的时间性,这就形成了当代状态。
在这个时刻,既然已经赶上时间而与之同在,就只好去引领时间了,就必须在时间中给时间选择一种未来,可是时间只给了主体领路权却不给解释权,所以我们无法解释未来。
2.意识的时间纪年
奥古斯丁之所以无法回答“不问时原本是知道的”时间是什么,是因为无法给时间一个概念——时间已是最基本的概念了,所以,对时间的最好解释也不过相当于同义反复。
时间可用来解释别的事情,而不可能被解释。
奥古斯丁想必熟知柏拉图对时间的经典解释,他不援引柏拉图自当另有原因。
柏拉图给出的是对时间的一个迂回解释:
宇宙的原型是永恒存在本身,造物主根据原型创造宇宙,可是宇宙始终变动不居,并不能表达原型那种无变化的永恒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造物主创造了时间作为“永恒的形象”(imageofeternity),有序的时间(chronos)以数列方式的无穷流变去勉强表现永恒性,无穷性虽不等于永恒本身但近乎永恒性。
过去、现在、未来表达的是生成形式,可以用来谈论事物,却不足以表达永恒,“对于永恒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划分并无意义,永恒之在‘一直是’而决不是‘过去是’也不是‘将来是’”,柏拉图如是说。
考虑到奥古斯丁是发现我思问题之第一人(笛卡尔则是发明我思理论的第一人),也许可以猜度,奥古斯丁已敏感到时间是属于我思的主观形式,因此不愿采用柏拉图的时间理论。
柏拉图的时间显然更适合说明自然时间,并不能解释人的时间性,即具有历史性的时间。
创造世界不是人的工作,人只能创造历史,不能创造时间,却创造了时间的历史性。
给时间赋予形象能够增进人对时间的理解吗?
孔子的川上名言是时间的一个经典形象,可孔子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可以追问:
流失的到底是什么?
是时间还是事情?
如果时间永无断绝地流走而又到达,时时如一,时时正当时,那么,时间流失了吗?
无独有偶,赫拉克利特也有个流水的隐喻,通常概括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这并非原话。
赫拉克利特的流水言论最早载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
“相传赫拉克利特说:
万物皆动而无物驻留。
他将其比作河流,他说你不能两次踏进同样的水流”。
可见赫拉克利特的意思很清楚:
流变的是万物而不是时间本身。
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时间形象是无穷直线(谁发明的?
待考)。
直线虽不如流水那么逼真,但直线对人的诱惑在于它能够把不可分的时间兑换为可分割的段落,这样似乎可以变相地使时间“停下来”而加以分析,但这是个可疑的诱惑。
假如时间真如直线那样可以分割,那么芝诺就确有理由宣称那些时间的悖论,例如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或飞矢不动等等。
然而,当直线最终被分割为没有长度的点,时间就更神秘难解了。
博尔赫斯发现:
假如每个现时是一个没有长度的几何点,那就意味着现时一半在过去,一半在未来,现时为空,于是“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纯粹现时,因此现时等于零”。
如此看来,化线为点并不是使时间停留而加以思考的恰当方式。
顺便一提,照片倒是具有让时间停留的效果,照片是可以凝视的,凝视就是历史性的,正是历史性留住了时间。
与无法凝视的录像相比,照片更具形而上意义。
正如前面提到的,存在是时间性,意识也是时间性,既然意识具有时间性这一魔力,就能够把握存在,也因此能够构造一个属于意识的主观世界,可以表达为唯心论的公式:
主体性(subjectivity)构造客观性(objectivity)。
从笛卡尔、康德到胡塞尔所建构的主体性都基于具有魔力的内在时间意识。
内在时间是主观时间,它并不是自然时间的对应形式,而是意识自身的运行方式,或者说是意识对自身的意识形式。
如果没有内在时间,人就失去主体性,就只是与万物无异的自然存在。
内在时间永为现时,因此超越了流失。
意识以现时为原点和出发地,让意向性双向地投向过去和未来,在过去和未来里形成任意远近的意向落点,就是说,意向性可以任意安排事件的显现顺序。
在这个意义上,蒙太奇本来就是意识自身的一种构成方式,难怪德勒兹发现了时间意识与电影艺术之间有着互相解释的关系。
无论五千年前还是昨天的事情与现时的真实距离有多远,在意识中都与现时等距,同样具有现时意识的同时性。
虽然历史事件按照自然时序而被记载,但所有的记忆却只有同一个时间,是现时意识中的“过去那时”;同样,所有的未来,无论什么时候来临,都是现时意识中的“将来到时”。
年月日是外在时间的纪年,而那时、现时和到时——更通常的说法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意识内在时间的纪年。
对于意识来说,年月日是记事的技术刻度,用于给事情的发生顺序记流水细账,却对时间的本质无所说明,而过去、现在和未来才是时间意识的自我解释,表达的是事情在意识中的出场方式,这是意识自身的纪年。
既然过去和未来都在现时里出场,现在时就是主体性的唯一时态,是意识自身的正时,既是时间的原点和出发地,也是时间两面的分界线,它把一切现实的划为过去,而把一切可能的划为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现时确是空无(同意博尔赫斯的说法)。
正因为现时本身为空,才有空地去邀请并接纳过去和未来的出场,因此现时也就成为时间的召集者。
当意识把过去和未来召唤到现时中来,过去的任何一个那时就不仅具有那个时代的当代性,也因现时之召唤而具有现时的当代性;同样,未来虽然尚未存在,却作为现时的可能前途被召集出场而具有当代性。
3.告别而不知如何出发
与意识不离不弃如影相随的现时既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时刻,现时就既是一个告别的时刻,也是重返的时刻,又是出发的时刻。
博尔赫斯通过时间分叉效应思考的是意识朝向未来的一面,而既然现时是两面朝向的,博尔赫斯的时间分叉效应也应该两面有效,过去的事情和尚未实现的可能性都同样作为思想问题而在场。
现时既然是意识的唯一时刻,也就是意识的恒定点,因此,现时永远都是时间的当代。
现时总是一个告别的时刻,又是出发的时刻。
如果告别而不能重返,告别就是丢失,不过,丢失的不是时间而是历史。
自然时间富有一切,挥霍不尽,既不看管也没有责任看管历史,一切发生了的事情都会随自然时间永远消失,而意识却能够实现重返。
然而,能够重返的不是事情,而是事情的意义以及存留的问题。
正是重返创造了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意识通过重返将过去的任一问题当代化,也创造了时间的历史性。
当然,当代性并非附着于自然时间的亲历性,而是召唤“那时”和“到时”的现时性。
当代性超越了时间的流逝而把那时拉入此时,那个重返的那时也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重新出发的此时。
既然意识之永时是现时,当代就不是时间顺序中的一个时段,而是过去和未来双向来到现时的汇集状态,也就是所有时刻一起在场的状态。
在自然感觉上,我们可以觉得时间在流向过去,也可以觉得在流向未来,但如果从历史性去看,过去和未来都同时流向现在。
因此,克罗齐也就有理由认为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代性不是某一类历史的特征而是一切历史的内在性质”,而过去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当代问题关联着过去的问题而使过去具有了当代性。
然而当代性却不仅是个史学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存在论问题,甚至是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神学问题。
意识使人成为主体,却又因为并非全知全能而不可能成为绝对主体,只能是受限于世界的卑微作者,只能创造历史而不能创造世界,因此,主体性暗含着自我否定的悖论性:
人无法自证他所创造的生活的价值,就是说,人的创造活动同时把他所创造的事情置于可质疑的境地:
我想了,也做了,但这只证明了这是我的选择,并不能因此证明所想所做的意义。
这里有必要重新解读笛卡尔的潜台词:
我思能够自证是无疑的,因为我思不可能怀疑我思本身,但我思却无法自证其所思是无疑的,因此,即使我思无疑,所思依然可疑。
笛卡尔也因此止步于对我思的证明而没有贸然去证明所思的绝对性。
这或许是笛卡尔早已暗示的主体性困境。
可是,按照唯心论的逻辑,笛卡尔止步于我思是不可接受的,它会导致主体性半途而废,于是,从康德到胡塞尔都试图证明无疑之我思如何能够直接保证无疑之所思。
把时间理解为内在意识,是康德和胡塞尔的天才之见。
既然时间成为意识的自我解释,驾驭着时间的意识就能够自我解说主观世界,我思就足以解释所思。
这个成就似乎证明了唯心论的胜利。
对于如此精进的唯心论,估计笛卡尔会佩服,但未必会放心,因为意识拥有主观世界只能显现意识自身,却不能解决外在世界的真实问题,即使意向性可以意得自满(fulfilled),却仍然难解身处外部世界之忧——海德格尔为之忧心的“被抛于世界中”状况点明了这个存在论问题。
存在论问题都落在意识的知识范围之外。
既然凡是已经知道的都属于过去,那么,意识无法认识的一个主要事情就是未来。
未来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现实的,所以不可知。
当所面对的问题既不是必然性也不是现实性而是可能性,主体就离开了知识状态而进入创作状态,此时主体赶上了时间,与时间同在,处于过去已经过去而未来尚未到达的临界状态,所谓当代状态。
这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是必须出发的时刻,可是,告别容易,却如何出发?
往何处出发?
假如能够给未来创造一种必然性……,这可想多了。
只有能够创造整个世界才能创造必然性,这是属于造物主的存在论问题,人无能过问。
按照莱布尼兹理论,造物主是世界存在的“充足理由”。
充足理由要求谓词完全而必然地包含在主词之中,这个存在论原则要求太高,非人力所及,难怪逻辑学家通常不同意把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当成逻辑定理。
人唯一能够自由做主的存在论问题,就是在诸多可能性中进行选择,选择可能性就是创造历史,它是属于人的创世论问题。
在缺乏必然性的情况下对可能性做出选择,行动(facio)的问题就超出了思想(cogito)的问题,未来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或者说,未来通过行动而存在。
人选择某种可能生活,类似于上帝选择某个可能世界,因此,行动(facio)即创作(creo)。
尽管创造历史与创造世界相比微不足道,却同样面对的是本源性的问题,同样经历着开端状态。
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创世状态,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属某个时期,既不是公元元年的特性,也不是公元两千年的特性。
为什么当代不是时间中的一个时段?
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不断无隙的连续流程,无处可以插入当代。
假如把当代等同于现在,既多余又误导,显然并非所有的“现在”都具有当代性,因为并非所有的“现在”都构成了历史的开端或者时间的断裂,而往往只是对过去的重复性延续。
所以说,当代性并非时间属性,而是存在状态,是给时间留下断裂刻度的机缘,按照德勒兹的用语则可以说是时间的“褶子”。
主体性的关键就在当代性,它是反思“自由何为”这个存在论问题的机缘。
假定上帝的创造就是把最优的可能世界实现为现实世界,那么,人的创作就是把可能生活实现为真实生活。
这意味着,人成为主体之时,时间就具有了历史性。
人存在于时间中,不可能像上帝那样在时间之外进行创作,因此,历史性的存在方式就是在流失中抵抗流失,在时间流失中留住存在的意义,在历史中创建思想的线索和问题的重返点。
于是,历史性意味着时间将反复出现开端状态,也就是反复出现“事情由此开始”的初始状态,这种初始性就是存在的当代性,因此人的存在不止是时限性的(temporal)而且是当代性的(contemporary)。
作为历史的作者,主体性的本质在于超越了因果性的自由,在于能够创造开端,可是也正是自由造成了当代性的困境:
在无数可能性中,创作是否有一种必然理由?
如果没有必然理由,创作的可信性又在哪里?
可是,假如创作有了必然理由,创作又将因为反自由而失去意义。
造物主为它的创作找到了必然理由,这一点既令人佩服却不令人羡慕。
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理论是这样替上帝论证的:
在上帝的意识中存在着无数可能事物以及无数可能世界,那些“共可能的”(compossible)事物可以组成一个可能世界,而“不共可能的”(incompossible)的事物就只能分属不同的可能世界。
在众多可能世界之中,全知的上帝确认了具有最大共可能性的那个可能世界为最优的可能世界,因此将其实现为真实世界。
这个神话性的存在论指出了上帝所找到的必然理由:
最大化的共可能性,就是说,能够与最多数事物共可能的事物就有存在的必然性。
我相信这是关于存在的最深刻的见解之一。
可是人在可能性中却看不出必然性在哪里,因此彷徨。
休谟证明了:
从过去不可能推论出未来,从一切已知不可能推出未知是什么。
这个论证从知识论注解了告别却难以出发的当代状态。
在对未来可能性茫然无知的情况下,最容易的解决方式是拒绝未来,让现在留在过去里,按照习惯或习俗去重复生活。
然而,总有某些无法抗拒的新问题或临界事态迫使人进入未来,强迫人成为作者,这种无助的时刻经常使人期望先知,或者圣人,或者预言家。
4.先知退场后只剩下作者
要是有先知引路就放心了。
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必然性的人是先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
“先知就是已经看到了在场的在场者之大全的那个人”。
荷马最早指出成为先知的一个关键条件:
因为有了阿波罗密授的预言术,所以先知卡尔卡斯“知道当前、将来和过去的一切事情”。
这说明,除非神授,人自己没有能力成为先知。
尽管人因为有内在时间意识而拥有一切时间尺度,却不能因此而知道在时间中生成的一切事情,人看到的是全部时间而没有看到“在场者大全”。
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人依靠先知或圣人指路,但这件事情有个隐患:
先知始终无法提供能够消除怀疑论的必然理由,更无法消除能够故意不听圣言的自由意志,而且,当出现许多先知而所言又互相矛盾时,我们无法辨别谁才是真正的先知。
先知引路的神话被基督降临、受难并复活这个精神性更强的神话所终结。
阿甘本解释说:
“既然弥撒亚已现身人世并实现其诺言,先知就再也没有理由存在下去了,所以保罗、彼特及其同伴自认为是使徒,而不是先知”。
使徒只传播信仰,说服人相信决定性的时刻总有一天会来临,在使徒的世界里,只需要坚定的信仰和耐心的等待。
可是,信仰和耐心是靠不住的,且不说日久难免产生“等待戈多”的迷茫,对信仰的解释学更产生了使精神陷入混乱的歧义。
信仰无法自证其信念的必然性和唯一性,也就无法阻止和排除互相冲突的理解,解释学不仅无助于证明信仰,反而使之变得可疑。
正如吉莱斯皮分析的:
神学解释学的内部冲突早已蕴含了摆脱神学的现代性起源。
奥卡姆就直截了当地割断了信徒对上帝的救赎指望,他说,上帝不欠人的债,也没有因为人之善行就必予拯救的义务,上帝想拯救谁就拯救谁,人无法猜中上帝之意。
这种唯名论的理解让人顿失安全感,重陷于求助无门的命运。
既然信仰也不比先知更能许诺个人命运并保证其必然性,信仰就不是方舟,最后审判对于个人就缺乏确定的意义,人依然无从逃避自由,依旧无助地面对无可预告的未来。
先知既已退场,使徒也不再作保,人注定还要承担成为作者的艰难命运。
意识虽是时间的召集者,拥有前瞻后顾的能力,人却茫然于何去何从。
自由选择的难处不在于选中什么,而在于舍弃什么。
除非能够预知必然性,否则取一而舍多岂非赢面最小的冒险?
创作成为一种冒险地生成(becoming),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
而能安慰作者的仅是,必然性不是创作的荣耀,因为必然性是不可能生成的。
既然创作是为了生成,就必须背叛必然性,必然性也就不是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即使从对必然性的渴求中解脱出来,不再需要先知的预告或者信仰的许诺,作者在分叉的多种未来面前至少也需要一个选择的理由,否则无从选择。
假定作者不是赌徒,那么,当告别了先知的预言和使徒的许诺,当代性的存在状态能否显示出选择的理由?
5.与在场经验拉开距离
当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有着相关却又相背的关系。
人从来都是历史的作者,每个时代也就各有各的当代,所有开创了一种生活和历史的创作从来都是当代性的。
然而,在反思人的自由问题之前,人不会去反思其当代性。
当代性的问题化是以现代性为条件和语境的,只有当先知、圣人和使徒都失去指点迷津的功效,同时,创作成为主体的使命而不再是偶然的天才成就,当代性才成为主体性的存在论问题。
假如未曾有建构了主体性的现代性,也无反思当代性的机缘。
现代性以新为标准。
这个定位早已成为共识,吉莱斯皮对此有着再清楚不过的论述:
新就是“把自己理解为自我发源的、彻底自由的和创造性的,而不仅仅由传统所决定或由命运和天意所主宰。
要成为现代的,就要自我解放和自我创造,从而不仅存在于历史和传统之中,而且要创造历史。
因此,现代不仅意味着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而且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来规定时间”。
其结果是,如雅斯贝斯所言,现代“最令人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宣布什么东西是过时的、守旧的或前什么的。
现代人的这种时代划分不同于改朝换代的年代学,而是历史进步论,是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自我肯定冲动”,可是这种在场乐观主义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在场焦虑:
为了革命性的新就必须反对传统所塑造的自己,而反传统的一个后果却是使在场性变得贫乏、无所依据而失去标准,正如阿伦特的担心:
失去传统不仅仅是失去过去,也因此失去未来,只剩下无以解释自身又无法阻止意义流失的在场经验,因为“没有传统就意味着无可遗赠给未来的遗言”。
当代态度是对在场经验的一种警惕,绝非在场经验的自恋形式,因为当代性的问题落在未来的时间分叉上,而并不落在自我经验上。
阿甘本把当代性看作是个人与时代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更确切地说,是以脱节或不合时宜的方式去接触时代的那种关系。
与时代十分吻合的人,或在每个方面都那么完美地与时代捆绑在一起的人,都决非当代人,因为他们都显然没有试图去看清时代,他们无法矢志不移地凝视时代”,而“真正的当代人,真正属于时代的人,正是与时代格格不入而又不去自身调整以便适应时代要求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潮流的人,可是正因为与时代脱节或不合时宜,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感知和理解所在的时代”。
对此,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怎样才能够与时代拉开距离?
又以什么样的目光对时代进行凝视?
严格地说,只有永恒性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性。
人非永恒,所以人的存在不具超越性,但意识有望借得某种永恒观点(subspecieaeternitatis),即一种无时限的观点。
维特根斯坦说过:
“如果不把永恒理解为无限持续的时间而理解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那么活在现在就是永在。
就我们的视野是无限的而言,就可以说人生无穷”。
既然当代性是主体与任何时间的等距概念,那么,“无限的视野”就不可能限于此时,而是召集一切时间共同在场的思想状态,它使得过去和未来能够超越时间的线性而在现时里一起出场,于是为时间撑开了一个无限的无形空间,在效果上形成一种无时间性。
过去和未来得以挤在现时里与现时平行,这样,主体就有机会在意识里站在别处,与现时拉开距离,不合时宜地观察现时,也可以去理解任何时刻。
凡是现实的都是暂时的,这一点甚至在古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