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docx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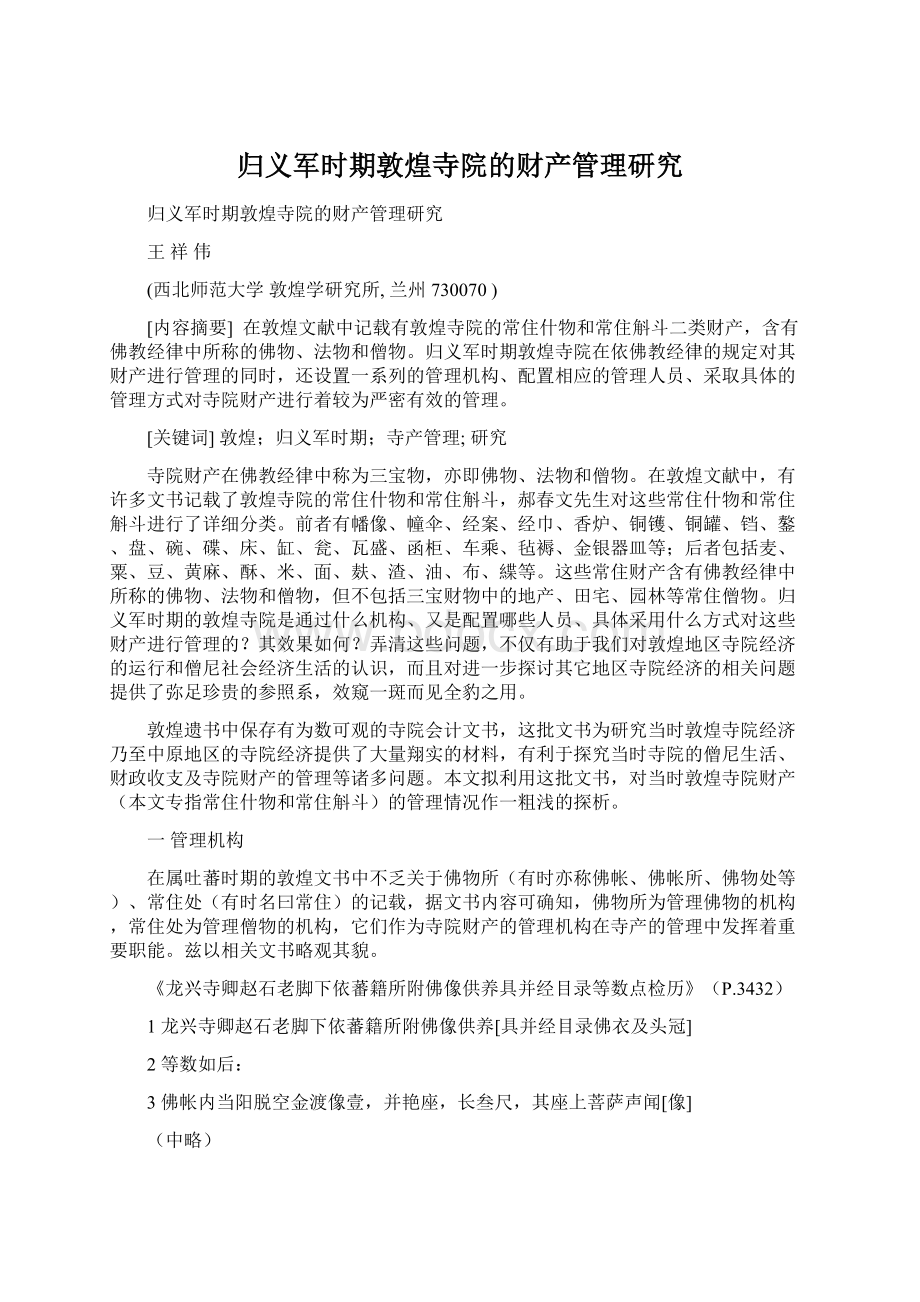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
王祥伟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兰州730070)
[内容摘要]在敦煌文献中记载有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二类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在依佛教经律的规定对其财产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置一系列的管理机构、配置相应的管理人员、采取具体的管理方式对寺院财产进行着较为严密有效的管理。
[关键词]敦煌;归义军时期;寺产管理;研究
寺院财产在佛教经律中称为三宝物,亦即佛物、法物和僧物。
在敦煌文献中,有许多文书记载了敦煌寺院的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郝春文先生对这些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进行了详细分类。
前者有幡像、幢伞、经案、经巾、香炉、铜镬、铜罐、铛、鏊、盘、碗、碟、床、缸、瓮、瓦盛、函柜、车乘、毡褥、金银器皿等;后者包括麦、粟、豆、黄麻、酥、米、面、麸、渣、油、布、緤等。
这些常住财产含有佛教经律中所称的佛物、法物和僧物,但不包括三宝财物中的地产、田宅、园林等常住僧物。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寺院是通过什么机构、又是配置哪些人员、具体采用什么方式对这些财产进行管理的?
其效果如何?
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地区寺院经济的运行和僧尼社会经济生活的认识,而且对进一步探讨其它地区寺院经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系,效窥一斑而见全豹之用。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为数可观的寺院会计文书,这批文书为研究当时敦煌寺院经济乃至中原地区的寺院经济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有利于探究当时寺院的僧尼生活、财政收支及寺院财产的管理等诸多问题。
本文拟利用这批文书,对当时敦煌寺院财产(本文专指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的管理情况作一粗浅的探析。
一管理机构
在属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不乏关于佛物所(有时亦称佛帐、佛帐所、佛物处等)、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的记载,据文书内容可确知,佛物所为管理佛物的机构,常住处为管理僧物的机构,它们作为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在寺产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职能。
兹以相关文书略观其貌。
《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P.3432)
1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佛衣及头冠]
2等数如后:
3佛帐内当阳脱空金渡像壹,并艳座,长叁尺,其座上菩萨声闻[像]
(中略)
16半,阔二尺,故。
经目录如后:
大般若经壹部,陆伯卷。
大方广佛花严经
(中略)
57佛衣及头冠数如后:
佛头观铜镀金柒宝钿并绢带壹,又头冠壹,锦
(后略)
该文书内容包括佛像供养具、佛衣及头冠、佛经,属佛教经律中的佛物和法物,而这些佛物主要藏于龙兴寺佛帐内,显然佛帐所为佛物的管理机构。
另北图鸟字84号《丑年—未年某寺得付麦油布历》中18行有“普光寺书佛帐所领得诸物色七宗布两匹”;P.3422中2—3行有“于灵图寺便佛帐麦壹拾伍硕”;S.1291中2行有“佛物处便麦肆硕”;S.1475(8v,9v)2行有“今于灵图佛帐所便麦叁硕”及S.1475(9v,10v)至S.1475(15v,16v)中均有向灵图寺佛帐所便麦的记载,这里佛帐所作为佛物的管理机构而经营便贷等业务的职能表现得极为淋漓透彻。
此外,关于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的记载亦不乏其有。
P.2583《申年比丘尼修德等施舍疏》(七)中3行有“布一匹施入报恩寺常住。
”4行有“花曡子花钵子一施入灵修寺常住。
”S.6829(4v)中2行有“今于永康寺常住处取栛篱价麦壹番驮”;P.2686中1—2行有“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硕,粟捌汉硕”;S.6233中2行有“报恩常住为无牛驱使”;P.3410中23行“报恩寺常住大床壹张”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文书的年代都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内容主要是便贷、领取、施舍。
在其后的归义军时期,这些业务活动在寺院仓库体系中表现的更为普遍,亦即仓库由寺院财产的储存所演变为集储存与管理为一体的管理机构。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诸寺的会计文书,其中关于净土寺的常住什物历、常住斛斗入破历保存最为完整,下面就以净土寺的文书为主,并兼及其它寺院的相关文书来分析这一变化过程。
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是一件完整的会计文书,记载了从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净土寺诸色入破算会情况,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移录部分如下:
1净土寺直岁保护。
2右保护,从甲申年正月壹日已后,至乙酉年正月壹日已前,众
3僧就北院算会,保护手下承前帐回残,及自年田收、园税、梁
4课、利润、散施、佛食所得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
5布氎纸等,总壹仟叁佰捌拾捌硕叁胜半抄。
(中略)
16捌伯肆拾陆硕叁斗玖胜半抄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布氎纸,承前帐回残入:
(中略)
27伍伯肆拾壹硕玖斗肆胜麦粟油面黄麻麸查豆布等,自年新附入:
(中略)
35伍伯叁拾玖硕肆斗肆胜麦粟油面黄麻麸查豆布等,自年新附入:
(中略)
245壹伯陆拾捌硕陆斗捌胜半麦粟油苏面黄麻麸查豆等,沿寺修造诸色破用:
(中略)
440壹仟贰伯壹拾玖硕陆斗肆胜半半抄麦粟油苏米面黄麻麸查豆布緤纸等。
破除外应及见在:
(后略)
本件文书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四柱结算方式,这种结算法的创立时间,前人多有论述。
关于四柱结算法就该文书内容可具体表述为:
“前帐回残+自年新附入-诸色破用=见在”。
四柱结算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是我国会计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提高了当时财务活动的效率,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文书中的核算内容基本上全为常住斛斗之属,包括上年盈余(前帐回残)、当年新入、支出(诸色破用)和结余(见在),一年一算会,当为净土寺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常住斛斗收入的全部,那么这些斛斗的管理机构又是谁呢?
下面依据P.2049V的内容将这一年内净土寺的收入来源列表如下来讨论本问题。
类
别
品名
利
润
春硙秋
硙
散
施
经儭
斋儭
念
诵
佛
食
梁
课
地
课
神佛僧料
菜
价
交
换
麦
—
—
—
—
—
—
—
—
—
西仓麦
—
粟
—
—
—
—
—
—
西仓粟
—
油
—
面
—
粗面
—
黄麻
—
—
麸
—
查
—
豆
—
—
—
西仓豆
—
布
—
—
生氎
—
由上表明了,净土寺西仓收入全为利润所得,并且对西仓麦、粟、豆的收入特别加以说明,这种现象在净土寺其它算会牒P.2040V、P.3234V(11)、P.2032V等文书中无一例外,且破支中凡属于西仓者亦俱特加标注,如前几件文书中有“西仓粟入”、“西仓麦入”、“西仓豆破”等。
但无论是破支还是入收,西仓仅有麦、粟、豆,而其它未注明归属者除麦、粟、豆外,还有油、面、粗面、黄麻、麸、渣、布、纸、氎等,亦即这些斛斗一部分归西仓管理,另一部分统属于其它机构。
这一现象在P.3234V(6)等文书中亦反映得非常清楚。
仔细爬梳整理敦煌文书中的寺院会计文书,我们不难发现有关净土寺东库、库、常住库等的记载甚为频繁,如下表:
材料来源
年代
库别
库存物品
S.6452(4)(6)(7)
十世纪中
常住库
油、面、黄麻、粟
P.3234背
(1)
982年
库
麦、粟、油、面
P.3234背
944年
东库
豆、黄麻、麻、麦
净土寺寺库名目多样,常住库与东库可能为同一指的,上表表明,其储存物除麦、粟、豆、黄麻等初级原料外,还有油、面、麸、渣等成品或半成品,这些内容与前述未注明归属者相吻合,至此,我们可以认为:
前述会计文书中未详管理机构的斛斗可能属东库(常住库)所管。
前面已经提及,西仓斛斗收入全为利润所得,并且对其入破都要特别注明,而东库入支情况并无此举,原因何在?
依佛教经律的规定,寺院三宝物是可以出贷的。
《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以下简称《行事钞》)曰:
“《十诵》,以佛塔物出息,佛言:
听之。
”这就为寺院和僧尼放高利贷打开了方便之门,敦煌佛教寺院和僧尼成为高利贷者,敦煌文献中不胜枚举(如前引文书S.1475、P.3422、S.1291、P.2686等)。
既然佛物、法物和僧物可以出贷生息,那么会计文书中的利润收入就可以理解为很可能是由敦煌寺院的常住斛斗出贷的结果。
同时,内律又规定,三宝财物不得互用。
《行事钞》曰:
“《四分》,瓶沙王以园施佛,佛令与僧等故。
知三宝不得互用,便劝施僧,僧犹得供佛法也。
”不但三宝财物不能互用,三宝物出贷的利息收入亦不能互用,佛物息收归佛,法物息收归法,僧物息收归僧。
《行事钞》卷中《随戒释相篇》云:
“《十诵》、《僧祈》,塔物出息取利,还著塔物无尽财中;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等。
僧物文中例同,不得干杂。
《十诵》,别人得贷塔僧物。
若死,计直输还塔僧。
《善见》,又得贷借僧财物作私房。
……。
《五百问》云:
佛物,人贷,子息自用,同坏法身。
”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佛教寺院,虽然在诸多方面并非严格执行佛教经律的规定,但其在某些方面亦会因循,起码在形式上如此。
既然内律规定佛物、法物、僧物及它们的出贷利息收入都不能混杂乱用,特别是佛物的特殊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故而在敦煌寺院中,它们被明确地剔剥分离而各归其所。
据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敦煌寺院中,起码在净土寺,西仓可能是佛物及其利息收入的储存处,而东库(或常住库)是僧物及其利息收入的储藏所,至于其它寺院,依佛教经律亦应如此,只是不一定以西仓、东库的固定名称表象而已(如S.1774、S.1642、S.1776中就有大乘寺的“北仓”),佛物、僧物及其它们的利息分别保存、各有所管则应无疑。
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仓库不仅只是寺院财产的储存地,有时还作为寺院常住财产的管理机构直接经营借贷或便贷业务。
如P.3234V《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S.6452
(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正于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S.6542(4)《壬午年(982)正月四日诸人于净土寺常住库借贷油面物历》、S.6452(6)《壬午年(982)二月十三日于净土寺常住库内黄麻出便于人名目》、S.6452(7)《壬午年(982)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等,这些借贷和便贷业务均由寺院仓库直接经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注意到:
吐蕃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的便贷,一般来讲,佛物向佛帐所便,如S.1475是向灵图寺佛物所便麦和青麦。
而僧物向常住(或常住处)便贷,如S.6829(4v)是向永康寺常住处便麦,P.2686是向灵图寺常住处便麦。
而到归义军时期直接向寺院仓库便贷则更常见。
这种变化是很自然的,可能只是程序上的简化而已,因为无论佛物还是僧物,它们都储存在寺院仓库之中,只不过在吐蕃时期分别由佛帐所和常住处管理,而在归义军时期可能有时由仓库直接经营,佛物所、常住处与寺院仓库在管理内容上是统一的,这一点可以通过S.1475(12v)得到印证。
1□年三月二十七日,阿骨萨部落百姓赵卿卿,为无
2种子,今于灵图寺佛帐家物内,便麦两汉硕。
3其麦自限至秋八月内纳寺仓足。
如违,其麦请
(后略)
赵卿卿是向灵图寺佛帐所便麦,至归还时送纳寺仓,显见佛物保藏于灵图寺仓无疑,并由佛帐所管理亦是事实。
此外,我们注意到,在归义军时期,“常住处”与“佛物所”分别作为僧物和佛物的管理机构的功能依然存在,如P.2613中55至56行有“小银泥旙子伍口,在索僧政院佛帐子内。
”又S.0372《丁亥年(927?
)正月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中有“常住”记载,详见以下录文。
1右合从丙戌年正月一日以后,至丁亥年正月一日以前中
2间一周年沿常往(住)所用
3总六百六十三石三斗一升七合油面麦粟麻滓粗面黄麻等
4三百二十六石八斗七升麦
5一百三十五石九斗三升粟
6四十八石六斗三升黄麻
7两石六斗七合油
8一百七石九斗三升白面
9三十八石五升谷面
10一石三斗粗面
11二石麻滓
显而易见,“常住”在该时期作为僧物的管理机构的功用并未丧失,其管理的斛斗内容比较全面,除麦、粟外,还有黄麻、油、白面、谷面、粗面、麻滓,这与前论净土寺东库所管内容相一致。
该文书暂不敢臆断是哪寺的入破历算会稿,若属净土寺,则更进一步证明前述净土寺东库是僧物的储存所和管理机构的论断的正确性。
若不属净土寺,则说明前述观点在敦煌寺院具有普遍性。
敦煌文书中还有仓司(见S.5806)、常住仓司(见S.4701)、南仓司(见P.4694)、西仓司(见P.2032v)等的记载,它们有可能是负责寺院仓库的管理机构或寺仓的具体办公地点。
兹据P.2032v(十一)试作一分析。
331净土寺西仓司愿胜广进等。
(中略)
366上件计得麦壹伯硕,计粟
367伍伯玖拾捌硕柒斗,计豆贰
368伯捌拾壹硕壹斗伍升。
369得当年人上利麦及豆替贰拾叁
370硕伍斗,得人上利粟及豆替伍拾贰硕贰
371斗伍升,得人上利豆伍拾叁硕陆斗伍胜。
372两件通计得本利麦壹伯贰
373拾[叁]硕伍斗,得粟陆伯伍拾硕玖
374斗伍升,得豆叁伯叁拾肆硕捌斗。
(后略)
前面已经论及,净土寺西仓收入均为利润入,这些利润可能就是佛物出贷后的利息收入,且西仓为净土寺佛物的管理机构。
由本件文书内容可知,西仓司愿胜广进经手的收入全为本利所得,这与前述观点是一致的,故西仓司可能就是具体负责西仓佛物出贷生息的机构,其职能与佛物所大致相当。
又P.4694中10行有“南仓司祥法律阴法律二人”;S.4701中第2行为“先执仓常住仓司法律法进、法律惠文等”,则测知“法律”为仓司中主要负责人的僧职。
可见,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有佛物所(有时亦称佛帐、佛帐所、佛物处等)、常住处(有时名曰常住)、仓司、常住仓司、南仓司、西仓司、都司(见后文)等,这些机构的设置,使得寺产的管理井然有序,从而保证了寺院生活的正常进行。
二管理人员
有了一套管理机构,就得有相应的管理人员来操作,通过对有关敦煌文书的检阅,可知在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经济活动中由不同的管理人员来主持运作,从而取得对寺院财产的有效管理。
《庚辰年(920或980)十一月算会仓麦交付凭》(S.5806)
1庚辰年十一月就殿上算会,旧把仓僧李校(教)授、应会
2四人等,麦除破外,合管回残麦陆拾壹硕肆斗柒升,
3现分付新把麦人仓司惠善、达子四人等,一一为凭。
4把麦人达子(押)
5把麦人法达(押)
6把麦法云(押)
7把麦人惠善(押)
(后残)
该文书表明寺库有专门的把麦人,在上届把麦人和下届把麦人之间有一交接手续,即将寺院仓库中过去支出与现存的财务数目登入交接凭据之中。
把麦人的僧职似很高,如“把仓僧李校授”,但在归义军时期,僧官职位泛滥,谢重光先生指出“可能有的僧政、法律已成为虚衔”,此处教授可能亦为虚衔,并非象吐蕃时期的“教授”那样位尊权重。
在交接时,新把麦人还要在凭据上画押为证。
关于仓库的管理人员常见的还有“所由”或“所由法律”,并且所由有不同的级别,诸寺有所由,都司亦有所由,吐蕃时期的文书北图碱字59号《辛丑年(821)二月龙兴寺等寺户请贷麦牒及处分》
(二)中都教授正勤的批语中之“所由”既指“都司仓所由”,而(六)中“付本寺所由”便指“龙兴寺所由”,并据此我们可知“所由”为寺院仓库收支的具体负责人,如P.3223《永安寺法律愿庆与老宿绍建相诤根由责勘状》就是仓司所由绍建因不与法律愿庆借贷寺仓谷麦而发生冲突的记载。
在归义军时期,“所由法律”名称甚为普遍,这可能亦与当时的僧官泛滥有关,故在所由后附上“法律”一职。
寺院盘点财物时,在判官主持下,所由法律、寺院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直岁及全寺徒众等共同进行,如下引点检文书S.1774《后晋天福七年(942)大乘寺法律智定等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状》等。
在众多的斛斗入破历文书中亦有尊宿、法律、判官、直岁、徒众等,如P.2974V、P.2049V。
与点检历不同,入破历中不见寺院三纲,但既然全体徒众都得参予,那么三纲亦应不例外。
全体徒众参加寺院财产的盘点、核算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寺院在财政管理上的民主性。
在寺院财产管理中,执事僧直岁是最常见、最基层的管理者。
但是直岁位轻任重,这在他参予盘点、核算等活动中得到反映,在寺产的核算活动中他的职能相当于今天的会计。
另外,北图碱字59号中有都教授正勤直接下给龙兴寺所由的判;P.2838
(1)《唐中和四年(884)正月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后有都僧统悟真之判,说明寺院的财产结算活动及其它经济活动有时要直接接受都僧统(吐蕃时期称都教授)的领导。
姜伯勤先生指出:
“都僧统(都教授)接受各寺的年度会计报告,批准各寺的年终决算。
”既然作为都司最高僧官的都僧统(都教授)对各寺院的财产核算进行着最终决策,那么都司亦是为敦煌寺院财产的最高管理机构。
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既有普通的把仓人、直岁、仓司所由等执事僧,又有寺院三纲、法律、判官等僧官,乃至敦煌地区都司的最高僧官都僧统,他们处于不同的职位,对寺院财产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管理。
寺院对寺产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故在选人时亦非常谨慎,为防止财产流失、被盗,寺院经律规定寺院必须选择诚实能净持戒者作为寺产的基本管理单位(如佛物所、常住处、仓库等)的管理人员。
《行事钞》说:
“故《宝梁》、《大集》等经云,僧物难掌,佛法无主,我听二种人掌三宝物:
一阿罗汉,二须陀洹。
所以尔者,诸余比丘戒不具足,心不平等,不令是人为知事也。
更复二种,一能净持戒,识知业报。
二畏后世罪,有诸惭愧及以悔心。
如是二人,自无疮疣护他人意,如此甚难。
”如是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者俱应是德操、修养兼备的僧官,抑或普通僧人,他们通过各司其职、分级管理对寺院财产进行着严密管理,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以权谋私现象的存在(详情见后文)。
三管理方式
前面讨论了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我们了解到,这些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职能与职责,对寺产进行着缜密的管理.但是,若要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在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兼备的同时,必须具备一套高效可行的管理方式。
(一)出便
敦煌文书中有众多便物历,出便对象多样不一,有麦、粟、豆、黄麻,还有油、面等。
有以个人名义出便的,如дx.1449《年代不明王法律出便于人名目》;北图83:
1901《辛酉年(961)二月九日僧法成出便于人抄录》;P.2932《甲子乙丑年(964—965)翟法律出便于人名目》;S.4654(IV)《丙午年(946)金光明寺庆戒出便于人名目》等,这些便物历的出便利率皆为50%,但我们不易确定其是僧人个人财产还是寺院财产,故不详论。
便物历中有许多系关于寺院财产的出便,如S.5873V+S.8567《戊午年(958)灵图寺仓出便于人名目》;P.3234V《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S.6452(6)《壬午年(982)二月十三日净土寺常住库内黄麻出便于人名目》;S.6452(7)《壬午年(982)三月六日净土寺库内便粟历》等,由于文书较长,恕不移录。
这些文书的结构相同,出便利率皆为50%(此利率仅是依据出便的本金和归还时的本利数来计算的,没有考虑出便期限,若将出便期限考虑在内,利率会有相应的变化),均至秋归还,如S.5873V+S.8567《戊午年(958)灵图寺仓出便于人名目》第二行载:
“当寺僧谈会便粟两硕,至秋三硕(押)”,其中P.3234V、S.5873V+S.8567中每一出便名目后还要画押,而S.6452(7)、S.6452(6)中并无此程序,这些便历一般还注明口承人(担保人)、见人等,可见在出便历中细节是较为统一严密的。
寺院通过出便常住斛斗的方式,一方面将常住百姓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一方面又通过高利贷获得巨额利息收入。
(二)借贷和贷
S.5845《己亥年(955)二月十七某寺贷油面麻历》、S.6452
(2)《辛巳年(981)十二月十三日周僧政于常住库借贷油面麻历》、S.6452(4)《壬午年(982)正月四日诸人于净土寺常住库借贷油面麻历》等借贷历或借历中,S.5845中14行贺安定和弘渐下有画押,而其它地方均无画押亦无签字,但S.5945《丁亥年(987?
)长史米定兴于显德寺仓借回造麦历》中既有指印又有签字。
见下:
1丁亥年四月三日,长史米定兴于显德寺仓借
2回造麦壹佰硕(印)口承二判官(签字)六月十四日又显
3德寺仓借回造麦十九硕,付硙户樊善友(签字)
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当时寺院财产的借贷历中手续并非严格统一,并且这些借贷(或借)历中无利息说明,但在一些贷绢、褐、布等之类的借贷契据中亦有“利头”的规定,并且若在规定之日不能按时归还,一般则要“于乡元生利”。
这种贷契与前贷便契在结构上亦是基本相同的。
关于“便”、“贷便”、“借贷”之间的区别比较含混,对此前贤早有论述。
而对这些契据中的利息规定,唐耕耦、陈国灿、余欣、那波利贞、堀敏一等国内外学者有过精辟的讨论,见仁见智,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借贷历使得寺院财产的破支在有了精确的明细帐的同时,保证了寺产的追回而不致于流失。
(三)算会
敦煌会计文书中有众多诸色入破历算会稿,但大多残缺不全,笔者仅见到P.2049V为净土寺二件完整的算会牒,除前引文书《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外,另有《后唐长兴二年(931)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愿达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由于这些文书结构基本相似,内容大致相同,故我们以《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为代表来分析敦煌寺院对常住财产的算会情况。
(录文见前)
如前所述,该文书是从甲申年正月一日至乙酉年正月一日间净土寺诸色入破算会,体例为一年一结算。
结算的内容主要是关于麦、粟、豆、油、苏、米、面、黄麻、麸、查、布、緤、纸等,结算方式是:
上年基数+当年收入-当年支出=当年结余
而当年结余在下一年又作为上年基数参与核算。
在核算中,净土寺全体僧众都得参加,该文书末尾就有1位直岁、16位徒众、3位释门法律和1位老宿的签名,算会结束后,僧众在算会稿中签名画押,最后形成一篇上报会计牒。
这种核算方式在当时敦煌寺院具有普遍性,如安国寺(P.2838
(2))、报恩寺(P.2821)、大乘寺(S.1625)等,甚至都司下管理儭利分配的机构—儭司亦是如此(见P.2638)。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算会并非皆为一年一结算,如P.2821就是报恩寺从丁丑年正月一日至庚辰年正月一日三年之间的算会。
除了全寺统一进行的总结性核算外,一寺内还有就某一物品或个人所管的入破算会牒和入历、破历等,如S.5806是关于仓麦的算会交付;S.4702、P.3290为黄麻的算会;P.3234V
(2)为油的入破历;P.3234V(9)系广进手上面破情况;S.1600(1v)为灵修寺麦破历;S.6829V系因修造而斛斗、布等的破历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不赘叙。
通过定期的核算,对寺院常住财产的收入来源、支出方向及现存在总体上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