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docx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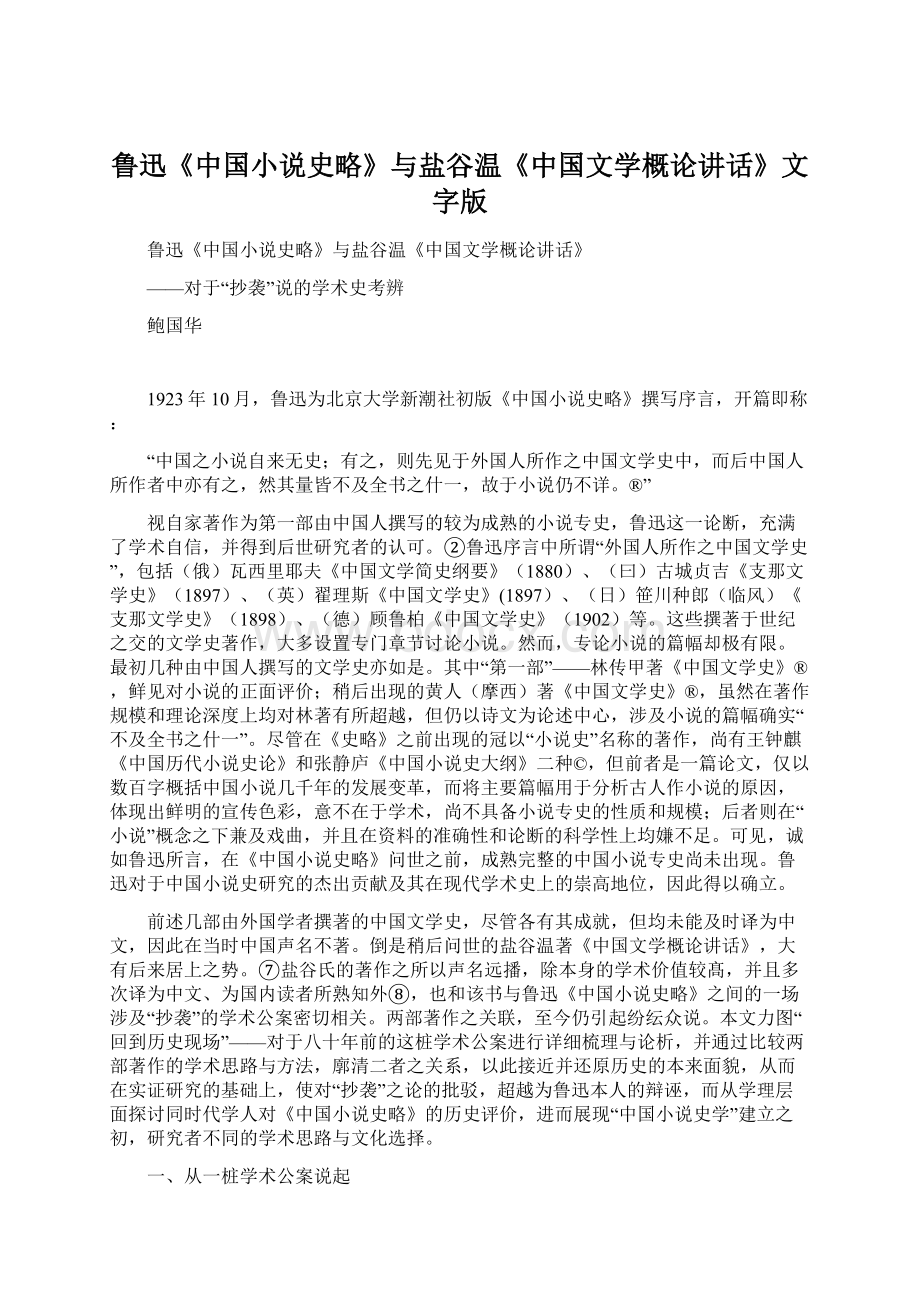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
鲍国华
1923年10月,鲁迅为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中国小说史略》撰写序言,开篇即称: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
视自家著作为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较为成熟的小说专史,鲁迅这一论断,充满了学术自信,并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认可。
②鲁迅序言中所谓“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包括(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曰)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英)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897)、(日)笹川种郎(临风)《支那文学史》(1898)、(德)顾鲁柏《中国文学史》(1902)等。
这些撰著于世纪之交的文学史著作,大多设置专门章节讨论小说。
然而,专论小说的篇幅却极有限。
最初几种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亦如是。
其中“第一部”——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鲜见对小说的正面评价;稍后出现的黄人(摩西)著《中国文学史》®,虽然在著作规模和理论深度上均对林著有所超越,但仍以诗文为论述中心,涉及小说的篇幅确实“不及全书之什一”。
尽管在《史略》之前出现的冠以“小说史”名称的著作,尚有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二种©,但前者是一篇论文,仅以数百字概括中国小说几千年的发展变革,而将主要篇幅用于分析古人作小说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宣传色彩,意不在于学术,尚不具备小说专史的性质和规模;后者则在“小说”概念之下兼及戏曲,并且在资料的准确性和论断的科学性上均嫌不足。
可见,诚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国小说专史尚未出现。
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及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前述几部由外国学者撰著的中国文学史,尽管各有其成就,但均未能及时译为中文,因此在当时中国声名不著。
倒是稍后问世的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⑦盐谷氏的著作之所以声名远播,除本身的学术价值较髙,并且多次译为中文、为国内读者所熟知外⑧,也和该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间的一场涉及“抄袭”的学术公案密切相关。
两部著作之关联,至今仍引起纷纭众说。
本文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对于八十年前的这桩学术公案进行详细梳理与论析,并通过比较两部著作的学术思路与方法,廓清二者之关系,以此接近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使对“抄袭”之论的批驳,超越为鲁迅本人的辩诬,而从学理层面探讨同时代学人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评价,进而展现“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之初,研究者不同的学术思路与文化选择。
一、从一桩学术公案说起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作为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从1920年12月起陆续油印编发,共17篇;后经作者增补修订,由北大印刷所铅印,内容扩充至26篇。
1923年12月,该书上卷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下卷出版于次年6月。
《中国小说史略》至此得以正式刊行。
⑨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该书问世之初,并未引起评论家和研究者的重视。
鲁迅在当时主要以小说家闻名,其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免为小说家的盛名所掩。
涉及该书的第一次论争也并未发生在学术研究范围内,而是陈源(西滢)在《闲话》及与友人的通信中,指责《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部分。
1925年11月21日,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称:
“现在著述界盛行“⑩窃”或“抄袭”之风,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一般人自己不用脑筋去思索研究,却利用别人思索或研究的结果来换名易利,到处都可以看到。
……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
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
要举个例么?
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
“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
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
……
“‘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
文学史没有平权的。
文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
……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⑪窃?
”
1925年10月1日起,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报头使用凌叔华所作画像一幅。
10月8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儂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像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
1925年11月7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发表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
11月14日《京报副刊》又刊登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花之寺》抄袭契诃夫小说《在消夏别墅》。
陈源这篇《闲话》以“劉窃”为主题,概源于此,实有为凌叔华开脱之意。
陈源与鲁迅因同年的“女师大事件”而交恶,因此怀疑上述两篇文章皆出于鲁迅之手,于是旁敲侧击,暗指鲁迅抄袭。
虽然“整大本的剽窃”一说的矛头所向,文中没有明言,但“思想界的权威”一语,实指鲁迅而言。
®然而既然陈源未曾指名,鲁迅“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略作回应:
“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
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
次年一月,陈源在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通信里,重提“剽窃”之事,并将矛头明确指向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
“他常常控告别人家抄袭。
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
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
‘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
这组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的私人通信,内容主要是陈源和周作人就“女师大事件”的余波展开的若干问答,以及试图在陈周之间进行调解的张凤举的来信。
不过,陈源在批评周作人之余,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鲁迅,围绕“剽窃”大做文章。
因“女师大事件”交恶于前,怀疑鲁迅著文指责凌叔华“抄袭”在后,陈源此举也就不难理解。
针对上述攻击和指责,鲁迅随即发表《不是信》一文予以驳斥: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
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
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
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
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
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
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
®”
在上述回应之后,这场纷争暂时偃旗息鼓。
然而鲁迅对“票窃”之说一直耿耿于怀。
直到十年后《中国小说史略》由增田涉译为日文出版,鲁迅称: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
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
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
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的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从这段充满了洗刷屈辱的快意之情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所谓“剽窃”事件给鲁迅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压抑与伤害。
其实,陈源又何尝不是在遭遇“女师大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冲突所造成压抑与伤害中,慌不择言,以致听信他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系‘剽窃’而来”的传言,不经查证不假思索,即以之作为攻击鲁迅的“有力”证据。
假使陈源认真阅读鲁迅和盐谷温的著作,再加以比较,恐怕不会犯此“常识错误”。
®此后,鲁迅和陈源都不再提及这场论争。
倒是在鲁迅去世的当年,胡适在复苏雪林信中重提此事,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鲁迅自有它的长处。
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
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亻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之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
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
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
在肯定鲁迅的学术贡献、驳斥“抄袭”说的同时,胡适指出陈源(即信中所谓“通伯先生”)之所以得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错误论断,源于张凤举的“小人播乱”。
张凤举其人及其在这次论争中所作所为,已有学者著文考证。
®应指出的是,尽管是私人通信,但胡适确信以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其书信日记等私人文字势必将公诸于世,与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样,被后人视为重要史料。
因此,胡适将书信日记也作为著作来经营,下笔审慎,结构精心。
可见,在与苏雪林的通信中,胡适将“抄袭”说的始作俑者归于旁人,实有为陈源开脱之意,同时将罪责坐实在“小人张凤举”身上,以正视听。
不过,使陈源“误信其言”的很可能不只张凤举一人。
时在北大任职的顾颉刚亦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并以此告知陈源,才引发陈源著文指责鲁迅“抄袭”。
尽管几位当事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此均讳莫如深,但1949年,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刘文典却在一次演讲中加以披露。
刘文典的演讲稿没有发表,今已不存。
但在刘氏演讲的第二天,即1949年7月12日,昆明《大观晚报》发表《刘文典谈鲁迅》一文,记录了刘氏演讲的要点,其中涉及顾颉刚与“抄袭”说云:
“顾颉刚曾骂鲁迅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某的著作,刘为鲁辩护,认为鲁取材于此书则有之,抄袭则未免系存心攻击。
®”
刘文典对所谓“抄袭”说持否定意见,但并未在演讲中指明“顾颉刚曾骂鲁迅”“抄袭”的消息来源。
刘文典之后,所谓“抄袭”说绝少为人提起。
直到近半个世纪后,顾颉刚之女顾潮在回忆父亲的著作中重提此事:
“在‘女师大学潮’中,鲁迅、周作人坚决支持学生的运动,而校长杨荫榆的同乡陈源为压制学生运动的杨氏辩护,两方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鲁迅与陈源由此结了深怨。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
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
……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
®”
顾潮的上述论断源出当时尚未公开的《顾颉刚日记》。
2007年,日记经整理正式出版,使顾颉刚持“抄袭”说的真相得以公诸于世。
在1927年2月1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按语云:
“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
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
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
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
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
®”
假使如顾氏所言,陈源著文宣扬“抄袭”说实源出顾颉刚,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胡适所指认的张凤举,那么,在前引致苏雪林信中,胡适力图为之开脱的就不只陈源一人了。
而且,顾颉刚一直将首倡“抄袭”说并告知陈源作为与鲁迅结怨的缘由,言之凿凿。
®然而目前尚无确证表明两人之结怨源出于此。
®”
以上之所以率先讨论这桩学术公案,意在“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并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尽管“抄袭”说不符合事实,但在当时持此说者却不乏其人。
然而无论是陈源、张凤举,还是顾颉刚,各自的出发点却未必相同,似不可概而论之,其中尤以顾颉刚的态度格外值得关注。
从上文摘录的顾氏日记看,顾颉刚持“抄袭”,既不像陈源那样出于私怨,为争一时之意气而完全不顾事实(在顾氏看来,显然是宣扬“抄袭”说为因,和鲁迅结怨为果)®,亦非怀有“小人”张凤举式的“播乱之心”(顾氏当时与鲁迅同为“语丝社”成员,虽彼此过从不密,但尚未结怨,刘文典所谓“荐心攻击”之说不确)。
而且,以顾颉刚为人为文之严谨,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歪曲事实、搬弄是非的可能性亦极小。
因此,顾氏之认定“抄袭”,很可能是出于自家的学术判断,源于对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思路和方法缺乏充分的了解与认同所造成的“误读”。
®因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态度,在表面的人事纠葛的背后,尚有从学术史的高度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考察顾颉刚的态度,也有助于使对“抄袭”说的批驳,超越单纯的为鲁迅本人的辩诬,获得进行更深层的学理探讨的可能。
二、顾颉刚的态度
前文已述,顾颉刚认为《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内容上有相沿袭处,据此判定鲁迅“抄袭”,但只在友朋间的闲谈中述及。
陈源却“听者有心”,不仅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加以披露,而且踵事增华,放大为“整大本的剽窃”,终于导致事态的恶化。
这恐怕也是顾颉刚所始料未及的。
尽管顾氏持“抄袭”说,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评价不高,但其立场却不曾公开表露。
直到十几年后,顾颉刚应邀撰写《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才得以公开自家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判断。
该书出版于1942年,其中设专章考察俗文学史(包括小说史与戏曲史)和美术史研究,在专论小说史的一节中,分别就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学术成就做出评价:
“胡适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贡献最大,在亚东图书馆所标点的著名旧小说的前面均冠以胡先生的考证,莫不有惊人的发现和见解。
……所论既博且精,莫不出人意外,入人意中。
对于中国小说史作精密的研究,此为开山工作。
“周树人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最初亦有贡献,有《中国小说史略》。
此书出版已二十余年,其中所论虽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现在尚无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说史读本出现。
“郑振铎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的成就也极大,当为胡适先生以后的第一人。
®”
顾颉刚对于胡适和郑振铎的小说史研究较多赞美之词,而对于鲁迅的态度则有所保留,用语颇为审慎,“小说史读本”一语,足见顾氏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基本判断,前后论断恰堪对照。
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和胡适在治学方面均做到了穿越“古今”、取法“中西”,二人又都对小说史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分别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格局和自家的学术地位,成为小说史学的开拓者。
同时,知识结构、学术理念、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又使二人的研究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分别以独具会心的艺术判断和严密精准的考证见长;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威望,使中国小说史学在建立之初即呈现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
可以说,鲁迅与胡适治学路径不同,成就却难分轩轾。
而郑振铎尽管也在小说史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其学术视野及理论开创性较之鲁、胡二人均略有不及。
由此看来,顾颉刚的上述论断,似乎有失公允。
而联系到鲁顾二人的在厦门和广州的结怨,顾氏对《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不高,很容易给人以夹杂了私人恩怨的印象。
然而,《当代中国史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史著作,作者不因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情感好恶而影响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判断。
不因人而废文的态度,使顾颉刚对于政治上“左倾”的郭沫若和时已与其交恶的傅斯年均作出极高的评价,奉前者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对后者之《性命古训辨证》亦颇有好评®。
因此,造成在学术判断上的“杨胡抑鲁”,与顾颉刚本人对于小说史学的学术定位密切相关。
顾氏治学,受胡适影响极深,奠定其学界地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也得益于胡适著述的启发。
此后虽以《古史辨》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但对胡适的授业之功依旧念念在心。
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之新范式的创建者,胡适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义。
@小说史学之于胡适,首先是其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证”视野下的小说,首先也是作为史料,而不是以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文类的身份进入其学术视野。
谈艺既非胡适所长,亦非其所愿。
虽然上述思路在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中只是初露端倪,但经其追随者的进一步倡导与发挥,逐渐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范式,也使小说史学在建立之初即呈现出史学化的趋向。
顾颉刚在胡适的这—学术设计中立论,将小说史纳入“史学史”的范畴之中加以讨论,以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评判尺度考量小说史写作的理论创见与文化职能。
《当代中国史学》之小说史专节在逐一点评各家的学术贡献之后,道出了自家对于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期待:
“因为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
®”
可见,顾颉刚在“史学”前提下讨论小说史写作,先验地带有”重史轻文’的倾向,视小说为可信之史料,主张利用小说考证社会史,从而将艺术判断排除在小说史研究的视野之外。
依照这一评判标准,《中国小说史略》一类以审美感受见长的小说史论著,较多描述与概括,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考察,给人以空疏之感,虽“首尾完整”,但深度不足,视之为“读本”尚可,史学创见则有限,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类概述文类特征的著作大同小异,难免有相互沿袭之处。
这正是顾颉刚认定鲁迅“抄袭”的依据所在。
《中国小说史略》学术价值因此得不到顾氏的充分认可。
与顾颉刚可堪对照的是,胡适一直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好感,不仅在前引复苏雪林信中为鲁迅辩诬,在为自家著述所作的序言中,亦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和鲁迅的学术创见颇为肯定,评为“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表面上看,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
然而,胡适着力关注的仍是鲁迅在小说史料方面的贡献。
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大加赞赏,不过是因为该书体例完整,能够为其小说考证提供可依循的历史线索而已。
对于鲁迅在小说审美批评方面的建树,则较为隔膜。
@有趣的是,出于相近的小说史研究理念和学术定位,胡适与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评判,均以“考证”为主要标尺,而依据相同的标尺,竟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一方指斥鲁迅缺乏个人创见,有抄袭之嫌;另一方则认为鲁迅在考证方面的胜于盐谷温,据此为其洗刷辩白。
可见,“考证”无法作为衡量鲁迅小说史研究之成败得失的有效标准。
不过,“考证”的标准却反证出《中国小说史略》的理论特色。
尽管鲁迅在小说史料的稽考上颇为用力,这方面的成绩也得到时人的大力揄扬®,但《中国小说史略》并不以此见长,维系该书学术生命的不是对史料的占有,而是基于自家的学术眼光,对史料作出重新的“发现”。
鲁迅之于考证,非不能也,实不甚为也,其长处在于通过寻常作品和寻常史料,产生不同寻常的学术创见。
特别是凭借自家对于小说艺术的超凡领悟力,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精准的判断,往往寥寥数语,或成不刊之论,这是其小说史研究最为人所称道处,却也是胡适等学者不愿为或不擅为的。
与胡适等赋予小说史研究以明确的史学归属和方法论依据不同,鲁迅治小说史,有专家之长,却素无专家之志。
鲁迅将小说史研究视为其整体的文学事业的一部分,着力于发掘作品的审美质素。
小说家的身份,赋予其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感性资源,促成了他审视小说的独特眼光,更铸就了鲁迅作为小说史家的“诗性”自觉。
因此,单纯以史学标准衡量《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成就,难免凿空之弊。
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不高,还源于自家对鲁迅的文化身份及其著述的学术职能的认定。
鲁迅和顾颉刚应聘厦门大学教职后,最初尚能相安无事,且彼此间偶有往来(这在二人的日记中均有所记载),但始终不以朋友相待,交情淡薄,颇有些“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
随着嫌怨的加深,分歧也渐趋明朗。
鲁迅以顾颉刚为陈源之同道,顾颉刚则称鲁迅为“不工作派”彼此难容。
事实上,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除担任本科生教学,编写《汉文学史纲要》,提交《<漱康集>考》、《古小说钩沉》,承担《中国图书志小说》的研究外,还指导研究生并审査论文。
®可见,鲁迅并非真正的“不工作”。
之所以被讥为“名士派”®,皆因顾颉刚对鲁迅的上述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的学术价值缺乏认同所致。
在顾颉刚看来,自家与鲁迅有从事研究与教学之分,在身份上亦有学者与文人之别,而教学工作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相去甚远,文人的文化贡献亦不能望学者之项背。
®顾氏强调自家“性长于研究”,“不说空话”,而鲁迅“性长于创作”,是“以空话提倡科学者”,与己相较,“自然见绌’@,于此可见一斑。
出于学者的优越感,顾颉刚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信中,对研究与教学的价值一判高下:
“在此免不了中山大学的教书,一教书我的时间便完了。
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的人,越衰弱便越兴奋,所以别人没有成问题的,我会看他成问题。
这在研究上是很好的,但在教书上便不能。
教书是教一种常识,对于一项学科,一定要有一个系统,一定要各方面都叙述到。
若照教书匠的办法,拿一本教科书,或者分了章节作浅短的说明,我真不愿。
若要把各种材料都搜来,都能够融化成自己的血肉,使得处处有自己的见解,在这般忙乱的生活中我又不能。
所以教了两年书,心中苦痛得很。
®”
这一重研究而轻教学的立场,使顾颉刚对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类从课堂讲义脱化而成的学术著作缺乏起码的认同与敬意。
在顾氏看来,这类著作不过是常识之汇集,虽有稳健博洽之长,却不利于研究者个人创见的充分发挥,学术含量不高,亦难免空疏之弊,且相互间在体例及论述上均大体相沿,视之为粗陈梗概的教科书“读本”尚可,而难以企及严谨的学术著作的理论深度。
同样,顾颉刚以学人为自家定位,而视鲁迅为文人,以此区别两人的文化身份,知彼罪彼,所依据的也都是对于文人的评判标准。
学人的自我期许和身份认定,使顾颉刚对于胡适一脉的学院派的小说史研究更为认同,将其学术贡献置于鲁迅之上,而将《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相类同,否定其原创性。
顾氏不把鲁迅视为学术同道,对其研究成果评价不高也是势所必然。
然而在鲁迅看来,教学与研究却没有这样明显的高下之分。
文学史(小说史)这一著述体式在中国的确立,实有赖于晚清以降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对近代日本及欧美文学教育思路的移植。
®这使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一经出现,即先天地具备教材性质,承担教学职能。
晚清至五四的学人选择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大都与其在学院任教的经历有关。
随着对文学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具有新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学史开始由教材式的书写形态向专著化发展,学术价值获得了明显的提升。
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不乏在观点和体例上卓有创见者,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个性,而且实现了对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潜质的创造性发挥。
《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也是作为大学讲义。
鲁迅以小说史体式承载其学术见解,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
®然而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中国小说史略》做出修改,足可见其将该书作为学术著作经营的用心。
衡量一部文学史著作学术价值的高下,除学术水平的因素外,还有赖于作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定位。
鲁迅非常重视文学史的学术职能,希望通过文学史写作,不仅满足教学需要,更要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希望奉献流传后世的学术经典,而非只供教学的普通讲义。
®鲁迅最初应授课之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