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docx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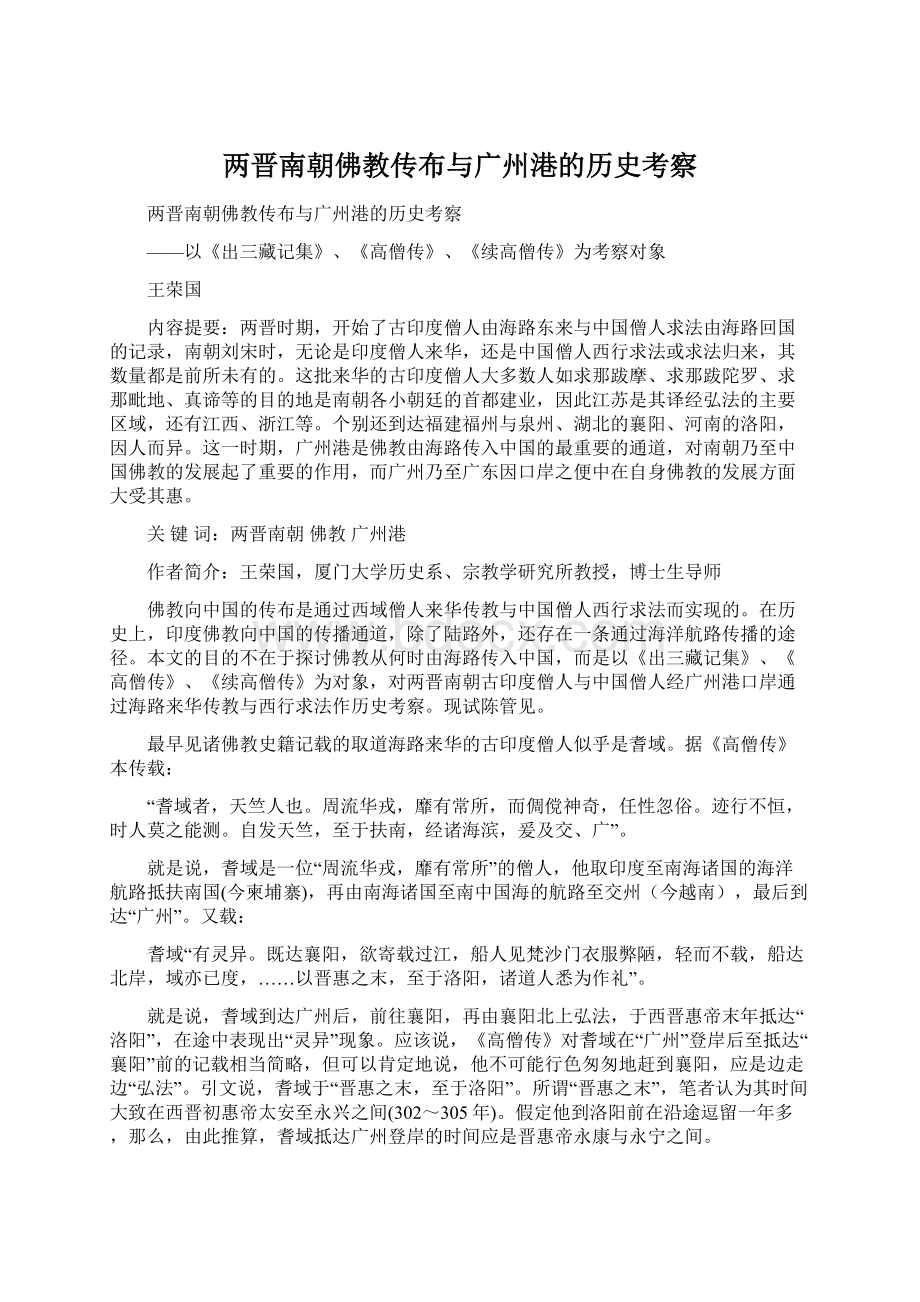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
两晋南朝佛教传布与广州港的历史考察
——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考察对象
王荣国
内容提要:
两晋时期,开始了古印度僧人由海路东来与中国僧人求法由海路回国的记录,南朝刘宋时,无论是印度僧人来华,还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或求法归来,其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批来华的古印度僧人大多数人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真谛等的目的地是南朝各小朝廷的首都建业,因此江苏是其译经弘法的主要区域,还有江西、浙江等。
个别还到达福建福州与泉州、湖北的襄阳、河南的洛阳,因人而异。
这一时期,广州港是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通道,对南朝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广州乃至广东因口岸之便中在自身佛教的发展方面大受其惠。
关键词:
两晋南朝佛教广州港
作者简介:
王荣国,厦门大学历史系、宗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佛教向中国的传布是通过西域僧人来华传教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而实现的。
在历史上,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通道,除了陆路外,还存在一条通过海洋航路传播的途径。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佛教从何时由海路传入中国,而是以《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为对象,对两晋南朝古印度僧人与中国僧人经广州港口岸通过海路来华传教与西行求法作历史考察。
现试陈管见。
最早见诸佛教史籍记载的取道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似乎是耆域。
据《高僧传》本传载:
“耆域者,天竺人也。
周流华戎,靡有常所,而倜傥神奇,任性忽俗。
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
自发天竺,至于扶南,经诸海滨,爰及交、广”。
就是说,耆域是一位“周流华戎,靡有常所”的僧人,他取印度至南海诸国的海洋航路抵扶南国(今柬埔寨),再由南海诸国至南中国海的航路至交州(今越南),最后到达“广州”。
又载:
耆域“有灵异。
既达襄阳,欲寄载过江,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船达北岸,域亦已度,……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
就是说,耆域到达广州后,前往襄阳,再由襄阳北上弘法,于西晋惠帝末年抵达“洛阳”,在途中表现出“灵异”现象。
应该说,《高僧传》对耆域在“广州”登岸后至抵达“襄阳”前的记载相当简略,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不可能行色匆匆地赶到襄阳,应是边走边“弘法”。
引文说,耆域于“晋惠之末,至于洛阳”。
所谓“晋惠之末”,笔者认为其时间大致在西晋初惠帝太安至永兴之间(302~305年)。
假定他到洛阳前在沿途逗留一年多,那么,由此推算,耆域抵达广州登岸的时间应是晋惠帝永康与永宁之间。
东晋时,我国僧人法显因“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于晋安帝隆安三年(339年)自长安出发,西渡流沙,越葱岭,往天竺求法。
再由中天竺到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在该岛居留二年,闻知师子国至广州有海道可回,于义熙八年(412年)乘商人的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国“复随他商,东适广州”,“法显于船上安居。
东北行,趣广州。
”“商人议言:
‘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
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50天即可到达广州。
但法显所乘的商船“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被吹至青州长广郡(在山东半岛)上岸。
所谓“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无疑是长期来往于这条海上商路上的海商总结的经验。
尽管法显最后没能在广州港登陆,但反映了当时广州港是中国与印度佛教互动主要的通道。
南朝时期,从广州港进出的僧人增多。
据《高僧传》载:
刘宋时的释智严,“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诰,遂周流西国”求法,抵罽宾,进入“摩天陀罗精舍,从佛驮先比丘谘受禅法”。
不仅如此,他还邀请了佛驮跋陀罗来华传法。
佛驮跋陀罗来华后,智严“常依随跋陀,止长安大寺”。
佛跋陀罗被姚秦的僧人所摈逐,智严“分散憩于山东精舍,坐禅诵经,力精修学。
”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宋武帝刘裕西克长安,路经山东。
其时,始兴王恢随行游观山川,至智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
”王恢启请宋武帝延请智严等到建业。
屡经恳请,智严才前往,住建业始兴寺。
智严性爱虚靖,志避諠尘,王恢特地为其在东郊另建精舍,即“枳园寺”。
据《高僧传》载:
智严在未出家时,“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为惧。
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谘诸明达。
值罗汉比丘,具以事问,罗汉不敢判决,乃为严入定,往兜率宫谘弥勒,弥勒答云:
‘得戒。
’严大喜,于是步归。
至罽宾,无疾而化,时年七十八。
”
就是说,智严于东晋时曾从陆路到西域求法,归国后,弘法于宋京建业,因尝受五戒,有所亏犯,后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积年禅观而不能自了,又从海路重游天竺,以解疑惑。
智严前往天竺的走法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从建业(今南京)乘海船前往,当时的航路是沿海岸线展开的,广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港口,智严所乘之船无疑会在广州港停靠,补充给养;其二,广州港是刘宋时对外贸易大港,智严可能先乘小舶到广州,再在广州港乘大商船前往古印度。
笔者倾向于后者。
但不管是哪一种,智严此次取道海路前往印度求法,不可能不与广州港发生联系。
与智严同时代的昙无竭(即法勇)等到古印度求法则取道海路回国。
据《高僧传》载:
“释昙无竭,此云:
法勇,……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诵经,为师僧所重。
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
遂以宋永初元年(402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
……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
停岁余,学梵书梵语,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
复西行至辛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
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木舫。
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余人,杂三乘学,无竭停此寺受大戒。
天竺禅师佛驮多罗,此云觉救,彼土咸云:
已证果,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阇梨。
停夏坐三月日,复行向中天竺界。
路既空旷,唯赍石蜜为粮,同侣尚有十三人,八人于路并化,余五人同行。
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
将至舍卫国,野中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
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之。
其诚心所感,在险剋济,皆此类也。
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
又据《出三藏记集》载:
“释法勇者,胡言昙无竭,……幼为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讽经,为师僧所敬异。
尝闻沙门法显、宝云诸僧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
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
……进至罽宾国,礼拜佛钵。
停岁余,学胡书竟,便解胡语。
求得《观世音受记经》梵文一部。
无竭同行沙门余十三人,西行到新头那提河,汉言师子口。
缘河西入月氏国,礼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
后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杂三乘学。
无竭便停此寺,受具足戒。
天竺沙门佛陀多罗,齐言佛救,彼方众僧云其已得道果。
无竭请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阇梨。
于寺夏坐三月日。
复北行至中天竺,旷绝之处,常赍石蜜为粮。
其同侣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屡经危棘。
无竭所赍《观世音经》,常专心系念。
进涉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师子从林中出,象惊怖奔走。
后渡恒河,复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
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遂得免害。
其诚心所感,在崄克济,皆此类也。
后于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
”
可见,二书所载大致相同。
引文中,所谓“宋永初之元”即刘宋元初元年(402年);所谓“随舶泛海达广州”中的“随舶”,即“随商舶”,意即随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船”泛海到达广州。
就是说,昙无竭(法勇)招集志同道合的僧人二十五人于刘宋元初元年,从陆路“发迹北土,远适西方”求法,途中经历千难万险,最后于南天竺随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船”取海路回到广州。
前述,智严属从海路前往印度求法的,昙无竭则属在古印度求法后从海路回国的,他们都是中国僧人。
这一时期,古印度僧人从海路来华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等。
求那跋摩是北印度罽宾国僧人,“导化之声播于遐迩,邻国闻风皆遣使要请。
”刘宋时,京师名僧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思欲餐禀”,于元嘉元年(424年)九月,面启宋文帝求迎请跋摩。
宋文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观等,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并致书于跋摩及阇婆王婆多加等,必希顾临宋境流行道教。
”据《高僧传》本传载:
求那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
路由始兴,经停岁许。
始兴有虎巿山,仪形耸孤,峰岭高绝。
跋摩谓,其髣髴耆阇,乃改名灵鹫。
于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
时众道俗,莫不肃然增敬。
寺有宝月殿,跋摩于殿北壁,手自画作罗云像,及定光儒童布发之形,像成之后,每夕放光,久之乃歇。
始兴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后茂之将死,跋摩躬自往视,说法安慰,……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时值虎,以杖按头,弄之而去,于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焉。
跋摩尝于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侯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
沙弥惊恐大呼,往逐师子,豁无所见,其灵异无方,类多如此。
……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邺,文帝引见,劳问殷懃”。
求那跋摩来华的年代,有关引文中没有明确说明,但引文说他“路由始兴,经停岁许……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邺”。
据此逆推,求那跋摩应该是在元嘉六年抵达广州的,确切地说,是在当年春季之后抵达的。
就是说,求那跋摩应宋文帝的邀请来华弘法,于元嘉六年夏秋季之间从海路来广州。
引文中的“始兴(郡)”设于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分桂阳郡南部都尉置。
治在曲江县(今韶关市东南),辖境相当今广东曲江、乐昌、仁化,乳源、南雄、始兴、连、连山、连南、阳山、英德、清远、翁源、韶关等市县地。
先后属荆州、广州、湘州。
梁以后辖境缩小。
隋开皇九年(589)并入韶州。
求那跋摩先在始兴郡境内弘法,于始兴的虎市山建立佛寺,又于寺外别立禅院修持。
得到始兴太守蔡茂之的礼敬,历时一年多,“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
因宋文帝重申礼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431年)正月达于建邺”
继求那跋摩之后来华的是求那跋陀罗。
据《高僧传》本传载:
求那跋陀罗“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
……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
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仰,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
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请,深加崇敬。
”
据《出三藏记集》本传载:
求那跋陀罗“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
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汎海。
……元嘉十二年至广州。
时刺史车朗表闻,宋文帝遣使迎接。
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
见其神情朗彻,莫不虔敬,虽因译交言,而欣若倾盖。
初住祇洹寺,俄而文帝延请,深加崇敬。
”
二书所载大致相同。
引文中的“随舶泛海”就是“随商舶泛海”。
就是说,求那跋陀罗以“有缘东方”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随商舶泛海来华,于元嘉十二年来到广州。
其时,广州剌史车朗上报宋文帝。
文帝遣使延请至京师,深加礼敬。
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是从海路来华在广州港登岸,而僧伽跋摩则是陆路来华而取道海路返国。
僧伽跋摩于元嘉十年从流沙至于宋京建业,道俗敬异,“咸宗事之”。
僧伽跋摩在建业一带进行译经、传戒与弘传律学。
据《出三藏记集》载:
僧伽跋摩于“元嘉中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
而《高僧传》则载:
僧伽跋摩于“元嘉十九年,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
”
对比二书所载,《出三藏记集》说,僧伽跋摩返国的时间是“元嘉中”,《高僧传》则说是“元嘉十九年”。
“元嘉”年号共30年,所谓“元嘉中”大致在“元嘉十五年左右”,但《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都说僧伽跋摩是元嘉十年来宋都建业的。
僧伽跋摩若是“元嘉中”返国,那么他来刘宋仅五年左右就返国,但结合《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有关僧伽跋摩在华从事译经、传戒与弘传律学的活动,其工作量绝非五年的时间所能完成。
笔者认为还是以《高僧传》所载的“元嘉十九年”归国为宜。
就是说,僧伽跋摩是“元嘉十九年”随西域商人的商舶返国的。
而在刘宋时,广州港是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僧伽跋摩“随西域贾人,舶还外国”,应是在广州港西航的。
刘宋末年则有菩提达摩从海路来广州。
据《高僧传》本传载:
“菩提达磨,……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
笔者在《菩提达摩来华事迹考》一文的考证认为,菩提达摩约于刘宋明帝至顺帝年间取海路来华,抵达“宋境南越”,确切说,即广州南海郡番禺县(位于今广州市)。
菩提达摩登岸后,先在南朝境内活动,后往北魏。
差不多与菩提达摩同时期来华的是谙究大小乘的求那毘地。
据《高僧传》本传载:
“求那毘地,……齐建元初(479~480年),来至京师,止毘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胜,迭相供请。
……毘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
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
《出三藏记集》载:
“求那毗地,……建元初(479—480)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胜,迭相供请焉。
……是以外国僧众,万里归集,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赠往来,岁时不绝。
性颇槒积,富于财宝,然营建法事,己无私焉。
于建业准侧造正观寺,重阁层门,殿房整饰,养徒施化,德业甚著。
”
显然,二书所载基本一致。
引文称,求那毘地“齐建元初来至京师”,没有明确说是直接来齐都,还是从广州港登陆后才前往齐都的。
但引文说:
“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居之”。
或“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赠往来,岁时不绝。
……然营建法事,己无私焉。
于建业准侧造正观寺”。
据此判断,求那毘地应是在“南海”(即广州)登岸,并在这一带弘法有一定影响,即“南海商人咸宗事之”后,才前往齐都的,否则南海商人不可能在求那毘地到齐都建业之后,也前往建业为其营建寺宇。
而且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绝大多数的僧人取海路来华是从广州港登岸的。
笔者认为,求那毘地应是从广州港登岸并在广州一带弘法,之后才前往齐都建业的,而他在广州口岸登陆的时间,应是在刘宋之末。
萧梁时,真谛(即拘那罗陀)应梁武帝的延请来华弘传佛教。
据《续高僧传》本传载:
真谛“于大同十二年(中大同元年,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
以太清二年(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
”
就是说,真谛是经海路于中大同元年八月中旬来到南海(即今广州)登岸的,两年后抵达梁都。
这期间,他在途中停留了两年,在广东境内应有比较长时间的弘法活动。
后来,因侯景之乱,真谛逃离梁都。
本传又载:
真谛于“(承圣)三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
后随萧太保度岭至于南康,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
建〔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
引文中的“始兴”即前文所说的广东“始兴郡”。
就是说,真谛于承圣三年春季,避乱来到广东“始兴郡”译经弘法。
陈武永定二年(558年)七月,真谛折返豫章、临川,后又转入晋安郡(今属福建福州一带),因“飘寓投委,无心宁寄”从晋安郡“泛小舶”至梁安郡(今属福建泉州一带)。
真谛至梁安郡的目的是“更装大舶欲返西国”。
据《续高僧传》本传载:
真谛于“(永定)三年(559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
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穆公頠延住制旨寺,请翻新文。
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惟识论等。
后穆公薨没,世子纥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
……”
由引文可知,真谛法师从梁安郡(今福建泉州一带)乘海船欲返国,命运捉弄人,结果又被风飘回广州。
真谛登岸后,受刺史欧阳頠及其子的礼敬,住在制旨寺等寺院从事译经与弘法。
真谛此次在广州译经弘法前后达九年多,最后在广州去世。
综上所述可知,通过广州港出入的僧人,多数是从海路来华传教的古印度僧人,少数则是前往古印度求法或求法返国的中国僧人。
这些通过海路来华的古印度僧人,西晋初年有耆域,刘宋时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求那毘地。
而僧伽跋摩则是陆路来华由海路返国的。
萧梁时有真谛。
在中国僧人中,东晋时的法显是由陆路前往古印度求法,从师子国乘商舶取海路返回广州,虽然意外被风刮到青州,但其最初的目标港口则是广州港;刘宋时的智严第二次到古印度求法是从广州港起航的。
与其同时的法勇是从陆路前往而由海路回广州的。
应该说,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另一途径。
前文揭示:
两晋时期,开始了印度僧人由海路东来与中国僧人求法由海路回归的记录,刘宋时,无论是印度僧人来华,还是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或求法归来,其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求那毘地等。
这一方面与南朝各小王朝特别是刘宋王朝对佛教的极力提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还与海洋交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早在先秦,我国南中国海海岸带的海洋区域就已经通过海路与域外互动。
汉代,广州(番禺)港开始成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港。
两晋至南朝时期,我国对外贸易以东南亚、阿拉伯和印度等国为主,因地利之便,海洋贸易商船几乎都云集广州港。
就航海技术而言,两晋时的大商船达到可乘200人以上的规模,航海已采用牵星法,并能利用信风。
这既为海洋贸易提供便利,也为佛教僧人往来于印度与中国提供方便。
这些由广州港出入僧人所译的佛经与所传的佛学,学界的著述多有论及,此不赘述。
从传播的区域考察,这些来华的古印度僧人大多数人如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求那毗地、真谛等的目的地是南朝各小朝廷的首都建业,因此江苏是其译经弘法的主要区域,还有江西、浙江等。
个别还到达福建的福州与泉州、湖北的襄阳、河南的洛阳,因人而异。
必须指出,从广州登陆的僧人多在广东作或长或短的停留并随缘弘法,其中求那跋摩在广州始兴郡停留一年多,“感德归化者十有七八”;求那毘地对广东的影响也较大,“南海商人,悉共宗事”;在广州弘法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是真谛三藏,入境时在广州作短暂停留,侯景之乱时,避乱始兴。
由梁安郡乘船归国途中遇大风被飘回广州,继续译经弘法,最后终老于广州。
应该说,两晋南朝特别是刘宋时,广州港是佛教由海路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通道,对南朝乃至中国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广州乃至广东因口岸之便在其佛教的发展方面大受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