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Microsoft Word 文档讲解.docx
《管窥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Microsoft Word 文档讲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管窥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Microsoft Word 文档讲解.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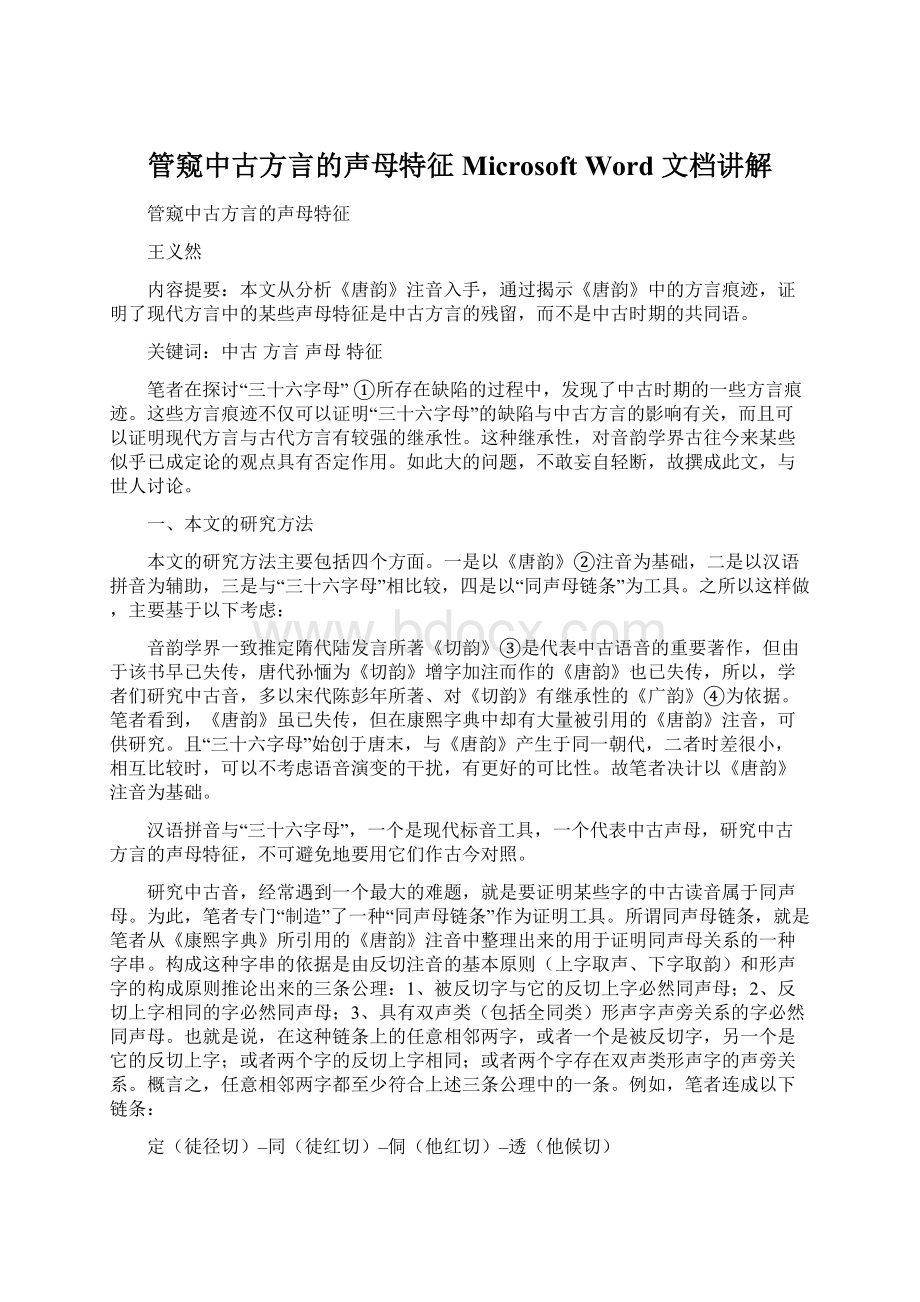
管窥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MicrosoftWord文档讲解
管窥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
王义然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唐韵》注音入手,通过揭示《唐韵》中的方言痕迹,证明了现代方言中的某些声母特征是中古方言的残留,而不是中古时期的共同语。
关键词:
中古方言声母特征
笔者在探讨“三十六字母”①所存在缺陷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古时期的一些方言痕迹。
这些方言痕迹不仅可以证明“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与中古方言的影响有关,而且可以证明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有较强的继承性。
这种继承性,对音韵学界古往今来某些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具有否定作用。
如此大的问题,不敢妄自轻断,故撰成此文,与世人讨论。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以《唐韵》②注音为基础,二是以汉语拼音为辅助,三是与“三十六字母”相比较,四是以“同声母链条”为工具。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音韵学界一致推定隋代陆发言所著《切韵》③是代表中古语音的重要著作,但由于该书早已失传,唐代孙愐为《切韵》增字加注而作的《唐韵》也已失传,所以,学者们研究中古音,多以宋代陈彭年所著、对《切韵》有继承性的《广韵》④为依据。
笔者看到,《唐韵》虽已失传,但在康熙字典中却有大量被引用的《唐韵》注音,可供研究。
且“三十六字母”始创于唐末,与《唐韵》产生于同一朝代,二者时差很小,相互比较时,可以不考虑语音演变的干扰,有更好的可比性。
故笔者决计以《唐韵》注音为基础。
汉语拼音与“三十六字母”,一个是现代标音工具,一个代表中古声母,研究中古方言的声母特征,不可避免地要用它们作古今对照。
研究中古音,经常遇到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要证明某些字的中古读音属于同声母。
为此,笔者专门“制造”了一种“同声母链条”作为证明工具。
所谓同声母链条,就是笔者从《康熙字典》所引用的《唐韵》注音中整理出来的用于证明同声母关系的一种字串。
构成这种字串的依据是由反切注音的基本原则(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形声字的构成原则推论出来的三条公理:
1、被反切字与它的反切上字必然同声母;2、反切上字相同的字必然同声母;3、具有双声类(包括全同类)形声字声旁关系的字必然同声母。
也就是说,在这种链条上的任意相邻两字,或者一个是被反切字,另一个是它的反切上字;或者两个字的反切上字相同;或者两个字存在双声类形声字的声旁关系。
概言之,任意相邻两字都至少符合上述三条公理中的一条。
例如,笔者连成以下链条:
定(徒径切)–同(徒红切)–侗(他红切)–透(他候切)
这一链条,可充分证明,在《唐韵》中“定”、“透”两字是作为同声母“t”来对待的。
不难看出,这种链条以简要的形式包含着一个复杂的推理论证过程,对同声母关系具有双向对称的传递性,起着“有之必然”的判定作用,是证明同声母关系存在的充分条件。
二、现代方言的几个特征
方言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现代方言的特征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只列举与中古方言有明显继承关系的反映在声母方面的特征。
1、“知、端”同声特征。
所谓“知、端”同声特征是指读“知”如“低”,把“知”字和“端”字读为同声母“d”,正如在“三十六字母”中把“知、彻、澄”三字作为声母“d、t”的代表字。
这一语音特征与“见、溪、郡、晓、匣”等字的古舌根音读法合在一起,被称为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残留,是学者们认为上古音“知”、“端”同源的重要依据之一。
这一方言特征以湘方言和闽方言为代表,是现代方言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
2、f、h混读特征。
所谓f、h混读特征就是指把f声母与h声母相混淆,也就是把“三十六字母”中“非、敷、奉”三字的声母与“晓、匣”两字的声母相混淆。
这一特征在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的表现,有的完全把f读为h,有的部分把f读为h;有的完全把h读为f,有的部分把h读为f。
这一方言特征也以湘方言和闽方言为代表,以读f为h最为典型。
3、w、m混读特征。
所谓w、m混读特征是指把以u开头的零声母字与m声母字混为同声母,也就是把“三十六字母”中的“微”母与“明”母混读。
这一方言特征主要以粤方言为代表,如广东话把“文”读作“门”,把“问”读作“闷”等等。
这一特征因被音韵学界作为证明中古“微、明”同母和“古无轻唇音”的根据,而有较大影响。
4、卷舌音与平舌音分混特征。
所谓卷舌音与平舌音的分混特征是指现代汉语拼音中的zh、ch、sh与z、c、s两组声母相混淆,也就是“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组声母(照、穿、状、审、禅)与精组声母(精、清、从、心、邪)相混淆。
这一特征与f、h混读的情况相类似,有的全部卷舌音都读平舌音,有的部分卷舌音读为平舌音;有的全部平舌音都读卷舌音,有的部分平舌音读为卷舌音。
这一方言特征在全国分布范围最广,七大方言区无一能把所有的卷舌音与平舌音彻底分清。
三、中古方言在《唐韵》中的反映
毫无疑问,要研究语音,首先自己就应当努力摆脱方言的影响。
但在中古时期既没有专门的标音符号系统作参照,也没有现代的语音记录传播手段为依托,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唐韵的编者自然也不能例外。
所以,仔细研究《唐韵》注音,仍可发现当时的一些方言痕迹。
下面分类加以论述。
1、《唐韵》中的“知、照”同声。
笔者精心连成以下同声母链条:
照(之少切)-沼(之少切)-召(直少切)-仲(直众切)-忠(陟弓切)-知(陟离切)。
根据这一链条,我们可以放心地做出在《唐韵》中“知”和“照”是同声母的判断。
把这一判断与“三十六字”母相对照就可发现,“知、照”同声并不是当时的唯一读法。
这是因为在“三十六字母”中,“知”和“照”不仅同时存在,而且还被分在不同的组中。
这就是说,在首创字母的唐末僧人守温那里,“知”字与“照”字不是同声母,与“端”字是同声母,这与《唐韵》注音的读法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字,在同一时代,有两种不同的读法,这只能用方言现象来解释。
这就证明“知、端”同声的方言特征,在中古时期已经形成。
反过来说,现代方言中“知、端”同声的特征,是古代方言的延续,而不是古代共同语的残留。
2、《唐韵》中的f声母。
f声母属于轻唇音,实际上是汉语声母系统中唯一的一个唇齿音,在“三十六字母”中有“非、敷、奉”三个代表字。
在《唐韵》中,f声母有一个丰富的反切上字群作为标音体系:
府(方矩切)、甫(方矩切)、方(府良切)、芳(敷方切)、防(扶方切)、奉(扶垄切)、风(方戎切)、扶(防无切)、非(甫微切)、飞(甫微切)。
这个字群可以连成以下同声母链条:
非(甫微切)-甫(方矩切)-方(府良切)-芳(敷方切)-防(扶方切)-奉(扶垄切)。
字群和同声母链条可以证明,中古时期的f声母是独立存在的,而这种独立存在又暗藏着一种方言迹象。
这是因为守温在初创字母时只有三十个,没有轻唇音(“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床、娘”六母是宋代学者添加的),f声母被遗漏了。
把这种遗漏与守温在“三十六字母”中对“知、彻、澄”三字的处理联系在一起,就可对这种遗漏做出正确的解释,揭穿被掩盖的方言迹象。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在现代,“知、端”同声(实际上就是zh、d混读)与f、h混读这两个方言特征是在同一方言区并存的,在唐代,这两个方言特征也是在同一方言区并存的。
守温正是受这种方言的影响,f、h混读都读h,感觉不到f声母的存在,所以既错误地处理了“知、彻、澄”三字,又把f声母遗漏了。
3、《唐韵》中的“微”母和“明”母。
“微”母在“三十六字母”中属于轻唇音,是现代以u开头的零声母的来源。
笔者从《唐韵》注音中,搜索出以下“微”母字群,包含了“u、uan、uen、uei、uang”等以u开头的零声母音节。
武(文甫切)、文(無分切)、無(武扶切)、无(武夫切)、亡(武方切)、问(亡运切)、微(無非切)、未(無沸切)、挽(無远切)、万(無贩切)。
“明”母在“三十六字母”中属于重唇音,是现代m声母的来源。
在《唐韵》中,“明”母字一般以“莫”字作反切上字。
下面是以“莫”字作反切上字的字群,包括了所有不含介音i的m声母音节,涵概了m声母音节的绝大部分。
马(莫下切)、末(莫拨切)、米(莫礼切)、木(莫卜切)、买(莫蟹切)、梅(莫杯切)、满(莫旱切)、门(莫奔切)、忙(莫郎切)、蒙(莫红切)、谋(莫浮切)、毛(莫袍切)
列出如此多的反切上字,旨在说明《唐韵》中的“微、明”两母各有归属,有较清楚的边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声母。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微”母字群中的所有字,可以用多种连法,轻而易举地连成同声母链条。
这些字循环互注,形成一个封闭、独立的标注体系(在《唐韵》中,找不到用其他反切上字为这些字注音的例子)。
这可充分说明,中古时期“微”母已经形成,而并非象某些学者所说,当时的“微”母尚未分化出来。
在《唐韵》中确实存在w、m相混的问题,而这种相混与现代方言中的w、m相混方式不同,不是“微”母混为“明”母,而是一部分“明”母混为“微”母。
具体表现是在《唐韵》中没有一个“微”母字用“明”母字作反切上字,相反,却有一部分“明”母字以“微”母字作反切上字。
这就是说,“微、明”两母相混在《唐韵》中的表现是单方向的,且与现代方言的相混方向是相反的。
其相混的范围仅限于“明”母遇到介音i时才混为“微”母。
如:
苗(武镖切)、鸣(武兵切)、岷(武巾切)、免(亡辨切)等等。
按照这种单方向的混同规律,“明”字理所当然的应属“微”母,所以《广韵》的注音是:
明,武兵切。
这种标注又与“三十六字母”出现了矛盾。
因为“三十六字母”虽经历代学者多次调整,但“明”字却始终是m声母的唯一代表字。
这种矛盾足以说明,中古时期的“微、明”混读,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至少在孙愐和守温那里,混读的方向是正好相反的。
联系守温始创三十个字母时遗漏轻唇音的事实,可以证明两地混读的范围也大不相同,在守温那里,全部“微”母都混为“明”母。
这与f、h混读都读h且因此遗漏f声母的情况是相同的,可以作为“古无轻唇音”这一错误判断的否定证据。
4、《唐韵》中平舌音与卷舌音的分混。
在《唐韵》中,平舌音与卷舌音分得比较清楚,其具体表现是“三十六字母”中的“精”组声母与“照”组声母大多数在《唐韵》中都各有归属。
但个别混同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如笔者从《唐韵》注音中整理出这样两个字群:
恻(初侧切)、测(初侧切)、侧(阻力切)、阻(侧吕切)。
俎(侧吕切)、装(侧羊切)、庄(侧羊切)。
分析这两个字群。
第一个字群中“恻、测、侧”三字,属于同声旁的形声字,声旁“则”是平舌音,这三个字也都应是平舌音,但前两个字却用卷舌音“初”作反切上字,显然是按卷舌音来处理的,这与第三个字“侧”以平舌音“阻”作反切上字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第二个字群中,“装、庄”两字都应是卷舌音,却与平舌音“俎”使用相同的反切上字“侧”来注音,显然是把这两个字当成了平舌音。
可见,《唐韵》中平舌音与卷舌音相混的情况虽然不多,但却存在,而且平舌音混为卷舌音与卷舌音混为平舌音两种情况都有。
四、一个被忽略的方言特征——y、w混读
这里的y和w,分别代表“疑”母和“微”母。
所谓y、w混读,就是指把三十六字母中的“疑”母和“微”母相混淆。
为了更清楚地表述这一特征,笔者把现代零声母分为三类:
单韵母i和以i开头的复合韵母自成音节的字为一类,称为i类零声母;单韵母u和以u开头的复合韵母自成音节的字为一类,称为u类零声母;其他韵母自成音节的字为一类,称为其他零声母。
经过这样的处理可以看出,i类零声母和u类零声母分别与“疑”母和“微”母相对应。
由于“疑”母字和“微”母字现在都属于零声母字,人们在研究方言特征时,根本不把“疑”母和“微”母当作声母来对待,所以y、w混读这一方言特征自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所忽略,文献中找不到这方面的论述,《方言例字表》中没有反映这一特征的例字。
所以,笔者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单独论证。
⑴、“疑”母的三个组成部分。
从《唐韵》注音所反映的情况看,中古时期的“疑”母是一个独立的声母,而且是一个覆盖范围非常广泛的声母。
它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纯粹“疑”母字,也就是与现代i类零声母相对应的“疑”母字;二是一部分“微”母字混入“疑”母,被视为“疑”母字;三是现代其他类零声母字。
以下同声母链条是笔者做出上述判断的依据。
1、疑(语其切)-语(鱼举切)-鱼(语居切)-玉(鱼欲切)-云(玉分切)-友(云久切)-又(于救切)-于(羽俱切)-尤(羽求切))-園(羽元切)袁(雨元切)
2、语(鱼举切)-牛(语求切)-遇(牛俱切)-愚(虞俱切)
3、于(羽俱切)-永(于景切)-荣(永兵切)
4、余(以朱切)-餘(以朱切)-炀(余亮切)-杨(与张切)-蛘(与张切)-恙(餘亮切)-逾(羊朱切)-瘉(以朱切)-由(以周切)
5、午(疑古切)-吴(午胡切);五(疑古切)-雲(五分切)-牙(五加切)
6、永(于景切)-泳(为命切)-为(薳支切)-薳(韦委切)-韦(宇非切)-胃(于鬼切)-伟(于鬼切)-媁(於非切)-畏(於胃切)-萎(於胃切)-威(於非切)-尉(於非切)。
7、宇(王矩切)-枉(迂往切)-汪(乌光切)-弯(乌官切)
这些同声母链条都是根据《唐韵》注音整理出来的。
其中,前三条实为一体,2、3两条是从第一条“语”字和“于”字处分别引出的两个分支。
链条1至4反映中古时期“疑、语、鱼、玉、云、袁、羽、于、又、友、牛、永、荣、余、以、杨、羊、逾、由”等字属于“疑”母字,当然,与这些字有双声类形声字声旁关系的所有字也都属于“疑”母字。
可见中古时期“疑”母能够包含所有现代i类零声母字。
链条5分为两段,从这一链条可以看出,“午”字和“五”字均以“疑”字作反切上字,而“吴、雲、牙”等字又分别以“午”和“五”作反切上字,说明现在看来应属“微”母字的“午”和“五”在《唐韵》中混入“疑”母,且又反过来直接作“疑”母字的反切上字。
在《唐韵》中,部分“微”母字混为“疑”母的例子可举出很多。
链条5、6、7大致反映混入“疑”母的“微”母字的范围,说明中古时期的“午、五、为、韦、胃、畏、萎、威、尉、王、乌、弯”等字,以及与这些字有双声类形声字声旁关系的所有字,都属混入“疑”母的“微”母字。
可见由“微”母混入“疑”母的字也是很多的。
以下字群的字都属于现代其他类零声母字,从《唐韵》所使用的反切上字看,中古时期也都属于“疑”母。
“ao”傲(五到切)、“ai”爱(乌代切)、“an”安(於寒切)、“ang”昂(五冈切)、“ou”偶(五口切)、“e”恶(乌合切)、“en”恩(乌痕切)。
这一字群几乎包含了所有其他类零声母音节,证明现代的其他类零声母字,中古时期,均归属“疑”母,且一般以当时属于“疑”母的“五、乌、於”为反切上字。
⑵、y、w混读是一种方言特征。
不难看出,在“疑”母的三个构成部分中,混入“疑”母的“微”母字占了相当的比例。
而由于这种混入,使有些字的注音难以拼读。
如:
伟(于鬼切),按照反切注音原则,用现代汉语拼音表示,它的读音应该是yui,这种标注显然违背汉字音节的声韵搭配规律,属于音韵学上的声韵不和,也就是说没有这种读音的汉字。
由此可以断定,《唐韵》中的y、w混读决不是当时的共同语,而是一种方言特征的流露。
《唐韵》源于《切韵》,《切韵》以当时的洛阳口音为基础。
所以,这种方言特征在《切韵》时代已经形成,且就依存在当时的洛阳口音之中。
y、w混读的轨迹只有分析大量的《唐韵》注音才能发现,人们日常翻阅字书,根本觉察不到,所以,对有些用混入“疑”母的“微”母字作反切上字的字,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如:
雲(五分切)、雨(王矩切)。
根据前一个注音,人们可能把“雲”读作“文”,也可能把“五”读作“与”;根据后一个注音,人们可能把“雨”读作“五”,也可能把“王”读作“yuang”。
这样,就会使这种混读特征由单向混读发展成方向相反的两个分支。
根据语音演变的缓慢渐进性,笔者认为,这种方言特征现在仍然存在,而且也会有混读方向不同的两个分支。
只是未经大规模调查,尚不能确定其地域分布的具体情况。
⑶、y、w混读特征的产生根源。
笔者发现,y、w混读特征的产生,与“乌、於、于”三字密切相关。
一方面,“於”是“乌”的古字,所以古时候叹词“於呼、於乎、於戏”等同于“呜呼、乌乎”,古楚方言称老虎为“於菟”或“乌菟”。
这些能证明“乌”与“於”是相通的,应当属于“微”母。
另一方面,“於”又与“于”相通,《说文解字》中便有此训,沿袭至今。
所以“於”和“于”自然也应当属于“疑”母。
一个“於”字两种读音,人们在运用反切注音选择反切上字时,又不注意回避双音字,结果使“於”字此处跟“乌”相通,彼处又跟“于”相通,导致“疑”母与“微”母相混,这就是y、w混读特征产生的根源。
如《唐韵》注音中有伟(于鬼切)、媁(於非切),又有於(哀都切)、哀(乌开切),前二者属于“於”、“于”相通,而后二者则属于“於”、“乌”相通。
笔者认为,正是“於、于、乌”三字的频繁混用,才使y、w混读的范围逐步扩大,形成一种方言特征。
综上所述,分析《唐韵》注音,我们可以发现,中古时期我国存在多种方言语音,不仅有人们熟知的至今仍然存在的平舌音与卷舌音混读、zh与d混读、w与m混读、f与h混读等特征,而且还有人们非常陌生的y、w混读之类的特征。
可以肯定地说,中古时期的语音状况十分复杂,没有统一的标准语音。
五、中古方言的影响
人们受方言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自己往往觉察不到。
所以,它的影响常常被人们忽视。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古时期的方言世代相传,至今仍保留着原有的声母特征。
他对国人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首先,它深刻地影响了“三十六字母”的形成,使这个饱含创意的语音教学工具一问世就先天不足,积极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负面影响却不断膨胀,持续了一千多年。
守温和尚由于受当时方言的影响,把本应属于“照”组声母的“知、彻、澄”三字单设一组,由正齿音变成了舌上音;当时早已存在f声母和“微”母,但他却视而不见,从而漏掉了整个轻唇音。
这些缺陷和其他缺陷结合在一起,使一直弄不清其病因的音韵学界变成了矛盾百出、高深莫测的领域。
如中古时期到底有多少个声母?
象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意见。
等韵学家们在这个基本问题不清的前提下编制的五花八门的等韵图,就更难让人接受。
其次是它会使人们产生错觉,接受误导,作出错误判断。
如传播至今的“知、端”同声特征和w、m混读特征,就被一些学者当作中古时期的共同语加以肯定。
自清代学者钱大昕⑤证明“古无轻唇、重唇和舌头、舌上之分”以来,众多学者多从其说,认为中古时期“重唇音尚未分化出轻唇音”,于是,纷纷对传统的“三十六字母”进行调整,把轻唇音“非、敷、奉、微”并入重唇音“帮、滂、并、明”。
这实际上是不顾历史真实情况,把轻唇音一笔勾销了。
笔者认为,所谓舌上音,就是声母d、t遇到介音i所形成的一种音位变体,如“低、铁、停”等字的声母,就应当属于中古时期的舌上音。
守温的错误仅在于把本属于正齿音的“知、彻、澄”三字当作舌上音来处理,而不能证明中古时期不存在舌上音。
所以钱大昕的证明不无阙疑,由此引申出“上古音‘知’母与‘端’母同源、轻唇音和重唇音相通”的推断也缺少有力证据。
注释:
①“三十六字母”,音韵学上传统的“三十六字母”,大致代表唐宋间汉语语音的声母。
按《康熙字典》等韵图为:
见、溪、郡、疑;端、透、定、泥;知、彻、澄、娘;帮、滂、并、明;非、敷、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状、审、禅;影、晓、喻、匣;来;日。
《辞海》中“郡”为“群”、“状”为“床”。
唐末僧人守温制定三十个字母,宋代等韵学家又增加“非、敷、奉、微、床、娘”六母,形成“三十六字母”。
②《唐韵》:
韵书,唐孙愐撰。
为陆法言《切韵》增字加注而作。
原书不传。
③《切韵》:
韵书,有隋陆法言著和唐李舟著两种,本文所及的是隋陆法言所著《切韵》。
原书久佚。
此书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酌收古音及其他方音,是唐、宋韵书的始祖。
音韵学上推为重要著作。
。
④《广韵》:
韵书,全称《大宋重修广韵》,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
原为增广《切韵》而作。
收字二万六千余。
研究中古语音的,大都以此为根据,研究上古或近代语音的,也以此作为比较的资料,是汉语音韵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
⑤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
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
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乾隆进士。
官至少詹事。
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主讲钟山、娄东、紫阳等书院。
治学方面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首先注意古声母的研究,证明古无轻唇、重唇和舌头、舌上的分别。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1979),《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
2、殷焕先(1979),《反切释要》,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3、岳俊发等(1984),《方言与汉字》,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沈阳。
4、张玉书等(清),《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7。
5、王力(2004.1),《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北京。
作者联系单位: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