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docx
《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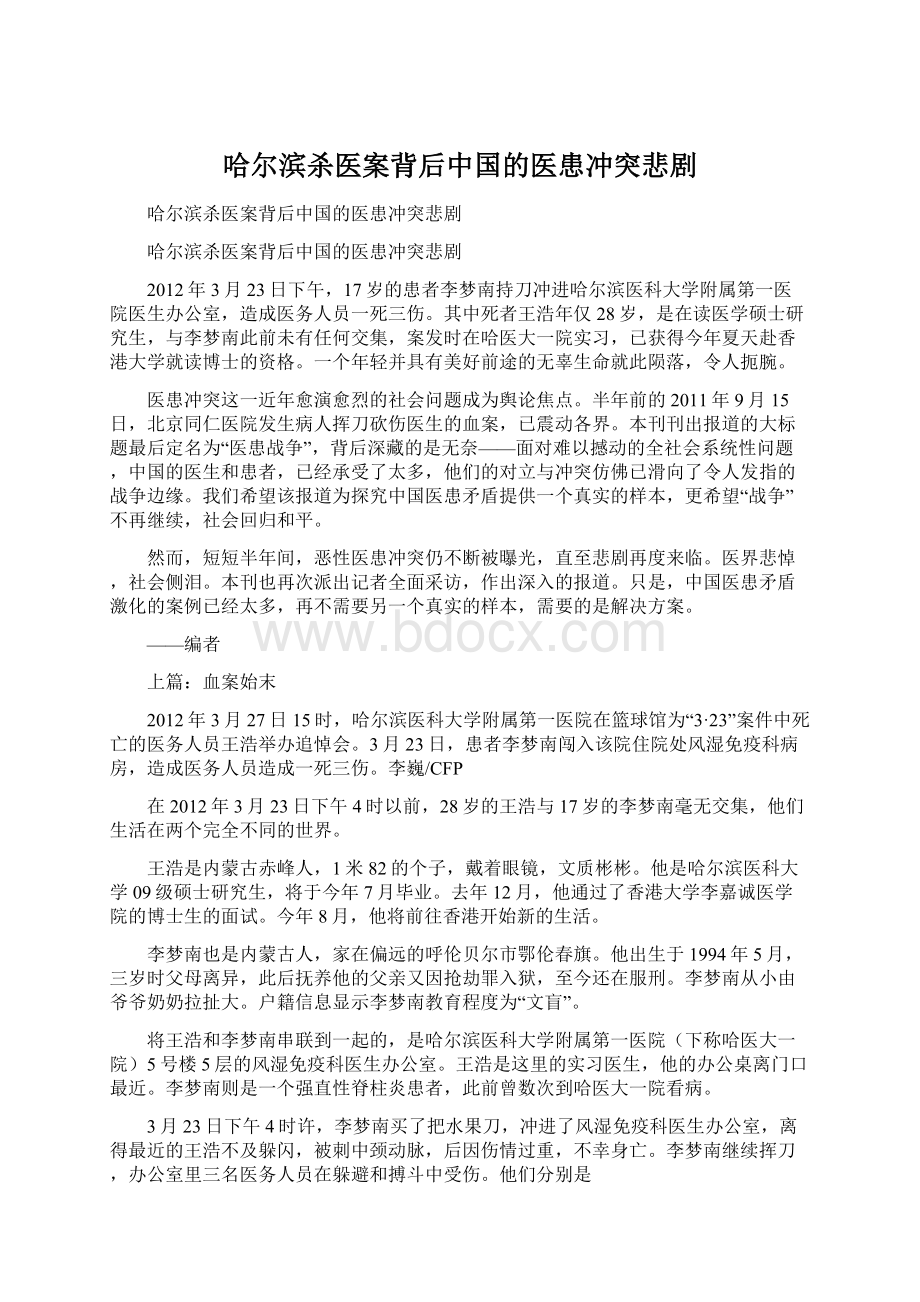
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
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
哈尔滨杀医案背后中国的医患冲突悲剧
2012年3月23日下午,17岁的患者李梦南持刀冲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生办公室,造成医务人员一死三伤。
其中死者王浩年仅28岁,是在读医学硕士研究生,与李梦南此前未有任何交集,案发时在哈医大一院实习,已获得今年夏天赴香港大学就读博士的资格。
一个年轻并具有美好前途的无辜生命就此陨落,令人扼腕。
医患冲突这一近年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半年前的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病人挥刀砍伤医生的血案,已震动各界。
本刊刊出报道的大标题最后定名为“医患战争”,背后深藏的是无奈——面对难以撼动的全社会系统性问题,中国的医生和患者,已经承受了太多,他们的对立与冲突仿佛已滑向了令人发指的战争边缘。
我们希望该报道为探究中国医患矛盾提供一个真实的样本,更希望“战争”不再继续,社会回归和平。
然而,短短半年间,恶性医患冲突仍不断被曝光,直至悲剧再度来临。
医界悲悼,社会侧泪。
本刊也再次派出记者全面采访,作出深入的报道。
只是,中国医患矛盾激化的案例已经太多,再不需要另一个真实的样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
——编者
上篇:
血案始末
2012年3月27日15时,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篮球馆为“3·23”案件中死亡的医务人员王浩举办追悼会。
3月23日,患者李梦南闯入该院住院处风湿免疫科病房,造成医务人员造成一死三伤。
李巍/CFP
在2012年3月23日下午4时以前,28岁的王浩与17岁的李梦南毫无交集,他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王浩是内蒙古赤峰人,1米82的个子,戴着眼镜,文质彬彬。
他是哈尔滨医科大学09级硕士研究生,将于今年7月毕业。
去年12月,他通过了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的面试。
今年8月,他将前往香港开始新的生活。
李梦南也是内蒙古人,家在偏远的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
他出生于1994年5月,三岁时父母离异,此后抚养他的父亲又因抢劫罪入狱,至今还在服刑。
李梦南从小由爷爷奶奶拉扯大。
户籍信息显示李梦南教育程度为“文盲”。
将王浩和李梦南串联到一起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5号楼5层的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
王浩是这里的实习医生,他的办公桌离门口最近。
李梦南则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此前曾数次到哈医大一院看病。
3月23日下午4时许,李梦南买了把水果刀,冲进了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离得最近的王浩不及躲闪,被刺中颈动脉,后因伤情过重,不幸身亡。
李梦南继续挥刀,办公室里三名医务人员在躲避和搏斗中受伤。
他们分别是
李梦南的叔叔、婶婶和姑姑都在外打工挣钱,带李梦南看病的任务只能落在身患胃癌的爷爷身上。
当地医院查不出什么问题,医生建议去大医院。
从家里乘火车九小时可直达哈尔滨,祖孙二人便到哈医大一院看病。
“哈医大在我们这最权威。
”李梦南家人告诉财新记者。
没钱,买不起卧铺,爷孙俩每次去哈尔滨,都是忍着病痛在火车上熬一宿,第二天一早赶到医院。
李梦南的叔叔回忆称,第一次去哈医大一院,并没有确诊,是按滑膜炎给李梦南治疗的,拿了些药就回去了。
回到家中,药吃完了,但李梦南的病未见好转,越来越重,甚至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无奈,2011年4月,李禄带着李梦南又去了哈医大一院。
第二次到哈医大一院,这次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
在医院,李梦南前后住了十七八天。
李禄说,李梦南住院期间,主治大夫推荐了两种药,其中一种是类克。
为了早点治好病,少让孙儿受罪,李禄选了贵的类克,通过静脉点滴注射了两支。
此外,还使用了一些其他药。
之后,李梦南的病情明显好转,“浑身不疼了,走路也好了”。
强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spondylitis,AS)是常见的慢性进行性疾病,病症主要是炎性腰背痛和关节痛。
重者背脊弯曲、不能从事一般的体力工作;轻者生活质量也将受到很大影响。
类克这种生物制剂,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都必须长期使用,一旦停用,疾病很容易复发和加重。
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上一任主任委员张奉春,引用一例针对十几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停药情况调查指出,一般在停用类克七八周之后,疾病就会复发。
每年多达十万元的治疗费用,是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沉重的家庭负担。
同样是因为太贵,这笔费用也不能通过医保报销。
“参加制定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目录的时候,我们曾把类克这些药物提上去,国家没同意。
”张奉春认为,只有国内开发出更便宜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药物,相应的治疗费用才能大幅度下降。
实际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连续多年资助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但是,“医药研发过程一般都长达一二十年”。
这对于患者无疑意味着久拖不治的困境。
对于李梦南的家庭而言,最好的前景是尽快“断根”。
李梦南的叔叔告诉财新记者,孩子着急把腿病治愈,以便早日打工挣钱。
李梦南的叔叔告诉财新记者,全家为治好李梦南的病,通过打工和借债筹措了4万多元钱。
但除了看病治疗的费用,更大的压力是往返哈尔滨的旅途开销。
为了省钱,祖孙二人每次外出都“挑最便宜的吃”。
李梦南此次住院,总计花了1.95万元。
在此类病中,这个花费属正常,但对李家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
首次住院两周多有明显好转后,李梦南即出院,医生嘱咐他两周后回医院复查。
李梦南回到家中后不久,出现发烧症状。
正好两周后要去复查,2011年5月10日,爷孙俩第三次奔赴哈尔滨。
李禄告诉财新记者,为了少让孙子受罪,给李梦南用的都是好的消炎药,但就是高烧不退。
后来在哈医大一院拍了胸片,医生初步诊断为肺结核和胸膜炎,哈医大一院无治疗肺结核科室,医生让李梦南转到专门收治肺结核的专科医院——哈尔滨市胸科医院去治疗。
在胸科医院,李梦南被确诊为肺结核。
考虑到哈尔滨花销太大,难以承受,加之李梦南能享受的医保在呼伦贝尔,在当地医院医保能报销约50%的费用。
“我们没有住院,也没有开药,就回呼伦贝尔。
”李禄说。
回到呼伦贝尔后,李梦南在爷爷陪同下,到当地的扎兰屯医院住院治疗肺结核。
李梦南的叔叔说,住了几个月后,医院判断李梦南肺结核已经痊愈。
2012年3月22日晚,带着对病痛彻底“断根”的期望,李梦南和爷爷再次奔赴哈尔滨,决心这次要住院治疗。
结核阴影
虽然类克不能应用于肺结核患者,但患者服用类克后,时有出现肺结核的案例。
医学界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据欧洲国家的统计,总体而言,强直性脊柱炎的患病率大概在0.1%至1.4%之间,目前没有中国的权威统计数字。
按照欧洲的比率来估计的话,中国的强直性脊柱炎患者有137万至1900万。
患者主要集中在年轻人,平均年龄只有26岁,男性和女性的患病比例基本为2比1。
80%的患者都是在30岁以前出现症状,只有极少比例才会在45岁以上出现症状。
广东省风湿病专业组常务委员、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主任医师肖征宇告诉财新记者,治疗首选药物是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至于是否使用类克,则会根据患者情况定。
非甾体类抗炎药目前仍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主要药物,“安全、有效、便宜”,但是这种药物并不能减缓疾病的发展,只是让患者疼痛感降低。
实际上,医学家至今仍不能确定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患者所能够选择的药物非常有限,直到21世纪初,TNF-α抑制剂被应用治疗,患者情况才有很大的改善。
类克就是TNF-α抑制剂的一种。
山东省省立医院一位风湿专家告诉财新记者,类克是TNF-α抑制剂中疗效最好的药之一,是行业内医生比较推崇的药,但价格昂贵,一般医院没有,只有大城市的二三级医院才有。
临床医生大多给年轻病人推荐使用这个药,因为早期的年轻病人,不治疗的话致残率比较高,使用类克一般都愈后良好。
但是类克确有潜在的副作用,更不能应用于肺结核患者。
类克的官方网站注明,“有报告指出,曾有使用者受到严重的感染,如肺结核和败血症,有些感染更会导致生命危险。
如果以往或最近曾接触过肺结核病患者,应告知医生。
如果身体容易受感染、曾经或已受到感染、或在使用类克时,出现感染症状,应立即向医生诊治。
”
患者服用类克后,时有出现肺结核的案例。
不过,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奉春告诉财新记者,他遇到过在使用类克之后感染肺结核的患者,但“结核的概率不是太高”。
在非甾体类抗炎药和类克的选择上,张奉春认为后者的疗效要好得多。
“非甾类药物,主要是镇痛为主,对病情的减缓没有多大帮助。
如果不考虑经济因素和其他问题,类克这类生物制剂毫无疑问是治疗这病的最好药物。
”
对于像李梦南这样未满18岁的年轻患者,张奉春认为类克是最好选择,即便李梦南所在地区属于肺结核高发区,“全中国其实都是肺结核高发区”。
但李梦南就是在初次使用类克后感染的肺结核。
他的叔叔对财新记者强调,李梦南是在应该第二次注射类克的疗程之前开始发高烧的。
李禄对财新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孩子得肺结核就是打类克这个药打出来的,我们家族没有肺结核史。
孩子之前也从来没有得过这个病。
”
李梦南的叔叔告诉财新记者,家人并不了解使用类克有导致肺结核的可能。
李禄也坚称,医生当时并没告诉他们这个药有出现并发症的可能。
由于院方不接受记者采访,医生当时是否充分告知难以确认。
但在李梦南得了肺结核后,他及家人对医生不信任的种子已经悄悄埋下。
血案
李梦南:
“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
据财新记者了解,李禄每次带李梦南来哈尔滨看病,都住在哈医大一院急诊科隔壁铁岭街的一家名叫乐一住的私人小旅馆。
旅馆在半地下,非常狭小,房间是一个个很小的格子间,多半没窗户。
旅馆老板娘告诉财新记者,爷俩住的是一晚上50元的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床。
去年爷俩来过两次,这一次是3月23日。
当天早晨7点多,坐了一夜火车的爷孙俩到达哈尔滨,直接去了哈医大一院。
因为之前住过院,此次来是复诊,没有挂号直接就去住院部找大夫看。
大夫问了情况后表示,要先到胸科医院去看肺结核。
于是爷孙俩赶去胸科医院拍了片子,又回到哈医大一院,结果接诊大夫说病历本上没有胸科医院医生的医嘱。
没办法,李梦南只好自己又去胸科医院,爷爷李禄因体力不支,先去了乐一住旅馆登记住店。
旅馆老板娘也向财新记者确认,李禄是下午2点半入住的。
当天下午3点多,李禄和李梦南来到哈医大一院5号楼5楼的风湿免疫科(住院部),大夫郑一宁说,看了片子治疗效果不错,但病灶没有完全钙化,因此让他们先回去休养三个月再来看。
爷爷和李梦南不愿意,觉得跑来跑去的,郑一宁表示自己没法做主,得问一下主任。
于是郑一宁带着爷爷到了副主任医师赵彦萍的办公室,但特意让李梦南留在门外。
因为类克这种免疫制剂会降低患者免疫力,会诱发感染,引起结核加重和扩散,专科医生在使用时非常谨慎,不但在结核的活动期不能使用,在结核的稳定期也不能使用,只有等结核病灶完全钙化才可使用。
据李禄回忆,赵彦萍大夫看了片子,问:
现在还疼不疼?
李禄回答说不疼了。
赵彦萍说,那就没必要用类克药了,这个药是生物激素。
整个过程赵彦萍没说多少话,双方交流正常。
一直在门外的李梦南也没出现什么异常。
赵彦萍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患者希望住院,但她和另外一位医生先后看了片子,认为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
李禄告诉财新记者,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回到了旅馆,他让李梦南喝了一袋奶。
李梦南随后自己就单独出去了。
旅馆老板娘记得,当天下午4点多,李梦南从外面跑进来,两手都是血,身上也有。
她奇怪问道:
“怎么到这了还打架呢?
”
李梦南没吭声,径直跑向房间,说了一句:
“爷爷,我把医生给拉了。
”
李禄愣了,只见孙子脖子、双手都是血,顾不上追问发生了什么,他就带上孙子前往隔壁的哈医大一院急诊大楼。
临出门时,他嘱咐旅馆老板娘:
“地上有血,帮忙收拾收拾。
”
两三分钟后,李禄带着满身是血的李梦南来到急诊科一楼,刚进外科治疗室,就听见一声尖叫:
“就是他杀的我们!
”从里面跑出浑身是血的女大夫郑一宁,边跑边喊:
“就是他杀的我们!
”
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邮政街派出所警察闻讯赶来,带走了李梦南和李禄。
据新华社3月29日的报道,李梦南在看守所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
”离开哈医大一院后,李梦南记得爷爷说“不收就回家吧”,但他没有听老人的话,偷偷地买了水果刀,直接冲进医生办公室。
李梦南认为,医生不了解他的辛苦。
他说,他家离哈尔滨挺远,家里条件也很困难,爷爷还患有胃癌,一次次做检查加上人生地不熟等等因素,让他和爷爷都非常辛苦。
共有之痛
医生可以治疗病人的生理疾病,但无法顾及每一个家庭的困难;犯罪行为不能因弱势而免责,但整个社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
李禄至今也不明白,孙子李梦南怎么会去杀人。
他记得,3月23日当天下午在哈医大一院就诊时,和大夫交流正常,李梦南也没有什么异样。
李梦南的叔叔也想不通侄儿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他告诉财新记者,“李梦南从小就很懂事,不打架,从来不跟人发生口角,管片民警都知道。
”根据其家庭情况,居委会还给李梦南办了一个低保,一个月有100多块钱。
“你可以去问派出所、居委会。
”李梦南的叔叔反复强调。
李梦南的叔叔很担心监狱中的哥哥知道儿子杀人承受不了。
“这孩子跟他父亲感情深,没进去前,他父亲(离婚)什么也没要,就要了孩子。
出事后,孩子是活下来的惟一”他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
旅馆老板娘告诉财新记者,李梦南这孩子看上去很内向,不怎么说话,很乖的样子。
事件发生后,哈医大一院相关负责人反复强调,这一事件与医患纠纷没有关系。
哈尔滨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锐忱看望受伤医生时称,经过公安部门的初步侦查,此案为偶发的治疗案件,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新华社的报道称,李梦南承认:
“我不应该滥杀无辜。
”他表示很想家人,他是一时冲动犯下的大错。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马皑告诉财新记者,李梦南的行为属于绝望心境状态下的挫折攻击。
由于家庭条件不佳,治病成本已经不堪重负,在缺少对弱势家庭特殊救助机制的状况下,对心情、心境乃至心态的影响巨大。
他对本次治疗抱着较高期望,但挫折使其转变为绝望,产生明显的外在归责,将暂时不能治愈的责任归于医生的推诿,并在情绪推动下产生报复、泄恨的动机。
马皑表示,医生可以治疗病人的生理疾病,针对每一个具体的病人,但永远无法顾及每一个家庭的困难。
这不是一个医生能做到的。
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悲剧。
马皑强调,犯罪行为不能因弱势而免责,但整个社会应该有意识关注弱势群体,建立解决机制。
李梦南的冲动导致了一个28岁实习医生的身亡。
王浩再也没有机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王浩在哈医大学习期间获得过国家专业一等奖学金、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
他生长在内蒙古赤峰一个普通的家庭,母亲退休在家,父亲在一家信用社上班,一个弟弟研究生毕业在银行工作。
这些年,先后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读研究生,王浩的父母也不容易。
《中国青年报》报道称,王浩曾经告诉同学,等自己当了医生,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绝对不收红包和回扣。
遇害前,他已在风湿免疫科度过了三年的实习时光。
那里的患者表示,王浩对患者非常耐心。
记者王和岩王晨徐超蓝方
下篇:
谁是受害者
哈医大一院刺医血案震惊全国医疗界。
3月26日,卫生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卫生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
时隔一日,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得到保护。
同时,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
中国医师协会则以“人神共愤,惨无人道”为题,强烈谴责残害医护人员的非法行为。
医患矛盾并未因此缓和。
一位接近哈医大一院的人士透露,事发后,几个科室都陆续出现患者威胁医生,如果治疗得不好,“也要捅医生”。
3月28日,哈医大二院的重症治疗病房又发生患者家属殴打医生事件。
令人震惊的是,在腾讯网站设置的投票中,选择对此事“高兴”的比例高达投票总人数的65%,而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却相对甚少。
甚至,一些人为医生被杀鼓掌叫好,发出“怎么才死一个实习生”的冷血言论。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多位医学界人士和患者看来,医患之间已危机四伏。
专业人士指出,无论患者还是医生,都是扭曲的医疗卫生制度的受害者。
3月27日,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中华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会长凌峰专程赶到哈尔滨,代表神经外科分会参加王浩的追悼会。
凌峰告诉财新记者,一个优秀的医学硕士毕业生,未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理想,就死于这样一个血腥事件,非常令人痛心、愤怒和难过。
凌峰同时也表示,李梦南的生活境况也确实令人同情,弱势群体,没有钱治病。
(帮助)这些人应该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关怀不够。
她希望全社会形成这样一个共识:
“伤害医生等于伤害患者自己!
”
患者怨气何来
“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
求医艰难、医疗资源短缺、医患沟通不畅、患者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悉数成为医患关系恶化的助推力。
在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三甲医院,不少患者的候诊时间超过三小时。
一些外地患者因挂不上号,不得不住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地下室,一等数日。
因为在北京就医,这些患者的医疗费用多数无法在当地报销,不得不自己承担。
3月29日下午,50多位挂号患者挤满了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垂体瘤专诊外的楼道。
一位老人因加号要求被拒绝,拍着分诊台质问护士,“你们这是把患者当亲人的态度吗?
”而护士尚未来得及回答就被另一位急着咨询的患者拽到一边,老人更加愤怒。
同样前来内分泌科就诊的一位山东患者,首次挂号时,从前一天晚8点开始排队,直到翌日清晨7点半,才挂到一位主治医师的诊号。
为这次诊疗,她已在协和医院旁的招待所住了半个月,每天的住宿费100元,“加上饭钱就花得更多了”。
然而,医生诊治时发现她尚未做B超检查,要求检查过再来复诊,她不得不为协和医院的B超检查再排队至少一星期。
另一位来自吉林的患者,除了就诊,还要求多开一点药。
本属于医保目录的药品在吉林当地药店遍寻不获,她只能依靠每次前来北京就诊时多加储备,更因此不得不全部自费,仅其中一种药品每月即需花费840元。
当被问及为何不在当地医院就诊时,上述患者均表示,对所在地医院的医疗水平不放心,已出现多次误诊,宁愿花费更多前来北京,至于“连乘医院电梯都要排队很久,只能认了”。
即便是协和医院的医生,都感慨“到协和医院看病的患者真是太辛苦了”。
哈医大血案发生后,协和医院针对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让16位科室主任“做一天患者”,从早上挂号做起,模拟患者在协和医院就诊的全部过程,并做体验报告。
“拥挤不堪的环境,有些就医流程的繁琐,还有时常挂不上号的无奈。
只有体验了,才真切地感受到患者就医的艰难。
”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晓军说。
北京华信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陈崇学将如今的医生坐诊称为“流水作业”,就在3月26日,他诊疗了逾60位病人,同日坐诊的另一医生则诊疗了逾40位病人。
陈崇学坦言,一天这么多病人,详细了解每人病情的发生、发展和结果时间有限,稍微详细一些,下一位病人就会大声疾催,只好快速诊疗。
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劝告自己的朋友,就医一定要找熟人,否则很难有医生“用心看病”。
一些医院存在的过度用药等不当诊疗行为也深受患者诟病。
由此,当患者为就医付出较高成本,而医疗结果却无法令患者满意时,医患矛盾油然而生。
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恰是医疗纠纷、医患冲突的主要诱因。
以李梦南为例,一家四口靠爷爷一月1000元的低保生活,仅一次使用类克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就花了上万元,且类克不属于医保报销范畴。
疾病花费,对本来经济困难的家庭是雪上加霜。
医生快速流失
医生纷纷改行的根源,还是由于其劳动及所承担的风险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接连发生的医患冲突,更给中国的医护人员和医学生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
医生的执业环境正在日趋恶化,已成为不少医界人士的共同感受。
在惨案发生后的几天,在离哈尔滨千里之外的上海,一个三级医院院长谈到哈尔滨事件,他说:
“我现在做急诊都很害怕,怕病人拿刀捅我。
”他一位学生的父亲在旁落泪:
“没想到儿子从事这么危险的职业。
”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强告诉财新记者,现在医院里年轻医生的流失非常严重,很多医生都去当医药代表,卖医药器械去了。
大量医生索性转行,放弃从事这一行业。
一位曾在协和医院急诊科工作过三年的医生告诉财新记者,三年中180人的急诊科,就有近20人离职,离职者大多不再从事医疗行业。
由于待遇等多方面因素,大医院的医生数量尚可维持。
虽然医生离职转行已很常见,但还有大量较低层级的医院医生转入大医院行医。
目前中国医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李博指出,中小医院医生短缺的现象尤为严重。
如是一来,中小医院医生流失,诊疗水平下降——诊疗水平下降,民众更加不信任小医院,转往大医院——大医院病人多,效益好,待遇好——中小医院医生继续流失。
而在这样的循环中,大医院的医患比持续走高,当医生面对如此之多患者的时候,没有办法同患者做细致的沟通。
在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看来,医生纷纷改行的根源,还是由于其劳动及所承担的风险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
他举例说,现在做整形美容的医生,基本上都在民营医院。
这些医院收费很高,对医生的补偿非常丰厚。
虽然做整形这个行当也有纠纷,但高收入给了医生补偿,医生就愿意干下去。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医学专业后继无人。
中国医师协会在2011年进行了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希望自己子女从医的医师仅6.83%,而不希望的达到78.01%。
而在2002年的首次调查中,两项比例分别为10.89%和53.96%。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说,以后医学世家会越来越少。
中国内地主要大学医学院录取分数,持续在低位徘徊。
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八年制班在北京的平均录取分比北大校本部低15分左右。
而近五年来上海交大医学院在上海的录取分数线更是比校本部低25分至60分(上海卷满分630分)。
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情况则更为典型,2006年复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上海的平均录取分数比复旦大学全校平均分数高4分;而到了2010年,临床医学在沪平均录取分数却比全校平均分低了6分。
足见医学生质量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李惠娟说,现在好大夫都担忧,自己将来生病会落在二流的人手里。
北大、复旦等医学院校尚且如此,一般的医学院校招生则更困难。
厦门大学于1996年创建医学院,由于建院较晚起点相对较低,医学院在厦大一直是较冷的专业。
2011年厦大曾将医学生学费从每年6760元调降到5460元,而2012年则宣布医学生全面免费,目的即是吸引优秀生源报考。
许多医学院学生在实习时都经历过医患冲突,甚至还有被打骂的经历,这些都给医学生的职业选择带来阴影。
还有医学生告诉财新记者,现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常向学生讲医患矛盾的尖锐。
此次哈医大一院医生被刺事件后,医学生群体的失望和愤懑更被推到极致。
临床专业的医学生放弃从医,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北京华信医院急诊科医师栾禹博从医四年,32位同班同学现在仍在从医的仅有21个。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李博告诉财新记者,他的大学同学已有一半多没有继续做医生了。
恶性循环
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并非简单的医疗资源不足,而是没有有序配置
为了缓解“看病贵、看病难”,中国政府启动新医改已近三年。
2012年“两会”期间,卫生部长陈竺透露,三年来,全国财政对医改新增投入已超1.1万多亿元人民币,未来还将不断加大投入。
为何医改不断深化,投入不断增多,但医患冲突愈演愈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即便如此,现在医疗投入仍严重不足。
医改强调医疗服务的公益性,但是公益性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医院只是公益性的载体。
政府作为公益性的主体投入不足,就把矛盾下放到了医院。
中国的公共医疗投入占财政的比例才百分之四点几,这个比例太低了。
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还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根在政府的政策错位。
由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公立医院不得不自行创收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