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留情.docx
《张爱玲留情.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爱玲留情.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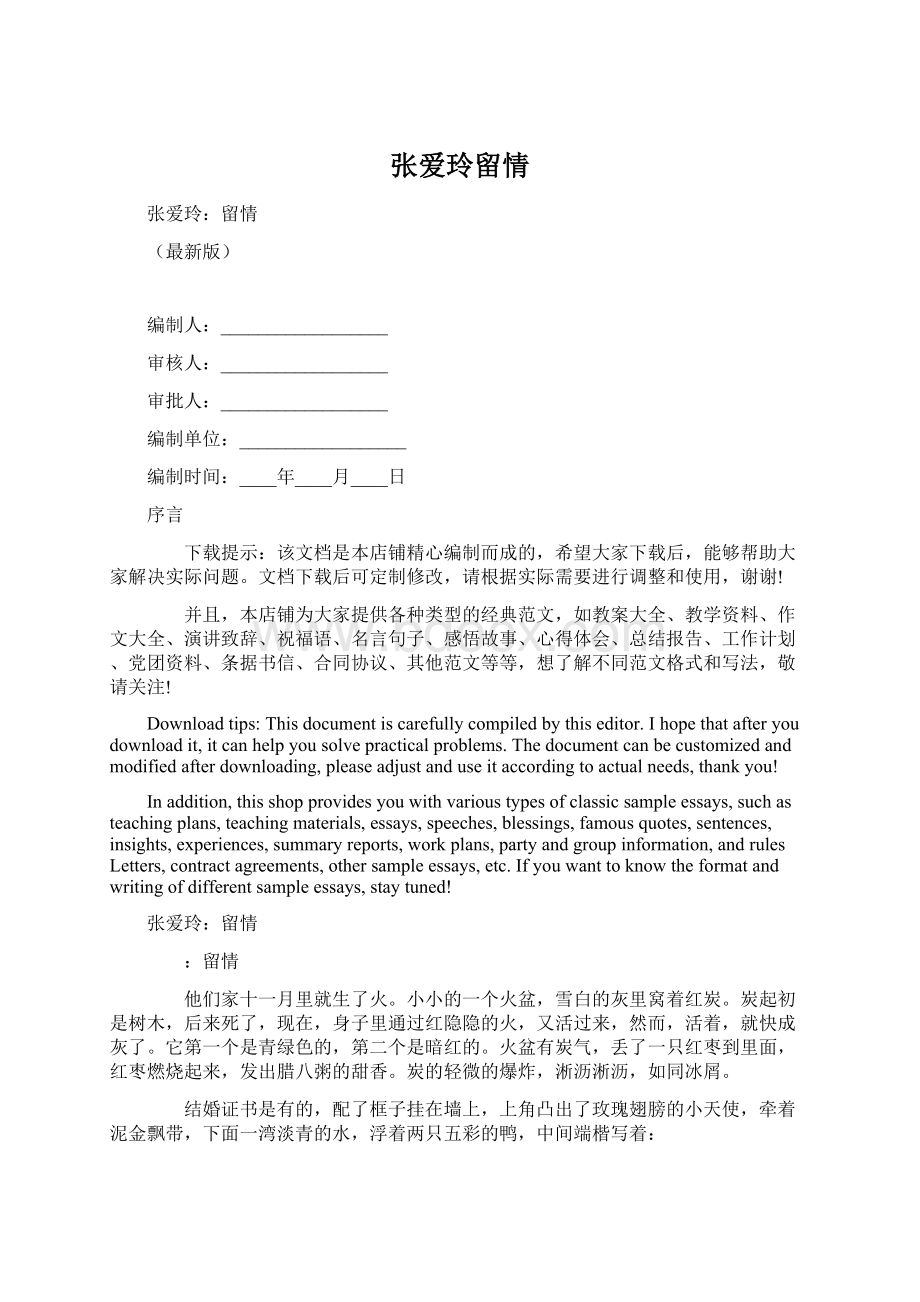
张爱玲留情
张爱玲:
留情
(最新版)
编制人:
__________________
审核人:
__________________
审批人:
__________________
编制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
编制时间:
____年____月____日
序言
下载提示:
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文档下载后可定制修改,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使用,谢谢!
并且,本店铺为大家提供各种类型的经典范文,如教案大全、教学资料、作文大全、演讲致辞、祝福语、名言句子、感悟故事、心得体会、总结报告、工作计划、党团资料、条据书信、合同协议、其他范文等等,想了解不同范文格式和写法,敬请关注!
Downloadtips:
Thisdocumentiscarefullycompiledbythiseditor.Ihopethatafteryoudownloadit,itcanhelpyousolvepracticalproblems.Thedocumentcanbecustomizedandmodifiedafterdownloading,pleaseadjustanduseitaccordingtoactualneeds,thankyou!
Inaddition,thisshopprovidesyouwithvarioustypesofclassicsampleessays,suchasteachingplans,teachingmaterials,essays,speeches,blessings,famousquotes,sentences,insights,experiences,summaryreports,workplans,partyandgroupinformation,andrulesLetters,contractagreements,othersampleessays,etc.Ifyouwanttoknowtheformatandwritingofdifferentsampleessays,staytuned!
张爱玲:
留情
:
留情
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
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
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
它第一个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的。
火盆有炭气,丢了一只红枣到里面,红枣燃烧起来,发出腊八粥的甜香。
炭的轻微的爆炸,淅沥淅沥,如同冰屑。
结婚证书是有的,配了框子挂在墙上,上角凸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下面一湾淡青的水,浮着两只五彩的鸭,中间端楷写着:
“米晶尧 安徽省无为县人 现年五十九岁 光绪十一年乙酉正月十一日亥时生
淳于敦凤 江苏省无锡县人 现年三十六岁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九日申时生……”
敦凤站在框子底下,一只腿跪在沙发上,就着光,数绒线的针子。
米晶尧搭讪着走去拿外套,说:
“我出去一会儿。
”敦凤低着头只顾数,轻轻动着嘴唇。
米晶尧大衣穿了一半,又看着她,无可奈何地微笑着。
半晌,敦凤抬起头来,说:
“唔?
”又去看她的绒线,是灰色的,牵牵绊绊许多小白疙瘩。
米先生道,“我去一会儿就来。
”话真是难说:
如果说“到那边去”,这边那边的!
说:
“到小沙渡路去,”就等于说小沙渡路有个公馆,这里又有个公馆。
从前他提起他那个太太总是说“她”,后来敦凤跟他说明了:
“哪作兴这样说的?
”于是他难得提起来的时候,只得用个秃头的句子。
现在他说:
“病得不轻呢。
我得看看去。
”敦凤短短说了一声:
“你去呀。
”
听她那口音,米先生倒又不便走了,手扶着窗台往外看去,自言自语道:
“不知下雨不下?
”敦凤像是有点不耐烦,把绒线卷卷,向花布袋里一塞,要走出去的样子。
才开了门,米先生却又拦着她,解释道:
“不是的──这些年了……病得很厉害的,又没人管事,好像我总不能不──”敦凤急了,道:
“跟我说这些个!
让人听见了算什么呢?
”张妈在半开门的浴室里洗衣裳。
张妈是他家的旧人,知道底细的,待会儿还当她拉着他不许他回去看他太太的病,岂不是笑话!
敦凤立在门口,叫了声“张妈!
”吩咐道:
“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两样素菜不用留了,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火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焐着,啊!
”她和佣人说话,有一种特殊的沉淀的声调,很苍老,脾气很坏似的,却又有点腻搭搭,像个权威的鸨母。
她那没有下颏的下颏仰得高高地,滴粉搓酥的圆胖脸饱饱地往下坠着,搭拉着眼皮,希腊型的正直端丽的鼻子往上一抬,更显得那细小的鼻孔的高贵。
敦凤出身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十六岁出嫁,二十三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方才嫁了米先生。
现在很快乐,但也不过分,因为总是经过了那一番的了。
她摸摸头发,头发前面塞了棉花团,垫得高高地,脑后做成一个一个整洁的小横卷子,和她脑子里的思想一样地有条有理。
她拿皮包,拿网袋,披上大衣。
包在一层层衣服里的她的白胖的身体,实哚哚地像个清水粽子。
旗袍做得很大方,并不太小,不知为什么,里面总像是鼓绷绷,衬里穿了钢条小紧身似的。
米先生跟过来问道:
“你也要出去么?
”敦凤道:
“我到舅母家去了,反正你的饭也不见得回来吃了,省得家里还要弄饭。
今天本来也没有我吃的菜,一个砂锅,一个鱼冻子,都是特为给你做的。
”米先生回到客室里,立在书桌前面,高高一迭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它齐了一齐,青玉印色盒子,冰纹笔筒,水盂,铜匙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阴天,更显得家里的窗明几净。
敦凤再出来,他还在那里挪挪这个,摸摸那个,腰只能略略弯着,因为穿了僵硬的大衣,而且年纪大了,肚子在中间碍事。
敦凤淡淡问道:
“咦?
你还没走?
”他笑了一笑,也不回答。
她挽了皮包网袋出门,他也跟了出来。
她只当不看见,快步走到对街去,又怕他在后面气喘吁吁追赶,她虽然和他生着气,也不愿使他露出老态,因此有意地拣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才过街,耽搁了一会。
走了好一截子路,才知道天在下雨。
一点点小雨,就像是天气的寒丝丝,全然不觉得是雨。
敦凤怕她的皮领子给打潮了,待要把大衣脱下来,手里又有太多的累赘。
米先生把她的皮包网袋,装绒线的镶花麻布袋一一接了过来,问道:
“怎么?
要脱大衣?
”又道:
“别冻着了,叫部三轮车罢。
”等他叫了部双人的车,敦凤方才说道:
“你同我又不顺路!
”米先生道:
“我跟你一块儿去。
”敦凤在她那松肥的黑皮领子里回过头来,似笑非笑眱了他一眼。
她从小跟着她父亲的老姨太太长大,结了婚又生活在夫家的姨太太羣中,不知不觉养成了老法长三堂子那一路的娇媚。
两人坐一部车,平平驶入住宅区的一条马路。
路边缺进去一块空地,乌黑的沙砾,杂着棕绿的草皮,一座棕黑的小洋房,泛了色的淡蓝漆的百叶窗,悄悄的,在雨中,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显着的外国的感觉。
米先生不由得想起从前他留学的时候。
他再回过头去,沙砾地上蹲着一只黑狗,卷着小小的耳朵。
润湿的黑毛微微卷曲,身子向前探着,非常注意地,也不知它是听着什么还是看着什么。
米先生想起老式留声机的狗商标,开了话匣子跳舞,西洋女人圆领口里腾起的体温与气味。
又想起他第一个小孩的玩具中的一只寸许高的绿玻璃小狗,也是这样蹲着,眼里嵌着两粒红圈小水钻。
想起那半透明暗绿玻璃的小狗,牙齿就发酸,也许他逗着孩子玩,啃过它,也许他阻止孩子放到嘴里去啃,自己嘴里,由于同情,也发冷发酸──记不清了。
他第一个孩子是在外国生的,他太太是个女同学,广东人。
从前那时候,外国的中国女学生是非常难得的,遇见了,很快地就发生感情,结婚了。
太太脾气一直是神经质的,后来更暴躁,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都同她吵翻了,幸而他们都到内地读书去了,少了些冲突。
这些年来他很少同她在一起,就连过去要好的时候,日子也过得仓促胡涂,只记得一趟趟的吵架,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快乐的回忆,然而还是那些年青痛苦,仓皇的岁月,真正触到了他的心,使他现在想起来,飞灰似的霏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面去,眼睛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
:
牛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
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
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
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
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
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
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
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
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他吃了一惊——听见背后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回头去看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一样也在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
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他们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
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
太阳晒到干菜上,随风飘出一种温和的臭味。
“到底打定主意怎样?
”她兜起蓝围裙来揩眼。
“……不怎样。
”“不怎样!
眼见就要立春了,家家牵了牛上田,我们的牛呢?
”“明天我上三婶娘家去借,去借!
”他不耐烦地将烟管托托敲着栏。
“是的,说白话倒容易!
三婶娘同我们本是好亲好邻的,去年人家来借几升米,你不肯,现在反过来求人,人家倒肯?
”
他的不耐烦显然是增进了,越恨她揭他这个忏悔过的痛疮,她偏要揭。
说起来原该怪他自己得罪了一向好说话的三婶娘,然而她竟捉住了这个屡次作嘲讽的把柄——
“明天找蒋天贵去!
”他背过身去,表示不愿意多搭话,然而她仿佛永远不能将他的答复认为满足似的——
“天贵娘子当众说过的,要借牛,先付租钱。
”
他垂下眼去,弯腰把小鸡捉在手中,翻来覆去验看它突出的肋骨和细瘦的腿;小鸡在他的掌心里吱吱地叫。
“不,不!
”她激动地喊着,她已经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
她这时似乎显得比平时更苍老一点,虽然她只是三十岁才满的人,她那棕色的柔驯的眼睛,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这一趟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了!
天哪!
先是我那牛……我那牛……活活给人牵去了,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这两只小鸡了!
你一个男子汉,只会打算我的东西——我问你,小鸡是谁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
我问你哪——”她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
“闹着要借牛也是你,舍不得鸡也是你!
”禄兴背过脸去吸烟,拈了一块干菜在手里,嗅了嗅,仍旧放在水槽上。
“就我一人舍不得——”她从禄兴肩膀后面竭力地把脸伸过来。
“你——你大气,你把房子送人也舍得!
我才犯不着呢!
何苦来,吃辛吃苦为人家把家握产,只落得这!
皇天在上头——先抢走我那牛,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鸡了!
依你的意思,不如拿把刀来记我身上肉一片片剁下去送人倒干净!
省得下次又出新花样!
”
禄兴不做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墙头上淡淡的斜阳影子,他知道女人的话是不必认真的,不到太阳落山她就会软化起来。
到底借牛是正经事——不耕田,难道活等饿死吗?
这个,她虽然是女人,也懂得的。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
烟囱里正蓬蓬地冒炊烟,薰得月色迷迷□□,鸡已经关在笼里了,低低地,吱吱咯咯叫着。
茅屋里门半开着,漏出一线桔红的油灯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口把整个的门全塞满了,那是禄兴,叉着腰在吸旱烟,他在想,明天,同样的晚上,少了鸡群吱吱咯咯的叫声,该是多么寂寞的一晚啊!
后天的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也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碰洒人一身。
树丛中露出一个个圆圆的土馒头,牵牛花缠绕着坟尖,把它那粉紫色的小喇叭直伸进暴露在黄泥外的破烂棺材里去。
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人唱着歌经过它们。
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的,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
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使他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放牛的孩子负着主人的使命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了他们。
他开始赶牛了。
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它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
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棉袄上,使他浑身都出了汗。
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杂种畜牲!
欺负你老子,单单欺负你老子!
”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
“你——你——你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牛的瞳仁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它那么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使禄兴很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
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
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
一面滚,他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
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
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打颤的声音告诉: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
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一九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