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docx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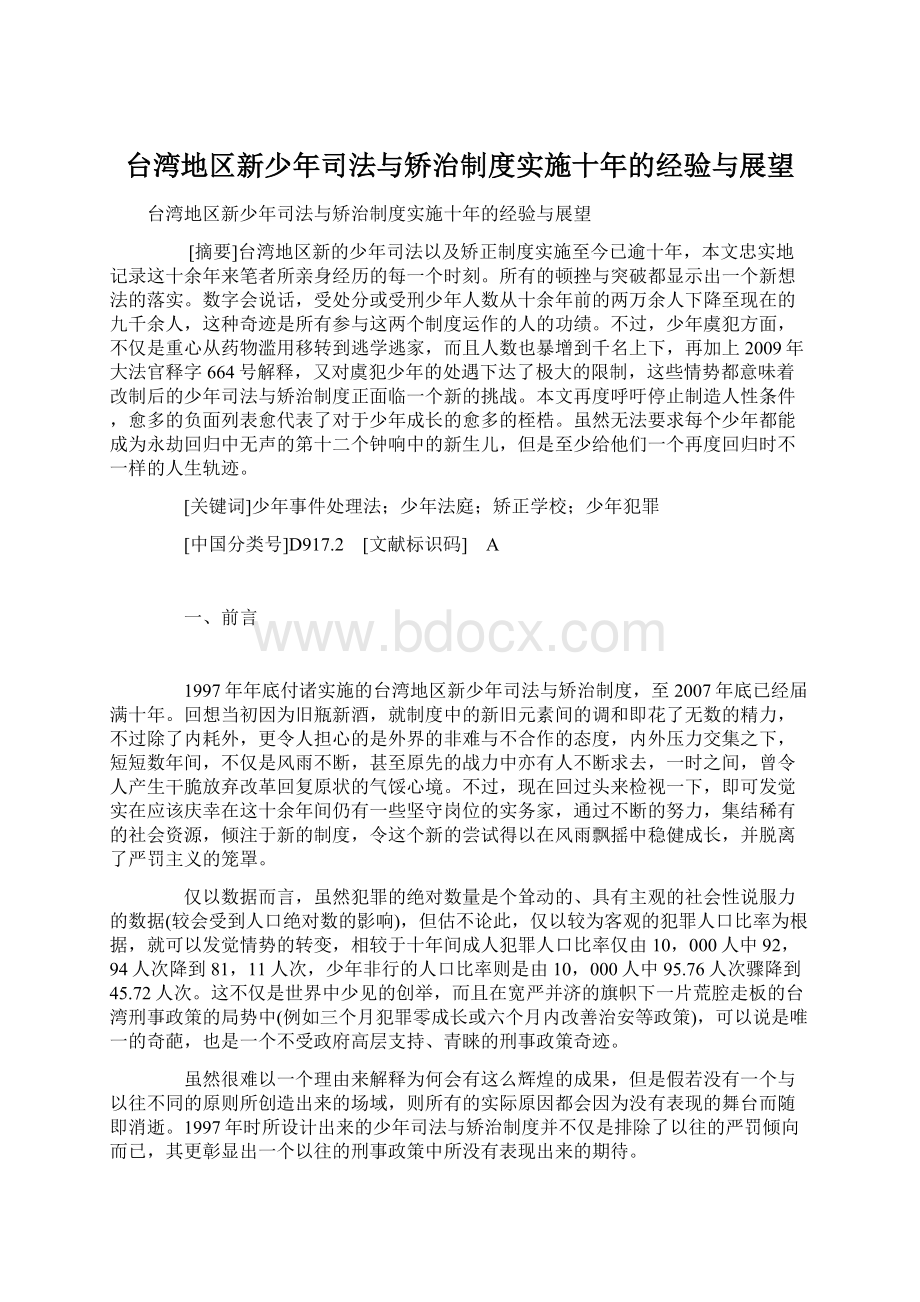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
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实施十年的经验与展望
[摘要]台湾地区新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正制度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本文忠实地记录这十余年来笔者所亲身经历的每一个时刻。
所有的顿挫与突破都显示出一个新想法的落实。
数字会说话,受处分或受刑少年人数从十余年前的两万余人下降至现在的九千余人,这种奇迹是所有参与这两个制度运作的人的功绩。
不过,少年虞犯方面,不仅是重心从药物滥用移转到逃学逃家,而且人数也暴增到千名上下,再加上2009年大法官释字664号解释,又对虞犯少年的处遇下达了极大的限制,这些情势都意味着改制后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正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本文再度呼吁停止制造人性条件,愈多的负面列表愈代表了对于少年成长的愈多的桎梏。
虽然无法要求每个少年都能成为永劫回归中无声的第十二个钟响中的新生儿,但是至少给他们一个再度回归时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关键词]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法庭;矫正学校;少年犯罪
[中国分类号]D917.2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1997年年底付诸实施的台湾地区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至2007年底已经届满十年。
回想当初因为旧瓶新酒,就制度中的新旧元素间的调和即花了无数的精力,不过除了内耗外,更令人担心的是外界的非难与不合作的态度,内外压力交集之下,短短数年间,不仅是风雨不断,甚至原先的战力中亦有人不断求去,一时之间,曾令人产生干脆放弃改革回复原状的气馁心境。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一下,即可发觉实在应该庆幸在这十余年间仍有一些坚守岗位的实务家,通过不断的努力,集结稀有的社会资源,倾注于新的制度,令这个新的尝试得以在风雨飘摇中稳健成长,并脱离了严罚主义的笼罩。
仅以数据而言,虽然犯罪的绝对数量是个耸动的、具有主观的社会性说服力的数据(较会受到人口绝对数的影响),但估不论此,仅以较为客观的犯罪人口比率为根据,就可以发觉情势的转变,相较于十年间成人犯罪人口比率仅由10,000人中92,94人次降到81,11人次,少年非行的人口比率则是由10,000人中95.76人次骤降到45.72人次。
这不仅是世界中少见的创举,而且在宽严并济的旗帜下一片荒腔走板的台湾刑事政策的局势中(例如三个月犯罪零成长或六个月内改善治安等政策),可以说是唯一的奇葩,也是一个不受政府高层支持、青睐的刑事政策奇迹。
虽然很难以一个理由来解释为何会有这么辉煌的成果,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原则所创造出来的场域,则所有的实际原因都会因为没有表现的舞台而随即消逝。
1997年时所设计出来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并不仅是排除了以往的严罚倾向而已,其更彰显出一个以往的刑事政策中所没有表现出来的期待。
换言之,虽然以往的刑事政策有循环的倾向,例如严酷的身体刑之后是较为宽松的具教育倾向的自由刑,而矫治思维退潮后,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正义模式下的自由刑与无孔不入的社会监视,但是1997年所设计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并不是以过往的、浓稠的国亲思想下的温情主义代替当时的严罚倾向,这种温情主义会在爱的司法的名义下展开过度绵密的矫治计划,而不管是严格的处罚抑或绵密的温情,这些都是一种规训,一种形象的创造,正如同身体刑、自由刑间的变化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一样,严罚与温情间的变化亦是对于“政治的生”的一种操控的表现而已。
基于这种反思,1997年所创造出来的制度是一个尊重多元力量的相互抗争以及展现出活生生的生命跃动的混沌,不以一个超越的、超然的理性予以规制,反倒是仅以复杂的、无方向性的系统维持住所有的生命跃动迹象,并适度减轻其间的矛盾、冲突,或更进一步地促成多样的可能性的制度。
法律这个制度基本上应该是利用法律语言的暴力将复杂、矛盾的社会事实解释成一个可以用较为简单的原则予以理解的法律事实,并以此为基础,而形塑出符合绝对的、普世的公平正义要求的解决方案。
但是反于这类的传统论述,这个新的法律制度是以法律的语言确保了非法律的世界,亦即其是存在于法律与非法的细缝中的特异存在,所以才说这是一个新的期待。
撇开绕口难懂的哲学论述,以通俗的法律用语而言,如不忌讳误解,这个制度不外是一种另类的不干涉(hands-off)主义的实践。
亦即,相信社会中的自愈能力,尽可能不处理轻微的犯行,对于严重的犯罪,亦是以人际关系的修复以及自信的回复为重心,仅提供处遇对象一个自力救济的能力培养机会而已。
所有的道德训诫、真理传述等,在此制度下都是一种荒谬。
本文的初稿曾发表于2007年9月在京都举办的日本龙谷大学矫正讲座三十周年纪念研讨会,经增删后已刊登在该校的定期刊物中,不过一方面这是篇日文的文章,而发表的杂志于日本国外亦难以得手,另一方面论文发表后,关于虞犯的部分有了新的发展,所以在再度施以增删后(减少介绍性的部分,增加理论方面的论述),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此。
制度实施已逾十年,最近台湾的“司法院”拟着手进行通盘的修订。
虽然本文于行文上不甚符合笔者以往的风格(本文仅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无多少批判倾向),但为敦促当局重视这十年来努力的成果,希望“司法院”不要更动难得已经确立下来的基础,所以仍羞愧地以一般人轻易即可得手的方式,表达笔者的企求。
以下先透过台湾现行制度成立经纬的介绍,说明制度的概要,然后一方面铺陈近十年来光鲜亮丽的成果,另一方面亦指摘出隐藏在少年非行现状后的问题点,藉此对台湾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的未来寄以期待与厚望。
二、现行制度的成立经纬与概要
台湾地区的少年司法以及矫治制度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式成立。
于1954年7月,“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现在的“法务部”)在教育与保护已取代严罚与威吓成为国际潮流的宣言下,委托以台湾大学林纪东教授为首的“少年法项目小组”来研拟符合时代要求的少年司法制度。
而这个法律研拟小组亦于极短的期间内,在翌年的1955年12月向“行政院”提出少年法草案。
这是台湾地区现代型少年法的肇始。
纵或这个法案其实仅是当时日本少年法的翻译,但是一方面没有美国强而有力的干涉,另一方面在当时台湾社会的紊乱状况下,事实上此法亦难以付诸实施,所以这种先进的立法是没有可能毫无修订地即通过保守的“立法院”的审议。
果真在1962年,“立法院”在冗长的审议后,将“少年法”改名为“少年事件处理法”,删除第一条的目的规定,于名称与目的上削减福利法的意涵,而强调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性质,并斥退设置与地方法院同级的少年法院的建议,改采与地方法院刑庭相同组织地位的少年法庭的体例,允许地方法院刑庭法官兼任少年法庭法官,最后亦将具有福利意涵的“保护处分”改名为管理训练意义明确的“管训处分”,令实质上是刑庭法官的少年法庭法官掌管刑事案件与管训事件的审判与审理(与日本法制不同,当时台湾已经规定在逆送案件的情形,检察官于搜查后,应向少年法庭起诉,所以少年法庭是同时管辖刑事案件与管训事件)。
而台湾的少年司法即在这种诡谲的气氛中所订立的符合“国际潮流”的基本法律下,展开了现代历史的第一页。
其后,这个法律在没有付诸实施的情形下,就被忽视了十年。
在此期间,政府根本没有致
三、挫折与努力
如上所述,台湾的新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是在一个欠缺共识的情形下,力挽严罚的狂澜而勉强付诸实现的制度。
制度的设计比以往更为复杂且难以操作。
此际即需要一些得柔软对应的实务家参与。
在这种的理解下,于制度实施的前几年,相关人士与部会即付出了许多的心力致力于人员的训练。
首先是法官的选拔与训练。
于新制度实施后不久,司法院就设计了一连串的训练课程并了以实施,几乎隔年就会开设初级、中级课程以及实务研讨会,以三四十名的规模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因为调训不易,所以这类的训练课程大体上都仅能举办数天,但是有鉴于台湾地区法学教育上的缺陷,当局活用了这些难得挪出的时间,将课程的重点移到法律以外所需专业知识的传授与启迪,数年下来,亦似乎有了一定的成果。
初级课程主要是简介制度的营运、少年心理学及犯罪学、人际关系的重建、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整合等;而中级课程则以初级课程为基础,讲授更为细致的部分,例如心理测验、处遇技巧的介绍与实作、司法与社会福利设施问的联系等;至于实务研讨会则是以实际上参与审理、审判的少年法官或拥有专业证照(后述)的法官为对象,进行一些外国法制的介绍以及台湾地区实例研讨等活动。
当然不仅是法官,对于其它的少年观护人,当局亦提供了相类似的讲习与研讨会的机会。
比较特殊的是针对法官的资格,“司法院”采行了专业证照制度。
虽然并不完全,但是现在大体上而言,若无“司法院”所颁发的少年法官证照,是无法担当少年法官的。
亦即少年法官除透过国家考试以及司法官训练所获得法官资格外,另需于成为一般法官后经过“司法院”的审核会议获得少年法官的证照,不然不得进行少年事件或案件的审理、审判④。
至今为止,“司法院”已经举行了两次的审核会议。
申请者除接受其相关适性的心理测验外,另需提出有关少年司法审理等的小论文(亦可以上述训练课程的心得报告代替),当然至今为止的相关“业绩”也会成为参考资料(院方提供)。
2004年时共有七十三名法官申请,合格者为五十一名;而2006年则是十四名申请,十二名合格。
由此可见,这个审核机制并不是个有申请即合格的浮滥审查。
对于合格者“司法院”会颁发有效期间四年的专业证照,过期后需再度申请市核。
但是纵或获得专业证照,只要没有少年法官的空缺,仍是无法当少年法庭或少年法院的法官。
当然多年来的严罚积习(更明确而言是不在乎少年是个实存的积习)是不可能仅以以上的努力即可克服。
2000年时在台中地方法院就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不祥事件。
台中地院少年法庭对于一位在四楼教室向对街的司法官宿舍投掷了一颗网球的未满十二岁范姓少年,以其触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重罪为由,而裁定了假日辅导的保护处分。
处分虽然很轻,但是一来法官不仅故意扭曲了交通往来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解释(主要是因为想藉此而警告该国中的其它同学),另一方面,法官也借口撤换了原先建议不付审理的调查官,在滥用协商式审理的情形下,下达了保护处分的裁定。
此事经过报导而引起立法委员的关心,进而发展成社会事件。
笔者还因为此事而专程拜访该国中,演讲“少年事件处理法”的精神,并且还将此事当成反省的材料而写入学术论文中。
事后,该名法官离开少年法官的职位,而另一位少年法官则直接负起执行假日辅导的工作,极力安抚少年的心情。
据这位现在已经因为身心俱疲而离开少年法官职务的法官所云,事件发生后,台中地方法院中以少年法庭法官以及观护人为主所组成的自主研习活动是更加地频繁举行。
由此事件可知,少年司法已经有了急遽的转变,并且“少年事件处理法”的基本精神已日渐落实,在以往若有类似事件发生,应该是会静静地被压制下来而不了了之。
比起以上“司法院”方面所做的努力,“行政院”方面则显得比较消极。
“行政院”的“法务部”本来是掌管所有收容非行少年的机构,但是在新的少年事件处理法中因为新增添了早期以及后期的转介机制,而因为这个转介机制的存在,导致“行政院”儿童局或地方政府社会局所掌管的收容式福利设施亦开始成为矫治、保护非行少年的制度中的一环。
不过,政府抑或该当社福收容机构都对非行少年的处遇毫不关心。
基本上他们是认为既然转介的裁定是由法院所为,则其后的处遇亦应该由法院负起责任,就像假若社会局下令收容,则收容的费用等自然是由社会局自行负担一样。
结果,法院方面在苦无对策的情形下,只好以独立预算的方式自行筹措收容费用,并以支付收容费的方式,勉强地将少年收容于社福机构。
事实上,纵或法院裁定转介甚至指定收容处所,如果没有经过事前协调,社福机构还是经常拒绝收容的。
纵或在这种情况下,若干少年法庭仍不放弃努力,一方面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亦不断加强与社福机构的联系,在这些人的热心奉献下,至少在早期转介的领域,已经有了确实的进步。
“行政院”方面的消极态度不仅是存在于社福单位,在应与矫正教育息息相关的教育单位的反应中,更可察觉到让第一线的法务或教育人员等感到寒心的态度。
于少年监狱与辅育院并存的时代,有关收容少年的教育问题,一律都是委诸“行政院法务部”研拟与执行。
而“法务部”方面,虽然对军事化生活管理、道德教育方面有所专长,但对于学科教育、职业教育等,则仅能委诸外部的兼任教师。
当然虽然名为生活管理、道德教育,但是本质上仅是一种一元化的规训管理而已,而学科教育方面,兼课的教师于下课后亦不可能留在设施内与收容人进行人际关系间的活动。
在这种的生活环境下,是不难想象收容人仅是在一元的环境下朝向既定的目标而接受训导,与日后应该要有的折冲社会与个人心理中的诸元的矛盾、活用人际关系、发展与善用自信等的能力的养成几乎是处于无缘的状态。
为改善这种现象,在矫正学校成立后,除导入校长、专职教员等具有与以往迥异的特质的人员外,另将课程区分为一般教育(以学科教育为主)与特殊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主),但更重要的是提供由辅导教师担当的辅导教育藉以撑起两者间的连结。
虽然教育的领域中亦不存在与特殊的矫正教育相关的学程与知识,但是“教育部”至少比警政系统的“法务部矫正司”更容易发展出特定的知识与技术。
所以少年矫正学校设置及教育实施通则规定教育单位应该负起协助矫正学校实施矫正教育的责任,并且为了加强法务与教育间的协调,通则也成立了允许外部专家参与的“少年矫正学校矫正教育委员会”。
这是一个跨部会的委员会,功能在于提供相关单位有关校长及教师遴聘、训练、教材开发、研究等事项的咨询,因为两矫正学校的校长与教师代表亦会出席,除咨询外,更有作为实务间沟通交流平台的效果。
这个委员会在初期的一两年,虽然频繁地开会,并适度地提供策略解决了一些例如教师研究奖励、学生学籍管理以及学生出校后更生联系等的问题,但是在当时“教育部”已经展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在数年后连“法务部”也都认为委员会功能不彰而实际上停止召开会议,改采自力救济的策略。
或许从一开始“法务部”即知道“教育部”不会有积极的参与意愿,所以不论是校长与教师遴选、训练抑或教材的编撰与研发等,其均自行筹措经费,而人力支持方面亦是以“法务部”的人手为主辅以相关外部人士的力量。
在这种艰困孤独的情事下,两所矫正学校在第一年克服了严酷的勤务条件,成功地达成了确保三分之二人力的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法务部”内也非绝无异议,终究矫正学校这个体制是个“外来的异物”,原先的身体当然会产生抗体。
除去一些人事上的倾轧事故外(主要是些发生在第一线法务与教育系统问磨合机制上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所剩两所辅育院的改制以及教育风格的更迭。
依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于通则实施后六年内“法务部”得分阶段将少年监狱与辅育院改制成矫正学校(改制完成后,少年辅育院条例会自动失效)。
虽然第一阶段的新竹少年监与高雄辅育院在紧锣密鼓的气氛下,顺利改制成功,但是其后因经费与人事短缺的问题,在无任何其它政府机关的外援下,“法务部”只得曲解法条文义(法条中的“得”是指“应”,但“法务部”却将此字改为有是否改制的裁量权的“可以”),一直迟未将所剩两所辅育院改制成矫正学校。
在一国两制的情形下,冲突自是难免,此事在经费拮据的情事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与以往的少年监狱、辅育院不同,矫正学校在处遇方面放弃了廉价的军事训练、职业训练或学科教育,而改采以人际关系的修复与自信的重建为重心的处遇,据此其处遇是在小班编制下每班均配置专科教师、辅导教师与教导员的体制下进行的。
这种处遇体制造成了庞大的人事经费负担。
比起残存的辅育院,其每名收容少年一年仅花台币十一万,矫正学校方面,则是高达一名一年新台币五十万。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内部引起了极为荒谬的批判,谓既然多花五倍的钱,则必须达成五倍的效果。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任务,纵或处遇效果可以用所费金额予以计算,在效果递减的情况下,花五倍的钱也无法确保五倍的效果,但是这类的耳语还是影响到了“法务部”的高层。
2002年当时的“法务部”部长陈定南认为所谓的业绩是以拿到多少职业证照来加以计算,其并主张读书拿毕业证书等是白领阶级的工作,这些在~般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失败过的收容少年,既然不喜欢读书,则应该尽早学习专门技术,取得职业证照后,就“黑手”的工作,更生复归,以此回报国家与社会的恩惠。
这虽然是个非常务实,也适度地表达了社会一般观感的见解,但是却是与新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的精神相违背的发言;此外,如果矫正学校内的处遇全面偏向于职业教育,则发展了数年的以人际关系的修复与自信的回复为重心的处遇方针将会遭到修正,甚至于消失。
在这种气氛下,2002年12月28日,为确定矫正学校内的处遇方针,
“法务部”召集了部内相关人士(部长、司长、专员以及两所辅育院的代表)、两所矫正学校的校长与教师代表、部外专家以及有两种不一样的设施的收容经验的出校生等,于新竹的矫正学校召开了首次的少年矫正学校之现状与展望座谈会。
会中不仅是第一线的教师与部外专家均一致肯认矫正学校的教育方针,甚至于那些被部长讥讽为特别选定的出校生亦一致反驳部长的指控,并明确表明在矫正学校的生活中确实感受到被尊重的感觉,从此而有好好活下去的自信。
其后虽然仍有不少的大小风波,例如校长聘书任期事件、南部黑函事件、绿岛移送事件等,令相关人土头痛不已,但是整体而言,矫正学校的处遇方针已经被确认,至今现场第一线的处遇担当者仍旧是日以继夜地在人际关系修复与自信回复的标语下,确实地开发、实施多样的矫正教育课程。
四、惊异的少年非行趋势
如上所述,台湾新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在历经波澜万丈的十年洗礼后,现在表面上已经逐渐稳定下来,但这不是意味着往后将是手拉手心连心共创光明灿烂的未来,事实上整个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汲取多元力量展现矛盾与冲突,并且就解决方案仅提供磨合的机制而已,所以假若上级指导方针、处遇的实际以及受处遇的少年均平静稳定下来,不再冲突跃动,那才是宣告此制度已经死亡的时刻。
在司法制度方面,虽然不能说是个崭新的创见,但是在摒弃严罚与爱的司法这两个极端的作为上,自然有其特异之处,且实务上亦不乏绽放异彩的事例。
至于矫正学校方面,则完完全全是个可以取代现在已经没落的外役监制度,而成为代表台湾向全世界展示的新制度。
虽是如此,对于这两个动荡中,而且也被期待会继续动荡的制度,除少数几本硕博士论文外,至今仍未有关于其成效的完整的、全面性的实证性学术研究。
于此无法深究原因何在,不过针对少年非行国内的研究倾向是比较偏重于原因研究一事应该是个重要的因素。
而且在重视原因论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认为“去除原因”一事就是应采的刑事政策内容,毫不深思原因与政策间可以加以区隔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与原因论相区隔的立法论、制度论或政策论当然会不太发达,自然也不会重视制度施行效果的分析。
不过,纵或从原因论与去除原因的政策相结合的观点而重视政策实效,此际亦会发生问题。
例如少年非行的原因如果是设定(美其名为研究成果)为好奇心强、心性不定、同侪影响、经济困窘,则事实上这些都是彰显何谓“优良”的负面列表,此际处遇是否有效果的指针将会是这些负面列表中的诸条件的去除,或作为负面列表中所有条件的复合结果的再犯可能性的去除;如果处遇没有成功,则可将被处遇人贴上德行不佳的标签,将之送回社会中,当成负面样版使用,藉此另可使得社会大众将他律地所设定的优良条件内化到其生活领域;这不外是一种内在化的社会控制技术,一种无法逃脱的桎梏。
更可怕的是,当社会大众接受了程度颇高的德行要求,但又发觉自身于社会生活中无法达成这种高标的道德水准时,会产生一种集团性的羞愧感,而这种羞愧感会让一般人开始崇拜具有虚假的道德形象的领导者;当贬抑败德者、掩饰自我的羞愧、进行造神运动的机制成形后,具有一般性、同构型以及强制性的法律制度会将这个机制推广到社会中的任何角落,此际“自律地遵守法律”这个形式意义非常浓厚的道德将会取代或许深思后即可能产生质疑的实质道德内涵,而成为规训这个社会的最大工具(民主法治),法化社会于焉诞生,活蹦乱跳的生命将会趋于死寂。
新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不是基于以上观点而设计的。
这是一个法律制度,但是在这个法律制度内所创造出来的是一个非法律的世界。
不管是争功诿过的私欲横流还是利益的折冲,或甚至妥协的沟通都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而且不会受到否定的评价,反倒是被视为是一种产生变化的契机,也只有在充满矛盾冲突的自然中,人们才有可能学会真正的生活态度,并寻找真正的自由。
当然虽然社会中仍有许多虚伪之处,但是比较起国家所营造的环境,还是会更靠近“自然”些,所以纵或应尽可能营造出接近自然的国家环境,但是基本上仍应将此视为最后手段,而极度尊重社会与个人的自然愈合能力。
以此为根本,则判定制度是否有效的基准将不会是内容浓郁的原因去除与否以及再犯率是否降低,而是非常形式的“制度所应处理的少年是否有减少(整体而言少年是否不再以犯罪为处理事务的手段)”,以及“社会是否仍旧可以容忍这个制度的存在(是否有尽可能先自行处遇非行问题,或甚至于积极与制度合作)”。
针对这十年来的现象,传统的论述仅是不断地强调少年非行的多样化、大量化、暴力化、一般化现象,并且反复倡导犯罪原因以形成对负面列表的强迫性概念,藉此建议强化道德训诫的国家级的、单调的处遇。
奇妙的是,现实上的少年非行现象并不是如此的不堪,事实上在这十年间少年非行现象已经悄悄展开新的面貌。
新的少年司法与矫冶制度是于1997年尾付诸实施的,当年的成人被告人数为192,214人,而有罪人数为151,077人,与此相较,2006年的成人被告人数为173,720人,有罪人数则为150,378人。
估不论详细的成人的犯罪内容,仅以此数据而言,可以说在这十年间,成人犯罪的情势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事实上除去媒体起哄与政治操作所产生的细微变化外,十年间成人犯罪的现象是呈现平稳横向推移的倾向。
与成人犯罪现象相比较,少年非行的现象则呈现出明显的异变。
1997年时,全部的调查人数是23,080人,除审理不开始的4,608人外,逆送到检察官处的有1,736人(包含绝对逆送与相对逆送),而付诸审理的有24,785人(包含前年未处理完毕的案件)。
但是新制度实施十年后的2006年资料显示,调查人数降到14,263人,而虽然审理不开始的人数没有多少变化,维持在4,286人,但是分母数(调查人数)的降低,正代表了审理不开始人数的实质增加,不过更明显的变化应该是逆送人数与审理开始的人数,前者降到仅剩279人,而后者则是降低到10.354人。
简而言之,虽然调查人数的降低并不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是逆送人数仅有十年前的六分之一,而审理开始的人数则是降到十年前的五分之二的程度。
从有罪人数方面,亦可获得同样的观察结果。
1997年的有罪人数为23,096人(其中保护事件有21,902人,刑事案件为1,194人),与此相较,根据2006年的统计,有罪人数是骤降到仅剩9,073人(其中保护事件为8,734人,刑事案件为339人)。
这些数据都不是一口气降下来的,其毋宁是以稳健的速度逐年降低,至2004年时下降速度渐趋平缓,维持横向平稳推移的状态发展至今。
此外虽然刑事案件均为有期徒刑,但是保护处分方面,则有内容上的区分,而从保护处分的内容观察,可发觉虽然配合上述的非行情势的趋缓而在绝对数上有降低的现象,但是在分配比率上,这十年来其实是仅有些微的差异而已。
1997年训诫与假日辅导人数为10,080人,保护管束的人数为9,712人,而感化教育(辅育院收容)的人数则为1,092人。
而到了2006年时,训诫与假日辅导为3,234人,保护管束为4,428人,至于感化教育(辅育院与矫正学校)方面则为467人(社福机构收容方面,这十年来都维持在150人左右)。
大体上都还能维持10:
10:
01的比率。
这种比率或许是同心圆的渐层结构所无法突破的一线。
虽然这十年来,少年非行情势逐渐缓和,但是也不是没有例外。
这个例外就是虞犯人数的增加。
台湾自从采行现代的少年司法与矫治制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