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心得论今本《列子》的文学性与文学影响.docx
《读书心得论今本《列子》的文学性与文学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读书心得论今本《列子》的文学性与文学影响.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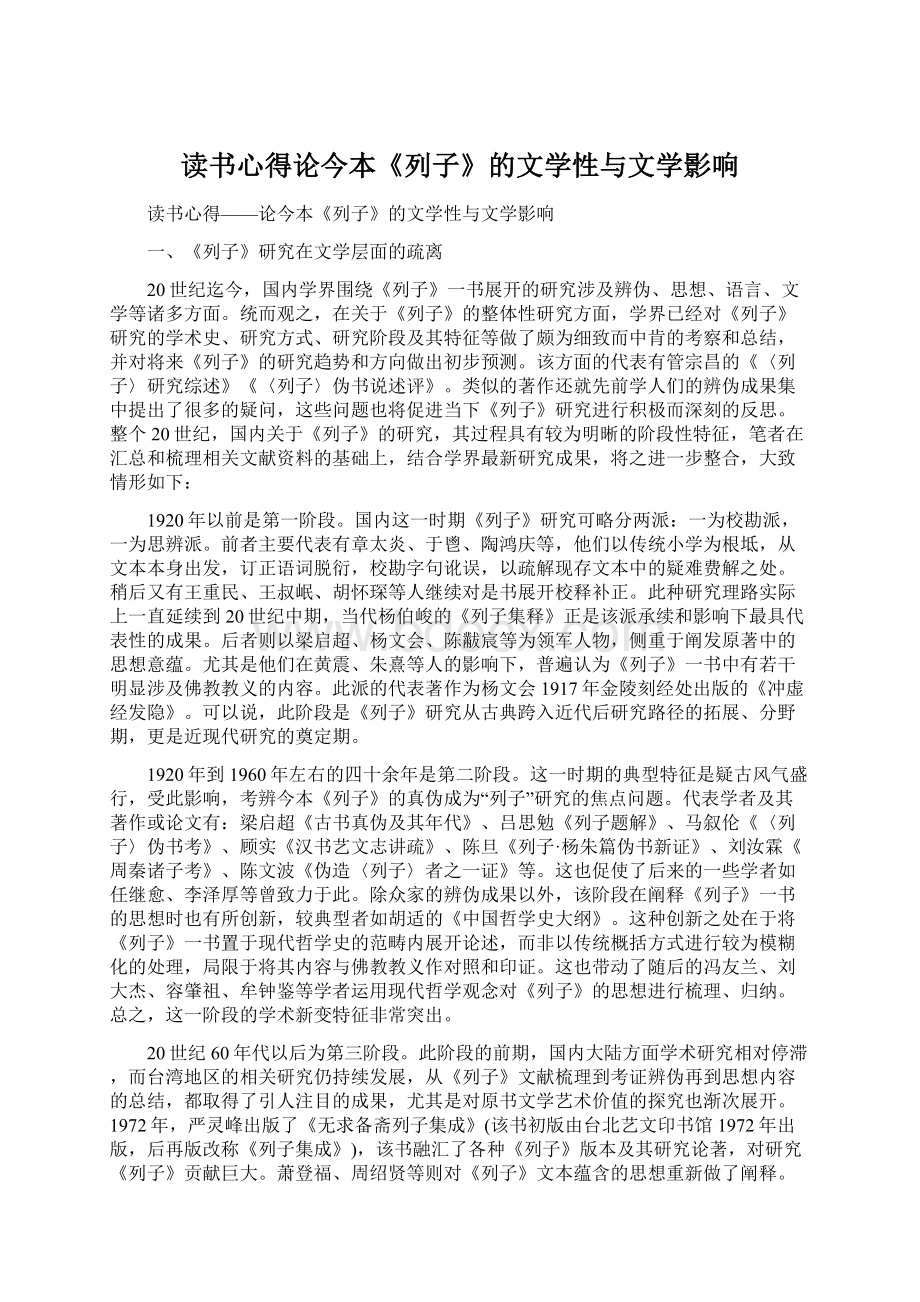
读书心得论今本《列子》的文学性与文学影响
读书心得——论今本《列子》的文学性与文学影响
一、《列子》研究在文学层面的疏离
20世纪迄今,国内学界围绕《列子》一书展开的研究涉及辨伪、思想、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
统而观之,在关于《列子》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对《列子》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式、研究阶段及其特征等做了颇为细致而中肯的考察和总结,并对将来《列子》的研究趋势和方向做出初步预测。
该方面的代表有管宗昌的《〈列子〉研究综述》《〈列子〉伪书说述评》。
类似的著作还就先前学人们的辨伪成果集中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些问题也将促进当下《列子》研究进行积极而深刻的反思。
整个20世纪,国内关于《列子》的研究,其过程具有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在汇总和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之进一步整合,大致情形如下:
192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
国内这一时期《列子》研究可略分两派:
一为校勘派,一为思辨派。
前者主要代表有章太炎、于鬯、陶鸿庆等,他们以传统小学为根坻,从文本本身出发,订正语词脱衍,校勘字句讹误,以疏解现存文本中的疑难费解之处。
稍后又有王重民、王叔岷、胡怀琛等人继续对是书展开校释补正。
此种研究理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代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正是该派承续和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后者则以梁启超、杨文会、陈黻宸等为领军人物,侧重于阐发原著中的思想意蕴。
尤其是他们在黄震、朱熹等人的影响下,普遍认为《列子》一书中有若干明显涉及佛教教义的内容。
此派的代表著作为杨文会1917年金陵刻经处出版的《冲虚经发隐》。
可以说,此阶段是《列子》研究从古典跨入近代后研究路径的拓展、分野期,更是近现代研究的奠定期。
1920年到1960年左右的四十余年是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疑古风气盛行,受此影响,考辨今本《列子》的真伪成为“列子”研究的焦点问题。
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或论文有: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吕思勉《列子题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陈文波《伪造〈列子〉者之一证》等。
这也促使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如任继愈、李泽厚等曾致力于此。
除众家的辨伪成果以外,该阶段在阐释《列子》一书的思想时也有所创新,较典型者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这种创新之处在于将《列子》一书置于现代哲学史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而非以传统概括方式进行较为模糊化的处理,局限于将其内容与佛教教义作对照和印证。
这也带动了随后的冯友兰、刘大杰、容肇祖、牟钟鉴等学者运用现代哲学观念对《列子》的思想进行梳理、归纳。
总之,这一阶段的学术新变特征非常突出。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
此阶段的前期,国内大陆方面学术研究相对停滞,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仍持续发展,从《列子》文献梳理到考证辨伪再到思想内容的总结,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对原书文学艺术价值的探究也渐次展开。
1972年,严灵峰出版了《无求备斋列子集成》(该书初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出版,后再版改称《列子集成》),该书融汇了各种《列子》版本及其研究论著,对研究《列子》贡献巨大。
萧登福、周绍贤等则对《列子》文本蕴含的思想重新做了阐释。
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列子》研究日渐复苏并发展。
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正如其题目所张,是依据语用学和语词演变的历史来为文献断代。
类似作品还有刘禾的《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马振亚的《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等。
对众家学者的“伪书说”进行系统汇总的著作则有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此文颇具标志性与示范性。
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伪说”声势渐大,主张此说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有:
许抗生《〈列子〉考辨》、陈广忠《为张湛辩诬——〈列子〉非伪书考之一》、胡家聪《〈列子〉是早期的道家黄老学著作》、管宗昌《〈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等。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可称作“深化、反驳、进阶期”,研究成果不仅反映在考辨《列子》真伪的最新例证和前沿动态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其思想性的发掘愈发深入、理性、系统化。
这种思想价值的探讨,又突破了《列子》原书思想研究视角的局限,而进阶到对该书早期注者张湛的思想的探究。
但是,真正从语言文学方面来关注《列子》的著作和论文依旧凤毛麟角。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学者讨论过《列子》的寓言艺术,如戴小实的《〈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但影响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探讨这一问题的作品略多一些,有陈建初的《〈列子〉反义词综论》、傅正谷的《〈列子〉梦理论与梦寓言述评》、章沧授的《〈列子〉散文多面观》等。
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于总结历代众家观点之基础上对《庄》《列》各自语言艺术与文学特色的精辟分析。
进入21世纪,关于此方面的学术著作才日渐丰富起来。
如杨漪柳《论〈列子〉对〈庄子〉寓言的运用》、王利锁《〈庄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辩议》、王东《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补证》、马振方《〈列子〉寓言文体辨析》、袁演《〈列子〉寓言的叙事分析》、高其伦《〈列子〉寓言类编与研究》、杨学东《〈列子〉寓言研究》等。
这类作品的持续增多表明,《列子》本身的文学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发强烈的重视,这对新时期的《列子》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
但是上述文章的特色是研究重心大都放在寓言文体上,多借助于语词手段,属于本体、个案研究的范畴。
笔者认为,欲不断推进该项研究,还应拓宽路径,以宏观视域来把握其文学影响,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中做过程论、生成论范畴的梳理与比较研究,以展开阐发和例证方才更为健全完善。
再看国外,20世纪《列子》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日本和西方学界。
近代初期,凭借较为深厚的汉学积淀和较高的汉学研究水平,日本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作品。
1897年,毛内千古发表了《列子の哲学》系列论文凡八篇,其文成功地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从而使得其对《列子》一书哲学思想的梳理和提炼更为全面和系统。
这种方法的运用也给中国学界给来了启示,1921年我国学者傅铜在其《〈列子〉书中之宇宙观》一文中就运用了现代哲学概念去阐释原书的宇宙观。
日本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列子》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有武内义雄、三上诚治郎、小林胜人、天野镇雄、山口义男等人,而诸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集中于考证辨伪和思想阐释方面。
如武内义雄作《先秦经籍考·列子冤词》强调“非伪说”,并逐条批驳马叙伦的观点。
此后,日本的《列子》研究便渐渐走向了相对沉寂。
但即便如此,相较而言,西方《列子》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日本。
西方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
1887年巴尔弗·弗雷德里克在《中国要籍解题》(ChineseScrapbook)上介绍了《列子》和列子其人,并把《列子》的真伪问题和思想价值联系起来开展研究;1893年福柯·安东发表了《杨朱享乐主义与列子泛神论思想的关系》(YangZhutheEpicureaninhisRelationtoLieh-tzuthePantheist),1912年又发表了《杨朱的纵欲观》(YangZhu’sGardenofPleasure);1912年,英国翟林奈出版了《列子译注》(TaoistTeachingsfromtheBookofLieh-tzu:
TranslationfromtheChinesewithIntroductionandNotes)一书;1960年葛瑞汉则翻译了《列子》(TheBookofLieh-tzu)全书;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者顾立雅和卜德才发文探讨《列子》的真伪问题。
总而言之,《列子》的关注度在西方汉学界较低,研究面也比较狭小,研究深度更难及日本学者。
在国外这些著述与研究中,深论《列子》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更可谓寥若晨星。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列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真伪考辨和思想阐释方面,对《列子》本身文学性及其影响的关注则相对欠缺,使得关于该书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疏离化的样貌。
事实上,现存《列子》的文学成就是相当突出的。
二、今本《列子》的文学性探讨及其文学艺术成就
暂且悬置对《列子》一书真伪问题的争议,仅就现今传世的《列子》文本而言,可将其视为一部兼具古代小说特质的优秀文学著作。
鲁迅曾提出,先秦诸子之作,“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1],这是对包括《列子》在内的所有道家经典的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钱锺书也对《列子》给予过“固众作之有滋味者”[2]467的评价;当代为该书作译注的严北溟则从一位专业翻译、注解者的角度肯定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有着相当的文学价值”[3]。
其实历史上,《文心雕龙》的著者刘勰在南朝时就已经直接对《列子》不吝溢美之词了:
“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
”[4]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因过多地褒赏、诠释《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的代表性和具有艺术美的典范性,又被《列子》的辨伪考证问题所纠缠,从而遮蔽并忽视了该书“文辞之美富”的魅力与价值。
具体而言,《列子》一书在探讨天地万物、人的生命与命运以及梦幻、养生、规律、变化等概念和问题的过程中,从古代神话传说、庄文屈骚里汲取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吸收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并将艺术想象、哲学思考与文学手法自然糅合,进而赋予了这种过程飘逸而奇幻的色彩。
《黄帝》篇中的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神人居于列姑射山,《周穆王》篇中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古莽之国与阜落之国”“樵夫寻鹿”,《汤问》篇中的偃师献倡等寓言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甚至是传奇性,在对它们进行书写和表现时,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力,使得整个故事离奇却完整、曲折而动人,并且合乎情理。
例如,周穆王这个人物本来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他是西周中期在位时间很长的一位君主,他的事迹较早地见载于《尚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之中[5],但自那时这个人物就已开始被文学演绎了,其流传也主要以神话传说为载体。
可以说,后世对他的文学书写已然超越了历史记载。
《列子》便很好地继承了该人物的这一特点,他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有着颇为奇幻的经历,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悟者。
再如《黄帝》篇中的“竟不知风乘我邪?
我乘风乎”,这与《庄子》里“庄周梦蝶”的情形、感受和境界何其相似!
加之书中所营造的神秘主义氛围,更可见出该书受到了诡谲雄奇的楚文化影响,或者说延续了发扬于陈楚的道家文化的一贯文风。
清末的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里曾总结道: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
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
[6]
这事实上反映出《列子》与《庄子》在风格和地位上的近似,而且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一定时期的创作特色与接受偏好。
如此一来,《列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其文学艺术成就就更值得玩味和探究。
上文提到过,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其《管锥编》中给予《列子》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方面:
《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
《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撦,每复语工熔铸……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
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能赝作《列子》,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
[2]468
在钱先生看来,虽然总体上《列子》一书在“文词”“名理”两方面较《庄子》略显逊色,但毕竟还在“寓言”文体、叙事风格、文章条理、语言精练等方面依旧拥有自身的特色和长处,评其是“自具一日之长”。
并且,纵然该书现存本是张湛伪造的,那么反而更应该凭借其独特而又难以遮蔽的文学光芒而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实至名归的地位。
郑州大学的罗家湘教授将此定位和表述为“《列子》伪不影响列子真”(出自罗家湘2017年12月17日在郑州大学“列子与中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名为《列子重构》的主题发言)。
诚然,今本中确有一些杂撺伪托的内容,但绝不能因此回避掉列子本人的真实存在和该书所具有的艺术真实性与文献价值。
总之,该书现存本无论产生于战国末期、西汉初期抑或是魏晋之时,都不应忽视其所具备的优秀文学性。
不仅如此,《列子》在刻画和表现人物形象方面也独具一格,其表现手法之丰富造就了众多逼真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除列子师徒以外,还有包括以周穆王为代表的诸多君臣、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师门、异士、隐士等人物与群体形象,涵盖面广又特征突出,经过改写、整合后能够很好地“代《列子》言”,共同传达出原书所要表达的意旨。
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形象类型,使人读完后更是印象深刻,从而体味其理。
前文已经大致介绍过书中的周穆王,这里再谈谈书中列子本人、孔子和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
列子本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除《汤问》《力命》《杨朱》三篇以外其他各篇均有涉及,并且在《天瑞》《黄帝》《说符》中的出现最为集中,但是前后形象和内涵却有较大的差别,个中原因值得细致探究。
这里仅从文学视角来分析,其他角度暂且不论。
其中《天瑞》对列子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平实质朴而又理论性极强的语言描写来完成的,围绕世界本原的问题,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记录了列子的自然天道观和自然生死观。
虽然讨论的问题是形而上层面的,充满了神秘玄妙的意味,但言语的强势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相当突出,给人以十分真实客观的感受,从而使话语的信服力大大增加。
《黄帝》篇里列子以其经历教导和告诫弟子,欲求道术精进必须先要达到无所谓是非、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
如此一来,更显神秘玄妙、虚无缥缈。
但书中并非采用单一的言语说教形式,同样是在本篇之中,“列子问关尹”和“列子为伯昏瞀人射”两个故事里列子就不再掌握“绝对话语权”了,也并非鲜明突出的主题形象,甚至沦为不再以“为尊者讳”对待的“配角”。
“列子问关尹”中列子是一个谦虚的求教者;“列子为伯昏瞀人射”的故事中列子本欲在伯昏瞀人面前表现一番,却被对方提出的更高要求所激将、所嘲讽,以致竟然显露出“伏地,汗流至踵”的窘态。
这里显然是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道家圣人“飘然隐逸”的形象虽打了折扣,却通过对其动作、神态的描写向人展现出列子更为真实、平凡的一面。
这样,作为“冲虚真人”的列子不再像其他诸子一样被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而是如常人一样有着偶尔的尴尬丑态。
不过,这类形象反使得列子更加亲切可感,具有生活气息。
至于“神巫来郑”“列子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的故事以及《说符》中的一些章节,列子本人在其中的角色则是作为事件的传达者或提问者,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作为其师友的壶丘子林和伯昏瞀人才是重点描写的对象。
另外,列子在全书开篇,即《天瑞》篇出场时,其身份就已经是一位“珠玉蒙尘”四十年的隐士了,临行前学生向他请教,直接要求他陈述其师壶丘子林的观点,可见在列子自己门下弟子的心目中,壶丘子林更为高明或者说列子的学问主要是继承于壶丘子林的。
纵观全书,能反映列子“宗师性”地位的描写极少,这在诸子书中也颇为罕见。
再看孔子。
有学者将今本《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分为三种:
由儒入道,亦儒亦道者;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7]。
这种划分较为中肯地反映了孔子在该书中被重新塑造的形象,但笔者认为此分法美中不足的是不甚清晰、精炼,故结合今本《列子》,进一步将其划分整合为“服膺于道者”“坚守于儒者”“调和儒道者”三种形象。
书中对孔子的塑造、改写是通过文学手段完成的。
先看孔子出现的频率:
《天瑞》中有“孔子遇荣启期”“孔子遇林类”“孔子子贡话生死”;《黄帝》中有“孔子评说商丘开”“颜回问孔子”“孔子问吕梁丈夫”“孔子适楚遇佝偻者”“魏文侯问子夏”“惠盎见宋康王”;《周穆王》中有“郑君评樵夫藏鹿”“孔子评阳里华子中年病忘”;《仲尼》中有“孔子闲居论乐天知命”“陈大夫聘鲁”“商太宰见孔子”“子夏问孔子”;《汤问》中有“两小儿辩日”;《说符》中有“孔子返鲁遇涉水者”“白公问孔子”“孔子评赵襄子得城而忧”“孔子预言以仁义”。
可见,今本八篇中有六篇都有关于孔子形象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在某些篇章中还占有很大的篇幅。
另外,有一些章节和故事,孔子在其结尾是作为评点人出现的,总结、评说、揭示道理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往往起着衬托或点睛的作用。
无论哪种形式,对孔子的语言描写都是最具分量、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孔子话语的打造又是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含义丰富、耐人寻味的。
例如,《黄帝》中孔子评说商丘开,首先给予的是“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的主题性、纲领性评价,然后再展开解说,最后推人及己,告诫弟子“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
这正是孔子尊道贵德、善学善教形象的生动体现。
再如,“孔子适楚遇佝偻者”中,当佝偻者叙述完其“承蜩之道”后,孔子便“顾谓弟子曰: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即马上回头告诉学生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做事时心无旁骛才能臻于化境。
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一言以蔽之”的说教风格。
而《周穆王》里当子贡将“阳里华子中年病忘”的事情告诉孔子后,孔子面对弟子的疑惑和请教,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非汝所及乎”,又转身吩咐颜回记下这件事。
这一回应就很耐人寻味了,也给了后人很大的阐释空间。
甚至,在《仲尼》篇中当鲁侯将陈国所谓圣人的事情告诉孔子时,孔子的表现书中只用了四个字来描述——“笑而不答”。
既意蕴无穷又不言自明,孔子智慧又神秘的形象立现。
还需说明的是,今本《列子》中的孔子是正面或中立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之处,这也是《列子》孔子形象较之于《庄子》的最大不同。
今本《列子》经魏晋人的整理,就必然与那时的哲学思想乃至社会思潮发生联系,故书中孔子的形象与态度当与魏晋“调和儒道”之思想不无相关。
因本文仅就文学层面而言,故不再展开另述。
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该书优秀独特的文学性。
“杞人忧天”的故事短小精悍,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反映出中原先民充满忧患意识的朴素宇宙观,同时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引出列子的观点,侧面勾勒出列子虚静放达的智慧形象。
“愚公移山”的故事围绕着愚公进行多层渲染而展开,层层铺垫衬托、节节推进抬升,最终使愚公“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的形象至今流传,时刻启迪人生切勿急功近利。
而与“愚公移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紧随其后的“夸父逐日”。
实际上,书中塑造的夸父形象虽然延续了《山海经》中的神话特质,但开篇便限定了“夸父不量力”的基调,赋予原故事以新意,意在强调不可“恃能以求胜”。
愚公和夸父的形象共同宣扬了要顺道不要违道的初衷,自然连及,水到渠成。
“两小儿辩日”则是将孔子这样一位“至圣先师”放在评判小孩子争论的位置上,寥寥数语且全程没有对孔子正面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场景自然,对接巧妙,手法新奇,极富深意。
尤其是结尾小儿的一句“孰为汝多知乎”更可谓神来之笔,画龙点睛!
如此,天下之大,圣人亦有不知之事,遇事不可徒凭经验的意旨便揭示了出来。
“纪昌学射”中写到纪昌先在飞卫的教导下克服眨眼、苦练眼力,达到在快如梭、尖如锥的极端状态下也不眨眼;接着又适应了微小如虱、细如牛毛的目标,并直至精准射中毫无偏差的传奇程度。
故事讲到这里本足以使人叹服了,但不料这一切其实只是铺垫,故事继而笔锋一转,随着纪昌射术的精进,其心态也发生了扭曲,妄图弑师自大却不意其师飞卫实则技高一筹。
整个故事设计巧妙,结构完整却情节曲折,篇幅甚短但真实生动,发人深思。
所要传达的“强中自有强中手,不可自以为是”的道理就蕴含其中。
还有《力命》中的“管仲与叔牙”“晏子谏景公”等故事,以及《说符》中的诸多小故事在此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此外,正如前文曾提到的,今本《列子》中很多故事的情节曲折而完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富有戏剧性,彰显着文学魅力。
它在说理、叙事和状物方面则是夸张不断,形式多样。
状物方面如上文讲到的“偃师献倡”。
还有一个较有特色的是,《列子》描写音乐也非常成功。
例如“薛谭学讴与韩娥善唱”的故事中,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韩娥吟歌则是“既去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化抽象为具体,画面感强烈,艺术效果极佳,趣味无穷。
类似的故事还有“匏巴鼓琴”“伯牙子期”。
综上可见,与其他诸子散文相比,今本《列子》在多方面颇有文学价值,可谓不逊色于《庄子》。
《列子》这部道家著作是“一部奇书” [8],对后世文学创作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效应。
从文学性上看,曾有学者称它是后世“文章之祖”[9]。
实际上,《列子》对我国汉赋、寓言、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因此,对《列子》的文学性进行细致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而正如前文所叙,20世纪对《列子》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真伪考辨和哲学思想研究,而忽视了对《列子》本身的文学性的研究,这也是造成《列子》研究没有《庄子》研究那么繁富热烈的原因。
鉴于此,本文才以现存的《列子》文本为研究对象,接下来将重点对《列子》中的小说特质进行深入考察,并联系历史扩大视域,结合实例细致地论证其该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三、今本《列子》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列子》一书较为独特的风格就是用寓言、故事来阐述哲理,以文学形式寄寓思想。
同《庄子》的寓言一道,其寓言、故事也应被视为后世小说的滥觞。
明代冯梦龙在《古今小说·序》中如此评论道:
史统散而小说兴。
始乎周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
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
[10]
今人孙望《中国古代小说述略》更是直接将《列子》寓言归入小说史的范畴展开论述,其书还具体谈到《列子》一书所描绘的“理想国”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笔者在此特以今本《列子》中以梦为叙述主体的寓言和该书中寓言的题材类型二者为例,探讨其与后世小说创作的关联性。
(一)《列子》梦寓言与唐代的梦传奇创作
《列子》中有关梦的寓言故事对其后梦小说的创作实际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列子》之后,晋时干宝《搜神记》里就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一事。
唐代则出现了一些有关梦的传奇,流传至今不少我们都耳熟能详,如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白行简的《三梦记》、沈亚之的《异梦录》和《秦梦记》等。
这类传奇小说都是将梦幻作为叙事主体来组织材料、谋篇布局的,而此类传奇小说可以溯源到《列子》,《列子》中不少寓言故事的写法是将现实拉入梦境,又融梦境于故事情节来表达道家思想或调和儒道思想,使人在品味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明白其道理、接受其教化。
诸多梦寓言里人物、背景、情节等要素兼备,从艺术手法到主题思想,都有着典型与示范意义。
《周穆王》篇正可谓专谈梦的一篇,共八个故事,大体都是以“如梦如幻”来说明世间万物的虚妄不实。
“昼想夜梦,神形所遇”,事才是梦的根源,不要迷惑于事物表面的纷纭变化,而应把握道的本质。
其中“樵夫梦鹿”的寓言故事: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
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
不胜其喜。
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
顺塗而咏其事。
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
既归,告其室人曰:
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
”室人曰:
“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
讵有薪者邪?
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
”夫曰:
“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
”薪者之归,不厌失鹿。
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
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
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
士师曰:
“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
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
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
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
”[11]107-108
这个寓言故事短小精悍,却既有人物情节又有背景描述。
围绕“鹿”展开的游走于虚实之间的故事,其艺术方式可以说就是在创作小说。
这段文字结构与情节完整,人物语言和形象生动,甚至还有着出色的心理活动描写。
更值得称道的是,今本《列子》故事里还有着鲜明而娴熟的对比手法。
如同篇的“尹氏与役夫”,其中有尹氏与役夫之间的主仆对比、昼与夜之间的时间对比、尹氏昼疲梦苦与役夫昼苦梦乐之间的身心状态对比。
而这些对比意在告诉人们梦觉相通相同,梦中的苦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苦,梦中的乐等同于现实中的乐。
也正是前文所说的“昼想夜梦,神形所遇”,把握道的本质才是关键。
关于上文提到的白行简《三梦记》,鲁迅先生也曾就此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