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爸爸郁文哉.docx
《回忆爸爸郁文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回忆爸爸郁文哉.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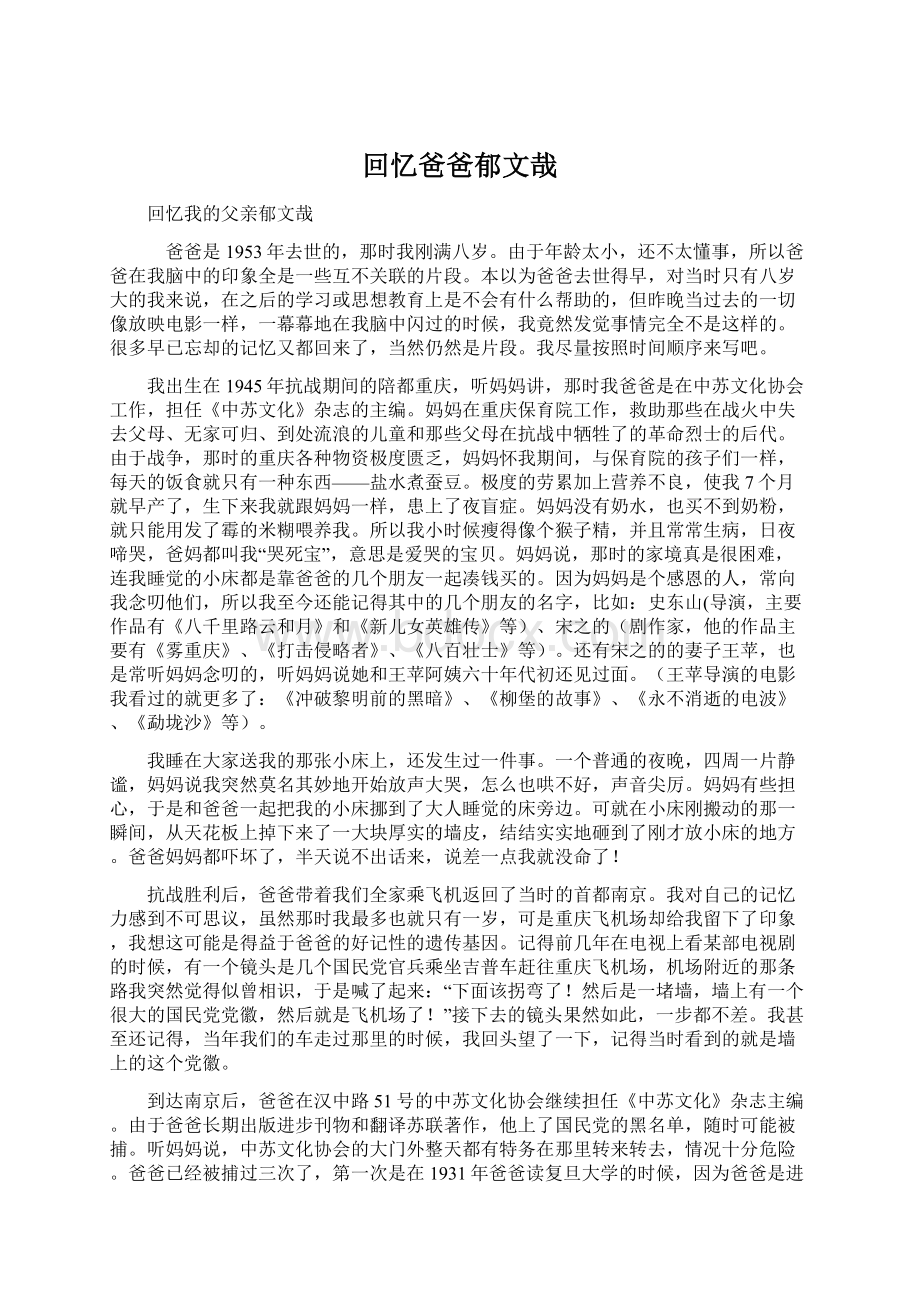
回忆爸爸郁文哉
回忆我的父亲郁文哉
爸爸是1953年去世的,那时我刚满八岁。
由于年龄太小,还不太懂事,所以爸爸在我脑中的印象全是一些互不关联的片段。
本以为爸爸去世得早,对当时只有八岁大的我来说,在之后的学习或思想教育上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但昨晚当过去的一切像放映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我脑中闪过的时候,我竟然发觉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很多早已忘却的记忆又都回来了,当然仍然是片段。
我尽量按照时间顺序来写吧。
我出生在1945年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听妈妈讲,那时我爸爸是在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担任《中苏文化》杂志的主编。
妈妈在重庆保育院工作,救助那些在战火中失去父母、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儿童和那些父母在抗战中牺牲了的革命烈士的后代。
由于战争,那时的重庆各种物资极度匮乏,妈妈怀我期间,与保育院的孩子们一样,每天的饭食就只有一种东西——盐水煮蚕豆。
极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我7个月就早产了,生下来我就跟妈妈一样,患上了夜盲症。
妈妈没有奶水,也买不到奶粉,就只能用发了霉的米糊喂养我。
所以我小时候瘦得像个猴子精,并且常常生病,日夜啼哭,爸妈都叫我“哭死宝”,意思是爱哭的宝贝。
妈妈说,那时的家境真是很困难,连我睡觉的小床都是靠爸爸的几个朋友一起凑钱买的。
因为妈妈是个感恩的人,常向我念叨他们,所以我至今还能记得其中的几个朋友的名字,比如:
史东山(导演,主要作品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和《新儿女英雄传》等)、宋之的(剧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雾重庆》、《打击侵略者》、《八百壮士》等)。
还有宋之的的妻子王苹,也是常听妈妈念叨的,听妈妈说她和王苹阿姨六十年代初还见过面。
(王苹导演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更多了: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勐垅沙》等)。
我睡在大家送我的那张小床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一个普通的夜晚,四周一片静谧,妈妈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放声大哭,怎么也哄不好,声音尖厉。
妈妈有些担心,于是和爸爸一起把我的小床挪到了大人睡觉的床旁边。
可就在小床刚搬动的那一瞬间,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了一大块厚实的墙皮,结结实实地砸到了刚才放小床的地方。
爸爸妈妈都吓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说差一点我就没命了!
抗战胜利后,爸爸带着我们全家乘飞机返回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感到不可思议,虽然那时我最多也就只有一岁,可是重庆飞机场却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想这可能是得益于爸爸的好记性的遗传基因。
记得前几年在电视上看某部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几个国民党官兵乘坐吉普车赶往重庆飞机场,机场附近的那条路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于是喊了起来:
“下面该拐弯了!
然后是一堵墙,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国民党党徽,然后就是飞机场了!
”接下去的镜头果然如此,一步都不差。
我甚至还记得,当年我们的车走过那里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下,记得当时看到的就是墙上的这个党徽。
到达南京后,爸爸在汉中路51号的中苏文化协会继续担任《中苏文化》杂志主编。
由于爸爸长期出版进步刊物和翻译苏联著作,他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随时可能被捕。
听妈妈说,中苏文化协会的大门外整天都有特务在那里转来转去,情况十分危险。
爸爸已经被捕过三次了,第一次是在1931年爸爸读复旦大学的时候,因为爸爸是进步学生,被国民党抓捕到上海龙华监狱,受尽铁窗之苦。
出狱后他去了苏联,进一步寻求革命真理。
抗战开始后,爸爸从苏联返回祖国参加抗战,由于宣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并教授俄文,爸爸在贵阳第二次被捕。
被保释出狱后,他到了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在那里编译《中苏文化》杂志,从译员干到主编。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合作被破坏,他又第三次被捕,在狱中受尽鞭挞之苦。
听妈妈说,爸爸被倒吊在房梁上,全身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血淋淋的就像搓板一样(因为“搓板”这个词很形象,所以它就牢牢地嵌入我的脑海中了)。
最后是由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保释,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爸爸的这段经历在三联书店出版的邹韬奋的书《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上有所记载。
为了避免爸爸再次被捕,地下党护送我们全家去了西柏坡。
这段过程我也有些印象:
记得先是爸爸带着我,装作散步的样子,躲过了国民党特务们的视线,去了上海。
在上海爸爸还带我去了姑妈家,去的路上经过一家食品店,爸爸在那里给我买了些动物饼干。
爸爸指着一块一块的饼干,告诉我每种形状代表什么动物。
然后地下党护送我们全家乘坐飞机去了北平,记得在飞机上,爸爸还给我买了一本很大的连环画册《三毛流浪记》,他一页一页地翻着,指着上面的图画给我讲三毛的故事。
那时我虽然只有三岁,但很多内容我都基本上能听懂了。
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副画,一张画的是四四儿童节(国民党统治时儿童节是四月四号),三毛被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捆得紧紧的,就像个粽子一样,由一个耍把戏的人把他举起来,让周围那些富家子弟们看杂耍,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一边吃着,一边用手指着三毛嘲笑着。
我那是第一次知道,虽然都是孩子,但孩子和孩子是不一样的,我知道了穷人的孩子是很可怜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心里很是难过。
还有一幅画,一个身穿皮大衣,双手揣在皮套筒里的阔绰女子,大冬天的,可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冷。
她穿着高跟鞋,昂首阔步,揣在皮套筒里的手上还拉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是一条卷毛小狗。
而三毛和他的同伴,却穿得破破烂烂、捉襟见肘的,在寒风中簌簌发抖。
这就是爸爸对我的最早的人生教育。
从北京去西柏坡时,地下党让我们全家都装扮成逃难的难民。
地下党给我们开的证明文件是用隐形色写在尿布上的,爸妈把它垫在了妹妹的尿布里。
记得在通过敌人封锁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可怕的事,那里有一队搜查的伪军,对要通过关卡的人严密地搜身,一个都不肯放过。
他们身穿一身黑,头上的帽子也是黑的,百姓称他们“黑狗子”。
他们的身上背着长枪,手里还举着鞭子。
黑狗子强迫爸爸妈妈分开,爸爸抱着妹妹,妈妈抱着我。
伪军让男人一圈,女人一圈,绕着圈子走。
谁走得不如他们的意了,他们举起手来就是一鞭子。
走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位老人,记得她头上戴着一顶古怪的大帽子,有一个伪军走到她跟前,不怀好意地用手在她的帽子上使劲拍了拍,只听啪啪地响。
伪军猛地一掀她的帽子,里面掉出很多铜板来。
这个伪军毫不犹豫,马上就把它们全都没收了。
这都是老人的活命钱,记得她放声大哭,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
我那时只有三岁,记得当时非常害怕,连头都不敢回了,两手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贴着妈妈的脸。
我甚至还记得眼睛向上翻了翻,看见的是蓝天和白云。
由于地下党的证明文件是在妹妹的尿布里,没有引起伪军的注意,我们顺利地过了关。
到了石家庄党的接待站后,爸爸从尿布里取出了我们的证明文件,党组织派来的人用牛奶在上面刷了一下,字迹就清楚地显现出来了。
于是我们全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党组织很快就派人来,把我们全家都送到了西柏坡。
那张爸爸穿着破大褂、化装成难民的地下党给开的路条,现由西柏坡的革命纪念馆收存。
2013年04月在纪念葛一虹诞辰100周年暨《葛一虹文集》出版研讨会上,我们碰到了田汉之子田大畏,他还提起了这件事,告诉我们说当年我们家和他们家是一起被地下党护送到西柏坡的(写到这儿我想起妈妈也曾跟我说过此事),还告诉我们说在第二天的欢迎新人的大会上,肖三同志激动地发言:
“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
今天田汉同志和郁文哉同志在地下党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我们西柏坡……”
在西柏坡时我也还记得几个镜头,一是我们住的地方,黄土的墙、黄土的房、有几级台阶(不记得是土做的,还是石头做的)通向简单的院门。
穿过小门,就是个院子,右边是我们的住房,十分简陋。
左边还有一间小屋子,不记得是干什么用的了。
记得那时的伙食分大灶、中灶和小灶。
妈妈吃大灶,爸爸吃中灶,我们孩子吃小灶,但每次爸妈都是把饭打回来后,放到一块儿,全家一起吃的。
在右边的那间小屋里有一个大炕,晚上爸爸经常躺在我身边哄我睡觉。
我还记得爸爸把两只手的十根手指绞在一起,做出各种姿势,灯光把手的影子打到墙上,墙上便时而出现活泼的小鹿、可爱的小白兔,时而出现凶恶的大灰狼,大灰狼的嘴还会一张一张的。
每次看到大狼,我总是很害怕,爸爸见状,就马上又把影子变成小鹿或小白兔了,于是我就安心了,睡着了。
在西柏坡时还有一件趣事,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们住处的前方是一条土路,经常有驴或马拉着车从那里经过,尘土飞扬。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门口玩,突然看到一辆马车从我们门口经过,那匹马一边走,一边拉马粪。
记得我当时感到非常好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这种动物,就更不用说马拉粪便了。
我十分兴奋和快乐,不由自主地就跟着马车走了。
马车拐了一个弯,继续向前走,突然我发现前方是一片开阔地,那不是我的家,我找不到家了。
恐怖向我袭来,我感到非常害怕,完全不知所措了。
突然我看到了路上的马粪,想起我是跟着马车走过来的,我想,踩着马粪走,就一定会找到家了。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把脚踩到那新鲜的、还热乎乎的马粪里,跟着马粪拐弯,终于找到我熟悉的那个门了。
我看到门口的台阶上下都站着人,有爸爸、妈妈,还有好几个阿姨,他们都出来找我了,以为我走丢了。
当他们知道我是如何找回家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夸奖我是个聪明的孩子,因为那时我才三岁多。
1949年解放军进入北京城,我们全家也随着父母工作的新华社一起来到了北京。
我和妹妹都被送入了新华社幼儿园。
那所幼儿园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不少阿姨都是高中毕业生,我后来所掌握的音乐、舞蹈、手工等基本训练都是在那里学到的。
这个时候我爸爸的工作也进入了最为繁忙的时期,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需要大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的经验,爸爸日夜辛劳,翻译了大量的资料和书籍,内容涉及面之广、劳动量之大,从我们后来找到的这些书报杂志来看,那真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人所能付出的极限!
爸爸为了不耽误工作,干脆就住到了出版社,我们孩子和妈妈只能周末去看看他。
我还记得,爸爸住的房间不大,每次我们去,爸爸就打开壁柜,我看见里面有很多被褥和枕头。
我和妹妹就一头一个睡在桌子上,妹妹睡在里面,我睡在外面,还要小心不要大翻身,不然就会掉下来的。
记得每天夜里我醒来上厕所,永远都是看见爸爸坐在外屋的写字台旁,桌子上是那种刚解放时常用的绿色台灯,嘴里叼着一个烟斗,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写书、翻译。
我人小,想的也简单:
爸爸怎么总也不睡觉呢?
后来爸爸得了癌症,我觉得这与他过度的劳累是有关的。
爸爸的模样我也还记得很清楚,他喜欢穿风衣,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
爸爸满脸的络腮胡子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胡子又粗又硬,每天早晨我总是坐在马桶上看他刮胡子,他先把胡子上涂满白色的肥皂沫,然后用刀片一点点地刮。
我小时候曾听爸爸的朋友们因他的胡子而戏称他为马克思,后来在其他人的著作中也证实了我的这一记忆,如曾担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于伶先生和葛一虹先生都曾提到过这一点。
爸爸的出版社在东城,而我们的新华社幼儿园在西城,我还记得幼儿园的门牌号码,是西单劈柴胡同12号。
到了周一,爸爸要送我和妹妹去幼儿园了,从东城到西城,坐三轮车去。
经过天安门时,爸爸还教我认上面的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那时还是繁体字。
每次到了幼儿园门口,我便乖乖地自己进去了,可是妹妹小,到了门口,总是扭啊扭的不愿意下车,甚至嚎啕大哭。
爸爸不忍心,就又乘坐三轮车,把她带回了东城,有时甚至要往返两次。
妈妈见状火了,说了声:
“我自己送!
”她把妹妹送到幼儿园门口后,便头也不回地自己走了。
妹妹见哭也没用,便一声不吭地进去了。
这事后来成了我们家的笑谈。
新华社幼儿园成立初期,妈妈在那里担任副园长,我们家就住在幼儿园里,爸爸一个人住在东城的出版社。
记得就在幼儿园里我们还搬过一次家。
因为那时刚解放,住房都是破破烂烂的,而那时的领导也与现在的领导不一样,我妈妈是幼儿园的领导,永远要带头住最破的房子。
我们家一开始住的是间很小的屋子,记得屋里只有一张大床,一张小桌子,一个脸盆架和刚一岁的弟弟坐的儿童车。
天花板是纸糊的,我和妈妈、弟弟,还有保姆大娘一起住在里面。
妹妹跟小朋友们住在幼儿园的寝室里,那里的房间都很大,比较结实,比较好。
记得我们住的小屋的右上角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破烂的大洞,黑黢黢的,周围是些破烂的纸条,经风一吹,纸条就晃呀晃的,洞里有时还会发出呜呜的怪声。
弟弟太小,躺在床上,每次抬头看见那个可怕的大洞,都会害怕地放声大哭。
他只要看到大洞,白天晚上都会哭。
妈妈担心他吵到别人,于是决定搬家了。
可就在我们家搬走的第二天,那间破屋子的房顶塌下来了。
妈妈跟我说过好多次,说是弟弟救了我们一家的命!
虽然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他总能在繁忙中抽出一些时间来关心我的学习。
我还记得5岁时,他教我数数和写阿拉伯数字,记得我很快就能从一数到好几百了,可是写5和8的时候却很费了些劲,我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笔。
我升到二年级了,爸爸又带我去文具店买了毛笔、长方形的“金不换”磨和一个亮晶晶的铜质砚台,还有大字本,因为我们该学写大字了。
我还记得二年级寒假的时候,我年纪小贪玩,每天跟小朋友一起玩闹,连寒假作业也不想写。
爸爸总是耐心地一次次喊我去写作业。
有一次我正在楼上玩得高兴,爸爸又叫我了。
这次是让我学画画,我老大地不愿意,磨磨蹭蹭地走到他跟前,看见爸爸已经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一个大鸭梨,梨子上还点了一些麻点。
爸爸让我照着画,我好像真的有这方面的天赋,第一次就画得很像。
爸爸夸奖了我,这使我来了兴趣,自动地又画了一遍。
从此我爱上了画画,一直坚持到自己都有了孩子。
可惜这些画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手里只剩下一张高一时画的列宁头像,但爸爸教给我的本事,却增加了我生活中的兴趣爱好,使我终生受益无穷。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爸爸有一块怀表,很漂亮,那是他从苏联带回来的,这在解放初期还是属于一种稀罕物,很少有人有的。
我看到怀表的秒针滴滴答答地走着,很是喜欢,总也摸不够。
有一天午睡醒来,我从爸爸的枕头下拿出这块表,就去上厕所了,在厕所里还是不停地把玩,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一不小心,怀表就从我手里滑落到厕所的坑里了,掉到下水道里了。
我知道闯了大祸,真是吓坏了,全身哆嗦,低着头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我不知道爸爸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我以为这次一定要挨打了,没想到爸爸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发,就把我领回房间了。
这给了我一次很大的教训,从此没有再动过我不该动的东西。
还有一件应该提到的事,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和妈妈一起住在她当园长的另一所幼儿园里,当时的孩子非常多,从刚出生几十天一直到学龄前的孩子都有,而且全部都是全托幼儿,只有在周末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才会把自己的孩子们领回家。
记得在幼儿园里我们经常搬家,因为只要园里有孩子生病了,妈妈就把我们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当病房。
最后实在没地方挪了,我们家就搬到了厕所里边的一间小屋里,每次回家,都要先走进厕所,再打开厕所墙上的一个小门,那里面就是我们的家,家里面永远弥漫着一股臭味儿。
爸爸周末也要回来,也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间厕所小屋里,但我却从没有听到过一次父母的抱怨,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
我还记得小屋的墙上挂着一张刚解放时最常见的画,就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人手里都抱着一只白鸽,题目是:
我们爱和平!
没多久,爸爸得了癌症。
我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他一下子给我买了一大堆玩具。
桌上放了一个大盒子,里面分成很多小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有一种不同颜色的小珠子。
这是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我用线非常耐心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串起来,就变成了漂亮的珠串了。
还有一个大皮球,后来我可以把它拍出各种花样来,左手拍,右手拍,转身拍,踢腿拍……到现在我还能拍呢,只是拍不动了,一会儿就累了。
还有一个乘降落伞的小人,我把降落伞下面的绳子一拉,降落伞就能弹跳到天花板上去,然后粉红色的小伞会打开,慢慢地落到地面,我那个年纪,好像永远玩不够似的。
对了,还有一个小的机械玩具,里面有很多齿轮,还有打火石,我们跑到黑暗的角落,转动把手,齿轮中就会有五颜六色的火花蹦跳出来,漂亮极了!
我那时还不懂它的原理,只是充满了好奇,一直玩个不停,引来了许多的小朋友,和我一起玩,大家都非常羡慕我有这么多的玩具。
我现在想,爸爸为什么会突然给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的玩具呢?
估计是他感到自己得了绝症,今后不能再关心照顾我们了,所以恨不得把我们一生所需要的东西全都买给我们。
想到这里,心里真是非常难过!
我想起了那时候一到冬天我就会皴手皴脚,因为我总是用水和泥玩,又不爱抹油,所以手脚都会脏得一塌糊涂。
爸爸每次回来,都会打来一盆热水,让我泡手泡脚,然后用一个小刷子,慢慢地一点一点给我刷干净,再抹上凡士林油。
我看到自己的手脚变白了,心里总是美得很。
对了,爸爸还给我买了一个夹作业本的小夹子,上面画的是一个古代女人,一手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另一只手举着一把大伞,艰难地向前走着,天上飘着雪花。
我不明白这幅画的意思,于是爸爸给我讲了孟姜女哭长城、鹅毛大雪千里送寒衣的故事。
爸爸还给我讲过故宫角楼的故事。
我常常想,爸爸去世得真是太早了,不然的话在他的帮助下,我在文学修养方面一定会有较大的进步的。
我还记得那个夹子,是爸爸带着我在文昌胡同东口的那家小文具店里买的,几年前文昌胡同拆的时候,我还特地找到了那家小店,拍了一张照片,可惜的是那时候小店已经腾空了,天花板也塌陷了一大块。
我一个人在那里站了很久,想念着爸爸。
我还记得八岁的生日,那天爸爸给我买了个生日大蛋糕、熏鱼、午餐肉和一个新铅笔盒,盒上画着一排小甲虫,每个甲虫的身上都坐着一个头戴尖顶帽子的小姑娘。
这个铅笔盒我一直用到了高中毕业。
爸爸对我的教育还有很多,我记得爸爸在翻译列宁的著作《社会主义与宗教》的时候,有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的都是宗教的各种名称和术语,我记得好像有“教皇”、“牧师”、“红衣主教”等等一大堆。
那张纸条一直夹在我的书里,纸面已经发黄了,但字迹还很清晰。
我曾想过,一般人对国外的各种宗教都是很难理解的,要翻译这样的书,得查多少字典、学习多少知识呀?
真是很不容易的!
爸爸翻译的书,包括各个领域的内容,而且数量极多,真可称为著作等身,有文学艺术、戏剧理论、科学、农业、地理、电影、话剧、摄影、新闻、画展、音乐、诗歌、马列著作……这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还需要下极大的苦功!
虽然他没有跟我说过什么,但这无形之中已经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中,爸爸的榜样都始终激励着我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认真工作。
还记得爸爸去世前,妈妈带着我去医院看爸爸。
爸爸躺在病床上,已经非常虚弱,瘦得皮包骨头。
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强忍着眼泪,不敢让它掉下来。
那时爸爸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了,但他跟我说的话让我牢牢地记了一辈子。
爸爸说:
“要记住:
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好好听话。
”爸爸是1953年8月3号晚上九点钟走的,就在那个钟点,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妹妹突然从幼儿园的寝室里跑了出去,黢黑的夜晚,她一个人跑到了幼儿园后院空旷的地方,对着爸爸所在的医院方向放声大哭。
阿姨追了出来,把她抱了回去,但她执拗地又跑了出来,跑到原地,对着医院的方向大哭。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三次,弄得阿姨也莫名其妙的,因为这样的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
第二天妈妈从医院回来后,大家才知道,爸爸正是在妹妹大哭的那个时辰走的。
这件事当时无法解释,按现在科学的说法,也许就是亲人之间的第六感应吧?
爸爸对我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妈妈对我讲过,说爸爸最愿意做他喜欢的专业。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当时就想,长大以后也要像爸爸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这在我后来的挑选专业和选择工作时都有很大的帮助,使我快快乐乐地过了一生。
妈妈还告诉过我,说爸爸是个很正直的人,凡事不管上级是谁,该说的话就说,该做的事就做。
他又是个极爱干净又爱劳动的人,总是不怕脏不怕累,自觉自愿地把办公室的公共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打扫完后,有的领导同志很不自觉,又蹲在马桶座上解手,把刚刚擦干净的厕所又踩得脏兮兮的了。
爸爸看到了,毫不留情面地批评了这位领导。
这些话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不争名利,不拍马屁,虽然当了一辈子普通百姓,但我始终活得快乐轻松!
我的孩子也受了我的影响,做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爸爸在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保姆,所有的人都喊她大娘。
爸妈工作忙,大娘对我们很好,帮了我们不少忙。
大娘的家境比较困难,所以才出来做保姆。
爸爸曾经说过,将来自己要给大娘养老送终。
后来爸爸先去世了,妈妈的工资已经雇不起保姆了,但因为多年来我们家和她相处得很好,大娘不愿意离开我们家,还对妈妈说自己不要工资。
妈妈说:
“那不就成了剥削你了吗?
”最后,妈妈帮大娘又找了一家工作,大娘才离开的。
这些对我们孩子来说,都是良好的教育,使我们懂得了,所有的人,无论工种有什么不同,无论是贫是富,大家都是平等的,要相互尊重,相互帮助。
小时候,妈妈曾经告诉我说,爸爸没有留下多少钱,说爸爸很喜欢读书,他的钱一是用来买书了,二是用来帮助朋友了。
哪个朋友有了困难,不用多说,他都会慷慨解囊,甚至不要求归还。
受爸爸影响,我也喜欢读书,我的儿子更是从小就酷爱读书。
家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1948年我三岁时在南京家的院子里“帮助”爸爸晒书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就坐在书堆当中。
南方潮湿,为了防止书籍霉变,时不时要把书放到太阳地里晒一晒。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读了爸爸给我买的讲述苏联女英雄的《古丽雅的道路》、草婴翻译的《小为什么》等书,记得《小为什么》很厚,有365页。
读完后,我两手捧着这本“大部头”,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一样,心里很有些成就感!
爸爸还给我买了一本苏联小学一年级的教科书,也是精装的,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图画,我很喜欢,反复地看。
时间久了,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俄文字母中的各种印刷体和书写体,大写和小写,常常在黑板上胡写乱画。
爸爸有个大书架,从地板直通到天花板,整整占了一面墙,上面有很多砖头一样厚重的书,不少是精装本的俄文书。
记得我刚认识几个俄文字的时候,曾经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很厚的书,书面上用俄文写着作者的名字:
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还以为这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的姓名呢,但乱翻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一点名堂,只觉得这像是个剧本。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俄罗斯剧作家A.H.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大雷雨》。
爸爸有过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多为后来的知名人士,但不少都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前,家中的木箱子里还保留了很多他们和爸爸的来往书信,记得来信最多的是电影导演郑君里,有一大摞呢。
郑君里在文革中被江青迫害致死,我记得1981年在批判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的夫人黄晨女士曾站起来,痛斥江青迫害其夫的罪恶行径。
郑君里先生导演过不少电影,我很爱看,像:
《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枯木逢春》、《宋景诗》、《聂耳》等。
我小时候曾经翻看过爸爸和他的来往信件,但除了他对我妈妈和我们的问候之外,我就什么也看不懂了,因为他们讨论的多是有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或瓦赫坦戈夫的戏剧理论的问题。
文革中我曾想取出来再看看,但妈妈因为怕被抄家,已经把它们都付之一炬了。
不过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爸爸去世至今已经有六十多年了,但直到现在,我还不断地在他的朋友们撰写的各种书籍或回忆录中,或网上看到他们提到爸爸的名字,使我深受感动。
爸爸翻译的各种书籍和编辑的杂志,旧书店里和网上也还在卖,因为这些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些专门研究抗战戏剧的博士生、研究生们更是写出了很多精湛的论文。
他们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记得有一位叫段丽的博士生,她竟然从那些只有笔名的文章中分析出了作者应该是我的父亲郁文哉,后来这一切都在我妹妹见到张颖后,得到了证实。
(张颖在抗战期间曾在中共南方局工作,担任过周恩来的秘书,解放后曾任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中国剧协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
后来我才知道,爸爸是我国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瓦赫坦戈夫戏剧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最早那批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也是《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的译者之一。
这些优秀的戏剧理论对我国抗战期间话剧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通过话剧宣传抗日,争取民心,鼓舞士气。
解放后,这些戏剧理论也被用于戏剧学院的教程中,对我国戏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爸爸去世后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们永远怀念他!
郁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