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docx
《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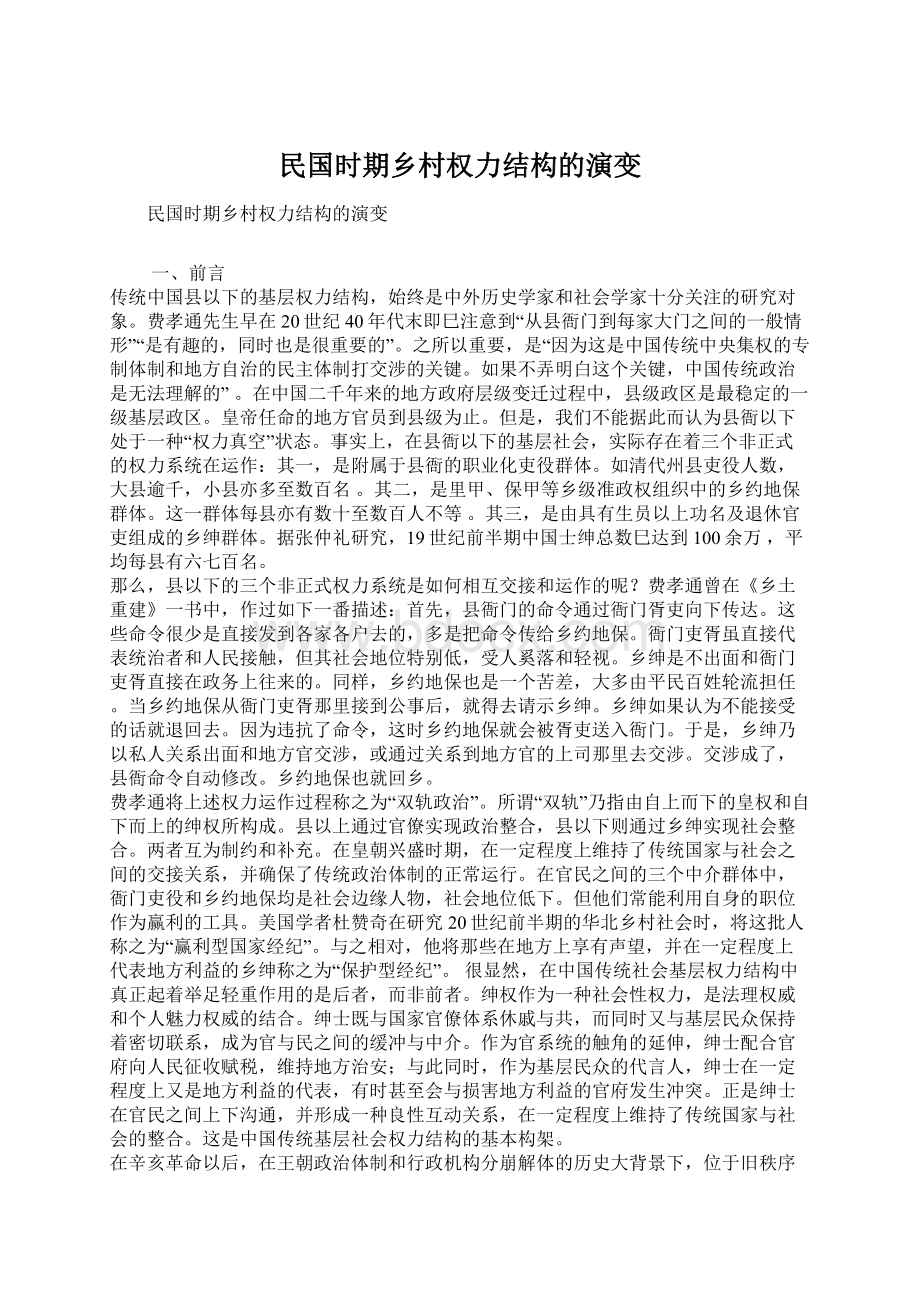
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
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
一、前言
传统中国县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始终是中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十分关注的研究对象。
费孝通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即巳注意到“从县衙门到每家大门之间的一般情形”“是有趣的,同时也是很重要的”。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和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打交涉的关键。
如果不弄明白这个关键,中国传统政治是无法理解的”。
在中国二千年来的地方政府层级变迁过程中,县级政区是最稳定的一级基层政区。
皇帝任命的地方官员到县级为止。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认为县衙以下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
事实上,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在运作:
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
如清代州县吏役人数,大县逾千,小县亦多至数百名。
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
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
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
据张仲礼研究,19世纪前半期中国士绅总数巳达到100余万,平均每县有六七百名。
那么,县以下的三个非正式权力系统是如何相互交接和运作的呢?
费孝通曾在《乡土重建》一书中,作过如下一番描述:
首先,县衙门的命令通过衙门胥吏向下传达。
这些命令很少是直接发到各家各户去的,多是把命令传给乡约地保。
衙门吏胥虽直接代表统治者和人民接触,但其社会地位特别低,受人奚落和轻视。
乡绅是不出面和衙门吏胥直接在政务上往来的。
同样,乡约地保也是一个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
当乡约地保从衙门吏胥那里接到公事后,就得去请示乡绅。
乡绅如果认为不能接受的话就退回去。
因为违抗了命令,这时乡约地保就会被胥吏送入衙门。
于是,乡绅乃以私人关系出面和地方官交涉,或通过关系到地方官的上司那里去交涉。
交涉成了,县衙命令自动修改。
乡约地保也就回乡。
费孝通将上述权力运作过程称之为“双轨政治”。
所谓“双轨”乃指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
县以上通过官僚实现政治整合,县以下则通过乡绅实现社会整合。
两者互为制约和补充。
在皇朝兴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交接关系,并确保了传统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
在官民之间的三个中介群体中,衙门吏役和乡约地保均是社会边缘人物,社会地位低下。
但他们常能利用自身的职位作为赢利的工具。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华北乡村社会时,将这批人称之为“赢利型国家经纪”。
与之相对,他将那些在地方上享有声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地方利益的乡绅称之为“保护型经纪”。
很显然,在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权力结构中真正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是法理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的结合。
绅士既与国家官僚体系休戚与共,而同时又与基层民众保持着密切联系,成为官与民之间的缓冲与中介。
作为官系统的触角的延伸,绅士配合官府向人民征收赋税,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言人,绅士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有时甚至会与损害地方利益的官府发生冲突。
正是绅士在官民之间上下沟通,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国家与社会的整合。
这是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基本构架。
在辛亥革命以后,在王朝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分崩解体的历史大背景下,位于旧秩序深层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
若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对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二、传统士绅的没落
“一谈到‘绅’,便联想到‘土豪劣绅’”。
章开沅先生这句话于不经意间道出了民国以来“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结构中最早发生近代裂变的,正是官民之间的中介群体“绅”。
作为社会恶势力之一,土豪劣绅自然历代皆有。
但土豪劣绅凸显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群体,却是民国时代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民国时期,绅何以会发生群体性的裂变和劣化?
要解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略为回顾20世纪初作为士绅群体所赖以存续的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皇权崩溃以后地方绅权的变迁。
有研究者称,当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时,不仅革命派的报刊几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十分平静,既乏愤激者,也少欢呼者。
当时的社会舆论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仿佛废除的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余年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一个制度。
一般的解释,认为废科举从倡议、改良到废除,已喧闹多年,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
这种说法实际只看到了当时社会心态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所谓废科举时的社会舆论,只可看作是当时少数上层士绅的心态反应。
而恰恰是这批上层士绅并未深切感受到废科举所引起的社会震荡。
因为他们或可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让自己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出国留学的机会,很快转变为近代工商业者、新知识分子或新式军人。
真正悲惨的是那些散居在广大农村的下层乡绅。
但他们当时既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更难于表露自己的心声,以至于今天很难揣测他们当时的心绪和处境。
难得的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清末民初的一位乡绅自述,我们可以从中略见一斑。
这部自述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1857-1943)所著的《退想斋日记》。
1896年春,当“裁科考之谣”传到刘大鹏所在的太原县时,立即引起士子们“人心摇动,率皆惶惶”。
1905年10月,当刘氏获悉已正式停止科考,“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
这不仅意味着仕途的中绝,更多的下层乡绅直接感受到生存危机,“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
对于家有恒产者,尚不虑及吃穿,“若藉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保以谋生科?
”果然,不到一两月间,已是“失馆者纷如”。
这些失馆者因“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
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官僚选拔机制,也是一种政教相连,耕读仕进并举的社会建制。
科举一废,读书者既无出路,教书者自亦失业。
刘氏自述中写道:
“人之一生,皆有悟业以养身家。
予藉舌耕为恒业垂二十年,乃因新学之兴,予之恒业即莫能依靠,将有穷困不可支撑之势”。
“嗟乎!
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刘大鹏的境遇无疑是当时数十万乡绅处境的缩影。
废科举不仅断绝了下层乡绅的政治仕途,甚至危及"下层乡绅的谋生手段。
衣食足而知礼节。
士既无以为生,自然也就难为其他三民的表率。
“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
”刘大鹏自然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乡绅劣化的一个造因实于此隐伏。
科举取士,每次幸运者总归是少数。
失败者难免会有一种挫折感。
但科举制度却有着一种“自我消解挫折感”的功能。
这种功能不自于它没有年龄限制,这就为每一个失败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企盼。
这种机会与企盼的存在,使个别的科场失意者很难凝聚成群体性的社会不满,而且不会形成对现存秩序的巨大的政治参与压力。
这一点,新式常常学堂体制迥然不同。
“科举初停,学堂未广,各省举贡人数不下数万人,生员不下数十万人,中年以上不能再入学堂,……不免穷途之叹”。
即使那么些年龄尚可入新学堂的生员,又苦于学堂因师资、教材、经费、校舍等问题而难以遍高于广大农村,而只得望而兴叹。
这样,在废科举之后的一二十年间,广大农村出现了一大批既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又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教育的“过渡群体”。
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将这些新旧递嬗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游离分子称之为对社会稳定具有破坏力的“游民阶级”。
这批人从原有的生存结构中脱离出来,又无法象城市上层士绅那么样被新的生存结构所吸纳。
上升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受阻,因而产生群体性的对现实的疏离和不满。
这是乡绅劣化的又一造因。
士绅本是与皇权共生的社会集团。
在科举废除,帝制倾覆后,士绅的“继替常轨”中断。
据张仲礼推算,清代士人考上生员、举人、进士时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4、31和34岁,而士绅的平均寿命为57岁。
也就是说,清末最后一代士绅经过一二十年的自然递减,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所剩无几。
不仅如此,民国建立后,科举功名身份不再具有帝制时代所具有的法理性权威,丧失了皇权体制的庇护。
“前清举人”、“前清进士”成为历史遗存,而不再成为获取社会优势地位和权势资源的凭藉和依据。
当然,法律的否定与社会的遗弃,其间还有一个时差和过渡。
因此,在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着科举制度的惯性。
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基层社会,传统士绅的落日余晖还将延续较长一段时间。
同样的情形也在湖北乡村社会存在。
三十年代初期,湖北省民政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各县风俗,……其最堪忧虑者,厥惟士绅之不安于其乡,在乡者之不愿出而问事。
往所谓任率简谅,倜傥之概,为之一变。
”笔者根据当时湖北各县士绅情形粗略统计(见下表),士绅离开乡村,迁居都市或外省者约占30%。
在乡士绅中大多老成凋谢,因循敷衍,有的维持资产,享乐田园,有的囿于旧道德,缺乏现代知识,不足以协力地方政务,有的因时局纷乱,世风浇漓,洁身自爱,不肯出而任事,还有的受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打击而退于无能。
另有一部分不肖士绅作恶乡里,武断乡曲,或分立门户,派别倾轧。
真正能达民隐,尚孚众望,并能协力地方的公正士绅寥寥无几。
显而易见,科举制度废除后,传统士绅群体中虽游离出一批作恶乡里,武断乡曲的劣绅,但到三十年代初,拥有科举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绅已濒临整体性没落的境地。
三、知识分子城市化
清末废科举与兴学校是同步进行的。
按理,当科举制度下的最后一代士绅衰亡没落之际,应是新教育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成长崛起之时。
但是,新知识分子与传统士绅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首。
在传统社会中,士作为四民之首与其他三民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尤其在基层社会,“地方士绅一言一动,乡里倚为重轻”。
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四民社会的解体,治统与道统逐渐分离;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大部分与农工商三民疏离,自然也难以赢得大众的信仰。
这一点,在乡村社会表现尤为明显。
三十年代《女子月刊》上曾有一篇文章,十分细致地描述了新知识分子在乡下人眼中的情形:
“我们如往乡村中去实地考察一下,当可知道现在一般未曾受教育的对于知识阶级所抱的是一种何种态度。
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
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即可成为号令。
……这种现象,从坏的方面来观察,是人民知识的低落,是绅权的膨胀;但如从好的方面来观察,亦可以说是知识界与非知识界的沟通。
过去中国的各种设施,能够使大部分人民奉行,不得不归功于这层原因。
但是现在学校出来的学生是怎样?
虽则现在一般知识界的学问、理解力较之过去均属优良,但乡村中人士对于他们却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的心情,不但不愿听他们的话,简直亦不敢听他们的话。
中国种种新政的实施,不能发生效果,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症结。
因为新政发施者是知识界,而要求效果,则须全国人民一致。
一般人既怀疑知识蜀,不信任知识,则对于知识界所发动的新,自然不愿奉行,不敢奉行。
二十二年浙江省余杭、临安二县农民不服从政府的强迫养育改良蚕种而发生的暴动,实在是很好的例证。
”
村农民对新知识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新教育的不信任。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即开始兴办学堂以取代旧的私塾书院。
但是,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并非在一夜之间靠一两纸诏书即可一蹴而就。
实际上,在清末民初,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还不如旧的私塾。
在乡村基层社会,新学堂更是有名无实。
有人回忆民国前期江西景德镇的教育时写道:
“那时的教育有一种不寻常的现象,新开办的学校生源不足,而教《四书》、《五经》、《幼学琼林》、《昔时贤文》、《三字经》等的私塾却有不少。
”
此外,农民对新教育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是私塾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时即有人指出,新式学校所授功课“距离农村生活过远,未能切合实用,结果学生能画汽车飞机,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佛郎,而不能计田忙漕。
”30年代,社会学者在湖南衡山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对乡村小学主张要“少唱游,多读书”,并且要求教古书。
笔者曾调查过几位受过私塾教育的老人,何以舍新堂而不读?
他们的回答大多是当时农民对新式学校的新教学法和新教科书等不信任。
有的说:
“新式学校很多时间浪费在文娱体育等方面,送子弟到学校去认不了几个字!
”还有的说:
“新学堂不念《三字经》,而念什么‘大狗叫,小狗跳’,那算什么学问!
”这固然表现出当时中国农民思想观念的务实和保守,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和普遍接受。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提倡以白话文来普及大众教育,开启民智,没料正是白话文教材竟然成为百姓大众不愿接受新式教育的一大缘由。
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无疑上下层民众与新知识分子疏离的一个绝好表征。
事实上,下层民众与新知识分子之间的疏离是双向互动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大多以农村社会为中心,其伸展手脚的空间主要是国家官僚机构鞭长莫及的“地方”或“乡里”,耕读在乡村,关心的事务也主要是农村。
少数迁居市镇的士绅仍然与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只是日常生活享乐之所,而不是其安身立命之地。
即使学而则仕,亦多在不惑或知命之年结束宦游,回到家乡收拾田园。
1933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江苏常熟农村调查时,好不容易碰到一位中学生,以至于在调查日记中慨然写道:
“我们跑过的乡村并不少,碰到中学生却是第一次。
”自南宋中国文化重心开始南移以来,苏浙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文化渊薮,未料这个时期的苏南农村,却连一个中学生亦如凤毛麟角,同时期的中国其它地区的农村,该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文化衰败景象呢!
尽管缺乏这个时期中国乡村教育的全面统计材料,但一麟半爪的个案亦能给人以一叶知秋的感觉。
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调查时发现,一些地主子弟在寻乌城东小学混张毕业文凭后,就大摆其架子,在名片上赫然印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煞是神气!
而且每年可以和那些老资格的秀才举人在家族祠堂里平分学谷和胙肉。
在一些内地农村,“粗识文字的小学毕业生便可以打起知识分子的幌子,俨然以绅士自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任意欺骗老百姓。
”在四川一些地方,每当某家有子弟小学毕业时,亲朋邻居要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如科举时代中举一样送去报条,以示祝贺。
自西潮东渐以后,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城市带有西化色彩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自然比日趋衰败破落的农村具有吸引力。
加之城市集中着财、权力、名位等社会稀缺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子弟一旦接受中等以上的新式教育,便尽量留在都市而不愿返回乡村。
大学毕业集中于大都市,中学毕业也想方设法留在省城和县城。
城市成为新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所和工作活动中心。
1930年,上海《民国日报》有一篇题为“乡村颓败了”的文章这样写道:
“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乡村小学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卷去了乡村的干柱,剩下的只有老弱和稚幼。
……乡村衰败了,没有一些生气,和黄褐的土块成了调和的色彩,死静、凄泠、枯暗、荒塞、简陋占据了整个乡村。
”
四、民国时期绅权的社会构成
在20世纪以前,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国家各级官僚的选拔体制,也是基层地方社会精英赖以产生的主要途径。
国家通过科举制度,利用儒家规范性意识形态,将官僚集团与绅士集团统摄于共同的国家统治目标之下。
科举停废后,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未能建立。
官僚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作官不复要求统一资格,仕途从此杂滥。
与此同时,基层社会精英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蜕变。
科举之时,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为跻身于地方精英之列的一条主要途径。
科举一去,“绅”的正规来源断绝。
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与传统士绅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
分析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
那么,民国时期跻身于地方“绅士”行列的“新贵”,其来源如何?
下面列举的几个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民国初年湖北襄阳县东津镇的三位“新乡绅”
王殿甲,原是江湖会里的大爷,辛亥革命时期是个革命党人,当过营一级的军官,以后回到家乡,成为东津镇的绅士,和其他绅士一起处理镇上的大小事情。
樊德斋,木场学徒和木材商人出身,读书识字甚少。
辛亥革命时,通过江湖会当上了地方保卫团团总、区长,依靠经济和政治势力而成为东津镇的大绅士。
宋德山,原本是乡镇上的一个二流子,辛亥革命时,曾当过一个相当于连长一级的队官,这样,他也成了东津镇上“说公了私”的绅士了。
以上三位“新乡绅”的出身,一是江湖大爷,一是学徒、商人,一是二流子。
很显然,他们原来都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
他们爬升到社会上层,跻身于“绅士”行列的阶梯,已不再是传统的科举功名,而是强权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杂途”出身的“绅士”在东津镇并未遭到传统正途士绅的排拒,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正途士绅的认同的接纳,才跻身于“绅士”行列。
如王殿甲回到家乡时,乡镇上的绅士没有一个不去拜望他的。
王也因此而身价倍增。
(二)30年初江西寻乌县20位权势人物
姓名教育程度经济状况职业及经历备考
何子贞中学毕业大专肄业曾任小学教师、县公安局长、警察队长、国民党党员劣绅
何学才收租几十石,承包牛岗税曾任县衙刑房书吏、堪舆劣绅
范明才收租八十石曾任县保卫团总劣绅
潘明征收租一万石,财产总值三十万元儿子做过县财政课长、县保卫团总、县长、县党部委员全县豪绅领袖
刘土垣中学毕业收租千石以上地主全县第二大土豪,但不活动,在县里没有权
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收租四百石曾任县教育局长、工程师、国民党员新寻派领袖
黄甲奎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教员、国民党员新寻派分子
何挺拔中学毕业收租三百多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胡镜如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县政府科员土霸
潘明典前清拔贡收租一百多石做过县知事、县教育局长等“寻乌五虎将”之一,很规矩
赖鹏池前清附生收租五百多石地主不与外事
汪子渊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劣绅
罗佩慈收租二百石做过县长豪绅
陈吐凤前清秀才收租二百多石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
邝太澜前清秀才“寻乌五虎将”之一
彭子径前清秀才收租三百石清末做过县衙巡检,民初曾任县财政局事务员“寻乌五虎将”之一
易颂周前清秀才收租二百石劣绅
钟咏柳留日出身收租二百石曾任武穴警察局长、本县实业局长反动首领
钟星奎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国民党县党部干事新寻派分子
谢肇凡中学毕业收租二百石做过县保卫团总、县府秘书新寻派分子
资料来源:
毛泽东:
“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71-1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上表所列江西寻乌20位权势人物,大致可分为新旧两代:
由前清拔贡、附生、秀才组成的旧士绅和新式学堂毕业生组成的新士绅。
据毛泽东调查,当时该县尚有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但这些人大多已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
显然他们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
过去秀才出身的“寻乌五虎将”已经倒台,已由中学毕业的一批“新寻派”取而代之。
20年代末30年代初,正值新旧两代递嬗之际。
当时,寻乌县共有大学生30人,中学生500人,小学生1300人。
大学生多数侨居在外地大都市。
在寻乌当地称霸的主要是一批中学毕业生。
从经济状况观之,这些人多为大中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大中地主都能成为权势人物。
大中地主中相当一部分不问外事,被当地人称作不中用的“山老鼠”。
从表列20人的职业及经历观之,多数曾出任过县一级公职,纯粹靠收租为生的地主很难进入士绅行列。
这一点仍和科举时代相同,即以参与地方公事为前提,用寻乌人当时的说法,就是这些人“能到衙门话事”。
20人中,只有一人被认为“很规矩”,两人一与外事,而被明确指称为“劣绅”、“土霸”和“反动首领”的却有八人之多。
(三)民国时期鄂西七县十二位地方权势人物
表1-4民国时期鄂西十二位权势人物动态表
姓名籍贯生年家庭及父辈职业教育程度主要职业权势资源备考
张文和建始1900世代经营糖食业,姑父为老绅士中学毕业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财务委员会主任、县中心小学校长、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三四十年代,张文和、范煦如、徐海如、罗裕民四人号称建始县“四大天
范煦如建始1905经营土布生意,世有土地私塾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县自卫大队长、区长、县银行董事长、县三青团分团干事长等王”,把持了整个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历任县长受其节制,并在地
徐海如建始1907大地主,伯父是秀才教会学校办教育兼营商业小学校长、县民众教馆馆长、县议员、县党部书记长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把持乡政,走私贩毒,同时交接官府,把持地方
罗裕民建始1896开中药铺,小有土地略识文字经商,办硫磺厂汉流大爷,县自卫大队长、县参议员、县党部执委各级民意机关。
傅卫凤恩施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团丁出身团防队队长、团总、三县边防联防总指挥、辖区百里、为恩施“团阀”之一拥枪割据,在其势力范围内独断专行,但也为地方办过一些有益的事,如兴办学校、创办邮政等,权势年限为1925-1942年
冉作霖利川1890父为清末拔贡,公正士绅地主兼商人,承包税收团总、民团大队长、自卫大队长、是利川有名的“团阀”在利川称霸一方,其权势年限为1917-1941年谭孔耀巴东1886土财主不习文墨地主区保卫团团总、区联防团大队长、巴东“团阀”之一独霸一方,鱼肉百姓,于1936年被国民党军委会武汉行辕处决,其权势年限为1920-1930年杨芝香咸丰1884家境清贫私塾设蒙馆教书,后办团练,御匪保民出任咸东联防主任、县长等职基本上属于地方自治型的“团阀”资料来源:
根据《鄂西文史资料》1987年第5期所载资料整理而成
就时期而分,民国前期,亦即北洋军阀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为团练、帮会(汉流)。
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或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
“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
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
”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作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
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60%以上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民国时期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
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藉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形成民国前期省一级军阀割据,县一级“团阀”割据的格局。
“团阀”与军阀并无质的区分,悉视其军事实力而定。
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的权势人物。
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
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坐标观念亦为之丕变。
民国年间,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则“妻室恨其懦”,愿为匪者,则“父老其能”的怪象。
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首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
前表内所举来凤县‘团阀’向卓安即为作匪起家。
事实上,民国时期,防御性的民团与掠夺性的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地方保安团队的名义授其匪首以官职。
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在鄂西各县,当南京国民政府势力深入以后,“团阀”们的出路不一,有的见风转舵,主动投靠国民党,跻身于基层政权与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负隅顽抗,不服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多被国民党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摄服。
从前表所举例证可以看出,民国后期,亦即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迹者,其凭藉主要是财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