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同步素材韩愈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docx
《《师说》同步素材韩愈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师说》同步素材韩愈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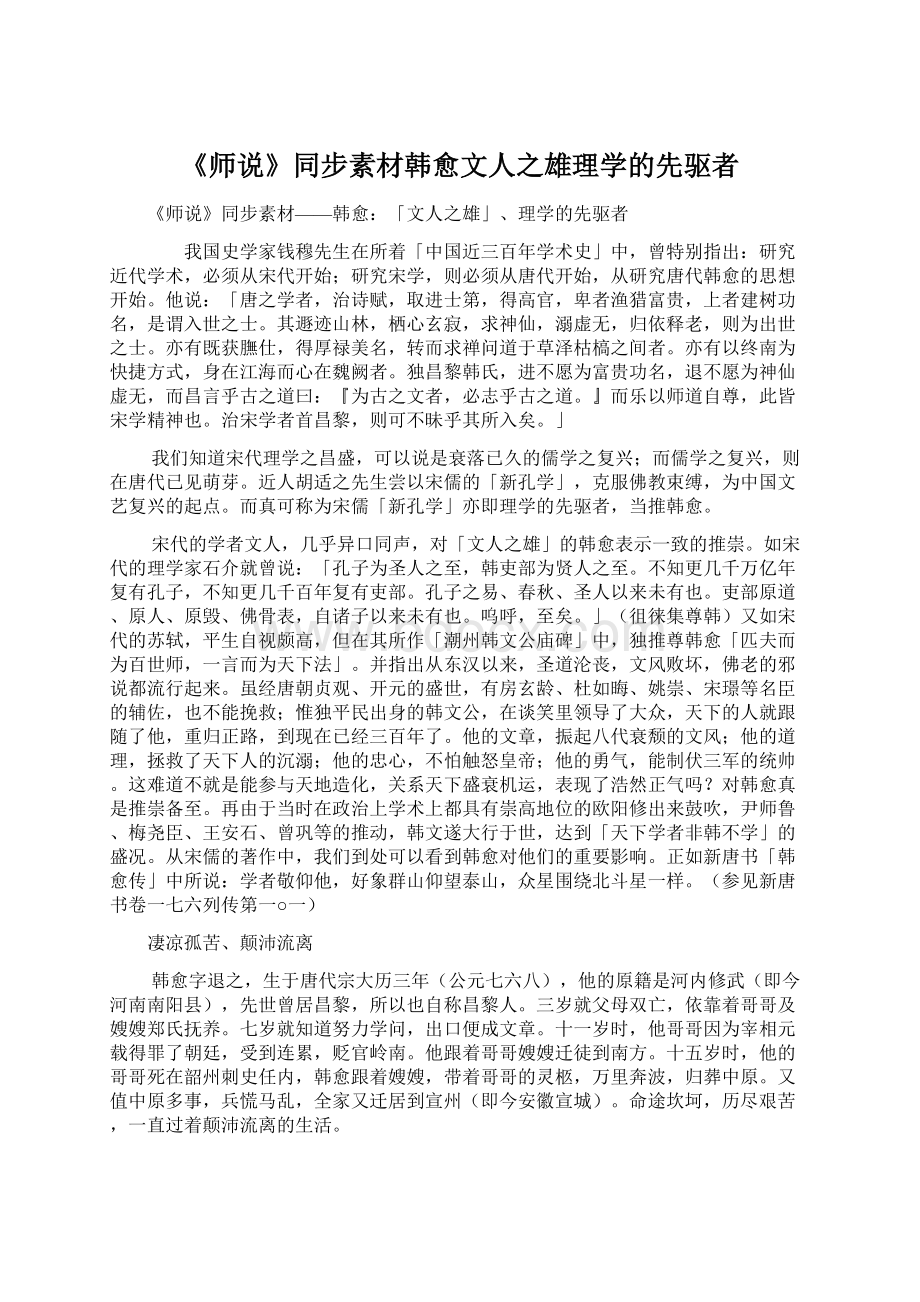
《师说》同步素材韩愈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
《师说》同步素材——韩愈:
「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
我国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特别指出:
研究近代学术,必须从宋代开始;研究宋学,则必须从唐代开始,从研究唐代韩愈的思想开始。
他说:
「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
其遯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
亦有既获膴仕,得厚禄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
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
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曰:
『为古之文者,必志乎古之道。
』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
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
我们知道宋代理学之昌盛,可以说是衰落已久的儒学之复兴;而儒学之复兴,则在唐代已见萌芽。
近人胡适之先生尝以宋儒的「新孔学」,克服佛教束缚,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
而真可称为宋儒「新孔学」亦即理学的先驱者,当推韩愈。
宋代的学者文人,几乎异口同声,对「文人之雄」的韩愈表示一致的推崇。
如宋代的理学家石介就曾说:
「孔子为圣人之至,韩吏部为贤人之至。
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年复有吏部。
孔子之易、春秋、圣人以来未有也。
吏部原道、原人、原毁、佛骨表,自诸子以来未有也。
呜呼,至矣。
」(徂徕集尊韩)又如宋代的苏轼,平生自视颇高,但在其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独推尊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并指出从东汉以来,圣道沦丧,文风败坏,佛老的邪说都流行起来。
虽经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的辅佐,也不能挽救;惟独平民出身的韩文公,在谈笑里领导了大众,天下的人就跟随了他,重归正路,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
他的文章,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他的道理,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他的忠心,不怕触怒皇帝;他的勇气,能制伏三军的统帅。
这难道不就是能参与天地造化,关系天下盛衰机运,表现了浩然正气吗?
对韩愈真是推崇备至。
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欧阳修出来鼓吹,尹师鲁、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的推动,韩文遂大行于世,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
从宋儒的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韩愈对他们的重要影响。
正如新唐书「韩愈传」中所说:
学者敬仰他,好象群山仰望泰山,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
(参见新唐书卷一七六列传第一○一)
凄凉孤苦、颠沛流离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他的原籍是河内修武(即今河南南阳县),先世曾居昌黎,所以也自称昌黎人。
三岁就父母双亡,依靠着哥哥及嫂嫂郑氏抚养。
七岁就知道努力学问,出口便成文章。
十一岁时,他哥哥因为宰相元载得罪了朝廷,受到连累,贬官岭南。
他跟着哥哥嫂嫂迁徒到南方。
十五岁时,他的哥哥死在韶州刺史任内,韩愈跟着嫂嫂,带着哥哥的灵柩,万里奔波,归葬中原。
又值中原多事,兵慌马乱,全家又迁居到宣州(即今安徽宣城)。
命途坎坷,历尽艰苦,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韩愈有三个哥哥,都不幸很早就死去;承接先人血脉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儿十二郎。
「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昌黎全集第二十二卷),凄凉孤苦的身世,颠沛流离的环境,更激发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的毅力。
终于读通了六经及诸子百家之学。
焚膏继晷、兀兀穷年
韩愈曾在他「进学解」一文中,借学生的口气说出他在治学方面所下的工夫。
说他嘴里不停地念着六经的文章,手里不住地翻阅着诸子百家的书籍;记事的书一定要抓住纲要,言论的书一定要探求深意。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说他学不厌;「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见全集第十二卷),是说他非但白天苦读,夜里还要点油灯继续用功,积年累月、努力不懈。
他在「答李翊书」中勉励他在治学作文上下工夫,希望他能达到古人立言境地,不要企望赶快成功,不要为权势利禄所诱惑。
要像种植果树,施肥养根,等待它结果;像点油灯,加上油,期望它发光。
他说树根深厚的,果实一定丰美;灯油充足的,发光一定明亮。
仁义的人,言论必定温和淳厚。
他谦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工夫到家了没有,不过他总算孜孜不倦的已埋头学习了二十多年。
当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见全集第十六卷),在家忘掉一切,出外忘掉道路,专心苦读思索,寝馈于古代的典籍之中。
当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的时候,只求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开始时真是很吃力,很难做到;在写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却不知道这是讥笑。
这样经过好些年,仍然不改变初衷,然后认识了古书里的正道与邪说,和那虽属正道但不纯粹的,都像黑白两种颜色那样明显易分了。
再尽力剔除不纯粹的,慢慢就更有所得了。
于是他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文思就像水流般涌出来了。
写出来给人看,有人鄙笑他,他就很高兴;赞美他,反而使他忧虑,因为他担心文章里还有迎合流俗讨人喜欢的地方。
这样又经过好些年,然后下笔如江河流水般滔滔奔放了。
他又恐怕还有驳杂的地方,再就勃发的文思,排除其不合于道的,平心静气地去考察,直到完全纯粹了,然后充分发挥。
还要在道德学识上有所涵养:
立身行道方面,要走仁义的路;读书明理方面,要从六经中探索其来源;并且要终身努力,在治学作文上用深厚工夫,才能有所成就。
韩愈的文章议论严正,规模宏大。
邵博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中指出: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
「文字要奇伟,有精采,有英气、奇气……但奇伟出之自然乃妙……;此存乎其人,读书深,志气伟耳。
若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
如韩公便是百世师。
」这就是韩愈自己所讲的「闳其中而肆其外」(语见进学解)「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语见答李翊书)的意思。
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韩愈因为读书多,所以见事多,理足而识见有主,下笔为文,遂能浅深反正,四通八达。
韩愈为学作文,更注重养气:
胸怀浩然,则能行乎其不得不行,言乎其不得不言,言行完全出乎真诚。
不徒托之以空言,且能见之于行事。
持身立朝,乃能表现高风亮节,直言敢谏。
新唐书本传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
人家讲他的坏话,毁谤他,也不惧怕,好几次得罪了执政,触怒了皇帝,被贬官、被放逐,到蛮荒远地亦不懊悔。
韩愈就是这种不仅能知「道」,而且真能切实行「道」的人。
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韩愈考取了进士,时年二十五岁。
因为生性耿直,不善奔竞,直到三十一岁才得到入仕的机会。
在做监察御史、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的时候,前后三次贬官,都是因为上疏奏陈政事,与朝廷议论不合而获罪。
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出言亢直,气势磅礡,忘一己之利害,置生死于度外,义之所在,则强立而不回,这是因为他平日集义养气,所蓄深厚,才能达到此一境地。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像水,言论就像漂在水上的东西。
水大了,那么能漂的东西不论大小都会漂了起来。
气和言论的关系也是这样:
气要是盛,那么言论不论长短,声音不论高低,都会恰当。
虽是这样,他自己还不敢说已接近圆满成功的地步;即使接近成功,为人所用,又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
不过,希求别人拔用,则必须迎合人的喜恶,自己好象是被动的器物,用与不用,完全操在别人手里。
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居心有一定道理,行为有一定规矩;用他,就把大道行于世人;不用他,就把道传给学生,或著书立说,留为后人的模范。
韩愈指出:
当世学古文的人很少;立志学古文,就必被遗弃于今世。
他真喜欢这种人的志愿,而悲哀这种人的遭遇。
他所以常称赞这种人,是劝勉他、鼓励他的意思。
(参见答李翊书)
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进学解」中指出,从前孟轲长于雄辩,孔子的道因此昌明,可是他游遍天下,奔走到老也没有人用他。
荀卿守着正道,发挥伟大的议论,为了逃避谗言到楚国去,最后丢了官死在兰陵。
这两位大儒,说出话来就是经典,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人效法,且超过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一生的遭遇却是如此。
上面韩愈所说的「言」与「文」,实在就是「道」,就是「理」。
理直则气壮,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
立志学「文」的人,也就是立志行「道」的人,这种人既不肯少贬其道以迎合时俗,更不肯自毁其道以盲从邪说。
这种人服官受到贬黜,被投闲置散,原是本份,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韩愈能够屡挫不屈,不怨不悔。
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惑
韩愈在伯夷颂中曾说: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
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把伯夷推尊到比「作为万世标准的圣人」更上一等,真可说是「推崇备至」的了。
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指出:
「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也。
」这实在是真正了解韩愈志节与文章的人所讲的话。
在韩愈以前一般人所写的文体,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文体呆板,多拘偶对,使作者的思想受到束缚,而且文格绮艳,陈陈相因。
韩愈起来倡为「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
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别人的非笑。
韩愈认为作文「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见答刘正夫书)。
故豪杰非常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见伯夷颂),不肯随俗浮沉,以邀一时之誉。
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
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人,但不为古书所迷,更不让古人牵着他的鼻子走。
能「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语),能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
他谏佛骨之对人主的忠心,是人臣中少有的;他趋贼营宣抚王廷凑的勇敢,也是同僚中少有的。
他讲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
以道弘文、以文贯道
韩愈在所着「原道」一文中指出:
博爱叫做仁;做事合宜叫做义;照着仁义做叫去做道;修养自己的天性圆满,无求于人叫做德。
他又指出:
他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义来一起说的。
也可以说韩愈所言之道,是仁义,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的。
进一步讲:
韩愈所讲的道,就修养说,则是正心诚意,以至修齐治平;就人生说,则是纲纪伦常,养生送死;就政治说,则是礼乐刑政,风俗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中庸第十三章)的意思。
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曾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
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全集二十二卷)韩愈的意思是说:
他是因为好古道而为古文,并不是为古文而后好古道。
这乃是「以道弘文」的意思;也就是「诚于中则形于外」,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的意思。
韩愈的女婿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
「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这不仅是说文章的好坏与入道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而是说「文」与「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
说「以文贯道」,与「以文明道」,及「以文载道」,有极大的距离。
「以文明道」是说文章可以明道教人,可以记事传世,是发扬道德的工具;文章的醇驳,看它见道的多少而有差别。
「以文载道」则其境界较「以文明道」更深一层,是说文章要能直趋圣人之大道,能窥大道之全,乃可以言「载道」。
「以文贯道」则又深一层,是说文道一贯,文以道为内容,道以文为形式,二者已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可渐渐达到「文道合一」的境地。
古时候的圣人,能体道于身。
道充于中,事触于外,形乎言而成文。
宣之于文,发之于功名事业,无非为其道之外见。
故其文即道,其道即文。
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
「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又能一合乎道;文以行立,行以文传。
所以宋朝的欧阳修说:
「昔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
」(记旧本韩文后)
以师自任、以道自任
韩愈作「师说」一篇,一开始即说:
古代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