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言志散文.docx
《周作人的言志散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周作人的言志散文.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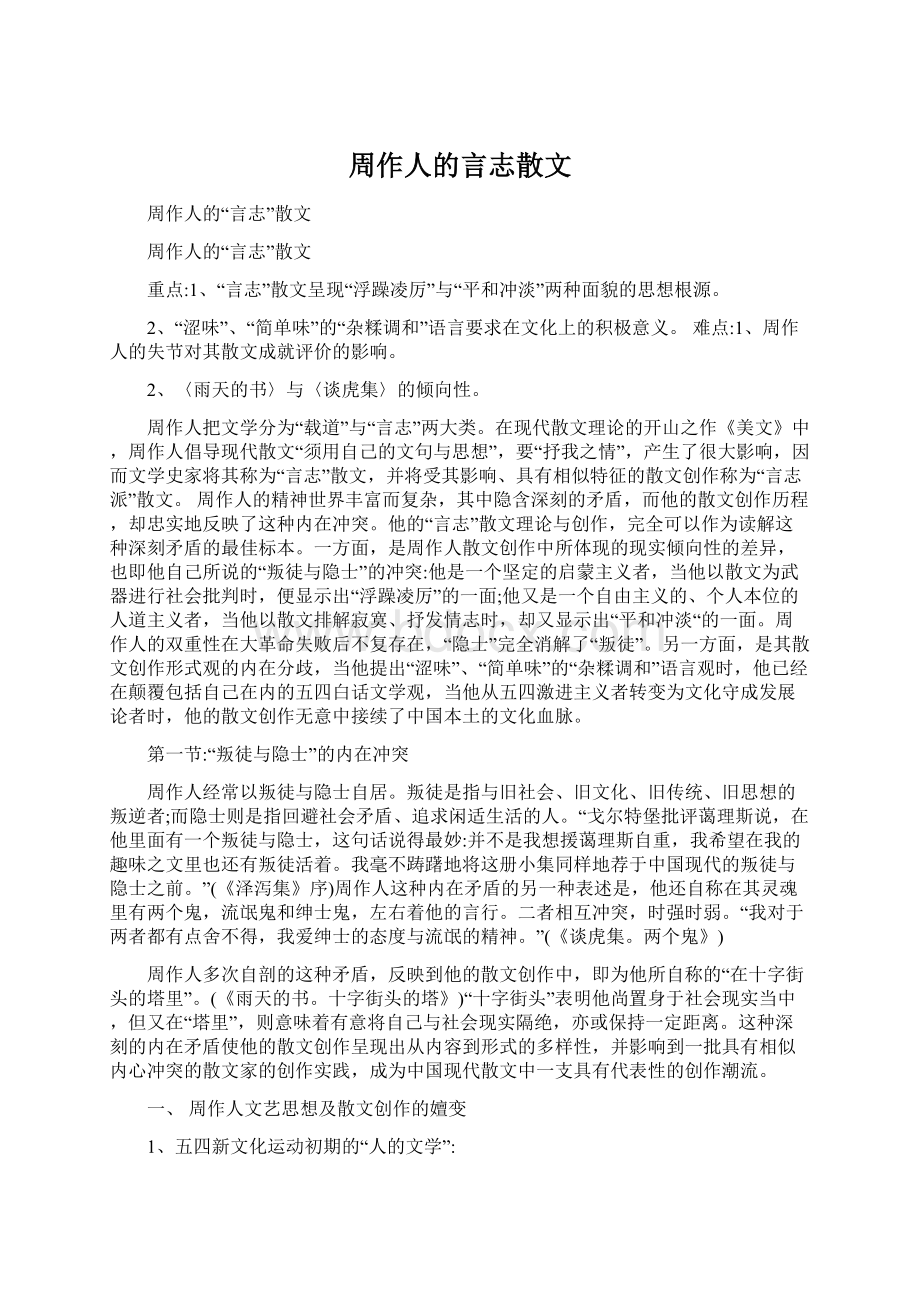
周作人的言志散文
周作人的“言志”散文
周作人的“言志”散文
重点:
1、“言志”散文呈现“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两种面貌的思想根源。
2、“涩味”、“简单味”的“杂糅调和”语言要求在文化上的积极意义。
难点:
1、周作人的失节对其散文成就评价的影响。
2、〈雨天的书〉与〈谈虎集〉的倾向性。
周作人把文学分为“载道”与“言志”两大类。
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开山之作《美文》中,周作人倡导现代散文“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要“抒我之情”,产生了很大影响,因而文学史家将其称为“言志”散文,并将受其影响、具有相似特征的散文创作称为“言志派”散文。
周作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复杂,其中隐含深刻的矛盾,而他的散文创作历程,却忠实地反映了这种内在冲突。
他的“言志”散文理论与创作,完全可以作为读解这种深刻矛盾的最佳标本。
一方面,是周作人散文创作中所体现的现实倾向性的差异,也即他自己所说的“叛徒与隐士”的冲突:
他是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当他以散文为武器进行社会批判时,便显示出“浮躁凌厉”的一面;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者,当他以散文排解寂寞、抒发情志时,却又显示出“平和冲淡“的一面。
周作人的双重性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复存在,“隐士”完全消解了“叛徒”。
另一方面,是其散文创作形式观的内在分歧,当他提出“涩味”、“简单味”的“杂糅调和”语言观时,他已经在颠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白话文学观,当他从五四激进主义者转变为文化守成发展论者时,他的散文创作无意中接续了中国本土的文化血脉。
第一节:
“叛徒与隐士”的内在冲突
周作人经常以叛徒与隐士自居。
叛徒是指与旧社会、旧文化、旧传统、旧思想的叛逆者;而隐士则是指回避社会矛盾、追求闲适生活的人。
“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
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
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之前。
”(《泽泻集》序)周作人这种内在矛盾的另一种表述是,他还自称在其灵魂里有两个鬼,流氓鬼和绅士鬼,左右着他的言行。
二者相互冲突,时强时弱。
“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
”(《谈虎集。
两个鬼》)
周作人多次自剖的这种矛盾,反映到他的散文创作中,即为他所自称的“在十字街头的塔里”。
(《雨天的书。
十字街头的塔》)“十字街头”表明他尚置身于社会现实当中,但又在“塔里”,则意味着有意将自己与社会现实隔绝,亦或保持一定距离。
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使他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样性,并影响到一批具有相似内心冲突的散文家的创作实践,成为中国现代散文中一支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潮流。
一、周作人文艺思想及散文创作的嬗变
1、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人的文学”:
1918年底,为筹办《每周评论》,周作人连续写了《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三篇论文,树起五四新文学的人道主义大旗,被胡适称为“最平实伟大的宣言”。
“人的文学”的核心价值由“自然人性论”和“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构成,周作人在稍后的《新文学的要求》中总结为“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
”他强调“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
凡有违反人性的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应记载世界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们的世俗情欲”,同时又是“反对家族本位
的”,是一种“现代人类的意识”。
作为上述理念在创作取向上补充,《平民文学》主张在题材及情感倾向上以“普遍”“真挚”为主导。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形成了周作人在五四初期完整的文学创作观,也是他早期散文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期间的“随感录”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及以《谈虎集》、《谈龙集》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不自觉地呈现“浮躁凌厉”特征的重要原因。
2、返身躬耕“自己的园地”:
1922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开设了一个名为《自己的园地》的专栏,连续发表《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等文,集中总结了近五年来自己文艺思想的变化。
这种变化深刻反映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的大背景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在时代中的选择。
周作人首先表达了他对五四文学中“为人生的艺术”的主流观点的异议,“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好了。
”在他看来,“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自己的园地》);“平民的贵族化,即凡人的超凡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化为末人了”(《贵族的平民的》);“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
”(《文艺上的宽容》)
1924年是周作人思想与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年头,年底借《语丝》创刊之机,周作人把一年来的思考,总结为对“生活的艺术”的追求,他说: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
动物那样的,自然而简易的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别无道路”(《雨天的书。
生活的艺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雨天的书。
喝茶》)由此,周作人“平和冲淡”的散文特征以结集为《雨天的书》为标志达到了真正成熟。
、置身于“十字街头的塔里”:
周作人“叛徒与隐士”的双重气质并不为他的文艺思想的定型而改变,他灵魂中的“流氓鬼”与“绅士鬼”的搏斗仍然在较长的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他们彼此纠缠,此消彼长,每当暗夜如磐时,他便以五四新文化的骁将姿态,针砭时弊,追根朔源,即便在二十年代中后期的散文创作,如《谈龙集》、《谈虎集》依然可寻“浮躁凌厉”之风,面对封建复古势力的回潮,五卅“雪耻与御侮”的论争,女师大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无不表现了一个“叛徒”应有的反叛的精神。
然而,他又始终坚守五四启蒙主义立场,强调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对各类激进主张保持高度警惕。
时代的旋涡终于使他转向“隐士”的一面,沉溺于自己“生活的艺术”,鼓吹闲适与趣味的“性灵小品”,乃至宣扬“苟全性命于乱世”,终于在抗战初期丧失民族气节,成为后世所不齿的汉奸。
纵观周作人的文艺思想与散文创作,从新文学伊始到整个二十年代都处于两种倾向交织的状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式的文体中、在《谈龙集》、《谈虎集》中以“浮躁凌厉”为主要特色;在《雨天的书》、《泽泻集》中以“平和冲淡”为主要特色。
及至,,,,年底发表《闭户读书论》,,,,,年初出版《骆驼草》,才彻底脱尽“浮躁凌厉”而专注于“平和冲淡”,在以后漫长的创作历程中,“平和冲淡”也一直是他散文创作审美追求的目标。
二、“言志散文”的“浮躁凌厉”与“平和冲淡”
、五四骁将的启蒙主义批判性指向的“浮躁凌厉”:
周作人散文中的“浮躁凌厉”首先取决于他对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在《祖先崇拜》、《论女裤》、《萨满教的礼教思想》、《抱犊谷通信》、《乡村与道教思想》等文中,周作人以其掌握的民俗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知识,将封建礼教的非人性揭露殆尽,同时,这些“短文不仅
将批判矛头指向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同时也包含当今的军阀统治以及普通民众的“国民恶根性”,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被作者称为“人事的评论”的散文中,如《复旧倾向之加甚》、《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忠厚的胡博士》、《大虫不死》、《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恕陈源》等,更是锋芒直指反动军阀统治及女师大事件中的章士钊、陈西滢、徐志摩等人,显现了一个所向披靡的斗士形象。
“浮躁凌厉”的另一方面还在于语气的剀切强烈,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一气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在《祖先崇拜》中写道: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决然的态度与“平和冲淡”类散文形成鲜明对比。
、个人本位人道主义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散文的“平和冲淡”,首先表现在对待阅读对象的平和、平等的态度上,如《北京的茶食》等名篇,本来就是写给友人的信札,更有甚者,为达到这种效果,他还故意虚拟一位受信人,《乌蓬船》中的子荣、《养猪》中的持光,其实都是他本人的笔名,所以在语气及行文中有着传统尺牍体的委婉、温润的特点,在更多的“闲话体”散文里,其中也隐匿着一个作者试图寻求人格平等的对话者,因此,亲切自然、真诚坦率的心理氛围的营造,便成为周作人“平和冲淡”类散文的追求目标。
“平和冲淡”还表现在对散文意境的追求上,周作人在《雨天的书》序二中说: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在《艺术与生活》序中写道自己心境的变化,“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雨天的书》集中大部分散文,尤以《山中杂信》系列为代表的简练淡远、理性冷静的意境特征。
“平和冲淡”最后还体现在题材选取上,周作人主张“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尤其是在后期的创作中,苍蝇虱子、佛道狐鬼、品茶饮酒、先贤逸闻皆可随手拈来,看似“不切题”,却无不涉笔成趣,如《故乡的野菜》、《苍蝇》、《拈阄》、《裸体游行考订》、《剪发之一考察》等,形成一种话题虽然芜杂繁复,文辞趣味却本色天成,平实通达。
第二节、周作人“言志”散文的文体风格
周作人具有现代作家罕见的文体意识,同时又具有深邃的文化意识,正是这两种意识的集于一身,才造就了周作人在现代散文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他是现代散文文体创制大家,由英法随笔借鉴而来的,被许多作家尝试过的“散文小品”在他手中臻于成熟;其二,他通过对“闲话体”散文的语言风格的要求,不仅使自己散文作品呈现出强烈的风格特征,也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观形成一种颠覆,促使其发展方向产生了转折;其三,周作人通过对晚明小品的阐扬,其真正意愿是能使现代散文在文化上认祖归宗,从而达到接续文化血脉的目的。
一、“闲话体”的由来:
、英法的随笔:
厨村白川曾在《出了象牙之塔》中对源于英国的随笔(,,,,,)做过这样的描绘: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这种文体在法国也有深厚的传统,被称为,,,,,,,,,,,,,,作为五四散文小品来源之一的英法随笔,其文体形成的内在规定性就带有“和好友任心闲话”的特点。
、公安、竟陵派的晚明散文:
把晚明散文看作五四散文小品甚至五四新文学的源头之一,也许是周作人的一己之见,他看重的是“抒性灵”
与“立真字”,即他认为的“真实的个性表现”的创作观,与周作人在精神上产生了高度共鸣。
但在文体风格上,
周作人式的“闲话体”散文与晚明散文的承递关系不宜过分夸大。
、“生活之艺术”的人生态度对“闲话体”的催生:
自《美文》发表以来,周作人一直试图在“随感录”文体之外创建一种更符合表达自己个性的散文文体,他曾尝试过“自言自语”的《夏夜梦》式的文体,也在《晨报副刊》发起“浪漫谈”专栏,寻求同道,努力“给新文学开出一块新的土地来”。
当他在《雨天的书。
自序一》中写出“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话,那是颇愉快的事”时,“闲话体”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散文文体已经成熟。
由周作人首创的“闲话体”在中国现代文学散文创作中影响最大,并贯穿整个三四十年代。
及至九十年代,随着“周作人热”的兴起,“闲话体”散文又显现出独特的活力。
二三十年代的废名、俞平伯、钟敬文,四十年代的唐弢、曹聚仁、黄裳,九十年代的董桥、止庵,均可视为“闲话体”风格的延续。
二、“涩味”与“简单味”
1、“涩味”与“简单味”的显现:
1928年周作人为他学生俞平伯的文集《燕知草》做跋时,第一次提出“涩味”与“简单味”的概念,他说:
“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
此后,周作人散文的文体风格追求更为明确而纯粹,“涩味”与“简单味”成为知堂散文的一个重要的识别因素。
文辞之简:
周作人为散文作者开出的制造“涩味”、“简单味”的药方是:
“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燕知草。
跋》)如为作者看重,并常举例说明的《知堂说》,全篇仅百余字,但几乎每句都有转折,以文言与白话口语杂糅,既简又涩,寓涩于简,给人一种从简约中体验丰富的审美感受。
心绪之涩:
周作人理性持重的个性,使他对情感外露的作品难以亲近,他的阅历与博识,也使他过早地形成一种“中年心态”,他自己不会轻易动情,也不会在他的散文里让读者激动,他甚至把因看小说而激动的读者,冷嘲为“呆鸟”(《立春之前。
明治文学之追忆》)。
周作人早期的几篇名作,如《故乡的野菜》、《乌蓬船》、《喝茶》,文中所体现的情思,都不是酣畅淋漓、神采飞扬,而是低徊涩滞,简慢淡远的。
三十年代之后,署名药堂、苦茶、苦竹、苦雨的作品,其心绪之涩更胜于前。
义理之隔:
“闲话体”散文是一种典型的“知性散文”,周作人并不追求“明白晓畅”,也不会将众人都知晓的道理纳入自己的创作范围,在对“杂糅调和”的追求中,“闲话体”往往给一般读者产生一种“隔”的感觉,没有足够的阅历和知识,如同堕入云雾之中,无法窥见其庐山真面目;而真正的读者却能探幽寻胜,从中取得很大的乐趣。
这种文体风格于三十年代后,在周作人更为专注的“钞书体”的创作中尤其突出。
2、“涩味”与“简单味”是对五四白话文学观的解构:
周作人提出“涩味”与“简单味”,要求“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的时间是1928年,其时距1918年由胡适等人提出,得到大多数人赞同的五四白话文学观不过十年,但其间的差异大到另人惊叹的地步。
对此过去解释为在五四退潮的背景下,周作人日渐消沉,脱离新文学阵营的一种倒退行为,这种典型的政治视角得出的结论,使我们难以发现周作人主张的积极意义。
被遮蔽的真相是,周作人以其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等“杂学”学识,更早地发现五四白话文学观中可能隐含割断文化延续性的缺陷,从而试图在散文创作上接续中国文化的血脉。
对晚明小品的推崇,其实也是周作人尝试重新确认现代散文的精神源头、以便使之获得本土
文化识别的一种努力。
这样,文体风格问题转换为另一个命题,即周作人在以“涩味”、“简单味”解构五四白话文学观,虽然它在十年前也曾得到自己的认同。
周作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认识水准下,无异于将自我边缘化,并使自己招致深深的误解。
然而,解构的过程也是创构的过程,周作人的价值,及至文化意识觉醒的九十年代才得到重新发现。
三、“尺牍体”与“笔记体”
1、“只是写给第二人”的“尺牍体”:
周作人与鲁迅一样,具有极为自觉的文体意识,《美文》的发表,无异于一篇创制文体的宣言。
出于对“平和冲淡”的需求,他很早就尝试了尺牍体的创作,《乌蓬船》即是一篇尺牍体的散文名作。
但是,更为专注地研究与实践,却是在发表《闭户读书论》之后。
周作人说:
“尺牍向来不列入文章之内,虽然‘书’是在内,所以一个人的尺牍常比‘书’要写得好,因为这是随意抒写,不加造作,也没有范畴,一切都是自然流露。
”(《夜读抄。
五老小简》)周作人认为,诗与小说因须给众人阅读,不免“做作”,而尺牍之所以成为“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是因为它“只是写给第二个人”(《雨天的书。
日记与尺牍》),故可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个性。
周作人写了大量他所偏爱的尺牍体散文,结集为《周作人书信》,从中更易见到他的“真性情”。
在他去世后,还出版过《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作人曹聚仁通信集》,现代文学中虽有以小说化的尺牍体而鸣世的作家,但于文体意义上贡献当首推周作人。
2、“文抄公”与“笔记体”:
周作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热衷于笔记体的散文创作,以至遭到“文抄公”的讥讽之辞,对此他颇感委屈,曾经在与友人曹聚仁通信时做过辩解,说他的本意是想在中国提倡英法两国式的随笔,在“性质较为多样”的随笔中另创别体,也即他所称为“笔记体的散文”。
诟病者常言的“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在他笔记体散文中确有存在,但论者不能体察周作人这样做的用意。
这里的关键在于作者对其记录对象的选择,古今中外,典籍浩如烟海,如何披沙沥金,连缀成珠,却需要不同凡响的胸襟与眼光。
在周作人笔记体散文中,即使不加评判,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言辞,也能反映出作者的意图,它们形成一种“互文性”,语义相互指涉,并生发出新的语义。
由此而来,这种“复合文本”在文本之外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意蕴。
无怪许多批评家在精研笔记体散文之后,将其称为周作人散文成就的最高代表。
3、“尺牍体”、“笔记体”与“闲话体”的关系:
“尺牍体”、“笔记体”尽管与典型的“闲话体”有相当的差异,但仍然是在“闲话体”之内的两种亚类型。
在日后奠定周作人散文文体特征原型的《雨天的书》中,两种文体的雏形均已出现,所以在周作人的早期作品里,它们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后来作者有意强化各自的文体特点时,它们的内在精神仍然是一致的,与“闲话体”产生的精神背景高度契合。
“尺牍体”是发信者与受信者之间的二人“闲话”;“笔记体”是摘录者与古人、读者之间的三人或多人“闲话”。
这样,周作人多次提及的渴望:
三两知己,啜苦茗,促膝闲谈,就在“尺牍体”和“笔记体”里化为纸上,超越了时空。
三十年代以后,周作人创作的重心已从早期的“闲话体”转而“尺牍体”和“笔记体”,尤其是后者,周作人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闲话体”在三十年代以后的延续,而四十年代以后,以〈我的杂学〉为代表,周作人的创作重心转向“自叙状”与“序跋体”写作,虽然文体风格有相当的变化,但仍然不脱“闲话体”总的审美要求。
周作人曾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苦雨》,我认为那是他无奈世界的优雅的写照。
他后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一直爱用“苦”字。
“苦雨斋”、“苦茶”、“苦住”等等。
20年代的文章,我觉得确有苦涩的人生况味,其隐含的人生价值难题,也颇为丰富。
但30年代以后,那苦味却搀杂了太多的与世无争的消沉,读这时的文章,鲜活的生命质感,便越来越少了。
有时读他趣味浓厚的书话,和好些近于掉书袋的文字,很被他的转变所迷惑。
其实,在那些趋古的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出世间的炎凉的,只是把己身之苦隐得太深,世人难以明?
罢了。
1926年,他曾撰文《两个鬼》,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身上两种精神的冲突。
“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
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
”,9,精神深处的不确切性,是他一直摇摆于入世与出世之间的根源。
但最终还是“绅士鬼”在他那儿占了上风。
差不多也在那个时期,鲁迅也讲过自己身上的矛盾。
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说: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
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10,周氏兄弟的这种复杂的感觉,我以为是真实的,毫无自饰的因素。
在周作人那里,是因为感受到周围的旧势力太大,不好抗拒,于是走到己身那里,以个体的自然之态,消受生命的乐趣。
既然个人主义者在中国只是少数,那么,注定的失败已在他的预料之中。
所以,最后便走向花草虫鱼,以古书与学术自省来苦度岁月。
作为一个知识者,这未尝不好,也是20世纪中国最缺少的文化心态与文化人格。
但是在乱世与国难当头的岁月,这种状态,便难以被世人所认同。
这一点,他是不同于鲁迅的,鲁迅后来的选择,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上所达到的境界,确非周作人所能比。
历史的过程,有时也在证明着这一点。
当周作人把自我放逐到精神的孤岛上的时候,他一直梦想在既不受外界束缚,又不为内在的欲望所驱使的飘然境界中达到人生至乐的境界。
这里,他既拒绝了宗教的神的诱惑,又回避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周作人一向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观念,但又竭力反对把这种自由建立在非理性的冲动的基础上。
他眷恋中国古代的人性论的思想,注重人性的自我修养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但这种自我完善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儒学的再现,而是不涉及他人利害关系的纯粹自我的涅?
。
正是从这种孤立的自我出发,他深深地感悟到了自由主义精神只有界定到自我的本身以及与他人的非冲突性的基点上,才能达到“存人道以配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极”的地步。
因而,这个结局是必然的:
他自觉地滑向了绅士阶级的道路上去。
文学之于他,完全是一种高雅的“趣味”。
周作人大概觉得,只有在超功利的审美观照里,才有可能避免理性法则所给人带来的悖论情绪。
他深深体味到,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任何带有倾向性的艺术,都必然充满道德的说教或偏激的情绪,每种确切性的观念都会在社会中转变为对自己的否定的力量。
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接受的。
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非人性的精神存在,只有超越罩在文学身上的充满悖论的外在形态,艺术才会成为真正人性的东西。
因此,最好什么也不谈,一谈便俗。
只有描绘人的趣味,人的爱好,如赏花观月等,才可能避免这种精神上的创痛。
应当承认,他对产生这种悖论情绪的逻辑秩序的认识,是具有超前性的。
1975年,
意大利哲学家卢哥?
科莱蒂提出过“无矛盾哲学原理”,他认为“矛盾只存在于命题与命题之间,而不存在于事物之间”。
11,这与当年周作人的东方式的感悟所达到的形而上的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但周作人把这一自我的独特的发现仅仅运用到对社会的逃避与自我修养上,没有像卢哥?
科莱蒂把这种观念运用到科学分析的体系中,并且把它转化为一场思维的革命。
他甚至也没有像鲁迅那样在顿悟到人生的真义的同时,把改造社会当成自己的使命。
周作人回避历史的前进是以悲剧为代价的这一规律,他超然于历史之上,梦想在纯粹的美的世界中
捕捉人性的光辉。
他的智慧由于仅仅闪现在自我的孤单的世界里,因而始终无法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
周作人没有找到一条与他人、与社会对话的途径,多少年里,一直孤独地在文学的世界中漂泊着。
于是,周作人在创作抒情散文的同时,也把视野投入到读书寻乐之中。
他涉猎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神话、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都是他关注的领域,他甚至也把相当大的精力用于读古书、寻古趣的杂学之中。
周作人读书,一方面为了达到“知”的满足,另一方面则是对“情”的需求。
他真诚地游历在中国文化、日本文化、西方文化之中,以达到“读书明理”的目的。
这使他的知识达到了同代人为之惊叹的地步。
东西方文明之于他,仿佛是精神上的祭品,既给他带来兴奋,又给他带来消沉,他长久地躲在书斋中,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的旧梦。
周作人时常醉心于
神话、童话、民俗的研究里,他一生始终关注着这些文化现象。
在古代希腊灿烂的神话世界中,那种人类的原始思维以及这种思维所模塑的人神同形的理性精神,对周作人的启示是巨大的。
“希腊精神即使不能起死回生,也有返老还童的力量。
在欧洲文化史上显然可见。
对于现今的中国,因了多年的专制与科举的重压,人心里充满着丑恶与恐怖而日就萎靡,这种一阵清风似的祓除力是不可少,也是大有益的。
”,12,周作人的认识是深刻的,但他的思想只到此为止,他的神话意识不过是流露在书斋之中的精神的闪光而已。
在童话的世界中,他则看到了闪现在人的童年世界的人性的力量,并且把它当作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加以观照。
人的童心、善良意志和富有创造性的想像力,使周作人看到了真正属于人类自己的精神珍品。
他在《〈儿童文学小论〉序》中大力倡导对儿童文学的研究,以此事对抗尊孔读经的非人道的教育。
这里,他把对神话、童话的宣传看成陶冶人的性情的途径,这与他的审美情趣是不无关联的。
他对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推崇,对蔼理斯性心理学说的重视,对日本浮世绘的热爱,等等,都是他的社会意识与审美意识驱使的结果。
周作人在数以千计的“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