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最新文档资料.docx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最新文档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最新文档资料.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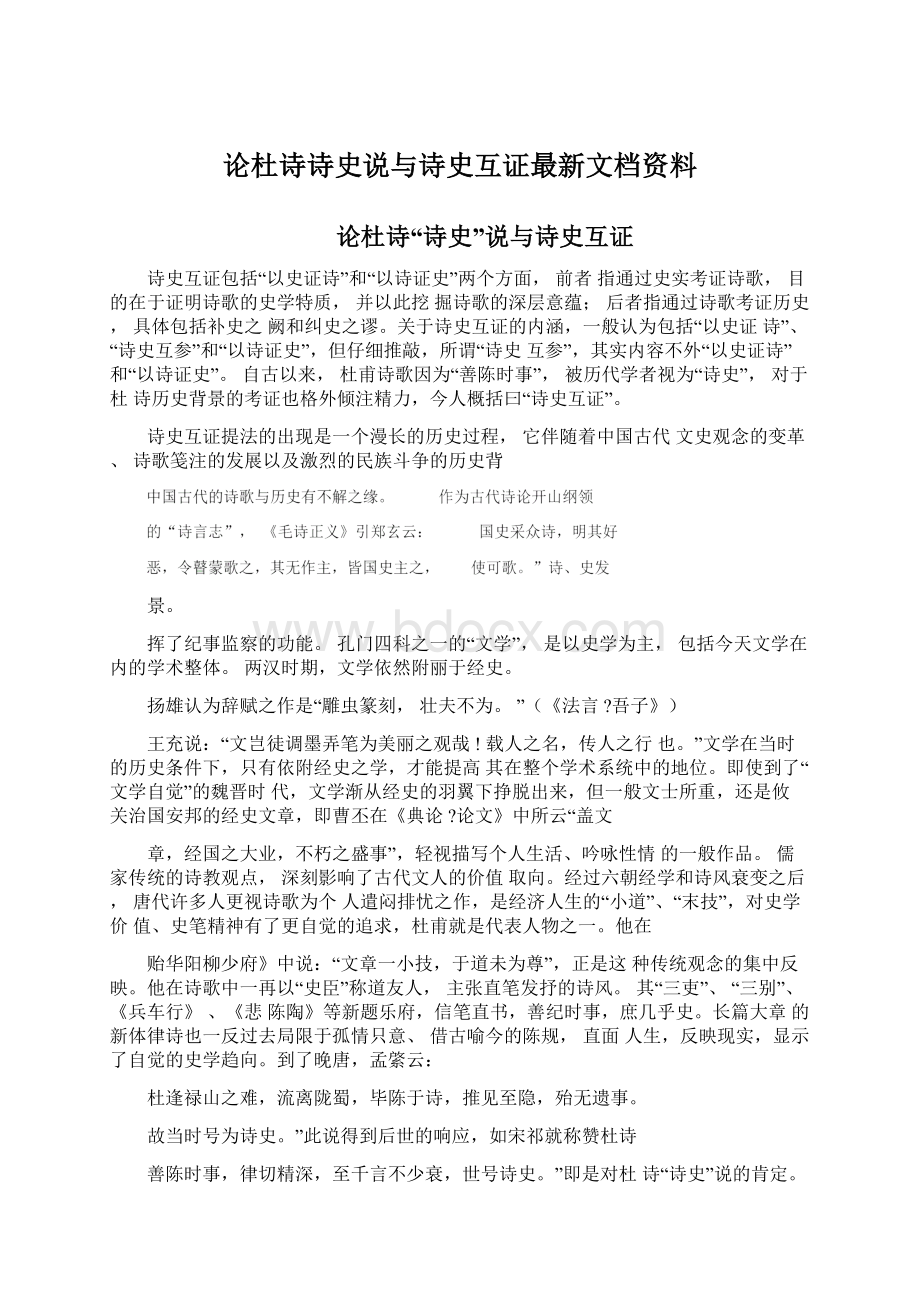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最新文档资料
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
诗史互证包括“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两个方面,前者指通过史实考证诗歌,目的在于证明诗歌的史学特质,并以此挖掘诗歌的深层意蕴;后者指通过诗歌考证历史,具体包括补史之阙和纠史之谬。
关于诗史互证的内涵,一般认为包括“以史证诗”、“诗史互参”和“以诗证史”,但仔细推敲,所谓“诗史互参”,其实内容不外“以史证诗”和“以诗证史”。
自古以来,杜甫诗歌因为“善陈时事”,被历代学者视为“诗史”,对于杜诗历史背景的考证也格外倾注精力,今人概括曰“诗史互证”。
诗史互证提法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中国古代文史观念的变革、诗歌笺注的发展以及激烈的民族斗争的历史背
景。
挥了纪事监察的功能。
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是以史学为主,包括今天文学在内的学术整体。
两汉时期,文学依然附丽于经史。
扬雄认为辞赋之作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法言?
吾子》)
王充说:
“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载人之名,传人之行也。
”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依附经史之学,才能提高其在整个学术系统中的地位。
即使到了“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文学渐从经史的羽翼下挣脱出来,但一般文士所重,还是攸关治国安邦的经史文章,即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所云“盖文
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轻视描写个人生活、吟咏性情的一般作品。
儒家传统的诗教观点,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
经过六朝经学和诗风衰变之后,唐代许多人更视诗歌为个人遣闷排忧之作,是经济人生的“小道”、“末技”,对史学价值、史笔精神有了更自觉的追求,杜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
贻华阳柳少府》中说: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正是这种传统观念的集中反映。
他在诗歌中一再以“史臣”称道友人,主张直笔发抒的诗风。
其“三吏”、“三别”、《兵车行》、《悲陈陶》等新题乐府,信笔直书,善纪时事,庶几乎史。
长篇大章的新体律诗也一反过去局限于孤情只意、借古喻今的陈规,直面人生,反映现实,显示了自觉的史学趋向。
到了晚唐,孟綮云: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世的响应,如宋祁就称赞杜诗
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即是对杜诗“诗史”说的肯定。
后代学者在运用“诗史”的概念时,又根据自己的诗学观点和对杜诗的理解,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面对之阐释、修正,从而极大丰富了“诗史”的内涵和学术性。
除了上述“善纪时事”的解释外,尚有:
其一,“史德史识”说。
认为杜诗有不隐恶、不潜善、不虚美的史家之德和“知本察隐”的史家之识,故或拟之
春秋》,或拟之司马迁,号为“诗史”。
如南宋周《清波杂志》卷十引李遐年之言曰:
“诗史犹国史也。
《春秋》之法,褒贬于一字,则少陵一联一语,正《春秋》法也。
”王质《西征从纪序》曰:
“自古经行天下,其著者唯司马子长、杜子美为广,其文若诗,皆宏伟洪博称之,岂不有所助哉!
”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曰:
“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文天祥序其《集杜诗》,从自己的切身遭遇中深感“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因谓“昔人评杜诗为诗史,
往往察微
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
杜甫在重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面前,知著,义正词严,富有史家之美德和卓识,故黄庭坚誉之“千年是非存史笔”,是甚有见解的。
其二,“近经”说。
此说从诗歌发展史的高度考察杜诗的历史地位,肯定杜诗“言理近经”、
有三百篇之旨,足与《国风》、《雅》、《颂》相表里”(蔡居厚《诗史》),故称之为“诗史”。
如明代的高云:
“公之忠愤激切、爱国忧国之心,一系于诗,故常因是而为之说曰:
百篇》,经也;杜诗,史也。
诗史之名,指事实耳,不与经对言也。
然风雅绝响之后,唯杜公得之,则史而能经也,学工部则无往不在也。
”将杜诗与《诗经》相提并论,称赞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以及赋比兴手法的完美结合。
其三,“补史”说。
清代浦
(杜诗)有与国史不相似者:
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
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
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
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
”其四,“自传”说。
杜甫奔波流离,辗转大半中国,诗歌无论叙事或抒情,每见自己身影,故后代学者得以考其生平踪履。
仇兆鳌说:
“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
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
x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
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端痫斯世斯民者乎?
读其诗者,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
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
”
虽然各种说法自有道理,但归根结底不能离开杜诗纪事写实的根本特质。
杜诗对导致封建社会中落的安史之乱有极为详细的描写刻画,前后八年,篇什之富,再现之真,远轶流辈,垂范后世。
自天宝十四载冬乱发前夕,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之句,对大乱将临已隐有预感。
至广德元年,梓州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喜战乱平息。
携家
悲青坂》、《对雪》、《塞芦子》、《哀江头》
官华州司功,有《洗兵马》、“三吏”、“三别”等。
加上晚年追忆之诗,总数不下四十篇。
恰如巨幅历史画卷,逼肖真实,曲折生动,艺术反映了八年离乱给唐帝国造成的永久疮痍以及给人
《奉同
民带来的深重苦难。
杜诗还善于记录重大社会主题,如《兵车行》
揭露玄宗穷兵黩武,《丽人行》揭露杨氏兄妹专宠跋扈,
江头》直斥统治者荒淫误国,《盐井》、《岁晏行》等记述田制
破坏、币制失策、横征暴敛等严重的经济弊端,《释闷》反映边
《驱竖
防松弛、外患连绵,《去秋行》、《草堂》、《客居》、《逃难》、
《三绝句》反映藩镇猖獗、害哋自雄、拥兵作乱的现状,子摘苍耳》、《岁晏行》等刻画贵贱、贫富、劳逸、苦乐诸多方面的不均现象。
“诗史”观念也集中体现于历代的各种杜甫年谱和杜诗笺
注之中。
自北宋吕大防开始,先后产生几十部杜甫年谱。
从今存的吕大防、蔡兴宗、赵子栋、黄鹤、朱鹤龄、仇兆鳌等人的年谱看,作者均采取诗史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探赜索隐,详尽考察杜诗中的史料线索,大致确定了杜甫一生的踪迹和大部分作品的系年。
而在杜诗笺注中,“诗史”的作用更为明显,成为笺注杜诗的一个先设观点。
从北宋陈禹锡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自题其书日《史注诗史》,到清初钱谦益、朱鹤龄等笺注杜诗,广引博征,该恰精审,辨疑纠伪,以两《唐书》、《通鉴》为主干,以各种地志、杂史、笔记、诗话为羽翼,互相发明考订,形成了阵容浩荡、学风坚实的“以史证诗”派。
宋代的黄
鹤注本在编年和考史上代表了宋人的最高成就,而随着史学及其
方法的发达,清初注家对唐史的研究日臻精密,“以史考诗”的
水平也超越往古。
在以钱谦益为核心的苏州以及江南地区,聚集了一批学有根底、精于考据的注杜、评杜和学杜的学人,人数达百人之众,形成了浓厚的研究唐史的风气,极大地推动了杜诗研究的深入。
他们认为杜甫命意是“心不孤起,仗境方生”,主张必须精通史书,熟稔典故,体察杜甫的生平经历和处境感受,如此方可解诗。
试看钱谦益熟练使用史料,似若己出,即可窥见其史学修养;据以阐释诗意,发皇杜甫之心曲,冀存少陵之真面目,澄清旧注之谬误,使杜诗底蕴大白于天下。
这在他自诩为“凿开日月,手洗鸿蒙”的《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
《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诸将五首》诸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几首诗笺注的宗旨,就是指出杜甫对玄、肃、代三帝及朝廷的讽喻。
尽管因求深求新而有可议之处,
但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杜甫“一饭不忘君”的愚忠看法,还原了杜甫的“真面目”,这是其最值得称说之处。
朱鹤龄亦据史重新解读《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收京三首》、《建都十二韵》等诗,一洗旧注之陋。
可以说,清初学者在“以史证诗”治杜方面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绩。
但也必须看到“以史证诗”的局限。
第一,杜诗相当忠实地
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杜诗中以为题材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考之
唐史,均大体合节;所吟颂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大致与史书相符。
例如杜诗《八哀诗》对王思礼、李光弼、张九龄等人的叙述,与
旧唐书》对照,大略基本没有出入。
合观称颂李嗣业的几篇诗,与新、旧《唐书》对照,可以说“遗貌取神”,基本抓住了李嗣业的精神风貌,是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合璧。
得杜诗可以论世知人,此非虚言。
但又不可不注意到,无论是史书还是杜诗,都是人写的,都是历史的客观和史官、诗人主观综合的结果。
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所谓的“二十四正史”,均是撰写者取舍、组织、阐释、叙述出来的,特别是在材料的取舍和人物的评价方面,更
然后
是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
所以“以史考诗”,首先必须正确而辨证地看待史书,不宜将之看作完全无误的铁证,再用杜诗对照。
宋代杜诗注家过信两《唐书》中杜甫的史料,以之解读杜诗,结果许多作品凿枘难合,甚至连诗旨都无法确定,就是吃了盲从正史之亏。
对待杜诗也是如此,不应将杜诗看作完全的“信史”。
杜甫本身限于各种原因,或错误记载历史,或有意无意疏忽某些史实的因素。
错误记载历史的例子,如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作《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十二首,朱鹤龄即指出:
河北入朝事,史无明文,疑公在夔州,特传闻而未实耳。
”而有意无意疏忽的例子,例如严武与杜甫十分亲密,但无论是生平大节还是评价,史书之严武与杜诗之严武还是有相当差距的。
《旧唐书》中关于严武在朝“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冀其引在同列”以及“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章彝)”的劣迹记载,在杜诗中不
可能见到;而《旧唐书》中对严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的此类评价,在杜诗中也不见丝毫踪影。
人们更可能记得杜甫在《八哀诗》中对严武“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美誉。
事实上,严武并非杜甫所认为的那样,是个可为国之栋梁的人才,至少《旧唐书》与杜甫的认识是不同的。
这种情况在杜诗中恐怕绝非一处。
第二,无论史书或者诗歌(文学),均只能反映部分的现实。
各种唐代的史料总和,也只是三百年唐帝国活生生史实的脉络而已;包括“诗史”的杜诗在内的所有唐代诗歌或文学之总和,也只是唐代生活的斑斑点点而已。
史和诗有不能对应交集的空白地带,那是历史的沉默之处,注家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株守现有的史料,力图为诗歌安排合理的历史归宿;对于史料不及处,注家应该知难而退,这就是“诗有可解,有不可解”的用意所在。
第三,史料和诗情有严格的区分。
钱钟书说得好:
“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
”“以史证诗”要求诗歌必须提供足够的史料线索,为笺注者明引或暗示寻求史料的通途幽径,正如几何学有
三点固定法”一样,诗歌作品必须提供足可“锁定”相应史料的数点“信息”,仅凭蛛丝马迹,考出所谓“史实”,再以之笺诗释意,鲜有不谬。
所以它一般多适用于叙事性强、直接描写与
时事有关的作品,或借比兴传统来表现现实社会的作品,至于那些抒情成分较多的诗歌作品,并不适合,杜诗尚有不少作品姑从旧编而无确证以系年,就是证明。
如果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势必沦于穿凿附会,宋注和清注皆曾犯过此类错误。
邓之诚说:
“钱谦益《读杜小笺》事事征实,不免臆测。
”钱注虽在杜诗旨意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事事比附史实,亦难逃臆测之诛,并在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作者的本旨深趣。
第四,“以史证诗”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作品。
准确赋予诗歌作品一定的时代和事件背景,可以避免对诗歌解释的随意性,为进一步解读和欣赏文本自身打下基础。
但从杜诗的笺注史来看,注家往往注目于史实、地理等背景考证,对诗歌审美反倒似乎视而不见,亦即所谓的“释事忘义”或买椟还珠。
杜诗之美,更多的是凝练之美、雄浑之美、韵律之美,而这不是枯燥乏味的考史释地所能给予的。
甚至清初出现了一些完全抛弃旧注的白文杜注,可以看作是对旧注过于注重背景考证的极端反叛,此举虽不值得提倡,但所蕴含的意义则当引以为戒,值得今人反思。
以诗证史”也由来已久,非后世或近代学者的发明,但直
经》等保存一定的史料。
《左传》大量引用《诗经》,多达一百九十首次;司马迁《史记》之《殷本纪》、《周本纪》,记载殷
之始祖契、周之始祖后稷的事迹,几乎全搬《诗经?
商颂?
玄鸟》
和《诗经?
大雅?
生民》,《诗经》成为补商、周史阙的重要材料,
均是典型的“以诗证史”的例子。
就是说,《左传》作者和司马迁在考定《诗经》多载上古之史的基础上,才将其援引入史的。
历代官方正史也不乏补诗入史的情况。
杜诗在宋代受到极大关注,其史料价值也得到重视。
黄鹤《补注杜诗》注《三绝句》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引著名学者鲍慎由的话说:
开州、成都远,不知其故,史不书,失之。
”说明北宋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刘克庄说:
“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为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得贞观、开元之唐矣。
新、旧唐史不载者,略见杜诗。
”
但“以诗证史”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种注诗的方法,而是一种考史的方法,具体而明确的内涵及目的是对史书的补阙纠谬,目的在史而非诗。
近代陈寅恪主张“以诗证史”,也是出于同样目的。
在他眼里,诗具有史的真实性。
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他以杜诗中关于“杂种胡”的诗句,补证“故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云:
杜少陵与安史为同时人,其以杂种目安史,实当时称中亚九姓胡为杂种胡之明证。
”此视杜诗为信史。
又在《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一文中,以唐史考证杜诗“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一句,得出杜诗中的“朔方键儿”即指同罗部落而言的结论。
他认为“唐代诗歌保留了大量历史记录,唐史的复杂性与接触面广这些特点,都在唐诗中有反映,成为最原始的实录。
文章合为时而作,所以唐诗中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象。
”但钱钟书显然反对“以诗证史”,在《谈艺录》中说:
“夫世法视诗为华言绮语,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姑妄听之。
然执着遣兴泛寄,信为直书纪实,自有人在。
诗而尽信,贝y诗不如无耳。
”在《管锥编》中更是反复致意:
“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和时局,牵合朝政;一切以齐众殊,谓唱叹之永言,莫不寓美刺之微词。
远犬吠声,短狐射影,此又学士所乐道优为,而非慎思明辩者所敢附和也。
”他批评的对象显然是指陈寅恪。
两人的观点皆有合理之处,但指向却不完全一致。
从陈氏看,诗是广义的史,自然无误;“诗史互证”作为一种考证文史的综合手段,也是适用的。
从钱氏看,强调“诗道之尊”和诗歌独有的美学价值,也未可厚非。
两人的根本分歧在于立足点的不同,陈是史学家,他眼里的杜诗都是史料,但具体到治杜注杜,
除了上述几例对杜诗研究有所助益外,作用并不明显,这就说明
今人习用的注释杜诗所谓的“以诗证史”,其实是对其内涵的一种误解。
以杜诗考证历史,目的在史而非杜诗本身,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杜诗所应该重视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