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师约会何君华.docx
《与大师约会何君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与大师约会何君华.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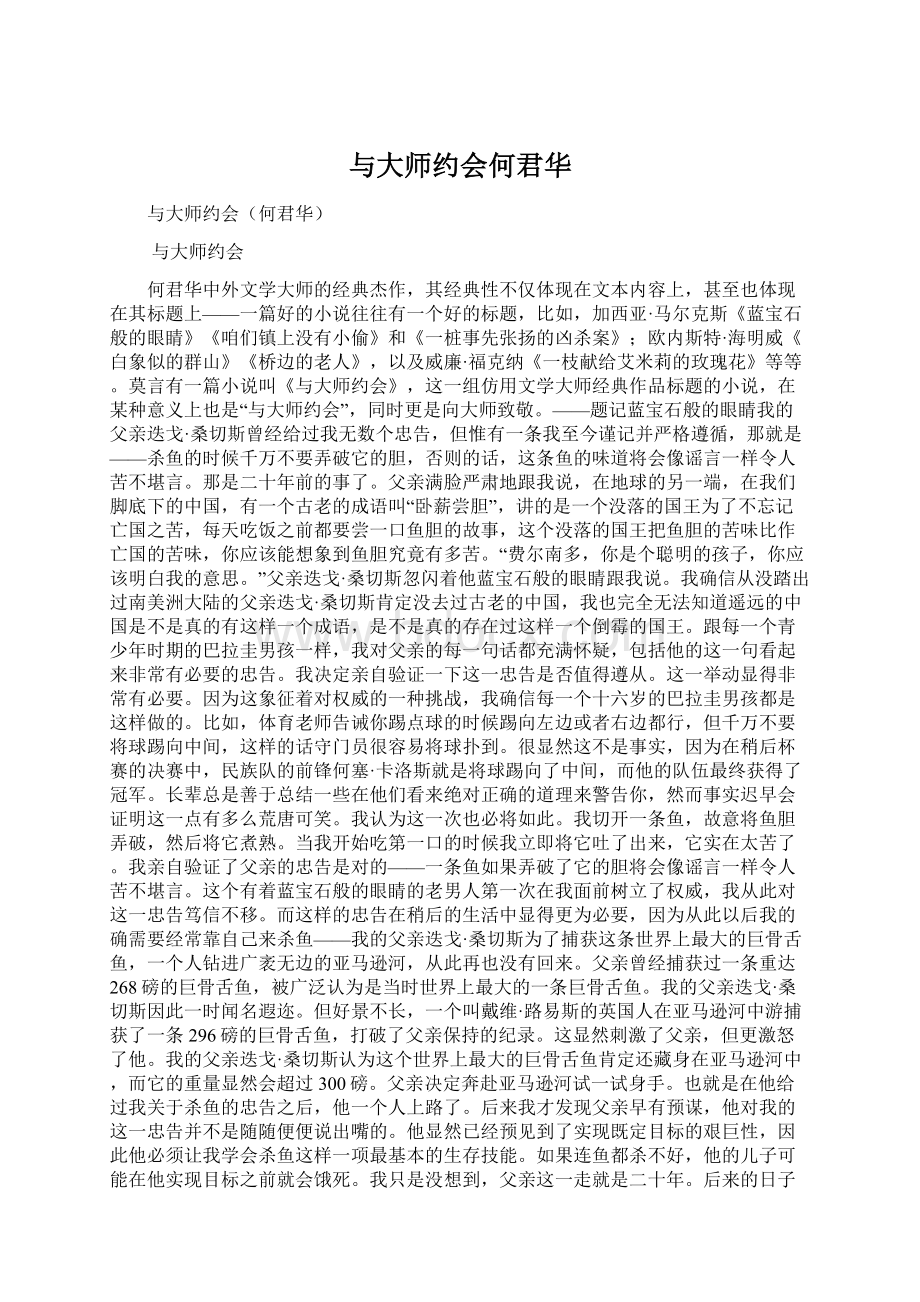
与大师约会何君华
与大师约会(何君华)
与大师约会
何君华中外文学大师的经典杰作,其经典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内容上,甚至也体现在其标题上——一篇好的小说往往有一个好的标题,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蓝宝石般的眼睛》《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欧内斯特·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桥边的老人》,以及威廉·福克纳《一枝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等等。
莫言有一篇小说叫《与大师约会》,这一组仿用文学大师经典作品标题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与大师约会”,同时更是向大师致敬。
——题记蓝宝石般的眼睛我的父亲迭戈·桑切斯曾经给过我无数个忠告,但惟有一条我至今谨记并严格遵循,那就是——杀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弄破它的胆,否则的话,这条鱼的味道将会像谣言一样令人苦不堪言。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父亲满脸严肃地跟我说,在地球的另一端,在我们脚底下的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成语叫“卧薪尝胆”,讲的是一个没落的国王为了不忘记亡国之苦,每天吃饭之前都要尝一口鱼胆的故事,这个没落的国王把鱼胆的苦味比作亡国的苦味,你应该能想象到鱼胆究竟有多苦。
“费尔南多,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父亲迭戈·桑切斯忽闪着他蓝宝石般的眼睛跟我说。
我确信从没踏出过南美洲大陆的父亲迭戈·桑切斯肯定没去过古老的中国,我也完全无法知道遥远的中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一个成语,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这样一个倒霉的国王。
跟每一个青少年时期的巴拉圭男孩一样,我对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怀疑,包括他的这一句看起来非常有必要的忠告。
我决定亲自验证一下这一忠告是否值得遵从。
这一举动显得非常有必要。
因为这象征着对权威的一种挑战,我确信每一个十六岁的巴拉圭男孩都是这样做的。
比如,体育老师告诫你踢点球的时候踢向左边或者右边都行,但千万不要将球踢向中间,这样的话守门员很容易将球扑到。
很显然这不是事实,因为在稍后杯赛的决赛中,民族队的前锋何塞·卡洛斯就是将球踢向了中间,而他的队伍最终获得了冠军。
长辈总是善于总结一些在他们看来绝对正确的道理来警告你,然而事实迟早会证明这一点有多么荒唐可笑。
我认为这一次也必将如此。
我切开一条鱼,故意将鱼胆弄破,然后将它煮熟。
当我开始吃第一口的时候我立即将它吐了出来,它实在太苦了。
我亲自验证了父亲的忠告是对的——一条鱼如果弄破了它的胆将会像谣言一样令人苦不堪言。
这个有着蓝宝石般的眼睛的老男人第一次在我面前树立了权威,我从此对这一忠告笃信不移。
而这样的忠告在稍后的生活中显得更为必要,因为从此以后我的确需要经常靠自己来杀鱼——我的父亲迭戈·桑切斯为了捕获这条世界上最大的巨骨舌鱼,一个人钻进广袤无边的亚马逊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曾经捕获过一条重达268磅的巨骨舌鱼,被广泛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条巨骨舌鱼。
我的父亲迭戈·桑切斯因此一时闻名遐迩。
但好景不长,一个叫戴维·路易斯的英国人在亚马逊河中游捕获了一条296磅的巨骨舌鱼,打破了父亲保持的纪录。
这显然刺激了父亲,但更激怒了他。
我的父亲迭戈·桑切斯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巨骨舌鱼肯定还藏身在亚马逊河中,而它的重量显然会超过300磅。
父亲决定奔赴亚马逊河试一试身手。
也就是在他给过我关于杀鱼的忠告之后,他一个人上路了。
后来我才发现父亲早有预谋,他对我的这一忠告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出嘴的。
他显然已经预见到了实现既定目标的艰巨性,因此他必须让我学会杀鱼这样一项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如果连鱼都杀不好,他的儿子可能在他实现目标之前就会饿死。
我只是没想到,父亲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后来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都在想,耗时如此之久就连我父亲本人可能也完全没有预料到。
我当然坚信父亲还活着,他蓝宝石般的眼睛依然会将我的生活照亮。
他之所以迟迟不肯现身的原因在于他还没有捕获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条巨骨舌鱼。
可能你也已经听说了,已经有人捕到了重达355磅的巨骨舌鱼。
这验证了父亲的预言,他很早以前就认定世界上最大的巨骨舌鱼肯定超过300磅。
而这样空前的重量显然给父亲的捕捞工作增加了难度,他不得不更加勤奋也更加艰难地工作,他必须日夜出没在亚马逊河上。
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显然让他无暇顾及别的任何事物,甚至也包括时间这可怕的魔鬼。
是的,时间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魔鬼。
二十年来,我的爷爷胡安·桑切斯和奶奶马丽萨·桑切斯先后去世,母亲艾伦娜·桑切斯声称她无法忍受将一生消耗在毫无边际的等待里,果断地改嫁给了一名乌拉圭商人卡塞雷斯·罗德里格斯,随后他们一起搬去了圣地亚哥再也没有回来。
时间这个魔鬼唯一没有打败的人是我。
我坚信父亲一旦捕到世界上最大的巨骨舌鱼就会归来。
我相信他会为我依然谨记他的忠告而高兴不已,尽管彼时我已经不再年轻,但他依然会忽闪着蓝宝石般的眼睛跟我说:
“费尔南多,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我在科罗拉多小镇开诊所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但是现在,我不打算干下去了,我太老了。
我决定从明天起退休。
也就是说,今天是我上班的最后一天。
在最后一天里,我决定做一件好事,一件特别一点的事,为我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句号。
我已经有了主意。
因为我看见瞎子乞丐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走进来了。
“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您能行行好,给我几个比索吗?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永远都是这句开场白。
“马里奥,遇上我你今天可真是行大运了!
”我抬起脖子对瞎子马里奥说道。
“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说实话,我并不明白您的意思。
难道您是说今天真的要大发慈悲给我几个比索吗?
感谢上帝!
”罗德里格斯看着我说,眼神充满期待。
“难道获得几个比索就称得上是行大运吗?
马里奥,你也太小瞧我了!
”乞丐永远都是乞丐,眼里只有那么一点儿蝇头小利。
“那么,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您能告诉我今天我究竟要行什么大运吗?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殷切地看着我。
“你还真得好好感谢上帝。
马里奥,我该怎么跟你宣布这个好消息呢?
我决定——给你做白内障复明手术。
马里奥,很快你就能获得光明了,我保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我斩钉截铁地说。
“哦,天哪!
我可没有钱支付昂贵的手术费用啊,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大惊失色地叫道。
“我没说要收你的手术费啊。
马里奥,听清楚了,我决定大发慈悲,免费为你做一次手术。
马里奥,你撞上大运啦!
”我大声宣布道。
“哦,天哪。
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您此前可从没这么做过啊!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惊讶地叫道。
的确如马里奥所说,此前我从未为一个病人免费实施过手术。
别说为他们做手术,就是一小盒胶囊我也从未免费给过。
我想在科罗拉多小镇树立这样一种观念,给人看病也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颇有技术难度的劳动,医生也是需要吃饭的,绝不是什么圣人君子,看病必须给钱,给钱才能看病,一个比索也不能少。
我当然知道有人在议论我太过绝情,尤其是在艾伦娜事件上。
三年前,可怜的艾伦娜小姐由于支付不起医疗费用眼睁睁死在我的诊所前。
人们对我展开了空前的抨击,甚至扬言要将我赶出科罗拉多小镇(他们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整个科罗拉多小镇只有我这唯一一家诊所,也只有我一名执业医生。
赶走了我,谁来给他们看病呢?
),但我对他们的激烈指责毫不在意。
说实话,艾伦娜小姐我可以救,但我不能为了救她而坏了我的规矩,让那些穷鬼以为没钱也可以看病,我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说你撞大运了啊,马里奥。
实话跟你说吧,今天是我作为执业医生的最后一天。
从明天起,我就打算退休了。
我决定为人免费治一次病来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当然,我也用不着为我自己亲手打破规矩而担心,因为明天我就要关门——我再也不会给任何人看病啦。
马里奥,你真是三生有幸,我决定把这唯一的免费机会给你。
”我高高在上地说。
“哦,天哪。
令人尊敬的费尔南多医生,您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感谢上帝,哦,感谢上帝!
”马里奥·罗德里格斯激动得语无伦次。
说实话,马里奥的病情并不复杂——先天性白内障,而这样的复明手术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马里奥家实在太穷了,即使是做这样简单的手术,马里奥家也拿不出一个比索。
要不是我今天大发慈悲,马里奥可能一辈子都是瞎子。
手术很成功。
这是我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做手术,反而是我紧张了那么一会儿。
尽管如此,我还是顺利为马里奥实施了手术。
马里奥千恩万谢地走了。
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完美地结束了。
我准备收拾好物品就此关门大吉。
就在这时,一伙人闯了进来。
我仔细看了一下,来人中有我认识的,领头的一个应该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的哥哥——费利佩·罗德里格斯。
费利佩·罗德里格斯气势汹汹地走到我跟前,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逼问道:
“费尔南多,你为什么要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为马里奥做手术?
你获得授权了吗?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没有抢劫犯,没有人干非法的勾当,我们只能靠马里奥四处乞讨,合法地博得人们的同情来养家度日。
现在,你无缘无故弄好了马里奥的眼睛,我们一大家子人今后吃什么?
”不等我开口申辩,费利佩·罗德里格斯就一拳击在我的额头上。
我瘫倒在地,打翻了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手术盘。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插进了我的后背,可能是一把手术刀或者手术剪什么的,我感觉后背有血流了出来。
我想爬起来,但根本爬不起来。
恍惚中,费利佩·罗德里格斯还在嘟哝着:
“咱们镇上没有小偷,连一个也没有,咱们可不能去偷去抢啊,犯法的事我们可不能干,可眼下该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重新把马里奥的眼睛弄瞎吧?
要不我们只能饿死……”有人建议道。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我已经无力阻止残忍的命运再次降临到马里奥·罗德里格斯身上,我感觉我的血越流越多,我就要死了。
一桩事先张扬的死人事件从一串混乱不堪的噩梦中醒来之后,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突然神秘兮兮地说道:
“七天之内,村庄里将会有人死去。
”很快,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早起后的这第一句话就传遍了整个科罗拉多村。
“疯老婆子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说,七天之内村子里就要死人啦!
”人们奔走相告。
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阿尔伯塔老太太说的是疯话,但仍然有人将十年前的一桩旧事重提,认为对于阿尔伯塔老婆子的话不可大意。
这桩旧事就是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准确地预言了科罗拉多村的一场洪灾。
那场洪水卷走了科罗拉多村十几户人家的二十多头牲口和六条人命。
在洪水突然到来之前的晌午时分,阿尔伯塔老太太曾挨家挨户通知了这一灾难即将到来的消息。
但悲剧的是,没有一户人家愿意听从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耐心的规劝,照样坐在自家屋里优哉游哉。
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对此痛心不已,只能眼睁睁看着洪水肆虐,不断劈开破旧的房屋并卷走惊恐的人群。
好在诸多村民都是靠下河捕鱼为生,多数都是游泳的好手,他们救起了慌乱的落水者,但还是可惜了几名老人、妇女和婴儿的性命。
人们耗费半年的时间重建了科罗拉多村,一部分人也就此建立了对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的迷信。
他们认为阿尔伯塔老太太是一个能与上帝对话的人,她能够知晓一些未来的事物。
但多数人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阿尔伯塔只不过刚好路过北部的村庄,看到了山谷后面疯涨的河水而已,哪里有什么预知未来的本事。
村庄里迷信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的人开始人心惶惶,他们认为老太太的预言终将应验。
他们纷纷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仔细查看身体的每一部分,确信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运转自如才放下心来。
公开宣称不相信阿尔伯塔老太太的人们也暗地里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尽管口头上不信,但谁不害怕倒霉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呢,还是小心为好。
所有科罗拉多村的人都坚信自己是健康的。
所有的科罗拉多人都相信如果阿尔伯塔老太太的预言如果应验的话,那么死去的人必将是老村长那塔利西奥·桑托斯。
因为那塔利西奥老村长已经在十八年前中风偏瘫,他已经在他那张陈旧的木床上整整躺了十八年,病魔也该把他带走了。
然而很快有人意识到,能夺走生命的并非只有病魔,还有很多其他并不少见的意外事件也能夺人性命,比如溺水事件,比如从山坡上跌下来,如此等等。
于是大家默契地呆在家里闭门不出。
不去下河捕鱼总不至于溺死吧?
不去爬山采果不至于跌死吧?
很快又有人意识到,呆在家里也并非十全之策。
因为还有令人胆寒的山体滑坡和地震。
很快,几乎所有人都同时想到了一个理想的避难场所——村子中间的自由广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去处了。
人们纷纷像蜜蜂一样涌向自由广场。
大家相互打着招呼在广场上住了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来到广场上的人们不仅包括笃信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的人,也包括那些口头上不信的人。
毕竟,谁也不愿意跟不可知的可怕的命运迎头赶上。
最后,就连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本人也来到了广场上。
不过,这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她是被她的孙子何塞·西蒙德斯强行背来的。
整个科罗拉多村唯有一个人没有来到自由广场,那就是那塔利西奥·桑托斯老村长。
他瘫痪在床,不可能徒步走来。
人们据此相信,如果阿尔伯塔老太太的预言果真应验的话,那么必定是那塔利西奥老村长死亡无疑。
人们进一步推断,导致老村长死亡的原因除了疾病以外,还有可能就是与房屋倾倒有关,那不是山体滑坡就是地震。
人们对此心知肚明,但没有一个人提出把那塔利西奥老村长抬到广场上来。
人们仿佛已经商量好了让老村长赴死,好让全村人躲过悲惨的命运。
有年轻人甚至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那塔利西奥老村长家查看他有没有死去,可每天早晨老村长都睁着溜圆的双眼神采奕奕,丝毫没有死亡的迹象,年轻人只好摇着头沮丧地重新走回广场。
人们就这样忧心忡忡地在自由广场上住下了,直到第七天晚上,这时人们的脸上才终于开始有了笑逐颜开的喜色。
马上就要躲过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预言的死亡截至时间了,有人开始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有人欢呼着爬上了广场中央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将军雕像。
就在这个时候,悲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从未有人攀爬过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将军雕像很快倾倒下来,砸向了坐在雕像底部的人群,可怜的人们来不及躲闪就被碾成了肉饼。
人群里的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急得直跺脚:
“你看,我就说要死人吧!
天哪,我的上帝!
”人们从雕像下面清理出六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的预言果真应验了。
从此,科罗拉多人对阿尔伯塔·西蒙德斯老太太笃信不移,她成了与神平起平坐的人。
白象似的群山往常这个时候站在桂花树底下等邮递员的人是母亲,但今天是我。
老师说,如果下个星期我还没有字典的话,就不要去学校了。
班上每个同学都有了一本棕色封皮的《新华字典》,除了我。
现在,我比母亲更需要一张汇款单。
每个月初,父亲都会从遥远的浙江寄一张汇款单回来。
母亲的化肥、爷爷的中药和我的学费都要指望这张小小的汇款单。
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邮递员都会骑着自行车从镇上赶来,交给我们来自远方的信件、报刊和包裹,当然还有绿色的汇款单。
我们偶尔也会到镇上去,但并不总是有这样的机会。
每逢收到汇款单,通常都是母亲带着身份证独自到镇上唯一的邮局去取现金,但有时她也会带上我和弟弟。
如果她愿意带上我和弟弟,就说明我们又要到照相馆去照相了。
我和弟弟就会高兴得像大同水库里的鲤鱼一样蹦起来,兴高采烈地跟在母亲后面跳个不停。
我们一大早就出发,上午去照相,中午要在镇上吃一顿大餐。
吃大餐——这正是我和弟弟欢喜不已的原因。
我们终于又能吃到久违的油条和炸饼了——我当时以为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这世上不可能再有更好吃的东西了。
我和弟弟总是舍不得一口气吃完,往往要拿在手里带回家去,在小伙伴面前骄傲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
我们的照片总是洗两张,一张放在家里的相框中,一张要随信寄给远在浙江的父亲。
母亲说:
“你们一天一个样,哎,这都半年了,你爸也不知道你俩又长高了多少。
”母亲一边说着,一边仔细地用早就写好的信纸把照片包起来,还一定要亲眼盯着营业员糊好封口贴上邮票才放心。
今天就是星期五,邮递员叔叔一定会来的。
我站在桂花树底下焦急地等待着,时不时地踢起树底下的小石子。
实在等不及了,我还跑去清溟桥头看过两次。
清溟桥头是镇上到村里唯一的路口,邮递员叔叔每次就是从这里摁着车铃到我家门口的。
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我跑到了这里,也依然没有看到邮递员的半点踪影。
我只好沮丧地往回走,母亲抱着一捆柴火过来跟我说:
“天都这么黑了,今天邮递员大概是不会来了吧。
再说,今天才是月底,你爸要到月初才会汇款回来呀。
”我不理会母亲的话,仍是痴痴地站在桂花树底下等。
母亲没有办法,抱着柴火进屋了。
天越来越黑,月亮也升了起来。
我一抬头,一片雪花蓦地飘落到我身上。
我这才发现,根本不是月亮升了起来,而是下起了大雪。
大雪纷纷扬扬,很快就将漆黑的乡村染成了白色。
我心想,突然下起这么大的雪,邮递员叔叔肯定不会来了。
我不得不懊恼地往家里走去。
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一阵翠鸟般的悦耳铃声传进了我的耳朵,邮递员叔叔来了!
那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自行车铃声了。
我迈开步子跑向蜿蜒逶迤的乡村公路,群山像白象一样涌向我的眼前。
果然,一辆雪白的自行车像白鸽一样向我飞来。
是的,那就是邮递员叔叔的自行车。
他正冒雪向我骑来。
不,与其说是骑,不如说是踩着滑雪板向我飞来。
他的身上已经落满雪花,一如去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堆的那个巨大的雪人。
他骑到我跟前,不住地解释说:
“隔壁几个村子信件多,又下了雪,所以来晚了,实在对不起。
小弟弟,有你家的汇款单……”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了,二十年弹指一挥,我依然记得那个遥远的冬日傍晚,记得那个在树荫下躁动地踢着石头子的少年,记得那白象似的群山,群山下的乡村公路上,那个雪人般的邮递员叔叔骑在自行车上像白鸽一样飞……桥边的老人如果赶不上清溟桥头的渡船,我们就不得不步行十几里山路去镇上上学。
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总是早早备好书包、大米和一个星期的腌菜,坐在大同水库岸边等渡船到来。
开渡船的驾船佬总是最后一个来。
仿佛知道我们无论等多久都会继续等下去似的。
驾船佬总是慢悠悠地把船锚抛上岸,眯缝着眼睛看我们这帮学生娃争先恐后地往船上挤,还不忘大声斥责道:
“莫挤莫挤,淹死你们这帮急死鬼!
”所有人都不理会驾船佬的训斥,还是像一群急不可耐的蝌蚪一样往上蹿。
驾船佬的船是杉木做的,吱吱呀呀,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看起来随时都要散架,但只要我们质疑起来,或建议他打一条新船时,驾船佬总是说这船没问题,肯定能坐人,保证淹不死你。
偌大的大同水库偏偏只有他这一条渡船,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跳进他的船舱。
等所有人都坐定了,驾船佬却丝毫没有要开船的意思。
有人坐不住了,催促道:
“怎么还不开,莫非等酒喝?
”“等酒喝”是乡里骂人的俗话,指一个人慢性子、怠惰,一般只有长辈对晚辈说。
有学生娃胆敢这样没大没小地骂他,驾船佬却并不生气,照样坐在船头上一动不动。
原来,驾船佬是在等迟来的学生,想多赚几块钱渡费。
还真有不着急的“吊死鬼”(“吊”和“掉”同音,指凡事掉在后面,不着急不抢先的人)慢悠悠地从山路上下来。
整整一下午驾船佬都不着急,这时候反倒着急起来,大声朝山上喊道:
“吊死鬼,还不赶快!
”听了驾船佬一声吼,几个吊死鬼才快步跑起来。
嘟嘟嘟……驾船佬摇响柴油机,船终于开动了。
船头劈开波浪,像一条巨大的青鱼,向下游的大同镇开去。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都会准时去清溟桥头等渡船,但是有一次,我也当了吊死鬼。
那是一个秋日的上午,我在池塘里帮爷爷挖藕,不小心弄湿了校服,奶奶非要等校服晒干才肯让我穿上去上学,也或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已经不记得了。
总之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我迟到了,我在狭窄的乡村公路上疯狂地奔跑着,风呼呼地从我耳边吹过,我感觉我肯定赶不上渡船了,我不得不一次次地加快步伐。
等跑过了三个山头,清溟桥头终于在我眼前出现时,让我欣喜不已的是,渡船竟还等在那里!
“吊死鬼,就等你了,还不赶快!
”驾船佬照例远远地吼了一句。
我连忙欢快地朝他跑去。
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这个驾船佬嘴上不饶人,心地倒是挺善良——他之所以每次都不肯早早开船,根本就不是为了多赚几个渡费,而是要等所有的学生娃都齐了才行。
驾船佬是那么精明的人,周围几个村子有多少娃在镇上上学他心里能不清楚吗?
他要是把船开走了,学生们该怎么去上学呢?
这个驾船佬!
我们支付的那几毛钱渡费怕是还不够渡船烧柴油的钱!
这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的事情。
那是在驾船佬的葬礼上,他的儿子偶然跟我说的。
他曾想把父亲接到城里去,他父亲死活不肯,他说:
“当年你不也是这样坐渡船到镇上去上学的吗,我若走了,谁来渡娃儿们去上学呢?
”现在,村里到镇上早已修起了水泥路,人们到镇上再也不用坐渡船,大同水库也开发成了旅游景点,连名字也改了,叫仙人湖。
过年回家的时候,一个人坐在清溟桥岸边,夕阳洒满金色的仙人湖,我还是会想起驾船佬。
一枝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花一枝鲜红的玫瑰花握在我的手上,马上,我就要将它献给美丽的艾伦娜·洛佩兹小姐,我准备正式向她求婚。
二十年前,同样有一枝这般鲜红的玫瑰花握在我的手上,我把它献给了美丽的艾米莉·桑切斯小姐。
那个时候我刚上中学二年级,艾米莉小姐是我的生物老师。
我几乎相信,艾米莉小姐是这个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那棕色的长发、洁白的牙齿,还有那美丽的乳房无不使我魂牵梦萦。
在植物园的一次户外活动中,我几乎就要用手触摸到艾米莉小姐光洁的乳房了。
当时,她正俯身在我眼前,试图用手去摘一片绿檀树的叶子。
她的身体倾向我。
两只饱满的乳房从她粉红色的领口呼之欲出。
我完全无法控制双手,我看见它们已经伸了出来。
是的,它们就要触摸到艾米莉小姐美丽的胸口了。
但是,我并没能触摸到它们,因为艾米莉小姐很快就摘下了叶子,旋即站直了身体。
我的手落空了。
“费尔南多,这是什么树的叶子?
”艾米莉小姐将她刚摘下的树叶举到我的眼前问道。
尽管我确信那是一片绿檀的叶子,但我还是用手接过树叶,说道:
“艾米莉小姐,让我仔细看一下吧。
”我的手指轻轻触碰到了艾米莉小姐的手指,而这正是我的目的。
我确信艾米莉小姐的手指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手指。
它们纤细、白嫩,指甲剪得光洁而圆润。
“这是一片绿檀树的叶子。
”我用肯定的口吻回答艾米莉小姐。
“不错,这的确是一片绿檀树的叶子,属于复叶类型,看来你对它的特征记得很清楚。
费尔南多,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艾米莉小姐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顿时感觉到了全世界最温柔的爱抚。
直至凌晨两点,我感觉艾米莉小姐轻轻的抚摸还在我的身上持续不止。
是的,我躺在寄宿制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失眠了。
我确信自己爱上了艾米莉小姐,在我十三岁的年纪。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里抽离出来,我发烧了。
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决定要献一枝玫瑰花给美丽的艾米莉小姐,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向她求爱。
一枝鲜红的玫瑰花握在我的手上,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学校走去。
教室里的同学们都出来了,唿哨也打了起来。
可是我完全不在乎,依旧步履坚定地朝校园走去。
我看到校长佩德罗·费尔南德斯从校长室怒气冲冲地冲了出来。
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叫嚣开除我,但我毫不在意,我的步伐依旧坚定而执着。
艾米莉小姐也出来了。
她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手握玫瑰花向她走去。
但是她很快镇定下来。
“费尔南多!
”我听到艾米莉小姐大声叫我的名字,我站定下来。
“这就是我让你去帮我采的玫瑰花吗?
”艾米莉小姐朝我走来,从我手中接过玫瑰花,转身向疾步跑来的校长佩德罗·费尔南德斯解释道:
“校长先生,这是我让费尔南多去采的玫瑰花,上一节课我刚刚讲到它,马上我就要讲解玫瑰花的授粉过程。
”艾米莉小姐说罢又转向我,“费尔南多,你可真是个勤快的孩子!
”“你确定是你让费尔南多采的玫瑰花吗,艾米莉小姐?
”校长佩德罗·费尔南德斯乜斜着眼睛问道。
“是的,我十分确定是我让他这样做的。
”艾米莉小姐坚定地说。
艾米莉小姐的语气有一种惊人的坚毅,让人听了几乎不容置疑。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并非真相,她哪里讲到了什么玫瑰花呀!
校长一甩手,气咻咻地转身走了。
同学们在教室前纷纷鼓起了掌,掌声越来越大,但我完全没听见,直至艾米莉小姐轻声叫我:
“费尔南多,走吧,我们一起去实验室。
”艾米莉小姐是这个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
哦,不,我确信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尽管我从未踏出这个小镇,但我确信如此。
我同样确信她还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人。
她用坚定不移的善良保护了我,避免了我在十三岁的年纪就被开除出学校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她阻止了我过早地陷入一场完全不会有结果的(甚至算不上的)爱情。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成了整个国家最著名的植物学家之一。
我的未婚妻艾伦娜·洛佩兹小姐是我在国家研究所的同事。
我将要献给她的这枝玫瑰花是我刚培育出来的品种,我将它命名为“艾米莉花园玫瑰”,我确信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品种,对于这一点我确定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