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郭于华.docx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郭于华.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郭于华.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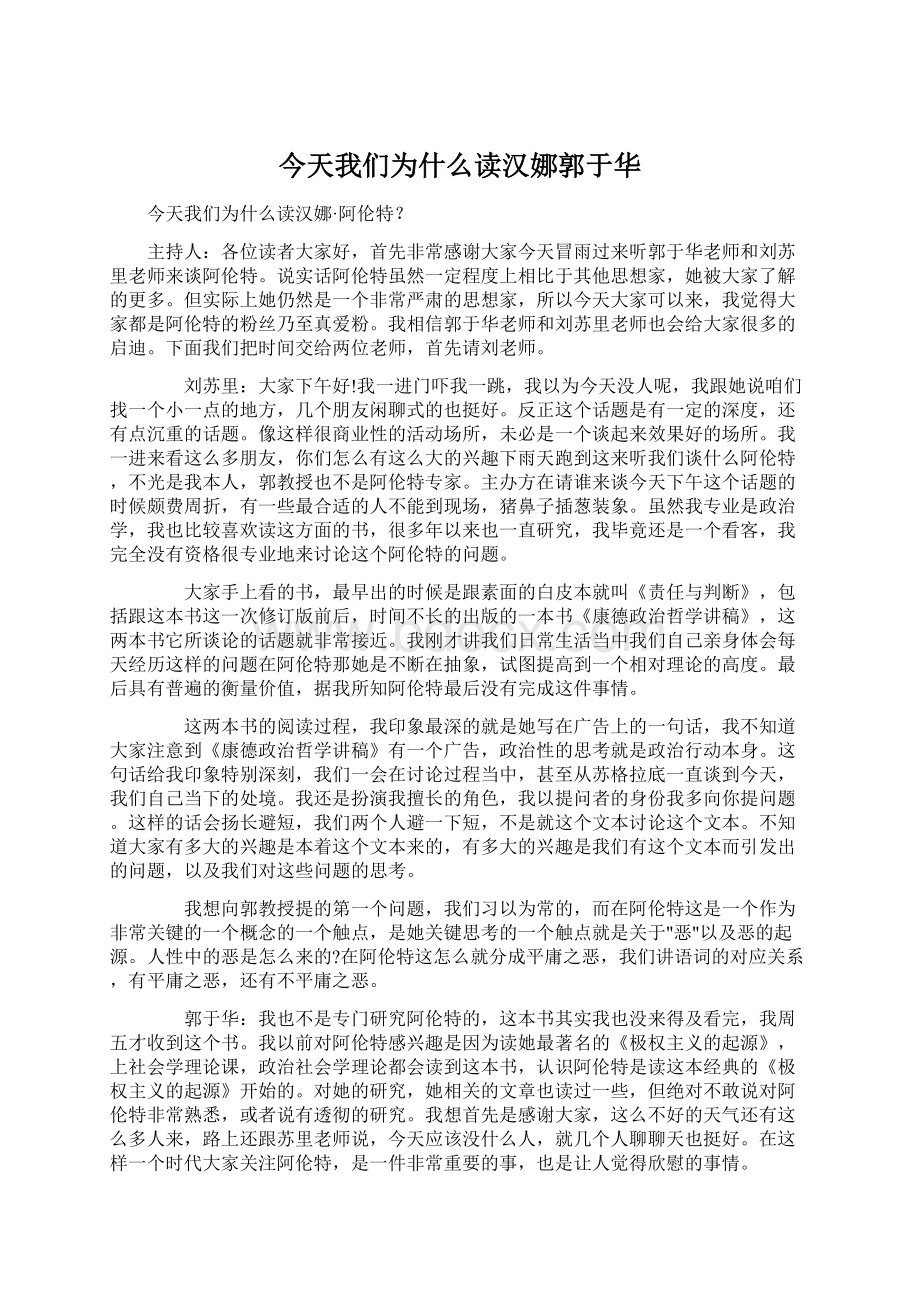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郭于华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
主持人:
各位读者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冒雨过来听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来谈阿伦特。
说实话阿伦特虽然一定程度上相比于其他思想家,她被大家了解的更多。
但实际上她仍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思想家,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来,我觉得大家都是阿伦特的粉丝乃至真爱粉。
我相信郭于华老师和刘苏里老师也会给大家很多的启迪。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老师,首先请刘老师。
刘苏里:
大家下午好!
我一进门吓我一跳,我以为今天没人呢,我跟她说咱们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几个朋友闲聊式的也挺好。
反正这个话题是有一定的深度,还有点沉重的话题。
像这样很商业性的活动场所,未必是一个谈起来效果好的场所。
我一进来看这么多朋友,你们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下雨天跑到这来听我们谈什么阿伦特,不光是我本人,郭教授也不是阿伦特专家。
主办方在请谁来谈今天下午这个话题的时候颇费周折,有一些最合适的人不能到现场,猪鼻子插葱装象。
虽然我专业是政治学,我也比较喜欢读这方面的书,很多年以来也一直研究,我毕竟还是一个看客,我完全没有资格很专业地来讨论这个阿伦特的问题。
大家手上看的书,最早出的时候是跟素面的白皮本就叫《责任与判断》,包括跟这本书这一次修订版前后,时间不长的出版的一本书《康德政治哲学讲稿》,这两本书它所谈论的话题就非常接近。
我刚才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亲身体会每天经历这样的问题在阿伦特那她是不断在抽象,试图提高到一个相对理论的高度。
最后具有普遍的衡量价值,据我所知阿伦特最后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这两本书的阅读过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写在广告上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有一个广告,政治性的思考就是政治行动本身。
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会在讨论过程当中,甚至从苏格拉底一直谈到今天,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
我还是扮演我擅长的角色,我以提问者的身份我多向你提问题。
这样的话会扬长避短,我们两个人避一下短,不是就这个文本讨论这个文本。
不知道大家有多大的兴趣是本着这个文本来的,有多大的兴趣是我们有这个文本而引发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我想向郭教授提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而在阿伦特这是一个作为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触点,是她关键思考的一个触点就是关于"恶"以及恶的起源。
人性中的恶是怎么来的?
在阿伦特这怎么就分成平庸之恶,我们讲语词的对应关系,有平庸之恶,还有不平庸之恶。
郭于华:
我也不是专门研究阿伦特的,这本书其实我也没来得及看完,我周五才收到这个书。
我以前对阿伦特感兴趣是因为读她最著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上社会学理论课,政治社会学理论都会读到这本书,认识阿伦特是读这本经典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开始的。
对她的研究,她相关的文章也读过一些,但绝对不敢说对阿伦特非常熟悉,或者说有透彻的研究。
我想首先是感谢大家,这么不好的天气还有这么多人来,路上还跟苏里老师说,今天应该没什么人,就几个人聊聊天也挺好。
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家关注阿伦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让人觉得欣慰的事情。
我们现场的这个广告,这个题目的设计,我觉得设计的特别好,一看就觉得深得阿伦特精髓,无"思"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读汉娜·阿伦特?
好像一下触动到心里很迫切、非常解渴的话题。
我努力地回答苏里老师的问题,但可能不能回答得让大家满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而且根据大家的了解,阿伦特特别重要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对问题给予一个现成的答案,而是激发出思考的能力、思考的愿望,是用问题来激发更多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去进行思考,而不是给一个现成的答案,这可能是阿伦特今天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
刘苏里:
她后期的研究这个特点比较明显,直到她去世几乎是有十年左右的时间,耶路撒冷的审判到她去世整十年多的时间,最后没有产生一个完整系统的论断。
一方面可能是它难,你要读她的书的过程当中,包括《人的境况》,还有《共和的危机》的危机,要做很多边界厘清工作的事情。
再一个就是是她的重要性,不仅历史给我们提供很多答案,每天我们都会遇到所谓责任和判断,判断什么意思,就是是非、对错、善恶、好坏,我们遇到这样的境况而它的复杂性,它的难度太高,来不及抽象,再给她十年的时间可能够了。
郭于华:
关于"恶"这个题目既是一个哲学思考之维,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现实之维,当然阿伦特她本身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大家知道她的观点、她的思想又跟她作为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这样一个切身的经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她对于恶的感受、理解到对其加以思考做出哲理的分析,其实是有着切肤之痛,有着她非常切身的现实基础的。
比如大家比较熟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汉娜·阿伦特》那个片子大家都看过吗?
她探讨的问题的起因那个报告。
很多人不同意翻译成(封面的)"平庸之恶",书的里面很多地方用"恶之平庸"来概括,她提出这么一种分析性的概念,不完全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分析性的理解。
虽然因此遭到很多的误解和攻击,但是读她的东西,你还是能够看出她想探讨的东西是什么,她并没有否认那样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给不光是对犹太人(犹太人也是人类),它给整个人类造成的巨大伤痛,从它的表象来看,它应该是一个极端的恶,一个绝对的恶,但是恶之平庸性和恶的极端性绝对性是什么关系?
我觉得阿伦特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这种体制、制度造成的恶和公民的个人责任是什么关系。
刘苏里:
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或者是个人责任与制度、体制、体系政府之责任。
郭于华:
她着重探讨这样的一个关系,艾希曼这个人,如果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一个个体身上,他是一个极大的恶的形象,就像是一个魔鬼,这个时候就等于说是归结到一个个体身上去了,而实际上它背后强调的是个人在体制当中作为体制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这是什么样的关系。
阿伦特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说用体制之恶遮蔽个人之恶,而是重在探讨集体的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
在她看来这样一种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这样选择的难题。
当你参与政治的自由和逃避政治的自由都被取消了,这个时候个人应该如何做?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归结到不思考、思维的匮乏。
她所说的思维是一种人的自我反思,人的思维。
在她看来思维特别重要的几个作用是,一个作用是她在书中说的--"揭露一切未经审问明辩之意见的偏颇",有一个纠正偏颇的作用,这些偏颇是没有经过思考造成的;把那些我们习以为常,而且经常冥顽不化之价值、学说、教条,信念的偏执迷妄加以铲除,这是思维最重要的作用;同时她说思维活动还能酝酿出良知,也就是说你能够去分辨善恶,能够分辨是非;当然还有就是第三个层面,思维活动还能够确保人的道德的完整性。
阿伦特把恶之平庸性跟思维的匮乏,即不思考、不反思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理解,我想借用哈耶克的那本著名的书《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意思,我想这本书大家也比较熟悉,在哈耶克看来,计划经济指令性经济是通往奴役之路,如果借用这样的表达,我想说,不思考,是通往邪恶之路,这是对恶的一种理解。
大家知道阿伦特所研究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极权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部制造恶的机器,它想要把所有的人,把他的部下都变成机器上的齿轮,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绞杀人们的生命和思想。
如果联系到我们社会的现实,这个比喻不难理解,咱们这用的比喻不是齿轮,我想问问大家用的是什么?
对,螺丝钉。
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变成螺丝钉,一个螺丝钉就是一个机器的零件,它怎么可能有自己的主张见解,有自己的思考。
而且这个螺丝钉非常的自觉,像《雷锋日记》里说的,"我要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闪闪发光,永不生锈"。
这个螺丝钉还不用别人来拧,它自己拧的特紧,而且把自己弄的闪闪发光不生锈,这就是极权体制下作为个体的一种处境,不思考就会带来这种螺丝钉的命运。
这个过程当中,阻碍你成为齿轮、成为螺丝钉的唯一障碍就是思考。
或者说思考的能力和思考的主动性是形成这样一种极权体制、变成齿轮和螺丝钉的最大阻碍。
刘苏里:
我打断你一下,阿伦特这么说肯定是有人质疑她,特别是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我刚才扫了一下在座的朋友们,超过50岁的人并不多,除了这位老先生以外。
我相信超过45岁的人也不多,如果不到45岁的话,不太会有感受,有一种情况就是被阿伦特批评的地方,因为阿伦特她在讲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时候,她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
强调恶是因为大家不思考,有一种情况,你根本整体不知道思考是什么的时候,你告诉我所谓恶的来源和人不思考或者思考的匮乏有关,如果我们想细致的厘清这件事情它成了无源之水。
我们两个经历过不知道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单位所造成的状态下,谁大脑是有思考能力的,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年轻的朋友不知道40年以前的中国,你大概多少知道一点今天的北朝鲜,北朝鲜的人性在政治领域一个共同体的生活中,它的人生当中的恶是跟他的不思考,他怎么思考。
北朝鲜连马恩列斯的著作都不售卖,因为他们不信那个东西,他们信主体思想。
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怎么来区分北朝鲜制度下个人的恶,第一它跟所谓不思考和思考的匮乏有关,他根本不知道思考是什么,也没有思考的参照物,也没有思考的对象,也没有思考的资源。
其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怎么检讨这个制度之恶,而制度之恶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这个具体的责任,阿伦特一再强调像艾希曼要承担最后解决法案他所应付的责任。
我不觉得阿伦特在谈到制度之恶的时候,她像谈论制度下的个人之恶这么的使劲,或者说她后头关于责任与判断的思考核心在个体这,而不完全是制度,当然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谈制度谈的多。
你是怎么看她有一种状况下,个体所谓恶的来源问题,以及个体的责任与制度的责任或者是集体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
郭于华:
我觉得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只阿伦特会涉及到,她毕竟还是涉及到集体责任和个体责任,这个在极权体制下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她还是涉及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只阿伦特,很多思想家也都涉及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一个社会现实的角度出发也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
大家在争论中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在说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
在制度、文化和人性这三者之间,大家其实有很多争论。
因为不乏文化决定论者,很多人会说今天中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留下的文化传统当中就缺少了宪政、民主、自由主义的因素。
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专制统治,它和它的意识思想文化是吻合的。
当然很多人就会不同意,我们把责任都归祖宗那去了,好像我们祖上没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不走上宪政民主的路径,不加入世界文明的主流。
也有人不同意归因到文化,认为制度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好的制度能够造就善,能把人性当中善的东西发挥出来,这样人性又出来了。
大家往往在这三者之间争论不休,到底哪个是决定性因素?
这样讨论就进入一个循环状态。
制度和文化造就人性,恶的人性又不能进行文化创新,它在制度上也不能进行制度创新,好似一个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
我想这样思考这个问题,这三者之间其实应该说是一个互构、互动的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
如果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中,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而今天中国的困境,其实是三者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虽然我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互构、互动的关系,但如果我们要破这个局,我们要破除这样的恶性循环,只能从制度层面入手,从制度层面进行变革和推动。
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就是从制度,当然主要是从经济体制开始的吗?
从这里开始社会转型的过程。
如果回到阿伦特的话,我想刚才苏里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不思考的原初性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法开始思考的情境。
刘苏里:
可能涉及到一点开放社会和半开放社会和开放社会加以区别的话,我们就更好理解这件事。
郭于华:
背后是一个政体的问题,我忘了阿伦特在哪说过,她表达过这个意思:
如果是一个专制政体,它也会限制人们很多权利,剥夺人们的权利,限制人们的自由,但是它不可能完全控制人们的思考、记忆、表达,也不可能完全控制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空间。
但是极权主义不同,极权主义是把所有的地方,大家注意极权主义的概念是从total那来的,totalitarianism意味着全面:
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私人生活领域的是全部要占领的。
极权政体下才有可能对人的控制、包括对人最不能控制的那些东西的控制达到一个极端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从政体的区别上理解的。
刘苏里: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我们经验当中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思考出发点。
比如说现在网上两波人互相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一个熟人在讨论近代以来的历史,他就问我,你说了这么多和我们学的不一样的东西都是从哪来的?
因为他在我的咖啡厅里,我说对面的书店里的书什么都有,他说是吗?
我说是啊。
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是北大的学生,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出版走到哪一步了,你在跟他说,我们互相认识,他才不会去反驳你,他不会拿他学的东西说你说的不对。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出版过,比如平型关大捷这个事是假的,他不知道这个事。
他说怎么可能,平型关大捷是假的呢?
平型关战役不是假的,但是我们从小学的平型关关于在抗日战争历史地位,以及在当时战役本身的情况,完全是假的,全是假的,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不知道重庆的抗日,台儿庄战役更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台儿庄战役,你怎么让他去思考,我来自我经验的。
还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一个人20岁之前美与丑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你父母带给你的,可是30岁以后的美与丑和你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我的经验直到今天为止的经验,我观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部分无论是70岁、80岁,还是17岁、18岁,当然年龄偏小一点,稍微好一点,特别惨的是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年龄段的人,几乎看不到会穿衣服的人。
大家不会穿衣服,样式、颜色、质地、和他本人的肤色、体型、气质,完全是乱七八糟。
你怎么看都不对劲你仔细想一想,按理说现在四十几岁到六十几岁这一批人,改革开放的时候,最小只有10岁,最大的才30岁,这里头我相信有很多人不仅在电视里面,报纸的广告可以看到那些模特,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去过国外。
可是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件事,你能给我回答吗,解决不了穿衣审美这件事情。
如果这个人连衣服都不会穿,他怎么可能在世界上看到其他的东西,比如看歌剧,听交响乐,住一个酒店他对酒店从洗手间到床到外面景色的融洽。
你让他改变,你让他在审美上是一个能思考的人,换句话讲你知道带路党和五毛这个争论,就我知道有一些五毛,他不是什么五毛,不是大家骂的五毛。
他不知道台儿庄是什么,关于台儿庄这件事,你说他是五毛,你就很冤枉他,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大家知道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信了20年、30年、50年的东西颠覆掉,还不如让他从11楼直接跳下去。
颠覆他的那个意义上的东西,他不一定出物理状态人的命,但是这个人精神死掉了。
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郭于华:
苏里老师的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今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
在座的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到别人给你们讲文革当中荒谬的事情,大家今天觉得也会匪夷所思,这事怎么可能啊?
那些人都疯了吗?
这是天方夜谭吗?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刘苏里:
每天都有,有人在课堂上就遇到这种情况。
关于上个世纪30年代大清洗,学生就说他是编的,没办法他就找俄文,学生说俄文也能编,他把当年的照片搬出来,学生说照片可以PS,学生就在课堂上和他吵架,最后他没办法把影像资料拿出来,学生讲那个可以剪辑。
当时老师都崩溃掉了。
郭于华:
不能崩溃,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了一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于人的根本性的摧毁,对于人的心智、头脑的根本性摧毁,这就是极权主义,如果说这是恶的话,也是最大的恶之一。
我早年写过一篇小杂文,当然也发表不了,自己挂网上了叫《叼着屎橛打滴溜,给个麻花都不换》,恰恰说的就是这种现象。
我们把它叫作意识形态的灌输,我们也叫它作"狼奶",其实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都是喝狼奶长大的。
我们相信平型关大捷,我们相信飞夺泸定桥,我们相信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打走了日本人。
我们不相信抗日战争当中主战场一直是国军在作战,这种历史的颠倒比比皆是。
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中国的四大恶霸地主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教科书,进入到历史书,进入到影视文艺作品。
大家知道都是谁对吧?
刘文彩、周扒皮、南霸天、黄世仁。
南霸天、黄世仁这两位是创作出来的文学形象,也可能有一点现实原型,基本上是虚构出来的。
而所谓周扒皮和刘文彩是实有其人,我自己做农民的口述史研究,会涉及到地主的问题,我曾经问同学们,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刘文彩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他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弄了水牢,又弄了收租院,迫害贫下中农,坏事做尽;周扒皮也根本不是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个事情通通没有发生过,我跟你们说你们能相信吗,很多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
在事实和历史真相重新呈现之后,大家会知道我说的不虚,我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大多数同学还是能够接受和明白的。
我一直跟同学说这些东西,已经过去的历史你如果想真的了解它的真相,了解它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苏里先生说到的你可以去看书,你可以找资料,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只要你想知道,你一定能够知道的。
其实很大的原因在于有些人不想知道,因为颠覆自己以往的、一直以来的认知,是一件痛苦的事,是一件觉得很难受的很不舒服的事。
我认为这和人性当中的一些弱点有关,回到阿伦特意义上就是对于思维我们有一种惰性,我们不愿意重新思考一些事情,这些事我们觉得很麻烦,又让自己不痛快,这是人性当中的弱点,惰性。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第一部分,反犹主义,分析当时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以至最后导致种族大屠杀,阿伦特发现一个现象,她分析反犹主义浪潮什么时候达到顶峰,在犹太人丧失了政治权利,也丧失了政治参与意识,不愿意参与政治,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的时候,他们除了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外,其他方面很边缘了,这个时候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那么容易被调动起来。
这一方面是不是跟人性当中最黑暗的部分是有关的?
再一个也跟犹太人当时他们自身退出政治领域,淡出公共领域,意味着你放弃了你的权利,你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引入我们关于恶的思考,有一个直接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解,这也是阿伦特的非常明确的观点。
她对于政治思考,她认为政治是作为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动物存在的,他要参与政治生活,政治性和公共性在阿伦特那经常是同时在使用,因为她认为作为政治的人,你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才是真正的人。
不难看到我们的社会当中,人人都觉得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多少人对政治感兴趣,今天依然如此。
商人就说"在商言商",学者你就是该做什么专业做什么专业去,艺术家该怎么表达,大家都跟政治没什么关系。
在我们社会当中,大家都逃离政治,特别厌恶政治,觉得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既肮脏又黑暗,我们恨不得离的远远的。
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原因,一是历史原因,我又要说到文革,文革那个时期政治是统领一切的,叫做"政治挂帅",所有的生活当中政治挂帅。
如果你的政治生命完结了,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在人的社会当中没法生存下去,我们曾经历过那样极端的政治覆盖一切生活--社会、文化、思想领域那样一个时代,它是一种恐惧,给人们带来恐惧。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大家觉得中国社会走上常轨,终于开始正常了,改革的设计师们也会提出叫做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大家都去搞经济搞生活了,关注民生,关注经济怎么快速发展。
大家觉得终于不被政治所迫害,或者嫌政治讨厌我就离开它,终于有了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从历史当中得到了这样一种教训:
大家离政治远远的。
这也是我们社会很多人不关心政治或者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家如果想一想,当你想逃离政治的时候,政治是绝不放过你的。
在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问题都是跟政治有关的。
如果你放弃政治的权利,你会有可能变成砧板上的肉,我们在今天这样说的时候,我是想说,其实政治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跟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关。
因为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是生活在人们之中,生活在社会之中,你不是鲁宾逊,你要跟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你有个人的权利,有自由独立的精神,与此同时,其他的个体跟你一样是这样的人,人和人之间要发生这种关联和互动,需要有一种合理的、正常的关系。
而这就涉及到公共性和政治性的问题。
我有时跟同学们讨论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觉得自己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出身比如说你生在农村还是城市,你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这是政治,因为它决定了你的权利待遇是不公平的,你是不是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权利;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你的住所今天有没有可能被征地强拆掉的,这是政治;你吃什么样的东西,你的食品安全有没有保证,这当然是政治。
很多人会说我不关心政治,但如果他的孩子被毒奶粉侵害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这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当然是政治。
我们关于恶的东西,包括阿伦特说的思考,思考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的行动,这可以促使我们探讨刚才这类问题。
刘苏里:
她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重要问题,比如说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不论是半开放的还是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也遇到这个问题。
托尼朱特他写了几本书,我们翻译过来,他主要谈的就是这个话题,怎么能够让沉浸在消费主义、自我享乐甚至比如说在精神上自我放逐的人群,能够换回他们对公共事务的热情。
说到底公共事务就是跟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多数人没兴趣,肯定是少数人来决定这些事情。
少数人决定事情的时候,一条铁路由东修到西的时候,因为不牵扯南北的人无所谓,他没有反应,东西的人不高兴。
等到再修南北的时候,东西已经发生过那样的事情,不仅他们要看南北的笑话,他们知道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南北没有援助他们。
少数人很容易决定所有的事情,阿伦特她在讨论恶之起源,恶的源头,我们如何抵抗平庸之恶,或者恶之平庸,她确实是越来越重视的是个人的作用。
包括比如说自我反思,回到自己的思考的状态,她为什么讲所谓政治性的思考,实际上关于公共事务的思考,你其实就是政治本身。
她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她认为一个自我的思考,并不是孤独,其实你考虑的所谓公共事务不仅跟你个人有关系,也是跟更多的人有关系,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你回到你自己本身,你的自我思考的本身不要陷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上去。
你的自娱自乐,自我欣赏,你自己同意自己,认为我自己都是对的,这种思考本身具有相当的比如说自我挑战性,乃至于自我否定。
只有这样的自我回归,自我思考,在她看来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你包括刚才于华教授讲这个主题,不知道是谁起的所谓无"思"的时代要把思打上引号,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跟无思那个名字是一样的谐音,还是他认为我们只是一个所谓没有思想的时代。
郭于华:
思是名词还是动词?
刘苏里: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现代世界的起源》,在结尾的时候很悲观的谈了一段话,那一段话让人震惊,大意是其实整个人进入到没有思想的状态,而且乐而忘返。
人类最近几十年产生的绝大部分的问题都和我们离思想、离思考越来越远,不再乐此不疲,或者习惯于过思考的生活,你不思考你就不会有思想。
我们回到阿伦特来,谈这个所谓抵抗或者抗拒、反抗恶的平庸的途径、方法还有手段,还有出路。
郭于华:
刚才苏里说到无"思"的时代,或者今天人类的处境。
大家肯定知道一个词叫做"快乐机器人",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今天这种消费主义的影响也好,大家说娱乐至死也罢,迷失在消费当中,都是一种快乐机器人的现状。
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个人并不赞同都归结于人性当中的弱点,即便人性当中有这样的弱点,它依然不是最主要的根源。
那个最主要的根源是那样一种统治造成的,因为这样一种统治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作为极权主义基础的、阿伦特把它叫做"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结构的群众"。
作为这样一种统治,它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群众,大家可以理解一下,无自我权利意识,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基本的人权、政治权利比如选举权,社会权利比如能够平等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权利。
她强调缺乏这样的自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