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体释论.docx
《吴中体释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吴中体释论.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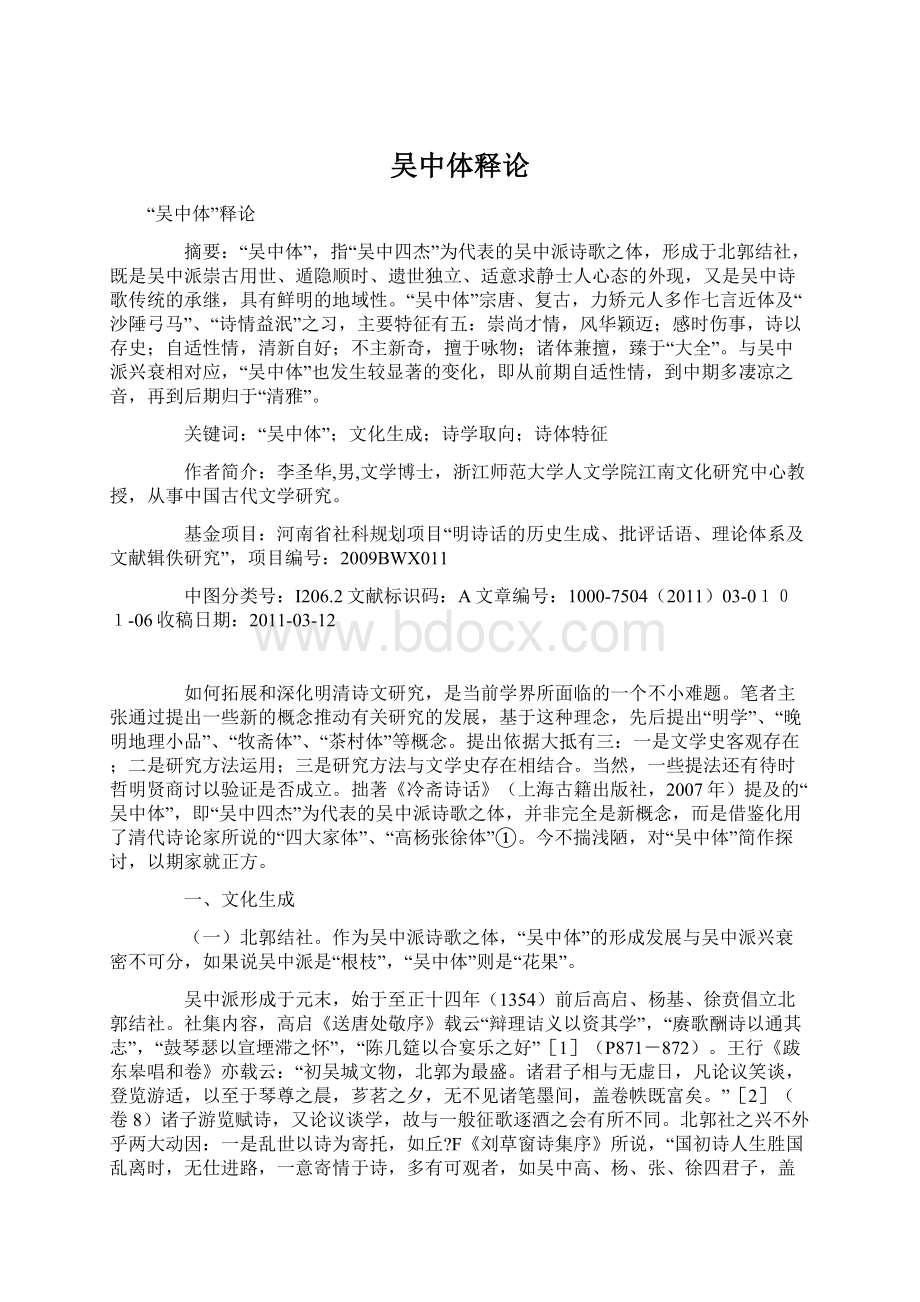
吴中体释论
“吴中体”释论
摘要:
“吴中体”,指“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形成于北郭结社,既是吴中派崇古用世、遁隐顺时、遗世独立、适意求静士人心态的外现,又是吴中诗歌传统的承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吴中体”宗唐、复古,力矫元人多作七言近体及“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主要特征有五:
崇尚才情,风华颖迈;感时伤事,诗以存史;自适性情,清新自好;不主新奇,擅于咏物;诸体兼擅,臻于“大全”。
与吴中派兴衰相对应,“吴中体”也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即从前期自适性情,到中期多凄凉之音,再到后期归于“清雅”。
关键词:
“吴中体”;文化生成;诗学取向;诗体特征
作者简介:
李圣华,男,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明诗话的历史生成、批评话语、理论体系及文献辑佚研究”,项目编号:
2009BWX011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7504(2011)03-0101-06收稿日期:
2011-03-12
如何拓展和深化明清诗文研究,是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小难题。
笔者主张通过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推动有关研究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先后提出“明学”、“晚明地理小品”、“牧斋体”、“茶村体”等概念。
提出依据大抵有三:
一是文学史客观存在;二是研究方法运用;三是研究方法与文学史存在相结合。
当然,一些提法还有待时哲明贤商讨以验证是否成立。
拙著《冷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提及的“吴中体”,即“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并非完全是新概念,而是借鉴化用了清代诗论家所说的“四大家体”、“高杨张徐体”①。
今不揣浅陋,对“吴中体”简作探讨,以期家就正方。
一、文化生成
(一)北郭结社。
作为吴中派诗歌之体,“吴中体”的形成发展与吴中派兴衰密不可分,如果说吴中派是“根枝”,“吴中体”则是“花果”。
吴中派形成于元末,始于至正十四年(1354)前后高启、杨基、徐贲倡立北郭结社。
社集内容,高启《送唐处敬序》载云“辩理诘义以资其学”,“赓歌酬诗以通其志”,“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1](P871-872)。
王行《跋东皋唱和卷》亦载云:
“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
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盖卷帙既富矣。
”[2](卷8)诸子游览赋诗,又论议谈学,故与一般征歌逐酒之会有所不同。
北郭社之兴不外乎两大动因:
一是乱世以诗为寄托,如丘?
F《刘草窗诗集序》所说,“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3](卷9)。
二是吴中相对承平富足,张士诚及其属官饶介等雅好文学。
二十三年(1363)九月,士诚叛元自立。
北郭诸子散去,张羽、徐贲偕隐吴兴,高启归居吴淞江上,社盟时续时断。
朱元璋军攻吴,北郭诸子陷围中,不废社集,放歌作答。
二十七年(1367)九月吴城之陷,构成北郭社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余尧臣、杨基、徐贲谪临濠,高启、张羽惶恐中隐遁山林。
洪武元年(1368),余尧臣授新郑簿,杨基授荥阳令,徐贲放归。
明年,高启、谢徽征修《元史》。
洪武三年(1370),高逊志、王彝续修《元史》。
尽管诸子幸得无恙,但旧盟难复。
高启睹故旧凋散,感慨系之,与王行思修复社盟,遂有洪武五年(1372)狮子林唱和。
洪武七年(1374),高启、王彝牵入魏观案死,北郭社初有复兴之象,即化为冷寂。
其后杨基、徐贲、张羽相继以仕宦得罪死。
吴中派进入衰落期,代表诗人为王行、韩奕、王宾、道衍。
王行洪武末牵入蓝玉党被杀。
道衍事燕王朱棣藩邸,力赞靖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已逸出吴中派。
韩奕、王宾高蹈于世。
吴中派后期诗歌活动真称得上寂寥了。
“吴中体”的形成发展与吴中派兴衰大抵一致,结合北郭结社活动,我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至正中到至正末,伴随结社之兴,“吴中体”形成,主于自适性情,“吴中四杰”、王彝、唐肃等人为代表人物。
第二时期洪武元年(1368)至十八年(1385)张羽卒世,吴中派入明遭际之变促生创作又一高峰,“吴中体”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三时期洪武十九年(1386)到永乐中,吴中派式微,诗风趋于“清雅”。
如徐泰《诗谈》所云,“至王行、王汝玉辈,渐入清雅,然不及高、杨耳”[4](P1205)。
(二)吴中派士人心态。
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体,研究中不应孤立地谈论风格,而应将士人心态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放在一起来探讨。
作为元末明初时代的产物,“吴中体”无疑是吴中派士人心态的外现。
吴中派兴衰与张士诚、朱元璋休戚相关,故探讨“吴中体”,有必要发覆吴中派与张、朱的关系及士人心态的变化。
北郭结社正值元末鸡鸣风雨之时,吴中派对蒙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不忘“中兴”。
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有平江。
就在北郭诸子自哀身陷乱离之际,时局发生变化。
第二年,士诚为摆脱与朱元璋争战不利,主动降元。
北郭诸子由此将士诚与朱元璋、陈友谅等割据群雄区别开来。
《明史》持朱明“正统”史观,鄙夷士诚,多有毁词。
事实上,他喜延揽人材,吴中相对承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士人还是充满吸引力的。
“东南名士多往依之”[4](P517),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真实。
“吴中四杰”被聘为记室①,北郭社一些人物正是为士诚所用始来吴中的。
高启对士诚及其属官饶介、蔡彦文的好感就体现了这种认同态度。
如《送蔡参军序》颂歌士诚“雄镇南藩,以戡乱为己任”,“方兴桓、文之业,内修外攘,以答天子之宠命”[1](P901-902)。
所谓认同,一方面是士诚降元,俨然“中兴”之望,异于乱世枭雄;另一方面是吴中远离战火,“一柝之警不起,民恬物熙,独保完实,斯其民亦幸矣”[1](P894-895)。
不过,他们与张氏政治集团的亲近关系建立在招安基础上,当这个平衡点被打破时,其间关系自然发生变化。
士诚叛元,诸子大失所望,纷纷遁隐。
吴中派期待元廷“中兴”,对张士诚治吴存有好感,对朱元璋、陈友谅持敌视态度。
朱元璋平吴后流放士诚旧属,对吴中派造成巨大冲击。
南北统一,朱明政权日益稳固,朱元璋在惩罚吴中文人后,有意放弃前嫌,显出君临天下的大度。
在此历史语境下,吴中派获得新生。
高启、王彝、谢徽、杜寅、高逊志参与修史,杨基、郑元、钱逵、余尧臣参与考礼。
都穆《都公谭纂》叹云:
“此可见吾吴文物之盛也。
”[5](卷10)吴中人文之盛固是事实,然吴中派能为朱明所用,更靠朱元璋态度转变。
洪武三年(1370),高启、谢徽并授翰林,未几朱元璋亲擢高启户部侍郎、谢徽吏部郎中。
对于这段特殊经历,高启以纪梦的形式作了记录,《志梦》并说:
“余欲书此以觉之,惧有诮夫诞也,乃私识之,且贻玄懿,聊相与自警焉。
”[1](P944-945)这类帝王宠遇与历史上君臣际会一样,大都出于偶然,而且也不会长久。
朱元璋推峻法重典于天下,肆行帝力而逆人情,高启、王彝竭力请归,已重忤帝意,未几死于魏观案。
不幸接踵降临,唐肃谪戍卒,杨基供役卒,徐贲下狱死,张羽投江死。
基于此,来看吴中派士人心态。
吴中派并非只是一群优游唱和、不关心世事的文人。
他们忧世愤时,内心涌动着热血。
杨基喜观古今事,探求成败得失,著《论鉴》十万余言。
高启、王行、宋克、道衍喜谈兵,豪侠自负。
高启在饶介幕中与倪雅论兵法“穷昼漏”,“自是每见,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1](P872)。
宋克击剑走马,思自树功业,学为兵法,将北走中原从诸豪杰计事,会道梗而归。
吴中派怀“中兴”之志,与张士诚政治集团合作,正是其用世心态的一种外现。
然所托非人,政治理想化为幻影。
失望之余,隐居避乱的想法然占据上风。
高启《野潜稿序》:
“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故君子不必于潜,亦不必于显,惟其时而已尔。
”[1](P881)隐去身与名以全其道,成为吴中派用世热情消退后的群体心态。
在朱元璋示以宠遇时,高启、谢徽、王彝等却未如其所说的士贵顺时那样立于庙堂,反而选择匿耀伏迹畎亩之间,岂非自相矛盾?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吴中派不慕荣利,遗世独立,元末如此,明初亦然。
如高启《槎轩记》自称天地间一槎,“亦安乎天而已矣”[1](P861)。
杨基《白发》吟唱“青山识我归来意,白发消人仕宦心”[6](P216)。
他们当然不是甘为士诚所用,而不甘仕朱明。
即使在元末,与士诚的关系也是很松散的,保持了独立自由人格。
诗人向慕人生适意,任情自然。
如王行《适轩记》说“适”之为道,不在于故求淡泊,而在与自然浑为一体[2](卷12)。
在现实中,尤其是社会大动荡之际,寻求自适还需要远离喧嚣,亲近自然。
如张羽以“静者居”名室,高启《静者居记》:
“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
”[1](P856)
二、诗学取向
吴中人文兴盛,渊源流长。
吴中派与越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体现了元末明初诗歌发展的地域化倾向。
“吴中体”形成于吴中,传承吴中风雅,渊源有自。
明人莫如忠《吴淞诗委序》称陆机、陆云、顾野王、顾况、张翰肇开吴中风雅,迄于明,诗道益广,“高、杨、张、徐四子崛起,后先其所撰造,几贞观、开元之逸响”[7](P2766)。
清初朱彝尊《张君诗序》复述及晋宋“江南音”与宋室南渡之功,以为“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8](P471)。
这是后人的说法,明初诗人谈及吴中诗歌渊源有所不同。
王?
《缶鸣集序》尤推重陆龟蒙、范成大,论元代吴中诗仅推陈谦一人。
王行《送陈士开序》指出元代人文衰落,吴中情况还算好一些,彬彬之风犹不尽废[2](卷6)。
所论各具识见。
从晚唐陆龟蒙到宋人范成大,再到元末前有陈谦、顾瑛,继有吴中派振起,风雅不绝。
昆山顾瑛主盟玉山雅集,鼓吹风雅,对北郭社多有启迪之功。
谈及“吴中体”近源,还有两位元末诗坛领袖值得注意:
一是无锡倪瓒,淡泊名利,以诗、书、画游戏于世,与“吴中四杰”为忘年友;二是会稽杨维桢,侨寓云间,往来吴下,诗号“铁崖体”,吴中诗人从游者甚众。
“吴中体”与元明诸体诗学取向相比,有何独特处呢?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吴中派反思近百年来元人多作七言近体之习,提倡复古,兼采汉、魏、晋、唐。
标帜复古是元末诗坛新潮流,越中派声气最盛,其次推吴中派,其间旨趣不尽相同。
吴中派力避近人专好七言近体之习。
王行《柔立斋集序》以为元人此习始于元好问《唐诗鼓吹》专取七律,赵孟?
\、虞集、揭?
菟勾罅ν旗敝?
,转相染习,诗道浸衰。
由此他提出追宗溯远,继承古诗传统,称道朱熹教人“须先学韦、柳”,谓由此上溯于《诗》乃康衢大道[2](卷5)。
谢徽为高启作《凤台集序》,叹说:
“四百年无此作矣!
”又说他厌近世之体,取师唐人,“于是古之习俗一变”[9](卷5)。
越中派以《诗》为本,不以宗唐为法,吴中派则推尊唐人。
唐肃《读唐人诗作》:
“一过抄诗百过吟,分明窥见古人心”,“英魂地下如堪酹,千载怜予属赏音。
”[10](P178)道衍《馆中公暇,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子厚诗四首》其一:
“挥洒自为乐,吟咏得真情。
”其二:
“闲澹意有余,鲍谢焉足拟。
”其三:
“古淡岂易学,五字真五师。
”其四:
“寓意一于诗,出语何清妍。
”[11](P559)吴中派诗人以唐人千载知音自许,学唐取法不一,在推重韦、柳上则趋于一致。
洪武初,徐贲编次高启诗成集,王彝《高季迪诗集序》指出高启力矫元人“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12](卷2)。
既肯定“情与诗一也”,又力辩“情”必有“节”始存古作者之意,盖鄙视蒙元不知“性情”、“礼义”,诗风因世而变,以至恶乱。
“情”、“节”合一说有其具体历史与诗歌背景,应该说,吴中派更重尚情自然。
如高启《缶鸣集序》称《国风》是真情自得之作[1](P906)。
王行《唐律诗选序》谓《诗》未有一定之律,“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盖几希矣”,惟有复归“拙而浑朴”,方不失自然之意[2](卷6)。
三、诗体特征
“吴中体”总体上呈现出深情自然、风神隽逸的风貌。
细绎其诗体特征,主要有五:
首先,崇尚才情,风华颖迈,隽逸清丽,甚而不避?
艳。
“吴中四杰”是“吴中体”的代表,高启诗尤为典范。
顾起纶《国雅品》说他“首倡明初之音”,四杰并称“豪华”,“惟季迪为最”。
如《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辞气淋漓,《李夫人歌》、《王明君》婉转情深,《吴趋行》、《惜花叹》隽丽多姿,《石射堋》、《池上雁》个性张扬。
就风华而论,实超出刘基、袁凯诸家。
杨基诗是“吴中体”又一典范,与高启相近,不过稍偏于?
华。
除从初唐四杰、韦应物那里汲取养料外,他还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五首风格?
丽,音调清婉。
诗序:
“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
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
”[6](P253)“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多有穿凿之嫌。
他之所以认定《无题》大有深义,盖不仅崇尚?
丽、清婉,而且注重寄托。
《眉庵集》看花诗多达数百首,如《约范园看杏花》、《九日袁赞府宅赏菊》、《宜秋轩桂》诸篇,结辞高华,隽永逸宕,浑然无迹,如江朝宗《眉庵集序》所评“?
丽纤蔚”,殊有唐人风味。
张羽、徐贲、唐肃等大抵不离于隽逸流丽。
张羽诗情喻幽深,清丽自然,偏于娴雅融润,顾起纶《国雅品》评曰“颇似钱、郎”。
徐贲诗气韵纵横,体裁精密,偏于风韵凄朗,《静志居诗话》卷三评曰“颇有类皮、陆者。
”唐肃更擅长简质华澹一路。
其次,不忘世情,感时伤事,情致绵丽,或识见雄特,诗以存史。
以绵丽之调吐写感时伤事之意是“吴中体”的擅长。
徐贲诗“如楚客丛兰,湘君芳杜,每多惆怅”[4](P1474)。
如《兵后过?
G亭山》:
“?
G亭西去远,一过一凄然。
雁宿芦中月,人归草际烟。
渔家多近水,戎垒半侵田。
尚喜余民在,停舟问昔年。
”[13](P191)写乱后悲凉之情,读之惊心。
《咏三虫》咏蝶云:
“花开心事已蹉跎,每怨春多恨转多。
赖有黄花相慰藉,不知风雨又如何。
”[13](P259)神韵清泠,哀怨动人。
徐伯龄评曰:
“其感慨之意见于言外,抑生值元末乱离之际,激愤而然耶!
”[14](卷8)又如《听笛》、《空木》、《次韵看花》等绝句,风神凄朗,弦外之音是无尽的怨意。
道衍诗,高启《独庵集序》称殊异僧家之流。
道衍确实无意说空说幻,其人介于释、儒之间,身在空门,心却逸出方外,不事“枯槁山林”之学,亦不作“枯槁之诗”。
如《废苑芍药》:
“阑绕荒烟砌满苔,花容仍拟旧时开。
白头邻叟贫犹在,记得金盘托荐来。
”[11](P603)寄写盛衰,感慨独深。
《废宅行》将历史兴废浓缩“废宅”一景,《乱后入城有感》历述平吴后见闻,一唱三叹,余哀不尽。
张羽《听老者理琵琶》属于吴中派擅长的借歌伎、梨园以见世变的题目,诗云:
“老来弦索久相违,心事虽存指力微。
莫更重弹《白翎雀》,如今座上北人稀。
”[15](P311)《白翎雀》俗称《海青打鹅》,元伶官石德闾制曲,音调悲怨,始虽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
高启、杨基未有咏作,然高启《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杨基《赠京妓宜时秀》正可与相对观,俱是在绵丽中传写了深沉的感时伤事之意。
吴中派生逢末造,经历朝代鼎革,“吴中体”生动纪录了一段真实历史与士人心灵史。
高启《送陈秀州》、《送流人》、《答余新郑》、《赠杨荥阳》,与前代的元好问、后来的吴伟业各领一代风骚。
洪武初赋咏吴中山水,“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废兴之故”,“存劝戒而考得失”[1](P907),有《姑苏杂咏》一编。
先是南京修史,与宋濂等商讨宋元兴废,《姑苏杂咏》也是他治史的余绪。
韩奕隐于医,徜徉世外,然非能忘世。
《题戏婴图》借题画写世乱:
“棕榈阴转画栏斜,两两斑衣戏落花。
借问江南二三月,年来此景有谁家?
”绝句极含蓄,但诗人生活时代的特征太明显了,所以我们不难体味所抒写的沉痛之感。
《送戍人二首》更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二云:
“全家万里戍,念汝特还乡。
雨露春时怆,山川客路长。
旧坊邻姓改,先垄墓田荒。
又迫公家限,含凄理去装。
”纪写朱元璋平吴后吴中士子谪戍异乡的悲惨历史,无疑是诗史之作。
再次,遗世独立,张扬个性,自适性情,清新自好。
吴中派诗人有志用世,但最大的理想还是作“专业”的诗人。
高启以为古人不专意为诗,后世始有专以诗名家者,《缶鸣集序》自称一事于此,疲殚心神,或视为废事丧志,然独念“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遂为之不置。
早在写此序前,他就发表了要作“专业”诗人的宣言,《青丘子歌》: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1](P433-434)杨基遁隐遗世,自号眉庵,亦驰聘于诗歌疆域。
诗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为乱世士人提供精神依托与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北郭社即构建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与诗人“选佛场”。
诸子对诗歌的酷嗜,即使在炮火纷飞中也不肯减去几分,“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12](卷2《衍师文稿序》)。
沉溺于诗不能自拔,自非玩物丧志。
以诗作为人生的存在,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
吴中派诗人追求自适,性情嗜好又略有不同。
高启、杨基喜好看花,张羽则酷爱听雨,《静居集》仅以雨为题者就有《雨中试笔》、《大雨山中作》、《雨夜》、《雨后望西山》、《雨夜偶成》、《雨中言怀》等十余篇,将“静者”志趣寄托一个“雨”字。
如《雨夜》:
“寝阁去门远,春雨荒园夕。
谁谓在人境,宛似空山客。
禽归暗竹喧,风断疏钟寂。
戚戚寡欢?
?
,良宵端可惜。
”[15](P43)雨中寂坐,感受天地自然,虽谓人境,宛若空山,不必饮酒登眺,已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愉悦,李白“相看两不厌”的超然。
王夫之《明诗评选》卷四评云:
“‘寝阁去门远’,何关雨夜,正得居雨者之神。
”吴中派诗人多擅长绘事,王行喜泼墨成山水,时称“王泼墨”,题画诗亦重意,不较笔墨工拙。
如《题听松卷》:
“长松知几树,树树着清风”,“那复钧天梦,知音自不穷。
”钧天一梦非所好,诗人深恋的乃是荡涤心胸的长松清风。
又如绝句《松云二士图》、《题画八首》、《秋景小幅》、《高林雪竹》,林泉逸兴,流于笔端,冲澹幽婉,无一丝尘俗气。
复次,追求独造,富有妙思,擅于咏物。
“吴中体”不故求新奇,然能出人意表。
如杨基《登宋宫故基》“尽道河边金线柳,腰肢犹似李师师”[6](P327),看似轻浮,实是细切传写历史沧桑之感。
徐贲《折杨柳》:
“人言折柳愁,我言折柳好。
倘向柳边行,识君去时道。
”[13](P81)轻俊可爱。
咏物是“吴中体”又一擅扬,四杰咏物堪称一奇。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以为高启《梅花》、杨基《芳草》及袁凯《白燕》俱一时少见之作。
道衍也是咏物的妙手,如《秋蝶》绝句:
“粉态凋残抱恨长,此心应是怯凄凉。
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
”[11](P601)婉曲动人,情意甚妙。
这类作品出自一个僧人之手,着实令人侧目。
最后,不满于元人专好近体七言,故诸体兼备,臻于“大全”。
高启《独庵集序》称诗之要曰“格”、“意”、“趣”,“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
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如是而诗之道备矣”[1](P866)。
所作或豪俊清丽,或冲淡幽婉,皆能造佳境。
《静志居诗话》:
“季迪之才,始于兼,故其体备。
”吴中派工于近体不必论,古体、乐府也取得很高成就。
如高启古体自然浑成,乐府不拘旧题,写出许多新意。
钱谦益推崇李东阳乐府,李攀龙盛赞王世贞乐府,李、王成就毕竟比高启差了一些。
张羽五言古《杂言》、《戴山石上听松风偶咏》咏怀写心,卓然名家;七言古《听蝉曲》、《温泉宫行》借初唐四杰华美“外衣”抒写历史感受,多有常人不能道之意;乐府《驿船谣》、《踏水车谣》摭取亲历见闻成篇,刻画下层民众悲惨生活,质朴感人。
这类作品情质相生,如《艺苑卮言》卷五所评,“如乡士女,有质有情”。
徐贲、杨基、唐肃、道衍、韩奕等亦是诸体兼擅,诗才殊众。
这在明诗史上尚是不多见的。
当然,作为吴中派士人心态、性情旨趣、诗学追求的体现,“吴中体”自非一成不变。
“吴中体”前期自适性情,中期多凄凉之音,后期归于“清雅”。
其中易代所造成的变化最引人注目:
一方面,从放拓到深稳。
吴中派元末诗个性张扬,难以束湿,入明后深稳之作渐多。
如高启《禁中雪》、《圣寿节早朝》等颂圣之作,风格稳重,寄兴深微。
徐贲巡按广东,《登广州城楼》:
“清时不用频兴感,万里惟存向阙心。
”[13](P230)诗人对时政、宦旅感受如何?
“清时不用频兴感”耐人寻味,正可见“兴感”亦自不少。
总体来看,吴中派入明诗收敛了不少放拓之气。
另一方面,从显露到含蓄。
吴中派元末诗放笔吐写哀怨,笔锋犀利。
入明后趋于含蓄隐曲,谈及政治,笔调更是含婉,高启《早至阙下候朝》写洪武初丞相炙手可热即是。
诗人遭际丧乱,及天下太平,又要面临残酷的杀戮迫害。
张羽《悼高青丘季迪》其一云:
“灯前把卷泪双垂,妻子惊看那得知。
江上故人身已没,箧中寻得寄来诗。
”[15](P308)泣咽悲歌,又岂能不含蓄?
后来张羽也未能逃脱明初文人之厄。
四杰及王彝等罹难后,“吴中体”归于“清雅”,也是一种极自然的变化。
概而言之,“吴中体”不屑苦吟,高华清丽,寄兴幽远,既不同于“元遗山体”之雄健苍深,“铁崖体”之艳宕新奇,也异于“李何体”之高古雄放、“中郎体”之轻灵隽永、“锺谭体”之幽深孤峭。
至于弊端,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流于“纤巧”,此恃才情太过使然。
但“纤巧”之作如高启《梅花》、杨基《春草》、徐贲《折杨柳》,含蓄而有情韵,轻俊而有思致,故又不当尽黜之。
四、诗史意义
吴中派为元明诗坛重派,《明史?
文苑传》总论所举明初以诗著者“高、杨、张、徐、刘基、袁凯”六家,“吴中四杰”就占据四席之位。
“吴中体”独标一格,不仅推动一代诗歌的创新与繁荣,也对明诗发展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宗唐、宗宋是关系元明诗史演变的大问题。
吴中派不满于元人专主七言近体,兼采众长,尤多法乳唐人。
尽管“吴中体”借鉴初唐四杰,推崇韦、柳及李商隐,不以李、杜为宗,但对明诗宗唐风气的形成仍有其特定的意义。
与此同时,“吴中体”的复古倾向也开启明诗复古端绪。
后人论明诗首重复古,论复古首推七子派。
这大抵是不错的,却不免忽视一点,即在明诗史上复古是前后一贯的。
吴中、越中派为复古初兴,前、后七子派近百年复古为再兴,复社、几社为三兴。
尽管三次复古的理论和旨趣各不尽同,但其间因承转变的关系不容轻视。
吴中派远承陆龟蒙、范成大清远、流丽之风,创立“吴中体”,不仅标志吴中诗歌真正黄金时代的到来,而且奠定了明清“吴音”风华整丽、风神俊朗的基调。
后世吴中诗人大都以“吴音”为尚,澹宕拔俗,风流俊赏。
如“吴中四才子”颇效法“吴中四杰”。
钱谦益《孙子长诗引》:
“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
士多翕清?
南剩?
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
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
徐昌谷,江左之逸才也。
一见李献吉,阳浮慕之,几欲北面,至今为诸伧口实。
皇甫子循,歌诗婉丽,?
?
年盛称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于其声光气焰耳。
”[16](P1086)由于不满吴中诗人“屈折”七子派声光气焰,指责“好随俗尚同”。
事实上,明代吴中诗人传习“吴音”不绝,已是诗坛一大景观了。
而且即使吴中诗人之变,亦不离于“吴音”。
徐祯卿受李梦阳影响,悔其少作,然所操仍是“吴音”。
王世贞为李攀龙鼓动,转事高歌朗调,中岁后幡然有悟,复返“吴音”。
后七子派后期复古浸润“吴音”,与此前颇有不同,皆可见“吴中体”的深远影响。
此外,“吴中体”崇尚才情风流与独立于世、适意自放,也为后世诗人树立典范。
“吴中四才子”适意人生,即是藻贯了这种诗歌精神。
看花诗为“吴中体”一大宗,明中后叶盛行于江南的落花咏,即是近承杨基、高启诸子咏花之风。
参考文献
[1]高启.凫藻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王行.半轩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丘?
F.重编琼台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Z].济南:
齐鲁书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