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论摄影摄影的社会定义.docx
《布尔迪厄论摄影摄影的社会定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布尔迪厄论摄影摄影的社会定义.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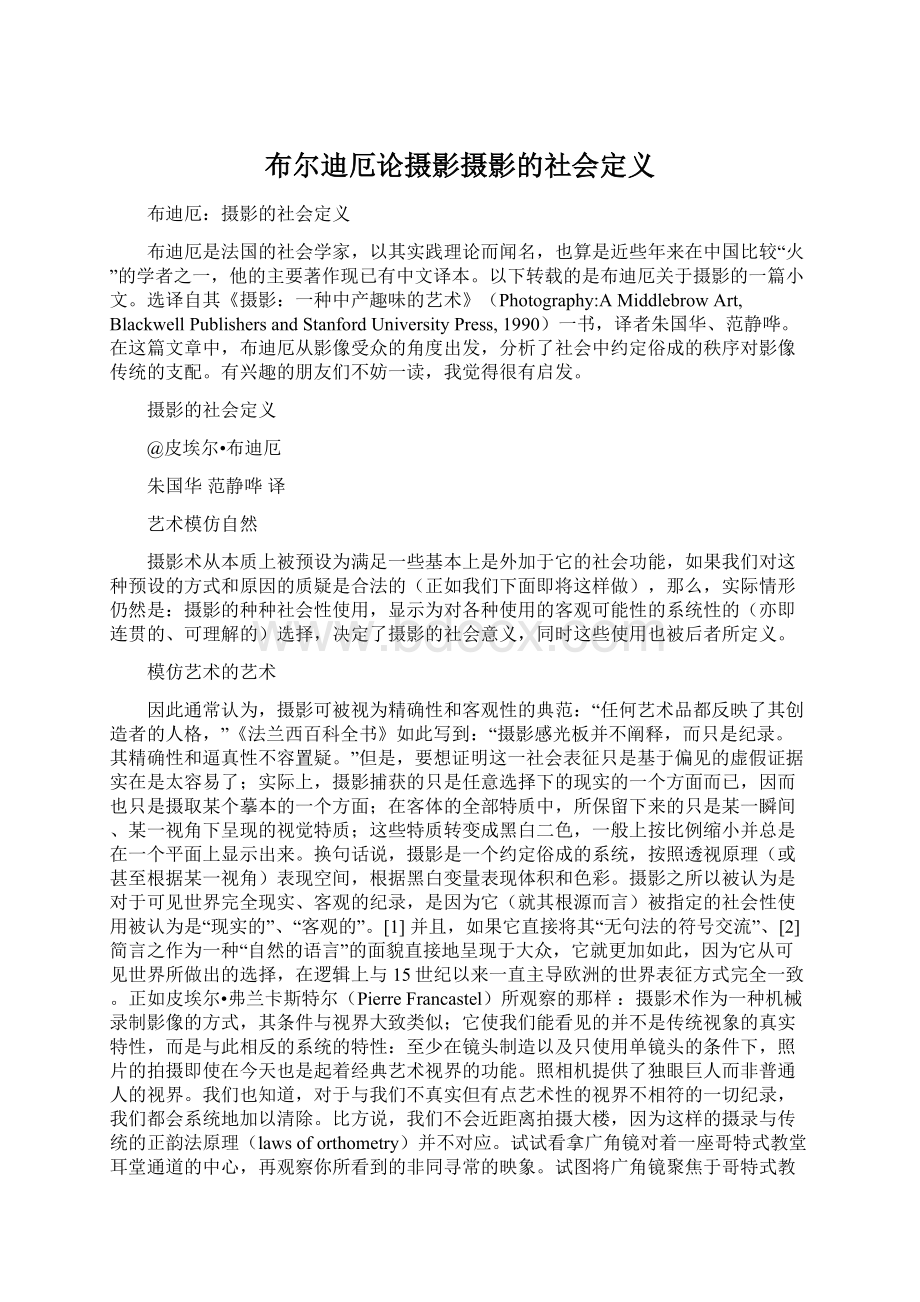
布尔迪厄论摄影摄影的社会定义
布迪厄:
摄影的社会定义
布迪厄是法国的社会学家,以其实践理论而闻名,也算是近些年来在中国比较“火”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著作现已有中文译本。
以下转载的是布迪厄关于摄影的一篇小文。
选译自其《摄影:
一种中产趣味的艺术》(Photography:
AMiddlebrowArt,BlackwellPublishersan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一书,译者朱国华、范静哗。
在这篇文章中,布迪厄从影像受众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社会中约定俗成的秩序对影像传统的支配。
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我觉得很有启发。
摄影的社会定义
@皮埃尔•布迪厄
朱国华范静哗译
艺术模仿自然
摄影术从本质上被预设为满足一些基本上是外加于它的社会功能,如果我们对这种预设的方式和原因的质疑是合法的(正如我们下面即将这样做),那么,实际情形仍然是:
摄影的种种社会性使用,显示为对各种使用的客观可能性的系统性的(亦即连贯的、可理解的)选择,决定了摄影的社会意义,同时这些使用也被后者所定义。
模仿艺术的艺术
因此通常认为,摄影可被视为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典范:
“任何艺术品都反映了其创造者的人格,”《法兰西百科全书》如此写到:
“摄影感光板并不阐释,而只是纪录。
其精确性和逼真性不容置疑。
”但是,要想证明这一社会表征只是基于偏见的虚假证据实在是太容易了;实际上,摄影捕获的只是任意选择下的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因而也只是摄取某个摹本的一个方面;在客体的全部特质中,所保留下来的只是某一瞬间、某一视角下呈现的视觉特质;这些特质转变成黑白二色,一般上按比例缩小并总是在一个平面上显示出来。
换句话说,摄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系统,按照透视原理(或甚至根据某一视角)表现空间,根据黑白变量表现体积和色彩。
摄影之所以被认为是对于可见世界完全现实、客观的纪录,是因为它(就其根源而言)被指定的社会性使用被认为是“现实的”、“客观的”。
[1]并且,如果它直接将其“无句法的符号交流”、[2]简言之作为一种“自然的语言”的面貌直接地呈现于大众,它就更加如此,因为它从可见世界所做出的选择,在逻辑上与15世纪以来一直主导欧洲的世界表征方式完全一致。
正如皮埃尔•弗兰卡斯特尔(PierreFrancastel)所观察的那样:
摄影术作为一种机械录制影像的方式,其条件与视界大致类似;它使我们能看见的并不是传统视象的真实特性,而是与此相反的系统的特性:
至少在镜头制造以及只使用单镜头的条件下,照片的拍摄即使在今天也是起着经典艺术视界的功能。
照相机提供了独眼巨人而非普通人的视界。
我们也知道,对于与我们不真实但有点艺术性的视界不相符的一切纪录,我们都会系统地加以清除。
比方说,我们不会近距离拍摄大楼,因为这样的摄录与传统的正韵法原理(lawsoforthometry)并不对应。
试试看拿广角镜对着一座哥特式教堂耳堂通道的中心,再观察你所看到的非同寻常的映象。
试图将广角镜聚焦于哥特式教堂交叉的左右两翼的中心,就会注视你将会获得的特别档案。
你将会看到,所谓的“常规视角”只是选择的视角,世界的面貌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
[3]
普鲁斯特对于摄影术令人窘迫的力量所做的解说非常美丽,这是日常实践被剥夺的力量:
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
我觉得,照相也和接吻一样,能使一个我们认为具有确定外表的东西变化出千姿百态,而每一个新姿态都和原来的姿态一样合适,因为它们各有一个同样是合理的透视角度。
[4]
普鲁斯特在另一个地方则描述了那些“自然风景和城镇的精彩照片”,它们可以提供一个熟悉的事物所呈现的奇特形象,这个形象与我们司空见惯的不同,奇特然而又是真实的,因此对我们来说倍加引人入胜,因为这个形象使我们惊异,使我们走出了常规,同时又通过唤起我们一种印象使我们回归到自己。
例如,这些“精采”摄影中的某一帧,体现了远景的一个规律,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城市中司空见惯的某一大教堂,却从精心选择的一个点上来拍摄。
从那个点上看,它似乎比房屋高出三十倍,而且与江边成突角,实际它与江边距离很远。
(译按:
上一段与此段均选自《追忆似水年华》中文版相关段落)[5]
在这些“神奇的”照片与普通照片之间是否差距巨大,正如透视作为一门现实科学与作为一种“幻觉”技术之间距离巨大?
[6]普通的摄影者根据他或者她所看见的样子摄取世界,也就是说,所依据的观看世界的逻辑从过去的艺术借用其典范与范畴。
[7]当图片利用真实技术的可能性,只要稍微摆脱普通摄影术和视界的学院气,就会引起惊奇。
这是因为,可见的总只能是可读的,总体社会环境中的主体总是诉诸于某些读解系统,这些读解系统中最常见的是一些支配大众摄影的、关于如何复制真实现实的规则系统;面对最特别的图片,摄影爱好者所解码的形式总是属于某一摄影传统的,例如对于质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如果疏忽一些典范的美学规范,如缺乏一个能与形式发生有意义连接的前景或令人能注意到的背景(例如棕榈树表现异国情调),那么,即使不招致完全彻底的拒绝也会阻抑人们的理解和欣赏。
但是大众摄影的整个悖论是在其时间维度中显示出来的。
作为对于可见世界的直接切入,摄影术所提供的手段将日常感知中紧凑的立体现实消解成无穷无尽稍纵即逝的平面轮廓,像梦境中的意象那样,为的是捕捉诸种事物在相互位置中绝对的独一无二的瞬间,为的是把握(如瓦尔特•本雅明所示)感知世界那些因为稍纵即逝而无法感知的方面,为的是捕捉此在的荒诞之中的人性姿态,这种此在是由“盐柱”所构成的(译按:
盐柱的典故源于《圣经》,罗德之妻不听劝告,回头看了一眼上帝所毁灭的城市,当下自己即化为盐柱)。
事实上,与所有人的期待刚好相反,日常实践似乎决心要剥夺摄影困扰人的力量,而远非将摄影的特殊使命视为捕捉关键瞬间——在这些瞬间中,可靠的世界丧失了平衡;大众摄影使现实暂时化,因而消除了消解现实的偶然性或任何表象。
[8]只有捕捉到从时间流中分裂出的庄严瞬间,只有将静止不动的人捕捉到永恒的平面中,才会失去侵蚀的力量;当一个行动呈现为一种形态时,它便总是将一个本质的、“不动的、”超越时间的运动具体化,将一个姿势的平衡或优美具体化成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一样永恒;挽手站立的夫妇所表现的意义,如果换一个姿势,则与梵蒂冈中卡托和鲍西亚携手的意义相同。
在日常美学的语言中,正平面描绘意味着永恒(与景深相对),时间性因正平面描绘而被重新引入,而平面意味着存在或本质,亦即不受时间影响。
[9]于是,农民依照拜占庭镶嵌画人物排列的布置和姿态,摆姿势照结婚照,也就摆脱了摄影将事物暂时化而使它们去现实化的那种了力量。
可见世界约定俗成的秩序因为支配着整个图像传统,并进而支配了对世界的整个感知,所以它会因为将自身铭刻在自然性的全部表象中而吊诡地终结。
日常实践并没有动用摄影术的全部可能性以颠倒这种秩序,而是使摄影术的选择服从于对世界的传统视界的范畴和典范。
因此,摄影能够显示为对最忠实于这个传统视界中的世界的纪录,亦即显示为最客观的纪录,也就不足为怪了。
[10]换句话说,因为摄影的社会性使用是从摄影的各种使用可能的场域中作出的一种选择,而这些使用可能的结构是按组织世界的日常视界的范畴而建立的,所以摄影影像可被视为是对现实的精确、客观的再现。
假如“自然模仿艺术”这句话为真,那么自然而然地,对艺术的模仿应该显示为对自然的最为自然的模仿。
在较深的层面上,只有以天真现实主义的名义,人们才能将对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再现视为现实主义的,这种再现之所以具有客观的表象并非因为与事物的现实本身的一致(因为这种一致只能通过社会条件制约下的感知形式来传达),而是因为它与界定其社会性使用的内在语法的规则相一致,符合对于世界的客观视界的社会定义。
当社会为摄影提供了现实主义的担保的同时,它只不过是在一种同义反复的确定性中确认着自身,也就是,当反映真实世界的某个影像忠实于它对客观性的表征时,它就真的客观了。
[11]
粗鄙的趣味
在普通人看来,摄影术是对真实世界最完美忠实的再现,究其原因,产生摄影的技术客体的社会形象与摄影的社会性使用无疑是同等的。
实际上“机械之眼”的完善就是根据对客观性和美学完美的通俗表征而实现的,这种表征的界定标准则是相似性和易读解性;正如西蒙顿(M.GilbertSimondon)所述,仪器的崇拜者和毁谤者往往都承认,一个仪器的复杂程度与其自动化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12]然而,出于同样的理由,因为艺术创造被通俗地再现为辛苦劳作,摄影行为无处不与这种通俗观念相抵触。
没有艺术家的艺术还是一种艺术吗?
无庸讳言,摄影并未实现工人阶级的艺术理念,亦即其模仿理念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像现实主义绘画那样对再现进行生产。
许多受调查者感到并表达出了他们眼中使摄影行为与绘画行为分开的差异;既然一个人所要做的一切只是简单地揿一下按钮,便能释放出作为照相机本质特征的客观智能,那么似乎并非有什么照片是不可拍摄的,或者说甚至没有哪张照片不是已经以一种虚拟状态存在着;因为这一事实,人们便希望照片通过被摄物体、通过拍摄时所做的选择、甚至在照片的最终用途中获得其正当性,这种用途会驱除人们下面这些话所反映出的认为拍照只是为了拍照,是无用的、不正当的、资产阶级的:
“这是浪费胶卷”或者“你得有胶卷来浪费啊”;“我敢发誓,有的人真的不知道他们的时间该怎么用”;“你得有空余时间才能做那种事;”“那是资产阶级的摄影”。
与此相反,静物即使并不常见,也是画家易于获得认可的主题,因为对于现实简单、成功的模仿预示着艺术的难度,于是也验证着技艺的精湛。
这导致了对机械再生产的态度上的某些矛盾。
机械再生产借助其毁灭性的努力,冒险剥夺着作品的价值;而价值正是人们力图授予作品的东西,因为它符合一个完整的艺术品的标准。
这一矛盾越发尖锐突出,因为艺术品,尤其在未被圣化之前,总是引起被蒙骗的恐惧。
免遭蒙骗的最可靠保证是艺术家的诚挚性,这种诚挚性是根据艺术品所需的付出、牺牲来衡量的。
摄影术置身于美术系统内部,其含混的处境除了导向其它矛盾之外,还可以导致作品的价值与生产该作品的行为的价值之间的矛盾,作品价值所实现的美学理想仍然是最为普及的。
但是这一矛盾只是在关于摄影的艺术价值的(常常是故弄玄虚、惺惺作态的)问题中才会变得明显。
这个矛盾既没有促使工人阶级改变附加于照片影像上面的东西,也没有促使人们关注一个萦回在美学家脑际的问题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
由于摄影艺术受制于机械,它是否容许对(哪怕是丑的、无意义的)对象加以变形,而我们习惯上承认变形才是艺术创造?
对于通俗自然主义而言,美的照片只不过是一件美的事物的照片,或者更罕见一点,是一件美的事物的美的照片,那么生产出最忠实的复制品的技术不是最有可能满足通俗自然主义的期待吗?
“现在这个不错,几乎是匀称的了。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
一个美女在照片上看起来总是很爽心悦目。
”于是,这位巴黎工人的话回响着诡辩家希皮亚斯那朴实言辞的余音:
“我要告诉他美是什么,而且不太会遭到他的反驳!
说实话,苏格拉底,事实是,一个美丽的女人,那就是美之所在。
”毫无疑问,摄影(尤其是彩色摄影)彻底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美学期待。
但是我们是否必须只要说明通俗照片是某种美学意图或理念的实现,或者,为了解释得充分,只要提到技术的障碍或限制就足够了?
确实,大多数临时摄影者只能使用功能非常有限的仪器;同样,通过与销售人员或其他业余爱好者进行交流而得来的通俗技能的基本原则,明显是由种种禁令所构成,如不要移动、不要斜拿着相机、不要对着光源或者在光线条件不好的情形下拍照;这些禁令能被一般经验所认证,是因为所使用的相机质量糟糕以及技术能力的缺乏。
但是,这些限制不是也很明显地包含了某种必须承认的美学吗?
违背这些规定不就会出现某种失败吗?
一种不同的美学可能会故意拍出模糊不清、焦距不准的照片,而通俗美学则视之为拙劣的失败的作品加以拒绝。
即使在通俗摄影中(如原始艺术便一贯如此),关于技术限制的解释之所以乍一看还差强人意,那主要是因为技术要求所划定的场域,亦即从技术角度讲所能拍摄的范围,大于社会要求所划定的领域,亦即必须拍摄的对象的范围。
在此情况下,一幅相片的技术及美学品质主要靠其社会功能界定,这种品质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其自身则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这样,一切事物的发生都好像说明摄影术是一种未明言的美学的表现,这种美学运用一种非常严格的方法体系,而且在某种类型的图像中(因为它自身的本质)在其客观性未被感知的情形下产生了客观性。
通俗“美学”在每个方面都与纯美学相对立,表现在照片以及传递在照片上的判断时,从赋予摄影的社会功能方面以及摄影总是被赋予一种社会功能这一事实上,通俗美学也遵循这一逻辑。
在传统形式上,这种美学严格地将美学与社会标准相认同,或者也许可以严格的说,只承认得体性、适宜性的规范,绝不排斥美的经验和表现;如果制造一种姿态或者客体的方式能够最严格的遵守绝大多数传统规范,那么,这种制作便会给作者提供一种可能性,即或多或少微妙的和成功的正当理由的可能性,这些正当理由可能会得到赞赏和赏识。
由于它预设了一种规范系统的独特性和一致性,这样的美学实现得最好的地方是在乡村社群。
例如,照片所摄取的姿势,其意义只有联系着整个符号系统中该姿势的位置才能得以理解,对农民而言,该符号系统规定了他的举止行为是否符合他与别人的关系。
照片常常将人脸向正前方,放在照片中心,在适度的距离以威严的姿势、纹丝不动地站立着。
实际上,摆姿势便是让自己拍出的姿势不自然,或者说并不是为了拍出自然的姿势来。
出于同样的意图,人们在乎自己的姿势是否端正、穿上最好的衣服,拒绝以平常面貌出现在日常工作中被抓拍。
摆姿态意味着尊重自己以及要求得到尊重。
当我们试图劝说摄影对象保持自然的姿态时,他们变得忸怩不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值得被拍摄,他们会说自己“不象样子”,我们所能希望的最佳结果就是模拟的自然,戏剧性的姿态。
[13]摄影者从生活中拍摄照片的行为似乎是荒谬可疑的。
于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些照片最终下落是什么?
巴黎?
它们起码会上电影吧?
因为你只会在电影院里才见到这种东西!
他们什么都放!
”在农民眼里,城市居住者服从一种知觉上的“啥事都成的习气”;这样的事情对他不大好理解,因为他所想到的潜在的摄影哲学,其依据是只有某些对象在某些场合才值得拍摄。
[14]我们必须避免直接将城市居住者对于“自然的”趣味与农民对于神圣的趣味对立起来;倘若这样做实际上就意味着忽视这样的事实:
向摆脱了社会习俗的美学所做的让步常常是似是而非的。
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度假造成了许多以随意态度为标记的照片的产生,这种态度是度假所鼓励的,也是对度假的表现。
实际上,“舞台”常常是预先就搭好了,如果像画家一样,许多业余摄影家强使他们的模特儿摆出沉静而做作的姿势姿态,这是因为,无论在何场合,“自然”总是一个文化理念,在能捕捉到之前,必须先创造它。
即便是抓拍的照片,对于自然之物的美学的成就,也遵守文化模式:
其理念仍然是“自然地”出现,无论是想露面或者必须露面。
在大多数集体照中,人们总被显示为紧挨在一起(通常处在照片的中心),时常勾肩搭背。
人们的眼睛齐聚于照相机,以至于整幅照片指向其自身的不存在的中心。
夫妇照片中,夫妻以完全传统的姿势,手搂着对方的腰站着。
在照相机前必须保持的行为规范,有时变得很明显,无论是以消极还是积极的方式。
谁要是在一个庄重场合(比如婚礼)的群体中摆出不适当的姿势,或者不注意看镜头或者不摆好姿势,就会引起不满。
视线的汇合和每个人的安排客观上证明了群体的内聚力。
这种感情的表达可以在全家福照片中看到,这样的照片被送给不同的受试者进行评判:
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人都赞成一种自然而庄重的姿势;如果照片中的人站得笔直的、纹丝不动、并且庄重,这些照片则比那些被认为是“从生活中摄取的”更受赞赏。
“在这张里,他们很自豪,他们走得出去……”“这张照片里,他们没有向前看,心不在焉。
这孩子倚着他爸爸。
”另外一张则引起“僵硬的”姿势和“庄重的”姿势的区别,前者会招致大笑,而后者则得到赞许。
另一方面,如果照片中的家庭成员似乎因为被彼此搞得分神,这张照片则会受到批评,这是因为从中读解出了家庭群体凝聚力的脆弱,而当拍摄这样的群体时要捕捉的正是这个。
人们通常总是在照片中寻求什么,也就是照片能够令人想起某些熟悉的面孔、值得记忆的地方或时刻,当人们不可能要求这些陌生人的照片也应提供这些东西时,便要求它们至少应该成为一种社会角色的表征;这种要求不必针对某个人自己的照片,因为这种照片自动地实现了这种要求。
“你看,这可是一个家庭。
我不喜欢这个当妈的,她看起来心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张她才有点当妈的样子。
不过都差不多!
她真是个好笑的母亲,吊着膀子……这张照片糟糕透顶。
啊!
这张不错,孩子都彬彬有礼,母亲让父亲晚着手臂。
这是张家庭留念照。
”当我们讨论个人照的时候,我们知道母亲是母亲,父亲是父亲;在匿名的照片中,不同角色的功能必须被清楚地符号化。
母亲、父亲还是未婚夫妻,照片必须显示出他们的身份。
对于正平面描绘的自发欲望确实有可能联系着最深层的文化价值。
荣誉的要求使人们拍照时摆姿势,正如一个人在他所尊重或期望得到尊重的人面前站正,脸向前看,抬头站直。
[15]在这样一个抬升荣誉、尊严和可敬的社会里,在一个任何时候都逃不脱别人关注目光的封闭世界中,给别人呈现自己最可敬、最尊严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近乎立正姿态的不自然的僵硬姿势似乎是这一无意识意图的表现。
坐着的人向观看的人传达的行为,就约定俗成的规则而言,是威严的、礼貌的,并要求观看者遵守同样的约定和规范。
他保持着脸朝正前方,也要求从一定距离之外看他的脸的正面,这种对彼此尊重的需求便构成正平面描绘的本质。
肖像照实现了自我形象的客观化。
因此,这只是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极端形式。
由此可以理解的是,拍这种照总是引起某种不安,尤其在农民中。
农民往往将其它群体的成员对他们的负面形象内在化,于是他们与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便很不协调。
由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尴尬,所以在要求放松的并将自己的身体展现为一种景观的一切场合,他们都显得笨拙和不自然,就好像在照相机前舞蹈或者亮相一样。
借助于遵守正平面描绘的原则和和采取最传统的姿势,人们似乎总是能尽量控制自我形象的客观化。
轴向构图与正平面描绘原则相一致,提供了一个尽可能清晰可读的表现图;仿佛是为了避免任何误解,即使这会意味着以牺牲“自然性”为代价。
观看别人而自己没被别人看到,观看别人且没有别人看见自己在观看也没有被别人观看,或者说,偷拍,甚至所有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拍照,都可说是对于别人形象的窃取。
当某人注视正在看自己的人(正在拍照的人),调整他的姿势,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希望给人观看的样子;人总是呈现自己的形象。
简而言之,当一个人面对他人捕捉并固定自己外貌的目光时,接受最仪式化的含义便意味着降低笨拙呆板的危险,意味着给予别人一个不自然的、预定的自我形象。
就象遵守礼节一样,正平面描绘是导致自我客观化的手段:
提供一个校准了的自我形象是推行自我感知规则的一种方式。
对待照片的态度,其成规性似乎关涉社会关系的风格,这些社会关系受到分层的、静止的社会的支持。
在这一社会里,家庭和“家”比起具体的个人来说更为真实,因为个人首先是靠他们的家庭联系而界定的;[16]在这样的社会里,行为的社会规则和道德代码比起个人主体的感情、欲望或思想来说更为明显;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交换严格受到圣化的习俗的调节,这些社会交换是在对他人判断的持续恐惧下、在舆论的警惕注视下进行的,随时要受到不可质疑、从未被质疑的常规的名义的谴责,它们总是受到给别人以最佳的自我形象这一需求所支配,这种自我形象最符合尊严与荣誉的理念。
[17]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社会的表征除了变成对被再现社会的表征,又能成为什么呢?
在城市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中,如果社会规范仍然支配着摄影美学,它们留下烙印的方式不会那么总体化、并且肯定不会那么绝对。
手工劳动者和文职员工意识到有一种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学院文化的存在,而他们则消费着学院文化的次级产品;当我们着手分析他们的判断时,就会明显地看到,表现在他们个人判断中的“美学”,其具体特征的来源是基于这一事实,即这种美学起码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视为众多美学之一。
即使当工人们把一张美丽的照片与一张从美学角度讲(甚至从道德角度讲)是美的事物的照片等同起来时,他们也知道对于完美还存在其它定义;更准确地说,与他们距离最远的社会群体的美学意图,或者那些群体对工人阶级的美学实践具有的负面形象,他们从来就不是全然不知的。
“通俗美学”不同于纯朴人那种毫无质疑地依附着一种连贯的规范系统的美学,它(起码是部分地)被定义并显示为学院美学的对立面,即使这一点并没有被很张扬地宣称过。
对于合法文化的参照,即使在手工工人中,也从未被真正的排除过。
由于他们既无法忽视挑战他们自己的美学的学院美学的存在,又无法放弃他们自己受社会条件制约的取向,更不必说,他们也无法维护这些取向,并加以合法化,因此他们只好通过建立一种双重的判断尺度(有时甚至非常明显),以逃避这一矛盾。
他们必须根据分离的逻辑来体验他们与美学规范的关系,因为他们必须把义务性实践与对这一实践的义务性判断分开来:
于是,即使他们向往别的照片类型,至少在意图上,他们也从不没想过要非难家庭照。
当某个受试者被迫在他所做与想做之间作出独立选择时,这套双重规范的表现就再清楚不过了:
“这很美,但是我可没想过要这样拍”;“不错,这很漂亮,但是也许你喜欢这样的,但是不合适我。
”这类客套话一再出现,便证明存在着一种使“通俗美学”成为“被支配美学”的张力。
这种美学并不包含着自身体系化的原则,就这方面而言,我们是否必须把工人阶级趣味判断的系统看为一种美学?
当人们着手重建“通俗美学”的逻辑时,它便显示为康德美学的否定对立,这绝非巧合;同样,通行的思想潮流则基于与它相对的立论,含蓄地回答了“美学分析”所提出的每个论题。
但是工人也许会采取一个与这位哲学家完全对立的观点,却并不因此抛弃他们判断的美学资格。
人们并不是有什么就拍什么,或说并不是每件事物都适合拍。
这里的论题暗含在全部判断中,它提供了证据,证明美学观点并不仅仅是任意的,而是象实践一样,遵从着文化模式。
“这不是你该拍的东西,那不是照片”,这类判断不容置疑、毫不含糊,常常伴以讨厌的手势,所表达的否定看法立刻就能看得出来。
对于规则的违反也许是明显可见的,但是规则却并没有被感知为规则,或者说甚至还没有被阐述为规则,然而这一事实并不会排除下述的可能性:
当运用于具体个案时,美学判断的关键存在于各种暗含的原则和规则所组成的体系之中,这些原则及规则主要靠美学判断无意泄漏而非直陈明示出来。
社会学把价值体系处理为许多事实,如果它客观地将可能被美学家视为反美学的种种实践和作品(犹如通俗摄影那样)置于美学的一般标题之下,那么,将这一点视为“通俗美学”的表现就有可能是一种颠倒的常人中心主义(ethnocentricity,此处参照了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的译法):
实际上,与上述这些实践相对应的经验,与艺术家和美学家从艺术品的沉思和生产所获得的那些经验相比,即使在不同的秩序内具有某种可比拟性,但它们实际上与追求自在自为的美毫无关系。
康德所分析的趣味判断预设着一种不同的经历过的经验,它就象大众对美的经验一样,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或者说,这种经验绝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条件之外,社会条件才能造就“有趣味的人”。
康德为了把握纯粹状态下美学判断不可化约的具体性,力求区别“取悦我们的东西”和“满足我们的东西”,并进而力求将“无功利性”与“官能利益”和“理性利益”加以区分;认为“无功利性”是使沉思具有独特的美学特质的唯一担保,“官能利益”界定了“愉悦性”,而“理性利益”则界定着“善”。
与此相对照的是,工人阶级总是期望每一图象清晰无误地实现某一功能,哪怕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