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docx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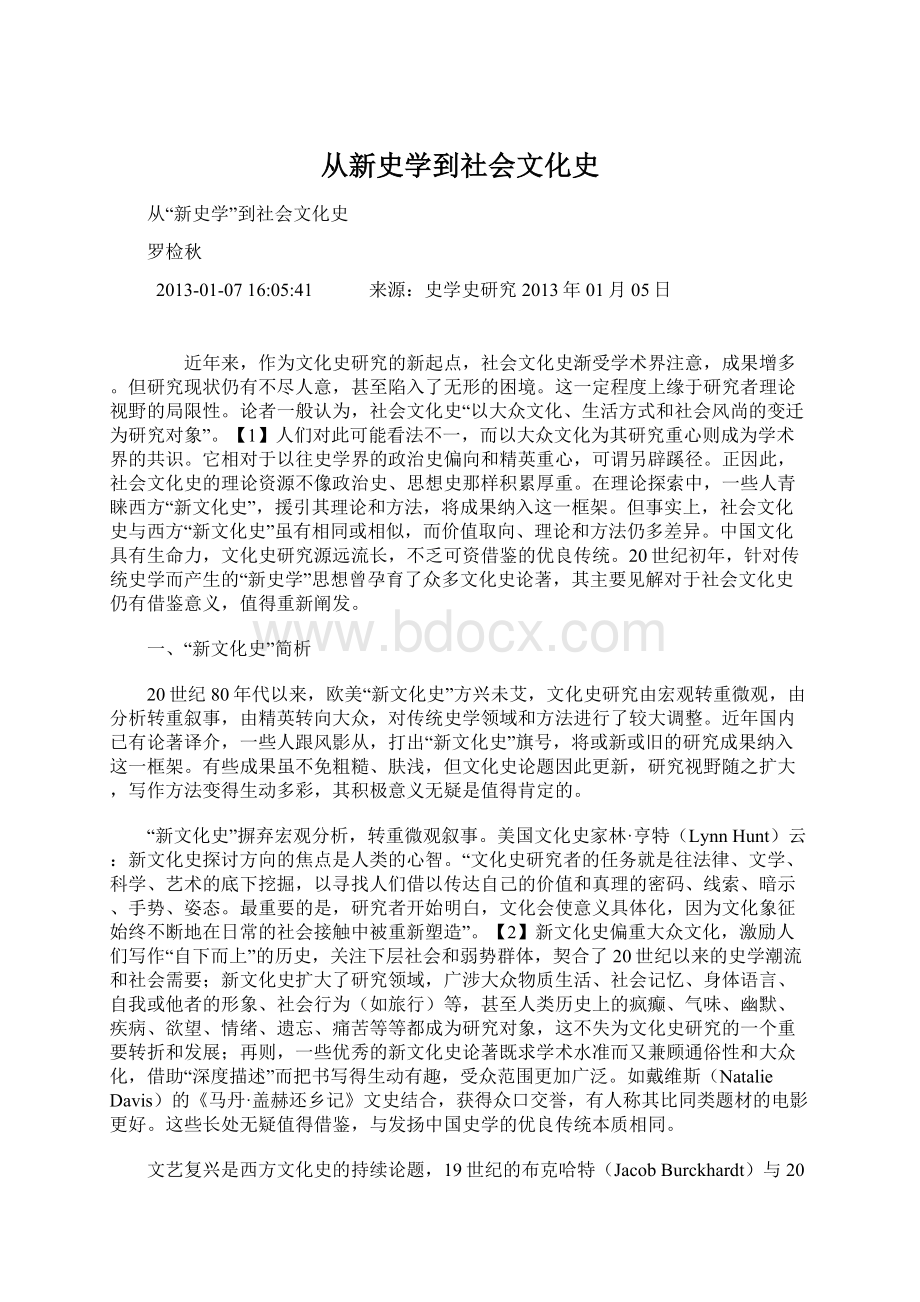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罗检秋
2013-01-0716:
05:
41 来源:
史学史研究2013年01月05日
近年来,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新起点,社会文化史渐受学术界注意,成果增多。
但研究现状仍有不尽人意,甚至陷入了无形的困境。
这一定程度上缘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性。
论者一般认为,社会文化史“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
【1】人们对此可能看法不一,而以大众文化为其研究重心则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它相对于以往史学界的政治史偏向和精英重心,可谓另辟蹊径。
正因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资源不像政治史、思想史那样积累厚重。
在理论探索中,一些人青睐西方“新文化史”,援引其理论和方法,将成果纳入这一框架。
但事实上,社会文化史与西方“新文化史”虽有相同或相似,而价值取向、理论和方法仍多差异。
中国文化具有生命力,文化史研究源远流长,不乏可资借鉴的优良传统。
20世纪初年,针对传统史学而产生的“新史学”思想曾孕育了众多文化史论著,其主要见解对于社会文化史仍有借鉴意义,值得重新阐发。
一、“新文化史”简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新文化史”方兴未艾,文化史研究由宏观转重微观,由分析转重叙事,由精英转向大众,对传统史学领域和方法进行了较大调整。
近年国内已有论著译介,一些人跟风影从,打出“新文化史”旗号,将或新或旧的研究成果纳入这一框架。
有些成果虽不免粗糙、肤浅,但文化史论题因此更新,研究视野随之扩大,写作方法变得生动多彩,其积极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新文化史”摒弃宏观分析,转重微观叙事。
美国文化史家林·亨特(LynnHunt)云:
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
“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
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2】新文化史偏重大众文化,激励人们写作“自下而上”的历史,关注下层社会和弱势群体,契合了20世纪以来的史学潮流和社会需要;新文化史扩大了研究领域,广涉大众物质生活、社会记忆、身体语言、自我或他者的形象、社会行为(如旅行)等,甚至人类历史上的疯癫、气味、幽默、疾病、欲望、情绪、遗忘、痛苦等等都成为研究对象,这不失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和发展;再则,一些优秀的新文化史论著既求学术水准而又兼顾通俗性和大众化,借助“深度描述”而把书写得生动有趣,受众范围更加广泛。
如戴维斯(NatalieDavis)的《马丹·盖赫还乡记》文史结合,获得众口交誉,有人称其比同类题材的电影更好。
这些长处无疑值得借鉴,与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本质相同。
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史的持续论题,19世纪的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与20世纪末年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Burke)明显不同。
布克哈特以四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凸显出政治对于文化的作用。
他阐发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内涵如文学、艺术中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竞争意识和人文主义倾向,主题包括意大利的道德、宗教以及科学。
而彼得·伯克聚焦于意大利近代初期的身体语言、幽默和搞笑表演、英国人在米兰的旅行、热那亚的公共与私人领域、学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等。
总之,后者彰显了文化史的多样性,强调文化史反映不同群体的声音和观点,包括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男人和女人,局内和局外人,当时人和后来人。
【3】
“新文化史”彰显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个性,注意认知不同民族文化,与近代学者偏重文化的趋同性,从西化或现代化背景研究民族文化史显然有别。
这些学术特色对中国文化史研究仍有借鉴意义,但有些倾向仍值得谨慎对待。
首先,“新文化史”的泛文化观念值得怀疑。
彼得·伯克指出:
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是“他们关注符号(the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
符号,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从艺术到日常生活,处处可见”。
【4】“符号”随处可见,文化随处皆是,见之于万事万物。
故“新文化史”强调把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史加以考察,或者对一切现象进行文化史认知,陷入了“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的偏颇。
彼得·伯克注意到:
“在这些年,几乎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已经写成了文化史”。
2000年以来出版的一些著作标题或副标题就有“历法文化史,因果文化史,气候文化史,咖啡馆文化史,内衣文化史,考试文化史,美发文化史,恐惧文化史,疲软文化史,失眠文化史,神幻蘑菇文化史,自慰文化史,民族主义文化史,怀孕文化史,烟草文化史,等等”。
【5】一切研究对象都被贴上“文化史”的标签,或者一切研究对象局限于文化史视角,这似乎未必恰当。
文化史的价值和特色在于较之政治史、经济史而偏重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
“文化”本质上是精神传统,是不依靠行政命令而形成的自然习惯。
物质生活、政治事件和人物固然需要文化史视角和诠释,但如果将社会生活泛化、标签化,则可能导致文化史趋于平庸低俗。
有的“某某文化史”,实际上只是“某某史”,既无文化史视角,又缺少对其文化内涵的阐释和分析,本可去掉“文化”二字,名副其实。
进而言之,泛文化观念导致“文化”一词成为掩盖庸俗趣味的学术外衣,给对文化一知半解者以可乘之机,甚至给怀疑、贬损文化史者提供口实。
另一方面,漫无边际地将所有历史纳入文化史,则文化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
不能体现学科特色的研究,客观上可能导致该学科的淡化、甚至消亡。
再则,“新文化史”侧重叙事的碎片化倾向也值得注意。
历史学不能停留于“宏大叙事”,文化史研究也不能长期集中于精英思想,而应重视下层社会及不同群体。
“新文化史”推崇“深度描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出版微观史学论著数百种,涉及村庄与个人、家庭与习俗、骚动、凶杀与自杀等内容,丰富了历史题材,拓展了研究领域,但一些描述局限于某人、某地的生活细节,而缺少必要的分析和洞见,不免流于猎奇求异。
“新文化史”家也认识到:
“如果是描述一件耸听但本质上不相干的暴乱或强暴的故事,或是怪人、恶棍或是神秘人物并没有意义。
描述对象应该选择那些能使我们对过去的文化有新的启发的人或事”。
【6】但从微观叙述入手而展现人或事的新启发并不容易。
就现当代人的历史常识和兴趣而言,人们一般还难以辨别、分析细小事件的描述,从而获得正确的历史认知。
故史学著作既不能全无价值判断,也不能完全排斥有意义、有启发的“宏大叙事”。
就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来看,这比有趣、猎奇的“深度描述”或许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三,“新文化史”的某些论题未必切合中国文化史的实际。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不同,近世中国与欧洲文艺复兴虽多相似,但两者内容和特质仍有差异。
近代一些人将两者比附,大多言过其实,体现了对中国文化的期望。
中西文化内容出入甚大,论题不必等齐划一,简单照搬。
比如,社会记忆和身体语言不失为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但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不是自然形成的,政府和党派在其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撇开这些背景,耻谈民间社会的历史记忆就可能见小遗大,似是而非。
同样,“新文化史”看重的感观史、情绪史在中国或许不如欧美重要,诸如疯癫、气味、搞笑之类的论题也未必契合中国实际。
例如,“新文化史”系列著作中,柯尔本(AlainCorbin)的《大地的钟声:
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深入描述乡民对钟声的感觉,从而考察其乡村组织和地方认同,而中国的乡村组织和社会认同显然更依赖于宗族。
如果研究者对中国宗族社会不甚清楚,而着迷于乡村钟声这类论题,岂非避重就轻,盲人摸象?
又如,英国史家罗伊·波特(RoyPorter)的《心灵铸就的镣铐》研究不同时期的“疯癫文化”,不同时期对异常人、对傻子的不同看法,自有其价值。
而在中国,类似的精神疾病可能会掩盖在五光十色的宗教信仰中,忽视民间信仰的特色和复杂性,可能根本无法洞悉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至于有人研究的哭泣、排气、内衣等身体史,或者专注于垃圾、厕所等论题,如果缺少文化史的诠释和分析,则近乎猎奇求异、低级趣味了。
一些“新文化史”学者不乏自知之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亦有所反思,以至于彼得·伯克怀疑“是否会看到新文化史在形式上更加接近传统的历史学?
”他认为可能性之一是,出现“布克哈特的回归”,“即重新对高雅文化的历史给予重视。
【7】但在中国,一些论者仍亦步亦趋,对其理论和方法缺少省思。
笔者以为,“新文化史”的一些经验(如大众文化取向、深度描述方法)不妨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借鉴。
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史仍需要发掘中国史学的理论资源。
二、“新史学”的取向
在中国,“文化”一词源远流长,文化史也不失为古学。
《庄子》“天下篇”综论先秦思想学术流派,可视为最初的文化史论。
在晚清中西融合中,“文化”一词增添了近代意义和西学色彩。
众所周知,近代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狭义则指精神生活,如知识、信仰、科学、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等。
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尝试对文化进行诠释、定义,运用其概念著书立说,文化史著作随之出现了。
近代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史观,如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凸显了文化传统的多样性和个性,重视精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
这与重视大众文化的“新文化史”反差明显,与之更为接近的史学源头是清末出现的“新史学”。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初年,美国史家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也提出建设“新史学”,力图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由政治史转重文化史,运用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
其某些倾向(如重视微观研究)与当代西方“新文化史”基本相同,故一些论者强调西方“新史学”到“新文化史”的学术传承性,甚至混而为一,统称为“新史学”。
两者是否属于同一史学流派,有多少异同之处,这里姑置忽论,而西方“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是在五四以后。
鲁滨孙的“新史学”与清末“新史学”不无相同或相似,如扩大研究范围、进化史观等,但两者没有直接关联,且差异尚多。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汲取了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的思想,又直接针对中国史学而论,成为中国史学变革的标志。
惟其蕴含丰富的民族性和文化内涵,其学术意义非翻译日人著作所能比拟。
中国史学素称发达,较之东西各国而独占鳌头。
中国“新史学”产生于民族文化和史学传统之中,本质上带有民族史学的深厚遗传。
“新史学”倡导历史研究由社会上层转向下层。
所谓“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
【8】所谓“人群”的重心不是上层社会,尤其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广大民众。
其创新性直接针对传统“正史”,即所谓“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和“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大弊端。
这种批评今天看来或许不免偏激,但当时并非无的放矢。
针对以朝廷为核心的帝王家谱,梁启超凸显了研究民族、民众历史的重要性;针对传统史学的“好古”取向和陈述方法,梁启超重视经世致用的“今务”、赋予历史著作更丰富的思想蕴含。
“新史学”的另一新境界是由政治史转重文化史。
历史上的金戈铁马,都市繁华,霸主英雄,皆如烟消逝,留下的只有不断积淀的文化。
文化为人类活动的成绩,梁启超给文化的定义是:
“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它“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业种业果而言”。
“物质的文化”是指“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之进步”;而“精神的文化”则指“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
他借用佛语,称“文化”为“有价值的共业”,人的“创造心、模仿心及其表现出来的活动便是业种”,其结晶便是“业果”。
此时,梁启超心中的文化相当宽泛,包括物质文化的成绩。
【9】
1927年,梁启超构想了编撰《中国文化史》的宏大计划,但对于工作繁忙而健康每况愈下的他,这只能成为未竟之业,仅写出不到10万字的“社会组织篇”。
该篇结构恢宏,征引繁博,共分八章,包括“母系与父系”、“婚姻”、“家族及宗法”、“姓氏”、“阶级”、“乡治”和“都市”七个专题。
其中阶级一题分上下两章,叙说历代等级和阶层,与后来的阶级概念有所不同。
【10】该书运用近代观念,勾勒、分析了古代氏族社会、婚姻形态和宗法、等级制度。
这些观念和方法在当时较为新颖且带西学色彩,体现了“新史学”注重民众、研究民族的取向。
《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内容宽泛,材料丰富,既不完全排斥“正史”资料,又没有集中于精英思想。
该篇取材于历代典籍、正史,而有些叙述,如关于传统“姓”与“氏”的分析、以新会茶坑村为例来说明“乡治”的情况等等,均独具价值。
此篇之作,仍取广义的文化。
按梁启超的说法,人类有了“社交的要求心及活动力”“业种”,于是就有言语、习惯、伦理等“业果”;有了智识的、爱美的、超越的要求心及活动力“业种”,于是就了著述、文艺、美术、宗教等“业果”;同样,有了“组织的要求心及活动力”的“业种”,就有了“关于政治、经济等诸法律”“业果”。
【11】他把人类社会组织看作精神生活的直接产物,体现了注重精神和制度文化的特色。
梁氏重视民间社会,所谓社会组织,显然是古代城乡的下层社会组织,而非政府结构。
从倡导“新史学”到撰写文化史,其中学术逻辑一脉相承。
三、“新史学”、“新文化史”之异趣
中国“新史学”强调书写社会民众的历史,与西方“新文化史”关注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感情和行为大致相同。
但由进化论孕育而生的“新史学”是融合中西、衔接今古的近代史学,与西方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新文化史”差异甚多,值得注意。
“新史学”受进化论滋润,体现了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色彩,所谓“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
故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应重视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历史哲学不可或缺。
同时,历史研究也是一门科学,不排斥科学方法,比如整理史料运用归纳法,叙述社会运动而究其因果。
惟其如此,“新史学”揭示民众生活的细微末节,却不排斥“宏大叙事”。
梁启超提出:
“故善为史者,必无暇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断断焉褒贬一二人。
”【12】梁氏晚年的许多论题均趋于实证而深入,但多属“宏大叙事”。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一度因政治化、工具化偏向而误入歧途,“以论代史”的空虚学风,千篇一律的宏观叙述积弊成习,无怪乎成为近年史学反思潮流的众矢之的。
但是,矫枉不必过正,相对主义、感觉主义则很难成为历史学的思想主流。
再则,“新史学”蕴含鲜明的价值评判。
梁启超将文化看作“有价值的共业”,强调史学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和新价值,以供人资鉴。
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论述均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故梁著“文化史”基本不涉及历史上负面的、落后的事物和现象。
这与“新文化史”囿于后现代语境,淡化价值评判和规律性探索是显然不同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史学”没有忽视和排斥精英文化,与“新文化史”大异其趣。
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分的讨论已历半个世纪,见仁见智。
两者虽非泾渭分明,但仍不失为研究文化类型与交融的有益途径。
梁启超晚年对“文化”再加辨析,认为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
梁启超重视精神生活,认为“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领”。
“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生活或狭义的文化。
【13】梁著文化史以精神生活为重心,涉及各社会群体的学术、观念和精神世界。
作为古代精英思想结晶的传统学术一直是梁启超史学的重心。
在他看来,“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
【14】他重视分门分类地整理人类文化成果,列举的文化专史包括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其中又分道术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文学史、美术史等。
这些专史以精英文化、甚至是精英思想为焦点。
当然,文化史不是专史的简单相加,而需要对文化现象和成就作整体、综合性的研究和阐述。
尽管如此,专史仍然是深化文化史研究的必要台阶。
在精英思想的形成、建构、扩散和衰退过程中,在精英文化与政治运作、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大众文化是不可缺少的媒介和平台。
反之,大众文化研究也不可能无忽精英思想。
近年一些文化史研究者追趋“新文化史”,排斥精英思想,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使文化史区别于哲学史、思想史。
其实,它们虽然均涉及思想、观念,而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文化史重视一般民众零散的、不自觉的、缺乏理论色彩的观念和信仰,而思想史、哲学史聚焦于思想家、哲学家具有理论色彩、成系统的思想和观念,追求更严肃、准确的分析和论证。
文化史虽然也涉及精英思想,但兼重一般个体或群体的情感和心态,研究思想产生、流播、变异和消亡的语境,这些均在一般哲学史、思想史范畴之外。
一个世纪过去了,文化专史不断产生,基于专史的综合性文化史亦不罕见,但不少是雷同、因袭之作,而所谓综合性研究又多流于专史的简单相加或改头换面。
这些文化史偏重于精英文化,有些很难与现今的哲学史、思想史区别开来。
一些文化史论著除了对政治、经济背景的概述之外,精英文化似乎与社会无关。
这或许是有的文化史研究者排斥精英文化的另一缘由。
四、“新史学”:
社会文化史的借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史研究步履艰难,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取径,相关专论也随之出现了。
其中有些注重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有的尝试理论探索,为深化研究提供资鉴。
有关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中,西方“新文化史”仍然可资借鉴,但如何发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新史学”思想仍有意义。
社会文化史“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取重大众文化。
近年海内外的大众文化史方兴未艾,研究大众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的论著接踵产生。
这种转变弥补了以往偏重精英文化史的局限,也与“新史学”取向一脉相承。
但是,社会文化史不能走向排斥精英文化的另一极端。
其倡导者也提出注意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注“精英文化社会化”问题。
【15】近年有的研究者明确提出:
社会文化史“既不能脱离大众文化,亦不能忽视精英文化”。
【16】社会文化史不排斥精英思想,只是对其认识、论述的角度与哲学史、思想史论著不同。
这种学术包容性恰恰是缘于大众文化本身。
大众文化与经济环境、政局变化相关,但直接受精英文化的引导。
古人说“上行下效”,民风随士风而变。
清中叶经世学者梁章钜曾云:
“昔人言变民风易,变士风难。
变士风易,变仕风难。
仕风变则天下自治。
然仕风与士风却是一贯。
士习果正,则仕风未有不清者,此正本清源之说也。
”【17】在缺乏制度建设而依赖道德修身的传统社会,士绅的社会角色无疑是重要而特殊的,士风对官风、民风的引导作用确实不可小觑。
清末梁启超也指出:
“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
若缺于彼而有以补于此,则虽弊而犹未至其极也。
”【18】他有感于晚清社会风气,推崇宋明士人的礼义廉耻之论,强调士人对移风易俗的意义。
风俗变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思想与社会生活的交融和互动。
晚清知识界改良风俗的主张既以近代生活方式为参照,而又有传统思想渊源,与清代士人观念、礼学主张无不关系。
另一方面,近代改良思想又以不同形式渗透于民间,从不同渠道引导、塑造了社会风尚。
两者对社会生活和风俗均有重要意义。
因此,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既有大众文化,又有士人文化;既关注社会风尚,又涵盖精英思想。
这与“新史学”的广泛包容性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与哲学史、思想史不同,社会文化史的重心不在精英思想本身,而是其社会运行,以新视角、新方法来研究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比如,思想史、哲学史家研究经典文本的内容,而社会文化史则考察该文本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流播、变异和影响等等。
就写作方法而言,历史著作既是生动有趣的故事,又不排斥科学化分析。
“新文化史”的微观叙事和深度描述固然可为社会文化史借鉴,但并不是唯一途径。
宏观的理论探讨,综合、贯通的研究,深入地分析和论辨,仍然是社会文化史不可或缺的。
这方面,“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仍有价值。
梁启超晚年认为,“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
【19】梁氏心目中的“大历史”不是传统的纪传体通史,而是研究各社会群体的综合研究。
这类著作理当建立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拼凑,重编成果。
同时,做“大历史”者需有成熟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思路。
他的《中国文化史》或许就是该主张的尝试,惟因精力、时间所限,仅撰写了“社会组织篇”。
因种种局限,当代不易出现古代那样的大史家,但汲取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避免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还是可能的。
同样,社会文化史仍然需要寻求意义和价值,不能排斥对历史规律的探讨。
梁启超认为,“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地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资鉴”。
【20】中国史学有载道:
表道的传统,明义不详事的《春秋》便是其宗师。
梁启超的主张并无新奇之处,但对于史学非价值化偏向仍然是药石箴言,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也有启示。
五、社会文化史的新视野
社会文化史当然可以作为一种研究视角。
历史上的政治事件、经济现象、英雄传奇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必然与文化环境、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从社会语境、人际网络、文化蕴含对其进行阐释和分析,都可看作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
但社会文化史的使命不限于研究视角,而有其特定的领域、论题。
笔者以为,关于深化、拓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不必过多地讨论定义,不妨具体地思考一下有待深化、加强的论题,故以下方面尤需注意:
1.不同群体的精神生活。
社会文化史关注社会生活,其研究对象无疑可以涉及物质生活的成果和轨迹,而重点是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或者说心智。
多年来,涉及精神成果、精神生活的文化专史洋洋大观,但偏重于精英阶层或著名人物。
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则集中于物质生活、风俗习惯,国外的中国大众文化史也密集于民间宗教和地方戏曲,研究大众精神生活的论题略显狭窄而浮浅。
文化和文化创造者不能完全等同。
精英文化的创造者并非都是社会精英,下层民众也直接或间接地为精英文化的形成添砖加瓦。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长期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但《诗经》中的“国风”则无论是古代的创造者,还是后来的传播者,皆有大众参与,而其文学形式也有民间文化色彩。
反之,社会精英也可能是创造大众文化的积极参与者、引导者。
民间宗教迷信一般被视为大众文化,但崇信者不限于乡民或城市平民,许多文人学者、官绅也是虔诚信徒。
有的文人学者还参与了民间宗教仪轨和理论的创造过程,成为神灵的代言人。
直到清末民初,因种种需要,官绅祭祀鬼神的仪式也较之民间更为隆重。
如果将研究视野稍加扩展,则精英和大众的精神生活均较以往的论题更为丰富。
传统士人的精神生活不限于“孔门四科”(义理、经济、考据和文章)或者琴、棋、书、画等高雅休闲。
有些仕宦之家的儒学不是信仰,而是生存之道。
士、商的联姻网络、迷信观念、戏曲嗜好、游乐休闲等等,皆足以展现不同时代、地域的士人心态和精神境界。
这些看似平淡的精神生活是深入剖析其思想、学术,乃至某些文化现象的重要途径,甚者有益于认知一时一地的政局和风气,显然值得多加关注。
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和边缘群体的社会生活也不总是那些婚丧嫁娶和多神迷信等所谓世俗文化。
他们的观念、信仰和精神世界原本丰富多彩,见诸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民谣、民谚虽由口头相传,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意识。
其中有些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反映了民众所思所想,隐含对政局和统治者的不满;有些则蕴含民众的生活信念和家教传统。
五四以后,一些学者面向大众文化,整理民间歌谣、民俗和民间故事等。
其后,“整理”工作已卓有成效,但多为民俗学或人类学课题,史学家参与较少。
于是,这些“整理”、“研究”偏重于描述,而忽略历史的、文化的阐释,而大众文化的丰富蕴涵也难以体现。
严格地说,目前许多涉及大众文化的论著实为“文化研究”,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