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琐谈上.docx
《笔法琐谈上.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笔法琐谈上.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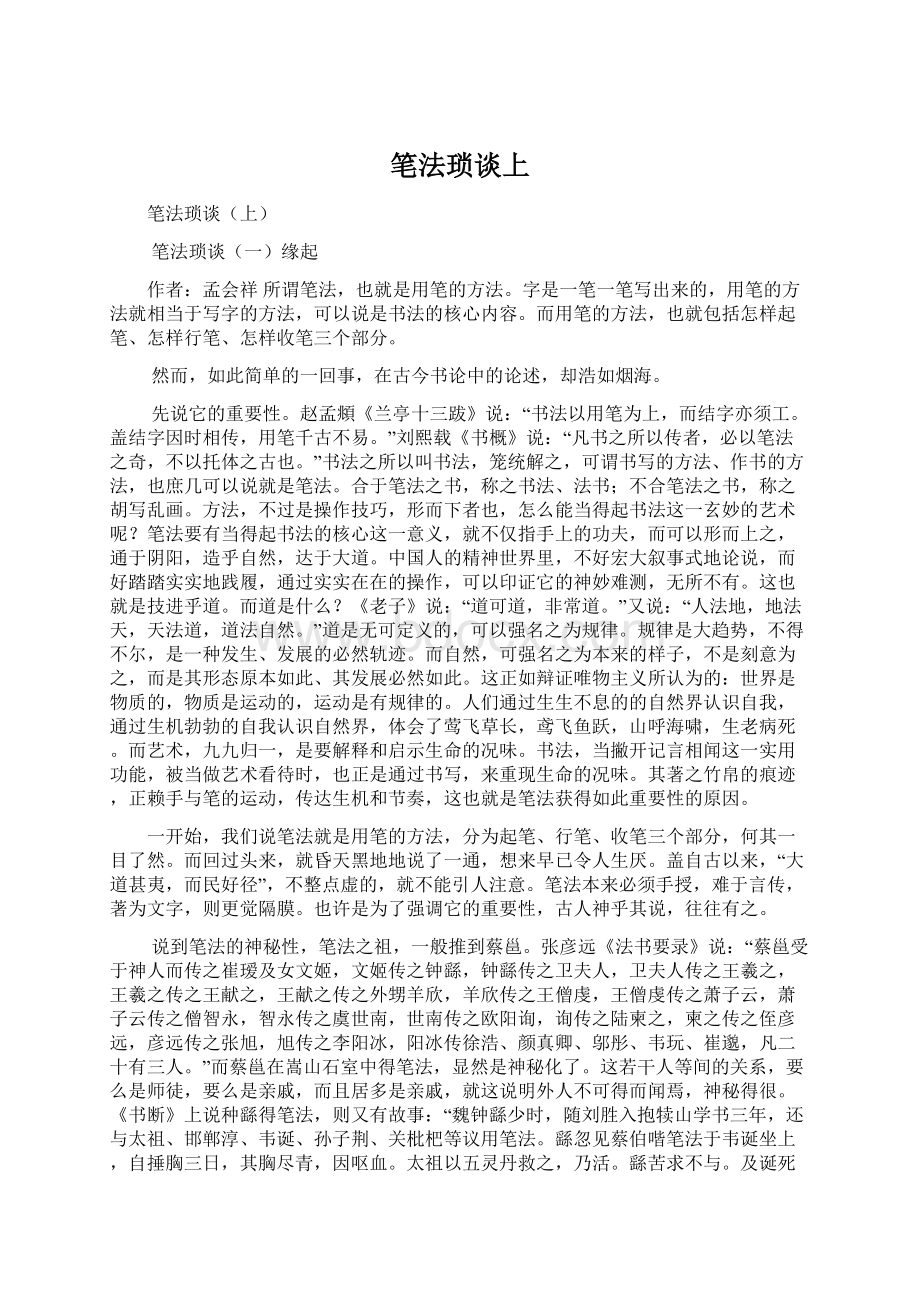
笔法琐谈上
笔法琐谈(上)
笔法琐谈
(一)缘起
作者:
孟会祥所谓笔法,也就是用笔的方法。
字是一笔一笔写出来的,用笔的方法就相当于写字的方法,可以说是书法的核心内容。
而用笔的方法,也就包括怎样起笔、怎样行笔、怎样收笔三个部分。
然而,如此简单的一回事,在古今书论中的论述,却浩如烟海。
先说它的重要性。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说: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
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刘熙载《书概》说:
“凡书之所以传者,必以笔法之奇,不以托体之古也。
”书法之所以叫书法,笼统解之,可谓书写的方法、作书的方法,也庶几可以说就是笔法。
合于笔法之书,称之书法、法书;不合笔法之书,称之胡写乱画。
方法,不过是操作技巧,形而下者也,怎么能当得起书法这一玄妙的艺术呢?
笔法要有当得起书法的核心这一意义,就不仅指手上的功夫,而可以形而上之,通于阴阳,造乎自然,达于大道。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不好宏大叙事式地论说,而好踏踏实实地践履,通过实实在在的操作,可以印证它的神妙难测,无所不有。
这也就是技进乎道。
而道是什么?
《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
”又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是无可定义的,可以强名之为规律。
规律是大趋势,不得不尔,是一种发生、发展的必然轨迹。
而自然,可强名之为本来的样子,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其形态原本如此、其发展必然如此。
这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人们通过生生不息的的自然界认识自我,通过生机勃勃的自我认识自然界,体会了莺飞草长,鸢飞鱼跃,山呼海啸,生老病死。
而艺术,九九归一,是要解释和启示生命的况味。
书法,当撇开记言相闻这一实用功能,被当做艺术看待时,也正是通过书写,来重现生命的况味。
其著之竹帛的痕迹,正赖手与笔的运动,传达生机和节奏,这也就是笔法获得如此重要性的原因。
一开始,我们说笔法就是用笔的方法,分为起笔、行笔、收笔三个部分,何其一目了然。
而回过头来,就昏天黑地地说了一通,想来早已令人生厌。
盖自古以来,“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不整点虚的,就不能引人注意。
笔法本来必须手授,难于言传,著为文字,则更觉隔膜。
也许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古人神乎其说,往往有之。
说到笔法的神秘性,笔法之祖,一般推到蔡邕。
张彦远《法书要录》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瑷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
”而蔡邕在嵩山石室中得笔法,显然是神秘化了。
这若干人等间的关系,要么是师徒,要么是亲戚,而且居多是亲戚,就这说明外人不可得而闻焉,神秘得很。
《书断》上说种繇得笔法,则又有故事:
“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
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
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
繇苦求不与。
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
”以钟繇的身份,居然捶胸呕血,像街上唱莲花落的,又干起盗墓的勾当,哪里会可信?
王羲之得笔法,有学于天台紫真和白云先生的传说。
天台,即浙江天台山,据说王羲之少时曾地那里学过书法,而天台紫真和白云先生,却不知道是什么人物。
他学于卫夫人,学于其叔父,当是可信的,而《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说: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
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时年五十有三,恐风烛奄及,聊遗于子孙耳。
可藏之石室,勿传非其人也。
”这文章显然是后人伪托。
说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毫不尊师重道,于理殊乖;而把笔法“遗于子孙”、“藏之石室”,也与王羲之风度大悖。
孙过庭在唐代都批评过了。
王献之甚至说得笔法于神鸟,孙过庭也尖锐地批判过。
总而言之,古人把笔法搞得玄之又玄,似乎一般人是难以接触的。
这一方面是尊敬书法的缘故;另一方面,则表现了文化的一种宿疾。
比如宗教,本来没有占卜命运、转化吉凶的功能,但是许多信众就只信这一套,而不肯读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古代关于笔法的这些玄虚之论,可供谈资,而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就是笔法难于言传。
这也像是宗教,明明主张不立文字,却又不能没有卷帙浩繁的经典,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古人大概不擅长科学论证式地传授,而强调启示和开悟。
所以,宋以前论笔法,大多采用比喻的形式,相互传授,也犹如禅宗的公案。
宋以后人,大概是嗜欲深了,所以天机浅了,论笔法,也逐渐理性起来、实际起来了。
比如,唐以前说用笔:
“锥划沙”、“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惊蛇入草、飞鸟出林”等,都是比喻。
而后世种种笔法、结构法,说得越来越细。
苛细的名目,以后我们也许会不时提到,要之,大多是从据说智永传下的“永字八法”生发开来的。
唐以前的比喻,很有文学艺术的色彩,然而无法操作,只能悟;后世生发开来,说得越来越细,操作性也不见得强,而往往苛细得让人头晕,言者未必了了,闻者当然昏昏的情况是常有的。
尽管如此,把笔法之祖的座位,让蔡邕坐下,也许是合适的。
丰富的笔法,正是成熟于隶书的,而蔡邕应该有隶书艺术的总结者形象。
史传李斯有《论用笔》一文,但很难想象李期自己的笔法有多丰富,内容也令人生疑。
而蔡邕的《九势》,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笔法的纲领性文件。
《九势》中前半总论,十分精彩;后半分述,屡用术语,不免有点专业色彩,我私心认为是后人伪托。
学术上的事,咱管不了。
《九势》云:
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
故曰:
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凡落笔结宇,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
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
藏锋,点画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
藏头,圆笔属纸,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
疾势,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趯之内。
掠笔,在于趱锋峻趯用之。
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
横鳞,竖勒之规。
此名九势,得之虽无师授,亦能妙合古人,须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
且说总论部分,可以理解为对书法、或笔法的哲学化、概念化的论述。
整个意思,紧紧围绕着一个“势”字。
书法是来于自然的,而自然是有阴阳的,阴阳是以“形势”呈现的。
点画中要有力的感觉,犹如肢体肌肤的鲜活。
势不可违,靠柔软的毛笔来表现势。
“势”的涵意,历来众说纷纭。
我理解的“势”,是生命的姿态。
生命的姿态什么样子?
就是力量和运动。
力量是运动的根由,运动是力量的表现。
古人仰观俯察,发现最美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的特征是就是勃发矫健的。
写字过程也是生命展现和理想展现的过程,写出的东西,当然也以有生命感为美。
正因为此,最初简单的一点一画、一撇一捺,慢慢以美的原则——也就是生命的原则加了演化;而书写的过程,也要同步于生理的节律,书写起来得力而痛快。
这大概就是笔法的起源。
笔法者,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写起来舒服,写出来的效果好看而已。
笔法琐谈
(二)误读
笔法起源于怎样写起来舒服,写出来的效果好看。
而写起来舒服,写出来效果好看的实质,是体现生命的意味。
如何才能有生命的意味?
对于书写过程来说,要有力、有势、有动感;对于书写效果来说,点画要“纵横有可象者”。
而“纵横有可象者”,并不是简单地描绘物象,而是从物象中获得启示。
如果把“纵横有可象”理解为俗语所谓“点点如桃,撇撇如刀”,那就太糟塌书法了。
我相信,书写活动一开始就是按美的规律演进的,所以才有姿态丰富的点画,才有美不胜收的书法。
先民选择毛笔书写,一开始就契合了一种神妙。
先民书写工具的演进,渺矣难考,而我们现在熟知的最早文字体系甲骨文,便是用毛笔书写的。
所以我们谈笔法,只在毛笔笔迹的范围之内。
自用毛笔书写开始,就有笔法的存在,随着时代的推移,笔法不断丰富。
到了魏晋,以王羲之为代表,笔法达到完备和成熟。
后世,则出现了不同方向的变异。
以此立论,则所谓笔法,即指最为高超的二王笔法。
其他所谓的笔法,都可以视为对魏晋笔法的改造或误读。
这样,有几个误读就需要明晰:
对篆书笔法的误读
在文字形成之前,先有刻画符号,刻画符号为硬物所为,当然谈不上笔法。
笔法必始于毛笔。
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和图画,除了毛笔书写者外,还间有以硬物划出者,那些硬物划出的粗细等匀的文字和图案,没有笔法可言。
西方始终以硬笔为书写工具,只能产生花体字,而不能产生笔法。
毛笔全向度的运动方向以及柔软性,是点画变幻的前题,也是笔法产生的必要条件。
然而,很长时间内,人们对篆书的认识局限于甲骨、金文,没有见过墨迹,所以也认为篆书是等粗细的线条写成的,因而没有多少笔法的意义。
即使近年出版的书法入门读物,还有人认为篆书只要把握字形就可以了,用笔极其简单。
这是一个明显的误会,是把经过刻划、模铸之后的产物,误会为篆书的原始形象即手书形象了。
如果篆书也是毛笔手书,那么,篆书就应该、也确实存在点画的姿致,也即存在着笔法。
甲骨中仍有刻画符号的遗存,有些刻划符号上面的动物之形,与其说是文字,还不如说是图画。
也许这样的刻画,线条是等匀的,是没有笔法意义的。
然而,它有装饰之美、纹饰之美。
这一审美渊源,在文字和书法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中断,极尽装饰的鸟虫书、中山王器那样工艺高超的字,甚至《泰山刻石》、《峄山刻石》,都富于工艺性。
我个人认为,这种笔法欠缺的书迹,实际上就是“美术字”,它美轮美奂,然而生命意味淡薄,“画”的意思要比“书”的意思多。
过去我曾经偏激地认为这样的字迹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
后来我看到有人写出中山王器那样的篆书,也看到有人写出铁线篆,不得不承认,确有心灵手巧之人能一挥而就,但它仍然欠缺自然之美和生命的感觉。
篆刻从来都是讲究工艺性的,圆朱文可以说把这种工艺性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书法如果也仅限于此,则格调必不高,因为人工的极致,也便离自然和生命的况味较远。
过去很多讲帖学的人,把魏晋以前的书法史一笔抹煞,可能就是出于这种意识。
如果我们看到《宰丰骨匕记事刻辞》,也许就会感觉到它的书写性。
它较好地保存了毛笔的书写迹象。
而《侯马盟书》本身就是墨迹,《郭店楚简》也是一样,联系到大量的秦汉简牍,一个以手书墨迹为轴线的书写史、笔法史就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这些墨迹点画起笔时笔锋的切入方法,点画中截的圆厚,以入自如的使转,几乎可以说与二王息息相通。
这才是古人书写的本来面目,是未经工艺修饰的原貌,是书写史、笔法史的主流。
这也说明,二王虽然是天才,但笔法并非向壁虚造,也是发展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这一大宗(出土的篆书墨迹并不多,显然是由于手书难于保存,而金石差可不朽)说成是手写书,它是自然的、未加修饰的,则与之相对的是书法史上的皇皇剧迹的金文等,则居多书写时就带有工艺性质,而且经过二度制作,部分原意已失,可名之为铭石书。
手写书与铭石书,相对峙也相互渗透,是文字和书法演进的矛盾的两个方面。
自古学篆,求诸金石,所以篆书中自然书写的意味淡薄,明清间有人用剪去锋颖的毛笔写篆书,求其线条均匀,早已成为一种工艺,也就几乎谈不上笔法了。
而赵寒山、八大山人、傅山等,可能因为并不擅长规规矩矩的篆书,以行草入篆,合于笔法,倒是暗合古人。
对铭石书的误读
这里说的铭石书,不局限于石,包括金、石和其他质材。
同样,手写书的材料也不限于纸,也包括其他质材。
手写书是墨迹,是自由、新鲜的;而铭石书是经过二度制作的,一般是庄重、矜持的。
手写书的自由、鲜活、富于生机,往往开创新书体;而铭石书的庄重、矜持、成熟,往往结束一种书体的演进。
像《散氏盘》可能较多地保留了手写书的意味;《盂鼎》、《毛公鼎》等把金文推向顶峰,也结束了大篆。
而大篆顶峰时期的墨迹,不可多得,若有,必是更加气象万千的。
像秦诏版权量可能较多地保留了手写书的意味,而《泰山刻石》、《峄山碑》把小篆发展到顶峰,也结束了小篆。
而小篆,特别是标准的小篆,在书法史上昙花一现,正是这种规范字、美术字生命力不强的体现。
它像秦代制度一样严酷,而同时期的简牍,是多么丰富多彩啊。
像《石门颂》、《杨淮表记》及很多小品刻石,可能较多地保留了手写书的意味,而《礼器碑》、《曹全碑》等把隶书推上顶峰,其后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则显然为隶书的发展画上了句号。
地不爱宝,汉代简牍出土无数,相形之下,前人叹为一碑一奇的汉碑,远远没有汉代简牍更为丰富。
当然,对于东汉丰碑大碣来说,像《礼器碑》、《曹全碑》等名碑,其书写水平极高,而刻手水平也极高,拓本就具有“下真迹一等”的分量。
它虽然不是手写书的自由表达,但其建立规矩,整饬有度,因而成为入门必学之碑。
大略言之,学汉碑得隶书之体,而参汉简得隶书之笔,学汉碑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石花斑驳上,恐怕就与笔法不太一致了。
汉晋间隶书余波的刻石,修饰首尾成为“折刀头”,与书写意味越拉越远,必然走向淡乎无味,难以为继。
魏碑无疑是铭石书的最大一宗。
“透过刀锋看笔锋”,也即写手与刻手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像“方笔之极轨”的《始平公造像记》是否是书丹原貌?
我认为不是书丹原貌,但并不否认这类书迹的书丹原貌会有方笔。
魏碑体的形成,约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自晋室南迁,中原精英南渡,北朝书家,承袭汉魏旧法,其楷书书迹略带隶意。
也就是说,其楷书以钟繇为师,或者笔法推远一点,以蔡邕为祖。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新体,在北朝后期也影响到北朝。
其二,魏碑作为铭石书,本身有保守的倾向,略带隶意,正是其本色,也是其追求。
其实,晋代碑志写手已经不能写隶书,而所写楷书还是带有浓厚的隶意。
如因郭沫若援引而著名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即是代表。
而至少从《正始石经》开始,碑刻之风,已有修饬点画首尾,务使方整,成为“折刀头”的旧习。
不唯《王兴之夫妇墓志》如此,同期的墓志大部分如此,“二爨”也是如此。
之所以修饬成“折刀头”,可能与便于下刀有关。
这一风尚为魏碑书、刻手所继承。
其三,魏碑体居多与佛教内容有关,受写经体的影响。
而写经体的僧俗写手绍承汉简,务求快捷,这是魏碑体体势的重要源头之一。
其四,因书、刻之间相互影响,有些书手也摹仿刀意,写出夸张的方笔。
如高昌延昌年间前后(相当于北周)的墓志,用笔居多是方圆并用的,而体势则带有隶意。
其中,《令狐天恩墓表》则明显带有夸张的方笔,很有点魏碑的意思。
这样的方笔显然利于刀刻,而经过刀刻之后,因为审美意识的参与,可能会进一步强调其方折刚狠。
下层文人与民间刻手的力量,不可小视。
尽管魏碑的阳刚之气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但不能不承认,文化的整体发展趋势是朝着雅驯方向的。
魏墓志中不少精品,并不剑拔怒张,而是融入了南派新体的因素。
魏碑中确实存在着骨气洞达、劲险刻利之美,需要汲取,但它毕竟是刀、笔结合的产物。
就一些过于修饰、任刀为体的造像记研误笔法,更是几于缘木求鱼。
碑派书家,如张裕钊、赵之谦,用毛笔写出了刀刻的效果,当代也有人用毛笔能把《始平公造像》临得很像,但这种类似于杂技的高难度动作,是否有契合生命的节律,我是怀疑的。
纯粹的碑派在清末民国间走入绝境,非没有原因吧。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也并不全是贬碑扬帖的意思,如果没有对铭石书笔法的误读,也就没有碑派的云蒸霞蔚,这是另一回事。
晋唐一体化和对二王的误读
二王典范在南朝精英阶层传承,与北朝刻石的群众运动相比,总感觉到气息微弱。
特别是梁元帝焚书十四万卷时,斯文凋丧,令人叹息。
陈隋间,好像智永成了一脉单传。
好在李世民颇好笔翰,使王羲之成为正统。
李世民的贡献,一方面使王羲之成为尽善尽美的书圣;另一方面,通过对《兰亭序》的传播,使更多的人接触到了王羲之书法。
兰亭论辩,郭沫若的观点站不住脚,算是失败了。
我也相信《兰亭序》是王羲之作品,而真迹沉埋昭陵。
《兰亭序》时代,肯定有标准的楷书、肯定有《兰亭序》风格的行书,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另一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思考,《兰亭序》的风格,在传世王羲之摹本和拓本中,差不多可以说是孤例。
如果仅就风格而论,像郭氏所说,它出于智永作伪,似乎更令人信服。
除《兰亭序》外,王羲之其他行草帖,都是夭矫不群的,体势变化万千,笔致变化万千,让人目不暇给。
这正是初创时期的生机和不确定性,也是其内涵幽深、玩味不尽的魅力所在。
而我们看到的《兰亭序》是成熟之美、无懈可击之美,这就产生了风格的歧异,也埋下了误读的种子。
特别是兰亭八柱,尽管出于欧虞褚大师临仿,经过刻拓,也多多少少,带有铭石书的某些特征。
看到兰亭八住帖的人,肯定比看到真迹乃至摹本的人多得多,因而,如果把杰出的书法家和家世赫赫者排除在外,由于种种条件的改变,今不逮古,势所必然。
当然,这并不是说宋以后的书法家都不理解二王,都不了解二王羲之在民间的形象,差不多变会定格在《兰亭序》、《怀仁集王圣教序》,以及李世民的碑刻上。
到宋代,出现了高桌椅,则人们对王羲之可能更加隔膜。
《阁帖》盛行之后,人们眼中的王羲之,是经过刻拓的、简化的王羲之,而高桌椅也便于接受这种简化。
好在现在出版发达,我们只要把古帖墨迹本和刻帖加以对比,就会感觉到刻拓的简化是多么可怕。
加上宋人学楷书,多从唐人大楷入手,这就为“院体”准备了所有的条件。
毕竟,像米芾那样能够时常看到二王真迹的人,是凤毛麟角的。
所以,书法,或者说笔法,差不多可以唐为界,唐以为前古,唐以后为今,由于种种条件的改变,今不逮古,势所必然。
当然,这并不是说宋以后的书法家都不理解二王,都不了解二王的笔法。
我们看到苏轼临的《讲堂帖》、赵子昂临的《远宦帖》,以及王铎临的大量二王帖,都是能够克绍山阴箕裘的。
但毕竟时代压之,赵子昂极知晋人,但他写出来的,也是简化的晋人或改造的晋人。
至于一般的书写者,可能终生无缘见晋贤墨迹、摹本,当然就会陷于误读,而自以为追步山阴了。
正如儒学一变为汉儒,再变为宋儒,欲知孔孟真意,不读《论语》、《孟子》是不可思议的。
笔法的误读可能,远甚于此。
欲了解二王笔法,当然最重要的依据是墨迹和摹本,而历代法书只是它的注脚。
笔法琐谈(三)姿式
写字,站着写还是坐着写,如何站、如何坐,是一个问题。
怎样拿毛笔,是另一个问题。
前一个问题,可谓之“身法”。
古人论述也不少,但没什么争议。
很多人谈到身法,要求烦琐,做起来不容易。
但是,我见过很多人写字,身法千奇百怪,似乎也不影响其掌握笔法。
所以,标准的身法,可能仅仅是一个标准而已,按标准去做,有利于书写、有利于身体健康罢了。
白蕉在《书法学习讲话》中总结了几条,我以为最明白,不弄玄虚:
两脚平放桌子下面,身体坐稳,重心不偏;
头要端正,视线才正确集中,看到全面;
肩背要直,不可倾斜,胸部和桌面保持适当距离;
左手按纸,右手提笔书写,左手对右手起着支援作用和平衡作用,对身体重心起稳定作用;
在书写巨幅大字的时候,左右脚分前后,如果双脚并立,不能使用出全身力量。
白蕉讲的主要是坐姿,站姿只讲了一句,也够了。
近年来,人们为探索古法,追踪古人书写时的身法,及于桌椅等相关因素。
这方面,工作做得最细,也最有成就的,要算孙晓云的名著《书法有法》。
她以西晋瓷俑、北齐《校书图》、五代《文苑图》等为佐证,证明古人基本上是一手执纸、一手执笔,悬空书写的。
(此前启功主编的《书法概论》中,也曾引用一幅古代图画,一手执笔,一手执一纸筒书写;另有一照片,像是启功先生自己的示范。
)想象在以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在细细的竹木简上书写,大概左手执简、右手三指执笔,左右手配合书写是便利的、合理的。
细细的简如果放在几上书写,可能反而不便。
我觉得,正是这一习惯形成了惯性,古人不把纸张放在几上书写。
至于把纸张卷成一个小筒书写,甚至纸长了还需要书僮抻纸,也来源于习惯而已。
这样的书写状况,产生相应的以转指为主的笔法,进一步相应的是,写的都是小字。
即如郑杓《衍极》所说:
“寸以内,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
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变也。
魏晋间帖,掌指字也。
”魏晋之前当然也有大字,比如汉碑,至少摩崖要采用题壁式书写,是不是三指执笔法,就很难说,而且,悬空书写时,也不可能再是左右手配合,臂腕恐怕都要发挥作用了。
铭石、题署一类的字,写法可能就不是标准的“古法”。
我认为帖学范畴内的古法,是以二王为代表的精妙的转笔方法,而铭石书传统中的笔法,始终都没有达到二王那样精细多变的程度。
到宋代,高桌椅配合的书写状况成为常态。
使用高桌椅非常方便,然而,左右手的配合减弱了,腕臂由悬空变得可以支撑了,执笔的姿式也便变成了“腕平掌竖”,总而言之,毛笔接触纸面的方式简单化了,“古法”也便慢慢失去了。
当代人即使知道古人的书写状态,大概也没有必要学魏晋人的样子书写。
时移世易,天地江河,无日不变,我们应该了解古人,但还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写字,席地而坐(包括古代的跪坐),坐在几上,都不大现实。
另一个问题,就是执笔法。
据说,唐代韩方明、陆希声论笔法,都来于右军,有拨镫法、“五字法”的说法。
“拨镫”一说指马镫,一说“镫”通“灯”,从来都莫衷一是,辨析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
实践证明,“五字执笔法”是实用而科学的,其他五花八门,都不重要。
李煜把拨镫法和五字法混为一谈,总结出八字:
擫:
大指上节下端,用力向外向右上,势倒而仰。
压:
食指上节上端,用力向内向右下,此上二指主力。
钩:
中指指尖钩笔,向下向左内起,体直而垂。
揭:
名指背爪肉际,揭笔向上向右外起。
抵:
名指揭笔,由中指抵住。
拒:
中指钩笔,由名指拒定,此上二指主转运。
导:
小指引名指过右。
送:
小指送名指过左,此上一指主往来。
五字执笔法,把五个指头的作用,皆用一个字说明,就是:
擫、押、钩、格、抵。
虽云五字,身教则易,言传难明,这里也不多说了。
讲五字执笔法,以沈尹默讲得最细致。
前人论执笔,“指实掌虚”最为重要。
虞世南《笔髓论》说:
“指实掌虚。
”李世民《笔法诀》说:
“大抵腕竖则锋正,锋正则四面势全。
次实指,指实则节力均平。
次虚掌,掌虚则运用便易。
”苏轼说: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
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
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柳诚悬之言良是。
”指实,才能笔实,点画才能果断有力;但指实不是用蛮力死死把笔。
苏轼说: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
仆以为不然。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
”掌虚,才能“运用便易”,使转自如。
使转自如,才能免于生拉硬扯的蛮力。
据说苏轼是用三指执笔法写字的。
苏轼不可能知道古人也用三指执笔法,恐怕他的三指执笔法只能是一种“坏毛病”,纠正不过来了,也就安之若素罢了。
按理说,在笔法上他应该没有发言权,但他以天才的颖悟,还是参透了笔法的真谛。
“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
”“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
”这几句话,实在是过来人语,度人金针。
其实,综前人所论,执笔是为了用笔,而用笔的实质,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
其一,就执笔深浅来说,大体以母指尖为支点,构成一个杠杆。
这样,笔锋向任何方向的运动,与笔顶都应该是相反方向的。
这实际上也是“逆顶”、“涩势”的原因。
苏轼还说过用笔“如逆水撑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也是要找到这种杠杆作用。
找到这种作用,是“拨镫”、是“拨灯”、是“拨挑”、是“写”;找不到这种作用,顺锋拖过,是“画”、是“描”。
苏轼所谓“浩然听笔之所之”,就是强调笔锋写过去,而不是人力拉扯过去。
也正是如此,“方其运也,左右前后,却不免欹侧”。
否则,笔杆如果总是垂直于纸面,哪里会有杠杆作用呢?
“老干体”那些人,写字时看起来很潇洒、很豪迈,实际上写出的点画是无力的。
其二,就使转来说,也大体以母指尖为中枢,构成一个转轴系统。
因为笔毫是软的,没有转的作用,势必偃卧。
有些碑派书迹,不娴转笔,为了防止笔毫偃卧,就且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