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旧唐书》的史料来源.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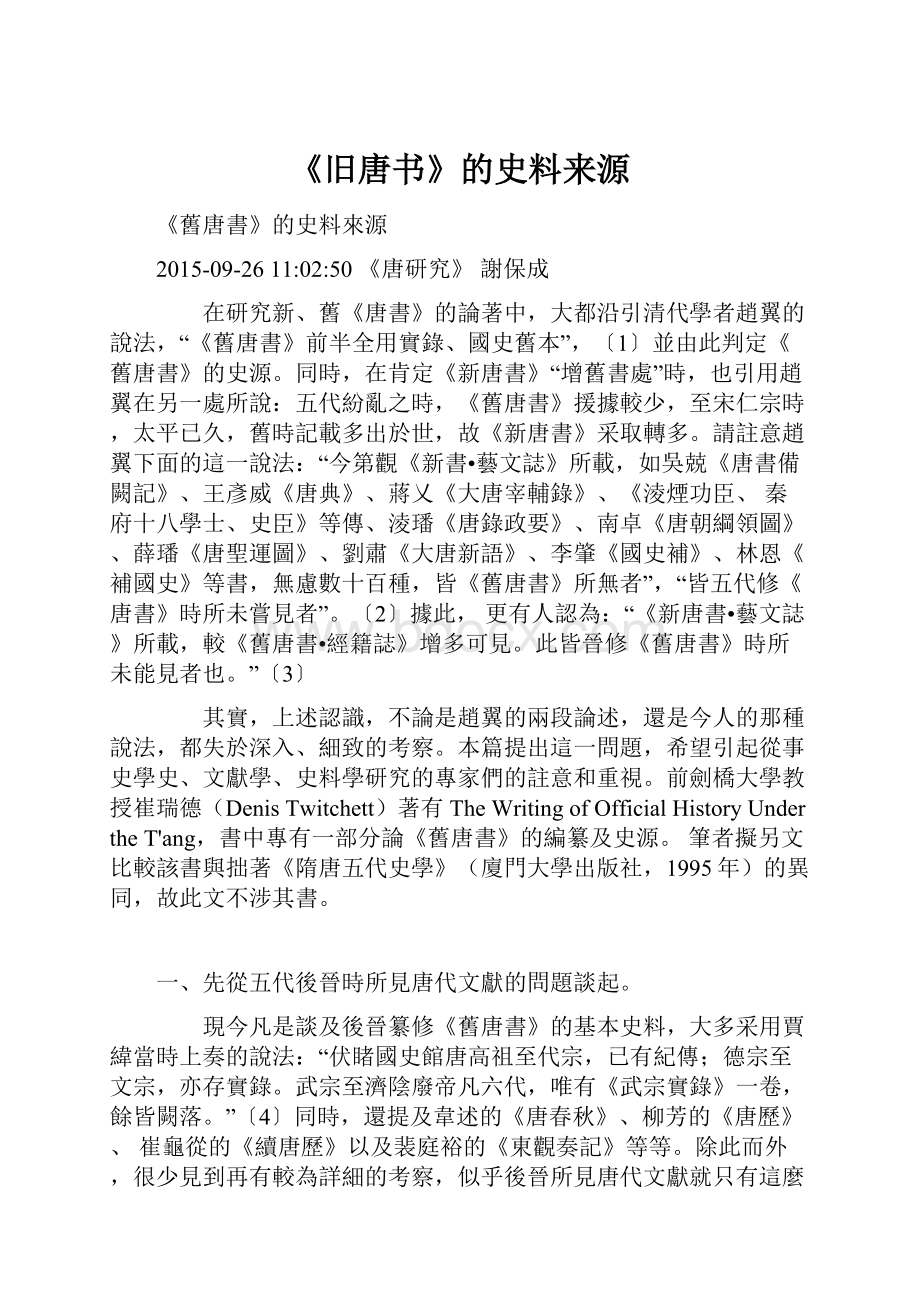
《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舊唐書》的史料來源
2015-09-2611:
02:
50《唐研究》謝保成
在研究新、舊《唐書》的論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學者趙翼的說法,“《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1〕並由此判定《舊唐書》的史源。
同時,在肯定《新唐書》“增舊書處”時,也引用趙翼在另一處所說:
五代紛亂之時,《舊唐書》援據較少,至宋仁宗時,太平已久,舊時記載多出於世,故《新唐書》采取轉多。
請註意趙翼下面的這一說法:
“今第觀《新書•藝文誌》所載,如吳兢《唐書備闕記》、王彥威《唐典》、蔣乂《大唐宰輔錄》、《淩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淩璠《唐錄政要》、南卓《唐朝綱領圖》、薛璠《唐聖運圖》、劉肅《大唐新語》、李肇《國史補》、林恩《補國史》等書,無慮數十百種,皆《舊唐書》所無者”,“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
〔2〕據此,更有人認為:
“《新唐書•藝文誌》所載,較《舊唐書•經籍誌》增多可見。
此皆晉修《舊唐書》時所未能見者也。
”〔3〕
其實,上述認識,不論是趙翼的兩段論述,還是今人的那種說法,都失於深入、細致的考察。
本篇提出這一問題,希望引起從事史學史、文獻學、史料學研究的專家們的註意和重視。
前劍橋大學教授崔瑞德(DenisTwitchett)著有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書中專有一部分論《舊唐書》的編纂及史源。
筆者擬另文比較該書與拙著《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的異同,故此文不涉其書。
一、先從五代後晉時所見唐代文獻的問題談起。
現今凡是談及後晉纂修《舊唐書》的基本史料,大多采用賈緯當時上奏的說法:
“伏睹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
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
”〔4〕同時,還提及韋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歷》、崔龜從的《續唐歷》以及裴庭裕的《東觀奏記》等等。
除此而外,很少見到再有較為詳細的考察,似乎後晉所見唐代文獻就只有這麼多了。
加之對《舊唐書•經籍誌》的錯誤認識,更助長了前述說法的流傳。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正確理解《舊唐書•經籍誌》的編纂特點。
後晉史官纂修此誌,是以毋煚的《古今書錄》為依據的,著錄的是“開元盛時四部諸書”。
至於開元以後的著述,他們不是沒有見到,而是不打算混雜其中。
關於這一點,誌文交待得十分清楚:
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
臣以後出之書,在開元四部之外,不欲雜其本部,今據所聞,附撰人等傳。
其諸公文集,亦見本傳,此並不錄。
〔5〕
據此,凡是《舊唐書》中提到的各家撰述,不論是“記禮法之沿革”,還是“裁國史之繁略”,亦或“諸公文集”,都是後晉史官“所聞”或所見,不應當排除其成為《舊唐書》史源的可能性。
首先,唐代的幾部關於“禮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舊唐書•經籍誌》都沒有著錄,但後晉時確曾為朝廷重視過。
《冊府元龜》、《舊五代史》都明確地記載了後晉天福四年(939,也即詔修唐史的前二年)關於修纂《大晉政統》的一番爭議。
左諫議大夫曹國珍上奏道:
請於內外臣僚之中,擇選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後《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為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略,目之為《大晉政統》,用作成規。
〔6〕
後晉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為允當”,即命太子少師梁文矩等十人為詳議官。
事雖未成,但曹國珍提到的那幾部書,當時顯然是見得到的。
在《唐六典》之外,所謂“前後《會要》”,即是蘇弁、蘇冕兄弟所撰《會要》與崔鉉監修的《續會要》,這在《舊唐書》都有記載。
《蘇弁附蘇冕傳》稱:
“冕纘國朝政事,撰《會要》四十卷,行於時。
”《宣宗紀》大中七年(853)記道:
“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鉉、薛逢、鄭言等。
”《大中統類》,在《宣宗紀》、《刑法誌》、《劉鉉傳》都有詳細記載:
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鉉“選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7〕唯獨《禮閣新儀》一書,《舊唐書》中只字未提,由《新唐書•禮樂誌》一知其為憲宗元和十一年(816)韋公肅“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而成。
《舊唐書•李漢傳》中,僅有韋公肅在憲宗時議禮儀的記載,稱其“理甚精詳”,“請舉而行之”。
至於“律令格式”,凡《舊唐書•刑法誌》中涉及到的各次刪定,無論開元以前、開元之後,都是後晉時見到了的。
此外,尚有不少“記禮法之沿革”的撰述,《舊唐書•經籍誌》雖未著錄,卻在紀、誌、傳中有記載,不僅見到了,而且還成為重要的史料來源。
例如,《玄宗紀》上、《禮儀誌》一都記述了開元二十年(732)九月所成《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頒所司行用之。
又如,《德宗紀》下、《杜佑傳》都記錄了貞元十七年(801)杜佑自淮南進《通典》二百卷,“大行於時”,“為士君子所稱”。
再如,《禮儀誌》五、《王彥威傳》不僅記述了王彥威“於禮閣掇拾自隋已來朝廷沿革、吉兇五禮,以類區分,成三十卷獻之,號曰《元和新禮》(案:
通常稱作《曲臺新禮》)”,〔8〕還註意到憲宗以後圍繞“王彥威《曲臺禮》”的多次辯論。
其次,對於《經籍誌》中提到的天寶以後“裁國史之繁略”的撰述,也作一點考察。
為了說明情況,先對唐代的實錄、國史簡要追溯一下。
自太宗始,在修前代史的同時,又設置了專修國史即本朝史的機構--史館,並逐漸形成系統的組織、明確的條規,把積累史料、編纂國史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走向制度化。
二百多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形成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系列,一是皇帝實錄,二是本朝國史。
玄宗及玄宗以前的各帝實錄,纂修情況記載不一,有一帝數部的,有卷帙不確的。
代宗以下,除了德宗、順宗之外,都是一帝一部實錄,直至武宗。
總括起來,後晉修唐史時,計有高祖至武宗十六帝實錄,這是沒有多大歧義的。
另一個系列,即唐代國史系列,情況較為復雜。
國史的修撰,是從太宗時開始的。
貞觀元年(627),姚思廉撰《唐史》紀傳,粗成三十卷。
高宗顯慶元年(656),令狐德棻等續成八十卷,名以《武德貞觀兩朝史》。
龍朔三年(663),許敬宗等又續為一百卷,並起草十誌,未半而終。
武則天長壽二年(693),牛鳳及另撰《唐史》一百一十卷,起高祖,終高宗。
長安三年(703),武則天命李嶠、朱敬則、劉知幾、吳兢等修《唐史》。
據劉知幾的說法,勒成八十卷。
吳兢又別撰《唐史》一百一十卷、《唐春秋》三十卷。
其後,韋述因高宗以來國史雖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始定類例,補遺續闕”,修成紀傳體《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包括《史例》一卷,史稱其“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
〔9〕安史之亂起,韋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肅宗至德二載(757)於休烈請訪求史籍,韋述才以其所藏送官。
之後,唐代國史的修撰,各類記載紛紜。
其中,《崇文總目》的說法較為清晰: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
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於開元,凡一百一十卷。
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誌、列傳一百一十二卷。
至德、乾元以後,史官於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誌、傳後隨篇增緝,而不知卷帙。
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10〕
該書因是韋述“始定類例”,又有《史例》一卷,所以署“韋述撰”。
韋述因吳兢舊本增至一百一十二卷,於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共成一百一十四卷。
史官令狐峘於紀、誌、傳後“隨篇增緝”,總成一百三十卷,則“未詳撰人名氏”的十六卷顯然是出自令狐峘了。
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實錄》四十卷的纂修者,這裏於肅宗之後“隨篇增緝”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
由此可以斷定,這部一百三十卷的《唐書》,是記述高祖至代宗一百六十二年間史事的紀傳體史書。
這也正符合後晉史官賈緯的說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
紀傳體國史,在令狐峘以後便不再有續修了。
受肅、代之際新起《春秋》學影響,其後編年史風大起,唐代的國史轉而為編年體了。
韋述在紀傳體《唐書》的同時,還有編年體的《唐春秋》三十卷。
柳芳續韋述《唐書》之後,也另撰《唐歷》四十卷,起隋恭帝義寧元年(617),迄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以敘制度為詳”。
宣宗大中五年,崔龜從監修《續唐歷》三十卷,起代宗大歷十三年,盡憲宗元和十五年。
〔11〕這些有關唐代歷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國史之繁略”者,在《舊唐書》的韋述、柳芳、崔龜從等人的傳記中,都有較詳的記載。
依照《經籍誌》的說法,這些撰述在後晉時是見到過的,現今的研究當中也很少有疑義。
除此以外,《舊唐書》紀、傳中還記載有不少《經籍誌》未著錄的“裁國史”之作,擇要舉其一、二。
《文宗紀》下、《李德裕傳》分別記錄了大和八年(834)李德裕進《禦臣要略》以及《次柳氏舊聞》三卷,又有《會昌伐叛記》、《文武兩朝獻替記》,皆“行於世”。
《文宗紀》下、《王彥威傳》都記有開成二年(837)王彥威“纂集國初已來至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傳》體敘事,號曰《唐典》,進之”。
〔12〕《蔣乂傳》稱:
“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輔錄》七十卷,《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
”又《馬總傳》以其“公務之余,手不釋卷,所著《奏議集》、《年歷》、《通歷》、《子鈔》等書百餘卷,行於世”。
其中,《年歷》、《奏議集》都是記錄唐代的“雜事”或集錄唐人的“奏疏論議”之作。
應當提起註意的是,上述舉例之中,王彥威《唐典》七十卷,蔣乂《大唐宰輔錄》七十卷以及《淩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等傳四十卷,都是趙翼認定為《新唐書•藝文誌》所載而《舊唐書》“所無者”。
下面,再來談《經籍誌》“不錄”而“見本傳”的“諸公文集”。
唐人文集,《新唐書•藝文誌》著錄不下四百種,而《舊唐書•經籍誌》僅有百十余種。
陸贄、韓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舊唐書•經籍誌》“所無者”,但《舊唐書》有關傳記卻大量采錄了他們文集中的文字。
從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紀傳體國史,只有皇帝實錄。
據現存的韓愈所修《順宗實錄》和《資治通鑒考異》所引唐代實錄,我們可以知道,《實錄》敘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傳記,只記其歷官、政績等,不錄表疏奏章。
《順宗實錄》卷四敘陸贄,從“贄字敬輿,吳郡人也”起,至“卒於忠州,年五十二”,是整個《順宗實錄》中最長的一篇人物傳。
《舊唐書•陸贄傳》也是全書人物傳中的一鉅篇,一人獨占一卷。
兩相對照,最為明顯的差異就是:
《舊唐書•陸贄傳》中的六則長篇上疏,《順宗實錄》中只字不提。
顯然,後晉史官不可能從“實錄舊本”中取材。
而陸贄的這幾篇奏疏,都見於憲宗時韋處厚所編的《陸贄論議表疏集》。
《陸贄傳》除了參取《順宗實錄》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陸贄文集,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韓愈,唐代實錄中是如何記述的,現已難加稽考。
但是,《舊唐書•韓愈傳》卻有這樣的記述:
“愈所為文”,“自成一家新語”,“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為之序。
”而且,傳中詳錄了他的《進學解》、《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和《鱷魚文》。
這足以表明,在傳寫韓愈時,後晉的史官一定是翻檢過《昌黎先生集》(或《韓昌黎集》)的。
直接從文集中轉錄而成《舊唐書》人物傳的,也為數不少。
以現今傳世的唐人別集看,數量最多的是集中的墓誌碑銘。
僅《全唐文》、《唐文拾遺》所收唐人所撰墓碑傳記,就接近一千篇。
撰寫墓誌碑銘的,又多是一代名家。
開元盛時,張說在撰寫碑誌方面的成就最大,與史傳竟似出自一手。
如其《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簡直就是《舊唐書•裴行儉傳》的藍本。
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與《舊唐書•王方翼傳》則如出一筆。
其後,便是權德輿,所撰墓誌碑銘在八十篇以上。
內中,記述公卿的碑傳,大都可與史傳相參校。
韓愈所撰墓誌碑銘,數量僅次權德輿,與張說大致相當。
在六十篇左右。
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還自撰墓誌。
書中《杜佑附杜牧傳》,完全是鈔錄杜牧的《自撰墓誌銘》而成。
這篇墓誌收錄在杜牧外甥所編《樊川文集》中,而且傳文又提到此集,後晉史官無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
以上三例說明,唐人文集無論《舊唐書•經籍誌》是否著錄,都是後晉史官纂修《舊唐書》的一項重要史料來源。
尤其是德宗以後的人物傳,事跡多據文集中的墓誌碑銘,疏奏更是直接節錄自相關的文集了。
應當說,這在當時是一條“捷徑”。
在《舊唐書•經籍誌》提到的“記禮法之沿革”、“裁國史之繁略”以及“諸公文集”三個系列的史源之外,還有未曾提及、也未著錄的雜史、小說之類的資料來源問題。
《資治通鑒》唐高祖武德三年(620)七月乙醜,有“羅士信為王世充所圍”一事。
其《考異》徵引了《太宗實錄》、《舊唐書•太宗紀》、《單雄信傳》和劉餗《小說》,經考證認為《舊唐書》記載失誤,是承襲了劉餗《小說》所致。
司馬光的這一考證,表明《舊唐書》的確參考過劉餗的《小說》,只不過是參考錯了而已。
當然,更有采錄雜史原文的諸多例證,後文將作詳述,這裏僅舉一簡單的實例。
李肇的《國史補》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條,其文為:
“李汧公勉為嶺南節度使,罷鎮。
行到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於江中而去。
”《舊唐書•李勉傳》記述:
大歷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
”就目前可見唐代雜史,只有李肇記述了“李勉投犀象”之事,《舊唐書•李勉傳》所記,文字如此雷同,極有可能是直接采錄自《國史補》。
總而言之,《舊唐書》的取材,絕不僅僅限於唐代的國史、實錄,也不應當以其《經籍誌》著錄的“有無”為判斷標準。
應該說,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國史,穆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實錄,宣宗以前有關“禮法之沿革”的各種典誌,以及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說,《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采摭。
而這些文獻,絕大多數已經亡佚,僅僅憑藉《舊唐書》才得以程度不同地保存!
在獲得了以上的基本認識之後,下面分別對《舊唐書》誌、列傳的史料來源進行具體考察。
二、自宋以來,歷代都以《新唐書》勝於《舊唐書》,再也無人過問《舊唐書》“十一誌”的情況。
為此,這裏多作一點考察,以見新、舊兩書各誌的優劣。
總的來講,《舊唐書》各誌基本上是代宗以前為詳,德宗至武宗漸略,宣宗以下則寥寥無幾。
這種現象固然與整個史料來源情況直接相關,但也應看到唐代後期值得載入史冊的定制原本就不多。
大凡誌中涉及到的唐後期的制度,多數都是較為重要的內容。
因而,有的誌的編纂情況就更應當引起重視了。
下面,依次進行考察。
《禮儀誌》七卷,主要依據《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改編,這似乎是公認的事實,但應作進一步的分析。
就其編排順序而言,不是按照吉、賓、軍、嘉、兇五禮來敘述的,而是依《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袷禘、五服、縗裳等項分卷記敘的。
所以,應該說:
記玄宗以前的禮儀,取材主要采自《大唐開元禮》,編排主要沿襲《通典•禮典》。
玄宗以後,取材較為復雜。
德宗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
〔13〕整部《舊唐書》雖然有四處提到王涇其人,卻無一處點出《大唐郊祀錄》其書,《禮儀誌》似未采用其書。
前文曾經提到,憲宗元和十一年韋公肅《禮閣新儀》三十卷,後晉史官雖然見得到,但《舊唐書》卻未涉及,多少有些奇怪。
接下來,便是元和十三年王彥威《曲臺新禮》三十卷,“集開元二十一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五禮裁制敕格”。
〔14〕這顯然是繼《大唐開元禮》的一部續作。
《舊唐書》中,不僅《憲宗紀》、《王彥威傳》都記述了《曲臺新禮》這部書,而且《王彥威傳》通篇都是記其“議禮”生涯的,足以顯見後晉史官是十分了解其人而又見到其書的。
就《禮儀誌》本身來看,在敘及穆宗至文宗議禮之事時,多次引錄王彥威奏。
《誌》五記昭宗大順元年(890)將行禘祭,有司請以敬宗、文宗、宣宗三太後祔享太廟,便是因為“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進奏的。
盡管博士殷盈孫“非之”,朝廷仍然“依行之”。
這一記載表明,《曲臺新禮》對穆宗以後的禮儀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舊唐書》纂修者也註意到了。
文宗以後的禮儀,主要圍繞宗廟、袷禘有過幾次爭議,集中在《誌》五、《誌》六,顯然是後晉所搜集到的一些散篇,經過編綴而成。
總起來說,《禮儀誌》取材主要源自《大唐開元禮》、《曲臺新禮》和文宗以後的一些散見的禮儀奏章,而編纂體例則沿用《通典•禮典》。
《新唐書》合《舊唐書》的禮儀、音樂為禮樂,其禮的部分主要是變換體例,按照“貞觀、開元”的“五禮之文”損益。
《音樂誌》四卷,有的論著認為,其文字“多本之於《通典》”。
如果說這是指有關唐代沿革、樂器,指歌、舞及其曲,指清樂、四方樂、散樂及坐立部伎等主要內容,是不錯的。
但這些只是四卷書中的一小部分內容,並不是全部。
實際情況應當是這樣:
《誌》一主要依據前後《會要》,並參照《通典•樂典》。
具體而言,誌文中“高祖受禪,擢祖孝孫為吏部郎中”以下,至貞觀十四年敕、八座議定“七廟登歌”的記述,是分見於《通典》卷一四三《歷代制造》、卷一四七《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而在今本《唐會要》中則是順序地編排在卷三二《雅樂》上,更便於直接采錄轉引。
誌文中的“麟德二年十月制曰”以下,至儀鳳三年(678)七月以前的記述,《通典》在卷一四七《郊廟宮懸備舞議》,《唐會要》在卷三二《雅樂》上。
以下記“乾元元年”事,見《唐會要》卷三三《雅樂》下;記“貞元間”事,見《唐會要》卷三三《諸樂》;記“大和三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見《唐會要》卷三三《凱樂》。
這都是超出《通典》記事下限的部分。
《誌》二主要本於《通典》卷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的《樂》四、《樂》五、《樂》六的各篇,並參取了前後《會要》。
惟其記“廣明”以後事,直至結尾,與今本《唐會要》卷三三《雅樂》下所記“廣明”以後事全同。
蘇冕《會要》、崔鉉《續會要》記事下限分別為德宗、宣宗,而王溥《唐會要》後晉時根本就沒有形成。
誌中的這段記事與今本《唐會要》的這段文字,顯然同出一源,即昭宗時修奉樂懸使、宰相張浚及太常博士殷盈孫等修定樂懸的論議、奏疏。
其《誌》三、《誌》四,則不本於《通典》及前後《會要》,似為後晉太常所保存或搜集的“諸廟樂章舞名”,這在後晉纂修《舊唐書》的總體籌劃當中是有明確規定的。
當然,有些是早已匯集成冊的,如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絳令太常博士、太樂、郊社令等員“銓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為五卷”。
也有收入文集當中的,如武則天大享昊天樂章十二首、享明堂樂章十二首,等等。
這類樂章之書,有些今天尚可見到,有些只能借助本誌知其大概了。
《新唐書》合禮樂為一誌,樂附於禮,僅二卷,較本誌減少一半篇幅。
寫到這裏,應當提出今本《唐會要》來說一說,因為下面還會多次涉及。
通常所說今本《唐會要》,是指“武英殿聚珍版書”所收,僅缺卷七、卷八、卷九、卷十,是現存最完整的王溥新編全本《唐會要》。
王溥新編,是在蘇弁、蘇冕兄弟《會要》四十卷、崔鉉監修的《續會要》四十卷基礎上,采集宣宗以後政事,重加厘定所成,共計一百卷。
元明之際,蘇氏、崔鉉前後兩次所修《會要》亡佚,王溥新編也出現錯雜和缺卷。
從以上的對照和下面的對照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認識:
凡今本《唐會要》與《舊唐書》中記事內容、敘述文字全同者,都可以說是蘇氏《會要》或崔鉉《續會要》原文。
反轉過來,又證明王溥新編《唐會要》,對於蘇氏、崔鉉兩《會要》很少改動,只是補續宣宗以後要事。
這對我們認識今本《唐會要》的史料價值,也有間接意義。
《歷誌》三卷,應當是本於韋述《唐書》。
其序文雖然追述了肅宗《至德歷》、代宗《五紀歷》、德宗《正元歷》、憲宗《觀象歷》,並稱“其法今存”,但緊接著寫道:
“前史取傅仁均、李淳風、南宮說、一行四家歷經,為《歷誌》四卷。
”所謂的“前史”,既有《歷誌》,又包括一行歷經的,只能是韋述的紀傳體《唐書》。
其傅仁均歷經,是指高祖時《戊寅歷》,行於太宗之世。
李淳風歷經,即《麟德歷》,行於高宗之世。
南宮說歷經,即《景龍歷》,為中宗時所造。
一行歷經,即《大衍歷》,行於玄宗之世。
由於《景龍歷》“不經行用,世以為非”,後晉史官“略而不載”。
他們“但取《戊寅》、《麟德》、《大衍》三歷法,以備此誌。
”本誌的史源,序文交待得再清楚不過了。
《新唐書•歷誌》較本誌大增,通記唐代二百九十余年八次修改歷法,還備錄了一行《歷議》十二篇,補充了反映中外歷法交流的《九執歷》及翻譯情況。
有關“三歷法”的記載,兩書誌當互校。
《天文誌》二卷,大部分內容、文字都與今本《唐會要》卷四二、四三、四四的相關記載同。
《誌》上自“玄宗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詔沙門一行改造新歷”,至“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收置於集賢院,不復行用”的大段文字,與《唐會要》卷四二《渾儀圖》載(開元)“九年,太史頻奏日蝕不效”以下文字全同。
誌中所載“諸州測景尺寸”,自林邑國至蔚州橫野軍,除無河南府外,其余與《唐會要》卷四二《測景》相關部分,不僅正文相同,連小註也都一樣。
《誌》下“災異”中關於日蝕的文字,與《唐會要》卷四二《日蝕》的記載同,只是無宣宗以下的情況。
這更加證明,本誌是采自宣宗初年以前成書的《會要》、《續會要》了。
其中的小有不同,當是輾轉鈔錄中的疏略所致。
關於彗星、五星臨犯、星聚、流星、雜災變等,大體與《唐會要》卷四三《彗孛》、《五星臨犯》、《星聚》、《流星》等類目前半部分的記述相同,是采自蘇氏《會要》相關文字纂成的。
《誌》下的“災異編年,至德後”這一部分,則超出《唐會要》所記,不少內容都見於各帝紀。
這一部分內容,極可能是後晉史官以肅宗至武宗各帝實錄為線索,再參照《續會要》及司天臺有關記載,綜合編纂而成。
說到《誌》下一定參照了《續會要》,還有一條鐵證未曾被人註意過。
在誌的結尾部分,有一項敘述太史局、司天臺沿革、設官的內容。
這本來是《職官誌》的內容,在《職官誌》二秘書省有詳細記述。
何以《天文誌》下會有此一項敘“舊儀”的文字呢?
原來,《唐會要》卷四四在記述各項災異之後,專有《太史局》一目。
稍加對照,便知《天文誌》下的“舊儀”,是直接節錄《太史局》之文而成。
《新唐書•天文誌》雖多一卷,但兩書誌互有詳略,可以彼此補充訂正。
《五行誌》一卷,記地震、山崩川竭、水災、雷電風雪、蟲災、火災及雜災變等,大體見於《唐會要》卷四二《地震》,卷四三《山摧石隕》、《水災》上,卷四四《水災》下、《木冰》、《螟蜮》、《火》、《雜災變》及卷二八《祥瑞》等目類。
除火災有一條“大順二年”事外,其余各事下限都無超出“大中七年”《續會要》成書這一年的。
據此,本誌也當是以前後《會要》為主要史源,並參取各帝實錄、有關奏疏而成。
《新唐書》增為三卷,所記災害現象超過本誌。
《地理誌》四卷,篇幅最長,雖其序文稱“今舉天寶十一載地理”,但誌中記府、州沿革,一般都是起武德,至乾元,然後列“舊領縣”、戶、口,再舉天寶戶、口。
以這樣的體例推測,最有可能采錄於韋述《唐書•地理誌》,起高祖,至代宗。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本誌與《通典•州郡典》、《唐會要•州縣改置》以及《元和郡縣圖誌》,寫法都不相同。
而賈耽的《貞元十道錄》雖然也是四卷,與本誌分道、卷數相同,但卻不見於《賈耽傳》,後晉史官似未見其書,甚至不知有此書。
兩個方面的推測,都無法排除本誌以韋述《唐書•地理誌》為史源的可能性。
誌中個別地方記事,有至唐末者。
如《誌》一陜州大都督府,自隋義寧元年,寫至唐哀帝即位。
這是因為,廣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犯京師,“車駕幸陜州”,以為大都督府;天右初,昭宗“駐蹕陜州,改為興德府”;哀帝即位後,又復為大都督府。
這些都與皇帝的行蹤直接關聯,因而破例記述,並源於實錄,取材最方便。
《新唐書•地理誌》更為完整地反映唐代地理沿革情況之外,主要是在地誌編纂體例方面的成就。
就考察唐代地理沿革而言,兩誌誰也無法取代誰。
《職官誌》三卷,主要記述代宗以前設官情況,但又未取韋述《唐書》。
《誌》一“錄永泰二年官品”,《誌》二、《誌》三的許多文字直接錄自《唐六典》及當時尚存的《宮衛令》、《軍防令》等。
代宗以後的制度,以德宗朝的變革補入最多。
在“武官”一項中,記左右神策軍、左右神威軍、六軍統軍、十六衛上將軍,基本都是補述的德宗貞元年間的制度,主要采錄的是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