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讲稿.docx
《词汇讲稿.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词汇讲稿.docx(4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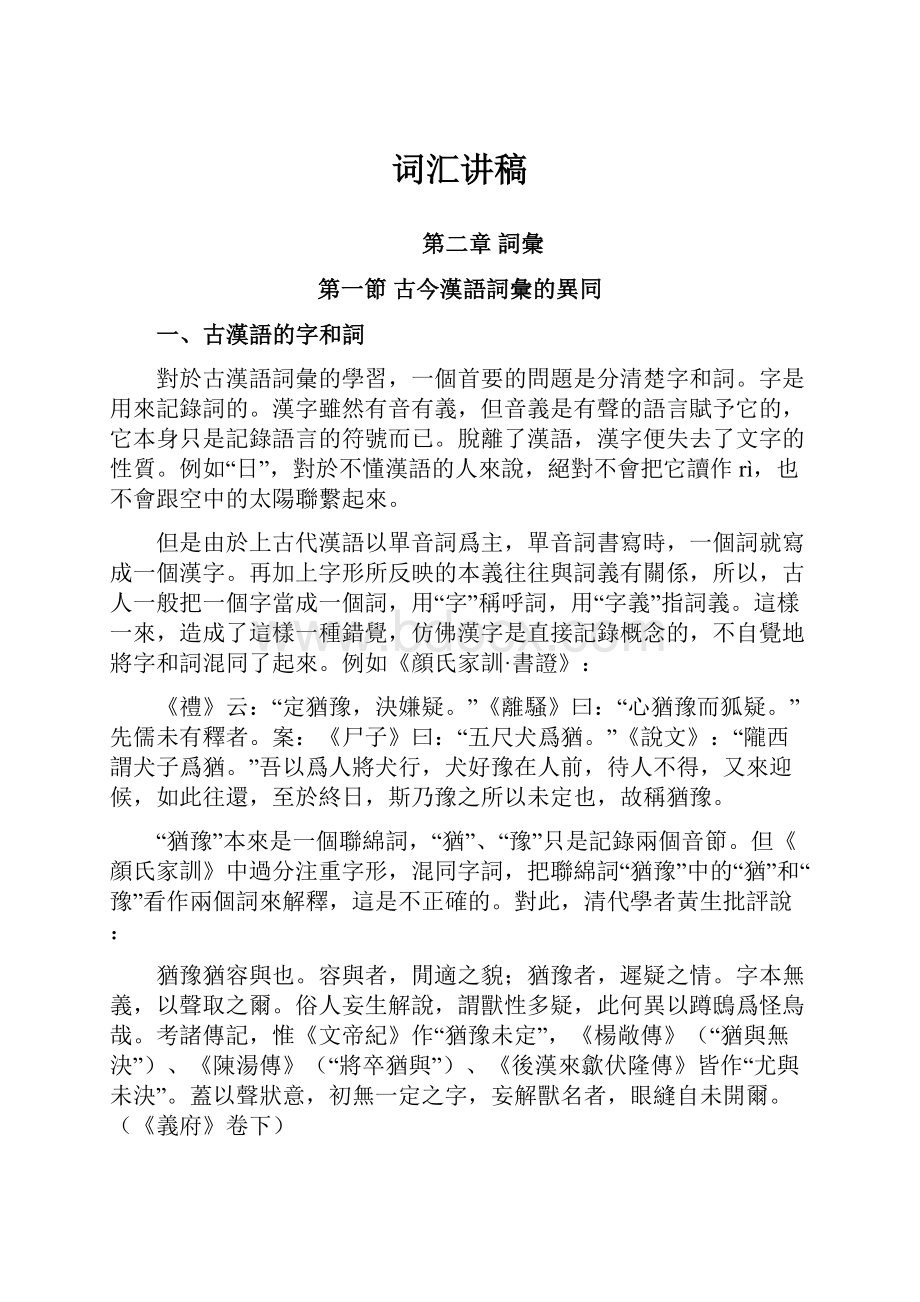
词汇讲稿
第二章詞彙
第一節古今漢語詞彙的異同
一、古漢語的字和詞
對於古漢語詞彙的學習,一個首要的問題是分清楚字和詞。
字是用來記錄詞的。
漢字雖然有音有義,但音義是有聲的語言賦予它的,它本身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而已。
脫離了漢語,漢字便失去了文字的性質。
例如“日”,對於不懂漢語的人來說,絕對不會把它讀作rì,也不會跟空中的太陽聯繫起來。
但是由於上古代漢語以單音詞爲主,單音詞書寫時,一個詞就寫成一個漢字。
再加上字形所反映的本義往往與詞義有關係,所以,古人一般把一個字當成一個詞,用“字”稱呼詞,用“字義”指詞義。
這樣一來,造成了這樣一種錯覺,仿佛漢字是直接記錄概念的,不自覺地將字和詞混同了起來。
例如《顔氏家訓·書證》:
《禮》云:
“定猶豫,決嫌疑。
”《離騷》曰:
“心猶豫而狐疑。
”先儒未有釋者。
案:
《尸子》曰:
“五尺犬爲猶。
”《說文》:
“隴西謂犬子爲猶。
”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未定也,故稱猶豫。
“猶豫”本來是一個聯綿詞,“猶”、“豫”只是記錄兩個音節。
但《顔氏家訓》中過分注重字形,混同字詞,把聯綿詞“猶豫”中的“猶”和“豫”看作兩個詞來解釋,這是不正確的。
對此,清代學者黃生批評說:
猶豫猶容與也。
容與者,閒適之貌;猶豫者,遲疑之情。
字本無義,以聲取之爾。
俗人妄生解說,謂獸性多疑,此何異以蹲鴟爲怪鳥哉。
考諸傳記,惟《文帝紀》作“猶豫未定”,《楊敞傳》(“猶與無決”)、《陳湯傳》(“將卒猶與”)、《後漢來歙伏隆傳》皆作“尤與未決”。
蓋以聲狀意,初無一定之字,妄解獸名者,眼縫自未開爾。
(《義府》卷下)
在古代文獻中,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字記錄的就是一個詞,字和詞具有一定的對應關係。
但並非所有字和詞都是一對一地對應。
在不少情況下,古代漢語的字,不等同於詞。
具體表現爲:
同一個字形記錄不同的詞;同一個詞用不同字形記錄。
這就是“同字異詞”和“同詞異字”。
(一)同字異詞
造成同一個字形記錄不同的詞的原因大致有下面幾種:
1.假借
(1)本無其字的假借。
例如:
夫——夫1(成年男子)、夫2(指示代詞)、夫3(語氣詞)
“夫”字本爲表示“成年男子”的這個詞造的字。
例如《詩經·秦風·黃鳥》: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特:
傑岀者)即其例。
漢語中表示“指示代詞”和“語氣詞”的詞,本無其字,但人們並沒給它們造字,而借用表“成年男子”的“夫1”記錄。
例如《戰國策·齊策四》:
“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
”此爲夫2(指示代詞)。
《論語·子罕》:
“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
”此爲夫3(語氣詞)。
這樣一來,造成“夫”一字多詞。
來——來1(小麥)、來2(動詞,來往的來)、來3(語氣詞)、來4(表約數)
《詩經·周頌·思文》:
“貽我來麰。
”麰,大麥;來,小麥。
“來”字本爲此詞而造,可是常假借作下面一些詞的符號。
來2(動詞,來往的來)。
《論語·陽貨》:
“來!
予與爾言。
”又來3(語氣詞)。
《戰國策·齊策四》:
“長鋏歸來乎!
出無車。
”又來4(表約數)。
《祖堂集》:
“這裏有三百來衆。
”
(2)本有其字的假借,即通假。
例如:
畔——畔1(田界)、畔2(背叛)
畔1本用來表示“田界”。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
”記錄“背叛”義的字本有“叛”字,可是古人本有其字而不用,通假記錄“田界”義的“畔”來表示。
例如《孟子·公孫丑下》: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這樣一來,“畔”一字表二詞。
矢——矢1(箭)、矢2(屎)
記錄“屎”的字本有“屎”字,可是古人經常不用它,通假記錄“箭”的“矢”字來表示。
如《莊子·人世間》: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矢”字身兼矢1(箭)、矢2(屎)兩項功用。
2.同形字
分別爲不同詞造字,有時碰巧會形體相同,這樣也會造成同字異詞現象。
例如:
怕(bó)——怕(pà)
《說文·心部》:
“怕,無爲也。
从心,白聲。
”這是淡泊之“泊”的本字。
如敦煌寫經《法句譬喻經》:
“不如寂靜無求,無欲憺怕。
”懼怕、擔心之義的“怕”是淡泊之“怕”的同形字。
如敦煌寫經《報慈母十恩經》:
“血成白乳與兒飡,由(猶)怕更饑寒。
”
姟(ɡāi)——姟(hái)
“姟”,古數名,萬萬兆曰姟。
《國語·鄭語》:
“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
”孩子的“孩”,俗寫時替換偏旁,寫作“姟”,這樣就和表示數名的“姟”同形。
例如敦煌寫經《大般涅槃經》:
“譬如女人産育一子,嬰姟得病,是女憂惱。
”“姟”在古文獻中也是一字二用。
有時由於字體的演變,原來形體不同的字,後來變成了同形字。
例如:
胄1(甲胄)-胄2(胄裔)
甲胄的“胄”,《說文》說是“从冃由聲”。
胄裔的“胄”,《說文》說是“从肉由聲”。
漢字隸變後,“冃”和“肉”都變作“月”,因此表“甲胄”,表“胄裔”同用“胄”字。
3.派生未造新字
一個詞由於詞義的引申,由甲詞派生出乙詞來,但乙詞的書寫形式仍然用甲詞的,於是就造成同字異詞。
例如:
快1(快意)——快2(快捷)
《說文·心部》:
“快,喜也。
”快本義是心情舒暢,此爲快1。
宋玉《風賦》:
“快哉此風。
”由此輾轉引申爲“快捷”義,此爲快2。
如《梁詩》: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
”快1、快2是意義有聯繫的兩個詞,但都用一“快”字記錄。
有些派生詞雖然仍用源詞的書寫形式,但讀音會發生變化。
如:
說1(shuō)——說2(shuì)——說3(yuè)
說1,說明,解釋。
《論語·八佾》:
“成事不說。
”說2(shuì),說服。
《孟子·盡心下》:
“說大人,則藐之。
”(要說服諸侯,就得輕視他)說3(yuè),喜悅。
《論語·學而》: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3後來在形體上也發生變化,寫作“悅”。
4.簡化合用
書寫形式本不相同的詞,有的在實行簡化字後合用一個字了,從而造成一字多詞。
例如:
后——后(帝王)、後(後面)
古籍中的“后”字,都表示“帝王”義。
例如《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殽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正是其例。
“後”的本義是走在後面,落在後面。
《論語·先進》:
“三子者出,曾皙後。
”簡化漢字時,“後”字的簡體利用了同音的“后”字。
如果用簡化字,“曾皙後”就寫作“曾皙后”。
這樣“后”就會記錄兩個詞。
在古漢語中“后”、“後”有別,我們決不能反過來把“皇天后土”寫作“皇天後土”。
复——復、複
復,復反義。
《左傳·僖公四年》: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複,重複義。
陸游《遊西山村》: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簡化漢字時,復、複二字都簡化爲“复”,記錄兩個詞。
(二)同詞異字
造成同一個詞用不同字形記錄的原因大致有下面幾種:
1.異體字
一個詞由音義和功能相同的異體字記錄,會造成同詞異字。
例如:
“絲線”——綫、線、綖
唐祖詠《七夕》:
“向月穿針易,臨風整綫難。
”“綫”改換聲符作“線”、“綖”。
北本《大般涅槃經》:
“作舍取泥,不取縷線。
”其中的“線”,南本《大般涅槃經》作“綖”。
“綫”、“線”、“綖”三字記錄“絲線”這個詞。
此外,如遍徧、睹覩、溪谿、啼嗁、烟煙、譌訛、蹟迹、村邨、鞍鞌、雜襍等都屬於這種情況。
古漢語中的聯綿詞往往有多種寫法,這也應算同詞異字。
例如“匍匐”是一個雙聲聯綿詞,是趴在地上爬行的意思,它有多種同音書寫的形式。
如《詩經·邶風·谷風》: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戰國策·秦策一》:
“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
”又作匍百、腹拍。
《秦和鍾銘》:
“高引有慶,匍百四方。
”敦煌《央掘摩羅經》:
“廚監惶怖,腹拍王前,‘若王原罪,乃敢實說。
’”
其他的聯綿詞,如委蛇(逶迤、委佗、委移)、躊躇(踟躕、峙躊、躑躅、躕躇)、旁徨(彷徨、傍徨、旁皇、方皇)等,往往都有多種書寫形式。
2.通假
前面說過,本有其字的假借(即通假)可以造成同字異詞。
這是從通假字的角度看的。
如果從本字的角度看,通假也可以造成同詞異字。
例如:
《論語·陽貨》:
“歸孔子豚。
”“歸”爲假借字,本字爲“饋”。
“歸”、“饋”記錄同一個詞。
《戰國策·秦策一》:
“面目犁黑,狀有歸色。
”“歸”爲通假字,本字爲“愧”。
“歸”、“愧”記錄同一個詞。
此外如伸信、修脩、飛蜚、矢誓、矢屎等,都屬本字和通假字記錄同一個詞的情況。
3.區別字
由於詞義引申或文字假借,往往造成一個漢字有“兼職”現象。
如果不造字分化職能,則會造成同字異詞。
如果造字分化職能,常在該漢字上添加偏旁以示區別,加偏旁的字叫區別字。
加偏旁的區別字和未加偏旁的本原字多屬同詞異字這種情況。
例如“昏”本義是日色昏暗,引申爲昏亂,如《呂氏春秋·誣徒》:
“昏於小利,惑於嗜欲。
”又引申爲結婚(古代婚禮多在黃昏舉行),如《漢書·晁錯傳》:
“男女有昏,生死相恤”。
起初本義、引申義都用“昏”字表達,後來分別寫作“昏”、“惛”、“婚”。
“昏”和“惛”、“昏”和“婚”都是同詞異字現象。
此外如“辟”的本義是“法”,但古籍中常借它記錄一些音同、音近的詞。
如《左傳·成公二年》:
“旦辟左右。
”(表躲避)《商君書·弱民》:
“農辟地。
”(表開闢)《史記·范雎傳》:
“秦地辟遠。
”(表偏僻)《戰國策·齊策》:
“不使左右親近便辟。
”(表寵嬖)一個“辟”字職務繁重,詞義容易混淆,所以後來分別加上偏旁,寫成“避”、“闢”、“僻”、“嬖”來分擔職務。
這樣“辟”和“避”、“辟”和“闢”、“辟”和“僻”、“辟”和“嬖”構成同詞異字現象。
二、古代漢語詞彙的特點
古代漢語(主要指上古漢語)詞彙的主要特點是單音節詞佔絕對優勢。
這一點我們把文言翻譯成現代白話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例如《論語·學而》中有一段話,用現代白話翻譯就是:
孔子說:
“學習了又時常溫習,不是很愉快嗎?
有朋友從遠方來,不是很令人高興的嗎?
人家不瞭解我,我也不怨恨,不也是一個有德的君子嗎?
”
但《論語》的原文是:
子曰: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
相比較,最大的不同就是文言字數要少一些。
其根本原因就是現代譯文中的許多複音詞在古代漢語中都用單音詞表達。
因此,我們在閱讀古文獻時,碰到兩個單音詞連用,不要誤認是複音詞。
例如:
人不學,不知道。
(《禮記·學記》)——知,瞭解;道,道理。
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史記·項羽本紀》)——地,土地;方,方圓。
雖然,猶有未樹也。
(《莊子·逍遙遊》)——雖,即使;然,這樣。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
(司馬遷《報任安書》)——夫,發語詞。
妻,妻子;子,兒女。
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
(《晏子春秋·內篇》)——其,它的;實,果實。
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墨子》)——所,輔助性代詞;以,介詞。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然,這樣;而,卻。
古漢語經歷了一個很長的發展演變過程。
當單音詞連用的結構使用較長時間後,人們因循使用,不再辨析它的內部結構,而只作爲一個整體來認識使用,它就逐漸成爲一個詞。
在古代漢語中,這些雙音節的、現代漢語當作一個詞的,什麽時候是詞組,什麽時候已成爲詞,這是目前“詞彙化”研究所關心的問題。
結構和詞的區別,可以從意義結構、結合關係的密切程度、詞重音、語法上的搭配等手段檢測判定。
例如“妻子”,當它表示妻和子女時,是單音詞連用;當它表示丈夫的配偶時,是雙音詞。
“人不學,不知道”中的“知道”是單音詞連用。
後來“知道”後面可以帶賓語了,“知道”就結合成了一個雙音節動詞。
“洗澡”,“洗”本是洗腳,“澡”本是洗手,“洗澡”是聯合式詞組,現在變成一個詞,動作的對象擴大了,而且可以說“洗澡了”,“洗一個澡”。
“休息”,起初是單音詞連用,作一個雙音詞,“息”字輕讀了。
再如上文所舉的“所以”和“然而”,在下面的例子中可以認爲已經凝固爲詞了。
過燥則堅,過雨則泥,所以宜速耕也。
(《齊民要術·早稻第十二》)——所以,因果連詞。
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
(《韓非子·內儲說上》)——然而,轉折連詞。
古代漢語雖然以單音詞爲主,但幷非沒有複音詞。
由單音走向複音是漢語詞彙發展的內部規律之一。
上古漢語複音詞的構成方式有如下幾種:
1.單純複音詞
單純複音詞雖由兩個音節構成,但只包含一個語素。
單純複音詞又可分爲:
(1)雙聲疊韻:
如踟躕(躊躇、躑躅)、恍惚(荒忽、慌忽)、逍遙(消搖)、侏儒(朱儒)、輾轉等等。
(2)非双聲叠韵:
如蝌蚪(科斗)、滂沱等等。
單純複音詞前人又稱爲聯綿詞。
聯綿詞的特點要從字形、聲音、意義三方面分析。
字形上,往往一個詞有多種書寫形式,如彷徨、仿偟;又如逶迤、委蛇、委遟、委移、旖施。
它們的聲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字形上主要是改變形符。
聲音上的特點是,多數是兩個音節之間爲雙聲或疊韻關係。
如“彷”“徨”二字古音都是陽部。
“委”“迤”二字古音都是歌部。
同一個詞的不同字形,聲音都是相同(或相近)的,所以認爲它們是一個詞。
意義上的特點最須注意,聯綿詞表現的是一種意義特徵。
如“委迤”表示彎曲延續的樣子,“仿徨”表示來回反復的樣子。
一個詞,由於字形多變,兩個音節結合緊了,聲音也會轉移,使用時不能依字形來認識意義,也不能根據不同的偏旁、不同的音符來分別其間的意義類別。
所以,一般地說,聯綿詞的意義,不能從字形上去把握,而只能從不同字形體現出的共同的聲音上去把握。
否則就往往會“望文生義”。
如《莊子·秋水》中的“望洋”: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爲疊韻聯綿詞,描摹迷惘直視的樣子。
字又作“望羊”“望陽”。
有人望形生訓,把“望洋”解釋爲“望着海洋”,這是不對的。
2.重言詞
重言詞就是重複兩個音節構成的複音詞。
可分兩類:
(1)單音與詞義無關:
如關關、伎伎(qíqí,從容舒展貌)、契契(憂愁苦悶的樣子)等等。
(2)單音與詞義有關:
如皎皎、巍巍、乾乾(自強不息貌。
《易·說卦》“乾,健也。
”)等等。
3.合成詞
合成詞由兩個或兩個以上語素構成,包括派生詞和複合詞兩大類。
(1)派生詞
派生詞就是附加式的合成詞。
如有夏、有衆、莞爾、勃然、反而、沃若、忽焉、復當、聊自等等。
(2)複合詞
複合詞可以根據組成成分間的語法關係分爲聯合、偏正、支配、陳述等形式。
例如干戈、得失、俯仰;四海、後生;將軍、折中;肢解、自殺等等。
聯合式的複合詞(通常是反義並列型的)有時偏用其中一個語素的意義,另一個並不表義,僅僅是一種陪襯,這就是所謂“偏義複詞”。
例如:
①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
②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
(漢樂府《孔雀東南飛》)
③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諸葛亮《出師表》)
④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
(《墨子·非攻》)
例①“去留”只有“去”義,“留”不表義。
例②“作息”只有“作”義,“息”不表義。
“作”是指勞作,即做事,“息”是指休息,不可能晝夜勤休息還會縈苦辛。
例③“異同”只有“異”義,“同”不表義。
因爲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賞罰便應一視同仁。
“不宜異同”便是應該相同的意思。
不可能既要求相同,又要求不同,否則便自相矛盾了。
例④“園圃”只有“園”義,“圃”不表義。
因爲古代“園”是種樹的地方,“圃”是種菜的的地方。
“竊其桃李”只能是“園”,而不是“圃”。
兩個意義相關相類的語素組合在一起,也會産生偏義現象,前人把這類複合偏義稱作“連類而及”。
例如:
①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禮記·玉藻》)
②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周易·繋辭上》)
③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孟子·離婁下》)
④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
(张若虛《春江花月夜》)
例①“車馬”只有“車”表義,“馬”不表義,因爲車可製造,馬卻不是可造之物。
例②“風雨”只有“雨”表義,“風”不表義,因爲潤物的只是雨,不是風。
例③“三過其門而不入”是禹的事,與后稷無關,“稷”是連類而及,只是一種陪襯。
例④“魚龍”中的“龍”也是“連類而及”。
三、古今詞義的異同
●基本詞彙的意義古今基本相同。
●由於文字假借、詞義引申等原因,少量的古今意義完全不同。
●大量的一般詞彙的意義古今有聯繫,又有發展,同中有異。
語言的詞彙是發展變化的。
社會的進步和人們認識的變化等因素,導致語言中新詞産生,舊詞死亡,使用着的詞有不少在意義上也逐漸有所改變。
我們今天閱讀古書,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古今詞義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
因此,正確認識和掌握古今詞義演變的有關知識,是十分必要的。
在漢語中,有一些詞是古今都用的,如有些自然現象的名稱(風、雨、雪、冰、水、火等),親屬的名稱(父、母、兄、弟等),肢體的名稱(心、耳、手、口、腹等),方位(前、後、左、右、上、下等),性質(大、小、輕、重、長、短等),它們都屬於基本詞彙,這些詞從古到今基本意義都相同,對於我們閱讀古書不會成爲障礙。
右:
右派。
(義項有增減)
在基本詞彙中,有一些詞,如“筆”,古代主要指毛筆,現代有各種各樣地筆(鋼筆、鉛筆、電子筆等),再如“鐘”,古代指一種樂器(如成語“鐘鳴鼎食”),現在指鐘錶。
“筆”和“鐘”的詞義古今有沒有變化呢?
這就需要借助語義場理論具體分析。
筆古:
[書寫或繪畫]+[工具]
今:
[書寫或繪畫]+[工具]
筆的材料和種類古今是有所不同,但這都屬於所指本身發生的變化,而筆這個詞古今都處在“工具”這個語義場中,所以它的詞義並未發生變化。
(義項基本相同)再看“鐘”:
鐘古:
[敲擊]+[樂器]
今:
[牆上/桌上]+[計時器]
我們看出,鐘在古代和“磬”、“鼓”、“笛”等同屬表樂器的語義場,而現在和“表”等同屬於計時器的語義場。
它和相關詞的對立關係,或者說在語義場中的位置發生了變化。
“鐘”的古今詞義變了。
(義項完全不同)
在漢語中,不少詞的詞義從古到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古書中有些貌似平常的詞,如果不具備一些古漢語知識,是不易理解的。
如: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史記·佞幸列傳》)
是黑牛也,而白題。
(《韓非子·解老》)
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杜甫《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像“年”(收成好)、“題”(額)、“恰恰”(密集貌)的這些意義我們現代漢語中已經沒有了。
漢語中大多數的詞古義和今義是既有聯繫又有差別的。
古今義之間的這種關係十分複雜。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觀察古今詞義的不同:
(一)意義的多少不同
一個詞古今意義的多少,往往會産生變化。
有的舊義消亡了,有的新義産生了。
如唱,本義是領唱。
《說文·口部》:
“唱,導也。
”(今用“倡”)《韓非子·解老》:
“竽唱則諸樂皆和。
”後來增加了“歌唱”義(如王勃《滕王閣序》:
“漁舟唱晚。
”),“叫喊”義(如《北史·孫修義傳》:
“居對大衆呼天唱賊。
”)。
再如杜甫《寄高適、岑參》:
“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信將。
”(書:
信;信:
信使;將,傳送)這裏“書”、“信”、“將”三詞的意義爲現代所無。
再比如池,在先秦既有“護城河”的意義(如《孟子·公孫丑下》: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也有“池塘”義(如《孟子·梁惠王》:
“數罟不入洿池。
”)。
發展到現代,減少“護城河”義,保留了“池塘”義,又增“邊高中窪處”義(如“舞池”、“樂池”)。
(二)意義的側重點不同
如“售”,古代漢語中,它側重於行爲的結果,指把商品賣掉。
《廣韻·宥韻》:
“售,賣物出手。
”《詩經·邶風·谷風》: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鄭箋:
“如賣物之不售。
”《大般涅槃經》:
“欲自賣身,薄福不售。
”現在“售”只側重行爲本身,如“售票”、“銷售”等。
“暫”的古義側重於行爲的迅疾,相當於突然、一下子。
如《史記·李將軍列傳》:
“廣暫騰而上胡兒馬。
”後來,它表示時間的短暫。
如韓愈《祭十二郎文》:
“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
”“再”在古代側重於行爲的具體數量,指某一動作行爲實行兩次。
如晁錯《論貴粟疏》:
“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再食”,吃兩次飯。
《史記·項羽本紀》:
“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
”“再拜”,拜兩次。
後來的“再”,則側重於行爲的重複,不限於兩次。
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再如古代的“感激”,側重於內向的感動、激發,現在的感激,側重於外向的感謝。
(三)詞義的輕重和感情色彩不同
詞義在發展中不但古今理性義有差異,而且色彩義也會發生變化。
一些詞在發展中意義的輕重起了變化。
如“恨”的古義是遺憾、不滿。
司馬遷《報任安書》:
“而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私恨”是私下遺憾的意思。
《漢書·蘇武傳》:
“子爲父死亡所恨。
”“亡(無)所恨”即“沒有甚麽可遺憾的”。
“恨”的今義是仇恨。
恨的古義輕,今義重。
而“怨”的古義重,今義輕。
如《史記·秦本紀》:
“繆公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
”這是說秦穆公恨孟明視等三人恨入骨髓,這裏“怨”顯然不是今天的埋怨、不滿,而是仇恨。
再如“處分”一詞在唐以前是“處置”義,如《孔雀東南飛》:
“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唐代産生了“吩咐”義。
如白居易《過敷水》:
“垂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騶且緩驅。
”元明時,産生“責備”義,詞義程度加重。
如《竇娥冤》:
“當罵呵,則處分幾句。
”發展到現代,詞義進一步加重,指對犯了罪或犯了錯誤的人的處理。
也有一些詞在發展中褒貶意義起了變化。
如“下流”,在古代指地位或處境低下,如司馬遷《報任安書》:
“下流多謗議。
”今天則指品德惡劣,並且有明顯的貶義。
“吹噓”在古代用於人事或言語多指替人宣揚、稱揚。
杜甫《寄岑嘉州》:
“馮唐已老聽吹噓。
”(馮唐是西漢人,曾任楚相,武帝舉賢良,有人推薦他,此時他已九十多歲了。
)現在“吹噓”指說大話,並且含貶義。
也有的詞古代含貶義,而現代轉變爲褒義的。
如《漢書·路溫舒傳》: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
”該例是說,治獄的官員用指供的方法引導犯人招供;案子報上去怕被駁回,就玩弄法律文辭對案情進行周密的加工補綴。
周內,即綢紩(zhì),羅織的意思。
“鍛練”在這裏指玩弄法律陷害別人。
後世多寫作“鍛煉”。
現在“鍛煉”一詞不但沒有這一意義,而且在“鍛煉意志”等埸合還含有褒義。
(四)詞義所指的名物制度不同
有一些詞從古到今中心意義沒有甚麽變化,但是由於古今名物制度的差別,它們的所指卻有所不同。
如漢代的膏藥是一種既可內服也可塗敷的膏狀藥物。
如《武威漢代醫簡》中記載的“治千金膏藥方”的用法,就有“吞之”、“涂之”、“摩之”等。
這與後代的膏藥一般只用於敷貼不完全一樣。
《孟子·滕文公上》: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如以今天的尺度去衡量,五尺則不是一般小孩的高度了。
戰國、秦、漢時的一尺約合二十三釐米,比今天的一尺要短。
《孟子·滕文公上》:
“秋陽以暴之。
”這裏是用周曆,周曆的秋相當於夏曆的五、六月,“秋陽”實際是夏天的太陽。
同樣的道理,《孟子·梁惠王上》的“王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和同書《離婁下》的“七八月之間雨集”,都相當於夏曆的夏季五、六月。
再如“坐”,唐代以前坐的姿勢都是兩膝著席或床榻,臀部壓在腳後跟上。
晉人皇甫謐《高士傳》(《三國志·魏書·管寧傳》注引):
“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兩腿向前伸開),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如以今天坐的姿勢去理解,“榻上當膝處”就費解了。
我們把由於古今名物制度的不同造成的詞義差別,也可以稱爲文化義的差別。
要認識這一類古今詞義實指的差異,就需要我們對古代的文化制度和社會生活有一定的瞭解。
【思考與練習】
一、查閱工具書,解釋下列各句中加綫的詞。
有兔斯(斯:
白)首,燔之炮之。
(《詩經·小雅·瓠葉》)
文質份份,然後君子。
(《論語·雍也》)
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孔雀東南飛》)
危身(危身:
人命危脆)不自在,猶如脆瓦坏。
(王梵志《危身不自在》)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
(蘇軾《與孟震同游常州寺舍》)
二、比較下列各組加綫成分的不同。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孟子·離婁上》)
恐有所間,動有規矩,得其所行。
(《太平經》卷一百十二)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莊子·秋水》)
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
(《三國志·吳志·三嗣主傳·孫皓》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