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狗的研究.docx
《一只狗的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只狗的研究.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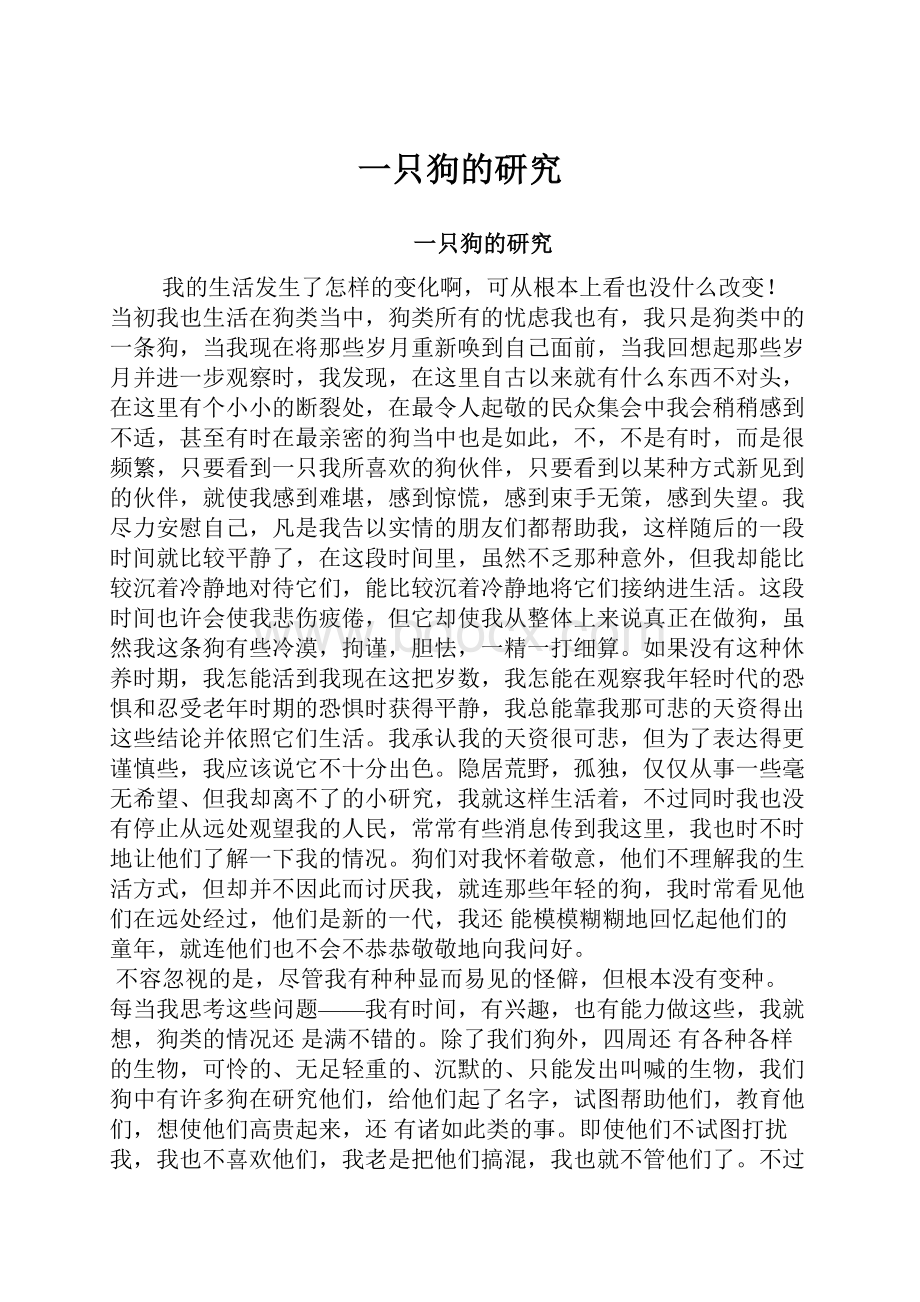
一只狗的研究
一只狗的研究
我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啊,可从根本上看也没什么改变!
当初我也生活在狗类当中,狗类所有的忧虑我也有,我只是狗类中的一条狗,当我现在将那些岁月重新唤到自己面前,当我回想起那些岁月并进一步观察时,我发现,在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什么东西不对头,在这里有个小小的断裂处,在最令人起敬的民众集会中我会稍稍感到不适,甚至有时在最亲密的狗当中也是如此,不,不是有时,而是很频繁,只要看到一只我所喜欢的狗伙伴,只要看到以某种方式新见到的伙伴,就使我感到难堪,感到惊慌,感到束手无策,感到失望。
我尽力安慰自己,凡是我告以实情的朋友们都帮助我,这样随后的一段时间就比较平静了,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不乏那种意外,但我却能比较沉着冷静地对待它们,能比较沉着冷静地将它们接纳进生活。
这段时间也许会使我悲伤疲倦,但它却使我从整体上来说真正在做狗,虽然我这条狗有些冷漠,拘谨,胆怯,一精一打细算。
如果没有这种休养时期,我怎能活到我现在这把岁数,我怎能在观察我年轻时代的恐惧和忍受老年时期的恐惧时获得平静,我总能靠我那可悲的天资得出这些结论并依照它们生活。
我承认我的天资很可悲,但为了表达得更谨慎些,我应该说它不十分出色。
隐居荒野,孤独,仅仅从事一些毫无希望、但我却离不了的小研究,我就这样生活着,不过同时我也没有停止从远处观望我的人民,常常有些消息传到我这里,我也时不时地让他们了解一下我的情况。
狗们对我怀着敬意,他们不理解我的生活方式,但却并不因此而讨厌我,就连那些年轻的狗,我时常看见他们在远处经过,他们是新的一代,我还能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他们的童年,就连他们也不会不恭恭敬敬地向我问好。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我有种种显而易见的怪僻,但根本没有变种。
每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我有时间,有兴趣,也有能力做这些,我就想,狗类的情况还是满不错的。
除了我们狗外,四周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可怜的、无足轻重的、沉默的、只能发出叫喊的生物,我们狗中有许多狗在研究他们,给他们起了名字,试图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想使他们高贵起来,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即使他们不试图打扰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老是把他们搞混,我也就不管他们了。
不过有一点特别明显,因此我不可能注意不到,这就是与我们狗相比,他们很少同心协力,总是怀着某种敌意默默地相互从身边走过,只有最普遍的利益才能把他们稍稍在表面上连在一起,而且就连这种利益也经常引发仇恨和争执。
我们狗则完全相反!
也许可以说,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唯一的群体中,另外,由于在时间的长河中产生的无数巨大差异,我们又是那样各不相同。
全都生活在一个群体中!
这就迫使我们相互走到一起,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对这种强迫心满意足,我们所有的法律和机构,无论是我还依然了解的一小部分,还是我已忘却的绝大部分,都源出于对我们有能力获得的最大幸福的向往,源出于对一温一暖地相聚在一起的向往。
然而现在却恰恰相反。
据我所知,没有一种生物像我们狗这样远远地分散开来生活,没有一种生物有如此众多的、一目了然的等级差别,种类差别,职业差别。
尽管如此,我们在充满激一情的时刻依然成功地一再相聚在一起。
我们怀着相聚在一起的愿望,而远远地分散开来生活的恰恰也是我们,我们从事着古怪的、连邻狗也难以理解的职业,恪守着不属狗类规定的规定,更确切地说是针对狗的规定。
这是些多么困难的事情,谁都不愿沾边的事情——我理解这种观点,与我的观点相比,我更理解它——我完全沉迷于其中的事情。
我为何不像其他狗一样行一事,和我的人民和谐地生活在一起,默默地忍受破坏这种和谐的一切,把它们当作大帐单中的小小失误忽略不计,时刻笑迎能将我们与民众幸福地联在一起的事,对那些非得让我们脱离民众的事——当然它们总是无法抗拒的——则不予理睬。
我还记着我少年时代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处在一种极度幸福又难以解释的兴奋之中,就像每只狗在孩提时代都要经历它一样。
当时我还是只年幼的狗,什么都令我欢欣,什么都与我有关,我觉得,我周围发生着许多大事,而我便是它们的统帅,我必须将我的声音借给它们,如果我不为它们奔跑,不为它们晃动我的身一子,它们只能痛苦地伏一在原地。
现在,孩子的幻想随年岁的增长已无影无踪了。
不过当时它们非常强大,完全左右住了我,到后来自然还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它似乎理所当然要引出一些狂一热的期望。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这种事和更为奇怪的事到后来我常常看都懒得看了,然而它当时给我的印象极为强烈,不可磨灭,它是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为以后的许多印象定向的。
事情是这样,我遇到了一伙子狗,更确切地说,不是我遇到了他们,而是他们朝我走来。
当时我已在黑暗中奔跑了很久,我预感到将要发生大事,那是一种很容易落空的预感,因为我总有这预感。
我在黑暗中奔跑了很久,漫无目的,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到,引导我的仅仅是模模糊糊的渴求。
突然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感到我已经到了地方。
我向上望去,已是明亮的白昼,只是稍有点儿雾气,一切都散发着四下翻滚的醉人气味。
我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向清晨问了好,这时,就好像是我用魔法召来似的,从某一暗处出来了七只狗,同时还发出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可怕的喧闹声。
如果我没看清他们是狗,如果我没看清这喧闹声是他们带来的——尽管我还分辨不清他们是怎么发出来的——可能我会立刻跑开,但我却停住了。
关于那种仅仅赋予狗类、富于创造一性一的乐感,当时我几乎是一无所知,我那慢慢才形成的观察能力在此之前当然也没有觉察到它。
如果自襁褓时代起音乐就是我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时刻充溢着我的四周,什么东西也不能迫使我将它和其它生活分开,只要暗示一下,只要设法用适合孩子理解力的方法向我暗示一下,那这七个大音乐艺术家就会令我更加意外,简直就令我五体投地。
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唱,他们几乎是靠一种顽强的毅力保持着沉默,但却由空空如也的空间变幻出冉冉上升的音乐。
无论什么都是音乐,投足抬脚,回首转头,奔跑休息,彼此之间的位置,彼此间的依序排列,它们大概是一个将前爪搭在另一个的背上,就这样排列起来,因此最前面的得挺一直身一子承受着其他狗的所有重量,他们或是将身一子贴近地面头尾相缠,而且从不出差错。
最后那只狗还不太有把握,他并不总能马上跟上其他的狗,有时也基本上能按着旋律晃动,不过没有把握只是相对其他狗有十分的把握而言的,即使他的把握一性一再差一些,甚至没一点把握,也丝毫影响不了其他狗,即大师们沉着地保持着节奏。
然而我几乎看不见他们,几乎不能一个个全看到。
他们走了出来,我从内心把他们当作狗来欢迎。
我虽然被伴随他们而来的喧闹声搞得稀里糊涂,但他们的确是狗,和你我一样的狗。
我按一习一惯观察他们,就像观察在路上遇到的狗。
我想靠近他们,和他们互致问候,他们也离得非常近。
他们的岁数虽然比我大许多,不属于我这浓密长一毛一类,但在个头和体型上也并不完全陌生,或者是相当熟悉,我认识许多此种类型或相似类型的狗。
我这样沉思时,这音乐声渐渐大起来,简直就抓住了我,把我从这些真正的小狗身边拖开,我完全违心地竭尽全力直立起来嚎叫着,好像我感到了疼痛,我什么别的也不能干,只能听这从四面八方,从高处,从地下,从所有的地方传来的音乐,将听者围在中央的音乐,令人压抑的音乐,劈头盖脑而来的音乐,近得要命也就如同在远处的音乐,似乎还能听见铜号声的音乐。
我又被放开了,因为我过于一精一疲力尽,元气大伤,虚弱得不能再听下去。
我被放开了,看着那七只小狗列起他们的队列,看他们跳跃。
我想和他们打招呼,想请他们教我,想问他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可他们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是个孩子,总以为无论何时都能提问题,而且谁都可以问。
但我刚要开始,刚刚感到与那七只狗建立起了亲密良好的狗的关系,他们的音乐又开始了,搞得我晕头转向,打起了转转,似乎我自己也成了这些乐师中的一个,可我仅仅是他们的牺牲品,我扑过来又扑过去,拼命祈求怜悯,最后终于逃脱了它的控制,因为它把我一逼一进了一堆放得横七竖八的木头里,那木堆在四周耸一起,而我一直没发现,此时它紧紧围住我,压得我低下了头,尽管音乐仍在外面轰鸣,我却有了一个稍稍喘口气的机会。
的确,我惊叹那七只狗的艺术——我理解不了的艺术,不过我不能理解它也不仅仅是由于我的能力——更惊叹他们坦然地将自身完全置于自己制造出的东西之中的勇气,更惊叹他们泰然自若地承受着这些而没被压断脊梁骨的力量。
可当我从我的避难所更仔细地观察时,我看出来,他们奏乐时与其说是镇静,倒不如说是极端紧张,他们的腿在移动时似乎稳健,其实每走一步都因惶恐而不停地一抽一搐,瑟瑟发一抖,他们似乎很绝望,一个个目光呆滞地望着另一个,舌头刚被控制住立即又疲惫无力地从嘴里搭拉下来。
这不可能是因为成功而产生的恐惧,谁敢于这样做,谁做成了这样的事,谁就不会再胆怯——究竟害怕什么?
谁会一逼一迫他们在这里做这种事?
我再也克制不住了,尤其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他们令人费解地需要帮助,于是我就在这一片喧闹中挑战似地大声喊出了我的问题。
然而他们——难以理解!
难以理解!
——不回答,就当我不存在。
对狗的呼唤不做任何答复,这是一种失礼,无论是最小的狗还是最大的狗,都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难道他们并不是狗?
可他们怎么会不是狗呢?
此时,当我更认真地听时,我甚至听到他们低声呼唤着互相鼓励,互相提醒着各种困难,互相告诫别出差错。
排在最后面的是那只最小的狗,大部分呼唤都是冲着他的,我看见他不时偷偷瞟我一眼,仿佛很乐意回答我,但却极力克制着自己,因为这是不允许的。
然而为什么这是不允许的?
为什么我们的法律一直要求无条件做到的事这次却是不允许的?
这使我心中火冒三丈,我几乎忘记了那音乐。
这些狗违背了法律。
无论他们是多么了不起的魔法师,这法律也适用于他们,就连我这孩子对此也理解得一清二楚。
我在那里面还发现了更多的东西。
他们的确有沉默的理由,比方说他们是出于负罪感而沉默不语。
因为当他们表演时,由于震耳的音乐我一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们已没有丝毫廉耻感,这帮可恶的家伙做着既最可笑又最伤风化的事,他们用后脚撑着直立起来。
呸,真见鬼!
他们脱一光身一子,炫耀着自己的一裸一体,还以此感到自豪,每当他们遵从良知将前腿放下片刻,便吓得不得了,好像这是个错误,好像这种天一性一是个错误,于是又赶紧抬起前腿,他们的目光好像在祈求原谅他们不得不稍稍停止了作孽。
这世界颠倒了吗?
我在哪里?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了我自己的生存,我不能再在这里犹豫。
我扒一开一团一团一围住我的木头一跃而出,我要去找那几只狗,我这小学生得做回老师,得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得阻止他们继续作孽。
“这种老狗,这种老狗!
”我不断对自己重复着。
然而当我刚刚自一由、离那些狗仅隔两三步时,那喧闹又开始了,它又降住了我。
这种喧闹我已熟悉,虽然声势可怕,但也许是可以克服的。
但透过这种喧闹,远处持续不断地传来一种声音,它清晰严厉,始终不变,也许它就是这喧闹中的真正旋律,它迫使我跪倒在地,如若不是这样,我努力一下也许可以顶得住这种喧闹。
这些狗奏出如此惑人的音乐。
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教训他们,就让他们叉一开双一腿,就让他们作孽,就让他们诱一惑别的狗犯下默默观看的罪恶吧。
我是一只如此幼小的狗,谁会要求我做如此困难的事情呢?
我变得比实际的我更小,我哀声而号,他们若就此事征询我的意见,我也许会同意他们的做法。
另外,时间过得并不长,他们就消失了,所有的喧闹声也消失了,他们从中现出身来的黑暗中的一切亮光也消失了。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整个这件事并无任何不寻常之处,在漫长的一生中,一只狗会遇到各种事,用一个孩子的眼光从整体上看,它们更令人吃惊。
此外,正如最确切的措辞所说的,此事和所有的事一样,当然不能“乱说”,后来事情就成了这样:
有七个音乐家聚在一起,在清晨的寂静中演奏音乐,一只小狗迷路跑到那里,一个不受欢迎的听众,他们想用特别可怕或特别庄严的音乐把他轰走,可惜没有成功。
他以提问题的方式搅扰他们。
有生狗在场就够受干扰了,难道他们还得接受这种干扰,还得通过回答问题来扩大这种干扰?
虽然法律规定必须答复每一只狗,但一只乱跑的小狗到底算不算应予重视的某狗?
或许是他们压根就没闹清他的话,他提问题的汪汪叫一声大概相当不清楚。
他们也许听懂了他的话并克制着自己做了回答,可他这只不一习一惯听音乐的小狗从音乐中却分辨不出回答。
至于后腿的问题,可能他们确实破例只用后腿走路,这是一种罪过,是的!
然而他们是单独呆在一起,七个呆在朋友中的朋友,在亲密的聚会中,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在自家的四堵墙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根本没有外人,因为朋友不算公众,那里不是公众场合,即使一只好奇的街头小狗在场也不算公众场合,鉴于这种情况,这不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吗?
也不完全是这样,但差不多就是这样,父母应该教育子女少到处乱跑,对此类事情最好保持沉默,要尊重老者。
到了这一步,这桩事情也就了结了。
当然,对于大狗来说已经了结的事,对小狗来说还不算了结。
我四处奔跑,我逢狗便讲,逢狗便问,我控告,我研究,我真想将每只狗都拉到事发现场,给他们指一指,我当时在哪里,那七个家伙在哪里,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跳舞并演奏音乐。
可大家都不理我,讥笑我,如果有谁能和我一起去,我也许会牺牲我的清白,也试着用后脚站立起来,以便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
而现在呢,大家对一只小狗所做的一切都感到生气,但最终还是原谅了他。
但我一直保持着这种天真无邪的本一性一,就这样成了一只老狗。
我对这件事的评价今天就更低了,不过依然和那时一样,对它我还在大声地谈论,还在将它还原成原来的样子,还在和那些在场的狗较量而且毫不顾及我身处其中的社会,总是干着既令我又令其他所有狗感到厌烦的事,然而也恰恰因为如此——这就是区别——我想通过调查研究彻底搞清这件事,以便最终再腾出眼睛去观察平凡、安静、幸福的日常生活。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工作起来完全和当时一样,直到今天也没罢手,虽说少了许多孩子的方法,但区别并不大。
起因也就是那场演奏。
对此我并无怨言,在这里起作用的是我的天一性一,即使没有这场演奏,我的天一性一也一定会另找机会显露自己。
只是事情来得那么快,这让我以前时常感到遗憾,它耗去了我的大部分童年,小狗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有些狗那里能持续好几年,可对我来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
没有关系。
世上有些事比童年更为重要。
可能要到上了年纪,通过一种艰辛的生活,我才能得到超出一个真正的孩子的承受力的童年幸福,不过我以后会得到这种承受力。
当时我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我的调查,材料并不缺乏,真遗憾,它非常丰富,丰富得令我在混沌中感到绝望。
我开始调查狗以什么为生。
可以说,这当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自古以来它就费尽了我们的脑筋,就是我们思考的主要对象,在这一领域里,各种观察、尝试、观点数不胜数,它已成为一门科学,这门科学规模巨大,它不仅超出个别学者的理解力,而且也超出了所有学者的理解力,除了整个狗类,谁也无力承担这门科学,而即使整个狗类还未承担起全部,已被压得气喘吁吁,它在早已占有的旧财富中不停地剥落,因此必须花费千辛万苦去填补它,何况我的研究困难重重,各种条件几乎无法满足。
对这一切大家和我没有分歧,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无意涉足这门真正的科学,我对它怀着它应得到的一切敬意,但要增强这种敬意我还缺乏知识,缺乏勤奋,缺乏冷静,特别是近年还缺乏胃口。
我将食品吞下肚子,可它根本就不值得我从农业角度事先有步骤地观察一番。
在这一方面,一切科学的那句提要就足够我用了,即母亲让孩子离开自己的怀抱投入生活时告诉他们的那个小小的准则:
“尽自己的所能弄一湿一切。
”这里不是的确几乎包容了一切吗?
对我们的祖先开始的这项研究到底还该添补什么重要东西?
各种细节,各种细节,而一切都是那样不可靠。
然而只要有我们狗在,这条准则就将存在。
它关系到我们的主要食物。
毫无疑问,我们还有其它辅助食物,但在非常情况下,只要没到特别悲惨的年龄,我们是能靠主要食物生活的。
我们在地上得到主要食物,而土地则需要我们体内的水分,以这水分为生,仅以这种条件向我们提供食物。
不应忘记的是,狗可以通过各种咒语、歌唱和动作使食物加速出现。
按照我的观点,这就是一切,此事从这个角度基本上再没什么可谈了。
在这方面,我和绝大多数狗观点一致,我严密防止沾惹任何这方面的异端邪说。
的确,我既无特殊之处,也没有固执己见,若能和同类意见一致我总会感到高兴,而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如此。
不过我的活动是在另一个方向进行的。
表面现象告诉我,只要按照科学原则喷洒耕作土地,它就会提供食物,也就是说以什么样的质量和数量,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地方和时间,都要符合完全或部分地由科学规定的法律的要求。
这些我都接受,但是我的问题是:
“土地从哪里获取这些食物?
”一个大家通常总托辞不理解的问题,对此他们顶多回答我:
“如果你吃的不够,我们会把我们的给你一些。
”大家都看重这种回答。
我知道,我们将我们获得的食物拿来分发不是狗类的优点。
生活是艰难的,土地是皱裂的,科学在认识方面显得那么丰富,但在实际成果方面却那么贫乏。
谁有食物,谁就将它保存起来。
这不是自私,而是恰恰相反,这是狗的法律,是一致通过的全民决议,是在战胜自私自利中产生的,因为占有者总是少数。
“如果你吃的不够,我们会把我们的给你一些。
”这种回答是一种常用的客套话,是一种俏皮话,是在逗乐。
这我从未忘记。
但对我更有意义的是,当时我带着我的问题满世界乱跑时,谁也没有这样取笑过我。
虽然我一直都没得到过奉送的食物——叫人家从哪里能立刻拿出来呢,即使赶巧人家手里有,可饥肠饿肚在大发脾气时当然不会想起顾及别的狗——但大家对提供食物还是满认真的,如果我能快得足以抢到手,有时我还真能得到点儿吃的。
我怎么会被另眼相看,我怎么会受到照顾优待?
就因为我是一条瘦弱的狗,营养不一良,对吃的关心得太少?
然而有许多营养不一良的狗在到处流一浪一,如果有可能,甚至连他们嘴边粗劣到极点的食物也会被夺走,这常常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原则。
不,我没受过优待,其实对此我仅有个清晰的印象,因此不可能详细地描绘。
大家不为我的问题感到高兴吗,不认为它们特别聪明吗?
不,他们并没感到高兴,他们以为这些问题全都非常愚蠢。
它们也只能是些使我引人注目的问题。
似乎他们宁愿做出那件难以置信的事,即用吃的塞住我的嘴——他们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想做——也不愿容忍我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能更容易地赶走我,更容易地禁止我的问题。
不,他们没有这种想法,他们虽然不愿听我的问题,但正是由于我的这些问题,他们不想赶我走。
我受到百般嘲笑时,我被看作愚昧的小动物时,我被推来推去时,其实正是我名声大振的时期,后来再也没有出现什么类似的情形,那时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事都可以做,从表面上看是受到粗一暴的对待,其实是在受恭维。
这一切仅仅是由于我的那些问题,是由于我的无辜,是由于我的研究欲一望。
他们是想以此来麻痹我,他们不愿采用强制的方法,而是想用近乎慈一爱一的方式引导我离开一条错误的路,一条其错误一性一还未明确到可以采取强制手段的路,不就是这样吗?
——某种敬意和畏惧也是采用强制手段的障碍。
当时我就有类似的预感,而如今我已一清二楚,比当时这样做的那些狗要清楚得多。
毫无疑问,他们想诱使我离开我的路。
目的并未达到,他们起的作用刚好相反,我更加专心致志。
我甚至发现,事实上我才是那个存心诱哄人家的狗,而且我的诱哄实际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全赖众狗的帮助,我才开始明白我自己的问题。
例如当我追问“土地从哪里获取这些食物”时,如果仅从表面现象看,土地到底用不用我去一操一心?
土地的忧愁与我有无关系?
丝毫没有,正像我很快就认识到的,这与我毫不相干,要我费心的只有狗,除此别无他物。
除狗之外到底还有什么?
在这辽阔空旷的世界上,除狗之外还能呼唤谁?
一切知识,一切问题,一切答复,都存在于狗中。
但愿这知识能发挥作用,但愿这知识能公之于世,但愿他们别明明知道十筐却对外对自己只承认一碗。
还有那最健谈的狗,一旦离开摆着上乘佳肴的地方,就更加沉默寡言。
狗们轻手轻脚围着同伴绕圈子,狗们浑身散发着贪欲,狗们用各自的尾巴相互一抽一打,狗们问着,请求着,号叫着,撕咬着,这才做到了即使不费任何劲也能做到的事:
充满深情的倾听,亲切的触一摸,恭恭敬敬的嗅闻,真挚的拥抱,你我的号叫融为一体,一切都是为了陶醉,遗忘,得到。
但有一样,狗们首先想做到的却依旧没做到:
承认自己的知识。
对于这种请求,无论是默默地还是大声地请求,即使你使出浑身本事去诱呀哄呀,回答你的顶多是麻木的表情,斜视的目光,混浊模糊的眼睛。
当年做孩子时我呼唤那几个狗乐师,可他们却一言不发,与当时的情形相比,现在没有多大变化。
某些狗也许会说:
“你对你周围的狗不满,对他们在这些重大事情上一言不发不满,你认为,他们知道许多,但却不愿全都承认,不愿让它们在生活中全都发挥作用,这种沉默,其原因和隐秘他们自然也一起藏在了沉默之中,毒害了生活,使你觉得难以容忍,你必须改变它,或者抛弃它,也许是这样吧。
但你自己也是一只狗,也有狗的知识,现在就请你把它说出来,只是别用提问的形式,而是得用回答的形式。
如果你将它说出来,谁会和你作对呢?
狗类大合唱将会开始,好像它正翘首以待。
随后你就会得到实情,你就会一清二楚,你就会听到承认,只要你愿意。
这种低等生活的顶盖,你在背地里如此诋毁的顶盖将会敞开,我们大家将狗挨狗升往高处的自一由王国。
假使达不到最后这一步,那情况将比现在更糟,毫不搀假的真实比半实半虚更难以忍受,那些沉默不语的生活维护者将被证实是对的,我们现在还怀抱着的微弱希望将变成完全绝望,这些话是有品味价值的,因为你不愿意按照为你限定的方式生活。
这么说吧,为何你指责人家沉默不语而自己也沉默不语?
”
很容易回答:
因为我是一只狗。
完全和其他狗一样,我严严实实地将自己封闭起来,厌恶自己的问题,出于畏惧而冷酷无情。
难道我向众狗提出问题,准确地说,至迟自我成为成年狗之后,我提出问题难道为的就是让他们回答吗?
我竟抱着这样愚蠢的希望?
难道我看不到我们这生活的基础,预感不到它的深渊,看不到建筑工地和昏暗厂房一中的工人?
我还在期待,按照我提出的问题这一切将会结束,将会毁灭,将会被抛弃?
不,对这些我的确不抱任何期望。
我理解他们,我们身上流淌着共同的血,那可怜、永远年轻、总是充满渴求的血。
然而我们共有的不仅是血,而且还有知识,不仅是知道,而且还有通往这些知识的大门的钥匙。
没有其他狗我也占有不了这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拥有这些。
那些包着最珍贵的骨髓的骨头硬如钢铁,只有所有的狗用所有的牙来一起咬,才能对付得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一种夸张。
只要所有的牙齿都拉好架势,根本就用不着咬,那骨头就会自己裂开,骨髓将无遮无挡地摆在那里,连最虚弱的小狗也能取到手。
如果我还要再接着比喻下去,那就是我的意图,我的问题,我的研究均针对着什么令人恐惧的事情。
我想迫使所有的狗聚在一起,我想让那根骨头在他们已摆好架势的压力下自行裂开,随后放他们去过自己喜一爱一的生活,然后我想独自,远远近近就我一个,吸下那骨髓。
这听起来真可怕,似乎我不仅仅想以一根骨头的骨髓为生,而是要以众狗的骨髓为生。
可这无非是个比喻而已。
这里所说的骨髓不是食物,而是相反的东西,是毒药。
为我这些问题忙得不亦乐乎的也仅仅是我自己,我想用四下里回答我的沉默鼓励我。
正如你通过自己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众狗沉默不语,并将永远沉默,这你能忍受多久?
这你能忍受多久,这就是我真正的终身课题,它超出所有其它个别问题,它只是提给我的,不会打扰任何其他狗。
遗憾的是,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比回答任何问题都容易:
估计我将忍受到我的自然终点,老年人的镇定越来越能抗住这些急躁的问题。
我可能将默默地死去,在一片沉默中死去,近乎宁静地死去,我将泰然自若地面对沉默。
好像是出于恶意,赋予我们狗的心脏强健得令人赞叹,肺绝不会提前用坏,我们抗拒所有的问题,甚至连我们自己的也不例外,这沉默的保垒就是我们。
最近我对自己的生活思考得越来越多,我在寻找我也许曾犯下的大错,应对一切负责的大错,但却没能找到。
可我肯定犯过这错误,如果我没犯过,又勤勤恳恳地干了漫长的一生却仍未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那就说明,我所想达到的目的是不可能的,而且由此将产生彻底的绝望。
看看你这项毕生的事业吧!
起初调查的问题是:
土地从何处获取我们的食物?
一只小狗本来自然会渴望生活的乐趣,而我放弃了所有的享受,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