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docx
《马拉之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拉之死.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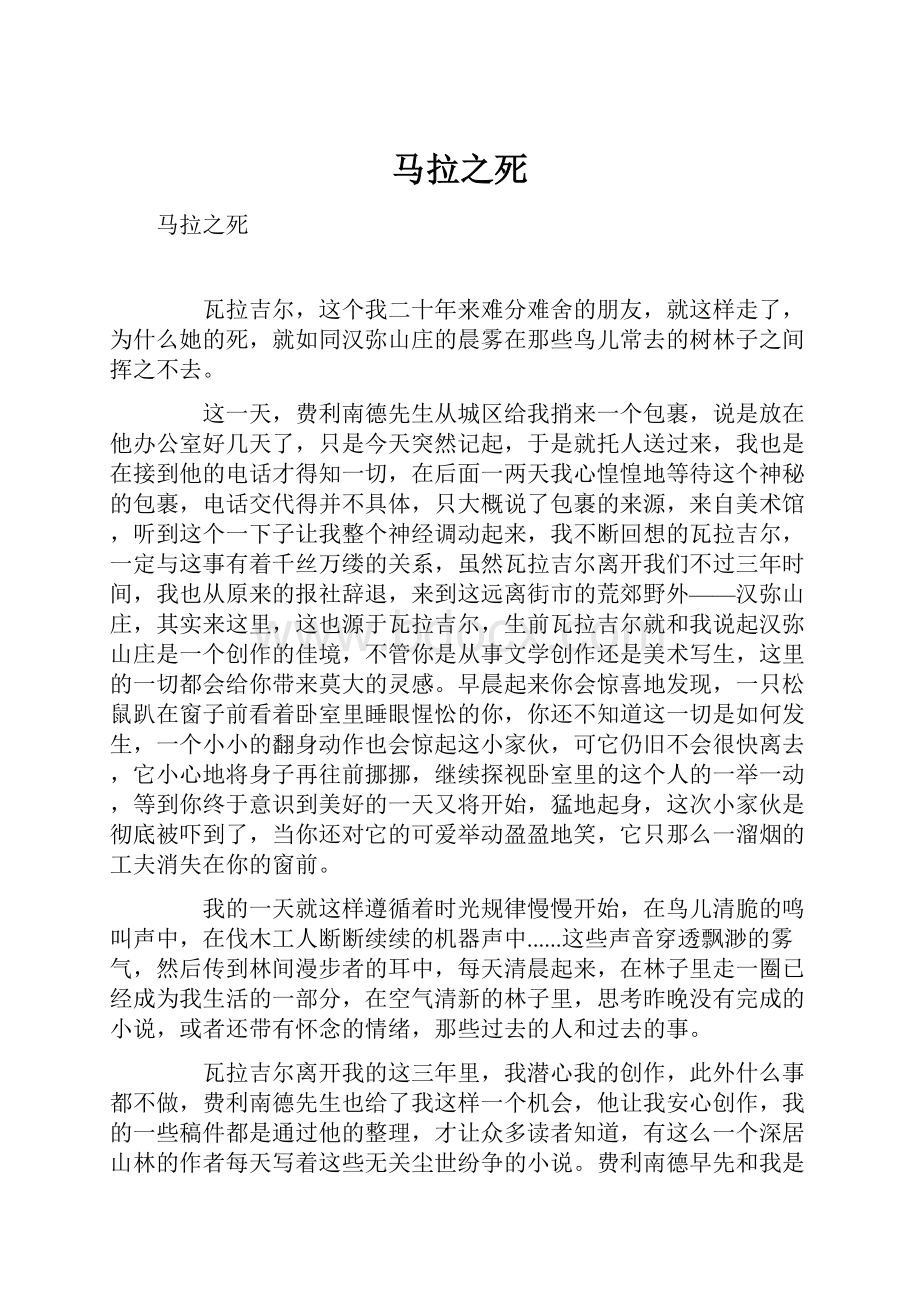
马拉之死
马拉之死
瓦拉吉尔,这个我二十年来难分难舍的朋友,就这样走了,为什么她的死,就如同汉弥山庄的晨雾在那些鸟儿常去的树林子之间挥之不去。
这一天,费利南德先生从城区给我捎来一个包裹,说是放在他办公室好几天了,只是今天突然记起,于是就托人送过来,我也是在接到他的电话才得知一切,在后面一两天我心惶惶地等待这个神秘的包裹,电话交代得并不具体,只大概说了包裹的来源,来自美术馆,听到这个一下子让我整个神经调动起来,我不断回想的瓦拉吉尔,一定与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瓦拉吉尔离开我们不过三年时间,我也从原来的报社辞退,来到这远离街市的荒郊野外——汉弥山庄,其实来这里,这也源于瓦拉吉尔,生前瓦拉吉尔就和我说起汉弥山庄是一个创作的佳境,不管你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美术写生,这里的一切都会给你带来莫大的灵感。
早晨起来你会惊喜地发现,一只松鼠趴在窗子前看着卧室里睡眼惺忪的你,你还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一个小小的翻身动作也会惊起这小家伙,可它仍旧不会很快离去,它小心地将身子再往前挪挪,继续探视卧室里的这个人的一举一动,等到你终于意识到美好的一天又将开始,猛地起身,这次小家伙是彻底被吓到了,当你还对它的可爱举动盈盈地笑,它只那么一溜烟的工夫消失在你的窗前。
我的一天就这样遵循着时光规律慢慢开始,在鸟儿清脆的鸣叫声中,在伐木工人断断续续的机器声中......这些声音穿透飘渺的雾气,然后传到林间漫步者的耳中,每天清晨起来,在林子里走一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在空气清新的林子里,思考昨晚没有完成的小说,或者还带有怀念的情绪,那些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
瓦拉吉尔离开我的这三年里,我潜心我的创作,此外什么事都不做,费利南德先生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他让我安心创作,我的一些稿件都是通过他的整理,才让众多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个深居山林的作者每天写着这些无关尘世纷争的小说。
费利南德早先和我是同事,之前我们就建立了深刻的友谊,通过他结识了很多出版界的人士,他读我的小说,读完之后总会不遗余力地夸耀,如此单纯的心境。
瓦拉吉尔也在生前见过他,她对我说,他给人感觉很和蔼,不像别的报社总编总一副严厉的样子,她还对我说,你在他手下工作就是福分,可我在瓦拉吉尔死后的一个月,还是辞退这份收入还算不错的工作,执意要从事小说,我走的那天,费利南德请我喝了酒,那一晚,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原来费利南德也有和我一样的理想,只不过他无从这样选择,在他身后是四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两位老人。
包裹在第二天到达,我花去一个上午的工夫,思量着这包裹,毫无疑问地来自美术馆,可偏偏是没有寄信人,我想这不会是瓦拉吉尔的丈夫,在后面的几年里,我和他已经断了联系,我关心的是瓦拉吉尔留下的两个孩子,他们已经上小学,这是费利南德先生帮我问到了,我也劳驾费利南德让他给孩子们带去圣诞节的礼物。
包裹的收信人清楚写着瓦拉吉尔身前最好的朋友。
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叠旧照片,和几张素描纸,素描上的全是某位年轻美丽的少女,她回头一弯浅浅的笑,她趴在窗前张望的样子,她那一条长裙贴着草地,画得可真好,原来这就是少女时代的瓦拉吉尔,毫无疑问素描里的,照片上的全是关于瓦拉吉尔,只是那个和她合影的男人,有点生疏,我猜测着这是瓦拉吉尔某个没有和我提及过的异性朋友,可素描和照片一定会有关系的,难道照片里的这个男人就是这些素描作者?
时光把我拉回到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当我读着瓦拉吉尔的信,并以为是这个原因让她真正离开人世,也因为她留给我的那个真相,让我对她的现在的丈夫另眼相看,我常常想,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埋藏自己肮脏的罪行,还能这样镇定,他的身体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把这个归结于上天对他的惩罚,他理应接受,难怪当瓦拉吉尔写下遗嘱让他在美术馆工作,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只是今天见到这些照片和素描画,被再次提及,我突然想到,瓦拉吉尔在她的那封长信中说到,她的初恋情人是一位画家,难道这真的是他的初恋情人为她所画?
我再看照片里的这个男人,面容英俊,身材高大,但他看镜头的眼神却是如此忧郁,他们两站在一起,面对镜头,好一对绝世佳人。
这个时候,令我讨厌地想到瓦拉吉尔现在的这位丈夫,可恶之极,我愤怒地对自己说,就是他,还杀了他,也因为他,瓦拉吉尔才想到死。
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让我来再次重复这句话,对,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杀他,这个平日里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就算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也不会绽放笑容的男人,居然以瓦拉吉尔丈夫的身份杀了她的初恋情人,这事情的最终原委,在瓦拉吉尔死后变成了一个迷,在她死后,我也没有继续追究过,要是之前问一问她现在的丈夫,是否就真的知道了?
可你想这样的事情,怎么能让一个“罪人”开口,何况我不想再和他说任何一句话,到头来。
恐怕事件的真相也只有他知道了吧。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我也正想给费利南德先生打去电话,问个究竟,至少让我知道这个包裹是谁给他的,我跑到楼下,电话还在不断响铃,我接起它,电话里是朋霍费的声音,我报社早年的同事,我正猜测着他打电话来干什么,朋霍费早年还是报社的记者,因为连续几次报道美术馆鬼魂事件而扬名,对于他的印象——是个极具新闻敏锐感的年轻人,他总能找到事件的本源,刨析问题也相当透彻,难怪现在坐到了副编辑的位置,曾经,他也因为美术馆事件试图采访我,只不过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绝中放弃,我当时就想,我如此沉痛地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现在做什么都没有用了,我也需要安静地收拾沉重的心情。
电话那头简简单单地说了几句,说明天要去汉弥山庄拜访我。
挂掉电话,我正思考这是怎么回事,朋霍费恐怕是冲着我今天收到包裹来的?
事隔三年,要是这件事再被提到,会引起怎样的效果,可这其中恐怕有很多人淡忘了,而这位年轻的朋霍费真是一位执着的人,这性格有点像瓦拉吉尔,什么事情都要追根问底。
其实我也想知道,我比任何人都更想知道,年轻的瓦拉吉尔,我的朋友,你在天堂是否事事顺心?
我坐在楼梯的台阶上,一时提不起精神,嘴里念叨着瓦拉吉尔,我无限怀念着瓦拉吉尔,我看到她走到我写字台边上,问我在这里干什么,然后又跑去房间里,把门一关说不要过来。
瓦拉吉尔死了,这已成事实,为什么记忆还阴魂不散,在某个夜里,我拉开窗帘,一个活生生的瓦拉吉尔飘在空中,穿着睡袍,没有表情,看到我之后迅速消失......
第二天,天刚刚亮,如我所料到的,朋霍费早早地就站在我的庄园外等候我出来。
我开门招呼一声让这位年轻人进屋说。
我对这位年轻人所表现出来的礼貌连连称赞,谈过了报社三年来的人事变化,当然谈到了瓦拉吉尔。
我问朋霍费为什么对瓦拉吉尔如此感兴趣,他心有准备地说,不妨让我来告诉你关于我的一件事,在我七岁那年,对美术表现出格外的兴趣,我的母亲将我托付给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让他教我画画,我常常和我的老师,来到汉弥山庄写生,这也是我来这里的一个原因,我们在汉弥山庄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当然对于我的老师来说,也是相当甜蜜的回忆,因为在这里,留有他的初恋,当时我们正在湖边写生,湖水照应着周围的景致,太美了,一个少女从湖边走过,她如此悲伤的脸,绝望的地往湖水的更深处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老师一把抱住这位少女,挽救了少女的生命,从此以后他们相恋了,后来,不幸的是我的老师自杀了......
我打断朋霍费的话说道,很抱歉,朋霍费,可这个与瓦拉吉尔又有什么关联啊。
朋霍费平静地说,因为瓦拉吉尔是我的这位老师的初恋情人。
我听了之后,简直不敢相信,世上竟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我一度地不敢相信,他所说的,要是他所说的是真的,整个事件当中,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他继续说,我的老师是自杀,这正是我怀疑的,在我看来,老师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要是真的是这样,我也对瓦拉吉尔非常怀恨,她当时就在他在身边,完全可以制止,只不过在她身边多了另外一个男人,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所以,这很难说。
经过朋霍费这么一说,我不得把昨天收到包裹交出来,他激动地拿着那些照片说,就是他,就是他,他是我的老师,那年我才七岁,在他们身后便是汉弥山庄再普通不过的木屋了。
我有意地再次打断他,问,可你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热衷?
这也正是我费解警惕的,作为瓦拉吉尔的朋友。
他缓缓地说,这我能理解,我只是为其中一个人的死感到可惜。
说完,朋霍费突然请求我跟他一同寻找照片里所指的那个木屋,他说,这木屋应该离不远,一起去看看好吗?
我默许地答应,只是对突如其来的不敢相信,可这又千真万确,他不可能对我欺骗,他从中没有什么可以捞到,事件只过去的三年,人们早就忘了一干二净,只是那些与之相关的人,恐怕终生也不能忘却。
木屋没有规律地散落在山林的各个方向,这么多木屋究竟那一座才是照片里所指那座,何况二十多年,也有一些木屋被移除了,边走边想,朋霍费凭借他七岁的记忆,带我一直往树林子的更深处走去,我们在一座木桥前停了下来,朋霍费指着对岸,说过了桥你看那里有一间木屋,那个就是我们从前的画室,我们现在先不要过去,你看那绳子都不太牢固,据说这座桥还是我老师建的,他因为对岸环境幽静,便建了这么一座桥,后来发生那件事情以后,就没有人再去过他的木屋,所以这座桥很少人走动,人们也不再顾及它是否牢固。
我拿着照片反复对照,和照片里相差无几,二十年了,还保持着原来的风貌。
我们站在桥这头很久,我问朋霍费,如果你知道了真相却和你所料想的不大相同,会怎么办?
他有些失落地说,前辈,我心中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真相,只不过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们还是回去吧,天好象要下雨了。
回到庄园,由于天气原因,朋霍费暂时在我的住所呆一夜,等到天亮再回巴黎。
这一夜,我从朋霍费那里得知这位老师的事迹,我也给他讲述我和瓦拉吉尔美好的友谊。
朋霍费问我,要是你知道了真相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怎么办?
我停顿了下说,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朋霍费也随声和道,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前辈,我要请求你的原谅,朋霍费在安静的空气中突然开口说话,前辈,我要请求你的原谅,原来失去瓦拉吉尔后,有一个人竟然如此伤心,图书馆鬼魂事件是我一手制造的,三年前的某一天,但这纯属一次偶然,我在美术馆同样看画展,看到一个酷似瓦拉吉尔的女人站在我老师的画前,多么专注的眼神,我试图叫她的名字,瓦拉吉尔——瓦拉吉尔,一遍一遍,她听到有人叫她,突然变得很慌张,她转过身去,在那么多的看画的人群中,实在是看不到我,接着美术馆工作人员将那副画摘走了,她于是回头,看见墙上的画不见了,慌忙跑出美术馆,那个时候,我还在看画的人群里,看着她如此慌张地离开,心里便暗暗升起报复的心理,你可知道,要是她更平静一点的话,我就不会那样做了,她的行为让我感到她就是那个人,杀死老师的人,在此后几天,我费尽心机地打电话给她,写莫名其妙的东西给她,以一个幽灵的口吻,时时骚扰她,她的事迹见报全是我一手操纵,正当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惩治她的罪行,没想到那么快,她居然自杀了,听人说她拔掉医院的输液管,用针扎自己的血管,我悔恨无比。
我把眼睛瞪得比以往都大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就是杀死你老师的人,这不可能,瓦拉吉尔是一个女人,以我和她相处那么多年,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何况他们是恋人。
前辈,请求你的原谅,这一时让你难以接受,除非你有证据,朋霍费说。
证据。
这时我脑子闪现出瓦拉吉尔最后留给我的那封长信,我迅速上楼,找出那封信,它至今还夹在我的一本书里,我将它交到朋霍费的手里,朋霍费问我这是哪里来,我说是瓦拉吉尔生前留下的,他小心地展开信笺,看到上面班驳的字体,再一遍问我,这真的是瓦拉吉尔写的吗,我说是的,二十年了,她写的字,我只要稍微看一下就能认出来,我接着说,如果你想要证据的话,我想这应该就是最好的证据。
朋霍费说,天那!
她患有妄想症,同时也会把自己罪恶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
我夺走那封信说,你真的就那么想吗?
瓦拉吉尔她是无辜的,一个可怜的女人,你要是真的那么想,我们就不可能一起再去探究事情的真相。
朋霍费说,我知道我的行为应该遭到你这样的礼待,可你想瓦拉吉尔,在那次美术馆的行为太让人觉得可疑了。
我们终于停止争辩,我知道我们的争辩是没有意义的,我会因为朋霍费的行为感到愤怒,对于他的歉意,我不想听,可他想弄清楚事实的决心跟我一样强烈,我一个人凭借着这些太难了,无疑朋霍费是最好的助手,我想我们携起手来一定能找到事情的根源。
我问朋霍费,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朋霍费说,应该先找到寄这些照片的人,他在美术馆工作过,但绝对不是瓦拉吉尔的丈夫,或许他现在还在美术馆工作,你要是真的想和我一道,不然我们明天一起回巴黎,去美术馆看看,能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还有那座桥,派人来修修,一定要过去看看。
凌晨两点,两个男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
天一亮,我们便驱车前往城市,早上八点美术馆还没有开门,美术馆的生意越来越好,很多地方被装饰一新,新得我都回想不起它原来的样子,九点开始迎接第一批观览者,我们插在队伍的最前面,检票的那个人居然是瓦拉吉尔的丈夫,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很快将目光收回,在后面的朋霍费对他轻蔑地假装咳嗽几声。
我问朋霍费,你带着记者证吗,朋霍费说带着,他问我记者证做什么,我说,呆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们很快在美术馆的一个专门陈列室找到那副画,我跟朋霍费说我们去找馆长吧,问问这副画是从什么时候被美术馆收藏的,到时候我们就借口说要写篇关于这副画的报道,朋霍费问,要是馆长拒绝怎么办,我说,不会的,这样的事情是给美术馆带来好处的。
很快地,凭借着朋霍费的记者证,来到馆长的办公室,那是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听了我们来这的原由之后,对于我们的采访,他似乎骤然变得谨慎,不时地看我们的脸,他说对于这副画,我是什么都不能说,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画的作者还活着,当时他将画卖给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保守这个秘密,千万不要说,关于作者的一切,以及他的生或者死,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确实不好意思招待,请你们回去吧。
走出美术馆朋霍费疑惑地问我,这老头的话能信吗?
我说看样子说的是真的。
朋霍费又问我,要是老师还活着,我也安心了,可他的的确确遭到杀害,居然“起死回生”,我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真相的追究。
我说,现在我也很乱。
可怜的瓦拉吉尔,这是真的吗?
朋霍费马上蹦出一个念头,要不我们现在回汉弥山庄吧,看看那些木屋。
我说,也只能这样了,又问朋霍费,那些照片如果是他寄的话,这又有什么意味?
另有他人?
按照事情常理,他就应该在美术馆工作过,不然馆长是不会知道他是否健在这样的事实,或者说美术馆里人都知道,包括瓦拉吉尔生前的这位丈夫,难道那个黑衣人就是他?
馆长的拒绝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可令我们不解的地方越来越多。
要是能和他见上一面就好了,我在心里默默说。
趁着黄昏,赶回汉弥山庄,见到那些浓雾在黑天之前,慢慢从四面八方升腾起来,我们再一次来到桥边,见一个人站在桥另一边,他怅若所失地对着深谷下流淌着的一条湍流的小溪念念有词,朋霍费对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看着他问为什么,朋霍费说因为终于见到了,你看那个人就是他。
我抬头望着那中年男子拣起脚边石子一颗一颗地往深谷投去……
真相探究下去太残酷了,而同样的残酷的是你我在时光中经过多年的流逝。